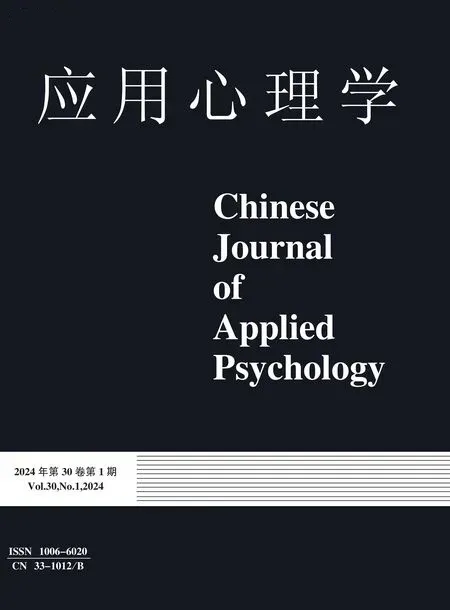社會疼痛情緒調節的認知神經機制:現狀及展望*
莫李澄 李宜偉 張丹丹
(四川師范大學腦與心理科學研究院,成都,610066)
1 引 言
人類是具有社會屬性的物種,社會關系對個體的生存和發展至關重要。我們在失去親人、失戀、被同伴排斥時,常常形容自己“心如刀割”“心痛不已”,這種因社會關系或社會價值受到破壞或威脅產生的負性情緒體驗被稱為社會疼痛(social pain;Eisenberger,2012)。社會疼痛常帶給我們災難性的情緒感受:約四分之三的人將“失去某位親友”列為人生中“第一難受”的事情;大部分人都有過至少一段由失戀引起的撕心裂肺、痛不欲生的經歷;媒體報道的因家庭虐待、校園欺凌而自殘自殺的兒童青少年案例層出不窮。社會疼痛會減弱人們的歸屬感、控制感、有意義的存在感,導致習得性無助和社交回避,進而引發社交焦慮、創傷后應激、抑郁等精神障礙(Durodié &Wainwright,2019;Richman & Leary,2009;Wang et al.,2017)。據統計,社會疼痛是精神障礙的主要誘因,人際危機是精神障礙患者尋求醫療救助時的最常見主訴(Rappaport & Barch,2020;Reinhard et al.,2020;Schilbach,2016)。近年,因新冠大流行造成的醫療和居家隔離、親友離世、失業等負性社會事件,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疼痛對全球心理健康的威脅(Brooks et al.,2020;Holt-Lunstad,2021)。
情緒調節是一種可有效消減社會疼痛的應對策略。情緒調節(emotion regulation)是指我們影響自己情緒的過程,包括我們什么時候產生情緒,以及我們如何體驗和表 達 這 些 情 緒(Gross,2015;McRae &Gross,2020)。由于本文的關注點為社會疼痛,后文中提及的情緒調節主要指對負性情緒的下調,即降低負性情緒強度。幾十年以來,大量研究在揭示情緒調節的認知神經機制方面取得了豐碩的成果(Etkin et al.,2015;Silvers & Guassi Moreira,2019;Zilverstand et al.,2017)。然而絕大部分已有的情緒調節研究采用國際情緒圖片庫(International Affective Picture System,IAPS;Lang et al.,1999)作為誘發情緒的材料,庫內的負性圖片主要涉及高喚醒、低自我相關的非社會事件。社會疼痛作為一種具有社會認知屬性的特殊負性情緒,具有低喚醒、高自我相關的特點。已知的在非社會情境發揮作用的情緒調節腦網絡在社會疼痛情境下還能完全適用嗎?
本文關注圍繞“社會疼痛”展開的情緒調節研究。揭示社會疼痛情緒調節的認知神經機制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價值。理論方面,社會疼痛情緒調節的研究是對已知的、主要基于非社會性事件的情緒調節腦機制的必要拓展,其研究發現可豐富和深化我們對情緒調節腦機制的了解,促進情緒理論的發展。基于IAPS 的研究往往將蛇、槍支、血腥尸體、臟亂環境等多類負性圖片混雜使用,材料的高異質性可能降低情緒調節效果(Morawetz et al.,2017)。與之相比,社會疼痛誘發材料的高同質性有利于在實驗中形成高效的情緒調節策略,此外社會疼痛的高自我相關性可增強情緒調節的動機(Nasso et al.,2020)。社會疼痛的這兩個特點有望增強情緒調節研究的效力(power),使研究發現更接近情緒調節腦機制的真實面貌。實踐方面,研究發現有望幫助臨床制定有針對性的社會疼痛治療方案。已知情緒調節障礙是精神障礙群體的一個跨診斷特征(Sloan et al.,2017),而人際危機又是精神障礙的主要誘因。圍繞社會疼痛情緒調節開展的基礎研究,其實驗方法和結果發現可直接遷移到臨床干預性研究中,為神經調控和神經反饋治療提供潛在的神經靶點(張丹丹等,2019;莫李澄等,2021),加速從實驗室研究到臨床應用的轉化,幫助精神障礙患者以及由新冠疫情等原因導致的大量亞臨床群體(Brooks et al.,2020),緩解社會疼痛、恢復社會功能。
盡管不少研究者已開始關注社會疼痛的情緒調節,但相比于非社會情境中的情緒調節,我們對社會情緒調節的認知神經機制了解得還遠遠不夠。本文分別總結非社會性和社會性情緒調節研究的已有發現,分析目前該領域尚未解決的問題,并給出具體可行的研究思路,幫助研究者在未來工作中深入揭示社會疼痛情緒調節的腦機制。
2 國內外研究現狀綜述
2.1 非社會性情緒調節的認知神經機制
本部分涉及情緒調節領域的主要關注對象,即人們對非社會性事件誘發的情緒進行的調節,例如采用IAPS 材料誘發情緒反應后進行的情緒調節。根據Gross 團隊提出的情緒調節框架(Braunstein et al.,2017),最典型的兩類情緒調節為:自動化內隱和主動外顯調節。自動化內隱調節由刺激喚起,是在無意識的情況下對非適應性的情緒進行的調節。主動外顯調節需要通過意識啟動,同時需要一定程度的自我監控,在實驗室研究中常利用情緒調節指導語來實現(Etkin et al.,2015)。在主動外顯調節中,人們最常采用的情緒調節策略是分心、認知重評和表達抑制。經典的情緒調節過程模型(Gross,1998)認為,分心策略在早期注意分配階段起作用,它要求個體將自己的注意分配至當前情境的中性方面或分配到無關事件上;認知重評在晚期認知改變階段起作用,它要求個體對當前的情緒性情境進行重新解釋;表達抑制在情緒體驗生成后的行為抑制階段起作用,它要求個體壓抑當前情緒的表達(Ochsner &Gross,2005)。其中,認知重評(cognitive reappraisal)能有效且持久減弱負性情緒體驗及情緒相關的神經反應,是值得推廣和應用于臨床訓練的情緒調節策略,也是研究者們關注的重點(McRae&Gross,2020)。
大量研究表明,情緒調節是自動或主動地利用前額葉為代表的皮層控制系統,去抑制杏仁核為代表的皮層下情緒反應系統的過程(Etkin et al.,2015;Frank et al.,2014;Zilverstand et al.,2017)。自動化內隱調節主要依賴內側前額葉皮層(medial prefrontal cortex,mPFC),特別是腹內側前額葉皮層(ventromedial PFC,vmPFC)(Braunstein et al.,2017;Fitzgerald et al.,2020)。vmPFC通過與顳葉皮層、杏仁核和腹側紋狀體的功能連接,自動提取與刺激相關的先驗信息,對刺激進行識別和評估,計算和更新刺激的情感價值,從而讓個體對刺激的情境進行恰當的反應(Delgado et al.,2016;Hiser& Koenigs,2018;Roy et al.,2012)。主動外顯情緒調節需要額外調用外側前額葉皮層,后者包括背外側前額葉(dorsolateral PFC,dlPFC)和腹外側前額葉(ventrolateral PFC,vlPFC)(Etkin et al.,2015;Frank et al.,2014;Morawetz et al.,2017,2020;Rive et al.,2013)。其中,vlPFC 是在不同調節策略間(認知重評、分心、表達抑制等)、兩個調節方向上(上調、下調)被一致性激活的腦區(Morawetz et al.,2017;Ochsner et al.,2012)。
目前針對情緒調節的大部分腦成像研究都圍繞認知重評展開,因此我們對認知重評腦機制的了解也最為深入。認知重評(cognitive reappraisal)是通過改變對當前情緒情境的解釋從而改變情緒體驗的認知過程,此過程需要抑制不適當的負性情緒評價,并從記憶中檢索出適當的替代解釋,同時還涉及目標維持、語義加工等認知過程(Ochsner et al.,2012)。腦成像研究發現,認知重評過程通常激活vlPFC、dlPFC、背內側前額葉(dorsomedial PFC,dmPFC)、后頂葉、輔助運動區等皮層區域(Buhle et al.,2014;Kohn et al.,2014;Morawetz et al.,2017)。其中,dlPFC 和后頂葉構成背側注意系統,負責對注意的主動控制,同時dlPFC 在工作記憶中維持多個對當前情境的解釋選項;vlPFC 負責從工作記憶中選取與調節目標相符的語義解釋對當前情境進行重新評估,隨后抑制dlPFC 的神經活動。在這個過程中,vlPFC 和dlPFC 需要有序發揮各自的功能,以確保認知重評過程的順利推進(Silvers&Guassi Moreira,2019)。至今僅發現一項腦成像研究對這兩個腦區在認知重評中的協作關系進行了考察,研究者采用動態因果模型發現:dlPFC 到vlPFC 具有正向功能連接,而vlPFC 到dlPFC 具有負向功能連接(Morawetz et al.,2016)。目前尚不清楚這兩條功能連接發揮作用是否具有時間上的先后順序。同時,如前文所述,以認知重評為代表的情緒調節過程依賴于前額葉控制系統對情緒反應系統的自上而下的調控。然而關于認知重評過程中這兩個系統間的連接通路一直存在兩種觀點(Ochsner et al.,2012)。直接通路模型認為,外側前額葉可直接影響皮層下區域以實現對負性情緒的下調。例如Wager 等(2008)發現,認知重評過程依賴于vlPFC 分別與杏仁核和腹側紋狀體之間的功能連接。間接通路模型認為,前額葉的其他區域需要通過vmPFC 才能調控皮層下情緒反應腦區(Hiser&Koenigs,2018;Roy et al.,2012)。例如Johnstone 等(2007)發現,vmPFC 在認知重評中介導了vlPFC 與杏仁核的負相關;Steward 等(2021)采用動態因果模型發現,vmPFC 是前額葉調節杏仁核活動的重要樞紐。
2.2 社會疼痛情緒調節的認知神經機制
與非社會性情緒調節不同,社會疼痛調節領域最早關注的腦區是背側前扣帶回(dors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dACC)。Eisenberger 等(2003)首次觀測了社會排斥激活的腦網絡,發現dACC 的激活水平與主觀報告的社會疼痛強度呈正相關,推測dACC 在社會疼痛情境下的作用類似于杏仁核等情緒反應腦區,負責疼痛警覺加工(Lieberman & Eisenberger,2015)。 Eisenberger 等(2003)還發現dACC 介導了右側vlPFC 與主觀社會疼痛強度的負相關,提示vlPFC 通過影響dACC 的活動來調節社會疼痛。與該觀點一致,后續的兩項社會疼痛研究也發現,右側vlPFC/vmPFC 與dACC/腦島分別具有負向功能連接(Maurage et al.,2012;Onoda et al.,2010)。雖然社會疼痛領域的不少經典研究都突出了dACC 的重要作用(又如Woo et al.,2014),近年的兩項元分析卻表明,社會疼痛顯著激活的腦區除了前額葉的vlPFC、dlPFC、vmPFC,還有腹側前扣帶回(ventrol ACC,vACC),而非dACC(Mwilambwe-Tshilobo&Spreng,2021;Vijayakumar et al.,2017)。社會疼痛的核心情緒反應腦區到底是dACC 還是vACC,目前尚無定論。
除了腦成像研究,學者們還利用經顱直流電刺激(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tDCS) 和經顱磁刺激(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TMS) 等神經調控手段,發現無論是情緒的自動或主動調節,vlPFC 和dlPFC 均在社會疼痛調節中發揮著因果作用(Riva et al.,2015;Zhao et al.,2021)。在自動化內隱調節方面,Riva 等(2012,2015)利用tDCS 激活正遭受社會排斥被試的右側vlPFC,發現tDCS 實驗組比對照組報告了更低的社會疼痛強度。類似的,Fitzgibbon 等(2017)利用TMS 證明了dlPFC 在社會疼痛下調中的因果作用。在主動外顯調節方面,我們課題組的系列研究發現,當利用tDCS/TMS 激活右側vlPFC并采用認知重評策略調節情緒時,被試報告的社會疼痛強度明顯降低(He et al.,2018,2020a,2020b;Li et al.,2022);當采用TMS 分別激活兩組被試的vlPFC 和dlPFC,并要求他們采用認知重評和分心策略下調社會疼痛時,vlPFC 激活組采用認知重評策略能獲得最好的情緒調節效果,而dlPFC激活組采用分心策略能獲得最好的調節效果(Zhao et al.,2021),該發現首次揭示了外側前額葉的兩個子區域在兩種調節策略間的雙分離,加深了我們對情緒調節認知神經機制的了解。
綜上,已有的研究表明,社會疼痛情緒調節的神經環路與非社會性情緒調節的神經環路相似,主要是vlPFC、dlPFC 等前額葉腦區對腦島、杏仁核、dACC 或vACC 神經活動的下調(Vijayakumar et al.,2017;Wang et al.,2017)。然而,由于此領域尚缺乏“腦調控+ 腦觀測”的雙向證據鏈,讓我們無法確信:以社會疼痛調節為代表的情緒調節過程是否真的是由前額葉發起的、對皮層下情緒反應系統的抑制。
當然,社會疼痛是一種具有社會認知屬性的負性情緒,對社會疼痛進行調節所涉及的腦網絡與非社會性情緒調節腦網絡相比,不僅具有相似性還具有特殊性。許多研究表明,社會疼痛情境顯著激活了負責心理理論、自傳體記憶、自我參照、社會認知等功能的腦區,主要包括dmPFC(Eisenberger et al.,2011)、顳頂聯合區(Morese et al.,2019)、 后 扣 帶 回 等(Mwilambwe-Tshilobo & Spreng,2021)。至今僅發現了兩項直接對比社會和非社會負性情緒下調的研究。 Vrtˇicka等(2011)早期的研究發現,社會條件比非社會條件更顯著地激活了mPFC、vlPFC、內側眶額葉、顳上溝、后扣帶回等腦區;而非社會比社會條件更顯著地激活了dlPFC、腹外側眶額葉等腦區。這說明前額葉的不同區域在下調由社會和非社會事件引起的負性情緒時出現了功能分離,同時調節社會情緒需要額外調用社會認知腦網絡。我們課題組采用TMS 激活vlPFC,讓被試分別下調社會疼痛和非社會負性情緒,發現vlPFC 對社會疼痛的下調作用更顯著(He et al.,2020a)。但這兩項研究都存在情緒誘發材料的缺陷:前者采用社會互動圖片對比物品/風景圖片(混淆因素:是否有人類圖像),后者采用社會排斥圖片(Zheng et al.,2021)對比單人負性情緒圖片(混淆因素:單人負性情緒的誘因可能是社會事件)。
除了上述區別于非社會性情緒調節的特殊性,社會疼痛的神經表征還經常被研究者們用于與生理疼痛(physical pain)的神經表征進行比較(Eisenberger,2015)。基于數據驅動的腦成像研究表明,加工社會疼痛和生理疼痛的神經環路既有共性也有差異。首先,以dACC 為重要節點的兩種疼痛的神經表征存在差異:dACC 在生理疼痛條件與丘腦、后腦島、內側前額葉等具有更強的功能連接,在社會疼痛條件則與vlPFC、dlPFC、顳頂聯合區等存在更強的功能連接(Woo et al.,2014)。其次,利用次級體感皮層和后腦島的激活特征,可特異性地區分社會疼痛和生理疼痛(Wager et al.,2013),提示生理(而非社會)疼痛顯著激活了軀體感覺加工腦區。然而,這兩項研究側重考察社會疼痛和生理疼痛的神經表征(可能涉及自動化內隱情緒調節),并未探討主動外顯情緒調節在兩種疼痛條件間的差異。我們課題組關注vlPFC 的TMS 研究發現,該腦區對社會疼痛的下調作用強于對生理疼痛的下調(He et al.,2020b),提示vlPFC 對社會疼痛調節具有相對的特異性。另一項關注dlPFC 的安慰劑效應研究發現,dlPFC在調節生理疼痛和社會疼痛時調用了不同的子區域(Koban et al.,2017)。盡管如此,我們對情緒調節腦網絡在社會疼痛和生理疼痛條件間的差異仍缺乏全面認識。
3 存在的問題以及解決方法建議
綜上所述,目前在情緒調節特別是社會疼痛調節領域,還存在許多尚未解決的問題。
第一,情緒調節的神經機制有待進一步澄清。首先,情緒調節過程是否的確是由前額葉發起的、對皮層下情緒反應系統的抑制?對此問題的肯定答復尚缺乏“腦調控+腦觀測”的雙向證據鏈(Kim et al.,2019)。其次,外側前額葉對皮層下情緒反應系統的調控是否必須通過vmPFC 才能完成?雖然目前更多的研究支持“間接通路模型”,即認為vmPFC 是前額葉控制系統和皮層下情緒反應系統的樞紐(Hiser&Koenigs,2018),但已有的證據均來自腦成像研究,尚缺乏有力的因果性證據。因此我們建議,未來研究可利用TMS 激活以vlPFC 或dlPFC 為代表的前額葉控制腦區,觀測由TMS 效應引起的情緒調節神經環路的連鎖反應,借助動態因果模型等有向腦連接分析方法,考察vmPFC 在該環路中的樞紐作用,以及情緒反應系統的神經活動改變(主要考察杏仁核,同時觀測腦島、vACC 等)。
第二,外側前額葉不同區域在認知重評中協同工作的時序尚不清楚。綜合現有的腦成像證據推測,認知重評首先由以dlPFC 為主的注意控制系統啟動,同時dlPFC 在工作記憶中維持多個對當前情境的解釋以供vlPFC 進行選擇;vlPFC 選取與調節目標相符的語義解釋并對當前情境進行重新評估,隨后抑制dlPFC 的神經活動(Silvers&Guassi Moreira,2019)。目前尚無研究考察dlPFC 和vlPFC 協同工作的時間進程。就此問題,我們建議首先使用雙線圈TMS 瞄準dlPFC/vlPFC,在認知重評的不同時間點,利用單脈沖TMS(single pulse TMS,spTMS)分別“一次性地”抑制dlPFC和vlPFC 的功能,并觀察情緒調節效果的變化。在澄清兩個腦區何時卷入認知重評之后,再借助交替式的spTMS 和fMRI 技術(interleaved spTMS/fMRI)考察兩個腦區的協同工作時序以及與他們相連腦區的反應,從時空兩個維度揭示認知重評的認知神經機制。
第三,社會疼痛的核心情緒反應腦區仍存在爭議。社會疼痛情緒調節的靶點腦區是dACC 還是vACC?盡管不少經典研究發現dACC 的激活水平反映了社會疼痛強度(Eisenberger et al.,2003;Woo et al.,2014),但腦成像元分析結果卻更支持vACC 對社會疼痛的編碼(Mwilambwe-Tshilobo & Spreng,2021;Vijayakumar et al.,2017)。目前推測,dACC 和vACC 同時參與社會疼痛加工(Rotge et al.,2015),其中 dACC 負 責 沖 突 監 控(Eisenberger,2015),對“預期違反”敏感;而vACC 負責對情緒的效價或強度進行編碼(Somerville et al.,2006),對社會疼痛敏感。為闡明dACC 和vACC 在社會疼痛加工中的作用,我們建議未來研究設置不同水平的預期違反和社會疼痛,利用基于實時fMRI 的神經反饋技術,要求被試分別調控vlPFC-dACC(Woo et al.,2014)和vlPFC-vACC(Morawetz et al.,2017)兩條通路的功能連接強度,觀測被試報告的“驚訝程度”和“社會疼痛強度”的改變,從而分離dACC 和vACC 在社會疼痛加工中的功能,明確社會疼痛的核心情緒反應腦區。
第四,社會疼痛情緒調節的特異性腦網絡尚不明確。首先,社會疼痛調節特異于非社會情緒調節的腦網絡是什么?已有的兩項研究發現,社會比非社會情緒調節條件更顯著地激活vlPFC、mPFC、顳上溝等腦區(V rtˇicka et al.,2011),進一步的因果證據表明vlPFC 對社會疼痛的下調作用強于對非社會負性情緒的下調(He et al.,2020a)。然而這兩項研究的情緒誘發材料存在混淆因素。我們建議后續研究采用嚴格控制的社會和非社會負性情緒誘發材料,通過腦成像技術明確兩種負性情緒調控的腦網絡的異同。例如,可采用社會疼痛和非社會負性圖片誘發情緒,控制兩套圖片之間的負性情緒強度、圖片中的人數等。社會疼痛圖片可包含親人離世、校園欺凌、失戀/情侶冷戰等場景,非社會負性圖片可包含個人業績不佳、個人物品損壞、個人失誤等場景。其次,社會疼痛調節特異于生理疼痛調節的腦網絡是什么?目前尚缺乏采用主動外顯調節任務直接對比兩種疼痛調節的腦成像研究,我們建議未來研究在此方向進行嘗試。例如,在嚴格控制疼痛誘發強度的基礎上,采用“回憶前任”范式誘發社會疼痛(Woo et al.,2014),采用電刺激儀的直流電模式誘發生理疼痛,進而利用fMRI 揭示社會疼痛調節與生理疼痛調節腦網絡的異同。揭示社會疼痛與非社會負性情緒/生理疼痛的情緒調節的重疊腦區和特異性腦區,有助于發現三者間的潛在交互影響因素,提高臨床對不同負性情緒和疼痛誘因的甄別效率和治療效果。
4 總 結
本文以“社會疼痛”這一特殊的負性情緒為切入點,綜述了情緒調節的認知神經機制。考察社會疼痛情緒調節的腦機制,一方面可深化我們對情緒調節理論的了解;另一方面有利于臨床制定有效的社會疼痛治療方案,幫助精神病患者恢復社會功能。通過梳理文獻,我們發現目前該領域主要有四個問題需要解答,針對這些問題,我們對未來研究提出了建設性意見。希望本文的觀點能幫助情緒領域的研究者,在社會疼痛情緒調節方向進一步深耕,早日全面揭示社會疼痛情緒調節的認知神經機制,并通過轉化研究造福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