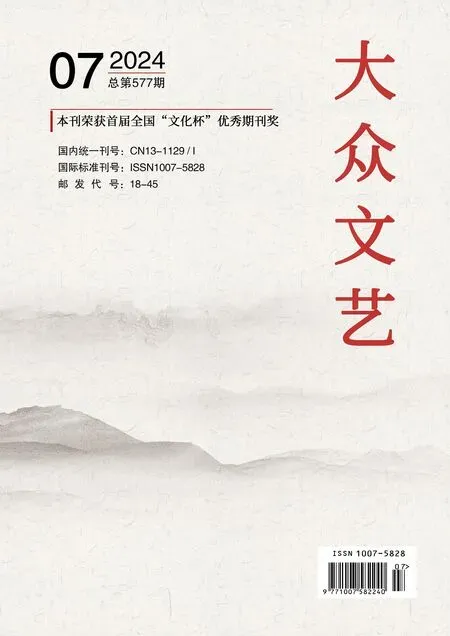文學(xué)文本中民族概念在英語中的變遷歷史研究
樓宗元 呂佶康
(湖州學(xué)院人文學(xué)院,浙江湖州 313000)
2022年6月28日,英國政府蘇格蘭首席大臣妮古拉斯特金正式宣布英國蘇格蘭地區(qū)的第二次獨(dú)立公投的計(jì)劃,稱將于2023年10月19日進(jìn)行獨(dú)立公投。在此之前,蘇格蘭曾早2016年便進(jìn)行了過另一次的公投脫英公投,但本次公投最后并都沒有獲通過,因此使蘇格蘭也不得不被繼續(xù)地留在了英國的體制內(nèi)。作為同一個(gè)國家中的不同民族,為何意見會這樣相左?這就不得不考慮到這幾個(gè)問題即:“民族”究竟指的是什么?它應(yīng)該如何確切的被表述,又是怎樣在歷史中一步一步變遷而來的?本文旨在嘗試回答“民族”在英語中究竟該如何界定以及其變遷的過程。
一、理論框架
語料庫作為經(jīng)驗(yàn)數(shù)據(jù)的源點(diǎn)被用于調(diào)查許多以語言為中心的研究命題,涉及語言應(yīng)用的諸多方面,是語言學(xué)者“默認(rèn)的資源”。語料庫技術(shù)能提供大量反映語言現(xiàn)象的例證,語料庫分析則能展示出預(yù)期不到的語言型式[1]。
Hardt-Mautner(1995)是首位倡導(dǎo)并使用了語料庫的研究方法來研究批判話語分析的學(xué)者,語料庫索引功能有效地結(jié)合了定量和定性的研究理念,能提供給我們強(qiáng)大的量化分析的基礎(chǔ)。以語料庫為基礎(chǔ)的研究主要通過對詞頻的考察,主題詞索引、搭配、詞叢、語法結(jié)構(gòu)和型式的觀察來識別話語的內(nèi)在意義,從而進(jìn)一步探尋語言與文化、社會的關(guān)系[2]。
結(jié)合對主題詞索引、搭配以及詞叢的統(tǒng)計(jì),可以有效地展現(xiàn)民族概念在英語中變化的時(shí)間線。基于歷史的角度,對“nation”和“ethnic group”以及類似意義的詞的定性定量研究可以幫助我們進(jìn)一步了解民族概念的變化。
此外筆者還運(yùn)用了觀察法進(jìn)行論述。在明確觀察對象(nation等表示民族意義的單詞)后,搜集了大量資料并進(jìn)行語言學(xué)上的追蹤,仔細(xì)考察了英語中民族概念發(fā)展的路徑。
二、追溯不同語境下民族概念的表述
本節(jié)中,筆者將著重運(yùn)用橫向比較法和調(diào)查法,來仔細(xì)探討不同單詞指代民族含義時(shí)的差別,并揭示出民族概念在英語中范圍逐漸擴(kuò)大的過程。
在英語主要有5個(gè)詞可以用于表示民族,即為:ethnic groups,race,clan,gentes以及nation筆者將按照由近至遠(yuǎn)的順序來論述。
在當(dāng)今英語用于表示“國家,民族,國民”意思且應(yīng)用最為廣泛的無疑是“nation”一詞,牛津詞典中給出的解釋為生活在同一片地區(qū)中,處在同一個(gè)政府管轄下的一群擁有相同文化、語言、歷史的人,它更偏向于一種宏觀描述,指的是國民全體或民族全體。它的詞根可以追溯到拉丁文中的nativus,意為“出生,降生”,詞源同還有g(shù)ene和populus,這三者都有著細(xì)微的分別。Gens的實(shí)詞形式為genitor,可譯為“父親”“父系”,指代的是狹義上的血緣親族,可譯為“氏族”。雖然gens的氏族含義早已經(jīng)淡出了人們的視野,但仍然作為民族的源頭有著重要影響;而populus的含義可譯為“人民”“楊樹”。S.P.Q.R.(即元老院與羅馬人民)作為一個(gè)廣為人知的拉丁語縮寫,其拉丁全稱便多為Senātus Populusque Rōmānus,而在《高盧戰(zhàn)記》中,凱撒也被多以“populi Romani”來稱呼羅馬,可見populus更偏向于一個(gè)政治概念,即政治意義上的羅馬人民。
由此推可得,由其意義上更加廣泛更普遍使用的由拉丁詞源nativus演化發(fā)展而來的現(xiàn)代英語單詞nation也都應(yīng)當(dāng)?shù)乩^承了其拉丁詞源nativus上的普適性,即用來指代一個(gè)廣義上的不列顛帝國人民,包括那些同處于詞源英格蘭島意義上的蘇格蘭高地人,威爾士高地人以及鄰近英國的愛爾蘭人。在近代以來,nation同樣可以指代國家的概念,可以說,nation的廣泛運(yùn)用從側(cè)面反映出了民族國家的正式形成。
Race同樣可以表示人種;種族;種群。根據(jù)童理民老師的考證,race該詞來自中古法語razza,種族,世系,家族,也有可能來自拉丁語radix,根,詞源同root,radish.該詞大概率是英語發(fā)展到第二個(gè)階段即中世紀(jì)英語時(shí)吸收融合法語而形成的,但隨著19世紀(jì)中葉種族主義進(jìn)入到英文語境中,race,racial二詞因常與racism(即種族主義)一詞相聯(lián)系而多少受到感染并變得逐漸貶義時(shí),用ethnic來替代該詞的情況便開始有所增加。
而ethnic groups的含義則較為簡單明了了。ethnic源自希臘語ethnos‘race’(種族),從ethnos的形容詞形式ethnikos演變而來。希臘作為西方文明的發(fā)祥地,ethnic也自然而然地帶上了學(xué)術(shù)性的光環(huán),多作為學(xué)術(shù)術(shù)語用于人類學(xué)與社會學(xué)之中,但也正在逐漸走向平民化。
Clan的字面含義雖然與英文gens相似,卻總在一個(gè)細(xì)微處又有著那些許多的含義不同,Clan可用來指代(尤指蘇格蘭的)宗族,氏族,家族,也可指代龐大的家族;宗派;幫派;小集團(tuán),并且更加用于蘇格蘭語境中。在中世紀(jì)時(shí),由于蘇格蘭物資的缺乏以及英格蘭對于蘇格蘭的封鎖,導(dǎo)致蘇格蘭的封建主義發(fā)展遠(yuǎn)遠(yuǎn)落后于英格蘭,其中蘇格蘭人更多地以氏族為單位進(jìn)行群居,由此形成了數(shù)個(gè)零散的利益集團(tuán)和家族。在筆者看來,相對于羅馬氏族所代表的政治概念,clan所指代的含義更類似于古代中國的門閥士族,一個(gè)具有相同利益和共同祖先所形成的一個(gè)利益集團(tuán)。
而由拉丁詞源gene演化而來的gens的含義則較為狹隘了。《韋氏大學(xué)英語詞典》中給出的三個(gè)含義中一個(gè)僅僅指代羅馬或希臘中的氏族,一個(gè)僅指代父系家族,一個(gè)則指代一族可以區(qū)分的相關(guān)親族。其含義僅僅局限于有著血緣關(guān)系相傳承的親族。時(shí)至今日,gens早已經(jīng)在表示當(dāng)下的民族概念中淡出,僅僅作為一個(gè)人類學(xué)概念保留在英語中。但是在中世紀(jì),gens同樣有著特殊的宗教含義:在舊約《詩篇》中曾用gentes(gens的復(fù)數(shù)形式)一詞來蔑稱毀滅耶路撒冷的異端民族,而在隨后被教皇烏爾班二世也被用于稱呼中東的穆斯林。就這樣,gens一詞便被賦予了宗教上的污名化。
由此可得,民族概念在英語語境中變遷的大致路徑應(yīng)為:gens→clan→race→ethnic groups→nation。但若要深入了解英國民族概念的變遷,就不得不了解英國民族概念的形成。
在《盎格魯-撒克遜編年史》中,出現(xiàn)頻率最高的為“nation”,但其他詞匯也有出現(xiàn),呈現(xiàn)出一種復(fù)雜多樣的局面,而由于中世紀(jì)早期近代民族意識尚未萌發(fā),nation更多地單獨(dú)指代國家即阿爾弗雷德大帝所創(chuàng)建的威塞克斯王國,并不指代近代意義上的英國與英國民族。
而當(dāng)時(shí)間來到文藝復(fù)興時(shí)期時(shí),隨著人文主義的興起,歐洲大陸上近代民族意識普遍萌發(fā),表示氏族等概念的詞匯“race”“clan”等逐漸減少,“nation”已經(jīng)逐漸在民族概念語境中爭奪到了統(tǒng)治地位。《Leonardo Da Vinci》是美國作家沃爾特·艾薩克森為文藝復(fù)興三杰之一的達(dá)·芬奇所撰寫的傳記,而達(dá)·芬奇所處時(shí)代的意大利半島政權(quán)更迭頻繁,局勢風(fēng)起云涌,光佛羅倫薩就歷經(jīng)法國,美第奇家族,奧地利等政權(quán)的統(tǒng)治,因此該時(shí)期民族被頻繁提及,氏族亦有所提及。
而莎士比亞所著的《李爾王》,更多地著墨于李爾王與三個(gè)女兒之間的糾紛以及悲劇情節(jié),對于民族和國家的直接描述較少,因此各個(gè)詞匯的出現(xiàn)頻率均幾乎于無,因此筆者不再贅述。
當(dāng)時(shí)間來到近代20世紀(jì)之后,由于蘇聯(lián)的高壓統(tǒng)治,大批基層民眾和持不同政見的知識分子被蘇聯(lián)秘密警察抓捕關(guān)押至古拉格所管轄的集中營內(nèi),這些囚犯來自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lián)盟的各個(gè)加盟國,民族不同,政見不同,再加上蘇聯(lián)政府的嚴(yán)刑拷打,民族沖突在此地迅速激化,因此各個(gè)側(cè)重不同但同樣指代民族概念的詞匯(nation,ethnic group,race,clan)再次被廣泛使用。
由此可見,英語中表示民族概念的詞匯歷經(jīng)了數(shù)次更迭與反復(fù),最終還是更具普適性的nation在語言權(quán)的爭奪中占到了上風(fēng),最終確立了nation對于民族概念的表達(dá)。
三、英國民族概念的曲折形成路徑
本節(jié)中,筆者將運(yùn)用觀察法,來闡述了英國民族從民族觀念稀薄,國家分裂走向英國民族意識正式形成,國家走向統(tǒng)一并建立起第一個(gè)資本主義國家的過程,并探究了指代民族含義的單詞在此過程中的變遷。
1.中世紀(jì)時(shí)期英國民族概念的發(fā)展
可是歷史進(jìn)程是無法預(yù)料的。1066年,征服者威廉于黑斯廷斯戰(zhàn)役中擊敗英王哈羅德(Harold),加冕為英國國王之后,英國民族國家的構(gòu)建進(jìn)程便被強(qiáng)行打斷了。征服者威廉不僅帶來了政治上的地震,更帶來了語言的沖擊和文化上的入侵。由于諾曼征服時(shí)期英格蘭語言尚未統(tǒng)一,疆界并未確定,民族意識十分淡薄,并沒有能夠在文化和語言上組織起對于法國文化沖擊的抵抗,因此英格蘭原有的本土文化迅速淪陷,其表現(xiàn)在法語成為社會主流語言并通行于上層貴族之中(包括英格蘭的本土貴族),而英語則淪為中下層民眾的語言,其中還夾雜著許多法語詞匯,前文中提到的“Race”便有很大可能是在該時(shí)期形成的,指代的是處在當(dāng)時(shí)英國上層社會的法國貴族與英格蘭本土貴族。
但語言上的變化尚在其次,更主要的是政治上的沖擊。征服者威廉帶來了先進(jìn)的封建制度,如引進(jìn)了歐洲的騎士制度,從此英國的騎士階層開始發(fā)展起來,英國的封建制度也在該時(shí)期逐漸建立起來,但英國的原生文化和民族都受到了極大的沖擊。雖然征服者威廉打斷了英國原有的民族構(gòu)建,但他也為英國帶來了先進(jìn)的封建制度和一個(gè)更加強(qiáng)力的中央集權(quán)政府,為日后英國民族國家的形成奠定了堅(jiān)實(shí)基礎(chǔ)。
2.英國民族國家的正式形成
資本主義的發(fā)展促進(jìn)了文藝復(fù)興與啟蒙運(yùn)動(dòng)的發(fā)展。文藝復(fù)興三杰之一的莎士比亞(Shakespeare)曾在其著作《約翰王》中以劇中角色約翰王的口吻對教皇的使臣潘杜爾夫進(jìn)行了辛辣的諷刺并且宣稱自己才是世俗世界中至高無上的君主,無疑反映出了當(dāng)時(shí)英國民族意識的勃發(fā)以及對于腐朽神權(quán)的唾棄。同時(shí)莎翁還在戲劇中抨擊了法國的民族英雄圣女貞德:在其著作《亨利六世》中,當(dāng)圣女貞德率軍解救奧爾良時(shí),王子查理對她大加稱贊,稱其為“法蘭西的守護(hù)神”,而當(dāng)奧爾良遭到偷襲兵臨城下時(shí),王子查理立刻轉(zhuǎn)變臉色,對貞德破口大罵,蔑稱她為一個(gè)“女騙子”;當(dāng)貞德被英軍俘虜后,對著四處尋找自己的父親唾棄到:“老朽的守財(cái)奴”“下賤的可憐蟲”。這種與現(xiàn)實(shí)相差極大的反轉(zhuǎn),不僅消解了圣女貞德作為法蘭西民族英雄的高尚形象,更借此機(jī)會解構(gòu)了法國的民族性。
幸運(yùn)的是,英國由于百年戰(zhàn)爭之后與法國的聯(lián)系逐漸減少,使英國躲開了歐洲歷史上第一次大規(guī)模國家混戰(zhàn)——三十年戰(zhàn)爭(又稱宗教戰(zhàn)爭,其重要誘因?yàn)樾陆膛c天主教的尖銳矛盾)。這場混戰(zhàn)發(fā)生于17世紀(jì),正值英國資產(chǎn)階級革命的白熱化階段。這場大混戰(zhàn)幾乎將所有歐陸國家都卷入其中并造成重創(chuàng),天主教勢力由于深陷這場戰(zhàn)爭中不能自拔而無暇理會更遙遠(yuǎn)的英國,英國也借此機(jī)會進(jìn)行貿(mào)易賺取高額的利潤,大大加速了英國資本主義的發(fā)展。
最終,在眾多因素的影響下,英國于1688年完成了光榮革命,推翻了已經(jīng)落后的封建主義,威廉三世入主英國,建立起了世界上第一個(gè)資本主義民族國家,揭開了世界史的嶄新一頁。
而在這個(gè)近代民族國家的形成過程中,民族的概念也不再僅僅指代民族,更指代與民族息息相關(guān)的民族產(chǎn)物——國家,即Nation,不僅包含著民族意識上的含義,更包含著政治上的含義。
四、結(jié)語
鄧小平書記曾經(jīng)特意寫道:“教育要面向現(xiàn)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英語作為當(dāng)今世界上最為通用的語言之一,承載著大筆珍貴的精神財(cái)富,而英國作為歷史悠久的古老國家,同樣有著可貴之處。英語中的民族概念數(shù)次變遷,反映出了一個(gè)民族的蹣跚發(fā)展歷程,對于中國這樣一個(gè)歷史悠久且民族眾多的國家來說無疑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
為此,我們要加強(qiáng)探究,積極實(shí)踐,為我國和世界的民族和平繁榮發(fā)展做出重要貢獻(xi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