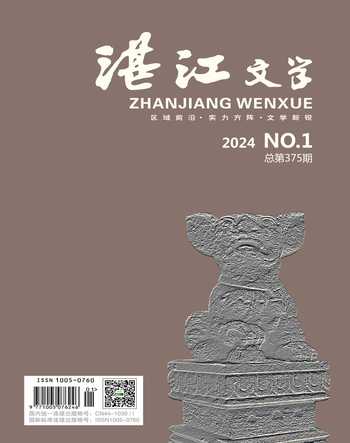狗尾草,隨風搖
邵婷
春風洋洋灑灑,肆意慵懶地輕吻大地的時候,山間田野里便布滿了綠色甚至于那生冷硬橫的水泥路閉塞狹窄的縫隙間,也叢生出星星點點的綠來。那是初生嫩芽的鮮綠,是原始木林的深綠,是貴如瑪瑙的翡翠綠,是搖曳在我童年時光里的狗尾草的綠。
狗尾草,學名狗尾巴草。顧名思義,它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形狀與小狗的尾巴相似,一桿桿,一叢叢,一片片,毛茸茸軟乎乎的。風過處,炸開的穗子高高地翹起,悠悠搖曳,翩翩起舞,讓人禁不住產生想要撫弄的沖動。它翠綠狹長的葉子向上生長、向四周散開,好似少女那被俏皮的微風撩撥而起的裙擺,托起輕盈纖細的身子,隨風扭動著腰肢。狗尾巴草的身影,與春風掀起的婀娜多姿的柳枝一齊,蓬勃在我家鄉的土地上。
因著特定的地理環境,土壤靈性與植物的生長習性,我家鄉的食糧主要以春小麥為主。依稀記得我七歲那年的春天,與母親一同在田野里播種小麥。遠山浩浩湯湯,綿延的山勢起伏不定,這一塊高高的,聳入云天,那一段又謙卑地伏下身子,放低了姿態。山與山相連,起承轉合,農民們難以尋到一塊平整的原野,以開墾播種,只能在陡峭的山間行走勞作,步履不息。于是,高原之上,一塊塊一洼洼平展整潔的梯田應時而生,如懸掛的天梯,層層疊疊。母親和我就是在這樣的田里勞作的。說是“母親和我”,其實干活的是母親,我只是搖晃著腳丫坐在地頭,欣賞著暖陽晴空下飄浮在對面山頭的流云,放空,遐想。身后是家中那頭衰老的黃牛緩慢而沉重的呼吸聲,母親“不近牛情”,揚手揮下的長鞭落在黃牛身上的響聲以及崇山峻嶺間此伏彼起的吆喝聲。
碧空下,永遠孤獨的山風行云般游走,吹起貼在我稚嫩臉龐上的碎發,空靈中夾帶一些難以琢磨的聲息。屏氣,凝神,仔細品味,我似乎聽到了千萬滴汗水跌落進泥土的聲音。書上說,揮灑汗水,收獲希望。年幼的我告訴自己,那是千萬顆希望迸發時生出的動靜。
溫煦的和風悠蕩,云彩飄移,圓蓬蓬的一大片忽地泛起漣漪。彼時,風的形狀是那鴛鴦戲水的湖中盛景,從山的背面飄來……美景不容辜負,我睜大眼睛,紋絲不動。對面地里的農人又一次揚起了手中的長鞭,落下,啪。古老的群山顫栗著發出寬亮低沉的回音,啪……我懼怕看見那雙眼角帶淚、無奈地浸著苦水的黑色眼睛,極快地收回了漫散的目光。遠方的風光是不清晰的,模糊的,看著看著就蒙眬了雙眼,腳底的風景才是新鮮的,真實的。地頭,高高隆起的田埂上,龜裂的土地裂縫里生長出一片綠茵茵的狗尾巴草。新生出來的葉子,細,綠,嬌,嫩。修長的莖稈拔節生長,孕育而出的花穗,綻著極細、極小的絨毛,像是剛剛滿月的嬰兒滑嫩臉龐上細軟的茸毛,令人不忍觸碰。
芳草萋萋,漸迷人眼。我終究是沒按捺住掌中難耐的癢意,伸手,向上提,狗尾巴草的草穗與圍繞著上支的葉叢分離,彎著頭顱,站在一張它無法抗拒的手中,沉默著,臣服于自身生命之外的力量。
掌中的狗尾巴草輕靈,地上的狗尾巴草美麗,它們都隨風擺動。花穗靈動著跳入我的眼眸,夢幻,輕盈,我不忍眨眼,生怕錯過它被微風撩撥而起的春光。慢慢地,它在我的眼中變了模樣。煙雨朦朧,霧氣繚繞,它成了書紙扉頁上溫婉秀麗的如畫江南,我仿若置身其中,在河邊岸畔古老的青石板路上漫步,轉入小巷,不經意抬眸,便會遇見一個丁香一樣地,結著愁怨的姑娘。
思緒紛飛,母親已經播種完畢,收拾好器具準備回家。我方才回過神來。狗尾巴草細密的絨毛間鑲著雨滴,晶瑩圓潤,玲瓏剔透。原來是落雨了。毛毛細雨,連成絲密密地織了起來,濡濕草尖。我拿著那株狗尾草,快速地跑到母親的身前。走出地頭,踏上鄉野的荒徑。小徑幽長,蜿蜒,崎嶇,宛如披著青綠外衣的長蛇,逶迤著爬向不知名的遠方。
剛剛能沒過腳踝的青草,搖晃著,掃落棲身在我褲腳的灰塵。那是一條有坡度的,略微有些傾斜的小路。我玩心大發,張開雙臂,順著小徑從坡頂飛奔而下。路兩旁植著的稀疏的樹木,直逼我而來;撲上臉頰,擁我入懷的風中帶著一種呼嘯的聲音,我的心里有一種要呼嘯的欲望。然而我最終沒有呼嘯,只是放肆地、豪邁地大笑。笑聲清澈,穿透塵石堆積而起的大山,悠揚回蕩。小時候的我喜歡那樣一種令人屏息炫目的速度與豪情。
大約每個生命在最初的數載光陰里,都曾這樣狂妄猖獗,肆意地奔跑過,大笑過。
“樂極生悲”這個成語,真是上帝信口說出的咒語,靈驗,禁不起世人一絲一毫的挑釁。斜坡的盡頭,我結結實實地摔倒在地,殷勤地擁抱住春雨潤澤過的土地。四腳朝天,衣物沾泥,膝蓋破皮,嘴銜青草與濕土,手中的那桿狗尾巴草也不見了蹤影,慘不忍睹!
沙石刺入皮膚,身體經受的劇烈的疼痛支使著我大腦的神經,就這樣,一動不動。抬眼,身前是一片從悶熱的泥土里滋長出來的荊棘叢林,彎曲著向上,生長攀爬,綴滿尖刺,堵住我的去路,張牙舞瓜,隨時準備著啜飲我血管里流動著的液體。后方響起母親匆忙奔下的腳步聲,人還未到,飽含著怒氣的責怪聲急走而來,其威之大,生生將橫亙在我眼前的荊棘叢林震得稀碎。小路露出它本來的面貌,峰回路轉,一片清明。我趕忙從地上爬起,麻溜地拍去衣服上的泥土,抹凈臉上的穢物,站在山腳,靜靜地等待著母親,或者是,靜靜地等待著母親的數落。
許是我的慘狀逗笑了母親,料想中的責怪并沒有襲來。母親走到我的身前,抬手,撫上額頭,從我梳起的馬尾間掂出一桿狗尾巴草。嫩綠的花穗,沾染了些深褐色的污泥。原來在我踉蹌摔倒的時候,它聰明地藏進了我濃密的頭發里,只不過還是沒能躲過與泥土擦身而過的命運。
我看母親的思緒被這株狗尾巴草占據,旺盛的好奇心又開始蠢蠢欲動,向母親詢問起了狗尾巴草的歷史。
回家的途中,母親侃侃而談。據傳,狗尾巴草是仙女下凡時,從天上帶下來的愛犬化作的。仙女在人間和一位書生相戀,但遭到王母娘娘的阻撓,仙女和書生為了在一起,不惜反抗王母娘娘。在對抗的最后的時刻,仙女的愛犬為了救助人而不惜舍棄自己的性命。最終仙女和書生化作了陰陽兩塊玉佩,在人世間流傳。相傳相戀的兩個人,如果分別獲得這兩塊玉佩,便能有情人終成眷屬。仙女的愛犬死后則化作了人間隨處可見的狗尾巴草,世世代代,傳承著對愛情的見證。
天空中,密布的烏云散了開來。春日溫暖的陽光,似母親慈愛的目光般鋪散開,斑駁,折疊,云端閃現一彎長虹。長虹映射下,雨后空氣中飄浮的塵埃,是夢幻的彩色。我不禁嘆氣,順手摘了一株路邊的狗尾巴草。一個悲傷的愛情故事。細細想來,自人類文明伊始,關于愛情的浪漫故事,大都有著梁祝化蝶的京婉凄清。有幸相遇,千帆過盡,終是難以再續前緣。機緣巧合,因果輪回,無盡思念,我們耿耿于懷,久念在心的,竟全是哀囀久絕的曠古悲情,破鏡難圓的悔恨之淚,是遺憾,不甘,執念。人們試圖從生理,心理,甚至是神學等諸多角度探索愛情所蘊藏的奇妙奧義,成果似乎還不錯,不是一無所獲,卻也并非大獲全勝。于是,一棵草,一滴云,一片羽毛,都可以與愛情產生千絲萬縷的聯系。
那天,我問母親,你和爸爸之間,有愛情嗎?母親沉默良久,埋著頭將狗尾巴草編成小狗的模樣,插入我的發梢,說:“我和你父親,過的是生活,不是婚姻。”
七歲的我,懵懵懂懂間也覺察出母親語氣里的失落,識趣的不再追問,被編織成小狗模樣的狗尾巴草,也不再隨風搖晃身子了。
山腳下的小路是平緩陡直的,盡頭是一條淌著涓涓細流的小河,幾塊巖石穩穩地立在河中央,高高地凸起,裸露出溜平的表面,充當水上橋的角色,截住了流水的去路。我酷愛聯想,行走在橋上,常常會產生這是一座狹窄細長的巖石小道,左右兩邊皆是萬丈之深的懸崖的錯覺。我深知這是錯覺,然而那種孤立無援的感受,出乎意料地真實。
我就是在這兒,在這條小河邊,遇見我的第二只小狗的。第一只小狗,是母親為我用狗尾巴草編織的。
它虛弱地跪臥在河邊的一棵柳樹下,伸著粉紅色的舌頭,貪婪,吃力地舔舐干凈的河水。灰撲撲的狗毛,渾身上下沾滿泥土,使人疑心它應是才從泥潭里爬出來。從它的身形外貌,不難推測它是被山里人家遺棄的小狗寶寶。那年月,農民們圈養的雞、鴨等牲畜總是莫名的不見了蹤影,拔葵啖棗之人更是暢行無阻,人們對此深惡痛絕,于是各家各戶的門口多了犬類的蹤跡。
月華初上,公雞打鳴時,犬吠最為熱烈,表明忠心似的,號叫著趕走那些躡手躡腳,摸著黑,茍到人家門前的心存僥幸之人。漸漸地,梁上君子少了。人類慣行千年的法則,用則養,無用則棄。初生的小狗被視為累贅,丟到荒山野嶺,成了在荒群中的孤狼的美味珍饈。人們毫不在意,夸夸其談,自豪地說,人類的道德良心戰勝了一切。
它大抵是累了,趴在那兒一動不動,我懇求母親允許我將它帶回家。若是讓它繼續留在這兒,毫無疑問,不久它就會成為一堆招惹蟲蠅的腐肉,臭氣熏天,遭人嫌惡,變成那棵柳樹的養分。母親也不忍一個可愛的生命就此湮滅,答應了我的請求。我很開心,手舞足蹈,一路小跑著,奔到它的身邊,拔了些生在河畔的野草,小心翼翼地揩去了它身上的灰塵,抱著它回了家。
回家的路途并不長,像是黃土里冒出的青草的一生,在一場又一場春雨里,伸展著柔軟的骨骼,噼里啪啦地生長,倏然而逝,一下子就到了頭。生活不經意泄露的春光流入眼眸,幻化成一棵參天的大樹,枝丫繁茂,彼此糾纏,在無數飛揚的塵土與時光的洗禮中,變成了那印證光陰流逝的年輪,一圈,兩圈……無數圈,被安放,被擱置,但不曾被遺忘。記憶是寬容的,長大了的人,總愛追憶往昔。狗尾巴草婆娑過的童年時光,是入了詩的。
它是條可愛的斑點狗。酷似巧克力的棕色斑點零星地散布周身,是落在素白雪地里的誘人的奶酪。在我的家鄉,它和大地上俯拾皆是的狗尾巴草一樣普通。小狗熟睡時,我愛用狗尾巴草那招人喜愛的花穗,輕輕摩挲它的鼻尖,逗的它哈欠連天。一日,我突發奇想,激動地向家人宣布,我們為它取個名字吧,就叫“狗尾巴”,怎么樣?父母對這事一向不重視,只有一年級的弟弟捧腹大笑,挖苦我給小狗取了一個這樣土的名字。我不服,沖他科普。“狗尾巴”這個名字,取自狗尾巴草。狗尾巴草具有清熱利濕,祛風明目的作用,是個寶貝,可金貴呢!弟弟半信半疑,我使出撒手锏:書上就是這樣說的。弟弟信了,欣然接受了這個土得掉渣的奇葩名字。然而他不接受也無妨,又不是給他起的。
村里的小學,離我家很近,穿過水泥路,再下個坡就到了。清晨,曙光初現,青草尖上的露珠還在酣睡,做著甜美的夢,幸福地裂開了嘴巴,破碎。狗尾巴晃著腦袋,在潮濕的路面嗅來嗅去,跟著我到了學校門口。我訓它:快回去,你不能進學校。它果真聽懂了我的意思,吐著舌頭,端坐在校門前,不動彈了。天氣悶熱,講臺上,老師妙語連珠,開合的雙唇像是玻璃水缸內不斷地吐露著泡泡的魚的嘴巴,一張一合,讓人腦袋發昏。許久,喻示著下課的電鈴聲響起,同學們蜂擁著跑出教室,與稱霸整個操場的野草一同撒歡。
我注意到狗尾巴仍然坐在校門前,閉目,等待著它的主人。操場上的其他同學也注意到了狗尾巴的存在,瘦弱的胳膊伸出,握住狗尾巴的前爪,一托,一拉,狗尾巴輕易地穿過了有著巨大縫隙的鐵門,即將售出的拍賣品般,局促地暴露在這許多視線中。狗尾巴的毛很光滑,在陽光的照射下,白得發亮,摸起來也很舒服。毛茸茸的腦袋,圓溜溜的大眼睛,蠢萌蠢萌的。眨巴兩下眼睛,便俘獲了小孩子們的芳心。他們把它抱上膝蓋,互相爭著搶著,給它投喂從家中帶來的美味,泡饃,大腸,五花八門,應有盡有,有的甚至還拿出了珍藏已久的干脆面。偌大的操場上,他們領著它,瘋狂地奔跑,摸爬滾打,清早還算干凈的衣物頃刻間沾滿塵土和雜草,以及青草爆出的鮮綠的汁液。
當他們得知狗尾巴是我家的小狗時,驚異地哇出聲,紛紛向我投來艷羨的目光。七八歲小孩子的思維大概就是:只有有趣的人,才配擁有這樣有趣的小狗,仿若五角星永遠填不滿的長方形容器,直觀,不懂嬗變。
套用世俗的觀點,我確實不是一個有趣的人,沉悶壓抑,不愛說笑,繃緊的臉皮像一面被卸下的發黃的鼓皮,巨石拋在上面也難聞其聲。校園里那只可愛的小狗是我的。這個消息徹底散播開時,小孩子們間衍生了些微妙的難以言喻的變化。他們綻著比花兒還要璀璨數倍的笑容,將藏在背包中的零食遞到我的手上,心安理得地揉搓狗尾巴脖頸處綿軟的柔毛。
狗尾巴們到來讓我成了焦點,一種陌生的、被關注的快感刺激著我的神經,虛榮心潮水般圍住了我,我洋洋自得,嘴角彎上耳根,天真地以為自己能在不斷漲起的潮水中重獲新生。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或許生而為人,最忌諱的就是大喜、大悲。那日,上帝脫口而出的咒語又一次靈驗。班里最調皮的小孩子,拿著從小商鋪買來的一塊錢的小刀,揪著小狗的尾巴,切,劃,割。嘴里還念念有詞,它的毛這么順溜,切了做毛筆,一定很不錯。幾只胖手牢牢地嵌住狗尾巴的身子,狗尾巴無力反抗,無望地嗚咽著,像北風卷起的枯葉瑟縮著吼出的悲鳴。我憤怒地奪過小刀,推開他,將狗尾巴護在身后,死命地瞪著他。鋒利的刀尖戳破掌心,鮮紅的血液,順著指尖滴落,啪嗒,啪嗒……荒唐的鬧劇,最終以鮮血噴發出的蛇信子般醒目的警告結束。人性中最原始的惡念、自負、輕視、盲從,組成了那日的我們。那是夏天,狗尾巴草毛茸茸,花穗間嵌著不太飽滿的籽粒;狗尾巴毛茸茸,依舊可愛,只是它不再,在我踏足過的小路嗅來嗅去。我沒看見它的眼淚,可是我所站立的地方,分明是一片泛著咸味的汪洋,任憑我在其中尋覓,跌宕,發霉。
“綠樹濃蔭夏日長”的暑假,大伯家來了一位精致的城里姑娘,齊肩長發,桃腮杏眼,甜美而討人喜歡,乃至鬢邊微微蜷曲的碎發,也是俏皮又不乏可愛。我家與大伯家挨得很近,僅隔一步之遙。大伯外出農忙時,總會將她帶到我家,命我陪她一起玩。我是極內向的,而她似乎也很慢熱。于是,我們倆就像兩個要事纏身的外交官,相隔數米遠,正襟危坐,點頭致意,相互謙讓,尷尬如同蟄伏在老墻根的爬山虎,攀緣而上,密密麻麻,相互纏繞,讓人喘不過氣。院子里,在外面瘋夠了的狗尾巴帶著一身的雜草,躺在水泥地上的陽光里打滾,使勁地搖晃腦袋,幾桿蔥綠的狗尾巴草跌落在地。她大概是很喜歡動物的,瞥見狗尾巴的身影,便忘了矜持,大呼小叫地跑到院子里,與狗尾巴玩鬧了起來。
我學著母親的動作,撿起掉落在地的狗尾巴草,變戲法似的,將它編織成小狗、小兔子、小老虎、花環、戒指、蟈蟈、籠子……她看著不起眼的狗尾巴草在我手中變換著不同的形狀,圓睜的杏眼里滿是不可置信,仿佛我同那射日的后羿般,也懷揣著什么諱莫如深的神秘力量。
曾在一位作家的書中讀到過,越長大,越喜歡孩子。深以為然。命運恩賜的,沒有經過深生熟慮的思想角逐的簡單友誼,只有在孩提時,才遇到過。不出幾日,團子與我,便親密地如同一個娘胎里擠出來的似的。她極度偏愛《熊出沒之雪嶺熊風》中白熊山的山神團子,大張旗鼓地向身邊人宣布:從今以后,你們就叫我團子。那時,溫柔地擁吻鄉村的東風已經流失散盡了,團子和我急切地想要抓住夏天的尾巴,在一片廣闊的原野上放風箏。偃臥在青草尖的蛐蛐,用力地扯著嗓子,吼出嘶啞的鳴叫;陽光下,綴滿枝婭的早熟蘋果,也長到了愛美的年紀,偷摸著在腮間染上紅暈。風箏的尾巴變得長,風中有了秋天的味道。
秋天,原野上的狗尾巴草,變成了神奇的紫色,一下一下,隨風搖晃,像極了仙女遺落的裙帶,在時光的最深處搖擺。孩童的注意力總是難以集中,飄入云端的風箏很快被我們遺忘。那段時間,團子和我近乎偏執地迷上了一種奇妙的昆蟲——磕頭蟲。它暗褐色的身子狹長扁平,表面略光滑。它的樣貌并不迷人,甚至可以說是丑陋,然而令我和團子著迷的并非它的外貌,而是它胸腔里發出的那一聲聲清脆的叩頭聲,似關節斷裂的聲響,刺激著人發麻的脊背,那原始的沖動與快樂。我們比賽著誰抓的蟲子多,打算帶回去沖家里人炫耀。回家的途中,遇到了位上了年紀、佝僂著身子的老人,她望著我們,說:知道磕頭蟲為什么向你們磕頭嗎?它是在求你們放過它,給它一個生存的機會。每個生命,都有其生存的法則,切莫干擾,尊重即可。我和團子聽得稀里糊涂,但還是放了它們。
如今想來,老人那融合進了一生的哲思的話語,意在教會我們平等地對待每一個如野草叢中的狗尾巴草一樣平凡的生命。宇宙不會窮盡,歷史也是,哪個生命不是滄海中的一粒肉眼琢磨不到的塵埃,我們,一粒塵埃,又何必瞧不起另一粒塵埃呢!
“自古逢秋悲寂寥”,原來秋天,是適合告別的。臨近開學,團子回到城里上學,臨走前她說,我還會回來的。那時我們都覺得,回來是理所當然的,理所當然到沒有人認為這是一個諾言。但它確是一個諾言,一個在時間里荒蕪了的諾言,被鎖在了年輪的最里層。村里的青壯年離去后,小學生們也開始陸陸續續地離開,我的人生軌跡也按著社會既定的規律前進,從鄉里,到鎮上,到城里,到市里……漸漸地,離家越來越遠了,狗尾巴被我丟在了老家的門前,守望,等待,老去。
前幾日經過幼兒園門前,緊閉的大門內傳出小孩子們稚嫩的歌聲:小狗尾巴搖搖,小草尾巴搖搖,小狗尾巴翹翹,小草尾巴翹翹。搖啊搖,翹啊翹,搖啊搖,翹啊翹,變成一棵狗尾巴草。
你說,童年的那株被編成小狗模樣的狗尾巴草,還在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