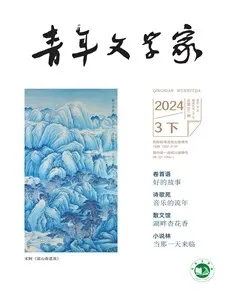20世紀90年代當代文學創作影視化特征研究
楊晶


20世紀80年代以來,小說改編影視劇的現象非常常見。影視作品作為一種受眾廣泛的娛樂方式,對其他藝術的影響日益明顯,尤其是對文學創作。眾多作家開始從影視作品中尋找創作靈感,影視符號在文學作品中的挪用越來越明顯。以王朔為代表的作家,在影視聯姻方面表現得尤為成功,出現了著名的“王朔現象”,即王朔每部作品改編成影視劇都非常成功,這些對當代作家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同時,劉震云的影視化小說創作也成為一種引人關注的文學現象。以上種種都為文學轉型提供了新的發展方向。文學與影視作為兩種不同的藝術樣式,各具創作獨特性,將影視技巧運用到文學創作中,為文學提供了新的發展契機,同時也帶來了極大的挑戰。本文將以劉震云的小說影視改編(即影視與文學的互動關系)為研究對象,著重探討影視改編對文學作品的影響及滲透。
一、影視成為文學創作的來源之一
影視對文學的影響集中在小說這類體裁。小說強調敘事,這是其與影視產生聯系的重要原因。文學創作的靈感來源很多,日常生活經驗成為文學創作素材的首選。但是,影視作品的豐富性、娛樂性同樣帶給作家們創作的靈感。麥家在創作小說《捕風者》時就直言不諱:“如果一定要問出處,勉強有兩個:一個是記憶中的老電影《尼羅河上的慘案》,另一個是……”茅盾文學獎的獲得者徐則臣在北影大講堂講座時提出:“我在電影中學到了很多東西……在寫小說《北上》中有些開闊的場景時,我的腦子里有非常清晰的意識,覺得這是一個俯拍的鏡頭,那是長鏡頭,又或是正反打鏡頭,所以今天如果有哪個小說家敢說自己完全沒有從電影中汲取養分,我覺得這是一個虛偽的話。”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對影視的喜好會因為影視作品中的一個細節或一個段落,促使作家開始創作,客觀經驗在這里已經被影視作品代替,成為作家靈感來源之一。
二、影視技巧運用在文學創作中
循著影視帶來的靈感,作家們也看到了影視創作規律同樣可以運用到文學創作中來,這可以豐富文學創作的內容,并豐富文學創作的技巧,滿足了文學從內容到形式的創新要求。眾多作家因為參與了影視創作,很容易就順手將影視鏡頭語言直接轉譯成文字敘述。
首先,最簡單也最明顯的表現即對話的增多。在這方面,劉震云的小說創作體現得最為明顯。例如,通篇存在大量人物對話的小說《一句頂一萬句》,不能不說受到了電影的影響。同時,劉震云的代表作《手機》也是先改編成電影劇本后才創作的小說。《手機》和《一腔廢話》這兩部作品包含了大量人物對話。這些對話的運用成為推動故事情節的必要元素,同時也是作家有意地模擬電影場景的結果。例如,在小說《我叫劉躍進》中,劉躍進用自殺威脅工頭時就有這樣一段對話:“嚴格倒一直沒說話,看他倆斗嘴;這時輕輕拍著巴掌:‘演得太好了。又問任保良:‘是你安排的吧?你還說你不會演戲,都能當導演了。任保良氣得把手里的盒飯摔了,栗子雞撒了一地:‘嚴總,你要這么說,我也上吊!又指指遠處已蓋到六十多層的樓殼子,上去踹劉躍進:‘想死,該從那上邊往下跳哇!嚴格這時攔住任保良,指指劉躍進,斷然說:‘人不用找了,就是他!”從以上內容能夠看出,在劉震云的小說中,出現了很多這樣在人物對話時將人物動作、道具直接表現的情況,我們可以明顯看出,這樣的文本可以直接運用到影視劇本中。反過來更為準確地說,是他的小說受到了影視的影響,小說中使用大量的人物對話是一種影視化的敘事策略。而且,小說中的對話處理也是簡潔直接,絕不拖泥帶水,少寫人物的表情和心理活動,以一種更加直觀、直接的方式呈現了故事情節。
其次,除對話的增多外,情節的戲劇化也是小說創作影視化的明顯表現。追求故事性,注意偶然與巧合來推動情節發展,成為20世紀90年代以來小說創作的又一明顯特征。例如,劉震云的小說《手機》,存在著大量的戲劇化的情節,這些偶然的巧合包括:嚴守一約定與情人伍月最后一次見面;嚴守一當日將手機忘在家中;從不主動聯系的伍月打來電話;妻子于文娟串休在家;嚴守一發現手機不在身邊回家僥幸拿回手機,心虛關掉手機;老家奶奶要和嚴守一通話;妻子聯系不到嚴守一,聯系費墨;費墨與妻子吵架,氣頭上說漏了嘴,打電話給嚴守一補救時卻讓于文娟接聽到了;嚴守一繼續撒謊,卻趕上伍月發來了曖昧短信。一連串的失誤和巧合將說謊者嚴守一步一步逼到絕境。
因為作家先創作了電影劇本,所以這段文字明顯強調戲劇的偶然與巧合因素,影視化痕跡尤為明顯。同樣在《我叫劉躍進》中,也是因為劉躍進尋找自己的包,開始了一系列離奇的情節。顯然,這種文本創作為后來的劇本改編提供了極大的方便,同樣也是影視化思維對文學創作的明顯影響。
再次,文學作品更加注意畫面感的營造。小說是一種語言藝術,而電影基本上是一種視覺藝術。顯然,作為視覺藝術的影視依賴的是聲色光影的綜合表現,即圖像的呈現。由于受到影視的影響,文學作品越來越注意畫面感的表現。例如,劉震云的小說《我叫劉躍進》中寫道:“胡同底有間屋子,房門就開向胡同。墻上的石灰縫,橫七豎八,抹得跟花瓜似的……”再如嚴歌苓小說《小姨多鶴》中寫道:“三面環繞的山坡上都陸續生起狼煙。隨著天際線由黃而紅,再成絳紫……天終于黑盡。”以上敘述可以直接作為影視劇本呈現的畫面,由此我們能夠看出,作家們重視通過文字來對畫面進行表現,這些都是影視作品中的視覺性特征在文學作品中的借用。
最后,蒙太奇手法的運用。蒙太奇手法的運用在文學作品中更是隨處可見,如平行蒙太奇、交叉蒙太奇、心理蒙太奇等手法。傳統小說一般運用線性敘事方法,嚴格按照時間順序講述故事。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期,先鋒小說在敘事上進行了更多實驗性的嘗試。于是,蒙太奇就被大量地運用到了小說創作中來。作家們對這種手法越來越熟悉,運用起來得心應手。例如,劉震云小說《我叫劉躍進》,作家已經超越古代小說“花開兩朵,各表一枝”的簡單的平行敘事方法,使用至少三條線索在不斷地平行和交叉中展開故事,制造了足夠的懸念,顯得故事精彩異常。小說中沒有明確的時間線索,更多地按照空間的變換,由劉躍進、青面獸楊志、嚴格三人作為線索。因為小說章節均以人名命名,所以在故事展開時,按照三人的行動及三人之間復雜的關系交錯展開,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十八章結束。直至偵探老邢出現之后,這種平行、交叉的故事線索才結束,回到了統一的時空中,展開下一步的敘事中。再如嚴歌苓,她的小說被改編成影視劇的頻率非常高,可能在其創作中就或多或少地考慮到了改編的便利性,于是,蒙太奇技巧就在她的小說中經常出現。例如,小說《陸犯焉識》中至少出現了三種蒙太奇手法。首先,平行蒙太奇的運用。小說以1954年為界,講述了祖父入獄前后的生活,將入獄前后的兩種生活狀態不斷地進行比較,兩條線各自展開,最后又匯聚到一起,由此向人們展示了祖父在20世紀的波折命運,時代巨變以及小人物命運形成了強烈的沖突。其次,心理蒙太奇的運用,即按照人物的心理活動,完全不受時空的限制,任意在現在與過去的時空中交替展開敘事。例如,小說先由關鍵物品—一塊手表的來源說起,再跳到1960年手表被換成幾個雞蛋,再跳到多年前祖父對祖母的對視而引發了此后的感情糾葛,再跳到祖父在收到手表的當天故事,到此終結故事,后來繼續轉移到了敘事者—“我”的視角,展開了又一段聯想,即關于墾荒情節的描寫,同時又隨機插入了幾個人物,幫助完成敘事。這樣的文字敘述,仿佛是一部影視劇一樣,完全不受時空限制,隨意地閃回或閃前,展現了主人公—祖父艱難而波折的一生。最后,隱喻蒙太奇的運用。這與象征手法運用十分相似。在小說中,隱喻蒙太奇的承載物是那塊“歐米茄”手表,它承擔了豐富的信息:對祖母而言,它是她愛情與幸福的見證;對于祖父而言,它就成為一個枷鎖,不得已接受手表,即接受不得已的婚姻,此后這塊手表也伴隨著他不幸的生活,最終又戲劇性地變成祖父對祖母愛的見證。一段錯位的愛情,一個時代巨變下知識分子的艱難追尋,一塊手表承載了太多的內涵。
當然,影視和文學的互相滲透和互相影響一直存在,這也給文學創作帶來了一些挑戰,文學創作的革新是否要一直依賴影視作品?文學作品的傳播是否要依賴影視?文學作品是否要保持自身的獨立?如果文學創作一直強調影視化特征,作家與讀者都滿足于圖像帶來的感官刺激,缺少理性思辨,感性美學逐漸成為潮流,這樣的文化現象我們是否能夠面對?影視對文學創作的負面影響也是存在的。
文學作品借助影視傳播后發行量確實在增加,但是文學創作的水準并沒有得到相應的提升。文學創作中出現的視覺狂歡,讓文學作品失去了獨立性,尤其是快餐式閱讀時代的到來,傳統意義的閱讀者不斷減少。視覺化的寫作讓讀者漸漸失去了理性思考的能力。影視化思維也影響了“讀者”們的閱讀習慣,即傳統文學中的抒情、描寫方式逐漸被他們厭棄。
我們需要注意的是,每種藝術都需要有自己的表達方式和思維方式。影視化思維越來越被重視,帶來的結果必然是文學思維的削弱。會有一些作家用影視劇本的方式代替小說原來的創作形式,這樣的做法無疑讓文學失去了自身的獨立性,會越來越單薄、淺顯。當然,進入21世紀后,我們看到傳統的精英寫作一直在艱難地行進。一些清醒的作家意識到了問題,試圖擺脫影視化創作的弊端,執拗地保持文學創作的獨立性。例如,莫言、蘇童等諸多作家,在與第五代導演多次合作后就有了很深的感觸。蘇童在談到與張藝謀合作劇本《武則天》后就提出:“這個長篇寫得很臭,我不愿意談它。我的小說從根本上排斥一種歷史小說的寫法,而《武則天》恰恰做的就是這樣一件事情,可以想象它跟我希望的那種創作狀態多么不一樣,而且一開始寫的時候我就想,不能虛構,武則天這么個人物不好去虛構她的。結果吃力不討好,命題作文不能作,作不好。”(《永遠的尋找—蘇童訪談錄》)莫言也提到:“一個小說家不應該跟在導演的屁股后邊,他必須保持自己的獨立性,也就是說,應該是導演來找小說家,不應該是小說家去迎合導演。”文學創作影視化現象確實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常見的文化現象,且這種現象也成為不可逆轉的潮流。當然,這種現象的出現對文學創作本身產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文學創作應始終把文學性放在首要位置,可以運用電影技巧為文學服務,提高文學創作的藝術魅力,而不是讓文學創作單方面成為電影作品的墊腳石。只有注意影視與文學的互動,才能夠推動影視與文學的共同進步。
本文系長春光華學院科研基金培育項目“20世紀90年代以來‘紅色經典影視改編現象研究”(項目編號:QNXS2023014)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