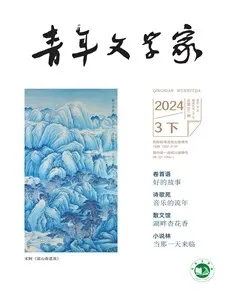歷史敘事中的生態觀照
胡濤
美國史學家海登·懷特在《后現代歷史敘事學》中稱歷史著作是“以敘事散文話語為形式的語言結構”。意大利歷史學家克羅齊指出:“沒有敘事,就沒有歷史。”可見“歷史”是可以存在于敘事中的。中國文學傳統中自古就有“文史合一”的創作理念,足見歷史與文學敘事關系之密切。然而,當代歷史敘事中,作家如何用文學去觀照歷史,是作家們在創作過程中需要思考的重要問題。對于書寫武陵地區土司歷史的貝錦三夫而言,長篇歷史小說《武陵王之皇木遺恨》在尊重土司歷史史實的前提下,其生態書寫是作者想要表達的重要價值訴求。作者在歷史記憶中,對武陵地區的自然生態和社會生態展開了獨特思考,其作品中流露的生態意識體現了作者對當代生態問題的關注與思考。
貝錦三夫在其小說中,以酉水河畔的盤順土司王向景春和朝廷木政指揮使徐珊為原型,引入了明朝嘉靖年間重要的歷史素材—“卯洞的皇木采辦”與“陽明心學的傳入”。作者在講述歷史事實的同時,不乏文學想象,深刻地反映了武陵山區的地域風情、畢茲卡的民俗文化和社會活動。作者在小說中的生態觀照正是通過對畢茲卡“原生態”文化的書寫和陽明心學指導下的生態實踐,以此來展現人、自然、社會三者之間的和諧統一。
一、歷史敘事中“原生態”的民族文化
所謂“原生態”文化,指的是“在大工業文明來臨之前還存在著的那些自然的生活方式、藝術形態和宗教信仰”(徐兆壽《一種新的寫作現象:原生態文化書寫》)。原生態文化內涵的重要特征是“地方性知識和民間色彩”。研究者通常用“原生態”來形容少數民族地區原始的自然環境和當地獨特的民風習俗、自然崇拜等民族文化。
“原生態的自然美是一種自然的大美。”(王諾《生態批評與生態思想》)貝錦三夫筆下的武陵地區,位于湘、鄂、黔、渝交界處,那里山高水遠,地理位置復雜,保留了最為原始的自然美。也正是這種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畢茲卡文化較少受到外來因素的影響,保留了較為原始的一面。而長期生活在武陵地區的貝錦三夫,在講述歷史的同時,用自身體驗向讀者展示了畢茲卡“原生態”的民族文化。
喪葬習俗是畢茲卡人重要的民俗之一,其喪葬儀式最能凸顯畢茲卡獨特的民族性格氣質。畢茲卡人對于喪葬特別講究儀式,“升幡竿,打鑼鼓、打繞棺、跳喪鼓,破血湖、解枉死結、祭奠青山”(《武陵王之皇木遺恨》)。畢茲卡人認為,舉辦隆重儀式才是祭祀故人的最好方式,場面越熱鬧越有意義,這種隆重的喪葬儀式并不是以表達在世者的悲傷為主要目的,而是表達一種特殊的意義—“以悲為喜”。對死亡持一種樂觀豁達的態度,是畢茲卡人對生命的特殊理解,另外重要的是他們希望在世者能夠幸福、團結。筆者認為這才是隆重儀式的最直接體現,試想一個家庭、一個族群內沒有穩定、和諧、幸福的關系,而是經常矛盾不斷,怎么會有喪葬儀式的舉行?怎么會有如此熱鬧的祭祀儀式?可見,畢茲卡人對生命的獨特理解,是集體無意識生殖崇拜的結果,他們希望子孫萬代團結幸福。
舍巴日是畢茲卡人自己的節日,在這天畢茲卡人會舉辦文藝體育和祭祀二者兼得的活動,即跳擺手舞,來祭拜祖先、崇拜自然。盤順土司普舍樹下的寬闊院壩是盤順土民們慶祝節日的重要場所。普舍樹作為盤順土民心中的特殊文化符號—福,“它是觀世音菩薩送給你們漫水人的福報,它能為整個漫水坪百姓普施幸福!”(《武陵王之皇木遺恨》)普舍樹更為奇特的是它能辨識族人,因為它的花瓣只會落到盤順族人身上。每年舍巴日,盤順土司王都會在普舍樹下與民同樂,為了表達對祖先的崇拜和對自然的敬畏。
另外,畢茲卡人對神秘的自然有著獨特的崇拜。首先是對神木的崇拜,盤順境內翔鳳山上的九陽金絲楠木是盤順向氏的祖跡神木,據說曾庇護過被追殺的向氏先祖。此后,每年夏至日便成為向氏祭奠祖宗、拜祭神木的大典之日。焚香祭祖,載歌載舞是常規儀式,以儺祭祖是此次活動的中心,包括儺祭、儺技、儺戲、儺舞、儺歌。這隆重的祭祀儀式一方面是為了表達族人對向氏先祖的追念,希望得到神木的庇佑,另一方面則是為了提高族人的自信心與榮譽感,維系族群關系,加強族群的凝聚力。
總之,貝錦三夫在向讀者講述歷史的同時,書寫了畢茲卡居住地優美的自然生態,呈現了畢茲卡“原生態”的民族文化。從這些民族文化中可以看出畢茲卡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理念:在喪禮中尊重自然、順應自然,在歌舞中親近自然、熱愛自然,在崇拜中敬畏自然、保護自然。當然,推動畢茲卡地區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用生態理念指導實踐,則離不開兩位重要歷史人物—王陽明及其弟子徐珊。
二、陽明心學指導下的生態實踐
王陽明是心學的集大成者。他于明朝正德元年間,得罪宦官劉瑾,被貶貴州龍場,并頓悟出“知行合一”“心即理”“致良知”“事上練”等心學理論。他在當地創辦龍崗書院,廣收弟子,通過講授心學來傳播陽明心學思想,這對當地土司“蠻夷”有一定教化作用。王陽明所處的時代正是西南土司制度上升時期,王陽明的心學思想在當時土司領域內廣泛傳播,“在潛移默化中實現了對土司社會的治理與教化”(茍爽《陽明學說對貴州民族社會的影響》)。而陽明心學在盤順土司境內的教化與影響則離不開王陽明的弟子徐珊,他是陽明心學的積極宣傳者和實踐者,是踐行生態理念的重要人物。因此,徐珊與陽明心學思想傳播成了貝錦三夫歷史敘事中的重要歷史素材。
徐珊作為朝廷官員來卯洞督查木政采辦工作,在與盤順土民的交往過程中,將陽明心學進行了廣泛的傳播。徐珊用陽明心學指導采木,其生態理念也得到傳播。盤順土司在陽明心學的指導下,不僅如期完成了朝廷的采木任務,更是把采木“后遺癥”控制到了一定程度范圍之內,“皇木砍伐,以明朝為甚,湖廣土司地區為害尤烈!”(《武陵王之皇木遺恨》)皇室采木,實質上就是封建徭役,對武陵山區環境危害巨大。但徐珊用陽明心學指導的采木工程,對盤順土司境內的環境破壞有很大程度的降低。
“明代興起的皇木采辦,有一套完整的體系,大致可分為勘察、采伐、轉運、運解交收、儲備等五個環節。”(譚慶虎、田赤《明代土家族地區的皇木采辦研究》)其中轉運樹木最重要的是“找廂”,即“先由石匠開采巨石,形成簡易的路基;架長空中地段,做好支架,然后以兩列杉木平行架設在路基和支架上,形如今日的鐵路”(譚慶虎、田赤《明代土家族地區的皇木采辦研究》)。在此過程中,為了尋找寬闊的路基,不可避免地需要重新開路、砍伐障礙物,為了保護環境,盤順土司王和徐珊多次商議運木路線,徐珊多次上山勘察最佳路線。徐珊作為陽明心學的傳播者,自身始終在踐行著陽明心學的核心思想,即“知行合一”,也就是認識與實踐的統一。徐珊自來到盤順土司后,秉持著“食君之祿,必事君之事;為民之官,必言民之言”(《武陵王之皇木遺恨》)這一為官信條,堅持忠君親民,所以在采木時,始終在做保護環境的努力。
而早期同作為陽明心學的傳播者費度,他的采木做法與徐珊截然不同。此時的費度已經被權力和欲望沖昏了頭腦,為了早日運走皇木而騰出手去尋找通天神木,他隨意下令,讓散毛土兵帶著火槍對沿途進行拉網式搜尋,破壞了當地環境;運送皇木時,同樣不聽取漂木工的意見,堅持首汛漂木,最終導致卯洞被堵,死傷十余人。可見,二人的做法截然不同,在“致良知”方面,費度被欲望蒙蔽了雙眼,在實踐中沒有良知,而徐珊真正做到了“心即理”,不為外界影響,遵循天理,遵循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思想。
土司境內,各司對于“王室子弟”的教育比較重視,如果土司內沒有學堂,就要去外地州縣庠序學習,以此來學習孔孟儒學、漢家禮儀。盤順代主夫人向鳳陽自小就被送到外地辰州府求學,更有幸親自受到陽明心學弟子徐珊的教導,這對她回族代政有重要影響。“知行合一”的思想一直指導著她踐行生態理念。
三、在歷史敘述中回望與反思
作者在后記中寫到,該作品是“重點展示當時的社會矛盾和人物命運,突出歷史的包容性與開放性,著墨于當時畢茲卡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美妙,著墨于艱難的生活景象和向往文明的追求,弘揚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歷史小說《武陵王之皇木遺恨》聚焦盤順土司地區的皇木采辦事件,塑造了眾多真實而又典型的歷史人物,向我們展示了武陵地區特定歷史時期的民族文化,其中流露的生態意識更是具有現代意義,值得讀者反思。
首先,對歷史的反思。作者的歷史敘事,始終堅持著理性,向我們展示了畢茲卡歷史文化,同時也發揮了文學的想象力。不論九陽神木是否真的存在,這在不影響歷史真實的同時,增強了作品的可讀性與反思性,讓讀者真正認識到歷史上的皇木采辦對生態造成了嚴重的破壞。武陵地區民族成分復雜,土司制度是“封建王朝統治階級用來解決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的民族政策,其義在于羈縻勿絕,仍效仿唐代的‘羈縻制度。政治上鞏固其統治,經濟上讓原來的生產方式維持下去,滿足于征收納貢。因此它是從政治和經濟兩方面壓迫少數民族的制度”(《明朝西南地區的土司制度與改土歸流》)。特定歷史時期,推行土司制度是符合當時社會發展的要求,最重要的是加強了少數民族地區的管理,增強了人們的民族認同感。另一方面它也對少數民族地區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壓迫。拿皇木采辦來說,它不僅浪費物力、財力、人力,加重了勞動人民的負擔,而且對武陵地區的森林植被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損失,導致大量珍貴樹木被采伐,使其難以恢復,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當然我們也需要辯證地看待歷史,在驚呼京都地區古建筑、皇室宮殿等文化遺址時,我們能想起武陵地區皇木采辦這一段艱辛的歷史。
其次,對欲望的反思。生態破壞與人類欲望的無限膨脹始終分不開,小說中的費度與徐珊同是陽明弟子,接受心學的洗禮,是陽明心學的重要傳播者,但后來漸行漸遠。這便是各種欲望侵蝕的結果,費度不僅想搶奪采木的先功,而且與朝廷要官嚴嵩勾結,私謀九陽神木,方便為自己安置一副死后不腐的棺槨。另外,土司境內看似平靜如水,實則暗潮涌動,各種矛盾都直接或間接地對當地生態的破壞埋下了隱患。可以說,作品從多方面給我們展示了權力私欲對自然生態美的摧毀,在自給自足的土司境內,山水雖美,但廟堂、江湖終究抵不過欲望的侵蝕,自然生態的破壞不可避免。陽明心學雖主張“心即理”,但需要人們有正確的主觀意識和認識能力—用生態意識來指導實踐,否則便會同費度一樣,與真理漸行漸遠。細讀作品可以發現,貝錦三夫在作品中流露了鮮明的生態意識,一方面謳歌了武陵山區多數土民有節制地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自覺生態意識,這是他們千百年來與自然共生總結出來的經驗;另一方面通過皇木采辦對武陵生態毀壞這一事實的展示,反映了自然生態與占有的問題,實質上是對現代人類中心主義的批判。現代文明社會中,“人與自然的疏離只是生態危機的表層顯現,自然生態遭到破壞反映的是隱藏其后的人類自身精神生態的失衡”(趙樹勤、劉倩《從“淺綠”到“深綠”—新時期生態文學研究綜述》)。如何處理好人與自然、生存與占有、人類精神生態與自然生態的關系,值得現代人思考。
巴爾扎克說:“小說被認為是一個民族的秘史。”貝錦三夫用傳統章回體的形式,在歷史的敘事中,向讀者展示畢茲卡神奇秀美的自然生態以及“原生態”的民族文化,并通過皇木采辦和心學傳播特有的素材,醞釀出了獨特的生態意識,有意地體現著對封建王朝、人類中心主義的批判,無意地在作品中流露出對自然的崇敬和對生命的敬畏的自然生態意識。小說悲劇的結尾無法掩飾作者內心的惋惜與無奈,九陽神木“含恨”被掩埋和心學傳播者含恨沉潭的悲劇結尾,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不僅是對畢茲卡歷史的反思,更是對現代生態狀況的焦慮與憂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