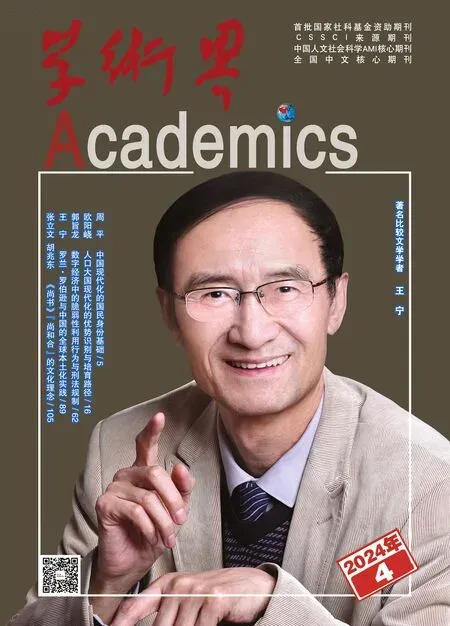明代兩淮鹽業與漕運、黃淮水利的關系〔*〕
謝 祺
(華中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 湖北 武漢 430079)
明代淮鹽是國家最主要的食鹽運銷種類,以淮河為界,淮北鹽產自海州境內鹽場,淮南鹽則產自江北淮南的泰州、淮安等府州的沿海鹽場。產出的鹽需要經過諸多河道運輸到南直隸西部、江西、湖廣、河南東南部等地銷售,京杭大運河的今江蘇境內河段(主要是淮揚運河)和大運河以東通往海岸的航道網絡(即俗稱“里下河”)的通暢對食鹽運銷至關重要。同時,黃河自南宋初期呈現向南改道奪淮河下游河道入海的趨勢以來,經過南宋、元代兩百多年的發展,到明前期“黃河奪淮”局面已經基本固定,兩淮鹽場和運輸航道基本上都屬于黃淮下游,受到黃淮水患影響較大,所以黃河、淮河、漕運的治理也都關系到鹽的生產、運銷能否順利。兩淮鹽業、黃淮水利、漕運的治理產生了越來越多的聯系,三者被后來的清人并稱為“東南三大政”。
關于黃淮水利、漕運水利,前人作過許多綜合性研究。〔1〕還有不少專題研究成果,首先呈現了明代黃河奪淮背景下黃河水利和淮河水利的一體性,尤其是以保證漕運優先的治河思想對明代水利政策有著深遠的影響;〔2〕其次,呈現了黃淮治理到了明代隆慶、萬歷年間,由于黃河河床抬高帶來的諸多問題,關于治理黃河的技術政策出現了諸多的爭議和政策的搖擺,爭議之中洪澤湖、淮揚運河東西兩側的地方利益都參與進治水的討論,〔3〕試圖將洪澤湖水朝對方的方向分流、排泄,如袁慧的研究指出,鹽業的利益也被加入有關治水政策爭議中,作為反對高家堰向東泄洪的借口;〔4〕最后,呈現了萬歷中期明祖陵被淹導致了治河政策制定的進一步復雜化。〔5〕而鹽業史方面的前人研究,除了梳理明代鹽政制度的變遷外,也都會論及明代中后期鹽政的諸多弊病,如勢要占窩、鹽引壅滯、商人長期守支、正額鹽引外征“浮引”等等,并最終導致明朝在萬歷四十五年開始實施綱法改革;〔6〕同時,鹽業發展也需要對淮揚運河以東的河道網進行維護。〔7〕
但鹽政與明代黃淮水利之間的經濟利害關系為何?明中后期是治理黃淮活動較多的時期,這與明代鹽政衰落的時期基本一致,那么鹽政的衰落與黃淮治理有無關系?這些是基于前人研究現狀,筆者產生的疑問。筆者將從鹽業的視角,探尋兩淮鹽業興衰與漕運、黃淮水利的關系。
一、明代前中期的兩淮鹽業與漕運
明代的淮鹽,生產于南直隸江北沿海地區,其運銷仍然依賴沿海通往淮河或長江的諸多航道,與漕運航道往往有著共同性。一些鹽業的稅收、緝私管理依托于漕運河道進行,如洪武二十七年,“溧水縣耆民奏朝廷,近開東壩,既利漕運,且便商賈,宜立稅課局、(鹽)批驗所、巡檢司各一所。從之。”〔8〕可見鹽與漕運的管理機構分布在地理上有相通之處。
在功能上,鹽法常常也會成為漕運的補充,如成化二十年,“詔以漕運糧儲,及兩淮鹽課給三邊……于浙江等處明年漕運糧內,量免七十五萬石兌運,令每石并耗米糶銀五錢,蘇、松、常三府倉糧糶賣二十五萬石,每石銀四錢,俱觧京轉運,以助軍餉。仍摘兩淮鹽課二十萬引,令大同管糧官,招商中納,以補不足。從之。”〔9〕當邊關需求糧食,而漕運糧食有限的情況下,鹽引的“開中法”〔10〕可以發揮對漕運不足的補充作用。在需要賑災之時,漕糧不足的情況下鹽務收益也會被用于彌補漕糧不足,如嘉靖九年,“戶部言比者漕運都御史劉節言,淮、徐地方災,二倉支運糧米無所從……漕船領兌各有定期,今責以帶運則搬剝收受不無停誤,既地方災甚,宜止以鹽銀收貯,候下年豐收糴買……詔可。”〔11〕可見鹽務所得資金成了漕糧不足的重要補充。
正因為鹽務與漕務的密切關系,職官上二者也有兼管。明代國家鹽政管理,除了在地方上設立都轉運鹽使司、鹽課提舉司、鹽課提舉司分司、鹽場等各級別的生產、運銷管理機構,以及在中央由戶部山東清吏司管理鹽務之外,在地方上也設立了巡鹽御史監察鹽務,逐漸成為實際上的地方鹽政長官,鹽運司、提舉司都受制于巡鹽御史。〔12〕除了專門的巡鹽御史,漕運的長官也經常兼有巡查鹽務的職能。如景泰三年九月,“勅總督漕運巡撫淮安等處右僉都御史王竑曰,已嘗命爾總督漕運,兼巡撫直隸揚州、廬州、淮安三府并徐、和二州,今復命爾兼巡撫直隸鳳陽府并滁州,仍兼理兩淮鹽課,總督運司官吏督工煎辦,時常巡歷行鹽地方,提督緝捕私販之徒。”〔13〕擔任總漕的王竑,奉命兼督鹽課、緝拿私鹽販,其中重要的因素,也是漕船水手常從事私鹽貿易,如奏稱:“各歲漕船還日多帶私鹽,吏不敢詰。”〔14〕所以需要漕運總督作為高級官員兼管鹽務,才能強化稽查。
但除了漕糧類似的糧食運輸功能,漕運水利工程的經費,也與鹽務相關,如景泰四年七月,戶部奏稱:“集丁壯于沙灣浚治漕河,該給口糧已令山東、河南及直隸大名等府糧稅,并山東囚犯贖罪米,及中納鹽糧等米,俱于臨清、濟寧二處上納備用。”〔15〕可見京杭大運河的維修經費,一定程度上來自鹽課的開中法。除了開中法,鹽務收益也直接用于漕運河道里運河的修治,如弘治九年,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鄧璋稱:維修高郵湖堤防的經費為“以淮陽、廬鳳等府贖罪米價,并兩淮運司余鹽價銀萬八千兩,為買石之費……事畢即止。上從之”。〔16〕航運水利條件的損壞,是漕運總督非常關心的,甚至漕船水手的經濟困境也要從鹽課解決,正德十四年總漕王佐曾為解決漕船水手欠私債引起的盜賣糧食問題,上奏《議借鹽銀償還糧運宿債》,試圖借鹽課銀替水手還債。〔17〕
當然,很多漕運水利工程,也服務于鹽業運輸。比如明代《漕運通志》中記載的航道就有名為“運鹽官河”的河流也“通漕運”,并且明朝在運鹽官河基礎上進一步深挖、擴建:“挑開白塔河注揚江,以便淛江等運船。”〔18〕所以漕運水利的建設與改善,也服務了鹽業。而漕運作為被后世稱為“天庾正供”〔19〕的重要運輸項目,直接關系到北京、北方邊防的糧食供給,最為朝廷所重視,工程服務鹽業航運更多是漕運工程建設附帶的功效。嘉靖七年,朝廷為了籌集糧食備荒,而漕糧不足,同時也存在灶丁將余鹽私自販賣的情況,于是“命漕運大臣兼理鹽政,灶戶正額之外若有余鹽,驗令報賣量征十之二三,分觧于淮安、徐州、濟寧、德、滄、天津等處,乘有收之年糴買雜糧收貯官倉……漕運不困而鹽法亦通矣”。〔20〕可見朝廷是想最大程度發揮鹽業的生產能力來彌補漕運不足,同時解決余鹽成為私鹽的問題。上述的事例可以說明,在官方的意識中,漕運與鹽業具有一定的功能類似性,雖然漕運水利工程也惠及鹽業,但鹽業是為漕運水利提供輔助的。
二、鹽業與水利經費
在明朝的鹽政制度內,鹽政的正額收入本來就是一定程度上為國家工程準備的:“淮、浙、長蘆引鹽,常股四分,以給各邊主兵及工役、賑濟之需;存積六分,非國家大事,邊境有警,未嘗妄開。”〔21〕其中的工役當然包括河工。但是,除了黃河河工,兩淮鹽場附近地區其他河道也是經常需要開展水利工程活動的。比如安豐場鹽課司的南新河“年久淤塞,成化二十年(鹽課)大使熊椎、義官吳瑀督工疏浚”。〔22〕再如梁垛場鹽課司的新開河“弘治三年判官徐公委副使任才疏浚”。〔23〕這兩個河道疏浚工程,明顯是鹽課司官員自行開展的疏浚工程。巡鹽御史發現河道有問題也會進行疏浚,比如呂四場鹽課司的運河,“成化二十年巡鹽御史李孟眰開”。〔24〕還有一些河道是鹽業相關的地域,由鹽政系統之外的其他行政長官來主導疏浚,如東臺場鹽課司的煎鹽河“洪武二十九年老人林貴奏準,差工部官,部夫開挑”。〔25〕這是由鹽場當地申請,經皇帝批準由工部來疏浚的河道。在石港場鹽課司的運河,則是由“弘治二年御史張公委揚州府通判文魁疏通”。〔26〕這是地方行政單位揚州府進行的疏浚工程。類似于以上的史料中,似乎可以從主導者身份推斷經費是從主導者自身所屬單位經費開支的,然而事實上并不一定。
如前述的新開河,曾有鹽場當地文人寫下《新開河記》記載嘉靖丙申年曾發生洪水,當地士紳稟報朝廷后,鹽運使、運同、運判等官員主導河流疏浚,并以工代賑:“(諸官員、士紳)相董厥事,出贖金若干兩,應賑者半焉,從民請也,召工開鑒,不勞于民,不取于眾,計工食力,計日成工,而運河以成。”〔27〕從此史料可見,有些工程雖然有官方背景,但是由當地士紳集團與官員自行集資。兩淮鹽場的另一個重要的水利工程就是范公堤,始建于宋代,后來屢毀屢修,至明代不斷在前代基礎上擴建,諸段堤防多相傳是范仲淹所建造,遂有“范公堤”的名字。〔28〕范公堤可以防風潮,保護鹽場,對海岸內的土地則可以防鹽堿化,保護農田。明代主要的大規模重建范公堤工程有:洪武二十三年被海潮破壞后“海門縣官以疏聞,起倩蘇、松、淮、揚四府人夫修筑”;其后,“永樂九年漕運總兵官平江伯陳公瑄起倩淮、揚二府人夫又重筑焉”;再其后,成化七年堤防又一次被海潮破壞,巡撫、都御史等官員“起倩沿海民夫兼各場灶丁凡數千人”來修筑完工。〔29〕所以范公堤在明代的多次重修主要是依靠政府征發民眾徭役來完成的。鹽運河道也有直接征發徭役疏浚的,如正統五年三月“直隸淮安府鹽城縣奏,伍佑、新興二場運河壅塞,阻商旅行舟,乞浚之。事下行在工部,覆奏請下淮安府,俟豐年興役,從之。”〔30〕淮北分司的“支家河”,嘉靖年間疏浚以后官員寫了《重浚支家河記》,稱工程先是商人劉禎上疏請于朝廷,得到工部批準后由當地都運使范鏓、副運使徐元祉等官員實施工程。〔31〕后來支家河上的堰、閘壩等工程,也由徐元祉實施,竣工后又有《參政李元景濟閘壩記》記載工程經費:“估計取之公帑者什一,多商捐貲效力,自相趨赴,徐子惟起倩以時,激勵有方而已。”〔32〕支家河堰、壩工程應是支家河疏浚的后續配套工程,工程主導者同為副使徐元祉,所以經費籌集模式應該類似,雖然確實使用了鹽運司公帑,但是為數不多,多數經費來自商人捐款。
所以可以認為,除了主干運河淮揚運河以外,以上的鹽場附近地區的諸多大小河道疏浚、閘、壩、堤等水利建設,雖然往往都由官方主導,但是主要的工程經費其實來自鹽場地方社會而非官帑,或發動鹽商捐款,或由士紳、當地官員捐款,或征發群眾徭役,來完成工程,長期工程也會造成一定的社會負擔。同時可見僅憑少量的官帑和商民、士紳捐款的模式,很難完成淮揚運河這樣較大規模的維護工程,鹽業依賴于國家的大規模黃淮水利治理。
明代的黃河河工,與運河、淮河河工是密切相關的。永樂年間刑部侍郎金純疏浚黃河故道,北引黃河入會通河,南引黃河入清口(淮安)以北的高地缺水區的漕河,并使得會通河以南清口以北的漕運直接使用黃河河道。〔33〕黃河到了成化、弘治、正德年間河床逐漸抬高,河道越來越不穩定。戶部侍郎白昂、都御史劉大夏治河,主導黃河主流全向南入淮河,并開挖向南的洪水分流河道,即所謂“北岸筑堤,南岸分流”。〔34〕明中期黃河下游淤塞,頻繁決堤泛濫,導致運河也淤塞,正德、嘉靖年間漕運多次中斷,最終使得嘉靖末期工部尚書朱衡在黃河外開鑿新運河,即“避黃行運”。〔35〕治理黃河的官制,明前期由總漕兼任巡撫并兼管黃河水利。明憲宗成化七年以工部侍郎總理河道,是設置總河侍郎的開始,黃河治理開始有脫離于漕運的職官。隨著嘉靖以后黃河泛濫日益嚴重,河、漕兩職務雖然分分合合,但明代總體仍以總漕兼理河道為主,至萬歷三十年以后河、漕二臣才不再合并。〔36〕總漕管理河道屬于兼管性質,明前期對于河工主要是小規模的修修補補,后來河道抬升水患加重,總漕逐漸力有不逮,成化七年以后總漕與總河職務總體分開,由此常產生二者之間的一些職權沖突,總河權勢逐漸上升。〔37〕明中后期的黃河河道抬升、洪水泛濫等問題,也使得傳統上一直作為漕運輔助的鹽務,對運河、黃淮等大型水利工程的支應越來越多。
具有代表性的由鹽務支出的黃淮水利經費就是“挑河銀”。挑河銀在明前中期不見史乘,較早記載為嘉靖三十八年:“詔留兩淮運司庫貯挑河銀二萬兩、鹽課銀二萬兩于鳳陽軍門支用,從巡撫都御史李遂請也。”〔38〕李遂即是當時的督漕都御史兼理巡撫,可見鹽政當局預備了挑河銀和部分鹽課銀,正是為了給治理漕、河預備的。挑河銀是鹽商繳納的:“隆慶二年尚書馬森題準,兩淮運司商人納挑河銀,二萬一千余兩,歲撥三千兩,恊濟洪夫。”〔39〕調用挑河銀基本是河工需要,如隆慶二年“詔以兩淮運司挑河銀三千兩發徐、呂二洪,協濟河工之費”。〔40〕挑河銀不僅直接用于河工,也會用于鹽場的洪水災害的賑濟:“兩淮巡鹽御史李學詩以鹽場水災,請扣留商人正鹽納銀每引一分,及挑河銀二萬兩,賑恤灶丁。從之。”〔41〕隆慶二年,挑河銀的繳納制度合并進鹽引制度:“擬定引價納銀,及該鹽關引起紙,賑濟、挑河等銀就將運司收買官引給與一道,以便照鹽發賣。”〔42〕從此,合法的鹽商都必須在鹽引正額銀兩外附帶繳納挑河銀才能買到鹽引。
明代以來黃河河床不斷抬高,漸高于淮河,導致淮河水越來越難以匯入黃淮下游,在黃淮交匯處反而也有黃河水倒灌淮河,淮河水和倒灌的黃河水漸漸在淮揚運河之西、淮安和泗州之間形成了巨大的洪澤湖。為了防止洪澤湖泛濫和影響漕運,在明代前期就已經形成了阜陵湖(洪澤湖形成前的當地小湖)東的攔水堰,成為高家堰的雛形。〔43〕后來明代中期隨著洪澤湖的水量不斷擴大,明朝在之前的攔水堰基礎上不斷加長、加高,就形成了“高家堰(高加堰)”。較大的一次擴建是嘉靖三十二年:“徐、邳等十七州縣連被水患……命戶部給發余鹽銀兩,及徐淮等倉存留糧米,選差大臣出賑,仍令工部行巡撫及河道官急將黃河下流設法疏浚……將高家堰增筑長堤,原建新莊等閘加石修砌,以遏橫流,但挑筑工料計銀十三萬九百余兩,乞發淮揚、滸墅二鈔關,并蕪、杭二抽分銀兩觧用,工部覆議從之,已命發淮、徐倉粟麥四萬石,運司余鹽銀五萬兩,遣刑部右侍郎吳鵬往賑之。”〔44〕可見,在治理黃河泛濫的過程中,鹽務的余鹽銀被用于治水政策中的災民賑濟,和加長高家堰、修建石閘等工程建設是配套實施的。從金額可見,隨著黃河越來越不穩定,鹽務與治黃相關的支用金額有逐漸增大的趨勢。如嘉靖年間官員論述:“徐、沛大水,黃河溢,得大司空朱公衡治之,鑿夏、邨等鎮新河百二十里,計工費以巨萬計,人或謂公不難費耶,公曰國喉咽也,舍而不治即歲歲計之,為巨萬者可指屈也,河工成,漕自是毋阻。”〔45〕官員也著力加大對治理黃河的投入,以此改善漕運。除了高家堰,其他的黃河、運河相關大型堤堰修筑也與鹽務收入相關,如萬歷四年漕運侍郎吳桂芳修高郵湖堤,其經費來源中就有:“河工銀共五萬八百六十四兩,兩淮鹽運司庫貯挑河銀三萬兩,俱留濟用。”〔46〕這樣的經費使用,延續了明前期已經存在的用鹽務支援漕運水利工程經費籌措的老傳統,只是支援治理運河的同時,在明后期,老傳統與支援黃河治理逐漸也聯系在一起。
治黃技術政策由于不同官員擔任總漕和總河,出現多次政策搖擺。萬歷初先是總河萬恭主張分泄淮水南下,總漕王宗沐則要求重修高家堰封堵淮水分泄;后來萬歷五年吳桂芳以總漕兼任總河,主張全淮敵黃;萬歷六年潘季馴仍以總漕兼任總河,繼續堅持全淮敵黃,并在加高高家堰“蓄清刷黃”的同時推行“束水攻沙”治理黃河;萬歷二十年由于明祖陵被水淹,潘季馴去職,總漕陳于陛主張泄淮,總河舒應龍主張分黃;后來的總河楊一魁又實施“分黃導淮”。〔47〕但總的來說,技術政策實施得最穩定、效果最好的莫過于潘季馴。潘季馴的束水攻沙論,不僅闡明水流挾沙能力和水流速度之間的內在關系,而且他還有一個思想是“蓄清刷黃”,即把淮河的清水注入黃河,增大水流的挾沙能力,他力主大修高家堰大堤,攔蓄全淮之水專出清口,匯入黃河。〔48〕(見圖1)所以,潘季馴在諸多技術政策爭議中必須力保高家堰得到加高,淮河水除了流入清口之外不能分流。

圖1 洪澤湖周邊地區示意圖〔49〕
治河技術政策的爭議夾雜了很多地方利益,正如當時泰州出身的官員陳應芳評論:“予淮南人也,盛言高堰之不可開,與泗人盛言高堰之必可開也,有如聚訟,得無各為其鄉也,與哉顧泗人所言者情也,而揆諸理則非是,專利于己,而忘其以鄰國為壑者也。”〔50〕加高高家堰很可能會導致洪澤湖西側的泗州被水淹,所以泗州人及為其代言的官僚堅決要求拆除高家堰、向東排泄淮水,而高家堰東的地方則為了自己的鄉土利益堅決要求保留并加高高家堰。如果單純地以保護自身各區域的利益為理由,很難駁斥反對意見。潘季馴能夠頂住壓力相對長時間實施加高高家堰的技術政策,同時保證工程財源,其實與朝廷的鹽務利益有著密切的關系。
三、隆慶、萬歷年間兩淮鹽業與黃淮治理的利害關系
潘季馴這樣論述高家堰的沿革:“(高家堰)至我朝平江伯陳瑄復大葺之,淮揚恃以為安者二百余年,久剝蝕而私販者利其直逹,以免關津盤訐,往往盜決之,至隆慶四年大潰……山陽高、寶、興、鹽諸邑匯為巨浸……馴曰堰決而塞筑……七月堤工告成,而清口深闊如故,八月河水大退,高堰外水及堤址者僅一百五十丈余,皆干地,再詢泗州之水盡已歸漕,膏可耕。”〔51〕潘季馴指出,高家堰保衛著洪澤湖水位下的高郵、寶應、興化、鹽城等地的安全,在明前期陳瑄大修高家堰以來,就長期發揮著防洪的重要作用,明后期江淮運河以東各地之所以頻繁水災,正是由于私販為了逃稅,常掘開高家堰私開新航道以逃避稅關盤查,久而久之,發展到隆慶四年造成了大決口。在潘季馴重新維修高家堰之后,淮河水全部從清口流入黃淮下游再入海,高家堰周邊地區的洪水被濾干,耕地也增加了。可見明代后期的黃淮下游地區的水患,除了黃河自身的河道淤抬以外,也有私鹽稽查松弛的因素。
所謂“私販”就是私鹽販,潘季馴在反駁持有開挖高家堰疏導淮河新河道觀點的官員時指出:“淮水從高堰出,則黃河濁流必遡流而上,而清口遂淤。今周家橋止通漫溢之水,而淮流之出清口者如故……即于周家橋疏鑿成河,以殺淮河之何如?馴曰漫溢之水不多為時,不久故諸湖尚可容,受若疏鑿成河,則必能奪淮河之大,而淤塞清口,泛溢淮揚之患又不免矣,況私鹽商舶由此直達,寧不壞鹺政而虧清江板閘之稅耶。”〔52〕潘季馴一方面認為,開鑿新的淮河河道會導致高家堰中流入清口的淮河水量減少,必然導致黃河倒灌和清口淤塞,仍會造成黃淮洪水泛濫;另一方面,為了反對開挖高家堰淮河新河道,就強調新的引淮河道會成私鹽販的運銷航道,鹽政稅收會減少。
因此,潘季馴很重視對私鹽販的防御:“此二堤俱在荒僻人不及見,而鹽徒私販奸商漏稅,又利高堰之直達揚州,每行盜決……以臣愚見,合無除多集夫役,以分布棲住于二堤矣,尤當各設精厲大使官一員使之同居堤上,專部而防御焉。”〔53〕為了堅決杜絕私鹽販盜決高家堰通往揚州,潘季馴要求派遣更多防守人員和官員駐扎高家堰上。高家堰的維護也需要得到巡鹽御史的配合,潘季馴稱:“高堰大使專管本堤,各令晝夜巡邏,遇汕即補,庶地有專轄而功可責成矣,臣已行司道會議通詳未報,乞敕工部轉咨漕撫、都御史及咨都察院轉行巡按、巡鹽御史再加查議,如果相應添設,覆請施行,不勝幸甚。”〔54〕可見,在加高和維護高家堰方針上,潘季馴與巡鹽御史有著共同的敵人——私鹽販。意識到私鹽販長期破壞高家堰的還有申時行,他曾經致函漕臣:“高堰左右為泗州等處鹽徒出沒潛行之地,往時多有盜決者,宜修筑堅固,且嚴防戢。”〔55〕潘季馴經申時行的大力舉薦得以起用,申時行也曾向明神宗稱贊:“潘季馴塞崔鎮筑高堰以后,河道安流,糧運無阻。”〔56〕申時行的防私鹽的建議或也是受到潘季馴的影響。高家堰本身處在淮鹽運輸的要沖,長期以來緝私鹽力度不足:“高堰而北由板閘則通淮北諸鹽場,自高堰而東由涇河、黃浦則通淮南北諸鹽場,自堰而西則通盱眙,自堰而南則通天長,東西二百余里,南北四百里,其地至為要害,中間止設洪澤巡司豈能兼制。”〔57〕所以潘季馴的封堵洪澤湖分泄路徑的技術政策是符合鹽務交通管控需求的。
除了私鹽問題,隆慶以來黃淮洪水對沿海鹽場的沖擊越來越大。《淮安府志》載:“鹽為國家之利,如廟灣之在山陽,如白駒、劉莊、伍佑……號十場,乃今國計既詘,商力又困,其利大不如前,況水溢而鹽湮乎。”〔58〕洪水不僅直接影響鹽業,對當地其他的社會生產都構成危害,地方志對此多有記載,如:“今水患相仍供億在困”;〔59〕“萬歷三年水患,軍余逃竄”;〔60〕“隆萬以來,河淮南徙,淮揚諸郡縣歲蒙水患”;〔61〕等等。
潘季馴的技術政策符合鹽務需求也體現在鹽場防洪上,如鹽政官員奏報:“議支河,查得先因高堰黃浦之決未,塞全淮之水傾注,高、寶、興、鹽之間田廬墳墓一望淼渺,當事者不探其原,惟尋其委,請開興化縣之丁溪、白駒二場海口,鹽城縣之周祿港至新河廟三十余里,又動支鹽運司銀二萬五千余兩,分貯于興、鹽二縣,大加疏浚,為泄水計,該臣巡歷于淮、泰各鹽場躬親踏勘,看得地外高內洼,無從宣泄,而潮水灌入填塞甚易……據兩淮運司判官孫仲科并灶戶管席等稟稱,自鹽城支河一開,將各場運鹽河水盡隨潮泄去,運河斷流,商不來支,鹽日消折,灶益困敝等因……今高堰堤成,黃浦決塞,是上流已斷,則地上干涸已無可泄之水,若復開浚海口,則地形外高,徒引倒灌之潮,且海口既多防御實難,是開私販之門,咸水灌入民田,為害不小,宜乎官灶、士民之告稟者紛紛也。臣至淮安,即與總河都御史潘季馴會議,亦云曾委官踏勘,誠不可開。……不惟可省重費,抑亦可免大患也,伏乞圣裁。”〔62〕對于開挖疏浚高家堰通往鹽城海岸的支河的工程計劃,鹽務官員頗為不滿,因為該計劃一方面會使海水倒灌,淹沒鹽場,也會使得運鹽河水流泄海中;另一方面花費巨大,要由鹽運司支出,造成鹽運司和灶戶的壓力。鹽務當局與總河潘季馴商討,試圖停止開挖疏浚支河的工程。而這樣的訴求,實際上與潘季馴的全淮敵黃,反對分泄淮水的技術政策是相應和的。
曾有官員認為,高郵、寶應、鹽城一帶水患多是由于從鹽場出海的幾條河道湮滅造成泄水不暢引起的,如總漕萬恭稱:“高、寶諸湖今建平水閘,俱引支流入射陽湖,注于海,正道也,而鹽城范公堤有入海五道,今堙其四,下流不疏,此高、寶、興、鹽之多水患乎。”〔63〕由此也有即使從鹽場利益考慮也應該開淮河支流入海的呼聲。但潘季馴將高家堰加高后,興化、鹽城等地積水干涸,鹽業水利需求有所變化:“興、鹽等處入海支河,原因高堰未筑,黃浦、八淺等決未塞,水勢浩蕩,故踵襲節年舊議,欲加挑浚,以泄積水,近勘得高堰筑完,黃浦、八淺俱塞,下流已干,無水可泄,而海口之水反高于內地,若復挑浚則海水灌入,既傷民田,復損鹽利,正在勘議,間隨該巡鹽御史姜璧躬親踏勘,題請免浚……其開挑興、鹽支河工費銀二萬五千八百七十六兩,原議于巡鹽衙門動支,運司銀兩仍聽該衙門作正支銷。”〔64〕原來在高家堰加高之前,興化、鹽城地區存在淮河入海支河,歷年都要疏浚以宣泄洪水,而且工程經費從巡鹽御史經費來出。章潢也指出繼續開興化、鹽城一帶支河是“妄舉以滋無益之費”。〔65〕高家堰加高之后支河水干涸,水位低于海面,海水倒灌反而影響鹽場生產和附近農田,經過潘季馴和巡鹽御史共同奏請取消了支河疏浚工程,減少了鹽政經費的支出,也保護了沿海鹽場的利益。鹽政衙門的經費支出由于高家堰的加高得以減省,潘季馴用鹽業利益的保障為自己的技術政策作支持,潘季馴與巡鹽御史相配合,由此,其技術政策得到朝廷的認可。
除了加高洪澤湖高家堰,高郵湖與漕河水利問題也與鹽業有關:“伏秋霪澇,與天長、六合諸山之水陡共注于(高郵)湖,止憑儀二閘宣泄不及,查得州灣頭原有運鹽官河一道,內由芒稻、白塔二河直達大江,勢甚通便,年久淤淺,先年刑部侍郎王恕曾議挑浚,計長三百四十里,道里遼遠,工費不貲,且議者又謂私販船只潛度難防,遂致中寢,殊不知……若從壩口密布樁柵,就令白塔巡司防守,自可禁絕,其余月分任從照舊筑壩,實為兩利而無害也,但慮錢糧不敷,今止議先從灣頭浚起,至泰州南門止計長九十七里,挑深四尺,面闊四丈,底闊二丈,并打壩合用夫工銀一萬零八百兩,相應于巡鹽衙門挑河銀內動支。”〔66〕六合、天長等地的雨水、山洪,本來并不排入漕河、高郵湖,有入江的河道,但長期淤淺,得不到疏浚,因為河道是運鹽官河。巡鹽衙門一方面為了防止私鹽販偷運,故意防堵閘壩不泄水,另一方面鹽運河道的疏浚工程要由巡鹽御史衙門出資完成,工程量巨大,所以巡鹽衙門有難色。潘季馴為了防止洪水排出高寶湖,增大運河以東的防洪壓力,也充分考慮鹽政的利益,提出防私鹽船不必封堵河道,只需要立木樁于河道中就可以阻止船只航行,且不影響泄水。同時針對鹽務系統持有的工程量過大的憂慮,潘季馴只對河道最關鍵的部分進行疏浚,減少了巡鹽衙門的支出壓力。
在基本完成“蓄清刷黃”的工程之后,潘季馴提出后續的工程維護經費的保障問題:“往年凡遇挑河等役每引帶鹽征銀以濟工用,議將淮南北共九十萬引,每引許商人帶鹽六斤赴掣,每斤征銀五厘,并隨余鹽銀兩上納,另項貯庫計每年帶征銀二萬七千兩以濟墾田之費……委應征解河工備用。隨該臣等會同巡鹽御史姜璧面議,得行鹽地方有限,若仍照原議墾田之費每年征銀二萬七千兩,或有未便,合無行令兩淮運司自萬歷九年為始,每引止帶鹽四斤每斤征銀五厘計,每年止帶征銀一萬八千兩,解淮安府貯庫,聽兩河修之用,俟積貯稍裕,又行停征,數年若支用匱,仍舊征貯,夫銀以挑河為名,今自儀真至邳徐一帶行鹽之河既于河臣任之,則此項銀兩亦系應撥之數。”其建議得到批準。〔67〕潘季馴回顧了以往的鹽引銷售時帶征河工經費的慣例,但在與巡鹽御史姜璧商議后,巡鹽御史認為帶征量過多,潘季馴也認為應該減少鹽引帶征量為四斤,以減輕鹽商負擔。說明潘季馴充分考慮了鹽商的困難,從長久穩固的提供河工經費的角度出發,既強調鹽商行鹽之河即河工管理之河,用鹽商繳納經費供給河工的正當性,同時也充分考慮了巡鹽和鹽商的利益,不給予他們太大的負擔。
萬歷二十年初,因明祖陵被淹,對加高高家堰的質疑之聲和分流淮河水的呼聲再次高漲:“有謂由傳寧湖合開之六合入江者,有謂浚施家溝、周家橋入高寶諸湖者,有謂施張福堤以廣泄淮之口者,又有謂開壽州瓦埠河以分上流之水者,總督漕運巡撫鳳陽周寀、陳于陛,巡按御史高舉合疏,上聞工部覆請咨行河漕撫按勘議,河道都御史潘季馴謂祖陵切近王氣攸關,與三省議,左俱下工部,尚書曾同亨以為河臣閱歷多年,宜悉河事,而撫按二臣又謂周家橋在祖陵后百里之外,主千疏浚,查先年緊急河工例,遣科臣往勘。”〔68〕這時有的觀點認為應該開淮河河道入江,有的認為應該分流洪澤湖水,有的則認為應該在淮河上游分流淮河水量,但不論哪一種觀點都反對潘季馴既有的全淮水“蓄清刷黃”策略。結果:“季馴謂祖陵王氣不宜輕泄,而巡撫周寀、陳于陛、巡按高舉謂周家橋在祖陵后百里,可疏浚,議不合。都給事中楊其休請允季馴去。歸三年卒,年七十五。”〔69〕潘季馴仍然試圖反對在高家堰周家橋處開口泄洪,但以失敗告終。潘季馴因此被罷職:“淮水漫泗州城,浸祖陵樹木,事聞,上震怒,為譴罷督河大臣。”〔70〕在此之后,明代后期治河的特點,正如前人研究所總結的,既要繼續保持漕運的暢通,也要保護明祖陵不受侵犯,這就使治河工作更加錯綜復雜,陷于十分被動的境地。〔71〕
四、潘季馴去職之后的水利與兩淮鹽業衰落
周家橋(周橋)位于高家堰東部,在此分流的流向是向東的,鹽政官員對于周家橋來水素來忌憚。萬歷十三年為此修成了弘濟堤:“寶應有氾光湖,素稱重險,國初平江伯瑄筑石堤于湖之東蓄水,以為運道,上有所受,而下無所宣,因決為八淺,匯為八潭,則興、鹽諸場皆沒,而淮水又間從周家橋漫入,洶涌排空。萬歷十年一日而斃者千人,十二年糧艘溺者數十,總漕李世達、按臣馬永登、鹽臣蔡時鼎議于石堤之東開越河以避其險,乃命工科給事中馮露往視之河身長一千七百七十六丈,凡為石閘二、減水閘三,為堤九千二百四十丈,石堤三千三十六丈,子堤五千三百九十丈,費公帑二十余萬,民不知役,總河王廷瞻以聞,賜名弘濟。”〔72〕可見,在正式開口周家橋宣泄洪澤湖之前,周家橋也偶然有過漫出洪水,對寶應一帶的漕運沖擊極大,沿海鹽場也都受到水災,總漕、巡鹽為此花費二十余萬兩修建了堤防系統,如果周家橋長期泄洪成流,淮河水必然使得運河以東地區難以承受。正如當時官員評論:“高堰勢高,淮水陡下,疾若建瓴……淮南一線之堤潰如破竹,高、寶、興、鹽之民求為魚鱉不可得矣,其為運道民生之患可勝言哉……今周橋、武墩、高澗,即所稱高堰也,武墩、周橋列于首尾,高澗當其中,開此三處即拆高堰無異也。”〔73〕所以鹽務利益者必然反對開周家橋來泄洪。
潘季馴去職后,總漕陳于陛再提向高家堰之東分流泄洪。對此意見,巡鹽御史王明奏稱:“目睹淮為泗患,撫臺陳于陛欲開周家橋以疏之,使遂開則六州縣生靈為魚,四百萬漕糧俱梗,而三十六鹽場亦沼矣。”〔74〕經過王明的奏議,明神宗表示:“河道眾論紛持,張貞觀著先勘泗州,其余河患仍與地方官詣勘,務圖永利,毋徒目前塞責。”〔75〕可見,即便是潘季馴去職,兩淮鹽課仍是明神宗難以割舍的財政利益,在其極其重視的明祖陵被淹問題上,神宗也為是否完全推翻之前潘季馴的技術政策而躊躇。工部對于巡鹽的利益訴求,也不能不考慮。遭到巡鹽王明反對后,總漕陳于陛也倍感壓力,提出辭呈。為此工部向神宗建言道:“會勘河工,于陛與總河尚書舒應龍俱屬首事大臣,以國事為急,豈可因言求退,以負任使,宜命與鹽臣虛心共濟,無拘小嫌,從之。”〔76〕這是工部、皇帝試圖調和巡鹽與總漕圍繞河工方案爭議,要綜合包括鹽政在內的各方利益來進行考慮的表現。
連年參與黃河治理,對于鹽政系統的經濟壓力較大,早在萬歷十四年巡鹽御史陳遇文就奏稱:“淮鹽額地既減,額課如故,邊引積至百萬,堆壅至三年,每歲余銀六十萬兩預征借觧,商人受困……又議漕、河大臣題,自萬歷九年為始,每歲于鹽單內,每引四斤,共征銀一萬八千兩,并課稅銀三千兩,河道銀九千兩,共銀三萬兩,以為河道歲修之用,節年因掣鹽缺額,難以取盈,致借運司開荒銀三萬二千一百余兩,正鹽逾壅。欲將加帶鹽銀一萬八千兩停征,仍余銀一萬二千兩,將徐、呂二洪逃亡洪夫,及靈璧縣逃亡堤夫銀,徐屬派剩麥銀共三千四十兩二錢,抵作加帶引鹽之數,不足者聽漕、河衙門隨宜取用,倘遇重大工程,比例題留贓罰船稅并漕、糧應用。部覆謂河工、鹽法均系國家重務,似難輕議,徐、呂二洪省剩銀皆系額設備用,難以那移,合行查議,余俱依擬,上從之。”〔77〕萬歷時期的兩淮鹽政已到了多事之秋,除了諸多學者指出過的勢要占窩、鹽引壅滯、商人守支困境等問題之外,引地也在縮減。而要由鹽政支出的漕運、河工水利經費卻不斷地增多,財政捉襟見肘,巡鹽御史希望從其他款項挪用,也沒有得到很積極的回應。在此背景下反對工程量較大的,且對沿海鹽場有負面影響的開支河、分流淮河或洪澤湖工程,是鹽政系統必然的反應。
隆慶、萬歷年間鹽商的負擔不斷加重。遂有官員在給巡鹽御史的信札中表達應減少鹽商的河工支出:“淮鹽額地既不可復,則補偏救敝誠莫如嚴侵越之禁,以消積引,至如河工加帶,本一時權宜遂為成例,省之而無礙于河工,有裨于鹽政,是則可行也。”〔78〕但是,從籌措河工經費角度看的官員、文人,仍然傾向于更大限度征收來自鹽商的經費,如明末有官員稱:“大役一興,為費不貲,誠宜整理鹽法,措置余利以給河工。”〔79〕可見有些官員即便看到鹽政困局,改革鹽政也是以服務河工為目的的。
萬歷三十年,由于河工經費取自鹽商過多,甚至引起了鹽商的群體抗議,戶部尚書趙世卿由此倡導減輕鹽商河工負擔:“兩淮運司鹽商余元俊等愿捐已資,鹽利銀五十萬兩助治河工……此其意不過假獻銀以為名,而蘄得行,其詭計以為奸,或藉此而越奪于鹽利之中,搜求于鹽利之外,或破壞鹽法以自殖,或挾詐地方以求充種種……御史蔣以化為鹽法極敝、商困難支等事之疏至矣……世豈有敲樸之下不能取常盈于正課,而囊槖之潤反能輸資助于河工者?……聚喧既真,則各商之困累必至,其困累既至,則助工之誣妄可知。”〔80〕當時有鹽商突然號稱能捐助五十萬兩白銀服務河工,卻引起了諸多鹽商的抗議。官員由此事引出鹽商普遍已經十分困窘的問題,疏稱當時一般的鹽商盈利已經很困難,能夠獲得五十萬兩厚利是不可能的,號稱能捐助五十萬兩的人實際就是一個騙子,以此試圖利用國家急需河工經費的心理來謀求某些回報的私利,這樣的捐助既不可能是真的,也與其他鹽商經營困難的現狀嚴重不符,故而引起鹽商群體的強烈不滿和相關御史等官員的檢舉揭發。另外,幾乎同時戶部也寫了《鹽法極敝商困難支急救倒懸以圖永利疏》陳述鹽政混亂和鹽商經營困難的問題。〔81〕此假冒捐助河工事件的揭發也說明,本身已經運營困難的鹽商,在河工經費不斷提供的背景下,其經營狀況更是雪上加霜。
潘季馴去職后,又有舒應龍、楊一魁先后繼任。舒應龍以分殺黃河水勢為手段,但實際仍堅持類似潘季馴的全淮敵黃,結果明祖陵仍被水淹,因此被罷官;楊一魁則一方面開了多條支河分減黃河主流讓其分流從淮北入海,另一方面分流高家堰淮河水入運河、芒稻河再入江,治河治淮方略逐漸兩者并舉。〔82〕此后明祖陵的洪水一度消退,但黃河泥沙淤積的速度很快,萬歷二十九年“河身日高,河水日淺,而蕭家口遂決,全河奔潰入淮,勢及陵寢”,但楊一魁堅持分泄黃河水,對堵口態度消極,最終“帝以一魁不塞黃堌口,致沖祖陵”〔83〕為由,罷免了楊一魁,其分黃實踐以失敗告終。此后明朝的治河方略并無明顯的創新,黃河分流入海,以及淮河也分流入海、同時分流入江的局面基本不變。黃河決口、改道、自行分流等情況越來越頻繁,明朝治河基本集中于各地的堵決口工程上,徐州、靈璧、興化、鹽城等各地頻遭水災,漕運也多次被影響,這些情況一直持續到明亡。〔84〕鹽政系統官員減少鹽場水患的愿望也隨之落空。“分黃導淮”不能解決黃河淤決問題,反而打亂了蘇北水系,造成了瀕海農田、鹽場的洪災。〔85〕崇禎六年的泰州當局回憶當地水利:“萬歷二十二年以前,鹽官三年一大開,一歲一撩淺……今則挑浚絕響矣。”〔86〕可見,經過萬歷二十年河工方針變化以后,萬歷二十二年以降泰州鹽官組織的水利工程基本廢弛,必然是水患頻仍的同時鹽政進一步衰敗,既缺乏鹽政官帑也缺乏商捐,再也難以組織起對運鹽河道網的疏浚工程。
關于明代中后期鹽政衰落的諸多原因,如勢要占窩、鹽引壅滯、商人長期守支、正額鹽引外征“浮引”等等,并最終導致明朝在萬歷四十五年開始實施綱法改革,其鹽政變化過程、原因已有諸多前人研究指明。〔87〕筆者對這些前人研究并無反對意見,但是仍想補充的是,鹽政長期為漕運、河工服務,鹽商也長期負擔河工經費,但萬歷二十年以后隨著明祖陵被淹的影響,潘季馴的以加高高家堰和全淮敵黃等主要治河技術的政策被廢止,對鹽商的負擔加重、對鹽業生產造成的影響也很大,水利問題也是明朝兩淮鹽政衰落的重要因素。
五、結語:明代鹽政與黃、淮、運河水利的關系
明前期鹽業發展得益于漕運淮揚運河的疏通,也不斷地為漕運服務,發揮類似漕運的一些功能。鹽政既是歷來漕、河工程的經濟支援者,同時自身也肩負鹽場附近地區龐大運河網的水利維護工作,在自身財力有限的情況下,實際上鹽場附近地區水利也依賴于黃淮、運河水利給自身帶來便利。明中后期隨著黃河治理問題的不斷凸顯,鹽務提供的河工經費越來越多的同時,鹽政利益越來越密切地被裹挾進治水官僚的技術政策爭議中。鹽政本身作為一種重要的國家財政,也利用自身的重要性,在漕、河水利技術政策爭議之中謀求自身的利益。這種利益也成為符合鹽政利益的潘季馴的技術政策成立、持續的重要理由,使得國家在決策技術政策時不得不對鹽務相關問題有所顧忌。
如鹽政官員巡防私鹽與潘季馴巡防盜掘高家堰的需求相配合,制止開放高家堰水閘向東泄洪與保護鹽場的需要相符合,和潘季馴一起反對開支河及大規模疏浚沿海河道與鹽政當局減少鹽業支出的水利工程量的需求相通。即便明祖陵被水淹而不得不從高家堰東南的周家橋泄洪,明朝也一度仍然考慮沿海鹽場的安全,對開閘曾有所猶豫。鹽務支出,不論官帑還是商捐,終究取之于民,或是商人,或是鹽場紳衿,不斷擴大繳納水利經費使得本來就已經弊端重重的兩淮鹽業進一步走向衰落,能夠繼續擴大提供的水利經費也越來越有限,不斷寄希望于潘季馴為代表的加高高家堰、全淮敵黃的技術政策來減少支出。但鹽業也最終隨著潘季馴的技術政策被放棄,進一步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