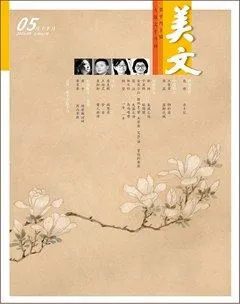失落之詩
船形廢墟
風暴的眸子里
住著永恒平靜的海
活著最大的困境是沒有困境
這是否意味著
漢語在此遭遇了
創傷后應激障礙
無窮的同義詞擠在一起
相互怨懟
無法與任何親愛的分擔陰翳
內心的廢墟持續被時間養育
直到長出絢麗斑斕的毒蘑菇
神的微笑終于在風暴中心降臨
暢飲微雪之時
把話埋在心里就有福了
——龐潔《風暴之眼》(節選)
廢墟作為凝聚在時間琥珀中的記憶載體,穿過歷史風塵,賦予過去以永恒的生命。在面對廢墟時,我們與另一個時空的記憶相連,眼前的空間退轉為過去生活的真實圖景。而置身“廢墟”上感受到的時間,更容易將人拉向歷史的縱深處,也更容易體會到“消逝”美學中的“危險”與“美麗”。
無論是龐貝城內的朱庇特神廟,赫庫蘭尼姆古城,還是廢棄的野長城,大多數遺址已成為人們津津樂道心向往之的知名景區。“我們容易遺忘的過去,構成了我們現在。”記住過去最好的方式,興許是去現場看看。我對“廢墟”有著天然的親近,所以,相比其他風景,我格外鐘情那些殘垣斷壁。不過,我也很少專門刻意地去探尋廢墟,內心也很抗拒被流行的“廢墟美學”過度渲染的對“衰敗”的浪漫化追求。我期待的是一種偶然的邂逅,如同在街角碰到久違的友人,或在午夜夢回聽到已逝的老祖母呼喚我的名字……
因緣際會,當我邁入新疆吐魯番交河故城,映入眼簾的高臺黃土與殘舊的建筑交相輝映,落日熔金,暮云合璧,天地渾然一體。資料介紹,這里是世界上最大最古老、保存最完好的生土建筑城市,也是保存2000多年最完整的都市遺跡。1961年,交河故城被列入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被譽為“世界上最完美的廢墟”;2014年6月22日,交河故城作為中國、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三國聯合申遺的“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中的一處遺址點成功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作為初來乍到者,面對這樣的遺跡產生天然的震撼再自然不過,即便,我對是否存在“最完美”的廢墟始終是存疑的,但即刻我便確認,這絕對是一次最完美的“邂逅”。
交河故城,位于新疆吐魯番市以西13公里處一座島形臺地上,地處牙爾乃孜溝兩條河流交匯而造就的一座河心島上,兩端窄而中間寬,島呈柳葉形半島。從空中俯瞰,更似一艘巨船,遠觀氣定神閑。考古學家李肖在《交河故城的形制布局》一書中詳細介紹了吐魯番交河故城的形制布局和時代分期。這里最早是西域36國之一的“車師前國”的都城,《漢書·西域傳》云:“車師前國,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可見,“交河”之名,根據河水繞城而得。
我從來相信每個人都在冥冥中與自己相關或相近的人或事物靠近,我們沒法刻意締結人和人之間的關系,我們喜歡誰拒絕誰,只能聽憑能量場的驅動,這在社交心理學中被稱作“磁場理論”。而在行走中,我也數次感受到“磁場”,人類總要在行走中確認自己,你與哪些事物有天然的親近感?它們帶給你內心的感動和沖動,是來自生命之初的喚醒,讓你此刻的靜默或沉思,歡喜或落淚都是那么自然。我也無數次在探尋古跡時審視自己的內心,當我們感懷往昔時,我們在感懷什么?
博爾赫斯在他的小說《環形廢墟》中講述了一個魔法師出于意志的決定,從可怕的沼澤死里逃生來到一個中央有石虎或石馬的荒廢的斷壁殘垣的環形廢墟——一座被火焚毀的火神廟宇。魔法師知道這座曾是火神廟宇的廢墟是他不可戰勝的意志所向往的地方,因為他要在這里實現他的“魔幻”——夢創造一個塵世間不曾有過的人。博爾赫斯喜歡“鏡子”這一意象,《環形廢墟》的模式就像兩面互相照射的鏡子,會聚出無窮多個循環的“幻影的幻影”,體現了時間之虛無。博爾赫斯寫道:“外鄉人夢見自己在一個環形階梯劇場中央,劇場和焚毀的廟宇有相似之處:階梯上黑壓壓地坐滿了不聲不響的學生;學生們的臉離現在有幾個世紀,高高掛在云端,但仍清晰可辨。”此刻,我就是交河故城的外鄉人,或者,我只是以外鄉人的身份重返兩千多年前的故鄉。那么,交河故城,你愿意接納我這個異鄉人唐突的造訪么。
我身處在一座船形廢墟中,匯聚在此的兩條河流也如鏡子般互相照射,歷史與此刻同在,亦真亦幻,作為非虛構愛好者,我并不想創造一個塵世間不曾有過的人,每一處夯土遺跡都在提醒我,遠處的駝鈴聲、裊裊的炊煙、先人的歌哭、戰爭的硝煙都在殘陽中述說往昔。現在的交河故城,是一只廢棄的銹跡斑斑的舊船,渡盡劫波,停靠在歷史的岸邊,成為一首無聲的詩、一尊靜穆的雕塑。
走著走著,我已落下隊伍很遠,周圍竟然一個人都沒有,斑駁的光拉長自己的影子,故城的建筑錯落有致,蒼涼渾厚,靜謐如油畫。我拿出手機,拍下了自己在這座失落之城上留下的影子,眼睛竟然有些濕潤了。“今我”“故我”相遇此刻,而未來的那個我,也在更遙遠的前方等候。米沃什熟悉的詩句再次涌上心頭:
這世上沒有一樣東西我想占有
我知道沒有一個人值得我羨慕
任何我曾遭受的不幸,我都已忘記
想到故我今我同為一人并不使我難為情
當我“直起腰來”,我望見藍色的天空與不同色調的金黃徐徐展開,有的耀眼有的黯淡。遇見廢墟上的落日,也是此次吐魯番之行最珍貴的時刻。太陽一點點地下沉,遙遠的蒼穹因這即將褪去的一抹余暉而顯得愈加生動壯闊,遠處的金黃漸次變為鐵銹。此時方感知到“獨愴然而涕下”的意境,這首詩絕非以往被解讀的“詩人生不逢時的哀嘆”,我相信陳子昂在幽州臺的那一瞬是獲得了釋然與超脫的,在“哀嘆”之余,他看見并理解了自己的“孤獨”,俯仰古今,與天地悠悠的“大孤獨”相比,個人的際遇悲歡微不足道,壯志未酬也算不得遺憾,詩人獨自面對無窮,這孤獨空曠而豐盈。
“廢墟”——人類共同的歸途,那么,何必刻意去渲染其衰敗,正如我們無需粉飾自己的生活,也不懼未來,坦然地走好腳下的每一步,即是對自我與歷史的尊重。
時間之殤
如今這世界
被無數的我們發明出新的命運
問題和答案都匹配得嚴絲合縫
人們談論天氣
也如祭祀儀式般循規蹈矩
慘白的詩行叫人羞愧
有人假裝逝去
而你假裝活著
黑夜撕開一道口子
雙眼如同獲取嶄新的視力
思緒在此緊急迫降
片刻的欣悅
如荒冢上的野花被喚醒
歷史和荒野自此都銘刻在心里
——龐潔《荒野中的冥想》(節選)
用來加速歷史消亡的武器,有時是戰亂,有時則是語言。史書里言辭的慣性,往往帶著枷鎖,撥開歷史煙塵,一些從溢美中墜落,還有一些如荊棘植物的根莖,盤在泥土里,骨骼般若隱若現。就像這遺址,清風拂過時,便回到了多年前的殺戮場。
今天,吐魯番最引人矚目的就是地處絲綢之路東西方文明的交匯之地。源于交通樞紐地位的地緣優勢成了吐魯番人招商引資的一張王牌。而那首由瞿琮作詞、施光南譜曲的《吐魯番的葡萄熟了》更是傳唱大江南北,令人無不向往。這是中國海拔最低的盆地,夏日驕陽炙烤,空氣仿佛在凝滯燃燒,難怪古稱“火洲”,而火焰山溝谷中的葡萄溝,卻是綠意盎然,田疇沃野。
但在兩千多年前,這份詩意和繁盛被戰火和血腥所籠罩。交河故城的位置正當絲綢之路要沖,“自車師前王廷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北道西逾蔥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班固《漢書·西域傳》),由交河出發往西,可沿天山南麓,經焉耆、龜茲、疏勒,是西漢絲綢之路的北道(即東漢及以后的中道)的重要節點;由此往北,可沿天山北麓,去往烏孫等地。漢朝要維護絲綢之路的暢通,鞏固在西域的地位,就必須保證對車師的控制。而對匈奴而言,車師國所在的區域土地肥美,被漢朝占領了,必然大大增強漢朝在西域的實力,因此不可不爭。這就是《資治通鑒》卷二十五中匈奴人所說的:“車師地肥美,近匈奴,使漢得之,多田積谷,必害人國,不可不爭。”兩大強國皆虎視眈眈,志在必得,其結果就是展開了一場西域最激烈和曠日持久的爭奪戰爭——五爭車師。
爭奪絲綢之路北道咽喉要地的戰爭成了車師人揮之不去的夢魘。王侯貴族、庶民百姓,無不在漢匈爭奪的戰亂中流離失所,生靈涂炭。漢匈對于車師之爭奪,始于漢武帝時期。公元前99年,漢武帝派兵攻打車師,匈奴以數萬大軍來救,最終,漢軍因寡不敵眾,被迫撤離,第一次爭車師便以漢朝的失敗告終。公元前89年和公元前72年,在第二次和第三次爭奪車師的戰爭中,漢朝得勝,車師臣服于漢朝。然而,在漢朝退兵之后,又重新被匈奴控制。公元前68年,漢宣帝派侍郎鄭吉攻打車師,鄭吉一舉奪下車師,并且在此屯田。但匈奴并不甘心就這樣失去車師,在此后的七年間,匈奴多次派兵攻打車師,鄭吉率領著1500名屯田兵屯駐交河城,面對地勢險要,建筑堅固的交河城,數萬匈奴士兵屢攻不下,數次敗走。公元前62年,漢朝正式設立戊己校尉,負責在車師進行屯田。兩年后,匈奴內亂,匈奴的日逐王歸附漢朝,漢朝終于控制了西域,車師也被漢宣帝正式分為兩個部分,即車師前國和車師后國,交河從此成了車師前國的王城。從張騫到鄭吉,經過了數代人近八十年的努力,至此,西域正式納入了漢朝的版圖之中。
這座古絲路上最繁華的城市人去樓空近千年,沒有人知道,車師人為了保衛家園如何在暗夜中疾走,考古學家興許也并不關心,那殘破的陶罐上婦女渾濁的眼神,有什么意味。如同所有偉大的遺跡,人類最早的愛恨、最遠古的詩意與悲情,是不是也在這里?唐代李頎《古從軍行》寫道:“白日登山望烽火,黃昏飲馬傍交河。”岑參詩云:“交河城邊飛鳥絕,輪臺路上馬蹄滑。”從這些詩句中,我們能感受到戍邊的艱辛與邊陲的硝煙。
經歷了腥風血雨的洗禮,兩千多年后,今天的游人也如雕塑一般久久地駐足,若干年后后世的考古學家會說:“瞧,這可是ChatGPT時代的人!”是的,現存可考的朋友圈里,充滿了現代人對歲月的追憶緬懷,對未知的惶惑憧憬,互聯網上爆款詞條批量生產,人們的合影中V形手勢志在必得。然而,這些并不能稱之為“遺址”。
失落之詩
而不完美在人們內部是如此焦灼
流水線依舊喑啞
在一個尚未被創造的夜晚
多數人孜孜不倦修復著
對生活無能為力的部分
最后,你在我內心建造的城邦
還沒有化作殘垣斷壁
謙卑日復一日庇護著我
直到時間墮入深淵
——龐潔《博物館之夜》(節選)
藝術史家巫鴻教授提到中文里表達廢墟的最早語匯是“丘”,本義為自然形成的土墩或小丘,也指鄉村、城鎮或國都的遺址。“丘”表達了傳統中國文化中對“往昔”的視覺感受和審美,以此來對照交河故城,再貼切不過。隨處可見生土夯筑的民居院落、殘破的土丘,在這時光雕琢的迷宮之中,呈現出無盡的幽思。而這片廢墟呈現出的幾何美學,也吸引著無數的攝影師和藝術家前來探究。
交河故城在歷經數千年的風雨滄桑之后,整座城池的建筑布局依然奇跡般地保存下來。無不得益于吐魯番得天獨厚的干燥少雨氣候。交河故城的建筑全部由夯土版筑而成,形制布局則與唐代長安城相仿。城內市井、官署、佛寺、佛塔、街巷,以及作坊、民居、演兵場、藏兵壕、寺院佛龕中的泥菩薩都還有殘存的痕跡。古城四央臨崖,在東、西、南側的懸崖峭壁上劈崖而建三座城門,因而交河故城也是一座雕刻在崖體上、沒有城墻的城。交河城址在維吾爾語中稱“雅爾果勒闊拉”,意為“崖兒城”。
《西游記》第四十五回寫道,虎力、鹿力、羊力三個大仙兒因為幫助車遲國解脫旱魃,深受車遲國王敬重,被奉為“國師”,在全國獨尊道教,把眾佛教徒驅服,為道教做苦役。佛教徒大多被虐死。唐僧師徒西行到達車遲國,見五百佛教徒被道眾暴力驅使,鬼哭狼嚎。三怪與唐僧師徒斗法,最終慘敗身亡。這個國家其實在歷史上確有原型,這就是車師國,但歷史上的車師國并不像《西游記》里那樣不待見佛家弟子,相反,對佛教可謂推崇備至,在交河故城西南有多達五十幾處佛教寺院遺址,有并列的洞窟7座,窟內尚存壁畫和回鶻文題記,是一座名副其實的佛城。
交河故城曾出土不少文物,如唐代蓮花瓦當、蓮花經卷等。1994年考古工作者在故城保護性發掘中,首次發現一座地下寺院和車師國貴族墓葬,并出土海珠、舍利子等一批珍貴文物。在交河城外,也就是河床外還發現有數千座南北朝至隋唐古墓群、數百座懸在崖體上的崖墓、溝西雅爾湖石窟群、鹽山大型石窟群等。最令人驚嘆的是,建筑形式除了沒有城墻外,整座城大部分建筑物不論大小基本上是用“減地留墻”法,從高聳的臺表向下挖出。寺院、官署、城門、民舍的墻體基本為生土墻,特別是街巷,狹長而幽深,像蜿蜒曲折的戰壕。人行墻外,像處于壕中,無法窺知城垣內情,墻內則居高臨下,控制內外動向,城中布防,極為嚴密。其建筑工藝之獨特,在世界古建筑史上也是獨樹一幟。這樣彰顯古代勞動人民智慧與創造力的建筑,實在不需要用“中國的龐貝”這樣的稱呼來為其增添“流量”,你遠觀或者走近,它一直就在這里,不悲不喜。
踩著腳下的黃土,我們所習慣的現代世界似乎遠離,廢墟是一條分割線,歷史的創口在此揭開。巫鴻在其力作《廢墟的故事》引用英國學者的文字:
“理想”的廢墟必須具有宏偉的外形以便顯示昔日的輝煌,但同時也要經歷足夠的殘損以表明輝煌已逝。既要有宏偉的外貌以顯示征服之不易,也需要破敗到讓后人為昔日的征服者唏噓感嘆。廢墟彰顯了歷史不朽的痕跡和不滅的輝煌的永恒,也凸示了當下的易逝和所有現世榮耀的曇花一現。所以廢墟能喚起的情感既可能是民族的自豪,也可是憂郁和傷感,甚至是烏托邦式的雄心壯志。
好吧,它們頹敗,也因頹敗而真實,當荒草覆蓋風化的城池,當炮臺開始坍塌。你會發現時間刻下的痕跡,那也是廢墟最動人心魄的地方。其形式之美與暗含退化、丟棄和沒落的“不安”之間的牽絆,也來源于美學內涵與倫理之間的拉扯,更是迅疾如流的現代化進程與遺忘之間的拉扯。
美國著名漢學家、哈佛大學教授宇文所安提出“(文明)所以能永遠延續發展下去,最重要的是因為它的結構來自它自身”。“回憶”與“被回憶”這一關于文明連續性的永恒主題,幾乎隱匿在大多數的中國古典文學作品里,中國的山川勝跡也正是在被回憶與追憶的過程中被賦予了人文景觀的特質。宇文所安在《追憶: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往事再現》全書都在回應著“無”的問題,宇文所安對此簡直憂心忡忡,他說:“從土臺上或許還看得出宮殿廢墟的大體模樣,在布滿龜紋的石塊上或許還勉強能辨認出上面的碑文。時間湮沒了許多東西,磨蝕掉細節,改變了事物的面貌。除了那些知道該如何去找尋它們的人之外,對其他人來說,‘以前的東西變得看不見了。正是那種按照某種一定方式來看待世界的意向,承擔著我們同過去的聯系的全部分量。”
這句結論似乎很悲傷,聯想到《尋夢環游記》中對于死亡的判定:“當最后一個記得你的人,把你忘記,那么你也就徹底從這個世界消失了。”當最后一個知道怎么去揭開空無或者空無的象征物——比如石碑、比如坍塌的高臺——背后暗含的歷史時,這處古跡和發生于此的人事代謝就將永遠消失。
在先人最初的吟唱《詩經·黍離》中,我們已感受過故國之思。“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這首詩作為最早的懷古詩實際上是把那片禾黍覆蓋之地指認為“墟”,也就是“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
人類如此害怕消亡,既有對肉體、身份、名望隕滅的恐懼,比這更殘酷的,當然是記憶的消逝,還有對宇宙萬物敬畏中產生的令人戰栗的謙卑。人的強大其實恰好是在認識自己的“弱小”中確立的。人們在中華文明的源頭即衍生出永恒的萬古愁,而這萬古愁,正是古今生活與情感的對接,不同文明之間的交融。人類正是憑這永恒的萬古愁,在城池銷毀、肉體消亡后,在炙手可熱的“元宇宙”神話被解構后,依然恒定地將破碎的歷史從精神上賡續為一條綿延不絕的長河,賦予了歷史之中的人所能夠煥發出的尊嚴,這條尊嚴的時間長河中,浮現著失落之城與失落之詩。
廢墟昭示著滄桑,見證歷史興衰。但它給人更大的啟示,是祛魅。“歷史的祛魅”過程,實質上是歷史從神圣化走向世俗化、從神秘主義走向理性主義的過程。對于普通人而言,你了解那些梟雄豪杰也是平常肉身,即便站在高處也無需虛張聲勢。幾千年時光悠悠流轉,無論是王侯將相,抑或英雄才子,俱都化作煙塵。而深入骨髓的家國情懷卻如一條綿綿不休的河流,始終流淌在每一個文人士子的筆底心頭,流淌在每一個炎黃子孫的血脈中,氤氳在中華大地每一寸山河間,成為國人不滅的精神圖騰。
廢墟是過程,人生就是從舊的廢墟出發,走向新的廢墟。在可知與不可知之間,廢墟內部升華出“詩”,廢墟和詩一樣,不接受瑣碎與平庸,它們必須具備獨特辨識度的語言系統,創造出原本不屬于日常生活里可以擁有的貴金屬的色澤。“故城”或“遺址”只是被歷史中斷的修辭,如同我們珍貴的母語,它的衰敗,也是“詩”的失落,需要后人用虔敬之心擦亮。我們的先輩曾在那里歷經人世險阻,當我們回到滿目瘡痍、浩渺寥廓的歷史現場中,我們的活著與死亡也成為其中的一部分。
(責任編輯:李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