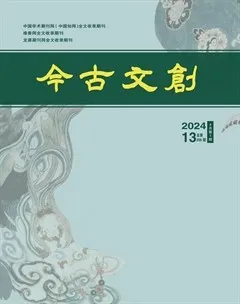黃宗羲君主論研究
【摘要】黃宗羲通過對君主起源、職能、君臣關系進行重新定位以及對人性的探討,建構起了其獨特的君主論。君主源于“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興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但是在人各自私利的情況下又有人出而治天下,這其中涉及人性的探討潛在的貫通在黃宗羲君主論建構里。黃宗羲的君主論既是對君主專制的一種理想型的糾偏,亦是黃宗羲基于兩朝經歷的一種突破性的政治暢想,而其對于人性的形而上的思考亦能反映理學在明末清初的一個發展向度。
【關鍵詞】黃宗羲;君主論;人性;自私自利;圣王之治
【中圖分類號】K256?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4)13-0066-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13.019
黃宗羲一生經歷了明末專制集權下朝廷是非不明、閹黨把持朝政的黑暗統治,目睹了明朝的滅亡,經歷過抗清復明的失敗,以致后來對整個封建君主專制集權產生了懷疑和否定,毅然建構起批判封建君主專制的思想。本文意圖通過黃宗羲的相關著作為依托,分析黃宗羲的君主論思想,試圖呈現黃宗羲君主起源、職能、君主起源背后的人性立論依據等觀點,在理論上梳理黃宗羲君主論和其人性論的一貫性關系。
一、黃宗羲對君權起源、君主職分及君臣關系的厘定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興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釋其害”[1]2。在最初的人類社會形態下,每個人都只著眼于自己的私利,無暇顧及其他。天下的公利沒有人去振興,公害也沒有人去消除,長久以往,禍亂窮困就會產生。出于興公利除公害的需要,需要“有人者出”,為天下興利除害,君主即由此產生。
黃宗羲在《孟子師說》說:“天地之生萬物,仁也。帝王之養萬民,仁也。宇宙一團生氣,聚于一人,故天下歸之。”[1]90天以仁生萬物,必不會讓人被私情所蔽,流于自私自利而最終導致禍亂爭奪,所以天生“聚一團生氣”的人為圣為王,使之治理天下,使民皆各得其所,各得其利,萬民也會歸順他,這便是君主的起源。雖然這個君主的合法性最后也是依托于天,但是黃宗羲顯然更偏重其職能設立——即是君主是為了替天下興利除害而設的。
君主的起源決定了君主的職分一定是以天下萬民的公利為中心的。是以黃宗羲說“原夫作君之意,所以治天下也”[1]8;“嗟乎!天之生斯民也,以教養托之于君”[1]11,黃宗羲認為,君主是為教養百姓、為天下興利除害而立的,設立君主的初衷要求君主畢世而經營不怠的應當是天下之事,所以為人君應當比天下千萬之人要勤勞,而又不享其利,故古之人以得天下為不可擺脫的桎梏,恨不得斷臂而去之,認為人君之位“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人人能讓君主之位而不會眷戀。所以“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真正明白君之職分的君主,當知道人主受命于天而明白治亂天下的艱難,必當剝去自己的人情私利而經營天下,行仁義之道以教養天下。古之君王能以教養天下為己任,故能制井田、學校、兵車、封建、喪葬、祭祀、禮樂以養民,其所為之事,所立之法,所養之兵,所制之刑,皆以民之利為出發點。后世君王則與之相反,一切所謂,為己而不為民。
黃宗羲認為,后世之君不明君之職分,導致了一系列后果:一是“以天下而養一人”(《孟子師說》卷六),將君民的關系惡化為相仇、對立的關系;二是將君臣關系惡化為主奴關系,造成君道不明,則君臣同為民之大害的局面;三是“行非法之法”,導致天下大亂;四是其“私”天下的行為讓其他人以為為君就可以享受至上的權力和快樂,故人人都圖之,從而頻繁引發戰亂。此可見,君主是否是一個合格的君主,關鍵在其能夠明白自己的職分,并畢世去經營,究極而言則在于其為己或為民也,為民,乃君之當為也,私己是君之當去也。
鑒于后世主從君臣關系所導致的后果,黃宗羲對君臣關系進行了重新定位。一是打破君主臣從的角色定位。明確君臣皆是為天下而設。《原臣》篇曰“緣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以群工”天下治理任務繁瑣,僅君主一人是完成不了的,所以需要設大臣和君王分治天下,這是臣的來由,側面也說明君、臣的關系是平等的。《置相》篇曰:“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則設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1]8就目的而言,君臣同為天下而設,不存在主從關系,就如張豈之所言:“‘君臣應是共同負擔人民公共‘利害事務的人員”[3]“為臣者輕視斯民于水火,即能輔君而興,從君而亡,其于臣道固未嘗不背也”,為臣者不能解決百姓水火之難,即便能輔佐君王得到天下也是對臣道的一種背離。二是打破君父臣子的綱常。黃宗羲認為“臣不與子并稱”,君臣之間并不是君父臣子的關系。《原臣》篇有言:“君臣之名,從天下而有之者也。吾無天下之責,則吾在君為路人”[1]5,父子是同氣連枝的關系,子得父之精血而生,父對子有生養之恩,所以尊敬愛順是為人子所當為。然而君與臣,一無血親之情,二無侍奉之義,只因治理天下之責聯系在一起,若非為治理天下,則君、臣無甚干系,相互為路人而已,不能擔“父子”之名。臣道非為子之道,君與臣終不能以父與子稱之。
二、黃宗羲君主論的理氣論依據
黃宗羲的“君主論”建構,與其在形而上層面的思考緊密相關。黃宗羲認為“天地間只有一氣充周,生人生物”[1]60“通天地,亙古今,無非一氣而已。氣本一也”。[4]609也就是說,氣是天地萬物得以存在的根本,是萬物之源。氣動靜而有陰陽,黃宗羲說:
氣本一也,而有往來闔辟升降之殊,則分之為動靜,有動靜則不得不分之為陰陽。然此陰陽之動靜也,千條萬條,紛紛轇轕,而卒不克亂。萬古此寒暑,萬古此生長收藏也。[4]609
氣闔辟升降的過程分為動靜,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而陰有陰之動靜,陽又有陽之動靜,這千條萬條的動靜就是氣生物的過程,氣之流行運動而有寒暑交替,春則氣化而生物,冬則消斂而收藏,如此,四時得以行,百物亦得以生,這是氣生物的過程,而無論寒暑消長,皆是一“氣”。氣是變動不居的,要認識這個動的氣只能通過“理”來見氣。黃宗羲對“理”做出了自己的界定,黃宗羲言:“夫所謂理者,氣之流行而不失其則也”[5]511“圣人以升降之不失其序者,名之為理”[6]438。氣不是靜止不動的,但又不是亂動,氣之升降闔辟皆有其條理、秩序,故氣化生萬物而能不亂,黃宗羲把氣的這種升降不失其序稱為“理”,說“理”更偏向對氣之流行而不亂的狀態描述,而言氣更強調天地間只是一團和氣,這也可以對天地之間萬物各自生長而不會混亂做出解釋。黃宗羲認為“理氣是一”的,關于這個“一”,可作兩解,一是理氣是一物兩名,二者是對氣的不同描述;二是理氣統一于一體上,有氣必有理,人由理見氣,理氣不離。關于第一解,黃宗羲有言:
理氣之名,由人而造。自其浮沉升降者而言,則謂之氣;自其浮沉升降不失其則者而言,則謂之理。蓋一物而兩名,非兩物而一體也。[7]1061
也即是說之所以有理、氣兩個稱名,升降沉浮的是氣,而氣升降浮沉而不亂稱為理,理、氣所指稱的是同一個東西。
關于第二種意義也即是說理是氣之理,有氣而有理,并非氣之外另有一個理存在,理是氣流行所表現出來的,所謂:“道理皆從形氣而立,離形無所謂道,離氣無所謂理。”[6]40理依于氣而立,又附于氣而行,從氣的升降變化才能見理之流行,氣流行而不失其條理、秩序便是理,故通常來說理不是單獨存在的,只有氣流行才能見理。理氣二者不離,也可以說氣是偏向動而理偏向靜。氣動而有條理,氣動而生成什么是定了的,理亦是定了的,然氣不動,亦不存在流行而生人生物,人也不可見理,所以理只是氣的流行,沒有離開氣而存在的理,理氣不離。氣聚則理聚,氣散則理散。
“氣”為生萬物之本,氣理是一的,黃宗羲從“氣理是一”推出了“心性是一”。關于氣、理、心、性的關系,黃宗羲是這樣描述的:
天地間只有一氣充周,生人生物。人稟是氣以生,心即氣之靈處,所謂知氣在上也,心體流行,其流行而有條理者,即性也……若有界限于間,流行而不失其序,是即理也。理不可見,見之于氣;性不可見,見之于心,心即氣也。[1]60
氣是“一本”,氣化生物,人物皆稟此氣以遂其生,而人物又各有不同,是為萬殊,而人得氣之靈以為心,《孟子師說》有言:“知者,氣之靈者也。”故人心有知,感于物而動,當惻隱自然惻隱,當羞惡則自然羞惡,這個心體流行出來而不失其序便是性,心為體,性為用,如果心體不流行,我們無以見性,性是心之性,心與性之關系一如氣與理的關系。氣、理、心、性并非四個不同的東西,同是一氣,“心即氣之聚于人者,而性即理之聚于人者”(《明儒學案·師說》),所以在天為氣者,在人為心,在天為理者,在人為性,氣、理是一,心、性是一。
心是動的,性相對來說是靜的,在人這里“其變者喜怒哀樂也,已發未發,一動一靜,循環無端者,心也;其不變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梏之反復萌蘗發見者,性也”[8]22。心是變動的,心自然而然動出的東西是確定的,這個東西就是性。黃宗羲曰“性者生而有之之理,無處無之。如心能思,心之性也;耳能聽,耳之性也;目能視,目之性也”[1]78。性無處不在,無物不有。如理不會失其序一樣,性亦是歷然不能昧的,黃宗羲說:“人受天之氣以生,只有一心而已。而一動一靜,喜怒哀樂,循環無已,當惻隱處自惻隱,千頭萬緒,轇轕紛紜,歷然不能昧者,是即所謂性也。”[9]408-409人心中所有,亦只是一性,有條理而不能昧此性之發見。
三、黃宗羲君主論的人性論依據
人同稟氣之精者,得氣之靈而為心,則人心中所有之性,莫不是一團和氣而無有一惡,黃宗羲是由理善來推性善的,黃宗羲有言“理無不善,氣則交感錯綜,參差不齊,而清濁偏正生焉。性無不善,心則動靜感應,不一而端,而真妄雜焉”[8]23。理本身就是條理粲然無有不善的,而理之具于人而為性,亦無不善,正如黃宗羲所言“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此意周流而無間斷,即未發之喜怒哀樂是也”,是故人性本來是善也。惡是心動出來才有這個區分的。關于惡的來源,黃宗羲是這樣解釋的:
夫不皆善者,是氣之雜糅,而非氣之本然。其本然者,可指之為性,其雜糅者不可以言性也。[8]755
黃宗羲強調,氣動而自然流露出來的才是性,而氣之雜糅則不能算性,氣動而有條理,理是善的,人得理而為性,故而性是善的。性之善就像寒必冬,暑必夏一樣自然;惡之生就像偶爾冬而暑,夏而寒一樣,雖偶有反常,然而萬古冬寒夏暑終是恒常不變的,是故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才是常道。雖氣之本然是善的,然氣在流行過程中,不能無過不及,此無過不及所形成的雜糅偏勝之氣,才是有可能致惡的原因。而大多數的常人由于此雜糅偏勝之氣所成的形質而呈現出善惡交雜的狀態,然其中體未嘗不在,也即是人性未昧也,所以即使氣質有偏,人只要能看到并抓住那個中體,亦能去惡而全其善,人心所有,無非善之性已,惡則是因為有“過不及”。
雖常人有善惡交雜的狀態,然而天生人不是只生常人,圣人得其“中氣”而生,故沒有過、不及之差;常人則是“雜糅偏勝”之氣所化,故而有善惡夾雜之弊。故需要圣而王者,養民教民,所謂“天地生萬物,仁也。帝王之養萬民也,仁也。宇宙一團生氣,聚于一人,故天下歸之,此是常理”[1]90,也就是說天以“仁”生萬物,必不忍萬物墮于“雜糅偏勝之氣”而不可自拔,故誕出集“中氣”而生的圣王來治天下之亂,得天地那一團生氣者,當圣而王之,天下萬民自然盡歸于其下,教養萬民是君王之責。在理想的狀態下,天生圣王而治天下,君王的合法性是天來保證的,但是黃宗羲限定了前提,必須是得天地中氣而能治天下者,才是當君王,得天地之“中氣”圣而王者去治理天下,這便是黃宗羲理想的圣王之治。
總之,黃宗羲的君主論是基于肯認人性善的潛在前提下建構起來的。黃宗羲的君主論對封建君主專制的批判其實是基于對三代以后君主專制高度集中、高度發展導致的系列問題、弊端的一種試圖性的糾正,不管是他對君主起源、職分、君臣關系、天下之法等等的重新界定,還是他對后世君主振聾發聵的批判,他都并沒有突破君主制度的樊籠,而是基于肯認君主制的前提下對封建君主專制的一種改良和糾偏,意圖把導致后世君主私天下的“私”欲去掉。黃宗羲君主的立論起源是因為人有“私”的部分,人人“私”則沒人去興公利,除公害。他所闡述的有生之初的“自私自利”更偏向一種原初社會狀態的描述,“是人類產生初期的社會狀況的一種概括”[2]163也即是一種“中性”的描述,在原始的社會形態下,人人自私自利,但是這個自私自利是出于一種生存本能的需要,并未造成什么禍害公共利益的后果(這個黃宗羲也并未提及),只不過是這種自私自利的狀態下,天下公利無人興,天下公害無人除,但是并不意味著這種自私自利就是非正當的、不合理的,反而是應該得到保障的。而事實上,在黃宗羲君主論的闡述中,他也寄希望于圣王,渴望或者暢想圣王之治,但是他也不把全部的希望放在不知何時才會出現的“圣王”身上,而是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和治法對在君王之位但是沒有“圣王”之德的人君進行制約和框束,期望能最大限度內保證君主是為天下萬民興利除害而服務,這也是黃宗羲對中國傳統賢能政治的一種突破。
參考文獻
[1]黃宗羲.黃宗羲全集:第一冊[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2]張豈之.論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J].人文雜志,1980,(02).
[3]黃宗羲.黃宗羲全集:第三冊[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4]黃宗羲著,沈芝盈點校.明儒學案:卷二十二[M].北京:中華書局,2008.
[5]黃宗羲.黃梨洲文集[M].北京:中華書局,2009.
[6]黃宗羲著,沈芝盈點校.明儒學案:卷四十四[M].北京:中華書局,2008.
[7]黃宗羲.黃宗羲全集:第七冊[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8]黃宗羲.黃宗羲全集:第八冊[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9]張師偉.民本的極限——黃宗羲政治思想新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作者簡介:
陳文藝,女,貴州畢節人,寶雞文理學院政法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宋明理學與清代儒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