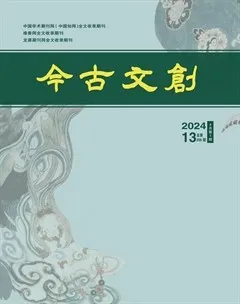康復中的救贖
金許珂
【摘要】《康復的家庭》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隨筆集。該書講述殘疾兒大江光為中心的日常生活,既表現了家庭成員對殘疾兒的接受過程,同時也探討殘疾兒對社會的接受。家庭成員們在相處過程中漸漸“康復”,互相接受,互相救贖,與“殘疾兒”達成和諧共生。
【關鍵詞】《康復的家庭》;“殘疾兒”書寫;接受;救贖
【中圖分類號】I107?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4)13-0025-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13.008
大江健三郎(以下簡稱“大江”)作為日本文壇巨擘,其多數作品以殘疾兒大江光(以下簡稱“光”)為原型,描繪了殘疾兒的生活、心理等各方面形象。同樣,《康復的家庭》作為大江以家庭為背景創作的隨筆,延續了其一貫的創作主題,從與殘疾兒光的日常生活入手,講述了在與殘疾兒的相處過程,家人們漸漸“康復”,探討了殘疾兒的生活問題,引申出與殘疾兒(人)和諧共生的理性思考。
“如何表現我這個殘疾兒子?如何解讀在實際創作的過程中,殘疾兒童與家人的共同生活?”這是大江文學中的雙重文學主題。相較于《萬延元年的足球隊》《個性的體驗》等小說,《康復的家庭》以散文的形式,通過簡單、溫暖而樸素的內容來展現上述主題。文中大江不光談到了悉心照料孩子的父母、身患疾病的岳母、體恤兄長的弟弟和妹妹等家人的生活,還講述了醫生森安信雄、專門研究X光射線治療的重藤博士、恩師渡邊一夫等人的故事,從生活、藝術、教育、文學等多方面展現對殘疾兒的心理變化,以及殘疾兒和家人共同的“康復”過程,完成與殘疾兒的互相救贖。
一、《康復的家庭》中的殘疾兒書寫
當殘疾兒光出生時,正值“青年人的自我存在危機”的大江仿佛被“擊中中心”。光出生時腦部發育不完全,做了畸形矯正手術后,又出現了癲癇病等新的癥狀。這給作者及家人帶來了巨大的麻煩,如同巨石“重重壓在了身上”。
光的殘疾表現在智力發育遲緩,認識能力不完全,無法將自己的想要表達的意思通過語言順利地表達出來。《康復的家庭》中如此描述他的癥狀:“他常常莫名其妙地突然站住不動了,甚至會徑直朝著自己想去的地方走”,或是由于發燒而“滿臉通紅,呼吸急促”,或是讓奶奶“好好地死”。諸如此類行為給家人帶來不少麻煩。為了照顧殘疾兒,大江需要在創作之余按時接送光去福利機構、在其發病時悉心照顧、在出現矛盾時耐心調節。而作為殘疾兒,光也表現出“祈求盡快從肉體的痛苦和精神的不安中擺脫出來的情緒”。毋庸置疑,殘疾既給家庭帶來壓力,又給患者本身帶來痛苦。
上田敏將人罹患疾病的過程分為:沖擊期、否認期、混亂期、解決期、接受期。大江認同上田的理論,并坦言自己的作品與“接納殘疾的理論”有重合之處。作為殘疾兒的家屬,大江認為比起殘疾兒,家屬體驗這五個階段更為明顯。以殘疾兒父親及作家的雙重身份,大江表現出家庭和殘疾兒童在“沖擊期”“否認期”“混亂期”中的痛苦:得知第一個孩子為先天殘疾的初期,年輕的父親苦惱不已卻抱著一絲治愈的希望,但當面對無法康復的事實之后就變得絕望而選擇逃避。在與殘疾兒的生活中,殘疾兒本人及家人共同經歷了遭受疾病沖擊的茫然,到對殘疾產生心理防衛的否認,再到無法否定殘疾不能痊愈的抑郁悲傷。
但殘疾帶來的并不只有痛苦。在《康復的家庭》中,大江發現其“對音樂具有敏銳天賦”:在三歲時,光便能辨認貝多芬、肖邦等音樂家地樂曲;在林中聽到鳥叫時,準確辨認鳥的種類;在小學畢業時,創作了《畢業》;在進入殘疾兒同學校高級班之后創作了《青鳥進行曲》。此外,光會在和父親鬧矛盾時依舊牽著父親的手,能體會到他人的情緒,還會激勵家人們積極生活。因此,通過描述家庭的日常生活,表現因家庭成員中存在殘疾的情況每個人的心路歷程,大江感受到在痛苦之外“殘疾兒童給父母帶來了極大的快樂”,這恰好印證大江的創作《康復的家庭》時的初衷,即表現每個人——包括其家人,從生病到康復的整個過程中所伴隨的真正的喜悅、成長和人格的完成。
二、大江對殘疾兒的接受
殘疾兒光的降生對父親大江來說無疑是一樁災難,面對一個畸形的兒子,他體驗了無助、恍惚、痛苦乃至絕望等一系列消極感受,但這也成了其用心靈去感受生命本質的契機,由此大江創作了《個人的體驗》《萬延元年的足球隊》等以“殘疾兒”為原點的作品。而《康復的家庭》是一部隨筆集,包括了在和光共同生活的三十多年的點滴,作品展現了大江逐漸接受了“殘疾兒”這一殘酷現實,并在文中多次提到“治療”“康復”“接受”等詞匯,這恰好反映大江在經歷“沖擊期”“否認期”“混亂期”后到達了“解決期”和“接受期”階段的心理變化,即從起初的痛苦絕望到接受并積極面對生活的態度的轉變。
《康復的家庭》中收錄著一篇題目為“沒辦法,干吧!”隨筆,而“沒辦法,干吧”這句話完美展現了大江從痛苦到接受的轉變的心路歷程。這句話看上去普通且直白,不似壯志豪言,卻是大江念念不忘且常掛嘴邊的人生格言,深含著大江在和殘疾兒的生活中感悟出的質樸人生智慧。表面上,“沒法子”展現出的是一種無奈和沮喪心情,甚至帶有悲觀絕望色彩。1963年,在光出生后不久,大江以記者的身份奔赴廣島參與第九屆禁止原子彈氫彈世界大會的籌備,1965年又趕赴沖繩采訪因原爆而被迫從廣島、長崎回到故鄉沖繩的人。這兩次經歷讓大江直觀地感受到了這些人的生活狀態——在不安和憎恨的同時仍不得不面對所處的窘境。這段經歷讓大江將自己個人的體驗(殘疾兒的出生)與民族的經歷相結合,自己的無奈與廣島、沖繩的原爆中受到傷害的人的堅毅相映襯。大江經受的是殘疾兒帶來的痛苦和絕望,“沒辦法”就是其對自己生存的窘迫境況的深刻而準確的認知。另一方面,從大江信奉的存在主義思想層面上看,每個人的出生存在偶然性和被動性,人在獲得生命的同時伴隨著對死亡的恐懼。因此,這一語“不僅客觀地披露了人的生存境況的悲劇性,同時也坦率承認,作為個體生命存在的人,本質上是一個弱者” 。
然而,盡管人本質上是個弱者,人的一生充滿坎坷,但是生命的存在與消亡是每個人無法逃避的宿命,每個人都得應對各種各樣的生存困境,因此只能不斷提醒自己:“干吧!”這也是人之為人的本分。光的出生對大江來說是一份“厚愛”,是大江無法逃避的命運。因此,大江當然只有老實地接受這一殘酷現實,發出“干吧!”這樣一句被逼無奈且毫無英雄氣概的感嘆。這并不能稱作一種豪情壯志或是人生壯舉,只是他作為一個“弱者”不得不做出的基本的符合人之常情的舉動。盡管之后的生活中,大江對殘疾兒悉心照顧,將他培養成一名音樂家,和殘疾兒一起“譜寫一曲華麗多彩的人生樂章”,但這并不是大江的初衷,大江對此也并未抱有奢望。所以,長期以來大江夫婦在生活中只是在感覺疲乏時,他們才互相提醒說:“干吧!”。
由此可見,“沒辦法”是大江對自己處境及人生命的悲劇性的客觀認知,“干吧!”則是大江作為“弱者”對自己無法逃避的窘境的真實回應。這句由兩組極其平常的話語組成的短句締造出一種令人心生敬畏的生命力量。面對殘疾兒的降生,大江體會到無法逃避的困難,“沒辦法”是他對無法回避的生存困境和自身力量弱小性的一種承認和“接受”,而“干吧!”則是在接受殘疾兒現實的基礎上迸發出的生命之韌性。大江曾坦言,在與殘疾兒的生活中,他慢慢發現殘缺的是自己的內心,而接受這種生活并為之行動,正是殘缺心靈漸漸“康復”的表現。
三、殘疾兒對社會的接受
從大眾視角看,有殘疾兒的家庭中需要承擔更多的是照顧殘疾兒的家人一方,作為殘疾兒的家屬需要克服許多困難和痛苦來“接受”殘疾兒,而作為文學大師的大江為讀者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即站在殘疾兒的角度,觀察殘疾兒慢慢“接受”自己的殘疾,“接受”自己與健全人的不同,“接受”社會的規則。在送光去殘疾兒職業培訓福利院時,大江看到許多殘疾兒童及其父母,體會到殘疾兒也會給父母帶來極大快樂,由此感嘆“殘疾兒童也不會夸張地表現自己正在經受的痛苦以及克服的困難,他們都具有很強的忍耐力”,而這種忍耐力表現在光身上便是對音樂的執著。
盡管光的智力發育遲緩,但從嬰兒時期開始,他就對音樂有敏銳的反應。三歲時光便能分辨貝多芬和肖邦的曲子,五歲時便能準確判斷出秧雞的叫聲,進入小學特殊班和殘疾兒童學校中級班之后,“一天到晚都在聽貝多芬、肖邦、莫扎特、巴赫等音樂家的作品”。在母親和老師的啟蒙下,光開始學習音樂,他每天醒來的第一件事就是聽音樂,總是俯在褥墊上或坐在飯桌旁作曲,連母親都只能偷偷看一眼譜子。田村久美子女士每周會來彈奏光的新作,與光研究創作得失,探討創作想法。看著光對音樂的癡迷,大江感受到光“生動而又充滿自信地表現出來的人最美好的素質”,這種“素質”可以理解為對美好事物自然而然的向往和沖動,就算是殘疾也不能阻礙這種沖動的迸發,這也是帶有宿命感的無法逃避的本能。
這種對音樂的癡迷讓光發現自己并不是一個只會給家人帶來負擔和痛苦的殘疾兒,他也是一個可以和健全人一樣享受音樂創作音樂的個體。音樂雖不能減輕光肉體上的痛苦,卻可以帶來精神上的鼓舞。可以讓他暫且以健全人的姿態去捕捉靈感、表達情感,給予他接受殘疾并堅持活下去的勇氣。通過音樂,光不僅給家人帶來了快樂,也讓自己能夠憑借音樂家的身份參與像廣島音樂會、薩爾茨堡夏季音樂節等社會活動,同時也結交了像森安信雄、田村久美子等社會人士。可以說,通過音樂,光不僅將整個家庭聯結起來,也將自己和社會銜接起來。讓光真切體會到自己的社會屬性,是作為作家和父親的大江能為光做到的最明智的教育。只有在發現自己的價值、發現自己對社會的價值的前提下,光才能夠勇敢地用殘疾人的身份去適應、接受社會的規則。
大江在堺市演講時看到街上有許多殘疾青年的輪椅,感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由于殘疾人出現的變化而煥發出新的生機,“與其說社會接納殘疾人,不如說殘疾人正在通過自己的實際行動接納這個社會,這就是他們的自立”。如果說大江對殘疾兒的接受是面對窘境不得已的選擇,那光對社會的接受則是生命本能的沖動,兩者既是一種對生命隨機性妥協,也是一種對現實無法逃避的抗爭,是作為弱者的人為了繼續生活而采取的本能行動,正是大江、光,以及其他家庭成員的共同行動,才讓這個家庭慢慢走向康復。
四、康復中的救贖
不幸成了病人,經歷了痛苦的心理過程,該怎樣以積極的心態面對殘缺的自己,而殘缺的自己又該怎樣在家庭和社會中發揮作用?大江認為,康復醫學的終極目標是對殘疾的接受。在與殘疾兒多年的生活中,大江體悟到這種接受是雙向的:作為殘疾人家屬需要接受家庭中存在殘疾人的現狀,作為殘疾人更需要接受身患殘疾的自己、家庭以及社會。而當家庭成員們共同達到了疾病過程中的“接受期”,則會漸漸從疾病中“康復”。這種“康復”不僅是從殘疾中痊愈,更是心靈從殘缺到完整的救贖。
大江沒有放棄光,悉心照顧,以作家和父親的雙重身份引導光走向社會;母親培養光的音樂天賦,用音樂療愈光;光的妹妹從小陪伴殘疾哥哥生活,成為助殘志愿者,投入到殘疾人志愿服務工作。這些努力讓光慢慢緩解了身體上的痛苦,也使得光能夠在一個充滿溫情的家庭氛圍中成長,能夠熱衷于音樂,實現自己的價值。
另一方面,光作為殘疾人也在努力讓家人“康復”。在給母親的賀卡上,光曾寫下:“到了今年,過了很長時間,好像痛苦的人很多。由佳里,再忍一忍吧。非常痛苦的不是媽媽,只是姥姥,我就放心了。”這里的“痛苦的人”指的是患癌的外祖母,由佳里則是光對母親的稱呼。讓大江意外的是光的語言庫里還存儲著“痛苦”“痛苦的人”這些生疏的詞匯,“這些平常不大用的詞,不知通過什么途徑收藏在了長子的心里”。可見,光雖智力發育遲緩,但是也能接受外界的信息,憑借自己的認知能力將吸收的知識輸出。在他的認知里,患癌是“痛苦的”,而作為家人的母親是需要“忍耐”的。這看似黑色幽默的話語,大江及妻子理解為“由于這種痛苦的疾病已經持續了很長時間,所以很快就會康復的”。這是同樣經歷了長久痛苦的光對疾病的認知,他也經歷著疾病的折磨,但是家庭讓他看到了康復的希望,因此他琢磨出如此見解,成了對家人樂觀面對疾病的鼓勵。此外,光時常聽祖母嘮叨她什么事都經歷過,只有死沒有經歷過,需要好好對待,因此光曾對祖母說:“奶奶,打起精神來,請好好地死!”這看似詛咒的話在祖母生病時給予了巨大的勇氣。殘疾孫子反復琢磨后說出的話給祖母增添了戰勝疾病的力量,仍處于康復階段的光卻給了家人們帶來了“康復”的、救贖的力量。由此可見,光雖然不能治療家人們身體上的痛苦,但是他的話語和行動真切地給家人們帶來了生活的希望和鼓勵。光帶來的心靈力量讓整個家庭中存在著一條“寬松的紐帶”,讓家庭成員們互相聯結卻不會產生束縛感。
當然,光的心靈力量最為受益的還是大江。在與殘疾兒的生活中,大江發現,每個人都要經歷不同的痛苦,但所有人都需要因生而為人這個理由去面對困難努力生活,在這樣的家庭生活中,雖然不斷有東西被破壞,卻也讓人對于不斷有什么東西會從毀壞中恢復、再生出來抱有希望。而這種恢復、再生的希望是光帶來的。光最矚目和令人驕傲的音樂天賦讓大江看到了努力下去的希望,也讓大江看到了這個家庭因為殘疾兒的存在而緊緊相連,逐漸填滿殘缺的自己。并且,作為一名高舉人文主義旗幟的戰士,大江從個人的“康復”的家庭出發,將目光轉向了因戰爭而滿目瘡痍的日本社會。他放眼整個日本社會:需要吸取力量的兩個主體,一個是與殘疾人共同生活的家人及其周圍的人,另一個是我們的社會和文化的時代。戰爭帶來的后遺癥一直摧殘著幸存者們,原爆帶來的傷害無法被社會忽視,越來越多的殘疾人需要被這個社會處置和拯救。大江以自己的家庭為例,通過接納殘疾兒光努力為社會中更多的殘疾兒家庭的生活方式提供基本形式,呼吁社會為殘疾兒以及殘疾兒家庭提供更多關懷,這既是大江自己獲得靈魂救贖的方式,也是大江為這個社會這個時代指明一條救贖道路。
參考文獻:
[1]大江健三郎.康復的家庭[M].竺家榮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
[2]胡志明.沒法子,干吧![J].高校輔導員學刊,2010,
2(01).
[3]胡志明.殘疾兒主題:大江健三郎文學出發的“原點”[J].安徽師范大學學報,2003,(05).
[4]張景榮.從《康復的家庭》中汲取共生的力量[J].文學教育,201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