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花》:人與城的斑駁記憶
劉竺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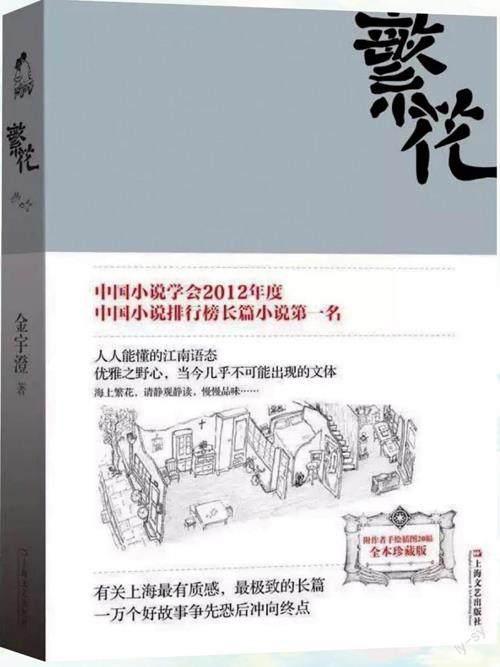
金宇澄的《繁花》是近年來受到讀者高度關(guān)注的小說。它從弄堂走出上海,又將上海帶到它所觸及的每個地方。近期,王家衛(wèi)執(zhí)導(dǎo)的同名電視劇以獨特的導(dǎo)演風格和大幅度的二次創(chuàng)作,讓《繁花》再度爆火。無論是小說還是電視劇,《繁花》給每個觸及它的人都帶來了相異的體驗。作為它的讀者,我遠離上海,這座城市對我而言,是若干符號的集合。所以,置身上海之外的我,更愿意將《繁花》理解為關(guān)于上海的人與城的斑駁記憶,它們連綴起來,指向上海,又瞄準光怪陸離的時代變遷。
《繁花》鋪開了記憶的畫卷,它首先是若干個體的記憶。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里,有幾句經(jīng)典獨白:“我的故事總是發(fā)生在夏天……那時候,好像永遠是夏天,太陽總是有空出來伴隨著我們,陽光充足,太亮,使得眼前一陣陣發(fā)黑。”“記憶總是被我的情感改頭換面,并隨之捉弄我、背叛我,把我搞得頭腦混亂,真?zhèn)坞y辨。”放在《繁花》里,也是如此。記憶不可捉摸,它常常會在頭腦中變形、模糊,但那些莫名其妙的事物、片段,又總像一個個閃光點,讓人猛然發(fā)覺,這些都曾存在過。《繁花》中,阿寶腦海里淮海路上的集郵者,小毛家老虎窗外密布的廠房,都是定格的記憶。當然,總有一些那樣的人和事,會讓人分不清他們是否存在過。在姝華對阿寶訴說失蹤的蓓蒂與阿婆時,她似乎還在夢中,夢里交替出現(xiàn)的人和魚,分明說的是,蓓蒂變成了一條金魚,阿婆變成了一條鯽魚,他們消失在了人生的長河之中。這些場景,亦真亦幻,出現(xiàn)又旋即消失,當回過頭時,只能看見滿地繁花,卻又無法聚攏過來。
《繁花》又是群體關(guān)于城的記憶。個體的記憶終究紛繁而又散亂,但當這些個體疊加起來時,又會構(gòu)筑起一個關(guān)于記憶的空間—不只停留在物品、風景上,它關(guān)乎傳統(tǒng),涉及過往,讓每個經(jīng)歷過的人深陷其中。《繁花》起于“弄堂”,飄往四方,它告訴每一個內(nèi)部或外部的人,這里就是上海。上海是什么?它可以是既“洋”又“土”的20世紀50年代,可以是“四海翻騰云水怒”的20世紀六七十年代,也可以是在五光十色中匆匆掠過的20世紀90年代。年代變遷,或許人們不再生活在“亭子間”,不必再為煤球爐發(fā)愁,但無論怎么變,它都在金宇澄的描述中歸于“咸話”(上海閑話、方言),而后寂靜無聲,用金宇澄的話講,這叫“不響”。
《繁花》中的記憶是交錯的記憶。小說章節(jié)錯落有致,一章講幾個主要人物的少年往事,一章講20世紀90年代的上海,交替往復(fù),直到終結(jié)。倘若《繁花》循著時間線索展開,我們看到的將是幾個人在一座城市里的生與死、愛和恨。但時代交替帶來的,則是切割與破碎:它切開了人物關(guān)系,切開了過去和當下,切開了現(xiàn)實與夢幻,切開了真實和虛無。小說里,阿寶有一個生活在香港的哥哥。哥哥寄來的畫片和郵票,讓阿寶腦海中浮現(xiàn)出想象的香港。淑婉的留聲機里傳出《卡門》,背后也暗藏著想象的異域。但時至今日,這種想象幾乎蕩然無存,我們不需要沖著畫片和郵票想象香港,一首《卡門》似乎也算不得“洋氣”,中與外、古和今,盡可以在互聯(lián)網(wǎng)中片段式的觀看里獲取,或是文字,或是圖像,或是影音。正如閱讀這部小說的方式,人物的年齡與身份隨著章節(jié)的跳躍任意切換,前因后果不必細致了解,他們的彼時與此時已經(jīng)展現(xiàn)在眼前。
記憶都是斑駁的,是碎片化的,但這些碎片綴連起來,就成了時代的變遷。之所以它被稱作碎片,是因為它在破碎以前,還是一個整體。當我們終于在反復(fù)跳躍中讀完這部《繁花》,并努力搜索記憶的碎片,將它們綴連起來時,不由得發(fā)現(xiàn),斑駁的記憶竟連成了包含人與城在內(nèi)的時代變遷。但這種時代變遷不是鳥瞰式的,而是隱于每個角落。它藏在淮海路國營舊貨店的鋼琴里,藏在南昌路帶天井的老洋房里,藏在工人新村里,藏在大宴賓客的“至真園”里。這正是《繁花》的打開方式,小說里展示的那些或土或洋、或宏偉或媚俗的事物,背后仿佛都蘊藏著什么,但玩味過后,卻會發(fā)現(xiàn),它們只是生活的背景,是“咸話”里的談資。
有時,個體是時代中的一粒沙,掀不起半分波瀾;有時,個體和他的生活,卻凝聚了整個時代,一如《繁花》里的滬生、阿寶與小毛,他們的命運各不相同,但在瑣碎的生活中,首先凝聚著人的斑駁記憶,其次指向上海這座城。這些記憶斷裂、破碎、跳躍、波動,像一堆無序的照片。但若逐張翻去,直到末尾,斑駁的印象自然會建構(gòu)起來,未必那么連續(xù),也不會十分清晰,但卻在那些不起眼的角落處,見證了時間的流逝。正如一樹繁花,開了又謝,聚了又散,朵朵不同,雜亂無序,但走遠了再看,還是那一樹繁花。
作品簡介
《繁花》是金宇澄創(chuàng)作的長篇小說,以阿寶、滬生、小毛等主要人物的活動為線索,講述了上海市民的生存狀態(tài)。小說的主要情節(jié)發(fā)生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與八九十年代,側(cè)重于展現(xiàn)日常生活。作品語言采用改良后的上海方言,加之大量描寫關(guān)于上海的器物、景觀、城市生活,兼采話本小說的表達方式,被認為是近年來地域文學、城市文學中的代表性作品。《繁花》于2011年在弄堂網(wǎng)連載,2012年發(fā)表于《收獲》,2013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2015年獲茅盾文學獎。此后,《繁花》經(jīng)歷了數(shù)次修訂并譯介至海外出版,又改編為舞臺劇等藝術(shù)形式。2023年底,王家衛(wèi)執(zhí)導(dǎo)的同名電視劇播出,迅速引發(fā)觀看與討論熱潮,讓《繁花》再度進入大眾視野。正如茅盾文學獎頒獎詞所言:“在小歷史中見出大歷史,在生計風物中見出世相大觀,急管繁弦,暗流涌動,盡顯溫婉多姿、余音不絕之江南風韻。”閱讀《繁花》,其實是從個體中閱讀整體,是從生活中感受波瀾壯闊的歷史大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