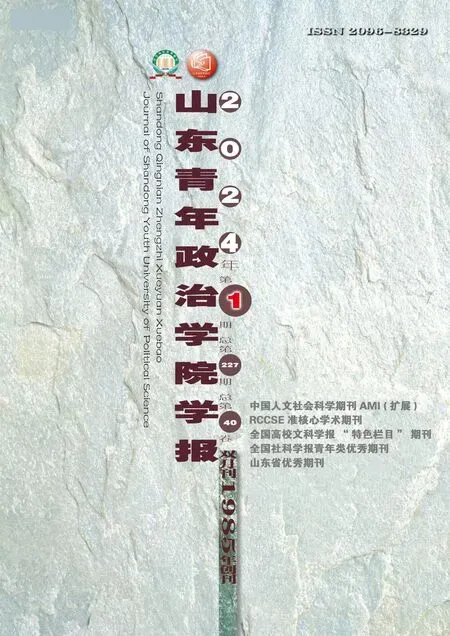《論語(yǔ)》詮釋的“本事”路徑探析
——以日藏孤本《三經(jīng)見(jiàn)圣編》為中心
曹景年
(孔子研究院 學(xué)術(shù)交流部,山東 曲阜 273100)
《論語(yǔ)》是儒家的首要經(jīng)典,千百年來(lái)詮釋《論語(yǔ)》的著作汗牛充棟,詮釋思想、詮釋方法也多種多樣,觀黃懷信先生主撰之《論語(yǔ)匯校集釋》及高尚榘先生之《論語(yǔ)歧解輯錄》可見(jiàn)一斑。面對(duì)浩瀚的前人成果,如果不采用新思路和新方法,《論語(yǔ)》詮釋很難再有新的進(jìn)展。近年來(lái),有些學(xué)者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例如楊逢彬先生在其家學(xué)淵源基礎(chǔ)上,采用傳統(tǒng)訓(xùn)詁學(xué)與現(xiàn)代語(yǔ)言學(xué)相結(jié)合的方法,對(duì)《論語(yǔ)》作了一些再詮釋(1)楊逢彬:《論語(yǔ)新注新譯》,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6。,提出不少新見(jiàn),引起學(xué)界的關(guān)注。筆者在研究整理明代四書學(xué)著作時(shí),在日本內(nèi)閣文庫(kù)公布的古籍中發(fā)現(xiàn)一部思路新穎、內(nèi)容奇特的著作《三經(jīng)見(jiàn)圣編》,該書提出并實(shí)踐了以“本事”解《論語(yǔ)》的獨(dú)特路徑,有不少可稱為“發(fā)前人所未發(fā)”的新發(fā)明,對(duì)于《論語(yǔ)》解讀有很大的啟發(fā)意義。本文即以該書對(duì)《論語(yǔ)》季康子諸章的詮釋為例,對(duì)其“本事”詮釋路徑作初步探討,或有助于推動(dòng)《論語(yǔ)》研究在新時(shí)代的新發(fā)展。
一、《三經(jīng)見(jiàn)圣編》及其“本事”路徑
《三經(jīng)見(jiàn)圣編》的作者譚貞默(1590-1665),字梁生,別號(hào)掃庵,嘉興人,崇禎元年(1628)進(jìn)士,曾任職工部、大理寺,明亡后經(jīng)洪承疇薦任職國(guó)子監(jiān),不久辭官歸家。譚氏博學(xué)多才,著述豐富,惜多不傳,《三經(jīng)見(jiàn)圣編》是其最主要的著作,起意于明天啟時(shí),完成于清順治初,耗費(fèi)譚氏三十余年心血,故他對(duì)此書非常重視,于書成后曾誓言“書存與存,書亡與亡”。為其作傳的屠存智對(duì)此書評(píng)價(jià)很高:“公生平著述最富,其大者《見(jiàn)圣》一編,以三十年苦心闡發(fā)圣賢微言?shī)W義,大都引據(jù)經(jīng)史注疏等書及先儒論說(shuō),斷以己意。時(shí)方遵守朱紫陽(yáng),而公多與辯駁,且其卷帙浩繁,人不能盡得,得不能盡觀,書又適成于滄桑之際,于是誹謗叢集,多見(jiàn)其不知量也。”(2)生平參清譚新嘉編《嘉興譚氏家譜》卷五屠存智撰《掃庵公傳》,光緒三十一年刻本,第10頁(yè)a-第14頁(yè)a。今人考證參朱則杰:《<清人詩(shī)文集總目提要>訂補(bǔ)——以曹勛等八位嘉興作家為中心》,《嘉興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17年第1期。此書因篇幅過(guò)大,流傳不廣,國(guó)內(nèi)久無(wú)傳本。1937年,譚氏后人譚新嘉從清初陸隴其《四書講義困勉錄》中輯得70余條,編成《三經(jīng)見(jiàn)圣編輯存》二卷,后影印收入《四庫(kù)全書存目叢書》經(jīng)部第166冊(cè),但體量?jī)H約為原書的1%,完全不能反映原書的基本面貌。幸運(yùn)的是,日本內(nèi)閣文庫(kù)(國(guó)立公文書館)藏有清順治刊本,完整無(wú)缺,并已在其網(wǎng)站公布(3)日本內(nèi)閣文庫(kù)官網(wǎng)網(wǎng)址:https://www.digital.archives.go.jp/,登記名“孔經(jīng)見(jiàn)圣編”,索書號(hào):經(jīng)043-0001,本文所引此書內(nèi)容皆出此本,引用時(shí)稱原書名“三經(jīng)見(jiàn)圣編”。頁(yè)碼以卷為單位,按中縫計(jì)數(shù),每卷分別計(jì)頁(yè)。。據(jù)此本,全書包括首四卷、《孔經(jīng)見(jiàn)圣編》一百二十卷、《孟經(jīng)見(jiàn)圣編》六十卷,合一百八十四卷,分為72冊(cè)。譚氏認(rèn)為《大學(xué)》為《中庸》下篇,且都是子思所作,故把四書稱為“三經(jīng)”。他又認(rèn)為《中庸》是子思直承《論語(yǔ)》而作,故可與《論語(yǔ)》并稱“孔經(jīng)”,《孟子》則稱“孟經(jīng)”。首四卷相當(dāng)于全書概要,包括《論語(yǔ)考目》《中庸解目》《孟子辯旨大略》。正文《論語(yǔ)》《孟子》皆逐章解說(shuō),《中庸》則以13篇論文的形式綜合闡述其結(jié)構(gòu)、要旨等。
《三經(jīng)見(jiàn)圣編》是一部考據(jù)性質(zhì)的著作,但與一般的訓(xùn)詁考據(jù)不同,其最鮮明的特色是把考證“本事”作為詮釋四書的基本路徑,并且在《論語(yǔ)》部分表現(xiàn)得最為突出。譚氏認(rèn)為《論語(yǔ)》大部分章節(jié)都是有“本事”的,他說(shuō):“《論語(yǔ)》之言,本事者什九,不本事者什一。”(4)譚貞默:《三經(jīng)見(jiàn)圣編》卷八,日本內(nèi)閣文庫(kù)藏清順治二年刊本,第11頁(yè)b。所謂“本事”,在現(xiàn)代語(yǔ)境下多用于文學(xué)研究,指的是文學(xué)作品所依據(jù)的事實(shí)或原委,如紅學(xué)家對(duì)《紅樓夢(mèng)》本事的探討。在《三經(jīng)見(jiàn)圣編》的語(yǔ)境下,“本事”具有相近的意思,指經(jīng)文所關(guān)涉的人和事,也就是“對(duì)誰(shuí)說(shuō)的”“什么時(shí)候說(shuō)的”“為什么這樣說(shuō)”這類問(wèn)題。歷代《論語(yǔ)》研究者也有不少關(guān)注《論語(yǔ)》“本事”的,但只有《三經(jīng)見(jiàn)圣編》真正將其作為一種主要的解經(jīng)方法來(lái)解讀《論語(yǔ)》。這一解經(jīng)方法主要目的是通過(guò)“知人論世”來(lái)探求《論語(yǔ)》本義,以糾正前人對(duì)《論語(yǔ)》的曲解和妄說(shuō)。知人,即對(duì)四書所涉人物的生平事跡、性格品行作全面深入的研討;論世,即把經(jīng)文放回到當(dāng)時(shí)之“世”中去理解,對(duì)經(jīng)文發(fā)生的歷史背景、相關(guān)事件、人物關(guān)系作準(zhǔn)確的把握。譚氏認(rèn)為,只有通過(guò)“知人論世”,才能真正理解《論語(yǔ)》的圣言、圣意。在解《論語(yǔ)·八佾》“定公問(wèn)君使臣”章時(shí)他說(shuō):“欲明夫子之言,則必于其時(shí)矣。定公之時(shí)何時(shí)也?承昭公、平子君不君臣不臣,習(xí)而安焉之時(shí)也。”(5)譚貞默:《三經(jīng)見(jiàn)圣編》卷十四,第6頁(yè)b。認(rèn)為要想準(zhǔn)確解讀本章的意義,就要將其還原到定公的時(shí)代及其當(dāng)時(shí)的處境。《左傳》是記載孔子時(shí)代最為詳盡的典籍,譚氏在解“哀公問(wèn)社”章時(shí)就說(shuō):“讀《左傳》不熟,而妄論哀公之問(wèn)社,宰我之對(duì)社,孔子之非宰我,是郢書而燕說(shuō)也。”(6)譚貞默:《三經(jīng)見(jiàn)圣編》卷十五,第12頁(yè)b。認(rèn)為只有深刻把握了《左傳》所提供的時(shí)代背景,才能對(duì)《論語(yǔ)》相關(guān)內(nèi)容有更準(zhǔn)確的理解。
在這一思路指導(dǎo)下,譚氏逐章探討了《論語(yǔ)》經(jīng)文的“本事”,建構(gòu)了一個(gè)龐大的《論語(yǔ)》本事體系,雖然其中某些觀點(diǎn)有穿鑿武斷之嫌,但讓人拍案叫絕、能夠啟發(fā)新知的也不在少數(shù)。以下即以《論語(yǔ)》中與季康子有關(guān)的章節(jié)為例,從三個(gè)層面來(lái)分析其“本事”詮釋路徑的特征、意義和價(jià)值。之所以選擇這部分內(nèi)容,一方面因?yàn)榧究底邮侵匾臍v史人物,相關(guān)記載比較豐富,對(duì)“本事”的考證不至流于單純的揣測(cè)懸想,另一方面季康子與晚年的孔子有非常密切的關(guān)系,對(duì)其本事的探討有助于深入了解孔子晚年的生活和思想境況。
二、據(jù)人物性格品行解讀經(jīng)文
季康子,名肥,季桓子之子,魯哀公三年(前492)桓子死后,繼任季氏家主,執(zhí)政魯國(guó)。季氏與孔子既有合作,又有斗爭(zhēng),關(guān)系非常復(fù)雜。孔子一直主張尊公室,抑私家,孔子墮三都時(shí)曾獲得季桓子的支持,但后來(lái)因觸動(dòng)季氏利益而為桓子抵制,不得已離開(kāi)魯國(guó)。康子繼任執(zhí)政之初,曾打算迎回孔子,但在他人的阻撓下沒(méi)有實(shí)現(xiàn),只把冉求召回去任家宰。哀公十一年,在冉求的運(yùn)作下,季康子終于召回了孔子。孔子晚年為魯國(guó)國(guó)老,季康子遇到大事都要咨詢孔子,雖然未必都聽(tīng)從孔子的教誨,但也充分體現(xiàn)了他對(duì)孔子的尊重。《論語(yǔ)》中季康子與孔子的對(duì)話共八則,其中只有四則與季康子本人關(guān)系密切。譚氏對(duì)這四則材料的解讀,都以季康子的品行和行事風(fēng)格作為基本依據(jù),并以此推斷其它部分經(jīng)文也與季康子有關(guān)。
《論語(yǔ)》中第一次提到季康子是在《為政》篇:“季康子問(wèn):‘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季康子向孔子請(qǐng)教如何使民眾敬、忠和勸勉,孔子告訴他要做到臨之以莊、孝慈、舉善而教不能三個(gè)方面。從字面意思看,這都是作為一個(gè)領(lǐng)導(dǎo)者的基本素質(zhì),沒(méi)有什么特異之處,但譚氏出其不意,從“本事”的角度進(jìn)行解釋,認(rèn)為孔子說(shuō)的這三個(gè)方面都是季康子日常行事中所缺乏的。
關(guān)于“臨之以莊”,譚氏認(rèn)為正是因?yàn)榧究底悠綍r(shí)待人接物不夠莊重,所以孔子才這樣說(shuō)。他引用了一個(gè)故事:“孔子適季氏,康子晝居內(nèi)寢。孔子問(wèn)其所疾。康子出見(jiàn)之。言終,孔子退,子貢問(wèn)曰:‘季孫不疾而問(wèn)諸疾,禮與?’孔子曰:‘夫禮,君子不有大故,則不宿于外。非致齊也,非疾也,則不晝處于內(nèi),是故夜居外,雖吊之可也。晝居于內(nèi),雖問(wèn)其疾可也。’”這個(gè)故事來(lái)自《孔子家語(yǔ)·曲禮子貢問(wèn)》,說(shuō)的是孔子拜訪季氏,季康子白天還在內(nèi)寢,孔子認(rèn)為按照禮法要求,如果不是在齋戒或疾病期間,白天是不能在內(nèi)寢的。從這個(gè)故事可以看出季康子為人不夠莊重有禮,故譚氏云“此即告以臨莊之意也”。(7)譚貞默:《三經(jīng)見(jiàn)圣編》卷八,第8-9頁(yè)。
關(guān)于孝慈,譚氏引用了季康子的另外兩個(gè)故事,其一云:“季桓子喪,康子練而無(wú)衰,子游問(wèn)于孔子曰:‘既服練服,可以除衰乎?’孔子曰:‘無(wú)衰衣者,不以見(jiàn)賓,何以除焉?’”這個(gè)故事亦來(lái)自《家語(yǔ)·曲禮子貢問(wèn)》,季康子服喪期間“練而無(wú)衰”,孔子認(rèn)為這不符合喪服的要求,這個(gè)故事說(shuō)明季康子不夠孝,故譚氏云“此即告以孝之意也”。其二來(lái)自《荀子·大略》而有節(jié)略:“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欲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康子曰:‘治民以孝,不亦可乎?’孔子曰:‘否。不教而聽(tīng)其獄,殺不辜也。上陳之教而民不從,然后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詩(shī)曰俾民不迷,昔者君子導(dǎo)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不至,刑措而不用也。’”魯國(guó)有父子之間打官司的,季康子以不孝為借口想要把兒子殺掉,孔子認(rèn)為要先對(duì)民眾進(jìn)行教化,教化不從才能動(dòng)殺。譚氏認(rèn)為這是季康子對(duì)民不慈的表現(xiàn),故云“此即告之以慈之意也”。(8)同上。至于勸之意則全在敬、忠之內(nèi),不敬不忠則不勸。
從譚氏對(duì)這則經(jīng)文的解讀看,他不再把這章內(nèi)容當(dāng)成泛泛的教導(dǎo)之語(yǔ),而認(rèn)為都是直接針對(duì)季康子的缺點(diǎn)而言,并引用與季康子有關(guān)的事跡來(lái)證明,從而凸顯了解季康子的性格和行為特征,這是譚氏“知人論世”詮釋理路的體現(xiàn)。《論語(yǔ)》中涉及季康子的另外三則對(duì)話前后相連,均見(jiàn)于《顏淵篇》。第一則是季康子問(wèn)政于孔子,孔子對(duì)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孔子告誡季康子要先正己才能正人。第二則季康子問(wèn)孔子能否“殺無(wú)道以就有道”,孔子說(shuō):“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fēng),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fēng)必偃。”告誡他為政不能隨便用殺,而要以德化民,自己有德則民也會(huì)有德。第三則季康子因患盜而問(wèn)于孔子,孔子回答說(shuō):“茍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告誡他盜賊多是因?yàn)樽约憾嘤?減少欲望自然盜賊就會(huì)減少。這三則詞義淺顯明白,譚氏沒(méi)有過(guò)多討論。(9)譚氏對(duì)這三章的解釋見(jiàn)譚貞默:《三經(jīng)見(jiàn)圣編》卷六十二,第24-31頁(yè)。
通過(guò)這幾章,大致可以看出季康子的性格和品行,為政嚴(yán)厲好殺、貪財(cái)多欲、缺乏禮的素養(yǎng)、不孝不慈等。以此為基礎(chǔ),譚氏斷定孔子另外幾句言說(shuō)對(duì)象不明的話,也是針對(duì)季康子而言。
(一)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論語(yǔ)·八佾》)
對(duì)于這一章,古今注解者都未明確對(duì)誰(shuí)而言,譚氏則認(rèn)為是針對(duì)季康子說(shuō)的:“此夫子專為大夫言之也,蓋在自衛(wèi)反魯之后,為季康子言之也。”并舉了季康子的相關(guān)事跡為證。(10)譚氏解此章語(yǔ),均見(jiàn)譚貞默:《三經(jīng)見(jiàn)圣編》卷十六,第41-43頁(yè)。
關(guān)于居上不寬,譚氏云:“康子不行周公之典,而欲以一井田出法賦,是取民不寬也。”此是據(jù)哀公十二年季氏推行田賦而言,田賦加重了民眾負(fù)擔(dān),所以是取民不寬。又云:“康子欲殺無(wú)道以就有道,夫子告以子為政焉用殺,子貢亦告之云:‘托法而治謂之暴,不戒致期謂之虐,不教而誅謂之賊,以身勝人謂之責(zé),責(zé)者失身,賊者失臣,虐者失政,暴者失民。’是用刑不寬也。”季康子為政嚴(yán)苛,動(dòng)輒殺人,前文已經(jīng)提及,此處子貢告之云云一事見(jiàn)《韓詩(shī)外傳》卷三,原文稱“季孫氏之治魯也,眾殺人而必當(dāng)其罪;多罰人而必當(dāng)其過(guò)”(11)此季孫雖未明指何人,但從其中“眾殺人”來(lái)看,結(jié)合《論語(yǔ)》季康子“殺無(wú)道以就有道”來(lái)看,當(dāng)指季康子無(wú)疑。,以嚴(yán)刑峻法治國(guó),導(dǎo)致民眾聽(tīng)到季氏生病就高興,聽(tīng)到季氏恢復(fù)健康就害怕,故子貢稱其“暴哉治乎”,告誡他為政者應(yīng)該以仁愛(ài)之心待下。這些都是季康子居上不寬的證據(jù)。
關(guān)于為禮不敬,譚氏舉了三個(gè)事例。一是為下之禮不敬,舉假馬事為例:“孔子適季孫,其宰謁曰:‘君使人假馬。’康子未言,孔子曰:‘吾聞之,君取于臣謂之取,與于臣謂之賜,臣取于君謂之假,與于君謂之獻(xiàn)。’季孫色然懼。是為下之禮不敬也。”(出自《家語(yǔ)·正論解》及《韓詩(shī)外傳》卷五)。按照禮法,君向臣索要物品稱取,臣向君要?jiǎng)t稱“假”,現(xiàn)在哀公向季康子要馬,而其家宰稱“假”,是對(duì)君上的不敬。二是居家之禮不敬,舉晝居于內(nèi)一事為例,詳前文。三是為主之禮不敬,舉孔子食于季氏為例:
孔子食于季氏,食祭,主人不辭。不食亦不飲而飡。子夏問(wèn)曰:“禮也?”孔子曰:“從主人也。吾食于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食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飡,作而辭曰:‘疏食,不敢以傷吾子之性。’主人不以禮,客不敢盡禮;主人盡禮,則客不敢不盡禮也。”
此事見(jiàn)《家語(yǔ)·曲禮子夏問(wèn)》,孔子說(shuō)“主人不以禮,客不敢盡禮”,很明顯是說(shuō)季康子接待賓客方面不夠盡禮。
關(guān)于臨喪不哀,譚氏從兩方面舉證,一是臨父喪不哀,舉季桓子喪,康子練而無(wú)衰之事為證,見(jiàn)上文;二是臨君之喪不哀,指的是昭公夫人孟子之喪:“昭公夫人孟子卒,孔子既致仕,而往吊焉,適于季氏,康子不绖,孔子投绖而不拜,是臨君之喪不哀也。”(見(jiàn)《家語(yǔ)·曲禮子貢問(wèn)》及《左傳·哀公十二年》)。最后一句“吾何以觀之哉”,譚氏云:“使之聞之也,箴之砭之也。”認(rèn)為是孔子故意說(shuō)這話讓康子聽(tīng)到,從而對(duì)他起到警醒的作用。
綜上可見(jiàn),譚氏通過(guò)廣泛征引與季康子有關(guān)的資料,確認(rèn)本章的批評(píng)對(duì)象是季康子,所舉例證有一定的說(shuō)服力,也使本章不再是一句抽象的教條,而具有了豐富的歷史情境。
(二)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論語(yǔ)·里仁》)
關(guān)于這一章的解釋古今眾說(shuō)紛紜,但從語(yǔ)法角度可以歸納為兩種,一是把 “懷德”與“懷土”,“懷刑”與“懷惠”分別對(duì)立起來(lái),懷德、懷刑代表君子,是正面的,懷土、懷惠代表小人,是負(fù)面的。另一種是把懷德、懷刑當(dāng)成前提,懷土、懷惠是相應(yīng)的后果,加上虛詞就是:“若君子懷德,則小人懷土;若君子懷刑,則小人懷惠。”言外之意是君子應(yīng)該懷德而不懷刑。兩種解釋中第一種是主流,皇侃、邢昺、朱熹、劉寶楠等都認(rèn)同此說(shuō)。持第二種解釋的非常少,最早見(jiàn)于皇侃《論語(yǔ)義疏》,但只是作為一種異說(shuō)來(lái)看待的:“一云:君若化民安德,則下民安其土,所以不遷也……人君若安于刑辟,則民下懷利惠也。”(12)見(jiàn)黃懷信主撰:《論語(yǔ)匯校集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330頁(yè)。其后,宋劉敞、程頤(13)朱子編《論孟精義》卷二引程頤云:“在上者志存于德,則民安其土;在上者志在嚴(yán)刑,則民思仁厚者而歸之。”但《精義》于其下又引語(yǔ)錄曰:“君子懷德,惟義之所在,小人懷土,惟事之所在;君子懷刑,惟法之所在,小人懷惠,惟利之所在。”可見(jiàn)程頤的觀點(diǎn)有自相矛盾之處。見(jiàn)《朱子全書》第7冊(c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147-148頁(yè)。也認(rèn)同此種解釋。
譚氏認(rèn)為從語(yǔ)法和行文角度看,傳統(tǒng)主流解釋是不通的,“懷土何以分配懷德,懷惠何以分配懷刑,卒不可得。”譚氏關(guān)注到劉敞的說(shuō)法,而對(duì)其大加贊賞,認(rèn)為發(fā)千古之秘,是“左券之言”,并引其解曰:“君子在上位者也,君子懷于為德,導(dǎo)之以德,小人乃懷土重遷;如君子懷于用刑,導(dǎo)之以刑,則小人不復(fù)懷土,將懷惠己者而歸之矣,所謂免而無(wú)恥也。此言小人之性無(wú)常,在上導(dǎo)之而已。信哉!此則左券之言也。”譚氏認(rèn)為本章的主旨是要求在位者尚德而不尚刑,只有這樣人民才會(huì)安心于生產(chǎn)生活,即“懷土”,刑罰只是社會(huì)治理的有益補(bǔ)充,而不是主要手段,如果主要任用刑罰治國(guó),殘害人民,那人民就會(huì)逃歸有恩惠的地方,即“懷惠”。他又舉出了《詩(shī)》《書》中“懷”字的類似用法,如“予懷明德”“懷保萬(wàn)民”“德日新,萬(wàn)邦惟懷”等,以印證此章之義:
懷德者,所謂“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guó),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樂(lè)土樂(lè)土,爰得我所”,懷土之謂也。懷刑者,所謂“毋從詭隨,以謹(jǐn)無(wú)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回遹其德,俾民大棘”、“民心無(wú)常,惟惠之懷”,懷惠之謂也。(14)譚氏解此章語(yǔ),均見(jiàn)譚貞默:《三經(jīng)見(jiàn)圣編》卷十八,第33-36頁(yè)。皇侃《論語(yǔ)義疏》在中土亡佚已久,今本是清初從日本回傳,故譚氏不得見(jiàn)。朱子《論孟精義》非普通士人習(xí)讀,可能譚氏沒(méi)有注意到,故只看到了劉敞的說(shuō)法。
譚氏的這些舉證很有說(shuō)服力,也與《論語(yǔ)》的其它說(shuō)法相呼應(yīng),如《為政篇》孔子就主張“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而反對(duì)“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但譚氏的解釋并沒(méi)有到此為止,而是進(jìn)一步指出,本章并非孔子的一般教導(dǎo)之語(yǔ),而是對(duì)魯國(guó)從政者的刺譏:“夫子自衛(wèi)反魯,不仕而憂公,家食而謀國(guó),有所刺譏,必中從政之病。如懷德懷刑之論,非無(wú)為而發(fā)也。”具體說(shuō)來(lái)就是針對(duì)當(dāng)時(shí)魯國(guó)執(zhí)政季康子說(shuō)的。譚氏先是將此章與“子為政,焉用殺”章參照:“他日,季康子問(wèn)政于孔子:‘如殺無(wú)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duì)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fēng),小人之德草,草尚之風(fēng)必偃。’此正所謂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也。”又引季孫多殺人事云:“季孫子之治魯也,多殺人而必當(dāng)其罪,多罰人而必當(dāng)其過(guò),自謂無(wú)暴矣,季孫疾則國(guó)人喜,瘳則國(guó)人皆駭,以死相賀,以生相恐。子貢曰暴哉治乎,虐者失政,暴者失民,是君子懷刑小人懷惠之象也。故曰為魯之從政者言之也。懷刑不懷德,無(wú)如季孫。”由季康子為政好殺,過(guò)于暴虐,推定此章是對(duì)季康子“懷刑”的批評(píng)。
譚氏對(duì)本章的詮釋是其“本事者十九”解經(jīng)路徑的精彩展示,他對(duì)此也頗為自信:“譚子有心,劉先獲之,若夫季氏本義,則千古未弋獲也。”后來(lái)清俞樾以及今人黃懷信先生都從劉敞之說(shuō),而未推至季康子(15)俞越、黃懷信觀點(diǎn)見(jiàn)黃懷信主撰:《論語(yǔ)匯校集釋》,第331-332頁(yè)。。
(三)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論語(yǔ)·里仁》)
此章在“懷德懷惠”章之下,也是孤零零的一句話,譚氏認(rèn)為此章是“夫子專為季康子、冉求用田賦之事而發(fā)也”。(16)譚氏解此章語(yǔ),均見(jiàn)譚貞默:《三經(jīng)見(jiàn)圣編》卷十八,第38-43頁(yè)。季康子于哀公十一年就田賦之事參訪孔子,孔子不同意,但季康子仍于次年強(qiáng)行實(shí)施。本章正針對(duì)此事而言,是在批評(píng)季康子欲望太多,必將引起眾人的怨恨。譚氏將此事與子產(chǎn)作丘賦所引起的反響作對(duì)比。據(jù)《左傳》記載,子產(chǎn)作丘賦引起眾人的怨恨,國(guó)人謗之為“蠆尾”,渾罕稱“國(guó)氏其先亡乎”,晉國(guó)的叔向也致書于子產(chǎn),批評(píng)他的這一舉措。譚氏評(píng)論說(shuō):“季氏富于周公,冉有為之聚斂而附益之,正用田賦之事,所謂放利而行也。子產(chǎn)之作丘賦,專利社稷而猶怨之,呼為蠆尾,況季孫專利私家,君怨之,大夫怨之,百姓怨之。”子產(chǎn)作丘賦是利于社稷的好事,尚且引起很多人怨恨,而田賦只對(duì)季氏一家有利,會(huì)招來(lái)更大的怨恨。譚氏還認(rèn)為“季康子患盜”章孔子批評(píng)他多欲,也可與本章的“放于利”相呼應(yīng):“放利而致盜,一時(shí)之亂政何如哉!”在這一解釋之下,本章的意義變得充實(shí)而豐滿,并且與相關(guān)各章的意義融通起來(lái)。
三、結(jié)合史實(shí)解讀經(jīng)文
譚氏高度重視史實(shí)對(duì)解讀《論語(yǔ)》的作用,他非常重視《左傳》,認(rèn)為只有熟讀《左傳》對(duì)相關(guān)事件的記載,才能對(duì)《論語(yǔ)》有更真切的理解。以下試舉兩個(gè)例子,來(lái)觀察譚氏以史實(shí)解經(jīng)的突出特色。
(一)“季氏旅于泰山”是祈福活動(dòng)
“季氏旅于泰山”章,一般認(rèn)為是孔子批評(píng)季氏祭祀泰山的僭越行為,而譚氏則另辟蹊徑,認(rèn)為旅泰山不是祭祀泰山,而只是一種祈福迷信活動(dòng)。(17)譚氏解此章語(yǔ),均見(jiàn)譚貞默:《三經(jīng)見(jiàn)圣編》卷十,第5-11頁(yè)。其主要依據(jù)是對(duì)若干史實(shí)的考證。
首先,譚氏認(rèn)為,祭祀泰山是事關(guān)周天子和列國(guó)諸侯的重大活動(dòng),與八佾舞庭、私廟雍徹等魯國(guó)內(nèi)部的僭越舉動(dòng)性質(zhì)不同,季氏絕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康子即欲僭侈擬君,而有事泰山,事關(guān)周室列侯,非一國(guó)事也,與私廟雍徹何啻梃楹?雍佾特窺室中之藏,泰山顯作國(guó)門之御。當(dāng)平子民不知君之時(shí)尚不敢為此,康子何時(shí)?非有狂疾,而何以為此哉!”而且,季康子與孔子接觸頻繁,禮法名分思想耳熟能詳,對(duì)于祭祀泰山這樣僭越周王職權(quán)的嚴(yán)重違禮舉動(dòng),應(yīng)該不會(huì)輕舉妄動(dòng)。譚氏說(shuō):“康子之世,冉求為宰,君臣之禮,圣門習(xí)聞,且哀公雖不用孔子,而優(yōu)禮崇問(wèn),正色侃言,一時(shí)三家無(wú)敢大為非禮。藉康子有跡于登封柴望之舉動(dòng),群臣百姓孰能容之?”
其次,泰山不在魯境內(nèi),魯無(wú)權(quán)祭泰山。《魯頌·閟宮》云:“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譚氏說(shuō):“龜蒙鳧繹之四山,魯境內(nèi)山也,泰山特魯瞻耳,非魯境內(nèi)山也。”又引《禮器》云“齊人將有事于泰山,必先有事于配林”,而斷定:“泰山者齊境非魯境,齊之所有事而魯之祭不越望者也。”諸侯只能祭其境內(nèi)的名山大川,泰山在齊國(guó)內(nèi),應(yīng)由齊國(guó)主持祭祀而非魯國(guó):“魯君不應(yīng)主祭,季氏安從生僭?”魯君本來(lái)就無(wú)權(quán)祭祀泰山,故也不會(huì)有僭越魯君之說(shuō)。
既然“旅于泰山”不是祭祀泰山,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譚氏認(rèn)為只是到泰山祈禱邀福,他解釋“旅”字云:“旅,陳也,所云陳其祭事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則其事固甚小而略也。”故此章意在批評(píng)季氏到泰山“祈佑邀福,與愚眾同”,他引用《風(fēng)俗通》《博物志》《福地記》等資料,認(rèn)為泰山不僅是王者祭祀、封禪之地,而且自古以來(lái)就是民間祈福圣地:“歷代以來(lái),泰安州之神,禱祠而求者走天下如鶩,不特自春秋時(shí)始矣。康子之旅泰山,祈佑邀福,與愚眾同見(jiàn),不過(guò)如是而已。”在此基礎(chǔ)上,譚氏進(jìn)一步認(rèn)為,《論語(yǔ)》另外一章“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jiàn)義不為,無(wú)勇也”也是針對(duì)此事而言,前半句是批評(píng)季氏旅泰山是非鬼而祭,是一種邀福諂媚行為,后一句是批評(píng)冉有沒(méi)能阻止季氏是見(jiàn)義不為。總體來(lái)看,譚氏立足于相關(guān)史實(shí),從祈福這一世俗心態(tài)來(lái)解釋季康子的行為,跳出了前人凡遇季氏必認(rèn)為是僭越、違禮的刻板形象,其所舉證據(jù)也有一定的說(shuō)服力。
(二)以“季氏將伐顓臾”章考證子路行實(shí)
譚氏通過(guò)“季氏將伐顓臾”章,對(duì)子路的生平事跡進(jìn)行了補(bǔ)充考證,并確證了“公伯寮訴子路”章的發(fā)生時(shí)間。
在這一章中,冉有、季路同時(shí)見(jiàn)孔子,似乎此時(shí)子路也是季氏的家臣。子路在孔子為魯司寇時(shí)曾做過(guò)季氏宰,并成為孔子墮三都行動(dòng)的有力助手,但此后未再見(jiàn)有為季氏宰的記載。朱子曾推斷說(shuō):“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shí),此云爾者,疑子路嘗從孔子自衛(wèi)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fù)之衛(wèi)也。”(18)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1983,第169頁(yè)。認(rèn)為子路在孔子歸魯后可能再次仕于季氏,但沒(méi)有提出證據(jù)。譚氏則通過(guò)考證確證了朱子的推斷。他先是舉《左傳·哀公十四年》的一條記載為證:“哀公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lái)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wú)盟矣。’季康子使冉有謂子路,子路辭。”由此他斷定“是歲季路尚與冉有同為季氏宰也”(19)譚貞默:《三經(jīng)見(jiàn)圣編》卷八十三,第14頁(yè)a。。然而《左傳》又載:“十五年春,成叛于齊,武伯伐之,弗克,秋,齊陳瓘如楚,過(guò)衛(wèi),仲由見(jiàn)之,曰……”,可見(jiàn)十五年“季路已適衛(wèi)為孔悝宰矣”,十四年尚在魯,十五年已入衛(wèi),那么從十四年到十五年之間,肯定發(fā)生了一些事,導(dǎo)致子路在魯國(guó)待不下去,而只能回到他的家鄉(xiāng)衛(wèi)國(guó)。這意味著,子路晚年也曾一度為季氏宰,但因某種原因離開(kāi)了魯國(guó)而回到衛(wèi)國(guó)。譚氏認(rèn)為,這中間所發(fā)生的事,正是《論語(yǔ)》所載的公伯寮訴子路一事(20)同上書,第14頁(yè)b。。
關(guān)于公伯寮訴子路(21)本段所引譚氏解“公伯寮訴子路”章語(yǔ),均見(jiàn)譚貞默:《三經(jīng)見(jiàn)圣編》卷七十四,第13-16頁(yè)。的歷史背景,何晏《集解》、皇侃《義疏》、邢昺《疏》、朱子《集注》都沒(méi)有關(guān)注,只有清代學(xué)者戴望推斷是孔子墮三都子路為季氏宰時(shí)的事,他說(shuō):“孔子為司寇,使子路帥師墮費(fèi),寮蓋以子路欲弱強(qiáng)臣訴于季氏。”(22)黃懷信主撰:《論語(yǔ)匯校集釋》,第1322-1323頁(yè)。其后崔述也主此說(shuō):“景伯之告,孔子以道之行廢言之,似不僅為子路發(fā)者,蓋孔子為魯司寇,子路為季氏宰,實(shí)相表里,子路見(jiàn)疑即孔子不用之由,然則伯寮之訴當(dāng)在孔子將去魯之前也。”(23)崔述:《崔東壁遺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407頁(yè)。譚氏認(rèn)為,這是孔子歸魯后子路再仕季氏時(shí)的事,他的理由有三點(diǎn),首先,孔子為司寇時(shí)頗得季氏信任,當(dāng)時(shí)并沒(méi)有人訴子路,譚氏分析說(shuō):“當(dāng)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使子路為季氏宰,將墮三都,于是叔孫氏墮?quán)C,季氏遂墮費(fèi)。墮費(fèi),季氏意也,所以鋤公山不狃叔孫輒兩強(qiáng)家宰也。時(shí)安有訴子路者乎?未幾而夫子去魯,與子路同適衛(wèi),主子路妻兄顏濁鄒家,是子路因夫子去也,非為訴也。”子路是因孔子去魯而同時(shí)離開(kāi),并非因?yàn)楸辉V。其次,子服景伯首次見(jiàn)于《左傳·哀公三年》,其主要事跡也都是在哀公時(shí)期,“哀公時(shí),康子執(zhí)政,凡會(huì)盟聘享大事,皆子服景伯主之。子貢介之,鮮有敗事。”因此,從其語(yǔ)氣“吾力猶能肆諸市朝”看,此時(shí)他在魯國(guó)有很高的權(quán)力和威望。而孔子為司寇時(shí),定公在位,季桓子主政,子服景伯還沒(méi)有登上魯國(guó)的政治舞臺(tái),根本不可能說(shuō)出這樣有底氣的話。最后,譚氏細(xì)致分析了孔子的語(yǔ)氣,認(rèn)為更符合哀公十四年遲暮之年的口氣,而與墮三都時(shí)的奮發(fā)氣象不同,他說(shuō):“子路自此去魯仕衛(wèi),不一年而死衛(wèi)矣,又不一年而夫子夢(mèng)奠矣,公伯寮之訴,蓋當(dāng)夫子七十一歲西狩獲麟之年也,然則將行將廢之命,夫子其知天命之終乎?《公羊》解云:天生顏淵子路,為夫子輔佐,皆死者,天將亡夫子之證,蓋有謂也。顏淵子路,與夫子共此天命者也。”公伯寮訴子路可能就發(fā)生在西狩獲麟之后,時(shí)孔子七十一歲,已到垂暮之年,心中頗多悲感,又聞聽(tīng)子路被訴,于是感慨系之,認(rèn)為道之行與不行,都是天命使然,豈是公伯寮能決定的?
通過(guò)以上幾個(gè)方面的分析,譚氏認(rèn)為公伯寮訴子路一事當(dāng)發(fā)生于哀公十四年,而子路也正因其訴而不得不離開(kāi)魯國(guó)回到衛(wèi)國(guó),并最終死在衛(wèi)國(guó)。而季氏將伐顓臾則發(fā)生在此事之前,當(dāng)時(shí)子路尚為季氏宰。譚氏的這一考證引據(jù)詳確,發(fā)前人所未發(fā),可以補(bǔ)子路晚年行實(shí)之缺。
四、據(jù)人物關(guān)系解讀經(jīng)文
《論語(yǔ)》表面看是一條條孤立的語(yǔ)錄,其實(shí)是以孔子為中心的復(fù)雜人物關(guān)系網(wǎng)的反映,很多語(yǔ)句都是基于特定的人物親疏上下關(guān)系而發(fā),只有在弄清楚人物關(guān)系的情況下才能獲得更好的理解。譚氏對(duì)經(jīng)文經(jīng)義的解說(shuō),往往借助于對(duì)復(fù)雜人物關(guān)系的梳理,以下仍舉二例。
第一,以孔子、冉有、季氏之間的復(fù)雜關(guān)系解讀“季氏將伐顓臾”章(24)譚氏解此章語(yǔ),均見(jiàn)譚貞默:《三經(jīng)見(jiàn)圣編》卷八十三,第13-23頁(yè)。。譚氏認(rèn)為,冉有、季路向孔子報(bào)告季氏將伐顓臾一事,并非二人的私自行動(dòng),而是受季氏的委托,“使二子征訪于孔子,尚懷不決之疑,來(lái)探孔子可否之意也。”因?yàn)檎鞣プ鳛檐妵?guó)大事需要高度的機(jī)密,季康子如果真想攻打顓臾,“即同二子謀,二子不敢不奉主命,而驟聞之孔子,泄軍國(guó)大計(jì)乎?”正因?yàn)榭鬃油砟暝隰攪?guó)威望極高,哀公和季康子都對(duì)孔子極為尊敬,國(guó)有大政必向孔子咨問(wèn)已成為慣例,所以孔子曾對(duì)冉有說(shuō):“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論語(yǔ)·子路》)哀公十一年,季康子曾就實(shí)行田賦之事派冉有咨訪孔子。而孔子也往往對(duì)國(guó)政利弊直言不諱,“即有聽(tīng)有不聽(tīng),而夫子正色侃論,靡所諱忌,彌縫匡救,不遺余力。固知非一端矣,是以伐顓臾之大舉,事未發(fā)而先聞。”對(duì)于季氏將要討伐顓臾一事,孔子分析了國(guó)家的形勢(shì),嚴(yán)厲地教育了冉求和子路一頓,要求他們勸止季氏的行動(dòng),充分體現(xiàn)了孔子憂國(guó)憂民的思想情懷。譚氏評(píng)論說(shuō):“此孔子為魯公、為季氏忠謀遠(yuǎn)慮,諄懇痛切,連帶四‘也’字,抑揚(yáng)鼓蕩,低回凄轉(zhuǎn),讀之可歌可涕,想當(dāng)時(shí)言者,呼吸耳提,不得只字間斷,一往深情,直從太和元?dú)庵袑懗鰺o(wú)限激烈,聞?wù)哂胁恍哪懢銊?dòng),愧汗浹背,翻然改圖者,非人也。”而最后的結(jié)果確實(shí)也符合了孔子的預(yù)期,“孔子痛言之,二子旋復(fù)之,而季氏亦旋聞之,旋已之,不復(fù)見(jiàn)其事于春秋經(jīng)傳也。”伐顓臾事未見(jiàn)《春秋》經(jīng)傳記載,可見(jiàn)此事并沒(méi)有執(zhí)行,由此可見(jiàn)孔子晚年在魯國(guó)和季康子心中的威望之高。
第二,以冉求在魯國(guó)政局中的關(guān)鍵地位解讀“季氏富于周公”章(25)譚氏解此章語(yǔ),均見(jiàn)譚貞默:《三經(jīng)見(jiàn)圣編》卷五十七,第10-14頁(yè)。。前人注解多對(duì)冉求持嚴(yán)厲批評(píng)態(tài)度,稱冉求“黨惡而害民”“心術(shù)不明”,認(rèn)為孔子說(shuō)“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是要與之?dāng)嘟^師生關(guān)系。譚氏則本著知人論世的態(tài)度,認(rèn)為孔子之語(yǔ)有其深意,并非簡(jiǎn)單地斥責(zé)冉求。譚氏分析了當(dāng)時(shí)的魯國(guó)局勢(shì),認(rèn)為冉求在當(dāng)時(shí)是奉孔子教誨,調(diào)和哀公和季康子關(guān)系、穩(wěn)定魯國(guó)的關(guān)鍵人物,“時(shí)哀公患三桓之侈,三桓亦患公之妄,君臣多間,國(guó)釁幾幾復(fù)作矣,夫子導(dǎo)哀公以自律,維持康子以不貳,俾冉求宣力調(diào)護(hù)其間。”哀公和季康子沒(méi)有像昭公和季平子那樣兵戎相見(jiàn),而始終相安無(wú)事,冉求發(fā)揮了重要的磨合作用,而季康子在哀公二十七年死后,魯國(guó)馬上就發(fā)生了動(dòng)亂,“哀公不旋踵而遜邾矣”。孔子雖然對(duì)于冉求有很多批評(píng),但冉求總體上還是能夠秉承夫子教誨的,所以不可能輕易與之?dāng)嘟^關(guān)系:“傳稱冉求進(jìn)則理其官職,退則受教圣師,其性多謙退,能承夫子匡救者也,旅泰山則責(zé)不能救,伐顓臾則極言而止,晏退朝則辨其政事之分,語(yǔ)季然則呼之具臣,而警以弒父與君亦不從。”冉求性格和順,為弘揚(yáng)孔子思想,穩(wěn)定魯國(guó)政局發(fā)揮了重要作用,故此章所謂“鳴鼓攻之”,只是一種警告,是“聲冉求之罪,而使康子聞也”,“聲冉求之罪,而使康子聞之,猶或可以止田賦,利公室……此夫子愛(ài)冉求以愛(ài)康子也,非絕冉求也,君子愛(ài)人以德,細(xì)人愛(ài)人以姑息,鳴鼓而攻,正愛(ài)吾徒以德也。”如果孔子真要與冉求斷絕關(guān)系,則“夫子所藉以匡救康子,彌縫魯事者伊何人哉!”這雖然只是一種揣測(cè),但從當(dāng)時(shí)人物關(guān)系的角度考慮,也未嘗沒(méi)有道理。
五、結(jié)語(yǔ)
綜合本文論述可見(jiàn),譚貞默的“本事”詮釋路徑基于這樣一個(gè)基本觀念,即孔子言論并非空發(fā),而必有具體場(chǎng)景和現(xiàn)實(shí)針對(duì)性,即所謂“本事者十九”,所以不能只局限于單純的語(yǔ)義詮釋,也要關(guān)注它的歷史語(yǔ)境。譚氏對(duì)《論語(yǔ)》“本事”的考據(jù)有幾個(gè)鮮明特征:第一,知人論世。通過(guò)考證人物性格、時(shí)代背景、人物關(guān)系等,對(duì)經(jīng)文做出全新的解釋,尤其人物性格是譚氏關(guān)注的重心,對(duì)季康子各章的解釋就是緊緊抓住了季康子好殺、貪婪、無(wú)禮等性格特征。第二,文獻(xiàn)互證。把其它文獻(xiàn)如《左傳》《孔子家語(yǔ)》《禮記》《韓詩(shī)外傳》等的相關(guān)資料與《論語(yǔ)》互證,又把《論語(yǔ)》前后相關(guān)章節(jié)聯(lián)系起來(lái),以類相從,形成一個(gè)“意義群”,在意義群中使各章的主旨更加鮮明。第三,情境建構(gòu)。本事詮釋不是單純的考證對(duì)話發(fā)生的時(shí)間、地點(diǎn)、所涉人物,而是將考據(jù)與經(jīng)文的解釋密切結(jié)合起來(lái),在考據(jù)的基礎(chǔ)上對(duì)經(jīng)文的主旨、要義進(jìn)行重新建構(gòu)。如譚氏在解釋“季氏富于周公”章時(shí)通過(guò)孔子、冉求與季康子關(guān)系的分析,還原了一個(gè)孔子冉求師弟匡救季氏、調(diào)和君臣關(guān)系的魯國(guó)政治格局。從這個(gè)意義上看,“本事”路徑不完全是考據(jù)學(xué),它實(shí)際上也是一種經(jīng)學(xué)詮釋學(xué)。
“本事”路徑對(duì)于《論語(yǔ)》詮釋具有重要的啟發(fā)意義。首先,使《論語(yǔ)》本文的意義更加豐滿。例如“季康子問(wèn)敬忠以勸”章,通過(guò)征引多個(gè)故事證明孔子所說(shuō)都是針對(duì)季康子的弊病而發(fā);居上不寬章、放于利而行章,將其與季康子聯(lián)系起來(lái),使這兩則經(jīng)文更有現(xiàn)實(shí)感。除本章所舉例證之外,譚氏對(duì)“夷狄之有君”章的解釋也很值得關(guān)注,他從當(dāng)時(shí)的歷史背景出發(fā),經(jīng)過(guò)縝密考證認(rèn)為這句話是在稱贊楚昭王,因?yàn)榭鬃訉?duì)楚昭王有很多正面評(píng)價(jià),還差點(diǎn)被昭王接到楚國(guó)。(26)譚貞默:《三經(jīng)見(jiàn)圣編》卷九,第37-43頁(yè)。譚氏這一觀點(diǎn)遠(yuǎn)比前人單純解釋句意更為形象生動(dòng)而意義豐滿。其次,突破傳統(tǒng)見(jiàn)解的束縛,提供全新的解釋。譚氏基于本事的解釋,常能突破前人定見(jiàn),而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jué),如對(duì)于季氏旅于泰山,傳統(tǒng)都認(rèn)為是批評(píng)季氏的僭越,而譚氏通過(guò)考據(jù)本事認(rèn)為是批評(píng)季氏去泰山祈福,是“非其鬼而祭之”。第三,進(jìn)一步加深對(duì)孔子本人思想、影響、社會(huì)關(guān)系的理解。如“季氏將伐顓臾”章,譚氏從字里行間讀出是季氏主動(dòng)派遣冉有子路向孔子征求意見(jiàn),而且事后也并沒(méi)有征伐顓臾,這些都體現(xiàn)了季氏對(duì)孔子的尊重和重視,也透露了孔子晚年在魯國(guó)的地位。總而言之,面對(duì)古今中外浩如煙海、五花八門的《論語(yǔ)》注解,《三經(jīng)見(jiàn)圣編》無(wú)疑是一部尚待充分發(fā)掘和重視的著作,其“本事”路徑也是一種很有學(xué)術(shù)意義詮釋路徑,有助于深化對(duì)《論語(yǔ)》和孔子思想的理解。當(dāng)然,由于資料的匱乏,探索《論語(yǔ)》“本事”會(huì)有很大困難,如果強(qiáng)探力索,還會(huì)流于穿鑿附會(huì)。但就可能的范圍內(nèi),參之以相關(guān)典籍,合之以前后章節(jié),考之以歷史行跡,再加以合理的推論與想象,在《論語(yǔ)》“本事”的探討方面,仍有很大的開(kāi)拓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