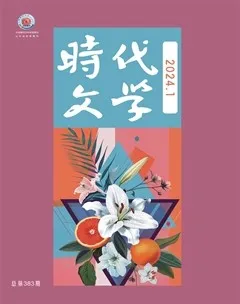日暮鄉關何處是
張立國 張宏圖
《芝鎮說》的作者逄春階寫過許多散文和報告文學,有多篇被《新華文摘》轉載,無疑他是成功的。但創作的激情使他不滿足于已有的成績,于是他又沖向了小說領域,便有了今天的《芝鎮說》。在與逄春階的多次接觸中,我們感到他能恭敬地對待周圍每一個人,又能保持自己獨立的思考。文如其人,體現在他的作品里也是既大膽突破又不逾矩,這便是我們眼中的《芝鎮說》。從家族生態出發展開敘事,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從家族內外的社會人文空間入手,在家族認同與排斥之中來探討“家族生態”“族際生態”以及民族存亡與發展,或許是目前探究中國文化的最佳視角。
一
在目前所有對《芝鎮說》的評論中,幾乎都提到了莫言的《紅高粱》,猛一看《芝鎮說》確實與《紅高粱》有相似之處,都有酒文化,都是在述說“我奶奶”,但與《紅高梁》的“虛構敘事”不同,在《芝鎮說》中,大多背景材料是真實的,是可考的。一個個歷史人物紛紛登場,無論來自于正史還是野史,它總是有史為據的。這一切構成了一個讓人毋庸置疑的“真實世界”。這樣寫人、寫物時有精準的依托,像被稱為“玉帶”的腰間黑痣,芝鎮的方位,1890年農歷八月初十的精準時間,《周易》《湯頭歌》《本草綱目》諸經典的引用,無不顯示其真實性的存在。然而故事卻是虛構的、魔幻的,整部小說其實是真實的歷史細節與文學細節描寫的巧妙糅合,是由真實推演、演化出虛構,抑或是由虛構推演、演化至真實,是虛構與非虛構的相互雜糅、交錯回望,由遠及近、由情入理,向著歷史深處求真溯源。小說敘事莊諧一體,磅礴、瀟灑、從容,并給人以“假作真時真亦假,真作假時假亦真”的審美享受。用當下的話說:這是在古今比較、新舊對照和前后映襯中謀求一種互文關系。抑或可以說這是一種別出心裁的跨文體寫作。用謝有順的話說:“好的小說,總是游走于紀實與虛構、微觀與宏觀之間,讓自我、意義、價值關懷、精神追問等,隱身于細節、經驗、語言和結構之中,進而實現某種綜合和平衡。”細細想來,逄春階如此書寫有其必然性。一是長期的記者生涯養成的職業習慣已內化為他的創作心理;二是他在散文和報告文學上的成功,鑄造了他的創作趨勢、創作取向和創作態度,他內心深處總覺得不將民間日常生活融入社會揉入大時代,會使作品陷入浮淺;三是他豐富廣博的知識積累,使他運用各種知識時得心應手,使小說具有藝術的信息量、思想的信息量、社會的信息量、歷史的信息量、文化的信息量等,作品的負載量遠遠大于作品本身。這是別人想學也學不來的。這三條均是長期積累的結果,非一朝一夕之功。
二
逄春階選擇的寫作對象是恰到好處的,是精準到位的,這主要是因為小說中芝鎮的風情、芝鎮的變革,是產生在特定的、典型的環境中。逄春階用他獨特的敘事方式和整體性的結構方式,寫出了芝鎮的獨特性、差異性以及文化上、精神上、生活上的歷史自發性,獨特的結構方式和敘事的節奏流程同頻共振,這就構建了《芝鎮說》整體性的價值和意義。
逄春階不是遠遠地觀看,更不是無節制地虛構和想象,他沒有遠離芝鎮的生活和鄉親,他與芝鎮零距離、無間隔地融為一體,且沉浸陶醉其中。他以同情之心看人看一切生物,以體悟之心著文,以智慧之心言說世道人心與存在之理,以語言之美鋪陳芝鎮的一切。
芝鎮不是概念,不是符號,它是歷史的,也是現實的,是精神的,也是物質的,是文化的,更是生活的,那么如何把它真實生動地表現出來?如何橫跨漫長的歷史,寫出芝鎮的演化變革?這就需要一種獨特的結構方式。
逄春階采用了“我”從童稚到成熟,從“小乖乖”到“大記者”,不停轉換“第一人稱”的敘事視角,運用隱喻系統和成人化的少年視角,在多層次的人性張揚與平衡中,進行了扭結如麻花的敘事。形式和內容必須琴瑟和鳴,將歷史與現實自然地糅合在一起,在懸念制造和蒙太奇畫面的不停切換中,從多角度多層次展示了公冶家族歷史發展變化的豐富性與多樣性,也從多角度展示了鄉鎮鄉土生活的全貌。正如李桂奎先生所言:“作為第一人稱敘述者的‘我似乎有一種‘戀祖情結。《芝鎮說》同樣有一種‘戀祖情結,這里有從古樸到現代的書寫,古的畫像與今的‘捏影照片相輝映,記錄下公冶家族的平凡生活而又與眾不同的奇跡。”(《芝鎮說》4頁)童稚是古樸的戀祖戀鄉的清純,是以童稚的純正的目光仰視世界,在死亡與苦難中尋求詩意。而成熟是理性的、批判的現代意識,從俯視點滴的民間記憶入手,呈現歷史片斷,關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留下難忘的家國記憶和民族大義。這巧妙地使文化崇拜與文化批判自然融合在一起,讓世情俚俗與風云變幻的歷史相連,讓地方性文明與世道人心相攜,讓精微古樸的日常生活描寫與時代變革的歷史畫卷互為鏡像,甚至互為表里。這也正符合我們所堅持的文化發展方向:繼承中批判,批判中繼承。
芝鎮至此不再是符號化的地名,而是具體可感的真實存在,不再是一個被作者凝視的對象,而是一個不斷塑造著芝鎮人、山東人、中國人的肉體和精神的復雜空間。《芝鎮說》是對民間視野、歷史視野、文化視野的一次重新發掘,是帶著啟蒙特征的鄉土寫作,更是對故鄉摯愛的見證。
三
逄春階行文的語言是快捷的,堪稱快節奏。在小說敘事中,快節奏意味著沒有使用延緩節奏的技巧,意味著作品沒有注水,意味著情節推動、敘事狀態的快速和跨越式進展。小說的內在力度和高密度的信息量支撐了其敘事速度,最終構成了一部大結構、大氣象的文學作品。
作者的敘事語言整體而言是儒雅、凝練、雋永的,有閱盡人間滄桑的味道,有乘勢向前的涌動,無散淡玩味的遺老遺少之風,讀之讓人感到磅礴大氣、瀟灑從容。
讓人稱奇的是在這樣的語速下,竟出現了許多連綿轉意,慢半拍的語言:
“老人家說,騎車累了,就喝口酒解乏。我聞到了地圖上的酒香。”(《芝鎮說》15頁)
“你這公冶令樞大爺啊,就是會瞎編故事,但伙計們點菜招待狗確實是真的。”(《芝鎮說》18頁)
“喝醉了還會狡辯,看來不缺心眼兒。”(《芝鎮說》28頁)
這樣的句式全書很多,既有歇后語的味道,又有連綿頂針的意味,用山東老百姓的話說,這叫“說話大喘氣”,是民間語言技巧的一種。所謂“大喘氣”是指一句話不一口氣說完,中間略有停頓,用逗號隔開,后半句或是前半句的解釋或是前半句的反轉。而恰恰是這種“說話大喘氣”的句式,給人一種自然轉折、興味綿長之感。這是逄春階獨有的句式,也是中國語言豐富性的又一種體現。小說是一種語言藝術,多彩多姿的語言表達方式,是小說成功不可缺少的條件。獨具一格的語言特色、語言風格是每一位成功的作家必備的文字素養。魯迅尖刻的入木三分的諷刺,老舍具有京味逗哏的調侃,錢鐘書深藏智性的幽默,雖然都可通稱為諷刺幽默,但各有不同,各具特色。《芝鎮說》產生的“逄式語言風格”,用“大喘氣”替代“但書”應是一種語言的探索與進步。我們不知道這是逄春階刻意為之,還是下意識的語言習慣,但應引起評論家和語言學家的充分關注。
作品結構活潑跳躍、波瀾起伏,敘事磅礴、瀟灑、從容,倒敘、插敘、直敘、折返、引述、綴語無不隨意差遣,弗尼思和公冶德鴻作為不可缺失的兩個藝術符號引領著作品敘事。跟隨作者的思路自然前行,使作品有奪目之力、無雕琢之痕。作品實際采用了一種將時間空間化的敘事策略,在作品的順時自然流淌中全面展開芝鎮大有鄉的人和事,再雜之逸聞趣事、插科打諢,如歷史傳說、民間傳說、神話傳說、現代傳奇,又如生活常識、民間俚語、史實考證……想不波瀾起伏、活潑跳躍都難。這種引經據典的寫作方式,大大增添了作品的知識性,給人一種智性審美的享受。作品從歷史敘事中展示了個人歷史的對比性,把被時代的高音所遮蔽的微弱的聲音,以及可能被我們遺忘的精神充分釋放出來。這種精神又跟記憶密切相關,由此,勾連起同代人的歷史記憶,也可能會喚醒非同代人的精神向往。
凡是敘事性作品,描寫是不能缺少的,描寫的成功與否是作品成功與否至關重要的因素。但每位作家在描寫的方法技巧上會各顯不同,各有千秋。逄春階的描寫有他自己的特色,具有多樣性、獨特性。首先是細致的場面描寫具有立體感、畫面感、可視性,如對二大爺踢雞、夠書的描寫,呈現出畫面感、鏡頭感;其次是描寫的準確性、細致性,如對民俗中祭祀的描寫;再次是描寫的趣味性,特別是對那些醉漢的描寫,可謂妙筆生花。另外,更讓人驚嘆的是那些震撼人心的對犧牲、血性、剛烈的描寫,如對高銘乾英勇捐軀的描寫,對日本人兇殘行為的描寫,以及對戲詞搭配的場景描寫、人物心理描寫、動物描寫、別具一格的景物描寫等。總之,《芝鎮說》的描寫是多元的、全方位的、生動的、新鮮的,是有別于傳統的。這恰是小說成功的原因之一。
以上從四個方面談了我們對《芝鎮說》以及其作者逄春階的管見,一己之見,未必正確,更談不上全面,只表示我們喜歡這部小說,并說出我們喜歡的原因。既然福克納能通過自己家鄉那枚“小小的郵票”,生發出一個“自己的天地”,莫言可由老家“高密東北鄉”,創造出“自己的文學王國”,那么逄春階也大可經由“芝鎮大有鄉”編織出自己的“文學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