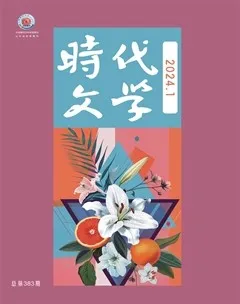逆行的金魚
董逸霏
1
天空被撕裂開一個洞,雨鋪天蓋地地澆下來,形成了一張破無可破的屏障,透明得像是膠質物,屏障外的一切景象都在模模糊糊地滑動。伸手,她甚至能摸到凸起的一塊兒,在肌膚表面流動,又順著指尖掉落。屏障順著她的動作被掀開,視線變得明朗,她甚至能看到睫毛的翕動,扎在下眼瞼處似有微刺的感覺。四肢像關節被抹了潤滑油的娃娃,齒輪開始轉動,她站起來,身上掛著的屏障的碎片又順著她的身體匯聚到了腳下。
四周圍著一群人,他們臉上的神情如復制粘貼,瞳孔外凸,嘴巴微微嘟起、張開,像在魚缸中溯游的金魚。“金魚”是什么模樣她并不清楚,但這個詞語已然生長在了她的大腦中,就和那些錯綜復雜的神經一樣自然,以至于她一瞬間就想到了這個比喻。
這些人有男有女,無一例外都穿著白色的制服,身上蓋著消毒水的味道。她突然感到煩躁,低頭看向自己的身體,鎖骨、胸部、肚臍、大腿、小腿、趾間,她可以準確地點出它們的名字。一種異樣的感覺突刺刺地長出,旁邊的架子上搭著幾塊白布,她扯下來,纏在身上,仿佛又為自己加了一層遮蔽。后來她才知道,這種刺刺的感覺名叫“羞恥”,雖然她自帶的詞典中包含了這個詞,但她真正弄懂它的含義也耗費了不少時間。帶走她的那個人姓李,他們叫他李博士,他給她取名為李玫,因為她的生日在四月末端,正是玫瑰開放的季節。李玫有時想,如果她有弟弟妹妹在九月出生,豈不是要叫李菊或李桂?
他們居住的地方離城市很遠,頗有與世隔絕之感,屋后有一片小院,他們剛來的時候這里還堆滿了廢磚瓦片等,李博士將那些東西清除掉后,她在裸露的土地上種花,第一年種玫瑰,第二年就種菊花,就這樣循環往復,他們的宅后只有紅與黃兩種色彩。
李玫并沒有時間觀念,她只分得清光和暗,太陽的出現驅逐了黑黢黢的夜,一段時間后暗色又再度壓上來。她沒去過學校,那些書本上的知識烙在她的骨骼上,她的一舉一動都是通過精密計算,測量出一個最合適的角度再執行,包括抬手高低與步伐之間相隔的距離,這樣能最大限度地延緩零件的老化。可惜這一切李玫并不知道,她從屏障中掙脫,又掉入了李博士為她鑄造的襁褓。只是有一天,李博士突然停止了動作。上一秒他還在沙發上讀書,下一秒就像斷了電的機器人,直愣愣地傾倒在沙發上。她蹲下來,打開離他們最近的一盞臺燈,李博士布滿瘢痕的臉上被歲月勾勒出數不清的溝壑,深深淺淺,錯綜復雜,像電視機中那些重巒疊嶂夾著的山路。電視機柜上放著他們的一張合照,年輕的李博士被困在了永不褪色的相框內。她才意識到他不年輕了,她之前卻全然不知,在流逝的時間內,只有她永遠矗立在洪流中央。醫學上,李博士的這種表現被稱作“死亡”,她突然不知道該怎么做,那些與生俱來就存在于腦內的知識派不上用場,她將沉睡的李博士拖到臥室的床上,抻開嶄新的被單,將他從頭到腳一寸一寸裹起來,像她平日對著教學做那些手工制品一樣,精致得無可挑剔。這費了她很多的力氣,李博士畢竟是男性,就算已形同枯槁,那些嶙峋的骨頭也依然存在分量。做完這一切,她走進洗手間,摸到電燈,明亮的光從頭頂傾瀉下來,刻在鏡子中的李玫,依舊是那張照片中的模樣。
2
兩天后,李玫按照李博士留下的電話本給研究所打電話,又過了半天,那些人來勢洶洶,像龍卷風一樣鋪天蓋地席卷而來,又將他們刮走。車上,有個看起來年紀與她相仿的女孩教訓她,為什么不早點通知他們,過了二十四小時,尸體已經從內部開始腐爛,會影響后續的下葬工作。那女孩一副不好惹的樣子,李玫什么也沒說,低下頭來,兩手放在胸前,不停地揉搓,看起來很心虛。
李玫下車的時候,更多的白大褂圍了上來,幾乎都是生面孔。他們將李博士抬下來,之前裹在他身上的被單換成了肅穆的白布,與那些白大褂融在一起。她想到了一個詞,“葉落歸根”,李博士本不屬于她,他從這里分離出來,死后自然也是要回到這里的。
李博士是眾人的焦點,李玫就跟在他們后面,游蕩進基地。一路上沒人同她講話,也沒有人對突然出現的她表現出驚訝,只是當她不存在,或是原本就是這里的一部分。
他們通過一條長長的走廊,四壁都被漆成白色,頂上白色的光撲下來,她在白色的波浪中踽踽前行。快要走到盡頭時,一個不知道從哪里出現的女人注意到了李玫,女人的目光擦過她的一瞬間眉頭擰成了麻花,扯著嗓子大喊:“這是誰負責的仿生人,怎么竄到這里來了?”
白大褂們轉過頭,先前在車上教訓過她的女孩率先反應過來,湊過去在女人的耳邊說了幾句話,女人的眉頭略舒展,對著女孩點點頭便離開了。白色軍隊繼續前行,女孩攔在李玫面前,說:“你不用往前去了,跟我來。”
她們拐進了另一條白色的通道,構筑與之前那條別無二樣,李玫甚至懷疑她是不是進了放大版的蜂巢,過于規整而顯得刻板。女孩要她的身份證。她從李博士留下來的錢包中翻出來,那張薄卡看似與正常人的身份證沒什么區別,但上面只印刷著她的照片與名字,并沒有出生日期。女孩又遞給她一張新卡,白色,上面印刷著三個數字——“001”。
“這是你的新名字,”女孩說,“你是這里生產出來的第一個具有自我意識的仿生人,所以你的編號就是001。”
“我的名字叫李玫。”李玫說,“這是李博士為我起的名字。”
“李博士已經死了。”女孩有些不耐煩,“你有名字只不過是因為那時仿生人還算稀有,現在我們這里每天都會生產出上千個仿生人,哪有精力給每個都起名字。”
女孩說完就離開了。李玫想起李博士對她說過的話,她的后頸藏著一個按鈕,它被植入在皮膚表層下,形成小小的凸起,只要輕輕一按,她就會被“格式化”。至于“格式化”的含義,就是抹去李玫自誕生后的一切記憶,包括烙在大腦的知識等。這個按鈕是李博士為避免她落入外人手中而準備的應急措施,畢竟那個年代的仿生人很珍貴。而現在,她突然有想要按下它的沖動。李玫今天沒有扎頭發,烏黑的發絲凌亂地掛在身上,她將手探進去,從里面撩起半邊頭發,摸到了藏在皮膚下面的凸起,它像一顆痦子。也許是它待在她的體內太久,那些神經已經與按鈕構成了某種緊密的鏈接,一碰就疼,針扎似的。她將頭發放下,將外衣的領子立起來,保護住自己。
自己絕對不是因為疼痛而放棄格式化的,她這樣想。她總覺得還有什么事情沒完成。李博士離她而去,很快就要變成這大千世界的一抔土,消散在風中。李玫走到了這條走廊的盡頭,兩邊是兩道玻璃門,右邊那一間像是正在進行著生產工序,一排排巨大的培養皿將房間填滿,一只機械手通過軌道連接天花板,在培養皿間靈活地游走。它伸進去,抓起一個仿生人,像是提著一只軟骨頭的雞,李玫看到那層屏障從他身上剝下,又落回培養皿。屏障是水,抑或是什么液體,與她誕生時裹著的那層一樣。機械手將仿生人放在傳送帶上,盡頭是一臺更大的機器,像是張著血盆大口的怪物,仿生人被送進怪物口中,便消失不見了。也就是這時,李玫才完全意識到她是這群仿生人的同類。李博士同她在一起時,他總是刻意模糊李玫的身份,幾乎將她當作一個普通人對待,久而久之,她也忘記了人會經歷生老病死四個階段,自己卻不死不滅。孕育她的不是溫暖潮濕的子宮,而是培養皿。于是,這天下午,李玫從基地中逃走了。
3
出逃的過程并不艱辛,基地的后方是垃圾站,李玫外衣里面穿著一件白襯衫,她將外衣拋棄,混進了白茫茫的醫療垃圾中。車輛開動的時候,她坐在那些被揉碎的塑料與白色包裝袋上,凜冽的風像小刀一樣,刮在臉上涼颼颼的,她有些后悔剛剛將外套丟掉。
車開得并不穩,一路顛簸,幾只塑料瓶骨碌碌地滾落,隨著車輛吐出來的黑煙,很快消失在她的視野中。天色暗了下來,大朵大朵的云蓋住了太陽,與天際線銜接,像是下一秒就要墜入大地的懷抱。李玫抬起頭,遠處的高樓刺破云層,露出半只尖角來。
車在一處廢品回收站前停下,趁著司機還沒下車,她靈活地從廢品堆中鉆出。大部分垃圾還算干凈,至少沒什么異味。她撣了撣衣服,向外走去。她之前看到的那處高樓似乎離自己更近了些,向上看,高樓大廈林立,霓虹燈牌絢爛,數不清的車輛縱橫在黑色的血管中。而四周多是低矮的老式居民樓,與炫目的燈光格格不入。她擠進一條小巷,一群小混混樣的男孩靠在看上去岌岌可危的磚墻旁抽煙,在她經過的時候他們中有人吹了個口哨。李玫繼續向前走,昏暗的天空飄起了雨。雨落在身上的感覺并不清爽,黏黏糊糊的,她切進屋檐與磚房的一處空隙中,抱著雙臂等著雨停。
門打開,一個孩子鉆了出來,并不怯,而是上下打量著李玫。她也回過頭去,這是個男孩,十二三歲的樣子,初秋天氣卻只穿著背心短褲,褲子上還落著兩塊補丁,看得出來,它的主人很想將其恢復原樣,但那兩塊布料插在短褲中實在突兀,像樂曲里不合調的音符。雨大了起來,男孩抹了把臉,看上去臟兮兮的。
“你是誰?”男孩率先破冰,“站在我家屋子下面做什么?”
簡單的問題,李玫卻不知道如何回答。如果交代了身份,她極大可能會被再次送回到研究所,她便說了自己的名字,李玫,喉嚨卻像塞了團棉花。
“雨太大了,”她抬頭望了望天,雨勢絲毫沒有減小的意圖,“只有你家的房子有屋檐,我在這里躲雨,雨停了就走。”
男孩半信半疑,正打算回屋去,里面卻傳來細細的呼喊,李玫沒聽清楚具體內容,但卻辨別出聲音的主人上了年紀,應該是男孩的奶奶或外婆。男孩進屋去,卻沒關門,李玫站在門口,想要向內探去,又覺得不太禮貌,于是靜靜地等待。過了一會兒,男孩出來,沒說話,揮揮手示意李玫進去。內里空間狹小,擠著一張飯桌、幾把凳子、兩張被屏風分割出的床,柜子被填補在空隙中,不少都掉漆抑或是開裂,一看便知是老古董。一個老太太蜷縮在靠里的那張床內,背對著他們,用像是校服外套的衣服將自己裹起來,聽到他們進來,她努力地用壓在下面的那條腿做支點,牽動著上半身立起,將自己旋轉過來,就像做飯時將煎餅翻面那樣,臃腫的身子落地時發出一聲悶響。
“我奶奶,”男孩說,“她身子不好,又逢雨季,這幾天腿痛得都下不來床。”
李玫想說現在不少人都在用人造四肢填補瑕疵的身軀,卻在這話即將脫出口的一瞬間收了回去。人造四肢價格高昂,她環顧四周,可能這一間房都不抵一條“人造腿”。李玫在李博士的庇佑下生活了這么多年,確實沒吃過什么苦,甚至她原來的一個臥室都要比這里寬敞許多。
“小姑娘,”老人開口,眼睛和睜不開一般瞇成一條縫。“這雨一時半會兒停不下來,你不如就在我們家坐坐,我讓小宇做飯。”
“小宇”應該是男孩的名字,他在聽到奶奶喊他時不情不愿地打開屋內的另一扇小門,鉆了進去。李玫這才發現原來這屋子不止一間房,這間分隔出去的應該是廚房,她本想跟進去看,但男孩順手把門帶上了,她只得搬來張凳子坐下。屋子內沒有時鐘,只在左上角挖開小小一道口子,填上一塊玻璃,以此來辨認大概的時間。李玫自進屋來就十分在意她對面那塊墻,墻皮脫落了大約一半,裸露出磚塊,斜在上方的一塊翹起來,看著也要掉下來。她幾次想站起身,將那塊搖搖欲墜的墻皮剝掉,但那像紙糊起來一樣的老太太卻幾次三番睜開眼睛,最后竟對她扯出一個笑容來,她不好動作,只好回應對方一個同樣生硬的笑。
男孩端著兩盤餃子出來,放在桌上,又回去拿了兩只空碗與筷子。沒有醋,李玫就蘸著餃子盤中的一點面湯吃。餃子餡兒還算鮮,皮破開后汁水順著舌尖流到喉嚨中,美中不足是缺乏鹽的點綴。男孩夾了幾只餃子,坐到老人面前,將餃子扎在筷子上,細細地喂進她嘴中,有不少湯汁順著口角流了下來,他撩起背心給奶奶揩凈,本就不甚干凈的背心又添了幾處暗黃。等奶奶吃完后,他才坐回椅子,慢吞吞地咀嚼。
4
李玫最終留在了男孩家。那天晚飯后雨還沒停,他們在屋檐下,李玫伸出手來接雨,頭頂的霓虹燈愈發絢爛,光柱穿破了雨幕,在高樓大廈間肆意舞動,像是在他們一步之遙外,卻又抓不住。男孩叫她不要碰雨,這些液體具有腐蝕性,雖然濃度不高,但帶來的危害不容小覷。后來他們就一直蹲在那里,斷斷續續地聊天。男孩的全名是顧新宇,還在上初中,放學后會去做兼職。李玫除了名字,并沒有什么可講的東西,她的知識豐富,對世界的認知卻貧瘠,她只能給男孩講一些她從電視機與書上看來的內容。男孩問她的年齡,李玫只記得自己從“屏障”中誕生的那一刻,他們說她是二十二歲,她的真實“年齡”可能都與男孩的奶奶一般大,但她只對男孩說“二十二歲”。
“你都去過哪些地方?”顧新宇問。
李玫愣了一下,想著該怎么回答,最后搖頭。說我去的地方很少,對外界的了解主要來自父親的告知,還有電視機和書本。
她不知道如何稱呼李博士,后想到他們是同姓,應該算是人類倫理上的“父女”關系吧。
“那你算是離家出走嗎?”顧新宇說。
“我父親去世了。”李玫說。她意識到這樣回答算所答非所問,但除此之外,她不知道該怎么回答,于是打岔,說:“我只是想看看這個世界真實的樣子,畢竟,我連金魚都沒有見過。”
“金魚?”
“就是那種全身是透明的金,尾巴還分成幾瓣的魚。”她描述道,“我之前也只在電視機上看到過。”
《重慶森林》中的金魚街,一尾一尾的金魚被封在透明的塑料袋中,掛在鐵架上售賣,在波光粼粼的水下孤獨地吐著泡泡。這個橋段令她印象深刻,有那么一瞬間她甚至覺得自己就是金魚,生來便圄于塑料袋一般的屏障中,只等得有緣人將她帶走,好還她獲得了短暫的自由。與金魚不同的是,金魚的壽命相對她來講,只有短短一瞬。
“嗯,唔。”顧新宇含含糊糊地說,“《重慶森林》……嗎?這個電影我好像聽過,但好像是幾十年前的老片了吧。”
“差不多吧。”李玫自己對時間本就沒什么概念。
顧新宇告訴她,這里靠海,這里的人原本會在夏天和秋天去“趕海”,運氣好會捕撈到不少海產,不知道有沒有她說的“金魚”。但這些年工業化過于迅速,污染與疾病泛濫,趕海就變得沒什么意義了。他從未去過海邊,那兒的污染程度是這里的兩三倍。
他們走進屋里,男孩和奶奶擠一張床,李玫獨自睡外面那張。她想不太明白他們為什么要“收留”她。是出于對她失去父親的憐憫?抑或是他們真切地對李玫講的那些東西產生了興趣?第二天,顧新宇放學后,帶回來一張折疊床,插在屋內剩余的地方,三張床排在一起像是幼兒畸形的牙齒。李玫問他哪里弄來的,他說從自己兼職的那家維修店拿來的,老板不要了,讓他扔出去,他就拿回來了。
李玫半信半疑,原本想問他打工的地方,后來看他并不是很想說的樣子,作罷。他們都有秘密,譬如李玫是“仿生人”,但為了自己的安全考慮,她的偽裝一直很好。
5
日子一天一天過去,在這里,春夏秋冬有了實感。如果說李玫原來的居所是溫室,那這里可以稱得上是環境極其惡劣的荒野。幸好冬天很短,只有那么兩個月,但他們依舊買不起可以取暖的東西。有時候顧新宇會偷偷用外套從修理廠兜點煤回來,將它們放進一個大桶里燒。每當這時候,顧奶奶的眼里終于透出點光來,緊接著便會用手臂靠著床將自己支起,瞇著眼瞧桶內濺出來的一兩點火星子。只是顧新宇的外套被染得黝黑,那些煤灰好像滲在上面一樣,怎么洗都洗不掉。
春天是最難挨的,濕氣伴著冷氣浸在人骨子里。李玫想著自己出去打工,他們這段時間一直靠著顧新宇兼職的錢與街道給的那點補貼過日子。后來想想還是作罷,一方面她擔心自己的身份被識破,另一方面顧新宇叫她照顧好奶奶,這段時間對于風濕病人來講最不好受,錢的事情他會想辦法解決。李玫也是這時候才撞破了顧新宇的“秘密”。她在某一天出門買東西的時候,看見他飛奔過街角,沖進一家黑漆漆的店面里,外套和頭發被風吹得豎起,像只張開了翅膀的鷹。那家店的招牌搖搖欲墜,上面漆著凹凸不平五個大字,她只能辨認出后三個字——“維修店”。李玫并沒有湊過去看,而是在當晚直截了當地問顧新宇,你工作的那家維修店是黑店吧?男孩的眼里閃過一瞬的訝異,隨即又斂回去。他們從房子里鉆出,又站在屋檐下,顧新宇問她,你其實是仿生人吧?李玫不回答,將話題岔開,繼續問顧新宇關于打工的事情。兩人就這樣默然僵持了很久,最后還是男孩先松了口:“那家店主要做機車維修,偶爾還接一些別的活兒。”
“我還以為你是在那種正規的維修廠工作。”
“怎么可能,我未成年,人家不會要的。再說,我們這兒哪里有那種大廠,都是小店。”
“那你怎么會知道我是仿生人?”
李玫其實也沒想再隱瞞了,她在顧家待了也有一段時間,她相信他們不會把自己的秘密捅出去。
“我說的‘別的活兒,就是仿生人維修。我們親自接觸過仿生人,自然能看出你們與人類的不同。其實你來到這里的第一天,我就有所發覺,不然……我也不會將你留下。”男孩說,“不過你放心,這里幾乎沒人見過仿生人,他們是看不出來的。”
李玫點點頭。仿生人價格昂貴,他們幾乎不會“生病”,但只要出了問題,還需另掏一筆可以算是巨額的費用送到指定工廠進行“維修”。顧新宇的服務對象應該是那些付不起修理費只能偷偷找“黑店”進行維修的人。但她后知后覺,男孩反而是因她是“仿生人”才選擇將讓她待在這里。她不知道該說些什么,李博士給她設計的語言系統還是太匱乏了。
后來他們誰都沒提這件事,又過了幾年,顧新宇高中快要畢業了。說是高中,實際上是掛名的中專,其實他當時的分數是夠上普通高中的,但他說,中專學費低,出來后分配工作還包吃住。他還說,現在的世界和之前大不同,就算他考上大學,工作也只是會體面些,工資不一定高。
李玫有時會到學校給顧新宇送午飯,他們學校砌的是土墻,門口用碎磚塊碎石塊兒一堆堆壘高,就像之前她在戰爭片里看到的戰壕,墻上邊用生銹的鐵絲網圈住,中間圍著幾棟矮小的房子。就算是上課時間,都有不少穿著校服的混混靠在墻邊抽煙,他們在見過李玫幾次后,目光總是不老實地在她身上滑來滑去,后來見她等的人是顧新宇,他們開始肆意編派他們的關系。李玫一開始還會和他們解釋自己是顧新宇的姐姐,混混們面面相覷,發出“哧哧”的笑聲,粗重得像是野豬從鼻子中擠出來的聲音。姐姐?什么姐姐,我看你是他在外面養的女朋友吧!李玫不想和他們多計較,總想著忍一忍就過去了,只是后來他們愈發放肆,有一次直接演變成了對顧新宇的謾罵。李玫從路邊撿起一塊石頭,直接砸在了混混臉上,她砸得又準又狠,所有人都愣住了,那塊石頭經過了太陽的炙烤,在她手中還有余溫,燙在皮膚上火刺刺的,那個混混反應過來,像只瘋狗一樣對著她撲了上去。
她理智回籠的時候,自己癱在地上,顧新宇蹲在她旁邊,臉上濺著血,左眼腫了起來,像有一只豐滿的橘子掛在了他的臉上。李玫伸手,對著太陽,看見沾在上面的液體,黑紅黑紅,黏糊糊的,在兩根手指分開的時候還拉出了細絲。四周空無一人,她知道自己現在的樣子一定很丑,心頭卻涌起一種說不出來的爽快,這是她第一次打人,在揮動拳頭的那一瞬間,她突然覺得自己和正常的人類并沒有什么區別。
很快警察就來了,他們帶著手銬,銀色金屬在陽光下明晃晃的很是刺眼,拷在手上時卻是徹骨的涼。李玫和顧新宇被押送上了兩輛不同的車,在分別的那一刻她抬頭,發現顧新宇也在看她,于是她將唇微微聚攏,腮幫鼓起,向對方做口型:剛剛我們打贏了沒有?顧新宇面朝太陽,陽光在他的臉上鋪開,蓋住半張臉,他只得將眼睛輕輕瞇起。但看見她像金魚一樣的神情,他原本繃緊的嘴角松落了下來,向兩邊緩緩扯開,竟露出了一個笑容來,他對她點點頭。這是這么多年來她第一次看到他笑,她總覺得顧新宇太過于成熟了,沒有孩子的樣兒。
與他們破敗的居所相比,警局的環境可以稱得上是天堂。警察審問她時她心不在焉,抬頭看懸掛在上方的時鐘,都快要下午五點了,她久久未歸,顧奶奶會不會擔心她,會不會挨餓?她的手不安地在桌子下方動來動去,她有搓手的習慣,但手銬的金屬環阻止了手指的碰撞。警察很敏銳,馬上猜測出她這是慌亂的表現,問她有什么事。她問,還有多久能結束,我奶奶一個人在家,她身體不好,我要回去照顧她。
令李玫意外的是,在警車前的那一次對視,竟成了她與顧新宇見的最后一面。他們都只受了些皮外傷,有個混混進了醫院,但最終也沒什么大礙。顧新宇因未成年只被拘留了一周,而李玫的仿生人身份暴露,被強制送回了基地。其實她能感覺到,她被審訊的那天,警察們一開始并沒有意識到她是仿生人,后來有人在外面敲門,其中一個警察出去,回來的時候臉上帶著一副了然的表情,他貼著同伴的耳朵說了些什么,于是那副神情也被傳染給了另一個人,接下來對她的判決就全部圍繞著“仿生人”這一點展開。而這里知道她仿生人身份的只有一個人。
李玫并沒有什么情緒,相反,“仿生人”這一身份為她免去了不少的麻煩,他們似乎對仿生人有著另外一套判決方式。至于顧新宇捅出她身份這件事,她并不是不能理解,畢竟他還有奶奶需要照顧,為了奶奶,舍棄“姐姐”是理所應當的事。
6
回到基地后,李玫的生活變得空白而單一。她被限制住了行動,鎖在一個小房間內,不過還是要比顧家的房子大上一些。房間沒有窗子,只有滿目的白,白墻、白色的桌子、白色的椅子、白色的床鋪……房間里附帶著獨立洗手間,她沒事做,經常坐在馬桶上,打開排氣扇,聽著扇葉鼓動的嗡鳴,一坐就是一整天。
過了一段時間,那扇緊閉著的門終于敞開,白衣人們帶著李玫出去,也不說去做什么,就和她第一天來到這里時一樣,白色的軍隊簇擁著她前行,一路上她聽到他們交頭接耳,說什么“檢查”“放逐”一類的詞,只言片語組不成完整的一句話。她被帶到另外一間房,里面許多一模一樣的儀器組成了鋼鐵森林,其中一個白衣人將她推進其中一只,合上蓋子,伴隨著“滴滴”聲,頭頂上的光亮起,那些小光柱像是一把把箭穿透她的身體,卻不疼,只是皮膚表層癢癢的。燈滅后,白衣人又將她帶出來,將她塞進一輛車內,空間很大,里面坐滿了同她一樣的仿生人,就連衣服也是如同復制粘貼一般。李玫挨到一個邊角,小心翼翼地坐下去,她旁邊坐著一個女孩,單看樣貌年齡與她相仿。
目的地是一座巨大的工廠,下車后,他們被一個看上去像總管模樣的男人排成兩列,男性一列女性一列,李玫在隊伍的尾端,她趁總管不注意,偷偷打量四周,發現身邊這些仿生人老少皆有,最小的看起來甚至不滿十歲。
他們的工作很簡單,仿生人“殯儀”,每天每人輪班十二小時,工作結束后可以在廠里四處轉轉,但是不能走出廠外。車上那個坐在李玫身旁的女孩與她分在同一間房,也是同一組,她們很快熟絡起來,女孩的編號是“383”,類別為家政仿生人,她在自我介紹時向李玫展示箍在手指上的老繭,又厚又粗的一層,與她年輕漂亮的臉蛋完全不符。女孩說她被生產出的年齡設定是二十歲,她效勞的那家主人由于不育,并沒有留下子孫后代,她在那一家人去世后被回收,進行身體檢查。由于還能夠正常運行,便被“發配”到這里工作。而這里的仿生人編號幾乎都在前一千,屬于“元老”級別,在他們后面被生產出的仿生人都會遵循正常人類的生老病死規律,“死”后被送到這里來,進行零件拆解,再運回基地,進行下一批的仿生人制造。
李玫不喜歡別人叫她的編號,她便告訴“383”她的真實姓名,女孩聽了之后很感興趣,也想給自己起個名字。恰逢那幾日李玫正在給她講花木蘭的故事,她特別喜歡那句“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便給自己起名關若飛。
某天,李玫突然發覺一直在廠里的男主管不見了,晚上回來聽關若飛給她講,男主管應該是去世了。她突然有種悵然若失感,總覺得她來到這里好像還沒幾天,男主管雖然大部分時間嚴厲,但對他們很好,做過的承諾一定都會兌現。新上任的主管有些懶散,甚至后面自由活動的時間都允許他們出廠。那天,李玫和關若飛時隔多年再一次“重見天日”,天公也作美,在原本灰撲撲的天中掛上半枚太陽,李玫遠遠地望過去,她第一次逃出基地的時候撞到的那棟又瘦又高的樓房依舊矗立在那里,似乎比先前長高了一截。
走過一條街的街角,遠遠地,李玫看到兩只白花花的腦袋湊在一起,她走近,是兩位在擺攤的老人,他們的面前放著兩個手編竹筐,筐內兜著一個個塑料袋,袋中兜著各色各樣的金魚,顏色有深有淺,在陽光下波光粼粼地閃爍著。她想走過去,無奈被路口剛亮起的紅燈封住了路線,年邁的男人恰好在等待的空隙間抬起頭,李玫的目光在擦過他的一瞬間停滯下來。顧新宇,就算他的臉被歲月揉皺成一張抻不開的布,她還依舊認得出他。
李玫的腿突然就無法挪動了,像是腕上被拴著千斤的秤砣,關若飛從后面跟上來,李玫從口袋中掏出幾張錢,叫她幫忙從對面的小攤上買一條金魚回來。之前工廠偶爾會給他們發錢,雖然錢在那時看似沒什么用,但李玫還是會小心翼翼地存了起來。關若飛問她怎么不自己去買,她搖搖頭,什么都沒說,將口鼻都沒進外套中。
關若飛很快將金魚帶了回來,交到她手中,她將塑料袋平攤在掌心,水順著重力流到下垂的兩側塑料袋中,魚因為缺水,在她手中奮力地鼓動。她又將袋子舉起,對著太陽,那尾金魚渾身透明,眼球外凸,尾巴分成幾瓣,像正在綻放的花朵,與她在電視機上看到的并無差別。她覺得自己胸腔中有什么東西要破土而出了,一鼓一鼓的,發出無聲的震動,像是那尾掙扎的金魚,又像是跳動的心臟。真奇怪,仿生人明明沒有心臟。
工廠不讓養魚,李玫便將那尾魚倒入她們經過的一條小河中。后來只要她們有機會出去,她便讓關若飛走過馬路,為她帶一條金魚。她站在路的對面,就那樣靜靜地看著他們,顧新宇和妻子關系一定很好,因為他們大多數時候都是面帶微笑,很恬然的樣子。李玫有時候想,自己要不要親自去買一次,但又不知道見面與他說些什么,還怕擾了夫妻二人的寧靜,便作罷。
一天下午,她們再次經過那條路口,發現那里居然空了出來,李玫以為是他們臨時有事,所以“缺席”一天。結果一連三天那里都是空的,有種莫名的寂寥。她走過馬路,詢問另外一個原先同他們一起擺攤的小販。小販看了她一眼,很是奇怪的樣子。
“姑娘,顧大爺前兩天去世了,你不知道嗎?”
李玫什么也沒有說,轉過頭去,關若飛問她,你還好嗎?她點點頭,手不由自主地伸到后頸,那里存在著一顆初始化的按鈕。她就那樣撫摸著那塊小小的凸起,并沒有哭出來,而是有種想要將它按下去的沖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