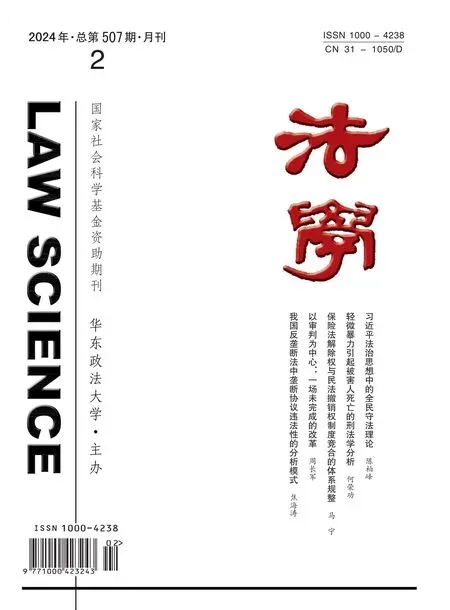輕微暴力引起被害人死亡的刑法學分析
●何榮功
一、問題的提出與概念厘定
輕微暴力引起(被害人)死亡,理論和實踐中習慣稱之為輕微暴力致人死亡,指的是行為人實施了輕微毆打、推搡等行為,因被害人特殊體質或者其他偶然因素介入或作用,從而引起被害人死亡的情形。〔1〕輕微暴力引起重傷也存在同樣的問題。出于行文便利,本文的探討只限于輕微暴力引起被害人死亡的情形。當然,本文的分析思路、方法和結論同樣適用于輕微暴力引起被害人重傷的情形。此類案件的特點是行為人實施行為的危險性及其強度與法益侵害結果之間的比例嚴重失衡。立足于行為人一方,其實施的只是輕微推搡、毆打等行為,行為本身難以認為具有造成刑法中傷害的危險性,遑論造成被害人死亡,卻出現了被害人死亡的重大損害結果。在刑法上此類行為如何定性,理論和實踐都存在爭議。有的從行為無價值論立場否定該情形成立故意傷害罪;〔2〕參見陳興良、周光權:《刑法學的現代展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 年版,第534 頁。有的提出該情形下死亡結果的發生難以認為是行為危險的現實化,輕微暴力和死亡結果之間沒有刑法上的因果關系;〔3〕參見黎宏:《因果關系錯誤問題及其應對——以行為危險現實化說的再闡釋為中心》,載《法學研究》2022 年第1 期,第116 頁。有的從預見可能性角度提出,行為人對被害人的特殊體質并無預見可能性,應當否定結果歸責。〔4〕參見蔣太珂:《被害人特殊體質司法現狀的刑法理論分析》,載《法學雜志》2016 年第1 期,第138-139 頁。本文并不否認輕微暴力和死亡結果之間是否存在刑法上的因果關系以及行為人是否具有主觀罪過對于此類行為定性的意義,但是,行為是犯罪成立的基礎,無行為則無犯罪,無行為也無從談起刑法因果關系。而且,行為人主觀上對于死亡是否存在過失,也離不開對輕微暴力和死亡之間關聯性這一客觀事實的判斷。所以,輕微暴力是否屬于犯罪實行行為,即是否屬于故意傷害罪或者過失致人死亡罪的實行行為,對于問題討論具有更為基礎的意義,這正是本文的研究視角和著力點。
厘清概念是研究問題的前提,需要說明的是,本文不使用“輕微暴力致人死亡”的表述。在現代漢語中,“致”即“致使”“招致”的意思。刑法條文中不乏該概念用語,比如刑法第263 條規定的搶劫致人重傷、死亡,第257 條規定的暴力干涉他人婚姻自由,致使被害人死亡等。在刑法條文使用“致”“致使”的場合,往往肯定構成要件行為和構成要件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但如本文所論證,輕微暴力引起被害人死亡的場合,通常情況下,輕微暴力并非故意傷害罪或者過失致人死亡罪的實行行為,在缺乏實行行為的場合,沒有進一步討論實行行為和法益侵害結果之間因果關系的基礎和必要性。而且,在該場合,被害人的死亡也并非行為人的輕微暴力所導致,只是由輕微暴力引起或引發,難以肯定行為和死亡結果之間具有刑法上的因果關系。概念應盡可能與事物的本質和構造相一致,“輕微暴力致人死亡”的概念并不契合此類案件的構造和行為性質,本文改用“輕微暴力引起死亡”的概念。
二、輕微暴力引起死亡定性的司法考察
(一)類型劃分與行為定性的實踐梳理
輕微暴力引起被害人死亡案件的類型,理論上有不同的劃分。〔5〕參見黃祥青:《輕微暴力致人死亡案件定性研究》,載《法律適用》2016 年第3 期,第66-68 頁。首先,根據行為的構造以及被害人死亡的原因,此類案件可以分為兩種類型,即輕微暴力誘發基礎疾病引起被害人死亡和輕微暴力偶然引起正常體質被害人死亡兩種情形。前者多表現為輕微暴力行為引起被害人原有的基礎疾病如冠心病、高血壓等發作而導致死亡;后者多表現為輕微暴力行為引起被害人磕碰或摔倒,繼而引起死亡結果。其次,根據行為人對被害人特殊體質等情況是否有主觀認識,可以分為明知型輕微暴力引起被害人死亡案件和非明知型輕微暴力引起被害人死亡案件,該兩種情形中行為的刑法定性存在明顯差異。在行為人明知被害人系特殊體質或者明知被害人是老人等特定群體的,行為完全可以依法成立故意傷害罪或者過失致人死亡罪。本文探討的主要限于非明知型情形。實踐中,對于此類行為定性,整體而言存在有罪(即故意傷害罪或者過失致人死亡罪)和無罪的不同做法。
1.有罪的觀點:故意傷害罪與過失致人死亡罪
本文選擇中國裁判文書網〔6〕參見中國裁判文書網,https://wenshu.court.gov.cn/,2023 年8 月17 日訪問。為案例來源數據庫,以2017 年至2021 年五年為檢索區間,以“輕微暴力”作為關鍵詞進行全文檢索,認定為故意傷害罪或過失致人死亡罪的生效裁判文書共計55 份,基本情況如下。
第一,從兩種類型案件的比重看,在55 份判決書中,輕微暴力引起被害人原有基礎疾病如冠心病、高血壓等發作而導致死亡的,共有36 份;輕微暴力引起正常體質被害人摔倒或者磕碰,進而引發死亡后果的,共有19 份。兩類案件在實踐中都比較常見。
第二,在罪名認定上,辦案機關主要存在三種觀點,即過失致人死亡罪、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罪和意外事件(無罪)。〔7〕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一、二、三、四、五庭主辦:《刑事審判參考》(總第49 集),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8-29 頁;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一、二、三、四、五庭主辦:《刑事審判參考》(總第103 集),法律出版社2016 年版,第44-45 頁。但從檢索的案例看,辦案機關的最終處理意見主要集中于故意傷害罪和過失致人死亡罪。其中,在輕微暴力引起特殊體質被害人死亡的36 件案例中,認定為構成過失致人死亡罪的共有27 件,占比75%;有9 件認定構成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罪,占比25%。而在被害人體質正常的19 件案例中,認定行為人構成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罪的有11 件,約占比58%;認定為過失致人死亡罪和故意殺人罪的為8 件,占比為42%。可見,被害人是否有基礎疾病等特殊體質對于行為性質認定有一定影響,整體而言,在被害人有特殊體質的場合,人民法院更傾向于認定行為成立過失致人死亡罪。
為了更好地指導實踐辦案,《刑事審判參考》和《最高人民法院公報》也發布了多個輕微暴力引起被害人死亡的案例。
案例1:洪志寧故意傷害案。本案是《刑事審判參考》第389 號指導案例,基本案情如下:被告人洪志寧女友劉海霞酒后故意將曾銀好茶攤上的茶壺摔破,為此與曾銀好女友方風萍發生爭執。陳掽獅(男,48 歲)上前勸阻,劉海霞遂與陳掽獅扭打起來。洪志寧趕到現場,揮拳連擊陳掽獅的胸部和頭部,陳掽獅被打后追攆洪志寧,追出二三步后倒地死亡。經鑒定,陳掽獅系在原有冠心病的基礎上因吵架時情緒激動、胸部被打、劇烈運動及飲酒等多種因素影響,誘發冠心病發作,冠狀動脈痙攣致心跳驟停而猝死。廈門市中級人民法院判決被告人洪志寧犯故意傷害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年零六個月。二審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原判對洪志寧的量刑過重,撤銷一審判決的量刑部分,在法定刑以下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并依法報送最高人民法院核準。最高人民法院予以裁定核準。〔8〕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一、二、三、四、五庭主辦:《刑事審判參考》(總第49 集),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6-31 頁。
案例2:楊逸章故意傷害案。該案系《最高人民法院公報》發布的案例。基本案情如下:被告人楊逸章發現田學山的編織袋內有其堂叔家的一張舊漁網,即持木棍毆打田學山,致田學山手臂、右肩等部位多處散在軟組織挫傷。田學山受傷后經送醫院搶救無效于次日8 時死亡。經法醫鑒定,被害人田學山生前患晚期門脈性肝硬化、巨脾癥、冠心病等嚴重疾病,在遭受外傷等誘因的作用下引起與肝臟連結的腹膜撕裂出血休克死亡。一審龍海市人民法院認定楊逸章犯故意傷害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年。一審法院依法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核準,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核準一審法院的判決。〔9〕參見最高人民法院辦公廳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公報》(2007 年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08 年版,第251-252 頁。
案例3:都某過失致人死亡案。本案是《刑事審判參考》第1079 號指導案例。基本情況是:都某及其子都某乙在親屬家吃過晚飯后,都某準備駕駛轎車回家。其間,陳某(被害人,歿年48 歲)駕車回家取物,其車輛堵住通道,雙方遂發生口角,繼而打斗,都某拳擊、腳踹陳某頭部、腹部,致其鼻腔出血。后陳某報警。雙方在派出所大廳等候處理期間,陳某突然倒地,后經送醫院搶救無效于當日死亡。經鑒定,陳某有高血壓并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因糾紛后情緒激動、頭面部(鼻根部)受外力作用等導致機體應激反應,促發有病變的心臟驟停而死亡。一審法院以被告人都某犯過失致人死亡罪,判處都某有期徒刑三年。都某不服,認為自己行為無罪上訴。二審法院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10〕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一、二、三、四、五庭主辦:《刑事審判參考》(總第103 集),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43-48 頁。
案例4:張潤博過失致人死亡案。該案系《刑事審判參考》第1080 號指導案例。2013 年5 月13日14 時許,被告人張潤博在十字路口因騎電動自行車險些與被害人甘永龍(男,歿年53 歲)相撞,兩人為此發生口角。甘永龍先動手擊打張潤博,張潤博使用拳頭還擊,打到甘永龍面部致其倒地摔傷頭部。甘永龍于同月27 日在醫院經搶救無效死亡。經鑒定,甘永龍系重度顱腦損傷死亡。一審法院以過失致人死亡罪判處被告人張潤博有期徒刑六年。檢察機關以一審法院定性錯誤,應認定為故意傷害罪為由提起抗訴。二審法院裁定駁回抗訴,維持原判。〔11〕同上注,第48-54 頁。
2.無罪的觀點
實務中,輕微暴力引起被害人死亡的場合,以意外事件(無罪)處理的也不乏見。
案例5:楊聰穎訴楊國建生命權糾紛案。楊先進(楊聰穎之父)因瑣事與楊國建發生口角,后雙方互相推搡,楊先進倒地,經搶救無效死亡。《司法鑒定意見書》認為楊先進符合因重癥冠心病致急性循環功能衰竭而死亡,其生前糾紛為死亡發生的誘因。公安局立案后作出《撤銷案件決定書》。〔12〕參見湖北省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2020)鄂01 民終8008 號民事判決書。
案例6:吳小小訴譚必文生命權糾紛案。楊元香(吳小小之女)與譚必文系夫妻關系,因家庭生活瑣事發生糾紛,譚必文打了楊元香背部兩拳,致楊元香踩到火坑里仰面倒在火坑邊的水泥地上。當晚譚必文給楊元香喝水后繼續讓楊元香休息。次日上午,譚必文發現枕巾上有嘔吐物便扶起楊元香詢問,楊元香沒有回答,并問是否要吃東西,楊元香只是搖頭,譚必文繼續將楊元香放在床上休息。下午,譚必文發現楊元香已經死亡。楊元香死亡原因的鑒定意見為:“楊元香系因自身腦血管畸形、鈣化并破裂造成顱內出血致呼吸、循環功能衰竭死亡,屬病理性死亡;本次外傷及相伴發生的情緒激動、體力活動增強可作為顱內出血的誘發因素。”公安機關以譚必文過失致人死亡罪立案后撤銷。〔13〕參見貴州省岑鞏縣人民法院(2017)黔2626 民初436 號民事判決書,貴州省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級人民法院(2017)黔26 民終2258 號民事判決書。
(二)小結
歸納實踐做法,可以發現此類型案件的辦理具有如下特點:第一,關于案件類型。理論上關于輕微暴力引起死亡的兩種類型在實踐中普遍存在。《刑事審判參考》刊載的指導案例和《最高人民法院公報》發布的案例也包含兩種情形,洪志寧故意傷害案、楊逸章故意傷害案和都某過失致人死亡案,屬于輕微暴力誘發基礎疾病引起被害人死亡的情形;張潤博過失致人死亡案屬于輕微暴力引起正常體質被害人死亡的情形。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指導案例和公報案例限于行為人對被害人具有特殊體質和基礎疾病并不知情的情形。第二,關于行為定性。對于輕微暴力誘發基礎疾病引起被害人死亡的定性,《刑事審判參考》刊載的指導案例的立場是有變化的。洪志寧案和楊逸章案中,人民法院將行為認定為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罪,考慮到罪責刑的適應,經最高人民法院核準,依據減輕處罰的規定在法定刑以下處罰。都某過失致人死亡案中,指導案例表明了行為成立過失致人死亡罪的立場。行為性質由故意傷害罪向過失致人死亡罪的轉變,反映了指導案例對此類行為輕緩化處理的傾向。行為定性的改變直接帶來了此類案件處理不再需要根據刑法第63 條第2 款的規定由最高人民法院核準減輕處罰。關于輕微暴力引起正常體質被害人死亡的案件,《刑事審判參考》第1080 號指導案例肯定此類行為成立過失致人死亡,而非故意傷害罪,也同樣顯示出對此類行為輕緩化處理的立場。
三、輕微暴力引起死亡刑法定性的爭議:問題點與評析
(一)關于故意傷害罪
不管是輕微暴力誘發基礎疾病引起被害人死亡,還是輕微暴力偶然引起正常體質被害人死亡,辦案機關之所以肯定行為成立故意傷害罪,都是認為此類案件中行為人客觀上存在故意傷害行為,主觀上有傷害的故意。洪志寧故意傷害案中,一審和二審法院都積極肯定被告人洪志寧主觀上具有傷害故意,客觀上實施了傷害行為。《刑事審判參考》在裁判理由部分對此分析道:“被告人洪志寧主觀上應當認識到對被害人要害部位猛擊的行為,可能會造成傷害被害人身體健康的后果,卻連續擊打。此時,被告人的傷害故意、傷害行為均已經成立。本案出現了被害人死亡的后果,因而符合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的構成要件。”〔14〕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一、二、三、四、五庭主辦:《刑事審判參考》(總第49 集),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9 頁。值得注意的是,對于此類案件中傷害行為和被害人死亡結果之間有無刑法因果關系,觀點并不統一,這直接影響到行為人對死亡結果是否需要承擔刑事責任。
第一,肯定傷害行為和死亡結果之間刑法因果關系的,往往會認為此類案件成立故意傷害罪的結果加重犯,行為人需要對被害人死亡承擔刑事責任。比如在洪志寧故意傷害案中,二審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指出:“被告人對被害人胸部拳擊數下的行為一般情況下不會產生被害人死亡的結果,但其拳擊的危害行為,與被害人情緒激動、劇烈運動及飲酒等多種因素介入‘誘發冠心病發作’導致了死亡結果的發生……被告人的行為與被害人死亡的結果具有刑法上的因果關系。”“雖然死亡后果超出其本人主觀意愿,但這恰好符合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的構成要件。”《刑事審判參考》在裁判理由中也指出:“被告人的傷害行為與被害人的死亡有一定的因果關系。如果被告人不對被害人進行擊打,就可能不會誘發被害人冠心病發作,猝死的結果也就可能不會發生。”〔15〕同上注,第27-30 頁。
第二,不積極肯定傷害行為和死亡結果之間刑法因果關系的,一般會認為此類案件成立故意傷害罪的基本犯,行為人不需要對被害人死亡承擔刑事責任。〔16〕實踐中,有的基于此類案件中行為和死亡結果之間不存在刑法上的因果關系,認為屬于意外事件。在楊逸章故意傷害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刑事裁定書寫道:“本院認為,被告人楊逸章用木棍毆打他人,并致人死亡的行為已構成故意傷害罪。但鑒于被害人死亡的主要原因是其生前患有嚴重疾病,楊逸章的傷害行為只是被害人死亡的誘因。楊逸章不應對被害人的死亡結果負全部責任。”〔17〕最高人民法院(2006)刑復字第121 號刑事裁定書。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定并沒有對行為和結果之間是否存在刑法上因果關系直接表態,其中,“行為只是被害人死亡誘因”“不應對被害人的死亡結果負全部責任”的概念表達,可以看出最高人民法院裁定對于此類案件中刑法因果關系整體上并非持積極肯定的立場。
犯罪是主客觀要件的有機統一,不管是輕微暴力誘發基礎疾病引起被害人死亡,還是輕微暴力引起正常體質被害人死亡,要認定行為成立故意傷害罪,客觀上必須存在故意傷害罪的行為即實行行為,但在該問題上明顯面臨疑問。如后文所述,我國采取的是違法和犯罪區分的二元違法體系,輕微傷害行為由《治安管理處罰法》規制,具有一定嚴重性的傷害行為才由刑法調整。換句話說,在違法和犯罪區分的二元違法體系下,根據刑法規定,故意傷害罪中的“傷害行為”范圍是有嚴格限制的,不同于日常意義上的傷害行為。拳擊胸部、木棍毆打等輕微暴力只是屬于一般毆打行為,并非刑法中的傷害行為,將其認定為故意傷害罪,混淆了一般毆打行為和刑法中傷害行為的界限,并不符合故意傷害罪的構成要件。
在因果關系方面,刑法中的因果關系指的是實行行為和構成要件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在缺乏實行行為的場合,沒有肯定因果關系的基礎和必要。既然輕微暴力難以認為屬于刑法中的故意傷害行為,那么,肯定輕微暴力行為和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便難以認為是妥當的。在此類案件中,有的辦案機關一方面積極肯定輕微暴力只是引起被害人死亡的偶然因素與誘因,被害人死亡的主要原因是患有基礎疾病,另一方面又認為輕微暴力和被害人死亡之間存在刑法上的因果關系,存在明顯的前后邏輯不能自洽的問題。實踐中,法益侵害的發生常常系多種因素共同或者混合作用的結果,某因素是否和法益侵害結果存在刑法上的因果關系,需要考慮該因素的性質及其對法益侵害結果發生的原因力,還應注意事物性質應由事物主要方面決定這一重要方法論。而且,刑法作為法治國家最嚴厲的譴責機制,其性質決定了刑法中的因果關系具有“質”和“量”的要求,相對于民事法中的因果關系,刑法中因果關系的認定要采取相對節制的立場,既然輕微暴力只是被害人死亡的誘因,被害人死亡的主要原因是其患有基礎疾病,那么,肯定兩者之間的因果關系,便難免存在拔高認定的問題。
綜上,輕微暴力引起死亡的案件,認定行為成立故意傷害罪,明顯面臨有無實行行為和刑法因果關系的疑問。
(二)關于過失致人死亡罪
主張行為成立過失致人死亡罪的理由主要是:(1)客觀上行為人實施的行為現實危險性較小,被害人的直接遭受打擊部位未形成傷害后果,行為人的行為有別于用棍棒、刀具等足以導致被害人輕傷以上后果的故意傷害行為,屬于輕微暴力行為,難以認為屬于刑法中的故意傷害行為。(2)主觀上行為人不具有造成被害人身體損傷的主觀故意,但行為人應當對自己的行為可能會導致他人死亡后果的事實有所預見,卻因疏忽大意沒有預見,對于被害人因基礎疾病發作或者倒地磕碰而死亡的后果,主觀上具有過失。(3)該類因民事糾紛引發的使用拳打腳踢方式相互輕微毆打致人死亡的案件,類似于民間的“失手打死人”情形,以過失致人死亡罪定罪處罰,符合罪責刑相適應的刑法基本原則,且符合公眾的一般心理預期。〔18〕參見吉林省榆樹市中級人民法院(2020)吉0182 刑初53 號刑事判決書,吉林省長春市寬城區人民法院(2019)吉0103 刑初344 號刑事判決書等。
在都某過失致人死亡案中,二審法院指出:“被告人都某應當預見擊打他人頭部、腹部可能導致他人死亡的危害后果,因為疏忽大意而沒有預見,仍拳擊、腳踹被害人頭部、腹部,以致發生被害人死亡的危害后果,行為和結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其行為符合過失致人死亡罪的構成要件。”〔19〕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一、二、三、四、五庭主辦:《刑事審判參考》(總第103 集),法律出版社2016 年版,第44 頁。又如王某過失致人死亡案(案例7)中,因購買的西瓜質量問題雙方發生糾紛,王某與被害人寇某徒手扭打造成寇某輕微傷。被害人寇某因外傷、爭吵、情緒激動等因素誘發其所患冠狀動脈發育不良伴粥樣硬化斑塊形成的心臟病急性發作,致急性心功能不全死亡。人民法院審理指出:“被告人王某雖不知被害人寇某患有心臟病,也預見不到寇某患有心臟病,但應當預見擊打他人頭部可能導致他人傷亡的危害結果而沒有預見,在主觀方面屬于疏忽大意的過失。被告人王某與被害人寇某短暫互毆即造成被害人輕微傷,外傷系被害人死亡的誘因之一,被告人王某的行為與被害人的死亡結果之間具有刑法上的因果關系,其行為構成過失致人死亡罪。”〔20〕福建省廈門市海滄區人民法院(2017)閩0205 刑初315 號刑事附帶民事判決書。
輕微暴力引起死亡的場合,輕微暴力行為要成立過失致人死亡罪,同樣需要滿足其構成要件,即主觀上行為人對他人的死亡必須具有過失,客觀上必須存在致人死亡的行為,即犯罪的實行行為。如后文分析,輕微暴力引起被害人死亡的案件中,輕微暴力連成立刑法中的故意傷害行為都存在疑問,如何能將其認定為致人死亡的行為即過失致人死亡罪的實行行為呢?都某過失致人死亡案中,雖然人民法院肯定了行為和被害人死亡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但是,其中所言的行為只是被告人實施的拳擊、腳踹行為,這些行為只是屬于一般毆打行為,系引起被害人死亡的行為,難以評價為導致被害人死亡的行為,即過失致人死亡罪的實行行為。從司法實踐來看,辦案機關普遍缺乏對此類案件是否存在過失致人死亡罪實行行為的必要論證和說明。與故意犯罪一樣,實行行為同樣是過失犯成立的客觀基礎,如果無法合理解決此類案件中的實行行為問題,那么,將其認定為過失致人死亡罪就不可避免地面臨疑問。此外,成立過失致人死亡罪,主觀上行為人還必須具有過失,有的案件中,人民法院對于行為為何不構成故意傷害罪積極予以說明,但是對于行為為何構成過失致人死亡罪,往往語焉不詳。〔21〕參見福建省廈門市海滄區人民法院(2017)閩0205 刑初315 號刑事附帶民事判決書。比較常見的情形是,辦案機關只是給出了行為人存在疏忽大意過失的結論,但缺乏必要的論證和分析。〔22〕具體內容可以參見湖南省婁底市中級人民法院(2019)湘13 刑終161 號刑事判決書,遼寧省鞍山市鐵西區人民法院(2023)遼0303 刑初53 號之三刑事判決書等。
(三)關于意外事件
相對于行為成立故意傷害罪或過失致人死亡罪,實踐中辦案機關最終將此類行為認定為意外事件的相對較少。認定行為成立意外事件的理由主要有:(1)客觀上行為人的毆打行為未造成直接打擊部位輕傷以上后果的損傷,之所以例外地發生死亡后果,被害人自身的特殊體質發揮了根本作用。(2)主觀上行為人對于被害人的死亡后果不具有故意或者過失的心理態度。比如,謝某某過失致人死亡案(案例8)中,被告人謝某某和被害人陳某某因建房糾紛發生沖突,被害人陳某某突然暈倒在地后死亡。人民法院審理認為,行為人是否能夠預見,是否存在過失,應以一般人在通常情況下的預見能力為標準。就本案而言,原審被告人謝某某與被害人陳某某因民間糾紛引發口角及肢體接觸,在現場有人勸阻的情況下,能夠對被害人造成的傷害是非常小的,對于一般人來說是不可能造成死亡結果的。根據司法鑒定,被害人陳某某患有冠狀動脈粥樣硬化癥,因情緒激動及外傷等因素誘發被害人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突然發作致急性心力衰竭死亡。本案中,公訴機關沒有提交證據證明原審被告人謝某某知道或應當知道被害人陳某某患有冠狀動脈粥樣硬化癥,原審被告人謝某某不能預見其與被害人陳某某發生口角及肢體接觸的行為可能會導致被害人死亡,故其主觀上不存在過失。〔23〕參見廣東省梅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6)粵14 刑終216 號刑事裁定書。
在輕微暴力引起死亡的案件中,行為依法是成立故意傷害罪、過失致人死亡罪,還是屬于意外事件,從表面上看,似乎主要是個主觀罪過問題,實質上此類案件的定性與是否存在犯罪行為以及行為和結果之間是否有因果關聯性密切相關。行為人對于被害人死亡究竟有無過失,當然要考察行為人的注意義務和認識能力,但行為人有無注意義務和認識能力,絕非只是行為人的個人主觀事項,根本上還與行為和法益侵害結果之間的關聯性及其程度密切相關。如果行為人沒有實施構成要件行為,卻發生了法益侵害結果,那么,自然難以肯定行為人主觀上對結果具有犯罪過失并譴責行為人;即便存在構成要件行為,如果行為和法益侵害結果的關聯性很低,那么,肯定行為人對法益侵害結果的發生主觀上具有犯罪過失,既缺乏事實根據,也是過于嚴苛的。所以,輕微暴力引起被害人死亡是否屬于意外事件,同樣離不開對是否存在犯罪實行行為以及行為和死亡結果之間因果關聯性的判斷。
(四)小結
綜上,輕微暴力引起被害人死亡的案件,將行為認定為故意傷害罪或過失致人死亡罪,都明顯面臨構成要件上的疑問,無論是《刑事審判參考》刊載的指導案例,還是《最高人民法院公報》發布的案例都沒有對其中的核心爭議點給出令人信服的分析說明。歸納起來,此類案件定性的核心爭議點集中于如下方面:一是客觀上此類案件中是否存在故意傷害罪和過失致人死亡罪的構成要件行為,即犯罪的實行行為;二是實行行為和被害人死亡結果之間有無刑法上的因果關系;三是在主觀上,行為人對被害人死亡是故意還是過失,抑或無罪過,行為人主觀上有無罪過,如上分析,該問題與客觀上是否存在犯罪實行行為以及因果關系有密切聯系;四是輕微暴力誘發基礎疾病引起被害人死亡和輕微暴力引起正常體質被害人死亡兩種情形中,單就被害人的身體情況和死亡原因而言,確實存在差異,這種差異是否影響此類行為定性。以上四個方面問題并非孤立存在,其中,是否存在故意傷害罪或者過失致人死亡罪的實行行為,是行為定性的前提和基礎,也是關鍵所在。下文從輕微暴力的行為構造即是否屬于故意傷害罪或者過失致人死亡罪的實行行為這一關鍵問題展開。
四、實行行為的構造與輕微暴力的刑法性質
(一)實行行為的構造與判斷
行為是犯罪的基礎,無行為則無犯罪,這是近代以來法治國家刑法的基本立場。由于各國法律傳統不同,刑法中行為的類型、范圍及其處罰立場不盡一致。在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刑法普遍以處罰既遂為原則,處罰未遂為例外,處罰預備為例外的例外。在數人共同犯罪的場合,刑法處罰教唆犯和幫助犯,只是教唆犯和幫助犯的成立具有從屬性,以正犯的成立為必要。可見,為了充分保護法益,各國刑法處罰的對象都不限于實行行為,而是延伸至實行行為的周邊,但實行行為在行為體系中具有基礎、核心地位。在我國,實行行為和非實行行為都是刑法處罰的對象,但實行行為同樣具有基礎地位。根據我國刑法規定,非實行行為包括犯罪的組織行為、教唆行為、幫助行為以及犯罪預備行為。作為行為的具體形態之一,實行行為具備刑法中行為的一般特征,即有體性、有意性、有害性。〔24〕參見高銘暄、馬克昌主編:《刑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22 年版,第60-61 頁。但是,區別于刑法中的組織行為、教唆行為和幫助行為等非實行行為,實行行為具有以下重要特征。
第一,實行行為是我國刑法分則規定的行為,這是實行行為的法律特征。無論是刑法中的組織行為、教唆行為、幫助行為,還是犯罪預備行為,除刑法分則有特別規定外,都由刑法總則規定。〔25〕基于犯罪行為復雜性和多種原因的考慮,立法將有些本質上屬于犯罪的非實行行為也規定在刑法分則中,此即為非實行行為的正犯化,比如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教唆他人吸毒罪等。與此不同,實行行為需要通過刑法分則構成要件的解釋來確定其實質和內容,〔26〕參見[日]西原春夫:《犯罪實行行為論》,戴波、江溯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年版,第13 頁。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實行行為被認為根本上是個刑法各論課題。
第二,實行行為是對法益的侵害具有“現實”“定型”危險性的行為。這是實行行為的實質特征。某一行為之所以會受到刑法規范的評價而被規定為犯罪,根本原因在于該行為侵害了法益或具有侵害法益的危險性。其中,組織行為是因為其對實行行為具有支配性而受到處罰,教唆行為是因為制造了犯罪人,創造了原不存在的法益風險而受到處罰;幫助行為和犯罪的預備行為之所以受到處罰,原因在于幫助行為使法益侵害的危險升高,而預備行為則蘊含著法益侵害的危險性,只是與犯罪的實行行為相比,法益侵害的危險性較低而已。可見,實行行為與非實行行為的區別并不在于法益侵害危險性的有無,而在于法益侵害危險性的程度和類型的不同。立法者之所以將某一行為規定為犯罪的實行行為,根本原因在于該行為對法益的侵害具有現實的、定型性的危險,或者稱之為行為危險的現實化。〔27〕參見黎宏:《因果關系錯誤問題及其應對——以行為危險現實化說的再闡釋為中心》,載《法學研究》2022 年第1 期,第116 頁。所謂對法益的侵害具有現實的、定型性的危險,具體包括如下三層含義。
一是,該場合下法益侵害的危險是現實存在的危險,不是虛構或者主觀臆造的。比如,迷信犯的場合就不存在犯罪的實行行為。只是刑法在性質上屬于社會規范,旨在維護社會秩序,評價、塑造和指引公民的行為,刑法作為社會規范的屬性決定了危險是否現實存在,并不完全依據科學因果法則判斷,也不會完全采取事后的判斷,而是根據社會法則和有利于實現刑法的社會機能進行的規范性判斷。換句話說,現實的危險并不完全等同于物理、科學意義上的客觀的危險。
二是,從法益侵害的時間看,現實的危險意味著法益侵害的危險是緊迫的、逼近的,而不是遙遠的。在有犯罪對象的場合,這種行為已直接指向犯罪對象,如果不出現行為人意志以外原因的阻礙或者行為人自動中止犯罪,這種行為將會繼續下去,直到完成犯罪。在結果犯的場合,將會發生法益侵害的結果。
三是,該場合下的危險是“定型性”的危險。〔28〕需要說明的是,近些年為了強化刑法參與社會治理,特別是基于對犯罪打擊便利的考量,刑法處罰范圍出現了擴張的趨勢,組織行為、預備行為等非實行行為的實行行為化就是表現之一,如恐怖主義犯罪立法。這在一定程度上動搖了實行行為的定型性特征,但定型性作為實行行為的主要特征并沒有根本改變。危險的“定型性”強調的是行為和法益侵害危險以及結果之間具有基本的關聯性和對應性,而非不確定的。換句話說,行為人實施該行為通常會發生特定法益侵害的危險及其結果。比如,如果認為某種行為屬于殺人行為,那么一般情況下,該行為具有致人死亡的危險性;如果認為某種行為系故意傷害行為,那么該行為通常具有致人死亡、重傷或者輕傷的危險性。在某種行為與特定法益侵害的危險和結果之間缺乏基本的對應關系和關聯性,即沒有定型性時,就不能將該行為拔高認定或評價為具體犯罪的實行行為。實行行為定型性特征不僅涉及實行行為的構造,更重要的是其關系到刑法適用的確定性。比如,行為人持槍瞄準被害人,行為明顯顯示出故意殺人行為及其危險的定型性,即使行為人辯解主觀上不具有殺人故意,只是傷害故意,這種辯解一般難以被采信。又如,行為人持刀砍向被害人的情形,該行為是屬于殺人行為還是傷害行為,尚無法定型,需要結合行為人主觀方面和客觀法益侵害結果認定。輕微暴力引起死亡的行為定性主要涉及的是實行行為危險的現實性和定型性的有無及其判斷問題。
事物都是特定時空下的存在,某種行為是否具有法益侵害的危險以及危險是否現實定型,不僅與危險本身有關,還與判斷的時點以及判斷標準有關,正因為如此,法益侵害危險以及實行行為有無的判斷本質上是個規范判斷問題。比如,行為人誤將玩具槍作為真槍搶劫的案件中,立足于行為時根據行為人的認識,系持槍搶劫,但根據事后查明的事實,行為人使用的是玩具槍,并不具有持槍搶劫的法益侵害及其危險性,無法肯定持槍搶劫的事實。又如,行為人誤將男性作為婦女實施強奸的場合,根據行為人的認識,其實施的是強奸行為,但事實上由于行為對象系男性不可能得逞。在刑法理論上,對于如何判斷是否存在犯罪實行行為,有主觀說、抽象危險說、具體危險說和客觀說的對立。〔29〕在大陸法系的刑法理論上,實行行為的判斷與未遂犯和不能犯的區分是個一體兩面的問題,該問題大都在未遂犯和不能犯的區分部分論述。
主觀說,也稱為純粹的主觀說,認為犯罪實行行為的有無應站在行為之時完全根據行為人認識判斷。主觀說被普遍認為系主觀主義刑法理論,在理論和實踐中均被摒棄。抽象危險說,在德國又稱“印象理論”,認為應以行為時行為人認識的事實為基礎,根據社會一般人的見地判斷有無犯罪實行行為。根據抽象危險說,上述持槍搶劫和強奸案中,都存在搶劫罪和強奸罪的實行行為。具體危險說強調,應以行為當時一般人認識的事實以及行為人特別認識的事實為基礎,以行為時為立足點,從一般人的立場判斷實行行為的有無。上述持槍搶劫和強奸案中,是否存在搶劫罪和強奸罪的實行行為,需要以行為當時一般人認識的事實以及行為人特別認識的事實具體分析。客觀危險說內部存在具體意見分歧。純客觀說主張,對法益侵害的危險應進行客觀的判斷,與行為人的認識或者計劃無關,法益侵害的危險不是從事前而應從事后判斷。根據該說,上述持槍搶劫和強奸案中都不存在搶劫罪和強奸罪的實行行為。修正客觀說意見各異,有的認為,應以行為時存在的一切客觀事實為基礎,以行為時作為判斷時間,判斷法益侵害危險以及實行行為。〔30〕參見張明楷:《刑法學》(上),法律出版社2021 年版,第455-461 頁。
輕微暴力引起死亡的場合,一般情況下,行為人對于被害人特殊體質或者基礎疾病并不知情,本文探討的也只限于該情形,被害人表面上系健康正常的,所以,抽象危險說和具體危險說一般都會否定傷害行為和致人死亡行為的存在,客觀說中有的觀點會肯定傷害行為和致人死亡行為的存在。司法實踐中的難點問題往往都是刑法理論的爭點話題,刑法理論和實踐中具體問題的爭議,往往涉及刑法的法規范性質和基本原則的理解,輕微暴力引起死亡的案件也一樣。究竟是站在行為時根據行為人的認識,還是站在事后根據客觀事實判斷行為危險的有無及其定型性,對該問題的回答涉及刑法的屬性這一根本性問題。根據刑法目的和刑法規范的性質,立足于行為時,根據行為人的認識判斷是否存在法益侵害危險以及實行行為,更為妥當。換句話說,立足于發揮刑法的預防機能和更為充分地保護法益,抽象危險說對于行為危險判斷的觀點更值得提倡。〔31〕筆者曾經提倡以事后查明的客觀事實放在行為時判斷有無實行行為,這種觀點有助于限制刑罰范圍,但并不利于刑法預防功能的發揮和法益的充分保護,現在看來有必要修正。參見何榮功:《實行行為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 年版,第63-67 頁。
首先,刑法的根本目的在于保護法益,為了周延保護法益,世界各國處罰的對象都不限于事實上或者客觀上造成了法益侵害的行為,對于法益侵害具有危險性的行為都會受到處罰,正因為如此,刑法處罰未遂犯是世界各國的通例。刑法普遍處罰未遂犯罪這一事實,本身就說明刑法并沒有采取純粹的事后客觀主義立場,否則一切未遂犯都將是不可罰。現實社會法益侵害的客觀事實沒有發生,情形是多種多樣的,如果只是偶然因素所致,比如對象錯誤或者手段錯誤,行為人主觀上的犯罪意圖和客觀上的行為明顯表現出了法益侵害的危險性,立足于法益保護和法益侵害的預防,刑法對此若完全沉默,將難以符合現代刑法目的和任務。特別是為了充分保護法益,現代刑法越來越強調刑罰的積極一般預防功能,立足于行為時,根據行為人的認識判斷是否存在法益侵害危險以及實行行為,即抽象危險說更接近、契合現代刑法的目的。〔32〕參見黃榮堅:《基礎刑法學》(下),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6 年版,第502 頁。
其次,法本質上系規范體系,無論民法,行政法抑或刑法都一樣,只不過刑法規范體系是以刑罰為主要內容的。從刑法規定看,刑法條文是以制裁規范表現的,即行為如果符合了刑法規定的要件,就面臨刑罰制裁的后果。比如,根據刑法第232 條規定,故意殺人的,處死刑、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節較輕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該條文雖然是以制裁規范表現的,但卻是以指示一定的行為樣態正當或不正當為內容的行為規范為前提。刑法第232 條對于故意殺人罪的規定,本身就顯示著禁止殺人的行為規范。正因為如此,刑法被認為是制裁規范和行為規范共同構成的整體,〔33〕參見[日]高橋則夫:《規范論和刑法解釋論》,戴波、李世陽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年版,第3 頁。制裁規范和行為規范并非對立關系。與制裁規范承載的確認前規范效力不同,行為規范與法益保護相關聯,由于無法否定預防性法益保護這一事前判斷性,相反,現代社會越來越重視預防性法益保護,所以,當存在對于法益的一般性的、抽象的危險,就有必要和能夠肯定違反行為規范。〔34〕參見[日]高橋則夫:《刑法總論》,李世陽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20 年版,第10 頁。立足于行為時,根據行為人的認識判斷是否存在法益侵害危險以及實行行為,可以更好地發揮刑法作為行為規范對公民行為的規范、指引功能。
最后,刑法并非單純的社會管理機制,而是一種社會譴責機制,某種行為是否應當作為犯罪處理,必須考慮刑罰譴責的必要性和正當性。行為人如果沒有犯罪意思,那么對其施以刑罰既不人道,也無實際預防意義。但是,行為人具有明確的犯罪意圖,比如行為人意圖持槍搶劫,結果誤將玩具槍作為真槍,又如行為人意圖強奸,對被害人實施暴力、脅迫行為,結果誤將男性作為被害婦女,在健全的國民觀念中,對上述行為進行譴責的必要性和正當性,應當是不言而喻的。
(二)輕微暴力的刑法性質
立足于犯罪實行行為的構造、認定方法和輕微暴力的特點,對于輕微暴力的刑法性質,本文的認識如下。
第一,輕微暴力行為不具有故意傷害罪客觀行為的定型性,依法不能認定為刑法中的故意傷害行為。如前所述,我國采取的是違法和犯罪相區分的二元違法體系,行為輕微違法的,屬于行政違法,由《治安管理處罰法》等行政法調整;行為嚴重違法的,才由刑法調整。正因為如此,我國刑法理論和司法實踐都重視區分一般的毆打行為和故意傷害行為。故意傷害行為,指的是非法損害他人身體健康的行為,由于刑法中的傷害只限于輕傷害、重傷害和傷害致死,所以,刑法中的故意傷害行為應采取限制解釋,并非指的是一切傷害他人身體健康的行為,而是指具有造成他人輕傷害、重傷害和傷害致死危險性的行為。也就是說,行為人一旦實施刑法中的故意傷害行為,那么被害人將面臨輕傷害、重傷害或傷害致死的危險性,行為和法益侵害結果之間應具有一定的對應關系,此即前文所強調的實行行為的定型性或者行為危險的現實化。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罪是故意傷害罪的結果加重犯,成立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罪,不僅需要行為人客觀上實施了刑法中的故意傷害行為,而且該故意傷害行為還應當具有致人死亡的危險性。當行為不是刑法中的故意傷害行為,因為欠缺本罪的實行行為,沒有成立故意傷害罪的余地,更不用談成立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罪了。
在張潤博過失致人死亡案中,《刑事審判參考》在裁判理由中對該問題有比較明確的闡述:構成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罪的行為,應當在客觀上具有高度的致害危險性。從法理上講,故意傷害致人死亡是故意傷害罪的結果加重犯。結果加重犯是刑法規定的一種特殊犯罪類型,一般以行為人對加重結果的發生“有客觀的預見可能性”而“主觀上卻沒有預見”作為構成要件。既然加重結果發生有著“客觀的預見可能性”,則意味著基本行為應當具有引發嚴重傷害甚至可能導致死亡結果發生的高度危險性。從立法上看,刑法對故意傷害致死行為規定了“有期徒刑十年以上、無期徒刑或者死刑”這樣嚴厲的法定刑,其處罰的對象也理應是在客觀上具有高度危險性的暴力行為,而不可能是輕微的暴力行為。〔35〕參見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第一、二、三、四、五庭主辦:《刑事審判參考》(總第103 集),法律出版社2016 年版,第52 頁。該分析注意到了實行行為的定型性特征,是很有道理的。遺憾的是,本案的裁判并沒有嚴格貫徹該理論和邏輯。輕微暴力引起被害人死亡的場合,輕微暴力本身連致被害人輕傷的危險性都沒有,客觀上這些行為大都只是造成了被害人輕微傷,自然談不上存在致人重傷或者死亡的危險性。在法律性質上,輕微暴力屬于一般的毆打行為,并非刑法中的故意傷害行為,即故意傷害罪的實行行為。在此類案件欠缺故意傷害罪的實行行為的情況下,當然難以肯定行為成立故意傷害罪。
第二,輕微暴力引起死亡的場合,欠缺過失致人死亡罪的實行行為,依法不能認定為過失致人死亡罪。過失犯屬于開放構成要件形態,行為人是否存在過失和是否存在實行行為需要刑法適用者的補充。從刑法條文的規定看,有的過失犯,立法者在設置構成要件時明確規定了犯罪的實行行為,比如交通肇事罪;但有些過失犯,立法者在設定構成要件時沒有規定犯罪的實行行為,比如過失致人死亡罪。在后者場合中,因為立法沒有規定犯罪的實行行為,只是規定了主觀上的過失和構成要件結果,這很容易導致司法者在犯罪認定中忽視對此類犯罪實行行為的判斷。一旦不重視過失犯中實行行為的判斷,那么,過失致人死亡罪很容易蛻變為“過失引起死亡罪”。只要行為引起了被害人死亡或者行為與死亡有關聯性,行為人主觀上對此有過失,就將成立本罪,過失致人死亡罪的處罰范圍將不當擴大,甚至淪為兜底條款。
根據刑法規定,成立過失致人死亡罪,客觀上必須要求存在本罪的實行行為以及該實行行為導致了被害人死亡結果的發生;主觀上行為人對實行行為導致被害人死亡具有的是過失的心理態度。在輕微暴力引起被害人死亡的案件中,如前分析,不存在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罪的實行行為,也更不可能存在故意殺人罪的實行行為,那么是否存在過失致人死亡罪的實行行為呢?對于這一問題的解答,首先要考慮的是過失犯是否存在獨立于故意犯的實行行為。對此,一種觀點認為,過失犯可以分為純正的過失犯與不純正的過失犯,前者是指只能由過失構成的過失犯,而后者是指既可以由故意構成又可以由過失構成的過失犯,不純正的過失犯與故意犯共用一個構成要件,因而其實行行為也是共同的。換言之,對于不純正的過失犯,不存在獨立的實行行為;對于純正的過失犯,存在獨立的實行行為。〔36〕參見陳興良:《純正的過失犯與不純正的過失犯:立法比較與學理探究》,載《法學家》2015 年第6 期,第107-110 頁。以此觀點,在輕微暴力引起死亡的案件中,如上文分析,由于不存在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罪或故意殺人罪的實行行為,因而也就不存在與之相對應的過失致人死亡罪的實行行為。另外一種觀點指出,過失犯的實行行為具有一定的獨立性,有必要獨立判斷,過失犯的實行行為核心表現為對客觀注意義務的違反,客觀注意義務是對社會一般公眾的 “基準性行為要求”,以社會的“一般理性人標準”加以判斷。〔37〕參見杜宇、畢海燕:《論過失犯實行行為的識別》,載《清華法學》2023 年第1 期,第121-127 頁。在輕微暴力引起傷亡案件中,在一般理性人看來,其只是一種輕微的推搡、毆打行為,這符合對社會一般公眾的“基準性行為要求”,因而行為人也就不可能具有法益侵害危險的預見可能性或法益侵害結果之回避可能性,自然也就不可能違背客觀注意義務。所以在輕微暴力引起死亡的案件中,也就不存在過失致人死亡罪的實行行為。而且,此類案件中,證據顯示得很清晰,輕微暴力只是死亡的誘因,此類案件的基本構造是:輕微暴力引起了被害人死亡,并非“致”被害人死亡。
綜上,輕微暴力引起被害人死亡的案件中,不可否認輕微暴力行為系侵權違法行為,但其既不具有故意傷害罪客觀行為的定型性,也不具有過失致人死亡罪實行行為的定型性,將此類行為認定為故意傷害罪或者過失致人死亡罪,在解釋論上都無法成立。換句話說,輕微暴力引起被害人死亡案件中,并不具有成立故意傷害罪和過失致人死亡罪的客觀行為基礎。
(三)還有必要說明的幾個問題
輕微暴力既不屬于故意傷害罪的實行行為,也不是過失致人死亡罪的實行行為,在欠缺實行行為的場合,自然沒有進一步討論因果關系和罪過的必要,但是,考慮到刑法理論和實務對此類案件因果關系和主觀罪過問題的關注,為了使問題的討論更全面清晰,下面對此類案件刑法定性中的因果關系和過失等問題作簡要論述。
1.關于因果關系。輕微暴力引起被害人死亡的案件中輕微暴力行為和死亡結果之間是否存在刑法中的因果關系,國外刑法對此也有爭議。比如,日本刑法理論界基于相當因果關系理論,對特殊體質情況下的因果關系大多持否定的態度。但在判例中,對特殊體質情況下的因果關系卻以條件說為主,肯定因果關系的存在,“行為人對患有某種疾病的被害人實施了暴力,被害人因而死亡的情形,判例均承認行為與死亡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38〕[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總論》,劉明祥、王昭武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年版,第82 頁。我國刑法理論界對此意見存在明顯分歧。持肯定意見的學者錢葉六教授寫道,特殊體質或者隱性病變不屬于介入因素,應將之納入因果關系判斷的客觀素材之中,同時考慮到具有特殊體質的人與正常健康人不同,即使是輕微的暴力,也具有導致其疾病發作而死亡的危險性,而當該種危險在結果中成為現實的時候,就應當肯定輕微暴力行為和被害人死亡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39〕參見錢葉六:《刑法因果關系理論的重要發展與立場選擇》,載《中國刑事法雜志》2022 年第4 期,第111 頁。持否定意見的學者指出,在極為輕微的侵害行為引起嚴重后果的場合,因為不存在所謂的行為危險,所以很難說現實結果是行為危險的現實化,因此應當否認輕微危害行為與嚴重后果之間的因果關系。〔40〕參見黎宏:《因果關系錯誤問題及其應對——以行為危險現實化說的再闡釋為中心》,載《法學研究》2022 年第1 期,第116 頁。輕微暴力引起被害人死亡的案件中,不僅涉及行為的刑法定性,還涉及侵權行為的民事責任。本文不否認輕微暴力屬于民法上的侵權行為以及該行為和被害人死亡之間存在民法上的因果關系,但是,刑法作為最嚴厲的制裁措施的性質決定了刑法因果關系有其自身特點,即相對于民法中的因果關系,刑法中因果關系的范圍要狹窄。一方面,在質上,刑法中的因果關系只限于實行行為和構成要件結果之間的關系,沒有實行行為,無從談起因果關系,刑法中的因果關系的判斷重視對是否存在犯罪的實行行為這一前提基礎問題的認定;另一方面,在量上,刑法中的因果關系也有程度的要求,對于實行行為和結果之間只是存在微弱關聯性的場合,要謹慎地肯定刑法中的因果關系。輕微暴力既不屬于故意傷害罪的實行行為,也不存在過失致人死亡罪的實行行為,所以,此類案件定性,并非主要是個刑法因果關系的課題。更何況,此類案件中,輕微暴力一般只是死亡的誘因,在量的方面也無法肯定刑法中的因果關系。〔41〕錢葉六教授之所以肯定該情形中存在刑法因果關系,與其對實行行為的界定有關。錢教授實際上將被害人特殊體質納入實行行為的判斷中,這種觀點為本文所不取。
2.關于過失。過失本質上是行為人違反了注意義務,與因果關系的認定需要注意部門法差異一樣,過失在不同部門法中的含義和認定方法也存在一定的差異性。比如在行為人駕車導致被害人死亡的場合,交警通常會根據《道路安全法》第22 條的規定,以行為人沒有文明駕駛從而認定其具有過失。但是,在刑法上,如果行為人不存在具體違反交通管理運輸法規的行為(如超速、闖紅燈),那么就不能輕易地以沒有盡到文明駕駛的義務為由認定行為人主觀上存在過失。所以,盡管刑法理論對于過失也存在輕過失和重過失的分類,〔42〕參見林亞剛:《犯罪過失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2000 年版,第239-243 頁。但較之民法中過失的判斷,刑法中過失的判斷要嚴格得多。比如,行為人是否存在刑法上的過失,需要具體認定,不能采取過于籠統抽象的判斷。又如,成立刑法中的過失還需要量或者程度的要求。行為人主觀上有無過失,表面上看是個主觀問題,系對行為人主觀罪過的判斷,但主觀認識是客觀事物在人的意識中的反映,對主觀罪過的判斷不可能脫離客觀事實。輕微暴力引起被害人死亡的案件中,行為人主觀上有無犯罪過失,同樣離不開是否存在犯罪實行行為以及行為和死亡結果之間關聯性及其程度的判斷。此類案件中,行為人并不明知被害人系特殊體質,在行為人眼中,被害人系健康正常的人,輕微暴力和被害人死亡之間的因果關聯性難以被肯定,在這種情況下,自然難以認定行為人主觀上具有刑法中的過失。過失犯的構成要件屬于開放構成要件,開放構成要件的判斷具有相對的不確定性和不明確性,這就為過失的擴張認定提供了便利,實踐中常見的情形是,當發生被害人死亡的場合,無法肯定行為人主觀上具有故意,很可能會理所當然地肯定行為人主觀上具有過失進而認定行為成立過失致人死亡罪,這很容易導致過失致人死亡罪過度擴張,滑向兜底條款。
3.兩種情形的定性有無必要區分。如文首實證數據顯示,在輕微暴力引起被害人死亡的兩種情形中,整體而言行為定性存在一定差異。行為人有特殊體質的,辦案機關以過失致人死亡罪處理為多;沒有特殊體質的,以故意傷害罪處理更為常見。犯罪指的是刑法規定的具有嚴重法益侵害及其危險性的行為,所以,犯罪認定必須堅持行為和被害(法益侵害)的有機統一。但在現實社會中,事物并非總是統一性的存在,輕微暴力引起被害人死亡就是行為和法益侵害結果兩者明顯失去比例、不協調、不統一的適例。本文并不否認兩種情形的構造存在的差異性。但既然現代刑法對于法益的保護是立足于行為刑法的體系展開的,在行為刑法體系中,是否存在犯罪實行行為以及實行行為是否具有法益侵害危險性是犯罪判斷的基礎,在輕微暴力引起被害人死亡的前述兩種情形中,行為的性質以及法益侵害的危險性并無明顯不同,所以,本文的論證和結論應統一適用于該類案件的兩種情形。
五、進一步的思考:關于此類行為處理的思考和建議
以上從刑法教義學的角度闡述了輕微暴力引起被害人死亡的定性,嚴格按照刑法理論和邏輯,輕微暴力引起被害人死亡的場合,行為既不成立故意傷害罪,也不構成過失致人死亡罪,將此類行為認定為意外事件,更符合行為的構造和性質。但眾所周知,刑法是現實社會的產物,刑法的適用離不開理論和邏輯,但也不可能在純粹的理論和邏輯中運行。實踐中辦案機關對行為性質的認定在立足于刑法規定的同時,還要綜合考慮刑事政策、被害人訴求、社會效果以及辦案傳統。輕微暴力引起被害人死亡案件屬于傳統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的犯罪類型,行為的定性與刑事政策和案件處理的政治效果關系不大,辦案機關更多關注的是法益侵害事實、被害人訴求、辦案傳統和普通社會民眾的法感情。一方面,我國有“死者為大”的社會文化情感,即便行為人只是實施了輕微暴力,但是面對被害人的死亡如此嚴重的法益侵害結果,社會民眾心理很容易滋生刑罰處罰的訴求;另一方面,面對被害人的死亡,家屬往往具有強烈的處罰訴求,特別是在其賠償無法得到滿足時,其訴求往往會對辦案機關和人員造成一定壓力。加之我國有重刑主義的法文化和思維傳統,在明顯發生嚴重法益侵害的情況下,保持刑法的克制將輕微暴力引起被害人死亡的案件認定為意外事件,是有相當難度的。為了妥善處理案件,辦案機關一般會在積極動員行為人對被害人賠償補償的情況下,對于行為的定性采取一定退讓或者妥協。具體來說,辦案機關一般既不會采取明顯對被告人不利的做法,將行為認定為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罪,也很難嚴格地按照刑法理論的邏輯將行為認定為意外事件(無罪),而是采取折中立場將行為認定為過失致人死亡罪。亦如《刑事審判參考》第1080 號指導案例張潤博過失致人死亡案的“裁判理由”所言,對輕微暴力引起被害人死亡行為以過失致人死亡罪定罪處罰,有助于貫徹罪刑相當原則,更符合公眾的一般判斷,容易為社會民眾接受。〔43〕參見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第一、二、三、四、五庭主辦:《刑事審判參考》(總第103 集),法律出版社2016 年版,第52-53 頁。但是,刑法適用事關罪與非罪的界限,應盡可能符合行為性質,保持節制,確保刑法適用的公正。對于此類行為的處理,本文建議是:辦案機關應重視行為人與被害方的溝通協商,行為人積極賠償并取得被害方諒解的,盡量避免將行為入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