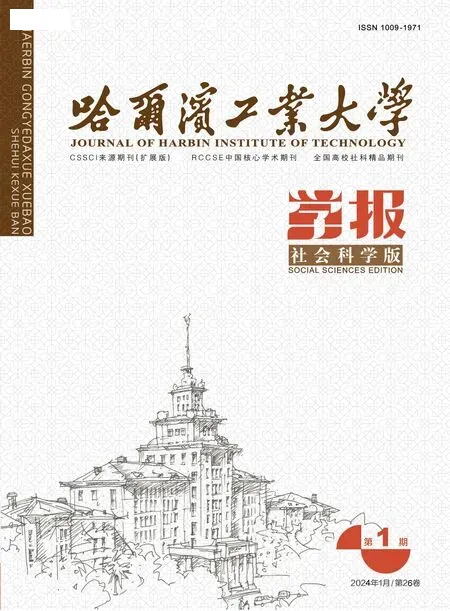社會學視域下中國唯美主義文藝思潮的理論譜系及反思
李桂全
(蘇州科技大學 文學院,江蘇 蘇州 215009)
唯美主義是藝術自律的具體表征。 藝術自律是現(xiàn)代性分解過程中審美文化場主體性論證的結(jié)果。 但是,中國唯美主義文藝思潮理論不僅是審美場域主體化的知識學建構,還是一個融入中國現(xiàn)代歷史等眾多他律因素的思想命題。 這無疑為我們梳理中國唯美主義文藝思潮的理論譜系提出了諸多挑戰(zhàn)。 如果無法清晰地梳理其理論譜系的歷史脈絡,那么就無法全面理解這場鑲嵌在中國審美現(xiàn)代性進程中聲勢浩大、影響深遠的藝術思潮運動,甚至僅僅把某一觀點如“為藝術而藝術”當作唯美主義理論的全部而以偏概全。 因此,考察中國唯美主義文藝思潮的理論譜系,不僅要關涉“為藝術而藝術”的理論綱領,還要深入到中國折疊的現(xiàn)代性之中。 目前關于中國唯美主義文藝思潮理論的研究多集中在唯美傾向的個體作家或者唯美主義思想的某一個方面的深度闡發(fā),遺憾的是,缺乏對中國唯美主義文藝思潮理論譜系化的整理研究與反思。 為此,本文在現(xiàn)有史料以及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從社會學視域梳理中國唯美主義文藝思潮的理論譜系。 為了能夠清晰地呈現(xiàn)中國唯美主義文藝思潮理論在歷史中的面貌,從中國唯美主義文藝思潮的內(nèi)在生成、美學實踐、審美擴張、美學消解等四個方面對其進行全方位的打量是有效路徑,從而使中國唯美主義文藝思潮理論以自我澄明、敞開的狀態(tài)呈現(xiàn)于歷史面前。
一、從個性解放到藝術自律:唯美主義文藝思潮理論的美學生成
眾所周知,西方唯美主義是現(xiàn)代性場域分解背景下,審美文化場主體化論證的結(jié)果。 西方唯美主義者也是在審美自主的合法性保護下充分享受著藝術場帶來的縱情、自主與自由。 但是這種邏輯路徑并不適合中國,正如劉小楓所言:“當漢語社會理論關注現(xiàn)代人文—社會科學的中國化或本土化問題時,必然涉及理論基設與民族的歷史經(jīng)驗的偶在性關系,因此,論者們試圖調(diào)校西方社會科學的問題設定,限制其理論框架在中國社會科學中的解釋有效性。”[1]140劉小楓的這一觀點無疑切中了西方理論的中國問題。 在此意義上,我們要想破譯中國唯美主義文藝思潮的理論密碼,就必須把中華民族的歷史經(jīng)驗納入進來。 為此,我們既要關涉到中國后發(fā)現(xiàn)代性與西方先發(fā)現(xiàn)代性的錯位現(xiàn)象,又要關涉到中國追趕現(xiàn)代性過程中現(xiàn)代性內(nèi)部不同的歷史階段在中國的折疊現(xiàn)象——現(xiàn)代性的不同歷史在中國同一時間中呈現(xiàn)[2]。
中國唯美主義文藝思潮生成于五四運動時期。 在此之前,盡管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的統(tǒng)治,但是強大的禮教傳統(tǒng)依然以堅固的形態(tài)宰制著人心,正如杜亞泉在1914 年《東方雜志》上所言:“終覺吾儕之社會間,積五千年沉淀之渣滓,蒙二十余朝風化之塵埃,癥結(jié)之所在,迷謬之所從,不可不有以擴清而掃除之。”[3]1盡管像他這種先覺之士有掃除之愿望,但是這一時期的社會狀態(tài)仍然是封建倫理占據(jù)統(tǒng)治地位的總體化社會。 在這種社會倫理下,個人生活意義的展開完全是在宗法倫理中獲得,正如許紀霖所言:“在古代中國,乃是一個家國天下連續(xù)體。 個人的行動和生活的意義,只有置于這樣的框架之中才能得到理解并獲得價值的正當性。”[4]46然而這種個體生命的展開方式基本上全都把自己交給了自己所處的共同體,也就是說在獲得共同體庇護的基礎上讓渡了自己的主體性,從而沒有了自己。 如果沒有西方文化的涌入,每一個體或許在這種倫理中安然不覺,但是隨著西學東漸,個體意識逐漸覺醒。 1914 年杜亞泉甚至認為“吾儕不改革自己之個人,而侈言改革社會,是實吾儕之大誤也”[3]4。他直接把個人改革的地位放在了社會改革的前面。 此后到了新文化運動時期,進一步對“個人”話語進行了論證,如陳獨秀強烈地批判了家國天下三種共同體之下的“忠孝節(jié)義,奴隸之道德也”[5]2的價值觀。 同樣發(fā)表在《青年雜志》創(chuàng)刊號的高一涵文章認為:“人則有獨立之才力心思,具自主自用之能力。 物可為利用者,而人則可為尊敬者也。 人之所以為人,即恃此自住自用之資格。”[6]6高一涵的論述具有了康德在《何為啟蒙?》開篇所論述的勇敢地運用自己的理智脫離自己招致的不成熟狀態(tài)的味道[7]22。 此后,隨著新文化運動的爆發(fā),個性解放的呼聲逐漸響徹中國大地。 然而此時面臨的情況是“既定的社會秩序并沒有為他們所要求的自由提供廣闊的天地,相反,倒是設置了各方面的障礙”[8]58,于是,這里產(chǎn)生了與傳統(tǒng)宗法倫理對抗的個人解放話語。 個人解放獲得的合法化論證的首要前提便是把傳統(tǒng)整一化的宗法倫理進行分解。 只有宗法倫理遭遇分解之后,人才能徹底解放出來,而分解的前提便是各個場域倫理的自我論證。 具體到文學藝術領域便是走出“文以載道”的傳統(tǒng)而走向文學藝術自身即藝術的自我指涉——藝術自律。 只有分解的場域才能為個體自由提供選擇,具體到唯美主義,正如劉欽偉所言:“唯美主義注重的是藝術本身,而要解決的應該是人生的問題。”[9]61因此,為藝術自律論證就是為個性解放論證。 個性解放的呼聲在五四響徹中國大地之后,藝術自律即“為藝術而藝術”的聲音也必然越來越強烈。 在這種意義上,中國唯美主義文藝思潮的理論邏輯路徑呈現(xiàn)出與西方相反的方向,即中國唯美主義文藝思潮是為了個性的解放所以要完成藝術的自律,以此分解總體化的封建倫理結(jié)構。 而西方唯美主義的發(fā)展是現(xiàn)代性早已經(jīng)完成了場域的主體化論證,即西方唯美主義是藝術自律的結(jié)果,并且西方唯美主義的功能是解決場域隔離、排斥帶來的現(xiàn)代性之隱憂。
在人性解放的呼聲下,為藝術場的主體化論證成為消解總體化宗法倫理結(jié)構的有效路徑。 當這種路徑遇到西方已經(jīng)完成詩學論證的唯美主義時,必然形成了一種內(nèi)在的契合,即對外追求個性解放與對內(nèi)追求藝術自律。 在內(nèi)在驅(qū)動與外在影響的雙重作用下,一場“為藝術而藝術”的運動就此轟轟烈烈地展開。 中國唯美主義文藝思潮的詩學體系也在此開始生成。 當然,在生成之初,由于缺乏深入的辨析,與其說是中國唯美主義文藝思潮的理論綱領,不如說是中國新文學形式的一種口號宣傳。 盡管如此,卻具有了開創(chuàng)性的意義。在這一階段,貢獻最大的莫過于創(chuàng)造社,其成員如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田漢、鄭伯奇等人。 在1922 年郭沫若針對功利主義的藝術觀發(fā)表了自己的看法:“假使創(chuàng)作家純以功利主義為前提從事創(chuàng)作,上之想文藝為宣傳的利器,下之想借文藝為糊口飯碗,這個我敢斷定一句,都是文藝的墮落,隔離文藝精神太遠了。”[10]177郭沫若不僅批評了功利主義的藝術觀,并且還對他曾懷抱的功利主義藝術觀產(chǎn)生了懺悔。 到了1925 年,他的“為藝術而藝術”的思想進一步明確,他主張“文藝如春日之花草,乃藝術家內(nèi)心智慧的表現(xiàn)……是沒有所謂目的”[11]2。 郭沫若在此持的仍然是藝術無功利性的觀點。 創(chuàng)造社的成員郁達夫也承認美是藝術的核心,并且文藝作品等都是天才的產(chǎn)物而不受外在道德的壓迫,如:“文藝是天才的創(chuàng)作物,是不可以用規(guī)矩來測量的。”[12]139這種倡導其實是用藝術場的審美倫理對抗社會的其他倫理,從而實現(xiàn)人性解放的訴求。 在藝術自律場中,不僅藝術家的獨創(chuàng)性要被論證,批評家的獨創(chuàng)性也要被論證,如:“真的批評家,是為常人而作的一種‘天才的贊詞’,因為天才的好處,我們凡人看不出來,必待大批評家摘發(fā)出來之后,我們才知道豐城獄底,有絕世的龍泉;楚國山中,有和氏的美玉。”[12]139成仿吾的“除去一切功利的打算,專求文學的全(perfection)與美(beauty)……”[13]5-6也強調(diào)唯美的文學觀點。 此外,創(chuàng)造社的鄭伯奇、田漢等都曾為藝術的純粹化進行論證。 當然在他們之間,甚至作家自身的藝術觀中也呈現(xiàn)出多元化甚至相互抵牾的地方。 盡管如此,這并不影響中國唯美主義文藝思潮詩學體系的構建,并對中國唯美主義文藝思潮理論體系的生成作出了巨大貢獻。
在中國唯美主義文藝思潮理論體系的生成階段,需要說明的是,其詩學缺乏深入的理論辨析,甚至在某種意義上只是借鑒了西方唯美主義和其他理論思潮的元素而簡單地加以改造形成一種口號性的宣傳。 “為藝術而藝術”的綱領很大程度上是在與文學研究會的“為人生而藝術”的論戰(zhàn)中形成的。 事實上,在中國唯美主義文藝思潮參與者的眼中,“為藝術而藝術”本質(zhì)上也是為人生的。 另外,由于其詩學自我論證的終極目的是個性的解放,因此,在訴求上又與五四啟蒙的人性解放的訴求形成了一種暗合。 所以中國唯美主義文藝思潮的詩學觀與五四啟蒙運動形成了穩(wěn)定的同構關系,從而二者相得益彰,彼此促進。
二、從藝術自律到藝術實踐:唯美主義文藝思潮理論的美學建構
如果說“為藝術而藝術”口號的提出是藝術場主體性自我論證進而分解總體化宗法倫理而邁出個性解放的第一步,那么藝術場內(nèi)部的建構無疑需要后續(xù)跟進,否則沒有藝術場學科體制的合法性保護,藝術場的審美倫理在發(fā)生作用的時刻可能再次遭遇被一體化宗法倫理消解的危險,個性解放的訴求也因此無從實現(xiàn)。 因為當總體化的宗法倫理再次發(fā)生作用時,人們生活世界的價值和意義又要回歸到家、國、天下三元穩(wěn)定結(jié)構的整體中。 此時藝術場剛為自身建立的“為藝術而藝術”的邊界可能再次被總體化的宗法倫理所打破,所以,此時中國唯美主義文藝思潮不僅需要為“為藝術而藝術”的口號高呼吶喊,更要為“為藝術而藝術”學科的合法性進一步論證,即對藝術自律進行建構。 只有在自律的藝術中提取、抽離出一種生存哲學,并將這種生存哲學放到現(xiàn)實生活世界的對立面,才可能以對抗、批判的美學姿態(tài)拯救在多重現(xiàn)代性折疊之洪水旋渦里掙扎的中國大眾,正如伊格爾頓所說:“審美的自律性成為一種否定性政治。”[14]369不管能否對現(xiàn)實構成一種切實的否定性力量,至少能夠提供一種審美的烏托邦。 因為在理論層面,自律的藝術通過審美所蘊含的自由人格已經(jīng)被康德、席勒以來的眾多思想家多次論證,成為深入人心的力量。 在唯美剛萌芽的中國除了簡單地借用西方之外,對建立起適合本土的、民族的自律化藝術體系則基礎薄弱。因此,中國唯美主義文藝思潮在經(jīng)歷了口號的喧囂之后,重要的任務便是深入到藝術學科的自律性空間中構建學科體系。 在經(jīng)歷了五四之后,中國唯美主義文藝思潮自身被時局重新洗牌,許多作家、批評家在動蕩的社會變革之中又進行了一次選擇,因此中國唯美主義文藝思潮的格局也發(fā)生深刻的變化。 中國唯美主義文藝思潮詩學體系的構建主力不再是創(chuàng)造社,文學研究會的部分成員反而加入進來,新成立的獅吼、純詩派等社團也紛紛為中國化的藝術自律進行論證,于是一場在藝術的審美觀照中實現(xiàn)人生解放的拯救路徑在五四運動的風波之后又興起了一輪。 具體而言,主要沿著兩條路徑:第一,唯美傾向作家人生的藝術化生活;第二,以新月派、純詩派為代表的純粹形式化努力。
首先,唯美傾向的作家以藝術化的生活對抗現(xiàn)實秩序,以藝術的純粹性為人生論證。 西方唯美主義倡導“為藝術而藝術”的終極目的是審美救人,即以在藝術中獲得審美狀態(tài)拯救被現(xiàn)代理性壓制的感性世界,從而達到人生的解放。 在中國,早期創(chuàng)造社的成員雖然借用了“為藝術而藝術”的綱領,但是并沒有深入的理論辨析,所以和中國的五四啟蒙運動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啟蒙運動的一部分。 因此,早期創(chuàng)造社提倡的“為藝術而藝術”其實是為社會啟蒙的。 雖然有個人解放的成分,但是并不純粹,所以當中國20 世紀20 年代中后期,啟蒙逐漸被其他社會矛盾代替的時候,其內(nèi)部的分裂也逐漸顯現(xiàn),即要么徹底地走向藝術的社會工具性,要么走向藝術的個人純粹性。 周作人便是這個時代風口浪尖上的躊躇者,在“五卅慘案”之前就開始走向了“自己的園地”,在經(jīng)歷了一番社會動蕩之后,更加堅定了他自己的選擇。 正如一學者的論述:“到20 年代末,周作人的心境更趨于沉寂沒落,曾經(jīng)作為啟蒙先驅(qū)之文化事業(yè)的文學,已由發(fā)起社會改造,文化啟蒙日益向內(nèi)收縮,起初還是一種知識分子集體性的精神烏托邦,寄托著人生的關懷,最終卻成了一己心靈的避難所。”[15]205由于時代環(huán)境的影響,朱自清、俞平伯、梁遇春、何其芳等紛紛走進純粹藝術的避難所中,并為此進行論證。 如周作人在《文藝的討論》中聲稱:“我以為文藝是表現(xiàn)個人情思為主……我想現(xiàn)在講文藝,第一重要的是‘個人的解放’,其余的主義可以隨便。”[16]在1922 年的這次討論中也可以解釋周作人為什么徹底地走向了個人化的文藝,為了獲得藝術上的慰藉,把生活藝術化,如“我們看夕陽,看秋河,看花,聽雨,聞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飽的點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雖然是無用的裝點,而且是愈精煉愈好”[17]。 在此一學者的分析可以說非常確切:“生活和藝術的唯美——頹廢化是一個統(tǒng)一的進程。”[18]91除了周作人之外,朱自清的“圓滿的剎那”、廢名的莊禪藝術精神等都為藝術化的人生進行了論證并自我實踐。
其次,對文學的形式化努力,其中最重要的領域便是對純詩的探索。 如果說中國唯美主義文藝思潮所嘗試的藝術化人生的努力是對藝術自律的升華,那么對文學形式化的探索則是對藝術自律的筑基。 因為藝術自律的基礎便是純粹的形式化,王爾德曾言:“藝術對事實絕無興趣;它發(fā)明,想象,夢想;它在自己和現(xiàn)實之間保持了不可侵入的屏障,那就是優(yōu)美的風格,裝飾性的或理性的手法。”[19]120正是這種美的屏障,為唯美主義者提供了逃避現(xiàn)代性場域分割帶來困境的避難所,而美的屏障在王爾德看來則是藝術的形式。 愛倫·坡1850 年在《詩歌原理》一文中提出,最好的詩作都是“為詩而詩”的結(jié)晶。 可見,藝術的形式化對藝術自律的合法性論證至關重要。 正因為如此,中國唯美傾向的詩人也開啟了一場“為詩而詩”的純詩學運動。 在20 世紀20 年代前期,周作人、梁實秋等就曾探索過純詩的理論,不過“為詩而詩”的純詩學觀念影響的擴大是20 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情[18]270,并逐步形成了純詩的格局,如象征派詩人穆木天、王獨清,海派文人邵洵美、朱維基,京派文人梁宗岱、朱自清、廢名等不同的純詩集體。在對純詩的理解上都有各自的看法,如穆木天、王獨清倡導的“詩的邏輯學”“詩的持續(xù)性”“詩的統(tǒng)一性”等詩歌藝術區(qū)別于其他文學藝術的獨特性;海派邵洵美提倡的“形式的完美”,正如在《詩二十五首·自序》中強調(diào)的“只有能與詩本身的‘品性’諧和的方式是完美的形式”[20]10;京派的梁宗岱不僅捍衛(wèi)詩的純粹性,還從哲學的高度為純詩提供哲學的基礎,正如他所述:“所謂純詩,便是摒除一切客觀的寫景、敘事、說理以至感傷的情調(diào),而純粹憑借那構成它形體的原素——音樂和色彩——產(chǎn)生一種符咒似的暗示力,以喚起我們感官與想象底感應,而超越我們的靈魂得到一種神游物表的光明極樂的境遇。 像音樂一樣,它自己成為一個絕對獨立,絕對自由,比現(xiàn)世更純粹,更不朽的宇宙……”[21]22總之,在詩的形式化方面,中國這些唯美傾向的作家都試圖在借鑒西方的基礎上為詩的形式化作貢獻。
不論是中國唯美主義文藝思潮的作家對藝術人生化的審美超越,還是對藝術形式的知識學建構,都促使唯美主義美學理論學科化的建構。 與此同時,中國唯美傾向的作家還進行著大量的藝術創(chuàng)作活動,在藝術理論與藝術創(chuàng)作方面共同進行著藝術實踐。 不過需要說明的是,這一階段的唯美主義美學理論在藝術場建構取得的藝術自律,其對抗的對象已經(jīng)不再主要是中國傳統(tǒng)的宗法倫理,而是隨著社會的變革而被卷入到政治革命的洪流之中。 正是因為社會矛盾的變化,個人的啟蒙也在消退,所以我們發(fā)現(xiàn)創(chuàng)造社早期的一些成員紛紛放棄“為藝術而藝術”的主張變成“為社會而藝術”,最典型的莫過于郭沫若的轉(zhuǎn)向。而“為人生的藝術”的一些作家反而轉(zhuǎn)向了“為藝術而藝術”,在很大意義上,他們?nèi)匀粓猿至宋逅膯⒚蓚€性解放的初衷,當然也有躲避政治現(xiàn)代性的嫌疑。 對于整個唯美主義思潮而言,這里遭遇了一個藝術中的重大問題,即是解放個人還是解放集體? 當把個人解放的優(yōu)先性放在了首位,也就逃離了社會革命,因此詩學只能向著純粹化、個人化發(fā)展;如果把集體、階級等放在了首位,也就融入了社會的滾滾洪流之中,從而放棄了藝術自律。 所以這一階段是中國唯美主義文藝思潮的詩學建構階段,也是其理論自覺階段,同時也是其思潮內(nèi)部的決裂時刻。
三、從藝術自律到藝術蔓延:唯美主義文藝思潮理論的美學擴張
中國唯美主義文藝思潮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思潮的發(fā)展中盡管不是主流,甚至在社會變革的年代處于被忽視、被遮蔽的處境,但是在進行理論探索的道路上取得的成果使自身逐步獲得了藝術自律的場域合法性。 如果說早期形式化的探索還在為藝術自律的學科建設進行論證,那么與此同時的人生藝術化生活的取向已經(jīng)具有了藝術向生活蔓延的萌芽,只是這種論證依然自我限定在藝術拯救人生的范圍之內(nèi)。 當藝術場取得的學科合法性開始具有一定影響力的時候,其場域的倫理便在無形之中賦予了藝術場中的藝術品、藝術家、藝術活動等一種話語。 而話語又隱藏著一種權力結(jié)構并天生要產(chǎn)生影響力,于是藝術場的審美倫理此時也就必然向社會生活蔓延。 如果說藝術場的審美話語抵不過政治話語,如面對社會政治情況,周作人走向了“自己的園地”、朱自清躲進了“藝術的象牙塔”,那么對于經(jīng)濟場而言,則非常歡迎這種藝術的審美話語。 事實上,審美話語在經(jīng)濟領域也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 對于中國的唯美主義文藝思潮而言,體現(xiàn)藝術場的審美倫理蔓延到經(jīng)濟領域最淋漓盡致的現(xiàn)象,莫過于上海都市空間的唯美主義文藝思潮在商業(yè)領域的蔓延。 具體而言,本文從以下三個方面展開論述。
第一,從審美解放到頹廢放縱。 唯美主義是審美現(xiàn)代性進程中閃耀的一環(huán),而審美現(xiàn)代性的解放方案便是“從藝術中體驗出一種自由的生命感,這種生命感以其‘異質(zhì)’‘震驚’等意義效果超越了理性的規(guī)訓和世俗的功利,進而帶來個人生命在通往永恒和無限路途上的自由釋放”[22]33。而這種“異質(zhì)”在唯美主義者那里便是美的愉悅以及融合感性沖動和理性沖動的形式游戲。 隨著現(xiàn)代性的推進,理性取得絕對的地位之后,理性的他者就處于被壓制的處境。 被壓制的他者也就是“異質(zhì)”絕不只是審美的愉悅。 如果說從“異質(zhì)”的爆發(fā)之中獲得的審美愉悅能夠使主體性達到自我超越,那么在“異質(zhì)”中的頹廢也能起到同樣的作用。 因為頹廢就是自我的消解,是對束縛身體體制的對抗,是對理性節(jié)制的拒絕。 這種對身體外在體制、理論性的拒絕必然帶來身體本身的解放,甚至這種解放的程度并不亞于審美。 而致力于解放的唯美主義在此就面臨著一個問題,即如何劃定“異質(zhì)”之中的崇高與低俗之間的界限。在此如果我們姑且把審美定義為崇高,那么頹廢可能就是低俗。 事實上,中西唯美主義都沒有明確的理論探析,所以唯美與頹廢也就成了一對孿生的兄弟,但是二者卻有著巨大的差異。 唯美是一種藝術自律,而頹廢則是對藝術自律的打破。頹廢者希望通過身體在浪費、消耗、放縱、越界等“對抗”行為中所產(chǎn)生的震驚快感統(tǒng)一起來,并企圖把瞬間的快感凝固起來并轉(zhuǎn)化成永恒,從而成就自我的絕對解放。 當中國的唯美主義文藝思潮沒有深入理論辨析的時候,卻把效果的等同性理解成了理論的一致性,于是也就把藝術自律的界限打破了。 所以從審美解放到身體放縱的過程在理論上是一次藝術自律危險的擴張過程。 因此,一旦承認了頹廢以墮落的形式對抗現(xiàn)代性也就意味著對藝術自律自身的否定。 由于“現(xiàn)代性存在于一種體驗世界的特殊方式中,一種不只是化約為我們內(nèi)心的反應,而且將其融合進我們內(nèi)在生活的方式”[23]83,所以頹廢的解放在日常生活中大有用武之地。 所以當唯美主義者以醉生夢死、自我放縱的形式去生活的時候,藝術自律的理論已經(jīng)在擴張,藝術自律的邊界也變得模糊不清。西方很多唯美主義者都過著波西米亞式的生活方式就是對這一理論最好的詮釋。 事實上,中國“頹加蕩”的唯美主義也是這一理論的現(xiàn)實樣板,像邵洵美、施蟄存、穆時英、葉靈鳳等作品中所描寫的上海都市體驗很大程度上只有在放縱的條件下才能獲得。
第二,從審美批判到商業(yè)動員。 唯美主義能夠產(chǎn)生批判效力的基礎便是站在現(xiàn)實生活的對立面即藝術自律,因此為了保持批判的效力必須為藝術自律進行論證。 中國唯美主義文藝思潮批判的對象最初不是現(xiàn)代性導致的“牢籠社會”,而是曾經(jīng)的宗法倫理所發(fā)揮的一體化力量。 面對這一情形,中國唯美主義文藝思潮大力為藝術自律進行論證,即便是融入上海都市的“頹加蕩”唯美主義文藝思潮也不例外,如在他們的《金屋月刊》創(chuàng)刊號主張:“我們決不承認藝術是有時代性的,我們更不承認藝術可以被別的東西來利用……我們要打倒有時代觀念的工具的文藝,我們要示人以真正的藝術……不愿受時代束縛的我們,怎愿被色彩與旗幟來束縛! 我們的作品,可以與任何派相像,但決不屬于任何派。”[24]6在邵洵美等人看來,真正的藝術是不被“時代束縛”,不被“色彩和旗幟束縛”的藝術,在藝術中“至上的美”才是真正的藝術。 對于藝術的階級性,他們也提出了質(zhì)疑,如章克標曾說:“文藝是與以利害關系的沖突或一致而分化的階級無關的。 在這一點上,我不懂提倡階級藝術、革命文學等等的人們的理論。”[25]332為了追求藝術自律,他們反對時代、道德或者階級對藝術的束縛。 他們刻意地模仿了西方唯美主義的藝術自律,但是并沒有給自己一個清晰的定位。 在西方,“‘為藝術而藝術’是審美現(xiàn)代性反抗市儈現(xiàn)代性的頭一個產(chǎn)物”[26]46。 但是中國現(xiàn)代性進程還沒有達到這一階段。 由于1840 年以來長期處于落后挨打的處境,中國對現(xiàn)代性的態(tài)度一直是急切的渴望,而對于現(xiàn)代性的任何場域都是大力的發(fā)展,商業(yè)現(xiàn)代性也不例外。當上海都市的商業(yè)文明發(fā)展起來的時候,中國的唯美主義文藝思潮對此不是排斥而是伸開雙臂的擁抱,并急切地享受著商業(yè)現(xiàn)代性帶來的便利,并把藝術的審美與商業(yè)的動員完全融合在一起了,于是藝術自律的邊界也就蔓延到商業(yè)文明的消費社會之中。 事實上,海派唯美主義不論是作家的生活方式還是作品的內(nèi)容都充滿了都市消費的內(nèi)容。
第三,從藝術場域到日常生活。 當中國的唯美主義者打開藝術自律開口的洪水大閘蔓延到商業(yè)領域的時候,不會想到它已經(jīng)難以再次回到藝術自律之中。 盡管一再宣稱反對時代、道德或者階級對藝術的束縛,并在理論的邏輯上追求藝術的形式化,如邵洵美曾言:“形式的完美便是我的詩所追求的目的。”[20]10但是,審美的藝術卻向生活到處蔓延。 也許他們自己也不覺得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如中國唯美主義文藝思潮中的張競生在《美的社會組織法》中試圖以美學的原則擴張到日常生活之中,張競生的目標不僅是日常生活審美化,并且要把審美原則擴張到社會的法權原則之中,向社會領域全面擴張,這無疑會產(chǎn)生日常生活審美化的后果。
此時在理解中國唯美主義文藝思潮的美學理論在擴張的時候需要注意兩點:一是這里缺乏了五四啟蒙個性解放的成分,而簡單地變成了感性的解放甚至是感官的放縱;二是唯美主義擴張后所對抗的對象變得模糊不清,既不是傳統(tǒng)的宗法倫理,也不是西方意義上的啟蒙現(xiàn)代性導致的理性對人的壓制,更不是像卡林內(nèi)斯庫所說的對市儈社會的抵抗。 于是,抵抗的對象不那么明確,但是似乎這些都在抵抗的對象之中,同時又有些新成分融進了唯美主義之中,如都市上海的商業(yè)文明。 總之,中國此時的唯美主義文藝思潮具有獨特性。 如果說西方唯美主義者王爾德站在法庭上拒絕世俗道德的審判是因為它依然站在藝術的文化山上而徹底地享受藝術倫理帶來的放縱,那么中國20 年代后期到30 年代的唯美主義文藝思潮的參與者,尤其是上海“頹加蕩”的商業(yè)唯美主義文藝思潮參與者則是以自稱“謫仙人”的姿態(tài)徹底下凡完全融入了世俗社會,并且把在審美倫理中獲得的解放性置換成在商業(yè)消費中獲得的解放性。 在此審美的命題也悄悄地發(fā)生變化,即個性的解放被簡化為身體感官的放縱與頹廢。 然而,他們一旦下凡也就打破了藝術自律的戒條,所以也就再也無法重返天界,也就是說雖然藝術的美學擴張了,但已經(jīng)沒有了藝術自律。
四、從唯美話語到救亡話語:唯美主義文藝思潮理論的美學消解
在中國多種現(xiàn)代性折疊的進程中,中國唯美主義文藝思潮的詩學體系在征用西方與西方化的日本唯美主義的基礎上迅速建立起自己的詩學體系,并在歷史本土因素融合之中使理論全面鋪展開來。 中國唯美主義文藝思潮的美學理論體系展開的最大特點便是融入了中國本土經(jīng)驗,甚至在關鍵的時候被這種本土的力量改變了自身的走勢與命運。 事實上,在中國歷史的進程中,中國唯美主義文藝思潮如同一顆閃耀的流星瞬間劃破星空然后又隱約地消逝在浩瀚的宇宙中。 尤其是在生死存亡的1937 年之后,唯美的聲音逐漸沉寂下來,這種冰火兩重天給我們留下無限的遐想。 這里面蘊含了眾多復雜的問題,其中最突出的莫過于救亡話語取代了唯美話語。
我們需要追問為什么救亡話語成為主導一切的話語。 為此,我們需要回到中國的傳統(tǒng)之中。傳統(tǒng)中國存在的載體是家、國、天下同構的共同體,并且以王朝共同體為政治意義的最高形態(tài)維持著中國的宗法倫理。 鴉片戰(zhàn)爭之后,隨著西方列強對中國的逐步蠶食,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此時王朝共同體政治開始遭遇解體,在告別古典社會形態(tài)的過程之中,按照現(xiàn)代性的發(fā)展趨勢應是建立現(xiàn)代民族國家,然而半殖民地社會導致中國難以建立現(xiàn)代民族國家。 而中國國人尤其是知識分子有著強烈的共同體歸屬情節(jié),像傳統(tǒng)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終極目的也不過是為了拯救共同體,個人生活意義的展開也是在這一框架之內(nèi)。 這種共同體崇拜的情節(jié)加之半殖民地社會的屬性必然驅(qū)使中國的知識分子重新建設共同體的愿望更加強烈。 只是此時的共同體性質(zhì)在歷史轉(zhuǎn)型的過程中發(fā)生了重大變化,王朝、天下等難以再召喚出個體的歸屬感,正如一學者的論述:“近代中國一個宏闊的時代轉(zhuǎn)變,就是‘天下’的崩散及其多重演變——向外轉(zhuǎn)化成了‘世界’與‘中國’,向內(nèi)轉(zhuǎn)化成了‘國家’和‘社會’。”[27]2在這種意義上,此時共同體“天下”被置換為“國家”。 國家由此成為現(xiàn)代性推進的單位組織形式,并為個體提供保護的功能,但是在中國,現(xiàn)代民族國家并沒有建立起來。 而沒有現(xiàn)代民族國家意義上共同體的保護,個體的審美自由就失去了解放的前提——國家都沒有解放何談個人解放? 正如史書美在描述中國作家經(jīng)歷現(xiàn)代性時所言:“在中國作家遭遇西方現(xiàn)代性之時,一旦作家們?nèi)サ魝鹘y(tǒng)的保護層,就再也沒有其他的東西可被用來代替?zhèn)鹘y(tǒng)以發(fā)揮中介的作用。 在半殖民地上海的都市語境中,人們經(jīng)歷了一種赤裸裸的現(xiàn)代性。”[28]427當沒有了共同體的庇護,我們很難想象個人生活意義如何在世界中展開,在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郁達夫小說中所呈現(xiàn)的國家的困境導致個人的苦悶,施蟄存等小說中理性壓抑感性最終導致主人公的滅亡等。 在此意義上,中國任何思潮流派的發(fā)展都不得不面臨這一問題——建立新的現(xiàn)代民族國家,中國唯美主義文藝思潮也不例外。 在西方,唯美主義是由審美倫理導向個人的解放,但是在充滿悲情歷史的中國,唯美主義不得不兼具國家解放的屬性。尤其是面臨著民族生死存亡的時候,救亡話語自然也就主導了唯美的話語。
事實上,近代以來國人對強大共同體的追求一直是強烈的。 即便我們所說的五四啟蒙運動,常常被定義為一場廣泛的個人解放的運動,但是其發(fā)起點也是反帝反封建的一場愛國運動。 在這種意義上個人解放運動與現(xiàn)代民族國家共同體的建立是交葛進行的,只是具體到唯美主義側(cè)重于從審美中提出個人解放的因素,但是當個人的解放與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建立發(fā)生沖突時,就面臨著優(yōu)先權的問題——先有個人解放還是集體解放?在歷史的洪流之中,他們的選擇已經(jīng)給出了答案。由于唯美主義在進入中國的時候,接受者沒有進行深入的理論辨析,而在很大意義上把它作為反抗封建傳統(tǒng)的工具。 當中國社會革命發(fā)生急劇轉(zhuǎn)型的時候,逐漸形成了理論自覺,創(chuàng)造社的成員后來大多數(shù)選擇了先有集體的解放才有個人的解放。 創(chuàng)造社把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解放寄托在階級的團結(jié)上,通過革命砸碎舊的國家機器而建立現(xiàn)代民族國家,他們紛紛發(fā)表文章,如李初梨的《怎樣的假設革命文學》、成仿吾的《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馮乃超的《藝術與社會生活》等。 如果說1925—1927 年的社會動蕩使得創(chuàng)造社的部分成員發(fā)生轉(zhuǎn)向(放棄個人轉(zhuǎn)向集體)僅僅是中國唯美主義文藝思潮中的一個序曲,那么到了30 年代,尤其是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時刻則是中國唯美主義文藝思潮轉(zhuǎn)向的一個高潮。 此時,唯美主義文藝思潮的參與者也都紛紛轉(zhuǎn)向為國家的救亡而奔走,就連中國最純粹的唯美主義者邵洵美也開始把文學的純粹性暫時擱置一旁而自覺肩負起抗戰(zhàn)文藝的重任。 在1931 年“九一八”事件之后,針對國民黨的不抵抗政策,邵洵美在1932 年《時代畫報》的第二卷第10 期上發(fā)表《容忍的罪惡》,對日本的侵略行為進行了強烈的譴責,對國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進行了言辭激烈的批判;邵洵美1934 年以《人言周刊》為陣地縱論時局,在第3 卷第2 期上發(fā)表的《詩與詩論》詳細地陳述了自己暫時放棄個人的美學追求而為國家的獨立奮斗的心跡;1937 年日本全面侵華、上海淪為孤島之后,邵洵美又創(chuàng)辦了《自由譚》,組織上海的文人進行文藝抗戰(zhàn),以藝術的形式宣傳抗戰(zhàn)救國的理想。 雖然邵洵美思想的變化僅僅是一個個案,但當中國最純粹的詩人都為民族的存亡而奔走的時候,其他唯美傾向的作家在救亡這一話語下進行著藝術的創(chuàng)作、批評實踐活動也成為多數(shù)的選擇。 由于中國的悲情歷史,中國的很多敘事只能在救亡的話語下展開。 在這種情況之下,中國唯美主義文藝思潮的聲音自然慢慢消沉下來。
雖然救亡的話語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甚至直接遮蔽了唯美的話語,但是這里面仍有需要追問或者在理論上需要澄清的問題。 最值得拷問的有兩個問題:第一,救人與救國是否具有兼容性;第二,審美救國是否可能。
首先,看第一個問題。 眾所周知,近代以來,中國一直處于落后挨打的局面。 在這種情況之下,歷代仁人志士進行了艱苦的探索,渴望建立強大的民族國家以立于世界之林,因此救國的任務一直存在。 與此同時,中國傳統(tǒng)共同體下的宗法倫理一直以強大的慣性力量存在,并沒有隨著清政府的滅亡而消失,在這種狀況之下,個體也就無所謂個體。 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zhì)致使個體解放的任務與救國的任務同時存在于中國的社會之中。 因此,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便是先救國還是先救人的問題,或者二者是否兼容,或者優(yōu)先選擇哪一項又會有什么后果。 在羅志田看來,“五四”時期天下主義已經(jīng)向內(nèi)演變成了國家與社會,但是“國家”在那時是一個有很多層次和面相的新概念,甚至也曾是一個被否定的對象[29]39。而對于天下外化的世界,國人則是雙重的態(tài)度:一方面,由于西方的現(xiàn)代性客觀促進了中國的進步,對西方呈渴望的態(tài)度;另一方面,由于殖民的掠奪造成了中國的苦難,對殖民呈對抗、拒絕的態(tài)度。總體來看,殖民控制的局部地區(qū)并沒有成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對“五四”時期的中國來講反對傳統(tǒng)才是主要矛盾,所以救人的急迫性大于救國的急迫性,所以五四的最強音是“救出你自己”。但是,救國的隱憂一直存在,并且隨著民族矛盾的加深,救人不得不讓位于救國。 在此我們看到救人與救國的優(yōu)先性完全是由社會變化的矛盾決定的。 中國社會結(jié)構的獨特性決定了二者在不同的時期只能選擇其一,而不是二者的兼容。 在此我們可以找到反面的例子,對于一直倡導個人主義“耕自己園地”的周作人其實在很大意義上是一直堅持“審美救人”的,所以當中國的社會結(jié)構變化時,這一選擇必然走向了叛國的道路,這也說明了救人與救國兼容的困難。
其次,看第二個問題,“審美救國”的可能性。唯美主義是通向個人解放,那么我們需要追問審美是否可能通向集體解放。 現(xiàn)代性之隱憂凸顯以來,西方眾多的思想家寄希望于審美的方案,甚至把它作為解決現(xiàn)代性危機的整體方案。 1968 年,法蘭克福學派的推波助瀾使審美走向街頭之后,直接的后果便是政府機構的癱瘓、社會的無序。我們?nèi)绻煤髞淼睦碚摵褪聦嵲倏?0 年代的中國,審美救國的方案注定是失敗的結(jié)局。 在當時,中國本身的社會秩序結(jié)構尚處于一種混亂之中,加之日本帝國主義的入侵,企圖通過審美方案趕走入侵者而建立現(xiàn)代國家更是不可能。 在唯美主義文藝思潮涌現(xiàn)之前,蔡元培就曾提出“審美救國”,但是這一理論遭遇了歷史事實的否定。 其在事實上是如此,在理論上同樣沒有可能性,因為審美的原則不可能代替現(xiàn)實社會的原則。
結(jié) 語
中國唯美主義文藝思潮理論譜系的發(fā)展過程中始終離不開西方以及已經(jīng)西方化的日本的影響。 他們作為一個或明或隱的他者影響著中國唯美主義文藝思潮理論譜系的生成與發(fā)展。 這種影響滲透到多個層次、各個環(huán)節(jié),對理論的譯介、模仿、創(chuàng)作都起著重要的作用,從而在話語層面影響著中國唯美主義文藝思潮的藝術自律。 盡管中國唯美主義的發(fā)展也以“為藝術而藝術”為起點,但是中國唯美主義文藝思潮始終指向的是現(xiàn)實的人生,并且在理論的鋪展過程中始終與中國的社會歷史現(xiàn)實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 所以其理論的邏輯除了借鑒西方藝術自我指涉的邏輯之外,又不斷地被他律的因素介入。 與此同時,中國的唯美主義文藝思潮在西方理論與中國現(xiàn)實的基礎上又吸收了傳統(tǒng)美學中的美學因素與美學趣味,如對古代的莊禪藝術精神有所繼承。 綜合來看,中國唯美主義文藝思潮理論譜系的發(fā)展既不是西方或者日本唯美主義的簡單翻版,也不是傳統(tǒng)審美脈絡中內(nèi)生的藝術新芽。 就歷史的事實來看,翻開這份年代久遠的名單,在20 世紀的二三十年代,中國的創(chuàng)造社(前期)、南國社、新月社、彌灑社、獅吼社、清華文學社、綠社、純詩派等社團都曾有過唯美主義的傾向。 如果僅僅從社會或者個人的角度去透視背后的唯美主義理論,則很難澄清其全貌甚至得出褊狹的結(jié)論。 只有把中國現(xiàn)代性的社會歷史事實這一主要因素納入進來,才可能為我們勾勒出一幅彼時中國唯美主義文藝思潮理論譜系的真實圖景,并且也為我們理解唯美主義在后來中國由于社會結(jié)構的原因而長時間處于遮蔽狀態(tài)提供了理論洞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