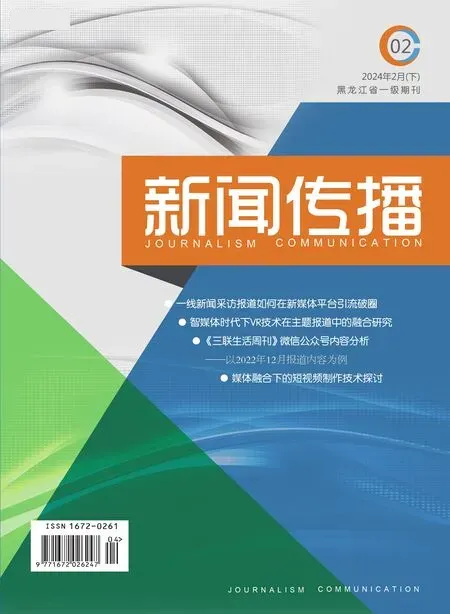社交媒體時代網絡流行語的價值觀呈現
汪雪
(安徽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蕪湖 241002)
Norman Fairclough(諾曼·費爾克拉夫)指出,“話語”在構建社會中起著重要的作用,“話語”既可以反映和描寫社會的實體與關系,又可以建構社會的實體與關系。歷史的變遷使得不一樣的話語在不同的社會背景下相結合,形成一個新鮮復雜的話語”[1]。本文運用費爾克拉夫的話語分析法,即從話語文本、話語實踐、社會實踐三個方面探討網絡流行語是如何一步一步地介入人們的生活,進而挖掘出網民使用網絡流行語呈現的總體價值觀,以期為未來合理對待網絡流行語的策略提供新思路。
一、網絡流行語的話語文本分析
語言永遠不能保持客觀的中立,它所展現出來的話語往往是特定的時代、特定的社會背景所造成的。所以,通過對網絡流行語這一特殊的話語進行文本分析,來理解其在特定的歷史階段所具有的特殊含義。
(一)時代性
不同時代孕育具有時代感的網絡流行語,在不同的社會背景、政治背景和文化背景下產生,每一個時期網絡流行語有所不同,每年排名第一的網絡流行語,如2018年的“命運共同體”,2018年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憲法修正案》,全球關注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2019年的“阿中”,2019年是新中國七十周年華誕,“阿中”的走紅,更是中華人民對祖國母親的深厚感情;2020年的“逆行者”,是在2020年暴發的新冠疫情面前逆向而行的人……
(二)娛樂性
網絡流行語是一種語言的變體,它充滿了活力和創造力,沒有了現代漢語的限制,網友們可以盡情的暢想,網絡流行語正是網民用來消遣和自我娛樂的方式。比如:“我酸了”“吃瓜群眾”“我不要你覺得,我要我覺得”等等。其實,各類網絡流行語具有較強的娛樂性,以迎合網民對自由、民主和開放的向往。
(三)不規范性
網絡流行語一般都要經歷“設置—衍生—模糊”的過程,在其形成初期,網民通過詼諧、比喻、縮寫等手段,創作出通俗易懂的詞語。當這個詞語被越來越多的網友所熟知,網民的自主意識也將進一步發揮作用,再創造出同樣的模因。而網絡流行語的最后形成,常常會被進一步編碼,賦予更多的指代含義。如今年流行的“emo”,一般是指負面情緒,意思是“我很沮喪”“我憂郁了”等這些意思,后經網民再次創作,又出現了“emoha”一詞,指的是人的心情在抑郁和開心中來回跳躍的狀態。
二、網絡流行語的話語實踐分析
按照費爾克拉夫的三維結構,話語實踐即文本向度與社會實踐向度的中介,關注話語生成、傳播、接受的過程,這絕非純粹的語言形式要素所組成,而是在政治、經濟力量、意識形態和文化的強力支配下的“意指過程”。
(一)線上與線下雙管齊下
在現實生活中,由于距離的限制和人們說話的習慣,一個詞語、一句話使用范圍是有限的,社會化媒體的即時、便捷、海量的特點為形成網絡流行語言的信息交互提供了強有力的技術支持,網民可以在同一時間就同一事件暢所欲言,形成強大的輿論浪潮,網絡流行語迅速應運而生。在交互式交流中,線上平臺使用的語言與線下社會使用的語言之間存在著交叉的特點,在使用網絡時,人們會將線下社會中的通用語進行改變,從而形成一種新的網絡用語。[2]
(二)模仿與創作齊頭并進
社會媒介對溝通環境和意見格局產生了更大的影響,互聯網用戶不再被迫接受各種信息,而是托夫勒口中的信息的生產和傳播者,即“產銷者”[3]。在“沉默的螺旋”“群體感染”下,網民開始效仿,開展網絡流行語的集體狂歡。網絡流行語從一個社交媒體發到另一個社交媒體,從一個帖子發到多個帖子,更有網民利用網絡流行語進行二次創作,比如將網絡流行語制作成簡單易懂的表情包、GIF等,實現符號能指的二次詮釋,人們可以從中捕捉更加明顯的價值取向。
(三)接納與認同循序漸進
網絡流行語在網上的傳播并非一帆風順,同時也容易被“噪音”所擾亂,其主要原因在于對其自身價值的扭曲。網絡流行語要獲取社會的認可,必經傳統媒體這一關。在2014年我國進入“媒體融合”元年,中國正在探索如何發展媒體一體化的實踐,互聯網上流行的詞匯是新媒體的重要組成部分,漸漸地被傳統媒體接受,如《新聞聯播》開始擺脫過去一貫的嚴肅刻板的態度,使用“點贊”“厲害了,我的國”等網絡流行語,這些網絡流行語蘊含積極向上的價值觀,加強了新聞傳播的效果。
(四)保存與收編深入人心
網絡流行語形成速度快,消散速度也快,部分網絡流行語因其蘊含豐富的價值觀被政府、市場和現代漢語收編。2014年大火的“有錢就是任性”,下一年“任性”被寫進了《政府工作報告》,警示政府在使用權力時不可任性,如在中國新聞網發表的評論《不能讓地方政府權力太任性》、《人民日報》論政《權力行使怎樣才能不任性》等。網絡流行語被現代漢語收編也很常見,第12版《新華字典》收集較高使用價值的詞匯,比如添加了“點贊”“刷屏”等一些與生活直接相關的詞匯。
三、網絡流行語的社會實踐分析
網絡流行語作為一種社會實踐,積極參與社會的建構,書寫民眾的價值觀念。在社會實踐分析層面,本文側重于從媒體身份和政治、經濟、文化背景出發,解釋網絡流行語所反映的權力關系和意識形態。
(一)政治控制
各個時代有著不一樣的流行語,是一種共同的回憶。在改革開放以前,流行語與社會的政治背景有著密切的關系。新中國成立,政治價值主導流行語,如“同志”“共產主義”“自力更生”等流行語,讓這一時期的流行語充滿著斗爭性,流行語大多為國家話語代言。
在解讀符號時,大眾并非完全處于消極狀態。霍爾提出三種解讀形態,分別是“優先性解讀”“妥協性解讀”“對抗性解讀”。新中國成立時,政治權力對民間話語控制程度較深,人們多是前兩種解讀方式,而改革開放后,人們參與公共討論的能力有所提高,更多地采用“對抗性解讀”,采用借代、隱喻、諧音等修辭手法對其進行“創造性編碼”[4]。
(二)經濟映襯
網絡流行語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我國的經濟發展情況。改革開放后,“科技是第一生產力”“尊重科學”“尊重人才”等流行語反映了國家對科學的重視。進入21世紀,“團購”“云計算”“山寨”等網絡流行語被收錄《現代漢語詞典》第六版中,如今“元宇宙”“碳達峰、碳中和”等新的流行語出現在人們的生活中。
網絡流行語對社會經濟具有反作用,部分網絡流行語本與經濟無關,但當網絡流行語撞上經濟事件,便會產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如2016年火起來的“洪荒之力”后用于財稅改革中,“看來這次財稅改革暫時不需要政府出洪荒之力啦!”從網絡流行語的流行和消亡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而流行語則是民聲、民情、民心的載體。
(三)文化碰撞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從網上的熱門詞匯中,我們可以看到當代中國網絡生態的價值,中國年輕人的積極心態,更重要的是當代中國的文化意識和信心。一些網絡流行語在社會中被廣泛流傳使用,現實中的各種文化領域的介入使其不斷發生意義上的轉變。首先是報紙、電視等傳統媒體與主流文化對網絡流行語的抵制,其次是消費文化在網絡語言中的轉化,最后是外來文化與網絡流行語的碰撞。在各種力量的博弈中,網絡流行語以自身的方式與其他文化交流對話,實現了網絡文化與傳統文化的共存、網絡文化與消費文化的交叉、網絡文化與外來文化的融合[5]。
四、網民的價值觀在網絡流行語中的反映
(一)符號化
“符號”常用來表示其他事物,是雙方交流的載體。在眾多的網絡流行語中,我們可以找到派生和擴展的意義社區,共同構建網絡流行的“話語”類型等。
索緒爾主張,所有的語言符號都有“能指”與“所指”兩種形式,而網絡流行語則是在能指與所指之間進行變換的,不再是一一對應的關系,脫離了其本身的文本意義,賦予了更為豐富的所指內容。以2021年的新詞“躺平”為例,由一開始的一個普通的肢體動作,如今引申為對某種事物的麻木。當前社會的文化多元性,網民們爭先對網絡流行語進行符號化的“再利用”,對現有的文化符號進行“二次創作”、重新“拼貼”,重新建構符號文本意義,也使得網民的價值取向和文化趨向都發生較大變化。
(二)個性化
根據CNNIC第51次《中國互聯網絡報告》,截至2022年12月,我國網民規模已經達到10.67億,較2021年12月新增網民3549萬,互聯網普及率達到75.6%,愈來愈多的網民涌入互聯網熱潮中。[6]2016年,《英國牛津詞典》將“Post-truth”作為年度關鍵詞,人們更愿意去看自己感興趣的東西,公眾從“信我”走向“秀我”,部分媒體變成了李普曼口中“媒體應當先理解,后定義”的相反例子。
在網絡這樣一個大舞臺上,網民不斷根據身處的環境與交往的對象調整在社交中的表演行為,正如戈夫曼提到的“前臺”與“后臺”,“后臺”的準備正是為了在“前臺”可以讓自己變得更完美,“個性化”是網民最看重的,現在的網民也越來越喜歡把自己塑造得與眾不同。
(三)消費主義化
在網絡媒體時代,網絡流行語和商業文化緊密聯系,并表現出很明顯的商業主義傾向,逐漸變成了發布者的“流量密碼”。這種娛樂性、無厘頭的網上流行文化并非為了刺激人們的購買,而是為了激發人們的心理和象征意義上的“欲望”。從網絡流行語的角度看,網絡媒體以“精神欲望”為導向,以達到經濟和社會效果,受眾消費形式多樣、內涵豐富的網絡流行語來滿足娛樂性的“欲望”,由此,二者便走向合謀。
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經常看到百度百科、知乎問答、微博等商業性網絡平臺文章中經常加入屬于不同時段的網絡流行語,他們抓住了受眾容易暫時被特殊用語吸引的特點,以達到提高閱讀量的目標。比如微博上關于“內卷”的話題,只要這些關鍵詞出現,大部分網友們會被其內容吸引,便會實現商業變現。
五、利用網絡流行語塑造價值觀的策略
(一)借船出海:接受網絡流行語,尋求價值觀認同
2020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加快推進媒體深度融合發展的意見》,媒體語言的轉化是媒體融合必經之路[7]。作為官方的代表,概括起來,媒體借網絡流行語“出海”時應堅持以下幾個原則:
第一,內容上取優美棄牽強。不少網絡流行語形象生動,感情色彩濃厚,已成為主流媒體語言系統的一部分。主流媒體應當保持媒體的定力,無論如何,語言的簡練和優雅不可丟棄,不能讓“娛樂至死”損害媒體的公信力。
第二,形式上取規范棄出格。網絡流行語產生的途徑多種多樣,主要包括自發創造、諧音、隱喻、縮寫、外來用語等,部分網絡流行語并不滿足傳統語言規范的要求,再加上信息爆炸,意義紛繁復雜的網絡流行語可能讓人無法深入理解,尤其對老年人十分不友好。
(二)堅守理性:擁抱網絡流行語,堅持正確的價值觀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國家的魅力、國家的團結首先是通過語言來表達和傳播的。”這對網民的媒介素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網民不僅要有個人私德還需要公德素養,還有一定程度的選擇、詢問、理解的能力[8]。
第一,學會辨別網絡流行語。正向的網絡流行語能夠清楚表達個人的思想見解,引導網民樹立正確的價值觀。負面網絡流行語不僅對網民自身身心健康不利,而且不利于社會正能量的傳遞。當前網民越來越年輕化,面對世界總是充滿好奇,他們很容易陷入追趕潮流、表現自我的漩渦。
第二,適度使用網絡流行語。網絡流行語面向的受眾有限,不分年齡、不分階層地使用網絡流行語會造成交流不暢,拉大人群的數字鴻溝,且網絡流行語廣泛使用會對傳統語言造成沖擊,不論未來的語言如何變遷,傳統中國語言才是民族文化的根本。
(三)“守門人”:全社會增強把關意識,凈化互聯網環境
首先,建立社會的“把關人”。全社會必須始終把握正確輿論的導向作用,加強對各類媒體和各類傳播平臺的監督,不給不良網絡流行語提供傳播的平臺。
其次,建立制度的“把關人”。短視頻公司應建立內部規章和法則,配合國家有關制度,樹立正確的價值觀以及責任觀,在規則范圍內傳播內容,限制管理。
最后,建立技術的“把關人”。技術把關即充分調動數字科技力量,以人工智能為主體,算法為內核,以人機交互為主要形式的新聞把關活動。在新聞采寫層面,系統就要對網絡流行語進行歸類分析,保證新聞文本生產的準確性;在新聞分發層面,通過數字化管理,實現“精準畫像”,增加信息發布的針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