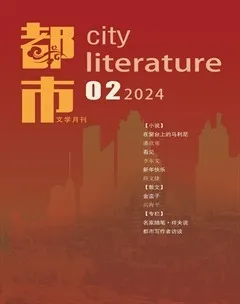新年快樂
傍晚六點多點,龔杰睜眼緩了好一會兒才爬起來關(guān)了鬧鐘。要說起床氣,天黑以后的氣要比早起的氣大得多。這么一想,龔杰不禁樂了。
手機還在響個不停,微信群多出了幾百條新消息,這是一個近五百人的跑步群。眉城雖說只有六十萬人口,但隨處可見跑者的背影。翻完這些有趣的人的有趣消息,才發(fā)現(xiàn)大豪給他打了兩個語音電話。他又是一樂,回了個帶問號的表情。大豪不久前體檢查出了脂肪肝,嚷嚷著要跟他跑步。瘦得像電線桿的人也會得這種病,龔杰真是想不明白。
大豪很快就開始了跑步,卻對龔杰的提醒充耳不聞,結(jié)果,用力過猛又不注意方法,沒幾天就弄傷了膝蓋。回老家休養(yǎng)了半個月后,大豪再也不跑步了,而是轉(zhuǎn)頭又跟別人去學(xué)騎行。這個比自己年輕幾歲的男孩真讓龔杰哭笑不得。一直沒收到大豪回復(fù),龔杰也并不在意。誰知道那家伙又在想哪一出呢。
離上班時間還早,他去常去的那家快餐店,吃了一碗餛飩和一個厚厚的牛肉餅后,就溜達上了彩虹橋。這里是擁擠城市的一處開闊天地。橋上看風(fēng)景的行人很多,成百上千張嘴同時說個不停。所有人好像都是一個活法,又活得各不一樣。龔杰第一次站在橋上的愉悅心情現(xiàn)在絲毫未變。周末或調(diào)休的時候,他總要來這兒跑一趟。
他有好幾天沒跑步了。望著不斷從他身后路過的跑者,想跑的情緒依然不大。正因為不想跑才去跑,這才是跑者的思維模式。這是一次跑步途中偶遇的一位跑友說過的話。或許出于這個原因,龔杰從不認(rèn)為自己是個跑者,因為他只有想跑的時候才會去跑步。
風(fēng)很大,他一個勁兒打冷戰(zhàn)。今年冬天冷得太快又太早。望著東邊的天際線,還能看見群山的輪廓,老家肯定下雪了吧。老家就在秦嶺香山腳下,每年早早就落雪。小的時候他最喜歡冬天,到處捂著厚厚的雪,家里什么事情也沒有,大人有大人們的樂事,小孩也有他們自己的樂事。他和伙伴扯著蛇皮袋子當(dāng)坐墊,把坡路當(dāng)作滑雪場,盡情地?fù)]霍著童年。開始痛恨那個地方是他上中學(xué)以后的事情了。等到上了大學(xué),他便決定畢業(yè)以后離那個地方越遠越好。如今這個愿望算是實現(xiàn)了。在南方那些年,他連雪的影子都沒見過。最初的時候,他還能從家人、同學(xué)的朋友圈里了解一些那個地方發(fā)生的事情。后來他和他們?nèi)紨嗔寺?lián)系,那時他二十五歲,自認(rèn)為剛從壓抑他的地方掙脫出來,覺得這個決定很酷。
回憶給他臉上帶來了異樣的笑容。直到冷風(fēng)吹得舌頭發(fā)硬,他才閉上嘴。龔杰總是把肥厚的雙唇一咧,讓眼睛在一堆皺紋中間閃閃發(fā)光。小時候舅舅常說他憑張笑臉就能干成很多事。他嘆一口氣,心想,要是能倒成白班就好多了,連續(xù)夜班實在難有好心情。
操作間里依舊是不停歇的機器轟鳴。聞到尿素的氣味,龔杰立馬來了精神。他以前從未在工廠做過工,要不是眉城沒辦法讓他拿起吉他,他還以為工廠生活就是人們抱怨的那樣。剛來的時候,他確實很不適應(yīng),因為需要一直彎腰坐著,腰背疼得厲害,習(xí)慣之前,想坐的時間長一點都難。但沒過多久他就喜歡上了這種工作節(jié)奏。身后的包裝袋堆積如山,手中的藥鏟一刻不停,他學(xué)會了用最少的次數(shù)鏟出規(guī)定的分量,規(guī)格越嚴(yán)越有干頭。因為是計件工,干得多掙得多。干活的時候幾乎人人緘默不語。他揮舞著藥鏟,想象著自己正在隨意撥弄琴弦,腦袋里響起無數(shù)的新旋律。整個操作間似乎也回響著琴聲。他干一會兒活兒,抬頭掃一圈,看著別人臉上保持的別扭神情,好像只有自己干活的時候是快樂的。于是,他對這座城市的感覺也不再是印象中的幽閉和生銹了。
龔杰長大的地方離眉城只有一百公里。小時候他常和姐姐進城。等他再長大一點,就不愿意和她去了,總覺得這座小城和他們那片丘陵地帶差不多。后來,父母開出天價彩禮也沒能留住一心遠嫁的姐姐,和山里多數(shù)的年輕女孩一樣,多年來姐姐和他們也只是靠著“節(jié)日快樂”這樣的短信在維持著親情。他二十一歲那年才第三次成功考上大學(xué),每當(dāng)他和新同學(xué)交換社交賬號的時候,泡在一個個酒吧里的時候,他總會想起那些一起長大的伙伴。他覺得自己還是個孩子,可是那些兒時伙伴大多已結(jié)婚,并且不少人還生了孩子。
“可怕死了。”有一次,他和當(dāng)時的女友聊到了這件事情,女友聽完沉默了一會兒后這樣說。他咧著大嘴笑了,那時的自己真是快樂。大學(xué)第一個學(xué)期,他就談戀愛了,讓那些中學(xué)生氣息還未脫盡的舍友們羨慕不已,得空就來找他取經(jīng)。他吆這個喝那個,儼然一副老大哥的派頭。大學(xué)四年,每月生活費不出兩個星期就會被他揮霍一空,算一算那幾年舍友們接濟他的錢也絕不會少。他們當(dāng)然沒說過要他還,只是這些事情偶爾冒上來的時候,他總會感覺自己還有賬沒還清。
封完二百個包裝袋,龔杰就躲進廁所抽煙去了。有時會無意聽到工友們討論一天能掙多少錢,他算了一下,要是逼自己一把,這個數(shù)字他也能完成。不過,那樣勢必會把這份工作變成苦差事。所以每完成二百的量,他就會起來走走。讓他開心的并不是把這份工錢裝進了兜里,而是可以去抽煙了。一個夜班抽四根煙就過去了。只要有期待,生活就能忍受。——這簡直成了他的人生哲學(xué)。
剛畢業(yè)那會兒,他還常用這句話安慰同事。那時候他在鐵路局的工務(wù)段當(dāng)線路工,每天面對的除了鐵道就是群山。多數(shù)同事的年齡都可以給他當(dāng)父親了。一同分配來的那個同事,從沒見過這樣的工作環(huán)境,天天嚷嚷著要辭職。龔杰聽到那些話就忍不住想笑。
當(dāng)?shù)厝税涯欠N略微隆起的土包也叫作山。他心想,這也算是山?老家就成了他寬人心的談資。結(jié)果他這個勸人的人不聲不響跑了,被勸的人至今仍在鐵道上。真是奇怪。
吸完煙還刷了幾個短視頻,龔杰才重新回到工位。APP推薦給他的都是些游客拍到的秦嶺腹地的雪景。這個冬天穿梭在秦嶺的那趟6063次綠皮火車突然火了。第一次看到類似的視頻時他還在深圳。時間洗去了真實與虛擬之間的差異,有一瞬間他感到老家那片大山是這個世界上最美的地方。這種感覺隨著冬天的逼近愈發(fā)強烈。
在深圳那幾年,為了還債,龔杰白天教學(xué)生吉他,晚上在快餐店兼職,老感覺一天24個小時不夠用。只有深夜回到出租屋,才會想想自己的事情。
謝天謝地債務(wù)總算還清了。不用再為錢發(fā)愁,人就重新變得樂呵起來。家長們對他的印象幾乎都不壞,孩子們喜歡和他待在一塊兒。一個學(xué)生還給他起了個“娃娃頭”的外號,他無端地喜歡這個外號。要做的事情見天變好,感覺真是好極了。然而自從看到老家那片大山后,過去的那種不安又回來了。
他和家人們并不是一下子就失去聯(lián)系的。那陣子他老是開口借錢,錢總是不能按期還。他又不敢告訴他們實情,好在撒謊的本事練出來了。只是一次,表弟打來電話討債,沒有一點余地,他沒辦法只得說了實話。表弟在電話里把他罵得狗血噴頭,一條朋友圈就把他所有的事情全抖了出來。曾讓家族引以為傲的大學(xué)生龔杰,如今是人見人躲的網(wǎng)貸者。
在快餐店炸雞塊的時候,龔杰認(rèn)識了個流浪漢,大約六十歲。龔杰發(fā)現(xiàn)那老家伙對別的同事什么話都說,還常逗得別人哈哈大笑,可在他面前總是一副可憐兮兮的模樣,弄得給他管飯成了龔杰每天必需的義務(wù)。不過也花不了幾個錢。他上班的時候就拿當(dāng)天沒賣完的簡餐給他,不上班的話就在路邊攤隨便打包一份順路帶過去。天氣好的時候,兩人就坐在店門口,望著深夜的街市,各自的吃食放在中間交換著吃。老人吃得很少,每次一大半的東西都要剩下來。
有一次龔杰忍不住問了句:“這些東西你帶回去是吃了還是扔了?”老人睜大了眼睛,說:“當(dāng)然是吃了。”龔杰就說:“看你這吃相,你一次就不能給肚子里多裝點?”老人立馬就反駁道:“不行。吃得越多餓得越快。”龔杰笑了。老人又接著說:“要是我把這碗飯全吃了,那最多只能頂半天不餓。如果只吃一半,就算沒弄到下頓飯也不怕。餓得心慌了,一想我還有可以吃的東西,就沒那么餓了。同一碗飯換個吃法,起碼能頂一天不餓。而且剩飯更頂餓。一疙瘩濕米飯一口就解決了,連個米味都吃不出來。你把它晾干,干得一個不沾一個,一粒米就得嚼好半天。一粒干米頂三粒濕米,等于一碗飯變成了三碗。還能餓肚子嗎?”
龔杰一下子紅了臉。十五歲以后,他感覺吃撐比餓肚子的滋味更難受,所以幾乎沒吃干凈過一碗飯。以前也最煩女友問他“吃啥呀”。女友對吃的東西很挑剔,稍有不滿,滿桌的東西便一筷子不動。兩人為吃飯不知鬧過多少次別扭。老人的話耳光一樣扇在他臉上。他當(dāng)下就決定,在這個城市一天,就不會讓老人再餓肚子。可不知從哪天起,他就再沒見過那個老人。同事們都說,這種人都是四海為家,況且人生無常,突然哪天就見不到了也正常。但龔杰覺得自己還在這個城市,就得做點什么才好。于是休息日里他就四處溜達,走進一個個背街的垃圾運轉(zhuǎn)站。晚上閉店,也總是最后一個走。望著窗外,可以看見二十四小時營業(yè)的便利店里,人們進進出出。但那個老人始終沒有再出現(xiàn)。
或許是還記著那個老人,龔杰對見到的流浪漢都發(fā)自內(nèi)心有種親近感。為此大豪沒少說他。這些年他不是不好意思聯(lián)系家人,只是他們——所謂的家人們——似乎并沒拿他當(dāng)家人看。有時候他獨自一人,一連好幾小時都在思考真正的家人是什么樣。
早上八點,走出操作間,疲憊一下子涌了上來。龔杰脫下工服搖搖晃晃去了衛(wèi)生間,撒完新一天的第一泡尿,才發(fā)現(xiàn)外面下雪了。天空儼然一張臟棉被,沉重的棉絮肆意下墜。下的時間不長,地上還沒坐住雪。他不打算睡覺了,準(zhǔn)備帶上吉他去橋上彈。昨晚腦袋里那段旋律,太適合在這樣的畫面里演奏了。
剛回眉城的時候他還想繼續(xù)教學(xué)生彈吉他。而且在幾個大學(xué)、中學(xué)附近租了房子。奈何一個月過去了,他連一個學(xué)生也沒招到。后來他還在網(wǎng)吧里住過一段時間,和大豪就是在網(wǎng)吧認(rèn)識的。大豪是附近學(xué)校的大三學(xué)生,一連幾個晚上都來通宵打游戲。大豪個子高得嚇人,也瘦得嚇人,打起游戲來又滿口的臟話,想不注意他都難。
有天晚上龔杰剛睡著就被捅醒了。“你花錢來這兒就是為了睡覺呀?”
龔杰沒好氣地說:“啥事?”
大豪嘴一咧說:“2K會吧?來上號!”見他沒反應(yīng),大豪愣了一下又問:“《英雄聯(lián)盟》呢?吃雞總耍的吧?”
龔杰不知道他說的是什么,就始終沒作聲。“天哪,你這種人為什么要來網(wǎng)吧?把你煙給我來一根!”就這樣,龔杰跟著大豪打了多半個月的游戲,才找到這份化工廠的工作。
第一次見到現(xiàn)在住的屋子,他就決定搬過來。干脆得讓中介都蒙了。這個小區(qū)的房子最難出手,因為身后不遠就是鐵道,隴海大動脈,火車會把整個夜晚撕得稀碎。中介帶著他轉(zhuǎn)了幾個小區(qū),條件遞減,最后似乎被他折磨得不耐煩了,直接說出來一個便宜得讓他咋舌的房租數(shù)字,帶他來了這里。
以前在鐵路上工作時,他從沒覺得自己喜歡過那份工作。如今離開鐵道,卻發(fā)現(xiàn)自己對鐵道有種純粹的愛。剛搬進屋子那個晚上,他早早躺下。沒多久,火車扯著汽笛呼嘯而過,大地隨之抖了起來。這種感覺太熟悉了。就像躺在一塊漂在海面的木板上,搖搖晃晃仿佛可以到達任何自己想去的地方。他居然舍不得就這么睡過去,直到聽了四五趟火車聲后,他才沉沉睡去。
他記得在鐵路上剛工作那會兒,整晚被火車吵得睡不著,后來鐵軌震動起來才能喚起他的睡意。等到從那里離開后,他反而再也沒睡過一個好覺。
那天在出租屋里,中介臉上異樣的表情一閃而過,不過還是被龔杰捕捉到了。他見識的白眼和臉色太多了,又能如何呢?想那么多干嗎,自己開心就夠了。這么一想,龔杰再沒什么難為情,背著吉他出門了。
白天沒有燈光,又下著大雪,橋上沒什么閑人。正合他意。他望著河景,掃著琴弦。空氣沉重,琴聲傳得不遠,但還是吸引了幾個行人。陌生的人們凍得原地跺腳,情緒卻很高。他開始只是彈,后來唱了起來。上學(xué)的時候同學(xué)都叫他“歌神”,近幾年雖沒人叫了,但這個外號可不是白有的。一連唱了四首,最早停下來的人沒有走的意思,還又聚過來一些。龔杰對這樣的場景不陌生。大學(xué)四年,大小的舞臺他上了無數(shù)次,每次都能收獲不少掌聲。現(xiàn)在看到有人給自己鼓掌反倒有點懼怕,他覺得自己的人生就是被這些掌聲拍壞的。有人問是不是可以點歌,還拿著手機找他的收錢二維碼。他笑著搖頭說,唱首自己寫的歌怎么樣?昨晚腦袋里那段旋律仍在耳邊回響,可他只想出了副歌部分的歌詞,于是現(xiàn)場填詞唱了起來,實在擠不出歌詞就哼哼,一首還沒唱下來,聽的人就散得差不多了。他已經(jīng)不是二十出頭的愣頭青,見不得別人說自己不好,哪怕一丁點兒。路人的反應(yīng)讓他輕松了不少。面對渭河和群山,他把自己的歌逐個彈唱了一遍,過足了癮才回屋。
一進門,龔杰就鉆進被窩了。雪捂了足夠的厚度,下得小了,屋子里很暖和,沒一會兒身子就熱了。很累但也著實開心。還能睡幾個小時,他調(diào)好鬧鐘,閉眼就睡了。
晚上六點半,鬧鐘響了。腦袋暈乎乎的,洗漱的時候,看見鏡子里自己熊貓一樣的黑眼圈,忍不住笑了。這是這個月最后一個夜班,明天就是新的一年了。一年又結(jié)束了。后面就是春節(jié),算一算,這是自己在外獨自度過的第五個新年了。以前為還債,每天過得緊張兮兮,從沒有過孤單。最近他動不動就感到孤單。五年啊,這么久了嗎……
感慨到一半,大豪的電話來了,問他晚上去哪兒跨年。
“晚上要上班啊。”他說。
“今晚還上個鳥班?”大豪劈頭蓋臉來了這么一句。
也是哦。龔杰不禁又笑了。
這幾年他可以說沒放過任何一個可以掙錢的機會。不過,他決定元旦加班也是因為想不到還有別的什么事可干。大豪這么一說,他突然發(fā)現(xiàn),單純地為某個節(jié)日休息一天是很有意義也很有必要的。
一個電話就解決了請假的事。龔杰重新?lián)Q了身衣服。大豪意思是他們先去喝頓酒,快零點的時候去彩虹橋拍幾個適合跨年發(fā)朋友圈用的照片和視頻,之后就去網(wǎng)吧。計劃得很完美,跨年夜就應(yīng)該這樣過。龔杰哼著曲子認(rèn)認(rèn)真真刮了臉,還抹了發(fā)蠟弄了個造型。望著鏡子里的自己,心想小伙子還是蠻不錯的嘛。
大豪一個勁發(fā)消息催他快點。因為事先沒有預(yù)訂,吃飯的地方可能不太好找。但也沒想到這么難。他覺得又冷又餓,一開始的熱情慢慢冷卻了下來。大豪嫌龔杰磨蹭,龔杰埋怨大豪為何不早一點訂個位子。你一句我一句,兩人有點馬上就要不歡而散的感覺。幸好有家火鍋店在他們前面只排了三桌。大豪嘴一咧決定就這兒了。
上了桌,大豪酒杯按得低低的,一聲“哥”就讓剛才的不愉快煙消云散了。幾杯酒下肚,兩人就開始滔滔不絕。話題不知怎么就說到了回家上。大豪說下個星期就準(zhǔn)備回家啦,學(xué)校放寒假了。龔杰就說羨慕,別說寒假了,像今晚這樣的情況,他自從畢業(yè)后就很少有了。大豪一本正經(jīng)地點著頭,大著舌頭說就是就是,他一點也不想步入社會,還說他的理想是當(dāng)個作家,坐在家里。龔杰想笑又不好意思,想了想說:“干啥都行,只要是正經(jīng)事。”大豪一聽就不高興了,非要他說說什么事才叫作正經(jīng)事。龔杰嘆口氣,說:“別像我一樣就行。”于是就把自己那檔子糟事全給大豪說了,于是那孩子就沉默了。
龔杰不在意地舉了舉酒杯,表示這些事情都過去了和自己現(xiàn)在無所謂的態(tài)度。大豪顯然沒把他的話聽進去,只是追問他為什么不告訴家人,尤其是親戚朋友已經(jīng)知道了他的事情,為何還不承認(rèn)。龔杰搪塞一通,不過大致說的也是實情。年少輕狂,因為借錢,被很多親戚朋友傷了自尊心,就決定自己收拾自己弄的爛攤子。可大豪老是想聽一些細(xì)節(jié),比如當(dāng)他知道龔杰五年沒回家了,就問:“別人都回家過年了,你在空蕩蕩的城市不覺得孤單嗎?”
而且龔杰已經(jīng)講到下一件事了,大豪才想起似的打斷道:“原來你那會兒住網(wǎng)吧是沒地方去,流落街頭了啊。”龔杰便惱了,說:“你能不能抓住重點,我想說你現(xiàn)在的處境其實挺危險的,時間很快就過去了,尤其是大學(xué)時光,賊他媽快。你是不是也得考慮一下畢業(yè)以后的事了,而不是整天泡在網(wǎng)吧里,哪怕談個戀愛呢。”大豪清醒了不少,說話利索多了,“我就喜歡打游戲,一天時間這么緊張,哪還有精力談戀愛?”龔杰又氣又覺得好笑,說:“那打游戲能當(dāng)飯吃?”大豪一臉驚訝道:“知道現(xiàn)在有多少人靠打游戲吃飯嗎?”龔杰還未反應(yīng)過來,大豪又把自己的家庭情況大概說了。龔杰趕緊表示自己的激動,連說:“那好啊。”大豪“啪”一聲把杯子砸在桌面上,吼了一聲:“好個屁。一想到畢業(yè)就要回我們那里,簡直讓我窒息。”
像,太像了。眼前這個少年,不就是五年前的自己嗎。龔杰心想。這家伙具備想什么就敢做什么的精神,而且明顯表現(xiàn)出對他過去幾年經(jīng)歷的佩服。當(dāng)然了,龔杰也很佩服自己。可如果回到五年前,知道一個選擇做出后,要過幾年那樣的生活,他還敢像當(dāng)年那樣去干嗎?現(xiàn)在想來,幸福的日子其實沒過多久,那幾年經(jīng)歷的事情只是隱去,稍一晃神,便如鯁在喉。和它一比,在鐵道上的生活簡直是天堂。他現(xiàn)在無事的時候,就喜歡趴在窗前望鐵道,冷峻的鐵軌,讓他平靜,心緒淡泊。想些事情,或者什么都不想,就只是發(fā)呆。
這時,大豪似乎意識到剛才的失態(tài),沮喪地說:“我父母是非常強勢的,別看我在你面前這樣,在他們面前我可是連屁都不敢放。不知怎的,他們越是規(guī)劃我的未來,越想把我按在籠子里,我就越想掙脫。”龔杰直盯著大豪,說:“我咋越聽越來氣呢?”大豪眼珠子一下子就突出來了,說:“你生哪門子氣?”龔杰只是苦笑,完了嚴(yán)肅地說:“我不想依賴任何人。這種話都是從那些有人可以依靠的人嘴里說出來的,像我們這樣的人絕不會說這樣的話。”大豪不耐煩地打斷道:“怎么不是,你以為只有你有理想?”龔杰搖了搖頭,說:“你那不是理想,我這也算不上理想。”大豪熱乎乎帶著酒氣的口氣飄了過來,語氣卻是冰冷的:“你確實太失敗了。不明白你怕啥呢,才三十歲就把自己關(guān)在那個化工廠里鏟那些鳥藥粉。”
龔杰有些不高興了,說:“你的意思是我就沒機會再拿起吉他了?你的意思是這么大的城市,我連一個學(xué)生都招不上?”大豪連忙又說:“那倒不是。我的意思是你不能總是只想著教別人吉他,不能認(rèn)為這樣就是好的。那么多酒吧、廣場,你去混混嘛,現(xiàn)在網(wǎng)絡(luò)這么發(fā)達,你去試試嘛。”大豪看龔杰沒什么興趣,就說了一堆想法和具體實施的細(xì)節(jié),揚言這些事情自己都能幫上忙。龔杰笑了一聲,說:“這就打算跟我干啊,還說自己是有理想的。”大豪想說什么,但筷子在空中劃了幾道,最終沒作聲。龔杰就安慰道:“這些都是填飽肚子以后的事。總之,要是我有個能為我規(guī)劃未來的父母,我就不折騰了。不過,我不勸你,你愛咋折騰咋折騰。成了更好,成不了,你父母不是把什么都已經(jīng)給你準(zhǔn)備好了嗎,回家唄。”大豪就問:“你怎么不回家?”輪到龔杰失語了,他還沒有正式想過這個問題呢。
當(dāng)初沒和任何人商量就辭了工作,和幾個大學(xué)同學(xué)合伙開了家吉他店。結(jié)果不到半年就關(guān)門大吉,并且落了一屁股債。他打電話給姐姐,雖不怎么聯(lián)系,也不常見面,但姐姐還是給他打了路費,希望他來她這邊,再想別的辦法。姐夫在他們當(dāng)?shù)乜h城有一家飯店,是那種只能擺四五張桌子的小店。知道他來幫忙,姐夫自然高興。
一開始,姐夫還不太好意思使喚他。但情況很快就不同了。姐姐撒謊說他還未正式工作,出來鍛煉鍛煉,要丈夫按月給他工錢。店里的事情龔杰干得一塌糊涂還累得要死。姐夫的臉色越來越難看,很多次就差說讓他滾蛋的話了。有一次,姐姐去參加家長會,而那個該死的中午,店里連一個客人也沒有。整個中午,姐夫的眼神針一樣扎得他不安。他坐著的時候扎他,站著也扎,不坐不站走著還扎。龔杰擔(dān)心這么下去,有一天會忍不住揍姐夫一頓,于是給姐姐發(fā)了信息,離開了。
龔杰比一般男孩敏感,自尊心又很強。小時候被父親當(dāng)著旁人訓(xùn)一句就會難過一整天。而父母呢,總是無緣無故地亂發(fā)脾氣。或許并非自己父母的過錯,那片大山里的父母好像都是這樣。他長大后,和父母之間的交流很少能超過十句。正因為此,事情剛開始變化的時候,他根本沒想過要讓父母替他收拾爛攤子。
吃飽喝足,兩人互相挖苦著,搖搖晃晃溜達著。跨年之夜,橋上擠滿了年輕人。龔杰心想,哪一年不糟糕,不然怎么那么多人提起“去年”都感覺比“今年”好呢?但人們迎接新年的儀式感從未缺席。希望和期待在這樣的時間和這樣的地點是肉眼可見的。老家的人們肯定不會為這么個晚上興師動眾。就連春節(jié)也早已變成了累人的事兒。那片大山的麻木是深入骨髓的。他突然理解了姐姐和那些立志走出大山的女孩兒們,也諒解了那些留在那里的伙伴們。他從來只考慮自己那些年是怎么過的,未曾想過家人們這些年是咋過來的。要是他突然出現(xiàn)在家人面前,會是什么樣的場面呢?媽媽那句就當(dāng)沒有兒子了,表弟的熱嘲冷諷,親戚朋友的冷漠……這樣的場景每想起來,他內(nèi)心還是會咯噔一下。總有一天,時間會解開這些疙瘩吧?雖這么想,可他還是沒有冒險的勇氣。
大豪本在拍一群大媽跳鬼步舞,拍著拍著就跟著跳去了。別說,跳得還真像那么回事。這家伙真是個活寶,好像永遠長不大。反正不像個成年人。高興的時候笑得滿臉肉在動,不高興了發(fā)幾句牢騷就完事。龔杰由衷地佩服,這種人無論在哪里都能交到朋友。有朋友就好。
龔杰掏出手機拍下了他的第一個短視頻。再有兩個多小時就是新年了,他突然想大喊一聲“新年快樂”。正想著,就有一雙手環(huán)抱住他的腰,接著他就被攔腰抱進了廣場舞的行列。他才發(fā)現(xiàn)當(dāng)個活寶居然如此快樂。
他們兩人踢踏著步子,像是要把那些擋在面前的障礙物一個接一個踢開似的,都鉚足了勁。兩人趁著酒勁盡情撒歡,直到精疲力竭,臥倒在地。“我想回家了。”龔杰說。大豪“哦”了一聲,說:“早該回去了。”
龔杰摸出手機,輸了一串號碼。空號。又輸了一遍,還是空號。手抖得太厲害。應(yīng)該不會記錯的。然而還是空號。別再為家里沒人尋找你傷心了,他暗想。
大豪拍了他一把。他盯著鍵盤又輸了一遍,沒有聲音,過了一會兒,“嘟——”了一聲,那聲音像靜電一樣打在他手上,他立馬掛斷了。打開微信添加好友,把號碼粘過去,點擊搜索。舅舅用自己的照片作頭像,老得簡直成了另一個人。但還是舅舅。龔杰搓著手機,望著大豪笑了。
責(zé)任編輯 高 璟
作者簡介:
薛文捷,男,1996年生。有小說見《延河》《都市》《中國鐵路文藝》等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