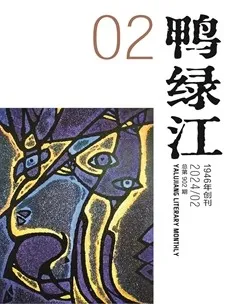鄉(xiāng)行散記
1
三年前,突如其來(lái)的疫情讓快速運(yùn)轉(zhuǎn)的“地球村”驟然慢了下來(lái),城市中一棟棟高樓大廈瞬間變成限制活動(dòng)半徑的水泥籠子。于是在那一年清明前后,我回到了老家紅沙石梁村,開(kāi)始拓荒播種。
說(shuō)是拓荒,也不完全是。過(guò)去村里家戶跟前但凡平整些的土地,都種滿了莊稼,春夏秋三季幾乎沒(méi)有閑著的時(shí)間和空間,就連塄塄坎坎都得栽上豆角、水蘿卜、南瓜抑或倭瓜。后來(lái),或隨子女入學(xué),或因外出務(wù)工——傳統(tǒng)耕種的收入實(shí)在太少了,農(nóng)田就一畦畦、一畝畝、一坰坰被撂荒了。那些被荒廢了十多年的土地,曾經(jīng)浸透了多少輩農(nóng)家的汗水,也曾經(jīng)收獲過(guò)多少玉米、高粱、稻谷、土豆;那些曾被精耕細(xì)作的菜園子,而今只能約莫看出個(gè)塄塄坎坎,只有芨芨草肆意瘋長(zhǎng)。
起初只是想開(kāi)墾一個(gè)小園子供閑來(lái)消遣,奈何到處都有雜草盤(pán)踞,面積又不甚大,用不成農(nóng)機(jī)具,只能一鐵鍬、一頭地開(kāi)拓。僅僅翻地、揀草根、再平整好,就耗費(fèi)了大半個(gè)月的時(shí)間。好在趕在春耕時(shí)分,這塊翻新的地終于能夠播種了。
沒(méi)想到,這一種就是三年。
剛開(kāi)始,純粹是作為一種消遣。到后來(lái),小園子在家人微信群里有了點(diǎn)名氣,竟?jié)u漸熱鬧起來(lái)。幾乎所有親戚都把回來(lái)種地作為一種樂(lè)事,不僅拓展了這塊辛辛苦苦復(fù)墾的園子,而且還把院子里、山梁上過(guò)去撂荒的地也都耕種了。因?yàn)橛辛诉@個(gè)小園子,因?yàn)橛辛松搅荷系母兀總€(gè)周末,每個(gè)節(jié)假日,我們一家人幾乎都是在老家歡聚的。這里成了大人和小孩的樂(lè)園。
是土地把親人聚在了一起。特別是一到五一勞動(dòng)節(jié)和臨近秋收的國(guó)慶節(jié),地里到處都是人。長(zhǎng)居村里的鄉(xiāng)親們打趣:種地的人比“地”都多,收秋的人比“秋”都多。
農(nóng)村的秋天是分外忙碌、辛苦的,一邊享受著收獲的喜悅,一邊揮灑著艱辛的汗水,此時(shí)揮灑的汗水甚至比春耕時(shí)分還要多。酒紅的高粱、飽滿的豆谷、橙黃碩大的南瓜、泛著粉紅光澤的紅薯,還有躺在沙地里的白皮土豆。最令我驚奇是白蘿卜,記得小時(shí)候的白蘿卜個(gè)頭都很小,細(xì)細(xì)的,歪歪扭扭的,現(xiàn)在的卻有七八歲小孩子的胳膊那么粗那么長(zhǎng)。父親說(shuō),現(xiàn)在用機(jī)器耕地,土厚,肥料也足,白蘿卜自然長(zhǎng)得好了。我一想,是啊,現(xiàn)在的孩子多壯實(shí)啊!
印象中的農(nóng)村生活,在秋風(fēng)蕭瑟中,彎曲迂回的鄉(xiāng)間小路上時(shí)不時(shí)會(huì)傳來(lái)幾聲吆喝牲口的聲音,要不然,就是幾聲拖拉機(jī)沉悶的嗒嗒嗒聲……秋風(fēng)吹過(guò)的田野,只剩下齊齊整整的玉米茬子和干草捆子。農(nóng)家小院里,那些高高疊摞起來(lái)的玉米架承載著一年滿滿的豐收喜悅。莊稼人評(píng)判一戶農(nóng)家勤勉或懶惰是有標(biāo)準(zhǔn)的,比如這些玉米茬的高度,比如這個(gè)玉米架的齊整度,再比如這個(gè)玉米架上玉米的數(shù)量等,一切很細(xì)微,卻能夠管中窺豹。當(dāng)然,每個(gè)村莊里也不乏路遙筆下王滿銀那樣整日想著不勞而獲的懶漢,但是絕大多數(shù)農(nóng)民還是勤勤懇懇勞作于田間地頭的,就像路遙筆下樸實(shí)而憨厚的孫玉厚。
再也不會(huì)有比土地更誠(chéng)實(shí)的東西了,除了洪澇、干旱等人類不可阻擋的自然因素外,勤勞者在它身上的付出與收獲永遠(yuǎn)都成正比。它是一名正直的評(píng)委,一年年的秋收時(shí)分,用收成來(lái)評(píng)判著莊稼人全年的勞作;它是一位睿智的老者,用自己的善良向莊稼人饋贈(zèng)希望和夢(mèng)想;它是寬厚的母親,會(huì)原諒人們一次次的懶惰與失誤,只要來(lái)年兢兢業(yè)業(yè),它仍然會(huì)讓你獲得快樂(lè)與幸福。
梁上川下的古老土地里,孕育出多少源源不斷的希望,風(fēng)中、雨里、空氣間氤氳著多少生命的氣息,一汩一汩地涌向心間,流淌漫延。
2
家鄉(xiāng)深藏在黃土高原的溝壑之間,一邊是崎嶇綿延的紅石山,雖不比秦嶺之郁郁蔥蔥,卻也不乏植被叢生;一邊是望不到邊的金沙山,一窩窩蒿草、一處處柳林將其點(diǎn)綴得恰到好處。村旁的小河是窟野河的一條支流,沿著鄉(xiāng)村公路日夜流過(guò),與萬(wàn)萬(wàn)千千的陜北河流沒(méi)有任何區(qū)別。河灘的柳林里棲息著一種鳥(niǎo),叫河鳥(niǎo),其貌不揚(yáng),沒(méi)有孔雀的絢麗奪目,沒(méi)有黃鸝的清麗脫俗。河鳥(niǎo)在逐代進(jìn)化中,早已將渾身的毛色與河床緊緊相和,連家鄉(xiāng)人都不會(huì)過(guò)分注意這種鳥(niǎo)。鄉(xiāng)親們喜歡南來(lái)的燕子在屋下筑巢,歡迎喜鵲飛來(lái)房前的樹(shù)梢報(bào)喜,聽(tīng)見(jiàn)烏鴉的嘶鳴便唯恐避之不及,可獨(dú)獨(dú)不會(huì)注意河鳥(niǎo)。是啊,為什么要注意這樣一種鳥(niǎo)呢?沒(méi)有婉轉(zhuǎn)動(dòng)聽(tīng)的聲音,又躲在離村莊遠(yuǎn)遠(yuǎn)的河床上生活,除非出去覓食,它都在河畔的柳林中,甚至連窩都做在沙蒿林中,讓人不易察覺(jué)。
河鳥(niǎo)是一種孤獨(dú)的鳥(niǎo)。從未見(jiàn)過(guò)它們會(huì)像大雁一樣結(jié)隊(duì)翱翔于天際,它只是將身體壓得很低,“嗖”地飛過(guò)河床,然后又不見(jiàn)了蹤影。沒(méi)人知道它何去何從。兒時(shí)的我,家就在離河不遠(yuǎn)處,對(duì)河鳥(niǎo)十分好奇。也曾細(xì)細(xì)翻遍河床邊的每叢蒿草、每蔟沙柳林去尋找河鳥(niǎo)的家,倒是撿到過(guò)河鳥(niǎo)蛋殼,特別小、特別薄、易碎。這是一個(gè)廢棄的河鳥(niǎo)窩,那是我距離河鳥(niǎo)最近的一次。再后來(lái),河水一年比一年小,河床悄然無(wú)聲地?fù)Q了個(gè)顏色,河鳥(niǎo)失去這層天然的保護(hù)屏障,大概再也無(wú)法安然生存。
很喜歡馮驥才筆下的珍珠鳥(niǎo),它深藏于被植株籠罩的籠子里,卻也能感受人類的善意,學(xué)會(huì)了與人類和睦相處,輕臥于先生肩頭,安然熟睡。而河鳥(niǎo)卻天性警覺(jué),在人類未注意它時(shí),便刻意保持距離;當(dāng)人類破壞它所賴以生存的環(huán)境時(shí),毅然離開(kāi)……濃煙翻滾、河水嗚咽,紅沙石梁兩座大山彼此對(duì)望卻只能聲聲哀嘆。離開(kāi)的,不僅僅是河鳥(niǎo),野兔、山禽亦已拔營(yíng)起寨,不見(jiàn)了蹤影。
生于斯、長(zhǎng)于斯的父老鄉(xiāng)親誠(chéng)惶誠(chéng)恐,害怕離開(kāi),卻不得不走,從此鄉(xiāng)愁氤氳。我們這一代早早進(jìn)城的90后,對(duì)農(nóng)村的記憶還有多少?我們像河鳥(niǎo)一樣遠(yuǎn)走高飛,心上卻銘刻著故鄉(xiāng)的名字,只在內(nèi)心深處去追憶童年的詩(shī)意棲居。
3
沿著門(mén)前的石路往上去爬,來(lái)到半山腰上一塊圓形的場(chǎng)地。這里是早年間農(nóng)民打谷物的地方。順著場(chǎng)邊的小路再往山腰深處走,就能遇到一座碾子。
碾子,在電氣化以前的中國(guó)農(nóng)村很常見(jiàn),是一種利用人力或畜力使高粱、谷子、稻子等谷物脫殼或把米碾碎成子或面粉的石制工具。沉重的石碾子將碾盤(pán)碾得細(xì)膩平整,碾盤(pán)的紋理被風(fēng)霜雨雪打磨得已經(jīng)粗糙。可以想象,祖輩們和祖輩們愛(ài)惜的牲口,曾經(jīng)繞著這座碾子走過(guò)多少圈,碾出過(guò)多少養(yǎng)育一代人又一代人的口糧。
記得小時(shí)候第一次踏上這條路,是因?yàn)猷従踊锇檎f(shuō),祖輩居住的舊窯那兒有一棵水杏樹(shù),要帶我去摘杏。
炎熱的夏季,到處都是紅色碎石頭的山上沒(méi)有多少高大茂密的樹(shù)木,曬得面紅耳赤又干渴難耐的我倆,沿著碾子路往前走著。這個(gè)時(shí)刻我們就盼著能趕快摘幾個(gè)水杏解解渴。山路嶇嶇繞繞,但走慣了還是很好走,我們一步一步往前趕著,離杏樹(shù)越近,離先輩們居住過(guò)的舊窯洞也就越近了。
陜北的窯洞深可達(dá)十米,夏季的太陽(yáng)只能照進(jìn)去一兩米,剩下的就是深不見(jiàn)底的黑暗了。窯洞的木門(mén)框已經(jīng)破敗不堪了,遠(yuǎn)遠(yuǎn)望去,幾口半山腰上的窯洞黑黢黢的,看起來(lái)瘆人。一邊是炎炎夏日里讓我“望梅止渴”的水杏,一邊是感覺(jué)隨時(shí)會(huì)把人一口吞進(jìn)去的黑窯洞,我們躊躇不前。最終,還是沒(méi)耐住水杏的誘惑,在小伙伴的慫恿推搡下,我們一起跨過(guò)去了……到底有沒(méi)有摘到水杏,水杏是青的還是黃的,味道是酸的還是甜的,我早已忘卻了,現(xiàn)在唯一記得的就是那炎熱的中午太陽(yáng)和那幾孔窯洞。
前幾年回去時(shí),我還專門(mén)上山去看了看那幾孔舊窯洞。
雜草叢中的路跡還很清晰,可以順利地走過(guò)去。只是,舊窯洞再也不像小時(shí)候那樣張牙舞爪地張著大口,它們已經(jīng)被黃土斜斜地蓋掉了一多半了,像個(gè)年邁的老人耷拉下來(lái)眼皮半倚在那里。那棵水杏樹(shù),枝葉依舊稠密,只是不大結(jié)果子了。
今年國(guó)慶再回去,不自覺(jué)地又爬上門(mén)前的小山。場(chǎng)里長(zhǎng)滿了芨芨草、白蓮蒿、小榆樹(shù),場(chǎng)畔的酸棗樹(shù)已經(jīng)混起了十幾株。還想再到碾子路上看看,不知是因?yàn)橛晁眠€是其他什么原因,這一次竟然已經(jīng)連路的痕跡都很難辨認(rèn)出來(lái)了。地上到處是村里特有的紅色小碎石,細(xì)細(xì)綿綿的碎石把路覆蓋成了一個(gè)新的小山坡,踩踏上去酥軟滑腳。考慮到邊上就是幾十米深的山渠,我便膽怯得沒(méi)有再嘗試。
碾子路就這樣上不去了。
兒子常常讓我給他講我小時(shí)候的故事。我慶幸的,是還能回到生養(yǎng)自己的那座老房子,指著一物一處娓娓道來(lái);哀嘆的,是再也沒(méi)有人關(guān)注那些舊窯洞、想念那些舊窯洞,亦不會(huì)有人還關(guān)注那個(gè)破敗的門(mén)框和長(zhǎng)滿雜草的場(chǎng)。這些事物仿佛隱匿在世界一隅,只要不去就不知道,只要不想就不存在。過(guò)去,是現(xiàn)在回不去的過(guò)去;現(xiàn)在,是將來(lái)到不了的過(guò)去。舊時(shí)的人都已經(jīng)走出來(lái)了,現(xiàn)在的人還在向著更遠(yuǎn)的地方邁進(jìn)。
4
深秋清晨,薄霧尚未完全散去,隱隱縈繞在山間。低處的楓葉火紅,在身后金黃的梧桐樹(shù)映襯下更顯嬌艷欲滴。楓林依偎著高大青翠的松柏,愈發(fā)明媚燦爛。遠(yuǎn)處山脊的草綠色即將褪去,原生態(tài)的背景生成了一幅天然的大寫(xiě)意。
漫步于天地間,盡情享受綠水青山的滋養(yǎng)滌蕩,誠(chéng)然感嘆大自然的手筆深遠(yuǎn)悠長(zhǎng),呼應(yīng)著如今世上喜氣洋洋的新光景。山對(duì)面,是挖掘機(jī)、翻斗車(chē)耗費(fèi)數(shù)月平整出來(lái)的新農(nóng)村宅基地;河對(duì)岸,是新平整出來(lái)的一百多畝的耕地——母親笑我,這下好好種個(gè)夠吧!
我的故鄉(xiāng),這個(gè)僅僅生存幾十戶的小村莊,即將又迎來(lái)一次新的遷徙。不是山上的土窯,不是山腰的石窯磚房,都成了一排排的二層小樓房……遙遙相望間,歲月的春秋在山鄉(xiāng)的巨變和奮斗的傳承更添神韻。
一陣風(fēng)過(guò)來(lái),叢林里一陣簌簌聲響起,樺樹(shù)以心形的葉,柳樹(shù)似剪刀的葉,楓樹(shù)以五角星的葉,榆樹(shù)像方塊牌的葉,都在以大地給予的本來(lái)模樣,經(jīng)風(fēng)霜?dú)v雨雪后,用更加飽滿成熟的狀態(tài),飄落下來(lái),再次奔向大地,回歸滋養(yǎng)它的熱土。
碾子轉(zhuǎn)啊轉(zhuǎn),山里的祖輩沿著路走下了山;磨盤(pán)轉(zhuǎn)啊轉(zhuǎn),轉(zhuǎn)出的日子磨碎在風(fēng)里、雨間;車(chē)輪轉(zhuǎn)啊轉(zhuǎn),村里的鄉(xiāng)親沿著公路離開(kāi)了村子……出去的路漫長(zhǎng)又遙遠(yuǎn),時(shí)光流逝近三十年。回來(lái)的路,轉(zhuǎn)過(guò)一個(gè)彎和又一個(gè)彎……如今的光景,是兒時(shí)做夢(mèng)都想象不到的模樣。我沒(méi)想到,有一天,柴火塔子燒土豆的香甜,會(huì)成為歲月沉淀后的幸福滋味。誠(chéng)如母親所說(shuō),好日子好光景是奮斗出來(lái)的,只要不放棄,生活總會(huì)越來(lái)越好。
就中國(guó)而言,神木相較于如雷貫耳的北上廣深,還是神奇而隱秘的存在。就神木而言,故鄉(xiāng)的小村莊是平凡到不能再平凡的存在,一樣的山,一樣的川,一樣的人,黃沙紅石只為能讓世人命名一個(gè)不一樣的名字。我熱愛(ài)我的故鄉(xiāng),單單因?yàn)樗巧茵B(yǎng)我的土地。我對(duì)故鄉(xiāng)的眷戀依戀與不舍,經(jīng)常在一次又一次回去的路上得到遞進(jìn)與升華——世界上最遠(yuǎn)的路是離開(kāi)的路,最近的路是回去的路。
夜深人靜,夢(mèng)是千回百轉(zhuǎn)的另一種回鄉(xiāng)。
作者簡(jiǎn)介>>>>
溫姣,陜西神木人,神木市文聯(lián)兼職副主席。在《人民日?qǐng)?bào)》《陜西日?qǐng)?bào)》《榆林日?qǐng)?bào)》等報(bào)刊發(fā)表作品。現(xiàn)就職于中共神木市委組織部。
[責(zé)任編輯 陳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