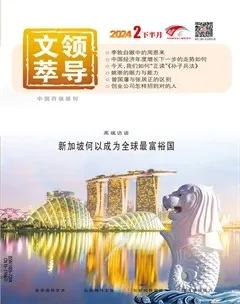科舉新星的大跟頭
清風慕竹
蘇州太倉人張溥才華橫溢,志向高遠,很早就以學識淵博聞名天下。公元1631年,張溥參加科舉考試,一舉中第,入選翰林院,當上了庶吉士,成為大明帝國前途遠大的后備干部。就在大家都以為一顆政壇新星將冉冉升起時,誰也未曾料到,他的天空并非艷陽高照。
入官場立足未穩,張溥就遇到了第一個麻煩。當時按照慣例,進士們的試卷都要集錄成冊,然后頒行天下,供后來的舉子們學習借鑒,這個試卷的序言一定要請科考中的閱卷老師(也稱房師)來寫,以示師生名分。
張溥中舉前以教書為業,他有個學生叫吳偉業,與他一同參加的科舉,結果會試第一名,殿試第二名,成績比他這個老師還要好。吳偉業對張溥極為敬重,寫序言的事兒居然把提攜他的房師李明睿晾在了一邊。張溥雖然知道這個潛規則,但卻不以為意,畢竟他才是吳偉業實實在在的授業恩師。
在古時官場中,潛規則比顯規則更有約束力,李明睿此時已是尚書級別的高官,一怒之下,他要消掉吳偉業的門生資格。事兒鬧大了,吳偉業不得不負荊請罪,登門承認錯誤,這件事兒才得以平息。張溥卻覺得李明睿未免小題大做,很不滿意,初涉官場,便與李明睿結下了梁子。
張溥的麻煩還遠不止于此。在明朝,根據慣例,會試的主考官都是由內閣次輔擔任,首輔因為位高權重,要考慮的國家大事比較多,一般不直接插手科舉的事。然而那一年,內閣首輔周延儒心血來潮,非要蹚這趟渾水。原來他發現那年參加會試的名士很多,就多了個心眼兒,想將這些人收羅在他的名下,成為他的門生。在那時的官場,門生是很重要的政治資源,可以讓自己的執政基礎更厚實些。周延儒這么事必躬親地一破例,自然引起內閣次輔溫體仁的不滿,兩個人為這件事兒暗中較上了勁。
張溥能進翰林院,其實是周延儒的有意栽培,可張溥卻沒往這方面想,他天真地以為那是自己才華出眾、實至名歸的結果。這底氣一足,就難免眼光高了。
翰林院的潛規則,新來的庶吉士見到館長就如同見嚴師,見到先入翰苑的前輩要自稱晚進,開會時不能往前排坐。張溥可不管這一套,見誰都像長輩見到晚輩似的,替皇帝草擬誥命敕令時指指點點,語氣就像領導給下屬下指示一般。翰林們看不慣,就向內閣告狀,周延儒自然好言勸解,而溫體仁正氣不打一處來,批示說:“庶吉士本來就是依例培養的后備人才,能成才就留下,不成才就離開,讓張溥走人有什么難的?”
作為一名官場新兵,還沒怎么著,就被領導給盯上了,這怎么說都是件煩心事兒。然而張溥不但不躬身自省,想想自己的毛病,調整一下心態,反而跟溫體仁杠上了。他搜集了溫體仁結交宮內太監、重用同鄉等違法亂紀的事,揮動如椽之筆,文不加點,頃刻之間就書就一份奏折,交給學生吳偉業,讓他上書彈劾。
吳偉業身為弟子,老師的話雖然不能不聽,但他也深知此時去挑戰一個內閣次輔的風險,于是折中了一下,將槍口對準了溫體仁的親信加同鄉——員外郎蔡奕琛。
這點雕蟲小技怎能瞞得過官場老油條溫體仁呢?張溥徹底得罪了溫派,再加上李明睿時不時地給他添點兒小堵,雖有周延儒的呵護,他在翰林院也待不下去了,便借著為父守喪之由請假回家了。張溥的官場游未及一年,便帶著無數的政治夢想黯然離開了京城。
令張溥沒想到的是,當他無比落寞地回到家鄉,等待他的卻是家鄉人如火的熱情。因為培養出了會元、榜眼這樣的優秀學生,他的身價早已在民間大漲,他還遠在京城時,附近的士子就跑到他在太倉的家中,向北遙拜,自稱弟子,都想沾點老師的仙氣。等他回到家鄉,登門請求收為弟子的人更是絡繹不絕。
重新找到自身價值的張溥精神煥發,他親自主持召開了民間社團組織——復社的大會,自任社長,大會盛況空前,“為三百年來,從未一有此也”。
作為一個在籍守制的官員,這動靜鬧得也實在太大了,很快就驚動了朝廷,引起了朝廷的警惕。再加上唯一賞識他的周延儒告老還鄉,死對頭溫體仁又升任首輔,張溥三年守制期滿,卻再也沒有得到起復的機會。張溥在家郁郁而終,死時還不到50歲。
蘇轍對他哥哥蘇軾四處碰壁、失意連連的解釋是:才高為累,道大難容。其實這只是說出了問題的一個方面。當年嵇康學成下山時,他的老師孫登曾跟他說了一番意味深長的話:火一產生就有光,如果不曉得利用它的光亮,跟沒有光亮沒什么差別。
(摘自《天津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