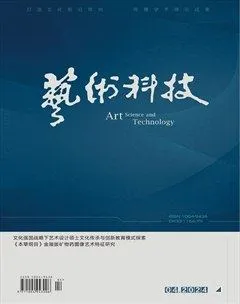論焦氏“心象說”對于斯氏“性格化”形象創造的再發展
摘要:目的:文章梳理焦菊隱先生“心象說”對斯氏體系中的重要理論觀點的繼承發展,打破一些長期存在的誤區,探析“心象說”的核心觀點。方法:文章通過對斯氏“種子論”“內心視像”“構思”等國外理論進行探究,結合焦菊隱先生以人藝學派為代表的舞臺實踐,歸納出“心象說”這套孕育出“心象”再“練”化到人物中的創造角色的方法。結果:該理論是在實踐過程中不斷對斯氏“性格化”形象創造的方法論進行提煉與改進,對斯氏“性格化”所要求的美學觀點與路線加以繼承與發展所形成的成果,為促使演員自覺、有方法地創造鮮明的人物形象,創造出的適用于我國話劇民族化的演劇方式。結論:直至今日,以焦菊隱先生為代表的北京人藝演劇學派仍然在運用“心象說”的方法,通過理論研究與舞臺實踐使斯氏體系在民族化、時代化的道路上繼續發展。“心象說”作為現實主義的“常青樹”,矗立在我國話劇藝術的百花園之中,這是我國話劇實現民族化的重要理論工具,也是社會主義戲劇藝術的光榮。
關鍵詞:? “心象說”;民族化;性格化創造;種子論;內心視像
中圖分類號:J8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9436(2024)04-00-03
0 引言
“心象說”是我國戲劇家、導演焦菊隱先生為創建具有中國特色的演劇體系、探索中國話劇民族化而提出并總結實踐的重要理論。它是以我國民族藝術美學觀念為指導,以話劇舞臺實踐為基礎,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體系(也稱“斯氏體系”)為土壤并將其他國外的體驗派與表現派的理論實踐加以揚棄而建立起來的一套演員進行形象創造的方法學說。“心象說”的釋意從某種角度來說既可以是實用主義的方法論,又可以是具有現實主義美學觀點的辯證法。那么,“心象說”是如何從斯氏體系中發展而來的?它與斯氏體系的其他學說有什么異同或者關聯?
1 與斯氏體系中的一些辨析
1.1 與斯氏“種子論”的辨析
談到焦氏的“心象說”,很多學者或者表演工作者會將其與斯氏的“種子論”進行對比探討,更有甚者會將兩種學說畫上等號。斯氏在《演員創造角色》中收錄了斯氏的學生涅米羅維奇·丹欽科的一段話:“為了使果樹或作物長出來,就應該往地里撒種子。劇作者創造物的種子也應該這樣撒進演員的心靈,腐爛和生根,再從那里長出屬于演員而在精神上與劇作者有血緣關系的新的創造物。”[1]同時,認識時期只是準備時期,而體驗時期則是創造時期。認識時期等于是翻松了土壤,以便體驗時期在角色沒有活躍起來的地方將活生生的生活的種子撒進準備好的土壤中。丹欽科指出,在認識時期需要以演員自身為土壤埋下角色的種子,而體驗角色的整個過程便是這粒種子不斷生長的過程,即斯氏體驗派所說的“生活于角色”,再使“角色生活于你”。帶著斯氏的“種子論”來看焦菊隱先生在《導演的藝術創造》中提出的觀點:“創造人物的初步過程,并不是一下子生活于角色,而應該是先要角色生活于你,然后你才能生活于角色。你必須先把你心中的那個人物的‘心象,培植發展起來,從胚胎到成形,從朦朧恍惚到有血有肉,從內心到外形,然后你才能生活于它。”[2]34將焦菊隱的觀點與斯氏的“種子論”放在一起仔細研究,就能發現斯氏的“種子”學說在創造人物的整個過程中是分階段而言的。斯氏將演員創造角色分為三個階段——認識時期、體驗時期、體現時期。“種子論”雖然貫穿其中,但是它分別在不同時期有著不同的說明意義。“心象說”與“種子論”的區別便體現在其不同的階段。
斯氏提出,創造形象首先應當發現未來人物形象的核心——“種子”。這里要明確斯氏體系中的“種子”從何而來。斯氏認為人物的“種子”來源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劇作家一度創作的劇本,二是演員自身內部。換言之,斯氏在創造人物的過程中更看重“從自我出發”,這也符合斯氏在“性格化”創造上遵循的“直覺和情感的路線”。而焦菊隱的“心象說”則認為,“心象”源于生活,焦菊隱將創造人物的過程概述為:將劇作家所創作的劇本、演員的自身因素以及最重要的生活現實進行“捕捉、培育、創造”,然后在演員的心中“孕育”出人物的心象,最后將心象“化”到演員身上。與斯氏“種子論”不同的是,焦菊隱認為應當在生活中尋找心象,或者說更重要的是符合生活的現實邏輯,并且要對上述三者進行“孕育”。其在提出“從生活出發”的同時破除了斯氏一直反對的對生活進行簡單模仿的弊病。那么,焦菊隱是如何運用“孕育”繼承并發展與斯氏不同的“種子論”的?
1.2 與“內心視像”的辨析
斯氏對于演員創造角色提出演員需要有明確的“內心視像”,斯氏在《演員的自我修養》“想象”一章中引用了托爾佐夫的結論:“只要我一指定出幻想的題目,你們便開始用所謂內心視線看到相應的視覺形象了。這種形象在我們演員行話里叫做內心視像。”[3]從狹義的角度來看,“內心視像”是演員創造人物形象的一個內部技巧,但是縱觀全書可以知道的是,斯氏體系中的“內心視像”一詞其實是一個極其廣泛的概念。演員通過對規定情境形成所感,從而在心中“看到”人物形象和與人物有關聯的一切,由此以角色的身份生活在規定情境之中。可以說,先有了內心視像這一技術技巧,再有從內心生發出角色的形象。與“內心視像”不同的是,焦菊隱在“心象說”提出之始,是特指演員對角色的感性認知,是演員通過對劇本及生活的體驗之后構思出來的人物角色的“心象”。雖然兩者的最終目的都是用于人物的“性格化”塑造,但是斯氏對人物形象的生發可以說是“從內到外”,從演員的內心培植生根,讓內心所感的一切體現在外部形象之中。而焦氏的“心象說”更多是“從外到內”,先對外界的規定情景進行分析,取人物的“大眾像”,并體驗人物的一瞥一笑、動作表情,之后再通過“孕育”演員看到人物的“心象”,最后將“心象”通過訓練“化”到角色之中。
通過上述分析得出,斯氏的“內心視像”與焦氏起初對“心象”的闡述的所指不同,塑造人物的途徑不同。焦菊隱先生通過“心象說”這套完整的方法塑造了一批又一批“性格化”角色。基于此,需要思考的是,在“心象說”不斷發展的過程中,是如何與斯氏“性格化”方法殊途同歸的?在實踐過程中又是如何運用發展的?
2 對斯氏“性格化”方法論的繼承與發展
通過對以“心象說”為指導的北京人藝經典劇目的分析發現,“心象說”在最后呈現的是完全符合斯氏體系中的現實主義創作規律和美學觀點的,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以焦菊隱先生為代表的北京人藝學派通過“心象說”這一方法論對斯氏“性格化”創作方法進行繼承與發展。上海戲劇學院的胡導先生指出,焦菊隱用“心象”這一概念,也許是為了讓演員更加明確這就是在自己“心”中所“看”到的角色形象;或者用斯氏體系的話語來說,就是演員用自己的“內心視覺”所“看”到角色的“視像”。胡導老師在肯定“心象說”在斯氏“性格化”基礎上發展的同時,指出焦菊隱先生在達到演員創造人物的最終目的——“我就是他”的之前階段,還將哥格蘭的“構思”說融入斯氏的“生活與角色”的整體創作,從而讓演員在創造的人物形象中體驗生活 [4]。這也就是前文所指的演員通過“孕育”將“心象”“化”到角色之中。
焦菊隱先生在對斯氏的技術方法進行思考實踐的過程中,發現了“從自我出發”“一切遵循直覺與情感的路線”這樣的方法論使得當時我國的話劇創作逐漸出現一些模糊的誤區,以至于將角色塑造成“已經陳腐下去的現實的意象”和陷入形式主義的溝壑。焦菊隱在思考這些問題時結合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及我國的實際情況發現,雖然當時肯定了生活是角色的來源,但是更應該肯定生活同樣也是一切創作方法和技術的源泉。由此,他提出“心象說”應當是“從生活出發”的方法論。生活可以讓演員得到在現實世界的方法,同時也能讓演員在藝術創造的世界里得到方法論。演員必須把生活的體驗和藝術創造的方法統一起來[2]42。以此為指導,焦菊隱先生在1950年至1953年排演《龍須溝》期間運用“心象說”與北京人藝一眾演員開始本土化的“性格化”創造。作為導演的焦菊隱將演員帶到劇本的規定情境之中,讓演員們深入體會龍須溝中勞動人民的生活。所有的演員不再是“參觀者”和“調查者”,而是在“龍須溝”生活的一份子,以此為演員塑造人物開啟靈感之門,為“心象”的萌發提供火熱的土壤。對此,焦菊隱這樣總結道:“當他們在龍須溝……和勞動人民的思想感情結合到一定程度之后,他們便能根據文學劇本里的要求把階層生活逐漸提煉,逐漸集中在劇本人物的個性上,隨后典型人物的恍惚迷離的影子就開始在他們的內心創造力里朦朧出現了。”[5]146
但是,在這一階段所形成的“心象”只是一個理性概念,真正使“心象”變成“真知”的過程是在進入角色的排演階段。在這一階段,與斯氏的走“直覺和情感路線”不同,焦氏再次將其發展成“練”這一可感可知的技術方法。在排演的過程中,心象是通過一次次的生活于劇本規定情境中而一點點“化”到演員身上的,小到一個眼神、一個手指、一個反應、一個步態,大到人物的臺詞、調度,都是在體驗過程中“練”出來的。到達這一步,實際上與斯氏所提出的“性格化”創造形象的最終結果和目的已經是殊途同歸了。以這樣的方法論為指導,將表現派的“構思”法和我國戲曲中的體現技術手段融入斯氏體系,目的是促使演員自覺、有方法地創造鮮明的人物形象。由此,焦菊隱先生先后運用“心象說”方法論創造王利發、程瘋子、蔡文姬等眾多人物形象,排演出《茶館》《虎符》《蔡文姬》等諸多經典民族化戲劇。
3 對斯氏“性格化”美學觀點的繼承與發展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最終要求演員對人物的創造達到“我就是”,斯氏體系在“性格化”形象創造中提出了“兩個自我”的重要理論概念。演員作為創作者的“第一自我”與作為角色形象的“第二自我”形成矛盾統一體。他強調演員需要化身角色,進入角色的規定情境中生活,同時作為角色的創作者,需要時刻監督自己的表演,駕馭表演的整個過程,激發演員的“有機天性”,“通過演員有意識的心理技術,達到有機天性的下意識的創造”。焦菊隱將斯氏體系創造角色的美學觀點總結為:第一,斯氏體系創造角色的過程是一個體驗的過程,也就是認識和實踐角色生活反復的過程;第二,斯氏體系創作角色的過程是演員的思想情感和角色的思想情感矛盾統一的過程;第三,人物的創作過程是演員內心的體驗和角色形象的體現相統一的過程[5]189。焦菊隱在繼承其觀點的同時,將《實踐論》與唯物辯證的規律融入角色的“性格化”創作中。在排演戲劇的過程中,他牢牢抓住在規定情境中“練”的方法論,重新思考斯氏“雙重自我”的辯證法,以“第一自我”為土壤,通過“生活”長出“第二自我”的種子。他強調,“人物的創造并不是靠‘直覺一下子完成的,形象也是沒有邏輯的順序出現的。第二自我在第一自我的身上一點一滴逐漸發展成長起來的,第一自我的因素,也是隨著‘心象的形成逐漸消滅下去的”[2]58。通過“練”這一長時間的過程,演員在每一次的生活中,更深入地發掘人物的內在特征,找到合理的情緒因素與行動動機,焦菊隱先生將“生活”與“第一自我”“第二自我”有機結合起來,發展出“心象說”,從而使演員通過“有意識的心理技術,達到有機天性的下意識的創造”。
可以說,“心象說”的發展不僅延續了斯氏體系現實主義的美學思想,還極大地豐富了屬于中國本土藝術形象中“意象與真實”的美學觀點。以“心象說”發展創造出的角色并不只是對固有形象的模仿,也不是照抄生活,而是在階級共性中提煉出典型個性。程瘋子、王利發、常四爺等人物的成功塑造符合斯氏體系的創作規律與呈現要求,豐富了我國民族化戲劇的美學價值與廣大人民群眾的精神生活。
4 結語
焦菊隱先生善于吸收和繼承前人的藝術成果,同時勇于革新和創造,他認為斯氏體系的一整套訓練方法是符合科學規律的現實主義創造方法,是為了創造真實、生動的舞臺人物形象而服務的。但這一套方法在實踐運用中帶有一些思想性和藝術性的局限性,特別是在“性格化”塑造的方法上,應該與其他學派中正確的部分以及中國演員氣質的實際情況相結合。經過本文的分析研究得出,“心象說”既不是將斯氏體系“完整拿來”,也不是對斯氏體系中的核心論述加以否定,而是在其基礎之上發展形成的一套系統理論。這樣的民族瑰寶在當今值得每一個戲劇人加以繼承與發展。
參考文獻:
[1]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員創造角色[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117-120.
[2] 焦菊隱.導演的藝術創造[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5:34,42,58.
[3]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第二卷[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87:89.
[4] 胡導.三個演劇學派的不同“性格化”方法[J].戲劇藝術,1991(2):19-28.
[5] 焦菊隱.焦菊隱戲劇論文集[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79:146,189.
作者簡介:鐘慶旻(1999—),男,貴州安順人,碩士在讀,研究方向:戲劇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