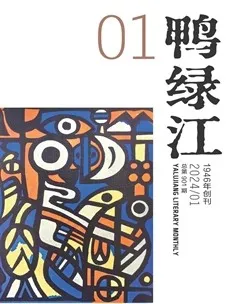賓館
劉齊
我生平第一次住賓館,是在廣州。圍繞這個賓館,我當(dāng)過幾天神秘人物。
神秘是我的自詡,郭先生另有看法。郭先生名叫郭秉箴,抗戰(zhàn)時(shí)在四川三臺的東北大學(xué)讀書,跟我父親是要好的同學(xué)。父親剛到遼西農(nóng)村“走五七”時(shí),郭先生不忘舊情,伸出援手,寄過廣東臘腸等東北罕見的食品。可是,他卻險(xiǎn)些將他老同學(xué)的兒子,也就是我,當(dāng)成一個特務(wù),至少是一個形跡可疑的不良青年。
1977年初,我出差羊城,奉父命拜訪這位比父親小兩歲的郭叔叔。開始一切正常,我只是對他的長相略感驚訝。他的眼睛比我爸的大,而且是雙眼皮,這還不算特別,關(guān)鍵他還長著中國人,尤其是中國北方人罕見的深眼窩。他的額頭,亦即算命先生所說的“天庭”,東北土話所說的“奔兒樓”,還特別光滑飽滿,因此眼窩越發(fā)顯得深而奇異。這次寫稿,我從網(wǎng)上得知他是廣東大埔人,童年隨父母僑居馬來亞吉隆坡。他的深眼窩與出生地和僑居地有何關(guān)聯(lián)?
拜訪臨近結(jié)束,郭叔叔隨意問我住在哪里,我說住在東方賓館。
盡管我的語氣力求顯得謙虛,但內(nèi)心仍有幾分得意,瞧吧郭叔叔,您同學(xué)的這個兒子,雖然來自基層,卻在廣州有如此高級的一個落腳之處。
誰知他的反應(yīng)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不提“東方賓館”四個字啥事沒有,一提郭叔叔的臉色馬上有所變化,馬上又有所掩飾,平靜地說:“走,我送送你。”
我自然要客氣地推辭,越客氣他越堅(jiān)決,而且叫上兒子,同樣是大眼睛深眼窩,活脫一個少年版的郭秉箴。
一路話不多,棕櫚樹,椰子樹,樹樹寧靜。
我很快感覺到,我是在被郭氏父子押送。這我雖然不爽,但能夠理解,廣州,中國的南大門,港澳的隔壁,多容易出特務(wù)啊。國產(chǎn)反特電影本來就不多,僅有的那么幾部,比如《羊城暗哨》,比如《跟蹤追擊》,演的都是廣州。而秉箴叔叔何等人杰,二十出頭像我這么大的時(shí)候,就在四川腹地,在東北大學(xué),跟我爸一起,揭露過特務(wù),戰(zhàn)勝過特務(wù)。現(xiàn)在突然鉆出一個小兔崽子,一個衰仔,人五人六,裝模作樣,居然冒充老同學(xué)的小孩兒,膽子太大了你也!
我知道,懷疑起自東方賓館,該賓館是當(dāng)時(shí)廣州出了名的高級酒店,就在廣交會對面,入住的外賓很多,因此對內(nèi)賓限制很嚴(yán),前天入住時(shí),我已被懷疑過一次。
起疑心的是北京一個部級單位的外事干部,皮鞋嶄亮而且總擦,用酒店提供的擦鞋布唰唰地擦。我被安排跟他同住。
這是一個雙人間,現(xiàn)在想來?xiàng)l件一般般,當(dāng)時(shí)感覺好得不得了,有沙發(fā)、茶幾、電話和獨(dú)立衛(wèi)生間,枕頭被褥散發(fā)的清新氣味讓嗅覺非常愉快,布料漿洗后的微硬爽滑又讓觸覺舒適無比,墻壁心想咱在視覺上也不能落后啊,就涂成了淡綠色,好像晨霧(晚霧也行)中的芳草地——比喻可能不準(zhǔn),好看是真好看。總之這樣的條件,一般人在70年代別說無錢消受,就是有錢,有很多的錢,怕也沒有資格住進(jìn)來。
外事干部大約有盤問人的習(xí)慣,但他不問年齡工資找沒找對象之類民生事項(xiàng),而只問一個比較警惕、比較“門衛(wèi)”的問題:“你是哪個單位的?”
我猝不及防,脫口實(shí)說:“我是沈陽鼓風(fēng)機(jī)廠的。”
他顯然對工廠不是很感興趣,更不關(guān)心鼓風(fēng)機(jī)是炊事用具還是鋼鐵石化設(shè)備,接著問:“你,是怎么住進(jìn)來的?”
怎么,還審上了?我有點(diǎn)來氣,偏不好好回答,硬邦邦地說:“沒怎么呀,一住就住進(jìn)來了。”說完把自己猛地往床上一扔,力道十足的席夢思又把我往天的方向猛地一彈。
斜眼瞧,干部正在發(fā)愣,悶了一會兒,不再提問,似乎把我當(dāng)成一個有點(diǎn)兒背景因此也有點(diǎn)兒脾氣的人。
剛才我不說我是工廠的,效果可能更好。出門在外,都是生人,誰知道誰呀?
共同住了一宿,又一起到餐廳吃了飯,干部的眼神逐漸溫和。我雖不才,多少讀過一些書報(bào),跟他能聊上幾句國際時(shí)事,巴拿馬,蘇伊士,說起來并不磕巴。
更提氣的是,一個英俊的青年軍人還特意過來看我。他是我的小學(xué)同學(xué)羅明,在廣州軍區(qū)空軍政治部電影隊(duì)服役,駐地就在附近的登峰北路。這等于讓我的所謂背景又神秘了幾分。略顯不足的是,他的軍裝上衣只有兩個兜,一看就是戰(zhàn)士;還有,空軍那種深藍(lán)色的軍褲又很容易被民間仿造,但這足以讓我的虛榮心得到滿足了。我故意不說他是小學(xué)同學(xué),只是親熱地聊天,還提到誰誰是誰誰的警衛(wèi)員之類,干部聽得一愣一愣,滿肚子疑問。
郭氏父子的到來,讓干部的好奇指數(shù)升到最高值。
那晚到了賓館門口,我說請回吧郭叔叔。他已經(jīng)很接近謎底了,哪肯輕易放棄,堅(jiān)持著,和東張西望的兒子進(jìn)了大堂,進(jìn)了電梯,經(jīng)過長長的鋪著地毯的走廊,將我一直送進(jìn)房間。
干部正在房中閑坐。不知何故,那幾天他哪兒也不去,總在房間里待著,似乎在等待著什么。見我們進(jìn)來,只一望,就觸電一般,馬上站起來。與其說是禮貌,不如說是被郭叔叔給驚到了,鎮(zhèn)住了。郭叔叔人長得精神,也威風(fēng),看一眼都會心生敬意,哪個還敢端坐一旁,更不敢問一聲,你是哪個單位的?
干部不知道,我當(dāng)時(shí)也不知道,“押”我過來的郭叔叔,竟是一位戲劇名家,擔(dān)任過廣東省戲劇家協(xié)會的領(lǐng)導(dǎo)。這些后期職務(wù)和聲望還在其次,關(guān)鍵他早年曾擔(dān)任過東北大學(xué)劇社社長、學(xué)生自治會主席,他如果將當(dāng)年英氣逼人的舞臺扮相展示出來,不知干部還要作何反應(yīng)。
郭叔叔跟干部簡單聊了幾句,帶著兒子離去,臨行想說點(diǎn)什么,卻什么也沒說。看樣子,他的疑問頂多消失了一半。
我給人的神秘感持續(xù)到第二天。
早飯后,我正跟干部聊天,一個小個子中年男人推門進(jìn)來,衣著氣質(zhì)比我還像基本群眾,我好歹還戴一副眼鏡,那人就裸著雙眼,眼珠子嘰里咕嚕亂轉(zhuǎn)。干部的“門衛(wèi)”意識又被激活,便問他找誰。
他并不應(yīng)答,而是沒事人似的直接進(jìn)了衛(wèi)生間,并且反鎖了門。
過了片刻聽到?jīng)_水聲,這才兩手濕淋淋地出來,撣一撣水,指著我說,找他。
“你認(rèn)識小劉?”干部問。
“怎么不認(rèn)識,他能住到這里,還是我聯(lián)系的。”
話音停住,我尷尬地點(diǎn)頭。
此人說得一點(diǎn)不錯,他的確是我住進(jìn)東方賓館的關(guān)鍵人物。
他姓歐陽,是我廠關(guān)系單位——廣州一家工廠供銷部門的職員。
那個年代旅館奇缺,臨行前我托人找到歐陽師傅,請他幫忙安排住處,他一口答應(yīng),條件是為他弄一頂“雷鋒帽”。
我有點(diǎn)為難,雷鋒犧牲十多年了,他的遺物存放在撫順雷鋒紀(jì)念館,撫順離沈陽倒是不遠(yuǎn),問題是人家能將帽子給你嗎?
打聽半天,總算明白,所謂雷鋒帽,指的是北方一種帶護(hù)耳的筒形棉帽,因其頗像雷鋒端著蘇式?jīng)_鋒槍在松樹下戴的棉軍帽,故名。雷鋒那張照片云彩一般,全國各地都能看見。原照背景是一些枯樹枝,松樹是后P上的。廣州那年奇冷,歐陽師傅便請我為他代購一頂。
原指望有個地方住就行,不料歐陽師傅能耐太大,走后門居然走到東方賓館,估計(jì)我們廠的書記主任也不一定住過這里。
謎底揭開,見過大世面的干部半晌說不出話。
我不用再裝神秘,反倒松了一口氣。
歐陽師傅坐下來,跟我聊業(yè)務(wù)上的事。聊完,脫衣服,上衣、褲子、背心、褲衩,統(tǒng)統(tǒng)放我床上,然后問干部,我用浴缸泡個澡,可不可以呀?
干部忙說,可以可以;又說,穿上拖鞋,小心滑。
歐陽師傅光著屁股,大聲說,中午我請你倆吃飯,賓館內(nèi)部菜,好吃不貴。
干部說,謝謝謝謝,你們兩個吃,我要出去辦事。
不要客氣嘛,歐陽師傅笑道,吃完再辦事啦。進(jìn)了衛(wèi)生間,探出頭:小劉啊,替我把他看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