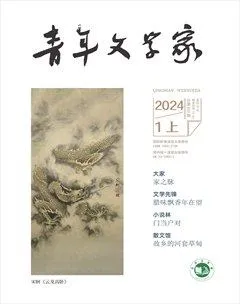香甜的回味
苑小紅

我很想喝一碗咸菜茨菰湯,我想念家鄉(xiāng)的雪。
—汪曾褀《咸菜茨菰湯》
我老家是魯北的一隅小村,只記得小時(shí)候的冬天特別冷,母親給我做的棉褲和棉襖特別厚。如果一夜大雪,早起門被封住,下學(xué)回來,手還是凍成了紅蘿卜,腳與棉褲、蒲靴凍在一起,脫不下來,鼻涕一大把,眼淚也不爭(zhēng)氣地流下來,唯一能安慰我的,就是母親煮好的熱乎乎、香噴噴的八寶粥了。
說是八寶粥,其實(shí)沒有八寶,也就是在玉米面粥里夾雜點(diǎn)自家種的爬豆、紅豆、綠豆之類;有時(shí)紅豆、綠豆也沒有,只有圓滾滾、紅白皮皮的爬豆加幾粒紅棗子。這八寶粥對(duì)我來說就是美味,它擺脫了純玉米面粥的單調(diào)乏味,也沒有玉米面的顆粒感,咀嚼起來軟糯而又筋道,口有余香,還能讓肚子保持長時(shí)間不餓。我是極愛那豆子粥的,記得有一次,母親在粥里放了較多的爬豆、綠豆,綠豆煮開了花,爬豆吸足了水分,胖胖圓圓的特別可愛。我放學(xué)回來,母親盛好冒著熱氣的粥,就忙別的事去了。于是,我用筷子挑出爬豆在嘴里漱一下,積攢在手里,手里盛不下了,就把圓滾滾、濕乎乎的爬豆裝在上衣兜里,這些煮熟的豆豆,成了周末的零食,成了我向小朋友炫耀的美食。
這樣幾次之后,母親發(fā)現(xiàn)了端倪,她發(fā)現(xiàn)我的衣兜經(jīng)常是黏糊糊的。唉,想想我當(dāng)時(shí)是多么可笑:吃東西不講衛(wèi)生,會(huì)生蛔蟲、肚子痛的。母親不苛責(zé)我,只是叮囑我再不要這樣做。我想,小時(shí)候沒有落下疾病,也多虧母親囑咐我洗干凈手再吃東西,我的衣服也總是被母親洗得干干凈凈。童年的八寶粥,以及我可笑的吃法里,藏著母親的愛和寬宥啊!我想,我和汪曾祺先生有的一拼了。他一生熱愛美食,我對(duì)美味的追求與喜愛,從小時(shí)候到現(xiàn)在,也從未停止。
那時(shí),父親遠(yuǎn)在百里外的義和(今屬東營市)上班,每個(gè)周末他都會(huì)騎著大金鹿自行車回家一趟,他的自行車后座和前筐每每載滿寶貝。每個(gè)周末都是我坐立不安、翹首以待的時(shí)候,大門外的高臺(tái)子是我等待父親的寶地。那天天已擦黑,我的脖子望得發(fā)酸,小狗虎子也耷拉了腦袋,父親還沒有回來。我只好回屋,先吃點(diǎn)米飯墊墊肚子,耳朵時(shí)時(shí)聽著窗外的動(dòng)靜。我吃啥也不香,偷偷地把干糧喂給虎子。只聽門外一聲響,父親的“座駕”到了—我放下碗筷,叫一聲虎子,我倆一起飛到了院子里。見到父親車筐車座滿滿當(dāng)當(dāng),我心里樂開了花。父親趕忙解繩子、卸下貨品,我跑前跑后,搭手搬運(yùn)。父親帶回家的,有日常的蔬菜、積攢下的白面,還有香皂等日用品,更有香甜的義和蘋果。
義和的蘋果種類中,當(dāng)屬“國光”“金帥”最有名。這兩種蘋果都耐貯藏,一直能吃到第二年春天。國光個(gè)頭兒小,水分大,放在水缸里,上面蒙一塊塑料布,慢慢吃。那時(shí),我最愛的是“金帥”,大大的個(gè)頭兒,金黃的外皮,面嘟嘟的,酸甜可口。母親給我和姐姐一人先分一個(gè),總是挑一些磕碰的、有疤痕的先吃,那些長得好的、個(gè)頭兒大的,母親總要留起來,放進(jìn)柜子里,說是用來聞味:金帥蘋果久存不壞,并且能長時(shí)間散發(fā)一種果香。我家的衣柜里常年散發(fā)出的果香,是家里最誘人的香味。等到有的蘋果表皮起皺,開始打蔫兒,母親會(huì)挑出一個(gè)給我們兄妹分食。一小塊兒蘋果,散發(fā)著沁人心脾的香甜,它滿足了我兒時(shí)對(duì)于水果的所有幻想。
如果說現(xiàn)在的孩子是生在福窩里,我覺得自己的童年也不盡是苦澀。童年的美味牽動(dòng)著我的味蕾,讓我時(shí)時(shí)沉浸在父母的愛、故鄉(xiāng)的情里,不能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