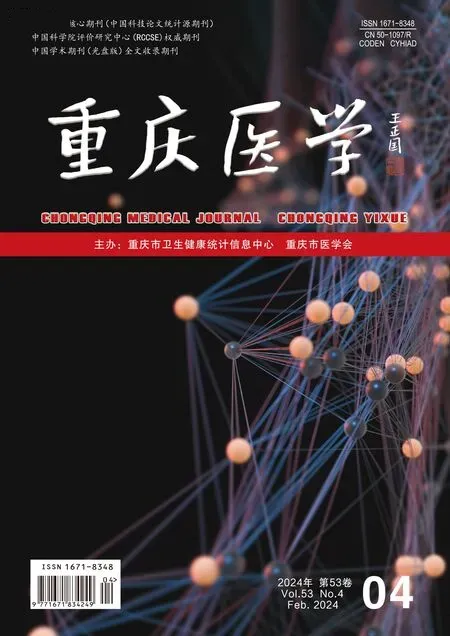神經內鏡下經鼻蝶入路治療鞍內蛛網膜囊腫1例并文獻復習*
趙丹旭,徐學君,章頂立,劉春光,陳科宇,李金輝,曹 毅
(成都市第二人民醫院神經外科,成都 610000)
顱內蛛網膜囊腫是一種先天性囊性病變,成人發病率1.4%~2.3%[1],約為顱內占位性病變的1%[2],發病部位多見于外側裂,也可發生于顱中窩、橋小腦角區、四疊體池、小腦蚓部等部位,其中鞍內蛛網膜囊腫(intrasellar arachnoid cyst,IAC)相對少見,發病率約占顱內蛛網膜囊腫的3%[3-4]。現報道1例神經內鏡下經鼻蝶入路成功治療IAC的病例,結合既往文獻探討IAC形成機制、鑒別診斷、內鏡治療要點等相關問題,以期為臨床診療工作提供參考。
1 病例資料
患者,男,53歲,因“間斷性頭痛2年多”入院,主要表現為彌漫性疼痛,間斷性反復發作,每次持續十幾秒后緩解,偶有眩暈及耳鳴表現,神經系統專科查體未見明顯異常。眼科檢查發現雙眼周邊視野散在缺損。頭部CT平掃(圖1A):鞍區擴大,可見大小約2.7 cm×2.3 cm團片狀低密度影,邊緣似見少許鈣化,考慮顱咽管瘤?垂體MRI平掃+增強:鞍區擴大,可見大小約3.5 cm×2.8 cm×2.3 cm啞鈴狀鞍內、鞍外囊性病變,視交叉受壓上移,垂體及垂體柄受壓后移,T1低信號,T2高信號,呈現為腦脊液信號,邊界清楚,信號較均勻,內見點狀T2低信號灶,T1WI增強后可見囊壁局部微弱強化,垂體、垂體柄受壓后移,部分壁略厚,其內囊性信號影未見明顯強化(圖1B~D),考慮IAC。術前激素水平評估除促甲狀腺激素(TSH)7.409 μIU/mL(0.55~4.78 μIU/mL)升高外,其余激素包括促腎上腺皮質激素(ACTH)、皮質醇(CORT)、泌乳素(PRL)、睪酮(TES)、生長激素(GH)、三碘甲狀腺原氨酸(T3)、甲狀腺素(T4)、游離三碘甲狀腺原氨酸(FT3)、游離甲狀腺素(FT4)水平均在正常范圍內。初步診斷為鞍區占位性病變、蛛網膜囊腫。

A:頭部CT顯示鞍區擴大;B:術前頭部矢狀位MRI T2WI顯示囊性病變呈啞鈴型位于鞍上及鞍內;C、D:術前冠狀位、矢狀位增強MRI T1WI分別顯示局部囊壁微弱強化(箭頭),垂體及垂體柄(箭頭)受壓后移;E:磨除鞍底暴露硬腦膜;F:內鏡探查囊腔見囊頂部有一層菲薄的蛛網膜(箭頭);G:脂肪及闊筋膜填塞囊腔;H:人工硬腦膜置于缺損骨窗內表面;I:鼻中隔黏膜瓣修補顱底缺損;J:術后2 d冠狀位MRI T1WI顯示囊腫消失,囊腔內筋膜填充物顯影(箭頭);K:囊壁病理(蘇木素-伊紅染色,100×);L:術后3個月矢狀位增強MRI T1WI顯示囊腫消失,黏膜瓣(箭頭)生長良好。
神經內鏡下經鼻蝶入路,磨除蝶竇前壁后見鞍底下沉并伴有鞍底骨質缺損,剪開鞍底硬腦膜見透明狀囊腫突入術野,術中證實為IAC。切除囊腫下壁送活檢,見清亮腦脊液流出,隨后內鏡進入囊腔內,見囊腫腔上方鞍膈缺損,僅有一層菲薄的蛛網膜覆蓋,伴有明顯搏動,且有低流量腦脊液隨搏動的蛛網膜裂孔滲出。囊腔下后方可見受壓的垂體柄及垂體組織,保留上述結構完整,此時蛛網膜囊腫內張力明顯下降。取腿部脂肪組織及闊筋膜,分層貼附于菲薄的囊腫上壁及填充囊腔,隨后將人工硬腦膜嵌入缺損骨窗的內表面,最后將帶血管蒂的鼻中隔黏膜瓣完全覆蓋于鞍底顱骨缺損部位,完成鞍底重建,以碘仿紗條支撐黏膜瓣以促進其生長并與周圍組織融合(圖1E~I)。術后患者頭痛癥狀緩解,眼科復查雙眼視野未見明顯異常。術后第2天復查垂體提示囊腫基本消失,視交叉受壓解除(圖1J);激素水平恢復正常;囊壁病理結果為蛛網膜囊腫(圖1K)。患者術后10 d出院。術后3個月,患者復診頭痛癥狀消失,無腦脊液鼻漏;垂體MRI增強掃描顯示:IAC消失,黏膜瓣生長良好(圖1L)。
2 討 論
2.1 IAC的發生機制
近年來有研究發現垂體柄和鞍膈的解剖關系及其發育結構特征是IAC形成的關鍵因素,BUSCH[5]通過788例尸檢發現鞍膈孔直徑變化很大,其中42%的尸體鞍膈孔開口狹窄,緊密包繞垂體柄,37.5%的尸體孔徑大于垂體柄,20.5%鞍膈縮小至硬腦膜邊緣或不存在。BERGLAND等[6]通過225例尸檢發現,39%的尸體垂體柄開口直徑大于5 mm,23%的垂體比蝶鞍深度至少短2 mm,使得鞍上蛛網膜下腔可以延伸到蝶鞍內。關于鞍區蛛網膜囊腫的起源及發生機制存在如下假說:(1)鞍內、外蛛網膜下腔交通關閉假說。BENEDETTI等[7]認為IAC與原發性空蝶鞍綜合征的形成機制相似,因鞍隔膜附著位置較低、鞍膈孔先天擴大或者缺損,鞍上池蛛網膜直接延伸至蝶鞍內,當鞍內蛛網膜上壁動態重構或正常結構移位,或發生腦膜炎、出血或炎癥事件后,鞍內、外蛛網膜下腔溝通關閉形成閉合性IAC[2,8-9]。在此基礎上,蛛網膜囊腫壁細胞有主動分泌產生囊液的功能[8],故可出現IAC進行性增大。(2)鞍上腦脊液脈沖式搏動壓及垂體、垂體柄的球閥機制假說。DUBUISSON等[10]認為鞍隔膜先天開口大于垂體柄時,在鞍上腦脊液脈沖式搏動壓持續作用下,鞍上蛛網膜通過鞍膈與垂體柄之間擴大的間隙疝入鞍內形成蛛網膜憩室,由于通道狹窄,腦脊液進入憩室后,憩室內壓力波動很小甚至幾乎沒有,與鞍上蛛網膜下腔腦脊液搏動形成壓力差,伴隨著腦脊液的壓力搏動,垂體及垂體柄充當閥門作用,部分或完全堵塞鞍膈缺損,致使腦脊液持續被截留在蝶鞍的憩室內,引起IAC逐漸增大,當鞍內壓增高達到顱內壓水平時,鞍內、外蛛網膜下腔交通關閉,最終造成IAC的發生。(3)鞍區蛛網膜移位、變形、分泌假說。長期以來多數研究認為鞍膈下沒有蛛網膜組織,但CAMPERO等[11]和QI等[12]研究發現覆蓋鞍膈的鞍上蛛網膜不僅可沿著垂體柄向上延伸,而且還可延伸至鞍膈以下。HARTER等[13]提出,IAC的形成可能源于發育過程中蛛網膜的異常分裂或折卷異常,蛛網膜內囊腫形成,囊腫壁細胞的內分泌作用促使囊腫體積增大,在鞍內形成囊性占位效應。(4)其他假說。ANDRYSIAK-MAMOS等[14]提出垂體所占的鞍內間隙隨著年齡的增長而減少。病理狀態下,如顱內高壓或垂體萎縮會增加蛛網膜下腔進入蝶鞍的概率[2,8,10],所以不論是鞍隔膜與垂體柄之間擴大的間隙,還是各種原因所致垂體大小與蝶鞍不適配,均可出現鞍上蛛網膜下腔疝至蝶鞍內,并因球閥機制使得IAC形成及逐漸進展。本文報道的病例術中利用神經內鏡抵近觀察的優勢,證實了鞍膈孔先天性擴大或缺失是IAC發生的重要機制。
總之,鞍內、外蛛網膜下腔交通關閉假說,鞍上腦脊液脈沖式搏動壓及垂體、垂體柄的球閥機制,囊腫腔與蛛網膜下腔之間因蛋白含量差異而產生的滲透梯度[10],囊腫壁細胞主動分泌產生囊液等多種機制共同導致了IAC的形成與進展。
2.2 IAC的鑒別診斷與影像學特征
鞍內囊性病變主要包括IAC、囊性顱咽管瘤、Rathke’s囊腫、囊性垂體腺瘤和空蝶鞍,其臨床表現及影像學特征存在一定相似性,鑒別診斷有一定困難[1]。除具有共同的臨床表現如頭痛及視力障礙等,IAC垂體功能較少出現障礙,偶爾可表現為性欲減退、陽痿、月經周期紊亂等[14]。囊腫在CT上表現為低密度,臨近骨質結構可出現局部受壓表現。常因囊內無菌性炎癥、腦脊液變性或蛋白質含量的不同而MRI呈現出與正常腦脊液細微信號差異。T1WI囊液呈低信號或略高于腦脊液信號,T2WI呈現與腦脊液相似的高信號,增強后囊液及囊壁無強化;液體衰減反轉恢復(FLAIR)序列呈低信號[4,14]。蛛網膜囊腫的確診需綜合臨床癥狀、體征、內分泌、影像及病理檢查等進行判斷。
2.3 IAC的內鏡治療要點
關于癥狀性鞍區蛛網膜囊腫的術式經過多年不斷發展革新,先后涉及經額顳入路開顱[7]、顯微鏡[15]或內鏡下[16]經鼻蝶入路、經腦室內鏡下鞍上/鞍內囊腫開窗[8,17]等入路,目前神經內鏡下經鼻蝶入路已成為主流治療方式[3,18]。結合該病例的手術治療,作者認為神經內鏡下術野更為清晰、明亮,抵近觀察的優勢在于多角度充分探查蛛網膜囊腫腔內部結構,并進一步證實鞍膈缺損是蛛網膜囊腫形成的解剖基礎,并精準指導鞍底重建修補,減少術后持續腦脊液鼻漏。
關于術中囊壁切除范圍、囊腔與鞍上池之間是否應建立溝通、囊腔內填充物選擇尚未達成共識。有學者提出應完全切除囊壁以減少囊腫的復發[15];另有學者認為囊壁的完全剝離可能會引起垂體功能障礙,故建議切除部分囊壁用于病理活檢,同時將囊上壁開窗,溝通囊腔與鞍上池,使囊液重新回歸正常腦脊液循環,減少囊腫復發;還有學者雖認同部分切除囊壁用于活檢的理念,但不支持切除囊上壁建立與鞍上池的溝通。近年來,隨著IAC切除病例報道的增多,大部分學者均支持囊腔內應充分填充內容物,如脂肪、肌肉、筋膜等,甚至術中發現囊壁與鞍上池之間有缺損時,可將填充物部分穿過缺損,這樣不僅可阻止蛛網膜的下墜和鞍內腦脊液的再次充盈,降低術后腦脊液漏發生風險,而且還可減少對垂體及鞍膈的損傷,待后續鞍膈與鞍旁蛛網膜粘連閉合形成自然分隔后,可達到鞍膈解剖學結構重建的目的[19-20]。作者的治療經驗為切除部分囊壁用于病理組織活檢,內鏡下仔細檢查是否存在囊腔與鞍上池溝通的證據,必要時以脂肪或筋膜等填充物封堵腦脊液滲漏孔,完全阻斷囊腔與鞍上池之間的溝通,后可行脂肪、肌肉或筋膜、人工硬腦膜等材料填充囊腔起支撐作用,最終達到預防囊腫復發的目的。
顱底重建是經鼻蝶入路切除IAC后重要的手術步驟,其重建質量影響術后并發癥發生及預后。HADAD等[21]首次報道帶血管蒂鼻中隔黏膜瓣顱底重建技術,該方式解決了腦脊液漏的難題,但術后顱底遺留永久性骨質缺損。在此基礎上,LENG等[22]提出“墊圈密封”技術,即使用自體筋膜及剛性移植物封閉顱骨缺損來完成顱底重建,解決了顱底缺損難題,但對于不規則的顱底缺損不能形成可靠封閉。除此以外,JIN等[23]提出“原位骨瓣技術”,即術中用高速磨鉆在顱底雕刻出“電話卡”大小骨瓣,用于原位修復骨缺損,同時聯合“帶血管蒂鼻中隔黏膜瓣”共同完成顱底重建,該方法既解決了腦脊液漏問題,又彌補了顱底不規則的缺陷,使得顱底骨缺損達到解剖學愈合,重建結構更加穩定。近年來,部分學者逐漸開始嘗試內鏡下硬腦膜縫合技術應用于顱底修補[3,9,24],該方法不僅能完全閉合硬腦膜漏口,而且能夠提供一定張力來阻擋顱內腦脊液沖擊,但是該方式對手術器械及術者操作技術要求較高,耗時較長。筆者的經驗是,術前需通過鞍區磁共振評估囊腔與鞍上池是否溝通,若存在明確溝通或者術中發現高流量腦脊液漏,除封堵漏口外,需采用墊圈密封技術或原位骨瓣技術達到解剖學封閉,同時聯合帶血管蒂鼻中隔黏膜瓣共同完成顱底重建,將腦脊液漏及術后顱內感染風險降到最低;若未發現明確溝通,且術中內鏡探查未見腦脊液滲漏及滲漏孔或僅有微量腦脊液滲漏時,腔內填塞后可直接行帶血管蒂鼻中隔黏膜瓣完成顱底重建。
綜上所述,IAC發病率低,發病機制尚不明確,目前神經內鏡下經鼻蝶入路是一種較理想的手術治療策略,既可提供清晰的手術視野實現直視下囊腫壁切除及減壓,從而緩解鞍區周圍重要神經結構的壓迫占位效應,還可在直視下實現多重顱底重建,以減少術后高流量腦脊液漏及顱內感染發生概率。因此,該手術方式值得進一步推廣及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