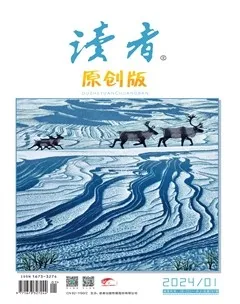人生滋味
錢紅莉
最近,我喜歡在菜市場閑逛。將一日量的菜買好,再去肉攤前駐足。俗語云:“小雪腌菜,大雪腌肉。”大雪過后,這座城市的人們三五成群集結于肉案前,大肆采買豬前胛裝香腸。攤主遵囑,撕一角小紙條,飛速劃拉幾筆“甜”“咸”抑或“麻辣”字樣,啪一聲貼在肉上,裝袋。按照前后順序,一份一份有條不紊地排列著。他將半只黑毛豬拖上案板,庖丁解牛般剔除肋排、筒骨、扇骨等,剩下軟塌塌的一堆肉冒著熱氣,這堆肉火速被分割成一塊一塊,一會兒便被主顧們認領完畢。我無比熱愛這喧鬧的氛圍,連同肉案師傅身上那條黑皮圍裙上亮晶晶的油光也是可親可珍的。
平素,我是連行路都著急忙慌的人,可是,一到深冬,一顆焦躁的心頓覺寧靜,以局外人的閑情徜徉菜市,咸咸淡淡補足人間煙火。
鄰居唯一的寶貝女兒定居深圳,早年間老兩口一并跟去看護外孫。年年寒冬,鄰居總要回來一趟。何故?不過是為了裝幾十斤香腸帶過去,說是那邊的香腸不合胃口。他們千里迢迢回來,就是為了故鄉一味。
每年冬天,為了吃上幾缽腌篤鮮,我必須腌點兒咸肉。往年怕麻煩,一律讓賣肉的老板娘協助抹點兒食鹽,拎回家,密封于不銹鋼盆里,放北邊臥室空調外機上靜置一周,晾曬。今年,決定改良一番。將花椒與鹽一起焙香后,一點點抹在肉上。另腌了幾根肋排,最近它們正被吊在竹竿上接受陽光與夜霜的洗禮。去露臺賞美景時,總要情不自禁將鼻子湊近聞聞,是復調的香氣啊—花椒的麻香裹挾著肉的咸香,豐腴、醇厚,確乎治愈人。寒風再哨幾日,便可享用了。咸排不僅與冬筍是一對好搭檔,亦可與白蘿卜同煨。世間總是白蘿卜常有,而冬筍不常有。將咸排剁成小塊,用溫水清洗后,入油鍋煸香,移入砂罐,滾水沒過,頂沸,霎時湯白如乳,再將白蘿卜切成大塊丟進去,改小火“咕嚕”數小時,關火揭蓋,蘿卜吸飽排骨的肉香氣,入嘴沁香馥郁,稍微抿一抿,即刻化作一汪汁水。末了,再啃排骨—得益于鹽與陽光的成全,這種咸香滋味直鉆肺腑肝腸。是的,確乎要啃,直接用手捏一塊,橫在嘴邊啃食,方顯身心舒暢。咸排骨的滋味較之鮮排骨,不知要高幾個檔次,二者之間注定隔著一條冬天的河流。倘吃得豪橫點兒,不與任何菜式搭配,直接隔水清蒸,美味會更上一層吧。
年歲漸長,我愈發熱愛手工。2023年又增了另一項技能:背靠暖氣片,先后切出10余斤蘿卜,將之晾成細如毛線的蘿卜絲兒。最享受的是切絲的過程,內心開闊又安寧,直至切得胳膊抬不起來,方才罷休。一日,牛肉打折,忍不住買回些許,切成大小適勻的塊狀,以鹽腌法炮制,食鹽、花椒雙雙加持,放入冰箱靜靜發酵3日,掛出晾曬。一塊塊肥厚、新鮮的牛肉在冷風中悠悠蕩蕩五六日,縮小至黝黑的一丟丟。縱以溫水浸泡過,下刀卻也生澀。熱鍋冷油,以小米辣熗鍋,與青蒜爆炒,入嘴,香確實香,但嚼牛肉嚼得腮幫子都酸了。牛肉較之豬肉,纖維密實,不能像后者那么狠曬。
一個寒風瑟瑟的早晨,早市魚攤前,忽現幾十條一米長的青魚,集體游弋于闊口深桶中,一群食客迅速圍攏來,嘰嘰喳喳不停。我抄起網兜撈起一條,起碼10余斤—用來腌制魚干,該有多美味啊。曬干后斬成一塊塊,放入陶制的壇子,底層擱半盞花雕,整個壇口以荷葉密封,待來年二三月時享用。揭開壇子,魚肉深紅,酒香撲鼻。
最近,我又打算腌一件物什。它太漂亮了,每次在超市遇見,都會多看幾眼,確乎是蕭瑟寒冬里一團團玫紅色火焰,比霜后的銀杏葉還要絢爛多姿。后者,我一出門總要撿拾幾枚,倘回到可以寫信的年月,想必會隨信附贈幾枚吧。惜乎,日子是往前過的,舊時光已不在。但我何以不能腌點兒蘿卜呢?不貪多,七八根足矣,切成食指般長短粗細,用縫衣針一條條串起,掛在露臺外一點點陰干,每每黃昏歸家,抬頭必見那一串串紅紅的火焰,想必暖意融融。將八角、花椒、香葉炒熟,碾成粉末,與蘿卜干同腌,放在糖水玻璃瓶中杵緊,密封月余。熱鍋冷油,扔幾瓣老蒜煸香,一撮蘿卜干下鍋熗炒,激點兒涼水,酸脆縱橫,香氣彌漫。早餐一碗小米粥佐以蘿卜干,咀嚼有聲。
說來說去,不過就為了一個平凡的胃。一碗粥、一碟咸菜,最得人生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