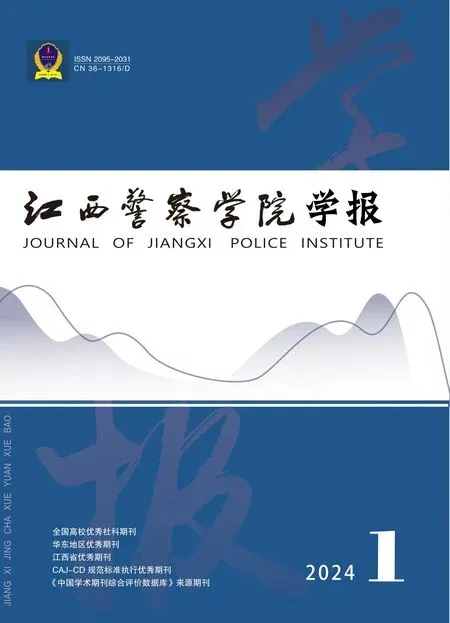襲警罪的處罰邊界研究
韓 雪
(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北京 100062)
一、問題的提出
2020 年12 月26 日由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十一)》(以下簡稱《刑法修正案(十一)》)將“暴力襲擊正在依法執(zhí)行職務(wù)的人民警察的” 行為從妨害公務(wù)罪中分離出來獨立成罪,并針對使用槍支、管制刀具或者駕駛機動車撞擊等手段暴力襲警行為配置了處罰更為嚴厲的刑罰。這是立法機關(guān)繼2015 年通過《刑法修正案(九)》增設(shè)暴力襲警從重處罰的規(guī)定后,對襲警犯罪立法作出的又一次重大修訂。在新冠疫情持續(xù)爆發(fā)期間,襲警罪的增設(shè)為威懾、打擊暴力襲警行為、維護警察執(zhí)法權(quán)威提供了堅強保障,也成為特殊時期適用最為頻繁的罪名之一。最高人民檢察院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顯示,2021年1 月至9 月,全國檢察機關(guān)起訴襲警犯罪共計4178 人,占《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17 個罪名適用總量的75.04%。[1]與高頻適用的司法實際不相適應,當前,理論界與實務(wù)界并未就襲警罪的認定標準達成一致意見,導致該類犯罪在不同地區(qū)出現(xiàn)了罪與非罪邊界模糊、此罪與彼罪認定標準不統(tǒng)一的問題。
司法機關(guān)在認定一暴力襲擊人民警察的行為是否構(gòu)成襲警罪時,爭議的焦點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第一,對于《刑法修正案(十一)》施行后辦理的暴力襲警案件,是否均應按照襲警罪進行處理,是否存在妨害公務(wù)罪的適用空間?第二,襲警罪的成立是否僅需行為人實施符合法定要件的暴力襲警行為,抑或還應同時具備形成法益侵犯的危險狀態(tài)或者造成人身傷亡的實害后果?第三,當暴力襲警行為造成人民警察死傷的嚴重后果時,適用襲警罪是否罰當其罪,有無升格適用故意傷害罪或者故意殺人罪的必要?下文即圍繞上述問題展開論述。
二、襲警罪的適用范圍
(一)實務(wù)爭議
以2021 年3 月1 日《刑法修正案(十一)》的施行作為分界,對于在此之后實施的暴力襲警行為,公安機關(guān)通常以襲警罪立案偵查并移送檢察機關(guān)審查起訴,妨害公務(wù)罪幾近喪失了其在立案偵查階段的存在空間。個別地方公安機關(guān)不區(qū)分襲警罪與妨害公務(wù)罪,對同一行為適用二罪進行立案、移送①江蘇省昆山市人民檢察院不起訴決定書,昆檢刑不訴〔2021〕235 號;江蘇省昆山市人民檢察院不起訴決定書,昆檢刑不訴〔2021〕278 號;等等。。與之相比,各地檢察機關(guān)對于襲警罪的適用要求則更為嚴格,部分以襲警罪立案偵查的案件最終被修改為妨害公務(wù)罪提起公訴或作出不起訴決定②貴州省六盤水市六枝特區(qū)人民檢察院不起訴決定書,六檢刑不訴〔2022〕11 號;河北省遵化市人民檢察院不起訴決定書,遵檢刑不訴〔2021〕46 號;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實踐中也出現(xiàn)了將實施于《刑法修正案(十一)》施行以前的暴力襲警行為認定為襲警罪的現(xiàn)象③浙江省金華市婺城區(qū)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2021)浙0702 刑初201 號;甘肅省康樂縣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2021)甘2922 刑初38 號;漢中市漢臺區(qū)人民檢察院不起訴決定書,漢臺檢刑不訴〔2021〕33 號;等等。。例如,在“王某某、蔡某某襲警案”中,襲警行為發(fā)生于2020 年10 月9日晚,審理法院以本案審理期間《刑法》第227 條第五款進行立法調(diào)整為由,將被告人的涉案罪名由妨害公務(wù)罪修正為襲警罪④吉林省臨江市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2021)吉0681 刑初2 號。。
(二)理論解析
《刑法修正案(十一)》施行后,應將暴力襲警行為認定為襲警罪抑或妨害公務(wù)罪,一方面取決于襲警罪與妨害公務(wù)罪的關(guān)系,另一方面則與新法的溯及力密切相關(guān)。前者決定了襲警罪適用范圍的廣度,即該罪用以懲治哪些行為方式;后者則解決了襲警罪適用的時限問題,即該罪對哪一時間段發(fā)生的行為具有法律效力。
1.襲警罪與妨害公務(wù)罪的關(guān)系
目前,學界的主流觀點主張,《刑法修正案(十一)》第277 條第五款規(guī)定的襲警罪與第一款規(guī)定的妨害公務(wù)罪屬于法條競合的關(guān)系,前者系特殊法條,后者屬于一般法條。[2]也有論者認為,二者不成立法條競合,襲警罪獨立以后,警察已從妨害公務(wù)罪的犯罪對象中分離出來,暴力襲擊正在依法執(zhí)行職務(wù)的警察的行為,僅可能涉嫌襲警罪,而不存在需要以妨害公務(wù)罪兜底的情形;同時,暴力阻礙其他國家機關(guān)工作人員依法執(zhí)行職務(wù)時,也不存在適用襲警罪加以定罪的可能。[3]
筆者贊同多數(shù)學者的觀點,即襲警罪與妨害公務(wù)罪存在特別法與一般法的法條競合關(guān)系。法條競合又稱法規(guī)競合,是指“一個犯罪行為,因法律錯雜規(guī)定,致有數(shù)法規(guī)(或法條)同時可以適用,但只在數(shù)法條中適用一法條,而排斥其他,成立單純一罪的情況。”[4]“我國刑法理論一般認為,法條之間存在包容或交叉關(guān)系時便是法條競合。”[5]無論以歷史解釋還是文理解釋加以展開,襲警罪與妨害公務(wù)罪均存在法條競合所應具備的包容關(guān)系。一方面,襲警罪脫胎于妨害公務(wù)罪,從完全被妨害公務(wù)罪涵蓋到作為妨害公務(wù)罪的從重處罰情節(jié),再到獨立成罪,皆與妨害公務(wù)罪保持著密不可分的聯(lián)系。《刑法修正案(十一)》將人民警察從國家機關(guān)工作人員中獨立出來單獨設(shè)罪,主要基于該群體執(zhí)行職務(wù)時間線長、接觸面廣、危險性高、最易受到暴力侵襲的屬性,意在強調(diào)刑法立法對警察執(zhí)法權(quán)威的保護,而非給予警察群體以特殊優(yōu)待。從此種意義上看,襲警罪并未完全脫離開妨害公務(wù)罪,而應被視為妨害公務(wù)罪的一種特殊形態(tài),表征立法對妨害警察執(zhí)行公務(wù)犯罪的關(guān)注與強調(diào)。另一方面,以法律文本觀之,獨立成罪的襲警罪依然設(shè)置于《刑法修正案(十一)》第277 條第五款,與妨害公務(wù)罪處于同一條文中,而沒有采取第277 條之一的形式,條文位置決定了本罪與妨害公務(wù)罪的聯(lián)系最為緊密,侵犯的法益高度同源。此外,襲警罪的罪狀表述也與作為妨害公務(wù)罪加重處罰條款時的內(nèi)容高度重合。由此亦不難看出,襲警罪與妨害公務(wù)罪的關(guān)系并未因其獨立成罪而發(fā)生實質(zhì)性的改變,襲警罪的條文依然是妨害公務(wù)罪的特別條款,而妨害公務(wù)罪則是用以規(guī)制妨害包含人民警察在內(nèi)的全部國家機關(guān)工作人員依法執(zhí)行公務(wù)行為的一般性罪名。
至于反對論者所提出的二罪不存在適用中包容關(guān)系的觀點,筆者并不認同。襲警罪的行為方式僅限于“暴力襲擊”的情形,適用范圍較為狹窄,既未涵蓋針對“正在依法執(zhí)行職務(wù)的人民警察”實施侵害但程度未達“暴力襲擊”標準的情形,又不包括威脅人民警察的行為,亦未將通過暴力破壞執(zhí)法裝備或者警用設(shè)備設(shè)施等手段來妨害人民警察執(zhí)行職務(wù)的行為包含其中。這就意味著,針對情形眾多、方式繁雜的襲警行為,襲警罪主要用以打擊情節(jié)嚴重的暴力襲擊行為,當襲警罪無法適用但卻具有妨害人民警察執(zhí)行職務(wù)的危險時,妨害公務(wù)罪便能發(fā)揮其一般條款的適用功能,彌合因襲警罪適用范圍的局限而造成的法律縫隙。上述反對論者的觀點割裂了二罪之間的緊密聯(lián)系,難以自圓其說。
綜上所述,獨立成罪的襲警罪指向暴力襲警行為,是我國刑法中用以規(guī)制暴力襲警犯罪的主要依據(jù),其是妨害公務(wù)罪的特殊形態(tài),犯罪成立以構(gòu)成妨害公務(wù)罪為前提;妨害公務(wù)罪是用以懲治妨害國家機關(guān)工作人員依法執(zhí)行職務(wù)的一般性罪名,對襲警罪起到重要的保障作用,對于實施襲警行為但尚未達到暴力襲擊程度或者采用威脅方法等妨害人民警察依法執(zhí)行職務(wù)的行為,符合妨害公務(wù)罪構(gòu)成要件的,可以以妨害公務(wù)罪論處。
2.襲警罪適用的溯及力
關(guān)于刑法的溯及力,我國采取了從舊兼從輕原則。對于行為發(fā)生與案件辦理時間存在跨越新舊法情形的,原則上應適用行為時的舊法,但新法不認為是犯罪或者處罰較輕時,適用新法。與《刑法修正案(九)》的規(guī)定相比,《刑法修正案(十一)》除了將襲警犯罪獨立設(shè)罪外,還對該罪的法定刑配置作了如下調(diào)整:一方面,將襲警犯罪基本犯的法定最低刑提高至管制,刪除可以適用罰金刑的規(guī)定,適度加大對暴力襲警行為的處罰力度;另一方面,增加一檔量刑幅度,強化對使用槍支、管制刀具或者以駕駛機動車撞擊等嚴重暴力手段襲警行為的震懾打擊。由此不難看出,本次修正在襲警犯罪原有罪狀的基礎(chǔ)上,進一步提高了該類犯罪的法定最低刑與最高刑。與妨害公務(wù)罪相比,獨立成罪的襲警罪屬于新罪、重罪。按照從舊兼從輕的追訴原則要求,對于行為發(fā)生于《刑法修正案(十一)》施行以前的襲警犯罪,應當按照妨害公務(wù)罪進行處理;行為發(fā)生于此后的襲警犯罪則可直接適用襲警罪。司法實踐中違反襲警罪溯及原則的做法應予糾正。
“近鄉(xiāng)情怯”就出自這首詩。說來唐朝對下放干部的管理有些松懈,挺大一個活人,說溜號就溜號了,但這一溜卻溜出一首好詩來。只不過,文章繁絮,精煉成詩,五言四句,其背后難言的因素多被隱去,更多表現(xiàn)的是一個長期客居異鄉(xiāng)、久無家中音信的人,在行近家鄉(xiāng)時所產(chǎn)生的一種特殊心理情感。而這又有極大的典型性和普遍性,終引起共鳴。
三、襲警罪的既遂標準
(一)實務(wù)爭議
實踐中,審判機關(guān)通常將認定一行為構(gòu)成襲警罪的理由描述為,行為人“暴力襲擊正在依法執(zhí)行職務(wù)的人民警察”,而未予詳述襲警罪成立既遂的裁量標準。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于2020 年1 月10 日聯(lián)合發(fā)布實施的《關(guān)于依法懲治襲警違法犯罪行為的指導意見》 明確提出,“不能僅以造成民警身體傷害作為構(gòu)成犯罪的標準,要綜合考慮襲警行為的手段、方式以及對執(zhí)行職務(wù)的影響程度等因素,準確認定犯罪性質(zhì),從嚴追究刑事責任。”依照該文件精神,實踐中,司法機關(guān)普遍并未將行為造成人民警察人身傷害的實害結(jié)果作為裁決襲警罪成立的標準,一些裁判文書明確提及被害人的傷情,另外一些則并未表明被害人是否受傷及其損傷程度。值得注意的是,在個別案件的判決中,隱藏著以被害人的身體傷害程度作為判定本罪成立與否的裁量規(guī)則。例如,在“肖某忠、蔡某琴、肖某丹襲警案”中,三人共同阻礙民警執(zhí)行職務(wù),肖某忠撕扯民警衣服,致一名民警輕微傷;蔡某琴抓咬一名民警,致輕微傷;肖某丹抓打民警,造成的損傷尚不構(gòu)成輕微傷。最終,法院判決,肖某忠、蔡亞琴的行為構(gòu)成襲警罪,而蔡某琴的行為則構(gòu)成妨害公務(wù)罪①貴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縣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2021)黔0627 刑初204 號。。本案還反映出當?shù)厮痉C關(guān)依據(jù)被害人身體損傷程度界分襲警罪與妨害公務(wù)罪的裁量特點。
(二)理論解析
1.襲警罪的保護法益
在論及襲警罪的既遂標準之前,首先應予明晰的是,該罪保護的法益包含哪些要素。“刑法的任務(wù)在于保護法益。”[6]法益保護的內(nèi)容對于匡正刑事立法、調(diào)節(jié)刑事司法具有指導作用。關(guān)于襲警罪保護的法益,學界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本罪保護的是單一法益,即人民警察的執(zhí)法權(quán);[7]另一種觀點則主張,本罪保護的是復合法益,除人民警察的執(zhí)法權(quán)外,還應包括人民警察的人身權(quán)。[8]筆者贊同上述復合法益說的觀點。理由在于:
首先,由條文所處的位置決定,襲警罪保護的法益為國家機關(guān)工作人員執(zhí)行職務(wù)的正常秩序,但這并不當然地排斥本罪同樣也包含保護人民警察人身權(quán)的法益內(nèi)容。立法機關(guān)之所以將襲警犯罪的行為方式限定于“暴力襲擊”的范圍內(nèi),意在規(guī)制此種對人民警察的人身安全形成嚴重威脅,并通過作用于人身來實現(xiàn)妨害人民警察執(zhí)行職務(wù)目的的行為。換而言之,“行為人對公共秩序法益的侵犯,是通過侵害警察的人身安全進而妨害公務(wù)來實現(xiàn)的。”[9]24
其次,將襲警罪的保護法益界定為復合法益,方能與其刑罰配置相適應。立法機關(guān)之所以為襲警罪設(shè)置了比妨害公務(wù)罪更重的法定刑,其原因在于“暴力襲警行為增加了‘惡報’的量”。[10]也即暴力襲擊行為比其他暴力、威脅行為的不法程度更深、社會危害性更大,不僅更易形成阻礙人民警察執(zhí)行職務(wù)的現(xiàn)實狀態(tài),還直接對人民警察的生命健康造成嚴重威脅并易引發(fā)實害性結(jié)果。由此,不難看出,正是因為襲警罪侵害的是復合法益,才使得“其危害高于單一法益侵害的妨害公務(wù)罪,這也讓襲警罪具有高度可罰性。”[11]
最后,將人民警察的人身權(quán)同時納入襲警罪保護法益的范疇,便于更加直觀地判斷犯罪成立與否,有利于司法認定和刑事打擊。[12]進一步而言,以人身權(quán)益是否遭受侵害作為襲警罪成立與否的判斷標準之一,意味著如果實施暴力襲擊行為尚未達到造成被襲人人身傷害的危險程度時,將不再納入刑法規(guī)制范圍。由此,一方面限縮了襲警罪的打擊范圍,避免因新罪增設(shè)而造成刑法打擊范圍過廣、無限壓縮公民自由空間的問題;另一方面,對于僅擾亂人民警察執(zhí)行職務(wù)的正常秩序卻并未對其人身權(quán)產(chǎn)生危害的行為,可以按照妨害公務(wù)罪進行定罪處罰,實現(xiàn)了二罪的合理界分。
2.襲警罪的既遂標準
關(guān)于襲警罪的既遂標準,在我國刑法學界存在行為犯說與危險犯說兩種不同的觀點。行為犯與危險犯是刑法學者依照刑法分則對犯罪構(gòu)成要件的不同規(guī)定,對犯罪既遂形態(tài)劃分的類型。行為犯指以法定犯罪行為的完成作為既遂標志的犯罪;而危險犯則是指以行為人實施的危害行為造成法律規(guī)定的發(fā)生某種危害結(jié)果的危險狀態(tài)作為既遂標志的犯罪。[14]根據(jù)危險程度和針對法益大小的不同,又可以將其中的危險犯劃分為抽象危險犯和具體危險犯。抽象危險犯中的危險狀態(tài)是一般的、抽象的、不確定的危險,只要行為人實施的行為具有危險性,便認為產(chǎn)生了危害刑法所保護的法益的危險狀態(tài);而具體危險犯中的危險則是具體客觀的、實在的、物理的,通常以“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為標志,法官必須就個案進行具體判斷,方可認定危險狀態(tài)是否已經(jīng)出現(xiàn)。[15]具體到襲警罪中,持行為犯說的學者認為,“立法既不要求情節(jié)嚴重,也不要求造成嚴重后果。從形式看,只要實施暴力襲擊警察的行為就會被認定構(gòu)成襲警罪。”[9]26持危險犯說的學者則主張,本罪的成立以行為造成特定危險狀態(tài)為必要。其中,又有抽象危險犯說與具體危險犯說的分歧。前者主張,“關(guān)于本罪的成立,重點是要通過行為人的行為手段、方式、情節(jié)等要素來考察行為的不法程度,而不是實際造成的損害結(jié)果。”[13]83后者則認為,“只有暴力襲警具有使執(zhí)法行為難以順利進行的現(xiàn)實可能性時,才能認為其侵害了本罪的法益。”[16]上述有關(guān)襲警罪既遂標準的論斷,也與論者所主張的本罪侵犯的法益直接相關(guān)。
筆者認為,具體危險犯說不僅契合襲警罪的立法精神,更符合司法實踐的現(xiàn)實需要。首先,本罪加重情節(jié)的罪狀表述為“嚴重危及其人身安全的”,即已表明該情節(jié)采用了具體危險犯的立法模式,在判斷犯罪成立與否時,既不以發(fā)生妨害人民警察依法執(zhí)行職務(wù)及其人身安全受到傷害的現(xiàn)實結(jié)果為必要,又不應將法定行為的完成作為既遂標志,而需要考察是否產(chǎn)生了具體、現(xiàn)實的危險。其次,與加重犯的立法模式相協(xié)調(diào),本罪基本犯同樣應歸屬于危險犯的范疇,并應將其界定為具體危險犯。理論界通說認為,“妨害公務(wù)罪是以抽象的危險為其處罰根據(jù)的”,“即以其實施暴力、威脅行為,對執(zhí)行公務(wù)有所妨害為已足,并不以因而導致妨害執(zhí)行職務(wù)的具體危險結(jié)果發(fā)生為必要。”[17]將作為妨害公務(wù)罪特殊形態(tài)的襲警罪定義為具體危險犯,并適度提高其入罪門檻,能夠與襲警罪略高于妨害公務(wù)罪的法定刑保持高度一致,有利于更加精準地體現(xiàn)二罪的銜序關(guān)系。最后,由職業(yè)屬性和工作性質(zhì)決定,人民警察對抗暴力侵襲的能力和安全防護能力均明顯高于其他國家機關(guān)工作人員。如果將襲警罪認定為抽象危險犯,則意味著暴力襲警行為一經(jīng)實施即可認定具有妨害職務(wù)執(zhí)行和侵害執(zhí)法人員身體健康的雙重危險,這顯然與人民警察所特有的武裝性質(zhì)并不相符,亦將造成刑法對人民警察與其他國家機關(guān)工作人員不平等保護的問題。唯有將襲警罪定位為具體危險犯,方能在維護人民警察依法履行職權(quán)、保護其人身權(quán)利的同時,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的自由空間,實現(xiàn)刑法謙抑。
綜上所述,襲警罪屬于具體危險犯,其成立與否的判斷標準應確立為,行為人實施的暴力襲警行為足以妨害人民警察依法執(zhí)行職務(wù),并對依法執(zhí)行職務(wù)的人民警察的生命、身體健康產(chǎn)生具體、緊迫、現(xiàn)實的危險。如果行為人實施襲警行為的暴力程度較為輕微,難以達到上述危險程度的,應排除出犯罪的范圍,具有行政違法性的,按照相關(guān)行政法律法規(guī)進行處理;如果該暴力襲警行為實際已經(jīng)造成人民警察死傷的嚴重后果的,應辨析本罪與相關(guān)犯罪的關(guān)系,決定適用恰當?shù)淖锩?/p>
四、襲警罪的罪行界分
(一)實務(wù)爭議
行為定性的不同直接決定刑罰裁量的輕重。受此影響,將一暴力襲警行為認定為襲警罪抑或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等關(guān)聯(lián)犯罪,往往成為控辯雙方爭議的焦點。由于認定標準并不統(tǒng)一,不同司法機關(guān)對同類案件采取了不同的認定方式。以行為人駕駛機動車沖擊公安執(zhí)法檢查卡口,拖拽或者碾壓人民警察為例。在該類案件中,行為人及其辯護人通常辯稱,行為人在客觀上僅實施了逃避執(zhí)法的行為,主觀上并無傷害、殺害執(zhí)法人員或者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尚未達到襲警罪或者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程度。對此,司法機關(guān)作出了如下認定:

①陜西省延安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裁定書,(2021)陜06 刑終214 號。②貴州省安順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2020)黔04 刑終111 號。需要說明的是,由于《刑法修正案(十一)》施行以后,涉及暴力襲擊民警或輔警的故意傷害、故意殺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案件并不多見,在此筆者主要列舉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施行以后發(fā)生的妨害公務(wù)及其相關(guān)犯罪案件。
(二)理論解析
1.襲警罪與相關(guān)犯罪的關(guān)系
襲警罪的增設(shè)不僅表明立法機關(guān)對于暴力襲警行為最為嚴厲的否定態(tài)度,其還與妨害公務(wù)罪、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等相關(guān)罪名相互銜接、緊密配合,共同形成懲治妨害人民警察依法執(zhí)行職務(wù)犯罪的嚴密罪名體系。有序協(xié)調(diào)和處理好襲警罪與相關(guān)犯罪的關(guān)系,是正確適用襲警犯罪、最大限度地發(fā)揮該罪懲治與預防作用的前提和基礎(chǔ)。如前文所述,襲警罪與妨害公務(wù)罪存在特別法與一般法的法條競合關(guān)系;該罪與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雖然規(guī)定在刑法分則的不同章節(jié),但并非毫無關(guān)聯(lián),其均包含著保護人身權(quán)利不受非法侵犯的精神內(nèi)核。在法定刑配置上,襲警罪的基本犯與故意傷害罪基本犯的法定刑相同,加重犯的法定刑低于故意傷害罪中有致人重傷以上加重情節(jié)的處罰力度;與故意殺人罪相比,襲警罪的法定刑明顯更為輕緩。作為襲警罪的有益補充,當暴力襲警行為造成人民警察嚴重傷亡后果,以襲警罪進行評價無法滿足罪刑相適應原則的要求時,應升格適用法定刑更重的故意傷害罪或者故意殺人罪。
2.襲警罪與相關(guān)犯罪的界分
在界分襲警罪與妨害公務(wù)罪、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等相關(guān)犯罪時,應以各罪保護的法益為基礎(chǔ),根據(jù)具體行為形態(tài)及其危害程度,決定最終適用的罪名。在論及襲警罪與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等法定刑較重的犯罪之間的關(guān)系時,首先應予回應的是,本罪“使用槍支、管制刀具,或者以駕駛機動車撞擊等手段,嚴重危及其人身安全的”加重處罰情節(jié)是否包含上述犯罪所涉及的致人死傷的危害后果。有意見認為,襲警罪加重處罰情節(jié)中規(guī)定的“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包含重傷與死亡后果,當襲警行為造成嚴重傷亡后果時,行為成立襲警罪與故意傷害罪或者故意殺人罪的想象競合犯,應予從一重罪處斷。[18]筆者并不認同上述觀點。一方面,從襲警罪的文本表述來看,“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 是對暴力襲警行為所造成的危險狀態(tài)的描述,將實害后果解釋其中超出了國民對該文字本身可能具有含義的預測范圍。另一方面,從刑罰配置來看,襲警罪加重犯的法定最高刑僅為7年有期徒刑,遠遠低于故意傷害罪和故意殺人罪的法定刑,與因暴力襲警導致被害人重傷、死亡的犯罪的危害程度并不匹配。如果認為襲警罪的行為方式能夠涵蓋重傷和死亡的后果,那么此罪的設(shè)立不但無益于保護人民警察的執(zhí)法權(quán)威,反而將降低刑法對于人民警察人身權(quán)益的保護力度,這顯然與本罪的立法初衷背道而馳。有鑒于此,筆者認為,本罪的加重情節(jié)并不包含造成重傷或死亡的實害后果,暴力襲擊造成人民警察重傷或死亡后果的,應當按照法定刑更重的故意傷害罪或者故意殺人罪定罪量刑。
至于前述行為人以駕駛機動車方式襲警的行為認定,應結(jié)合具體案情分而述之。具體而言,以人民警察人身為對象進行撞擊、擠別的,構(gòu)成襲警罪的加重犯;在逃避檢查、強行闖卡過程中,無意剮蹭、帶倒、拖拽人民警察的,宜認定為襲警罪的基本犯;在強行闖卡過程中,無視現(xiàn)場執(zhí)法人員和社會其他人員的生命、健康和財產(chǎn)安全,采取反復撞擊、突然加速、追逐競駛等形式?jīng)_撞現(xiàn)場執(zhí)法人員或者執(zhí)法人員所乘警車,達到危害公共安全程度的,應認定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直接沖撞、碾壓執(zhí)法人員,或者明知已造成執(zhí)法人員被拖拽的狀態(tài)仍然無視被害人的生命健康強行闖卡,造成執(zhí)法人員重傷、死亡后果的,按照故意傷害罪或者故意殺人罪論處。
五、余論
總體而言,現(xiàn)階段各地司法機關(guān)對襲警犯罪普遍采取了較為嚴厲的刑事司法政策,呈現(xiàn)出打擊范圍廣、公訴量大、適用實刑多等特點。有學者不無擔心地指出,“按照這種趨勢發(fā)展下去,襲警罪很有可能成為繼‘醉駕型’危險駕駛罪之后的第二大罪名。”“如果輕罪立法化之后司法不加控制,將所有的襲警行為都以犯罪論處,那么勢必造成濫用刑罰的后果。”[9]26上述論斷折射出該學者對于襲警犯罪可能陷入打擊失度、刑罰恣意困境的深深憂慮。對此,應做全方位審視。首先,應予正視的是,在部分地區(qū),襲警罪的適用確有過度擴張、打擊范圍過大的趨勢,這與目前該罪處罰邊界不清晰、裁量標準不統(tǒng)一有直接關(guān)系。為進一步規(guī)范法律適用、統(tǒng)一司法裁量標準,公檢法三機關(guān)應當盡快制定犯罪邊界清晰、裁量標準明確、行刑銜接順暢的司法解釋性文件。其次,實踐中該類犯罪呈現(xiàn)出打擊數(shù)量持續(xù)增加的特點,與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背景下警務(wù)工作覆蓋面廣泛、執(zhí)法服務(wù)事項繁多、人民警察參與程度深入不無關(guān)聯(lián)。同時也反映出,當前暴力襲警現(xiàn)象頻繁多發(fā),懲治襲警犯罪的形勢依然嚴重。對于暴力襲警行為,應充分發(fā)揮襲警罪獨立設(shè)罪的立法價值,進一步織密法網(wǎng)、嚴肅查處,最大限度地壓縮襲警違法犯罪空間。最后,還應清醒地認識到,刑罰的作用具有局限性,僅依靠刑罰制裁不但無法阻卻襲警犯罪的滋生,反而容易激化警民矛盾,削減公眾對人民警察的信任和警察執(zhí)法的認同。有鑒于此,應當綜合運用行政處罰、強化教育宣傳、提升警察執(zhí)法能力等多種手段,構(gòu)建懲罰與預防相結(jié)合的襲警違法犯罪防控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