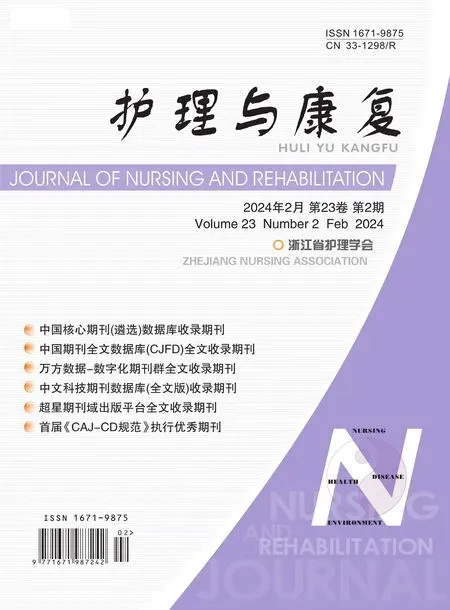癌癥住院患兒Child Life干預研究進展
秦奎英,王 彬,吳小花
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兒童醫院,浙江杭州 310052
癌癥研究中心數據顯示,全球兒童和青少年的癌癥發病率為0.005%~0.090%,且病死率高達25%[1-2]。癌癥住院患兒除面臨難以控制和管理的癥狀群如疼痛、惡心、嘔吐、厭食、疲勞、焦慮、抑郁之外,還需應對放療、化療、擇期手術等壓力事件,從而產生一系列壓力反應如信任感缺失、依賴性增強、死亡恐懼感等,進而啟動防御機制,運用攻擊性舉動、不合作行為等進行對抗,這種對抗在影響診療效果的同時也給家庭成員的心身健康帶來負性影響[3-5]。兒童醫療輔導(Child Life)是國內近年來引入并受到重視的一種人性化心理照護服務。兒童醫療輔導專家(Certified Child Life Specialist,CCLS)通過治療性游戲、音樂、繪本等方式為患兒提供心理準備、非藥物疼痛管理、健康教育等服務,以降低患兒負性情緒及疼痛感受,增強其應對能力,改善患兒和家庭的短期和長期結局[6]。美國兒科學會于2004年指出,CCLS應被納入致力于照護癌癥患兒的多學科團隊[7]。作為跨學科及以患兒和家庭為中心的照護的一部分,Child Life服務自提出后已在國外癌癥住院患兒中被應用,并取得良好效果[8-9],而國內關于如何在癌癥住院患兒中實施Child Life干預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干預方式及臨床效果有待驗證。本文就Child Life的起源與發展,應用于癌癥住院患兒的干預內容、效果進行綜述,旨在進一步推進該服務在臨床的應用。
1 Child Life起源與發展
Child Life服務最早于1922年美國密西根州的Mott兒童醫院開展,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經歷了快速發展[9]。美國兒科學會定義Child Life項目為可獲取的、連續的、整體的、以家庭為中心的、醫療服務配套的愛心性和人文性有效照護[10]。Child Life專業人員協會自1982年正式成立以來一直專注于開發和推廣為患兒及家庭提供心理照護的干預措施,如心理準備、治療性游戲、疼痛管理等[9]。美國兒科學會和Child Life專業人員協會關于Child Life服務的政策聲明從干預措施到干預領域,以及到Child Life專業數據中心的建立和職業認證資質提升等,已歷經4次更新和補充,是綜合兒童保健服務系統的質量基準,也是兒科護理卓越的指標[9]。CCLS的服務場所已不再局限于兒童醫院,開始擴展到私人診所和家庭臨終關懷機構等,服務范圍也延伸到安寧療護、行為健康、創傷和兒童保護服務等領域[5,9]。
2 Child Life應用于癌癥住院患兒的干預內容
自Child Life服務開展以來,各國研究者在癌癥住院患兒應對醫療程序的不同階段對其進行驗證,分為醫療程序前的心理準備、貫穿整體醫療過程的疼痛管理、情緒及情感支持三部分。
2.1 心理準備
醫療程序前的心理準備是一系列技術和流程的總稱[7],是Child Life工作的核心組成部分,信任關系的建立、提供與發展水平相適應的醫療程序相關信息、鼓勵提問和情感表達是心理準備的核心三要素[9]。張冠珣等[11]構建的急性白血病患兒癥候群干預方案中詳細羅列了心理準備服務條目及內容:第1天通過對話與患兒和家庭建立治療性關系;第1天至操作前1 d通過繪本、手偶、動畫片為患兒講解白血病病因、治療方案和化療常見不良反應等,并向患兒示范操作過程,操作中互動,必要時進行角色扮演等。Engvall等[12]對57例患兒在接受放療程序前進行心理準備干預,包括通過平板電腦播放放療題材的動畫等進行視聽干預、聯合動物毛絨玩具和放療機器模型幫助患兒開展角色扮演游戲,提供適當的材料供患兒在放療開始前開展繪畫活動等。結果顯示,心理準備干預可以促進親子關系及同伴互動,特別適用于幼齡患兒。未來應進一步探索、發展和完善適用于不同年齡段患兒的干預措施和技術方案,為此類干預的發展提供基礎。
2.2 疼痛管理
癌癥患兒面臨癌癥本身引起的疼痛如神經浸潤、外部神經壓迫引起的炎癥以及癌癥相關疼痛如放療、化療等引起的神經損傷或黏膜炎等[13]。CCLS持續倡導非藥物疼痛管理策略,其與多學科團隊成員合作,結合藥理學、心理學方法等,幫助患兒制定個性化方案,以應對反復、持續的疼痛[14]。2020年,Loeffen等[15]發表了一篇CCLS在內的多學科團隊共同參與制作的關于減輕癌癥患兒穿刺相關操作疼痛管理的臨床實踐指南。該指南推薦的所有疼痛管理措施均遵循循證理念,其中對操作開始前>1 h、開始前1 h、開始前5 min以及操作中將藥理學和心理學干預相結合給予強推薦,對操作開始前5 min以及操作中主動分散注意力和催眠術給予強推薦,對被動分散注意力給予弱推薦。分散注意力是CCLS使用最廣泛的技術之一,屬于疼痛管理的認知策略,具體措施包括提供與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玩具、虛擬現實平臺、互聯網技術以及電子和數碼設備的應用、呼吸技巧以及引導式意向游戲等,此類技術已被證明可以成功減輕侵入性操作中患兒的疼痛。但值得注意的是,Child Life所有分散注意力策略的制定必須符合患兒的發展水平和個性化需求,可采用新生兒疼痛評估量表、兒童疼痛行為量表(Face,Legs,Activity,Crying,Consolability,FLACC)、修訂版Wong-Baker面部表情疼痛評估法、口頭評分法等工具評估患兒疼痛程度[6],并根據干預效果適時作出調整。
2.3 情緒及情感支持
研究[16]表明,癌癥患兒及家庭成員在患兒生命末期均存在高水平的情感表達需求。CCLS具備專業的技能和資格,能為家庭提供特定的情感表達機會[14,17]。CCLS在終末期癌癥患兒中積極開展如兒童死亡教育、家庭會議、繪畫療法等活動,使患兒認識到死亡是身體功能的終止,是不可避免的自然現象,并幫助患兒和家庭開展遺產建設,如人物模型、手印、指紋等的制作,讓患兒更好地和家人告別[5,14];同時,CCLS鼓勵患兒臨終前和家人分享、傾訴自己內心的想法和感恩,修復與家人之間可能原本受損的關系。患兒離世后,CCLS會針對家長的預期性悲傷,通過電話回訪、文化或宗教祭奠儀式等形式進行哀傷輔導,并與多學科團隊成員合作開展如音樂療法、芳香療法、耳穴療法等,通過家庭哀悼、家庭尊嚴干預、心理社會療法等措施緩解家長的復雜性哀傷[18]。1999年,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法規規定由認證的CCLS為經歷創傷的家庭成員免費提供喪親服務[10]。這對幫助家庭平復喪親后復雜的情緒以及情感、回歸正常生活等尤為重要,也是人文關懷的體現,國內可借鑒。
3 Child Life應用于癌癥住院患兒的干預效果
3.1 緩解焦慮、恐懼等負性情緒
癌癥住院患兒常因入院后面臨許多侵入性醫療操作等而產生焦慮、恐懼等負性情緒。治療性小丑和音樂療法是Child Life 的輔助干預措施[19]。Lopes-Junior等[20]對16例癌癥患兒進行治療性小丑表演干預,收集干預后1 h、 4 h、9 h、13 h的唾液樣本以測定唾液皮質醇和α -淀粉酶水平,結果顯示,干預組在干預后4 h的心理壓力和疲乏水平均有所改善。Wong等[21]對25例接受腫瘤治療的患兒開展音樂治療,治療師為該干預制定了37項個體化目標,每3個月對目標達成情況進行評分,直至1年,干預次數180次,結果顯示,目標達成率為89.2 %,患兒焦慮、抑郁等情緒紊亂癥狀明顯減少,患兒的情感需求得到滿足。未來開展此類干預應在對患兒進行個體化評估的基礎上,結合診斷、干預目標、干預時長和次數等確定干預模式,開展個體化干預,盡可能緩解患兒的負性情緒。
3.2 減輕疼痛
疼痛是終末期癌癥患兒的高發癥狀。Hsiao等[7]對18例進行骨髓抽吸或腰椎穿刺當天的白血病患兒開展心理社會干預,CCLS在患兒鎮靜前根據患兒的年齡和認知程度,開展如計數、吹泡泡、閱讀故事等活動,或指導患兒實施應對策略,如呼吸練習、交談、引導式意象等,結果提示,CCLS提供的心理社會干預對減輕患兒疼痛具有重大潛能。角色扮演是Child Life干預形式的一種,葉阿琴等[22]對50例需行輸液港穿刺的癌癥住院患兒進行角色扮演,在操作前讓患兒在游戲中了解整個輸液港穿刺的過程,50例對照組采用常規宣教形式。結果顯示,觀察組和對照組在穿刺過程中的疼痛評分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前者明顯低于后者。目前的大多數研究集中在某一個醫療程序,未來的研究應該考慮癌癥患兒漫長的重復治療軌跡,進而開展縱向設計研究來驗證Child Life項目的干預效果。
3.3 提高理解和配合度
患兒對醫療程序的理解和配合影響因素較多,包括年齡、認知以及對家長的依賴性等,且干預空間較大。美國邁阿密癌癥研究所對癌癥患兒在放療前和放療期間接受的心理社會支持開展問卷調查,其中CCLS在放療前對患兒進行心理準備干預,包括提供與患兒發展水平相適應的信息、視聽教具、教學玩偶和小冊子,定期開展團體設備參觀、信息會議以及應用虛擬現實平臺等。結果顯示,干預后患兒和家庭對放療程序的理解更加清晰,對放療程序的接受度、配合度得到提高,整體的放療體驗得到改善[23]。馬晶晶等[24]將138例惡性腫瘤住院患兒隨機分為實驗組和對照組,實驗組在常規護理及健康教育的基礎上,每月進行Child Life游戲干預,包括角色扮演、表演游戲以及繪畫、音樂等藝術游戲,結果顯示,實驗組患兒護理技術操作依從性高于對照組。未來開展此類Child Life服務應盡力爭取醫院的支持,完善相關配套服務及專業的人才配置等,促使患兒更好地配合治療。
3.4 改善患兒醫療體驗及提高家庭滿意度
近年來,患者體驗和患者滿意度已成為關鍵的質量和績效指標,而CCLS干預的開展可對患兒和家庭滿意度產生積極影響[9]。Basak等[5]提到,CCLS以魔法為切入點取得1例14歲終末期癌癥患兒的高度配合,幫助多學科團隊順利完成對其全面評估及有效干預,減輕了患兒對醫療程序的抵觸,促進了患兒醫院生活正常化,幫助患兒實現終末期的高質量生活,患兒的體驗及家庭成員的滿意度均處于較高水平。治療性游戲是CCLS開展工作的重要和具體表現形式[9]。Teksoz等[25]對30例患兒開展創造性游戲干預,結果顯示,游戲干預使患兒將醫療經歷與游戲體驗結合起來,改善了醫患關系及醫療體驗,提高了患兒及家庭滿意度。目前對癌癥住院患兒醫療體驗及滿意度評價缺乏統一的衡量標準及方法,建議未來采用重復測量的方法,通過時間縱向追蹤患兒及家庭主觀幸福感的演變,并及時向團隊反饋。
4 Child Life服務發展的現存挑戰及發展趨勢分析
4.1 建立中國特色的Child Life專業人員培訓考核體系及相關質量控制和評價指標
目前,國內缺乏類似于 Child Life專業人員協會的權威資質認證機構,服務開展的質量控制與評價指標也并未統一[26]。培訓考核方面,可聘請有資質的相關專業人士,如專業的CCLS、心理學或社會學專家等,集中進行固定時長的理論和實踐授課并進行結業考核,同時制定相關的崗位職責并督促完成固定時長的臨床實踐;質量控制方面,可制定相關的規章制度及服務質量評分表,每月、每季度、每半年、年終進行工作質量考核,并對表現優異的護士和科室進行表彰;評價指標方面,可將患兒體驗和家庭滿意度作為關鍵的質量和績效評價指標[9,26-27]。我國醫療機構在推動Child Life服務開展的實際工作中可借鑒上述經驗,在探索中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的Child Life專業人員培訓考核體系及相關質量控制和評價指標,提升癌癥住院患兒的照護質量。
4.2 國內Child Life發展趨勢分析
近年來國內多家大型醫療機構逐漸開始醫院游戲項目,主要由護士或醫務社工開展類似Child Life的服務。浙江、上海、四川等地的Child Life兼職護士或專科護士崗位的設置和管理工作也在穩步推進中,通過開展專項培訓、舉辦繼續教育學習班或組織學術論壇等方式,邀請相關學科專家參與,為Child Life后續的發展打下良好基礎。隨著熱度的提升,Child Life相關發文量自2018后較之前有大幅增加。相關游戲輔導專業道具和游戲輔導項目不斷出現且仍有較大開發空間。建議未來爭取更多CCLS人員配置、財政支持等相關政策、法律支持,以推動國內Child Life的發展。
5 結語
對癌癥住院患兒運用不同的Child Life形式進行干預,在緩解焦慮、恐懼等負性情緒,減輕疼痛,提高理解和配合度,提高家庭滿意度,改善患兒醫療體驗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我國的Child Life起步較晚,今后應結合我國國情開展更多高質量、多樣化的Child Life干預研究,方案的開展應建立在對患兒及家庭進行整體評估的基礎上,從而為我國癌癥住院患兒及家庭提供整體照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