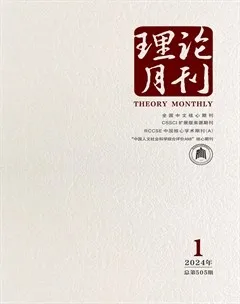超越死亡:論胡塞爾內時間意識理論中的愛之共同體
王朝璐
[摘 要] 自我維度在內時間意識中顯現為生活主體,愛之共同體是生活主體的重要階段。探討愛之共同體的發生進程,勢必要聚焦其中的關鍵節點——人格生成、世代生成以及愛之共同體。同時,還應抓住自我維度這條線索,從自我通過同感單向地通達他者,發展為自我與他者彼此通達,并嘗試消弭主體之間的間隙,來展現愛之共同體的雙重主體間性。在愛之共同體中,內時間意識真正完成了個體化,顯現為完整意義上的個體存在,推進了內時間意識由時間性發生向人格性發生的轉變。由此,歷史、文化等具有實踐意義的事件才能發生,并推動實踐現象學視域的展開。
[關鍵詞] 內時間意識;人格;家庭;死亡;愛之共同體
[DOI編號] 10.14180/j.cnki.1004-0544.2024.01.016
[中圖分類號] B516.52? ? ? ? ? ? ? ? ? [文獻標識碼] A? ? ? ? [文章編號] 1004-0544(2024)01-0153-08
內時間意識理論是胡塞爾現象學的重要理論,與之相關的主要著作如《內時間意識現象學》(1893—1917)、《關于時間意識的貝爾瑙手稿》(1917—1918)已有成熟的中文譯本。而僅剩的《C手稿》(1929—1934),由于其自身的特性,在語言表述、主題討論、章節關聯等方面與成熟的學術著作相比更具復雜性,增添了翻譯工作的難度,至今未有成熟的中譯本面世①。目前,國內對于內時間意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部分:第一,關注內時間意識理論本身的邏輯發生與內容梳理。第二,基于內時間意識理論的邏輯發生與主要內容,分析其中的關鍵主題與核心視角,主要涉及存在、自我維度、交互主體性、生活意義等。第三,基于比較視野、發生視角、實踐視域等對胡塞爾內時間意識理論進行創新性的解讀與重構①。這些研究從不同方向展現了胡塞爾內時間意識理論的復雜性與可挖掘性。有鑒于此,筆者擬從內時間意識理論的重要內容——自我維度入手,基于尚未引發廣泛討論的《C手稿》的相關部分,嘗試重建生活的原初意義,揭開生活的實踐視域,以期補充圍繞內時間意識展開的相關討論。
在胡塞爾的內時間意識理論中,“原印象—滯留—前攝”的統一體是關鍵所在。這三者由純粹的意識靜態結構發展為彼此關聯的發生統一體,使現象學的實踐視域得以敞開。在《C手稿》中,胡塞爾力圖對此進行多維度的闡釋。盡管受限于文本本身的不完整性,但一條通達生活本身的路徑逐漸顯現——“生活主體”(Lebenssubjekt)成為一個重要的切入視角。內時間意識作為原初時間維度,是所有意向體驗的最底層維度,也是始終伴隨著一切體驗的流逝感。生活主體是自我維度在內時間意識中的顯現,這使胡塞爾在時間性中正式關注到了個體存在。他通過分析生活主體顯現的雙重主體間性,解釋了自身與他者彼此通達的可能性,并嘗試通過闡釋愛之共同體的生成,回答死亡這個終極問題。可以說,這樣一種探討體現出的是胡塞爾對生活本身的現象學追問。
一、作為生活主體構造起點的人格生成
想要完整把握具有主體間性的生活主體,就要從人格共同體的生成開始。在內時間意識中,人格的生成需要基于當下的單子共同體,也就是具有“清醒狀態”(Wachheit)的單子共同體,我們不妨稱之為“清醒共同體”。要解釋這一共同體,就要引入“單子全體”(Monadenall)的概念。胡塞爾認為,它是一種“為彼此與共彼此的存在”(Füreinander- und Miteinandersein)②。以單子a和單子b為例,它們是對方的“為我在彼”(Für-mich-da),即彼此具有間隙的兩個主體存在。當單子a和單子b都具有自身主體存在的意義時,它們就構成一個單子綜合(a,b),即單子全體。它兼具單子a的第一人稱維度以及單子b的第一人稱維度,也就是兼具單子共同體a(b)與單子共同體b(a)。對于單子全體來說,它可以是無限多個單子的綜合,成為一種普全意義上的單子。在這個意義上,胡塞爾認為單子“在內在時間性中是一種沒有開端也沒有終結的自身構建”③。
在普全意義上的單子全體中,所有單子都是第一人稱維度的、與其他單子具有間隙的主體存在,清醒共同體則指向某個第一人稱維度的單子共同體。在內時間意識的個體化進程中,單子作為進入時間性之中的生活主體,原初地是處于當下的清醒單子,因而其單子共同體原初地是一種清醒共同體。所以,從時間性發生的維度來看,單子全體原初是一種普全意義上的清醒共同體。按照自我的本己本質性,對象只能被給予同一個“我”(mich)。“我”作為清醒單子以及清醒共同體只能具有唯一的第一人稱維度,也就是說,如果生活主體是清醒單子a,那么它在進入主體間的維度之后只能是清醒共同體a(b),而不能是清醒共同體b(a)。這個具有唯一確定的第一人稱維度的清醒共同體就是人格共同體(die pers?nliche Gemeinschaft)或人格化的人(Person)。“人格”在胡塞爾這里具有兩個方向:“其一:對于自然主義觀念相對立的人格主義觀點的探討,以及對精神世界之構成的現象學描述。它涉及人格自我(das personale Ich)或精神自我(das geistige Ich)與自然世界的關系,亦即心靈與自然以及心靈與肉體的關系;其二,對于社會和共同體問題對應的個體問題的探討,以及通過同感(Einfühlung)對他人的構造問題。它涉及個人自我(das pers?nliche Ich)或個體主體性與社會主體性(die individuelle oder soziale Subjektivit?t)的關心問題,亦即心靈與心靈的關系問題以及交互主體性問題。”[1](p21)值得注意的是,胡塞爾對愛的探究也具有兩個方向,分別是單子生活的精神之愛和愛之共同體(geistige Liebe und Liebesgemeinschaft)①,正對應著人格的兩個方向,從第二個方向的人格入手探討愛之共同體不僅是可行的而且是合適的。但是,無論是人格的兩個方向,還是愛的兩個方向,在嚴格意義上都不是彼此獨立、互不干涉的。很多時候胡塞爾會在這兩個方向上同時推進,以使其彼此印證。
清醒共同體作為人格共同體或人格化的人,關鍵在于共同體所具有的清醒狀態。一方面,對于最原初意義上的單子共同體來說,它沒有開端也沒有終結,死亡問題并不在它的視域之中。只有當它具有清醒狀態時,它自身唯一的第一人稱維度才會被確定下來,它才能從保證清醒狀態持存的角度嘗試超越死亡。由此,單子共同體成為清醒共同體。另一方面,在這個清醒共同體中,“為我存在的整體”(das ganze Für-mich-Sein)成為世界之中的人格化的人、人類化的人(Mensch)②。
在此,人格生成顯現了從“為我在彼”向“為我存在的整體”的轉化,這個轉化只能在清醒共同體的意義上發生。首先,“為我在彼”意味著普全意義上的主體存在。所有單子都是以自身第一人稱的維度、彼此之間具有間隙的方式存在,也就是說,單子共同體具有普全的第一人稱維度。而“為我存在的整體”先要確定的是“為我”(für-mich),即唯一的第一人稱維度,這只能依據清醒共同體的清醒狀態實現。其次,“為我存在的整體”意味著單子之間的間隙被消解了,單子成為“在彼此之中”(ineinander)的存在,這也是愛之共同體的重要生成動力③。單子之間間隙的消解并非指單子的主體存在意義的消失,而是清醒共同體只能確認并顯現自身唯一的第一人稱維度。這可以從清醒共同體的周圍世界的層面來理解:清醒單子a通過同感清醒單子b構成了屬于清醒單子a的清醒共同體a(b),清醒單子b則以主體存在的方式進入清醒單子a的周圍世界A生成周圍世界A(b)。與純粹的時間對象進入周圍世界相比,以主體存在的方式進入周圍世界的清醒單子b還將它自身的周圍世界B融入了周圍世界A的視域之中。因此,清醒共同體a(b)的周圍世界不僅顯現為A(b),同時也顯現為A(B),可以被看作兩者的綜合。所以,單子之間間隙的消解關鍵在于周圍世界的視域的融合。關于視域的融合方式,胡塞爾并沒有給出明確的解釋,但是從他使用“融合”這個概念的一貫指向來看,周圍世界視域的融合絕不僅僅指向空乏的結構,也指向內容或者說充實的可能性。至此,清醒共同體成為人格共同體,人格化的人在當下能夠通過融合周圍世界視域的方式通達他者的主體存在,這也表明周圍世界的視域具有開放性。
人格的生成還必須要有作為中心的自身身體①,以使第一人稱維度在身體中得到顯現。只有清醒共同體的身體才是第一人稱維度的身體主體,其他的身體主體則是第二性的,并作為切身身體被給予。對于第二性的身體主體來說,一方面其周圍世界以融合的方式進入清醒共同體中,另一方面其自身作為切身身體以時間對象的方式被給予,這兩種方式是共存的。所以,如果要使每個清醒單子在共同體中都有成為中心的可能性,就要盡量保證單子的清醒狀態,使清醒共同體始終處于當下的生成之中。在此基礎上,人格共同體所進行的意向體驗就能進一步生成更高層次的社會意義上的、文化意義上的人格共同體,從而進入世代生成之中。
二、具有雙重主體間性的世代生成
隨著第一人稱維度被唯一確定,清醒共同體成為人格共同體,即人格化的人。諸人格化的人彼此之間構成“世代生成性”(Generativit?t)的人格共同體,也就是說在世代生成性的人格共同體中顯現兩種意義上的主體間維度——“在彼此之中”(Ineinander)與“在彼此之間”(Miteinander)。“在彼此之中”強調視域融合的方式,對于人格化的人來說,其他主體存在以周圍世界的視域融合的方式進入它的周圍世界;在融合的基礎上,“在彼此之間”是一種普全意義上的第一人稱維度,強調其他主體存在之于自身的中心意義,即成為那個確定的人格化的人,從人格的意義上顯現出普全性。只有同時具備這兩種主體間維度,人格化的人才能構成世代生成性的人格共同體,傳統、歷史、文化才能從中顯現,展開現象學的實踐維度。
首先,世代生成性的人格共同體要以“在彼此之中”的人格化的人作為基礎。一方面,在人格化的人中,其他主體存在以人格的權能、習性在當下顯現[2](p369)。這意味著,其他主體存在可以通過類似習得的方式,成為人格的習性,也就是生活主體的基質,影響生活主體的當下構造。人格化的人可以同無數個其他主體存在“在彼此之中”,由此無數個其他主體就遵循著生活主體的內在時間性,并按照內在時間性的“滯留—原印象—前攝”三位一體的方式進入習性自我維度。需要注意的是,這無數個其他主體存在并不一定同時被給予,彼此之間也并不一定存在聯系。但是,當這些主體存在都進入這個人格化的人之中時,它們就會按照這個人格的內在時間性共同發生作用。對于人格化的人來說,其自身就是無數個清醒共同體的被動綜合。另一方面,人格化的人不僅強調自身的清醒狀態,也就是自身唯一的第一人稱維度,而且強調自身在當下進行體驗的必要性。只有這樣,其周圍世界才能是既朝向過去又向未來敞開的視域,這個“視域性”(Horizontalit?t)就是世代生成性的核心——“傳統性”(Traditionalit?t)[2](p369-370)。所以,人格化的人必然正在進行當下化的行為,生活主體正是在當下化的行為之中才獲得人格的意義。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人格性的發生是一種當下進行的發生,既生成生活主體的基質,又生成周圍世界的視域。
其次,在“在彼此之中”的基礎上,諸人格化的人自身還會顯現“在彼此之間”的維度,成為世代生成性的人格共同體,而其核心正是傳統性。胡塞爾認為,“在彼此之間”維度上的共有傳統由當下的行為體驗產生,世代生成性的人格共同體顯現為個體的世代:一方面,每一個人格化的人通過當下的行為體驗都能產生傳統,這些傳統通過行為體驗之間的關聯,“統一體化”(Vereinheitlichung)為世代生成性的人格共同體的傳統;另一方面,傳統是處在動態生成中的,是“成長中的、新的、廣泛的傳統”(erwachsende, neue, weitere Tradition)。這種動態發生也需要在當下的行為體驗中進行,至此世代生成性的人格共同體成為“溝通的—社會的”(kommunikativ-soziale)共同體[2](p370)。這意味著,世代生成性的人格共同體能夠進一步成為社會意義上的共同體,其關鍵在于人格共同體中諸人格的傳統的統一體化,即視域的統一體化。對于人格化的人而言,其他主體存在以習性自我的方式進入其自身,成為其基質。這些主體存在的周圍世界以視域融合的方式一同在人格化的人之中顯現,生成此人格化的人在此當下的周圍世界的視域,人格化的人的視域已經在融合意義上進行了統一體化。世代生成性的人格共同體的視域則在融合意義的基礎上進一步統一體化,這種統一體化是兩個彼此之間具有間隙的人格化的人在行為體驗中進行的,是兩個第一人稱視角的統一體化,可以被看作一種綜合。因此,傳統是雙重意義上的統一體化,對處在這個當下的行為體驗中的所有第一人稱視角的人格化的人都有意義。換句話說,世代生成性的人格共同體中的所有人格化的人能夠在同一第一人稱視角視域中存在,這個綜合的視域就是傳統。胡塞爾認為,這個具有傳統的人格共同體就是具有世代生成性的個體。至此,個體在雙重主體間的維度上顯現,內時間意識的個體化問題有了一個較為完整的闡釋。
世代生成性的人格共同體通過統一體化獲得傳統,不僅推動了第二個方向上人格意義的發展,使個體顯現為世代性的個體,而且推動了第一個方向上人格意義的發展。統一體化的傳統在人類化的人的意義上顯現為“歷史性”(Geschichtlichkeit),在歷史性中人格共同體作為人類獲得了“世代無限性”(Generationsunendlichkeit)[2](p437),以世代生成的方式保證人類持存——這與日常意義上所說的人類種族的無限延續性相符合。胡塞爾也將人類化的人稱為“民族”(Volk):一方面,民族可以與其他民族以一種交互的方式構造聯系,如通過戰爭、文化交流形成完整的民族人格性和民族文化,這種構造歷史性的方式是間接的、類比的、含混的;另一方面,這種含混的構造方式是民族之間通達方式的特性。對于第一人稱維度的民族來說,總有其完全無法理解的其他民族,但胡塞爾認為,一個民族只要以身體活動、身體感知的方式來通達,就能獲得對于其他民族的“本己理解”(eigentliches Verstehen)[2](p371)。這種對通達方式有效性的信任源于現象學的意向性,這可以從“碎玻璃與碎冰塊”的例子中得到進一步闡釋:我前一天晚上回家,在家門口看見了一堆碎玻璃,但第二天早上我卻發現,昨天看見的那一堆碎玻璃其實是碎冰塊。索科拉夫斯基認為,無論是第一天看到的碎玻璃,還是第二天看到的碎冰塊,在看到的當下都是真實有效的。在這兩個當下中,事物都是公開被給予的,也就是按其自身被給予的,所以碎玻璃與碎冰塊都屬于同一個時間對象的視域,只是在不同當下顯現中有著不同被充實的可能性[3](p14-15)。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民族之間構造的歷史性依據意向性具有一個視域,間接的、類比的、含混的方式都屬于視域中蘊含的可能性,因而在被充實的那個當下是真實有效的。
在此,人類化的人具有了人格化的人的視域,在第一個方向的人格意義中顯現出了第二個方向的人格意義。因此兩個方向的人格意義并非彼此獨立,而是相互交織、彼此印證。由此,胡塞爾也將第一個方向的世代無限性解釋為第二個方向的個體的相合——個體能夠通過聯想的融合方式,在單個個體的維度和在彼此之中的主體間維度的雙重性中通達本己自身與他者自身①。
在世代生成維度上的人格共同體顯現了兩重彼此交織的人格意義,這再次強調了清醒狀態對于人格共同體的必要性。在世代生成性中,清醒狀態不僅指人格共同體處在現時當下,而且指人格共同體處在當下的行為體驗中,即正在進行當下化的行為活動。世代生成性無論是作為視域綜合的傳統,還是作為人類的歷史性,都需要在當下的行為體驗中持存。世代生成性的這兩重彼此交織的人格意義正對應著愛之共同體的兩重人格意義。事實上,愛之共同體的討論需要從第一個方向的人格意義,也就是作為人類化的人入手。
三、愛之共同體的生成
“愛之共同體”(Liebesgemeinschaft)在胡塞爾內時間意識的相關文獻中以家庭、友誼的形式出現。由父母、孩子構成的家庭與由朋友構成的友誼首先顯現為第一個方向上的人格共同體,也就是人類共同體,胡塞爾將人類共同體中的主體間維度稱為“鄰人關系”(Mitmenschheit)[2](p318)。在人類共同體中,胡塞爾通過對死亡問題的探究,即人類如何在家庭、友誼中超越自身的死亡,來闡釋鄰人關系的含義。
家庭的建立源自夫妻之愛,胡塞爾稱之為“性別本欲”(Geschlechtsinstinkte)。丈夫本欲地指向妻子,而妻子也本欲地指向丈夫,家庭就此建立①。孩子的產生則要基于在性別本欲之上的更高的本欲,胡塞爾認為,這是一種“階段性的撫養興趣”(das periodische Interesse der Ern?hrung)。只有丈夫顯現出父親的維度,妻子顯現出母親的維度,孩子才得以真正誕生。因此,家庭作為愛之共同體具有兩重維度:一是丈夫、妻子二者構成的共同體;二是丈夫、妻子、孩子三者構成的共同體,或確切地說是父親、母親、孩子三者構成的共同體。從第一重維度向第二重維度推進的關鍵就在于獲得階段性的撫養興趣,家庭成員對于自身死亡的超越正是在這種跨越維度的意義上來說的。
首先,讓我們聚焦愛之共同體的第一重維度,也就是夫妻之愛。它是在平等、自由的原則上構成的。一方面,夫妻雙方在一種平等的意義上指向彼此,兩者之間的關系并非主奴關系,或生物意義上的自然規律的強迫與屈從關系。構成夫妻之愛的雙方仍然持有著各自的意愿,且尊重對方的意愿②。只有這樣,夫妻雙方在共同體中的所有行為才能符合各自的性別本欲,第二重維度上的撫養興趣才能符合性別本欲且自發地產生。第一重維度的愛之共同體還顯現出一種社會意義:夫妻雙方需要在人類社會中作為勞動者,通過工作獲得食物、衣物等生活材料來維持自身的生存。只有在自身意愿的意義上,也就是夫妻雙方都是自愿為了家庭而工作,這種工作行為才能超出生物意義上的本欲而顯現為性別本欲,從而顯現為愛之共同體的行為。另一方面,夫妻雙方在平等的基礎上,在一種尊重對方意愿的意義上遵循自身意愿,也就是說,夫妻雙方的自身意愿成為彼此的自身意愿。由此,夫妻雙方具有自由且一致的意愿,這樣第二重維度中的撫養興趣才能同時作為夫妻雙方的自身意愿而產生,推動愛之共同體進入第二重維度——由父親、母親、孩子構成的家庭。黑爾德強調,母親不是獲得孩子的工具,這也是由夫妻雙方同時具有的自身意愿來保證的[4](p253)。孕育孩子的行為必須且只能由母親來承擔,所以母親需要自愿承擔整個過程,期待孩子的誕生,這樣人類的孕育才能與生物意義上的動物本欲有所區分。對于父親來說,這個自身意愿也是必要的,否則站在父親的角度上母親就成了獲得孩子的工具,而保證父親自身意愿的就是第一重維度的夫妻之愛。因此,夫妻之愛是構造家庭這個愛之共同體的基石,其核心在于夫妻雙方同時具有的自身意愿,這也正是家庭超越死亡的關鍵。
通過對作為人類共同體的家庭超越死亡的方式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人類共同體始終“在彼此之間”,并未達到“在彼此之中”。一方面,人類意義上的家庭成員始終具有生物學意義上的軀體,這些軀體之間顯然是具有間隙的;另一方面,人類意義上的家庭成員承認自身的死亡,并通過與自己的孩子建立意義的方式延續自身,這種父母與孩子之間的愛是一種普遍意義的愛,所以人類意義上的家庭成員在普遍意義上超越了死亡。這意味著,家庭成員彼此之間的間隙并未被消解,而是構造了一個更大的共同體。但是胡塞爾討論共同體的初衷就是要達到“在彼此之中”,家庭、朋友作為愛之共同體需要進入彼此現實意義的視域中,構成現實的周圍世界,而這就需要依靠第二個方向的人格意義①。其實,胡塞爾在人類共同體的意義上已經顯露了對“在彼此之中”的關切,他認為母親具有“生活在孩子之中”(lebt im Kinde)的本欲[2](p170,314),所以,愛之共同體在第二個方向的人格意義上的展開是必然的。
愛之共同體在第二個方向的人格意義上的展開,關鍵在于確定唯一的第一人稱維度——“為我”(für-mich)。這樣愛之共同體中的其他主體存在才能作為“為我存在的整體”(das ganze Für-mich-Sein)進入當下的生活主體之中,生活主體才能在既“在彼此之中”又“在彼此之間”的雙重主體間維度上生成愛之共同體。一方面,每個家庭成員都具有自身第一人稱維度,向其他家庭成員敞開。其他家庭成員則以主體存在的方式進入這個生活主體中,也就是作為基質意義上的習性自我進入生活主體的同一性統一體之中。而且,其他家庭成員的周圍世界也以融合的方式進入這個生活主體的周圍世界之中。另一方面,每個家庭成員都能夠與其他家庭成員進行統一體化,通過綜合的方式生成一個對所有家庭成員來說都在第一人稱維度上有效的傳統,這是一種普全意義上的傳統。盡管生物學意義上的死亡不可避免,但是在普全意義的傳統中,家庭成員作為生活主體可以在愛之共同體中繼續持存。
從生活主體的意義上來說,愛是一種穿透能力[5](p280):生活主體可以憑借愛進入雙重主體間維度,最終超越死亡。這種作為穿透能力的愛不僅存在于父母與孩子之間,而且存在于兄弟姐妹、長輩親眷等所有家庭成員之間。所有家庭成員都能在這個動態發生的傳統中持存,家風、家訓其實就是這個傳統的顯現形式,具有一種普全意義。有穿透能力的愛在朋友之間也存在,我們不妨將它作為本欲的興趣來理解。在這個意義上,友誼的生成過程就是兩個生活主體朝向同一個興趣,努力達到這個興趣的零強度的過程。按照愛之共同體對清醒狀態的要求,只要這兩個生活主體能夠在同一個當下進行朝向興趣的意向行為,無論興趣的強度是否一樣,都能生成友誼,成為朋友。因此,對于友誼來說,興趣就是具有普全意義的傳統。朋友之間可以具有多個相同的興趣,如此一來友誼對于他們來說就是興趣的綜合。他們每個人都能在這個普全意義上的興趣中持存,從而超越死亡。
四、結語
胡塞爾探討愛之共同體的目的在于通達“真實的自身”以及他者的“真實存在”②,核心在于雙重主體間性,即自我與他者的相互通達。自我與他者的差別只在于是否具有當下的第一人稱維度,這使內時間意識中的自我維度由“我”向“我們”變化。當“我們”中的“我”足夠多時,“我們”就可以成為無限接近原初時間維度的愛之共同體。在愛之共同體意義上進行的所有意向體驗既符合共同體中每一個“我”的內在時間性,也符合普遍意義上的內在時間性。生活主體只有處在愛之共同體中,才能在最大程度上本真地彼此通達。
胡塞爾對自我的探討一貫謹慎,在最初對內時間意識的闡釋中盡量避免自我的出現,而他對生活主體的反復探討則表明,初期的謹慎并非忽視,恰恰是為了進行全面且充分的考量,這是現象學方法至今依然具有生命力的重要原因。心內世界與心外世界的二分,個體存在之間的間隙,都是生活實踐無法跳過的問題。胡塞爾使用意向性、雙重主體間維度、同感等概念進行探討,展現出開放性的實踐視域,為理解人類共同體提供了一種新的視角。在具有融合性的世界視域之中,愛之共同體具有的穿透能力,可以在個人之間、民族之間,甚至國家之間起效。作為胡塞爾國家理論的重要概念,愛之共同體在當下仍然具有鮮活的生命力,能夠為各種共同體理論帶來新的啟發。由此可見,內時間意識理論不應當僅被看作純粹的概念討論。在根本上,它為我們提供了通達生活實踐的必由之路,而照亮它的方式則潛藏在胡塞爾尚未引起廣泛討論的手稿或文獻中。這也正是現象學當代意義的重要構成部分。
參考文獻:
[1]倪梁康.胡塞爾與舍勒:人格現象學的兩種可能[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
[2]Edmund Husserl.Sp?te Texte über Zeitkonstitution(1929-1934): Die C-Manuskripte[M]. Dordrecht: Springer, 2006.
[3][美]羅伯特·索科拉夫斯基.現象學導論[M].高秉江,張建華,譯.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
[4][德]克勞斯·黑爾德.世界現象學[M].倪梁康,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
[5]倪梁康.胡塞爾現象學概念通釋(修訂版)[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