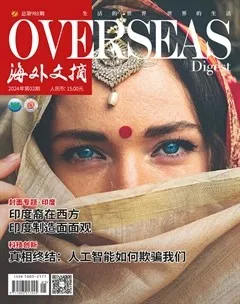互聯網世代的職場人生
無夏

麥肯錫公司咨詢師賽巴斯提安·布克“現在,我們可以不僅僅為工作而活。”
作為麥肯錫公司的新生代,賽巴斯提安·布克的日子顯得有些太過愜意了。他在紐約接受了視頻采訪,談及如何安排自己的時間時,笑得很開心:逛逛博物館,看看百老匯,和朋友們一起吃早飯,晚上喝喝小酒。兩周后,他將前往洛杉磯旅行,然后去巴拿馬和哥倫比亞玩一個月。
工作?可以等一等嘛。
布克已經在這家咨詢公司就職近兩年,這也是他第二次利用“降薪休假”制度。這一制度規定,除去常規的休假,咨詢師在完成某個項目后,每年可以休假最多兩個月,可以一次性休完或者分幾次休。他們的年薪會相應減少,減少的額度分攤到全年。簡單來說,就是布克自己購買了一點自由時間。
而這是23歲的布克可以提出的要求,他是公司爭相搶聘的那種高潛力員工。麥肯錫公司只能同意。盡管同時工作的咨詢師會因此變少,但公司希望對年輕人保持吸引力。布克說,如果沒有“降薪休假”制度,他21歲本科畢業后可能不會選擇這份工作,畢竟咨詢師行業向來以沒完沒了的加班和業績壓力著稱。

布克表示,他完全愿意努力工作,在有項目時,他總是每周工作超過40小時,對于咨詢師來說,這聽起來也很正常。但是,他還想留點時間給別的,比如旅行、朋友和家人。入職時,他最關心的問題是:在全職工作的同時,我還能保有一部分自我嗎?這份工作是否為休閑生活留有空間?“對于我父母那代人來說,工作就是生活,”布克說,“而現在,我們可以不僅僅為工作而活。”
布克屬于互聯網世代,他們出生于1995年到2010年之間。他們對職場的模樣有自己的想法,期待工作適應他們的生活,而不是反過來。如果問他們職場生活中的優先性排名,他們會將工作生活平衡排在非常靠前的位置,僅次于工資。
人力資源服務公司任仕達最新發布的《工作趨勢報告》數據顯示,18到24歲的受訪者中,有58%表示,如果一份工作阻礙了他們享受生活,就會選擇辭職。此外,38%的受訪者承認自己已經因此辭過職了。
“我們不會說我們不想工作,我們只是希望能在新型工作模式下工作。”咨詢師布克這樣說道,“上一代人也有責任適應我們的需求。”
年輕人可以有這樣的自信,因為他們十分緊缺。有數據表明,到2035年,德國就會失去多達700萬就業者,因為嬰兒潮一代退休了,而年輕人越來越少,他們有能力改變職場條件。
麥肯錫的招聘主管約納坦·施泰因巴赫表示,如今,更多求職者會詢問公司是否實行彈性工作制、有沒有可能兼職以及他們的具體工作內容是什么。這是個驚人的轉變。“近幾十年,求職者在面試時提出的最典型問題是:我能多快升職?我能掙多少錢?”施泰因巴赫說。
新生代的新力量源自各方關系的簡單逆轉。上世紀90年代,職位稀缺,畢業生能找到一份工作就要感恩戴德了,如今則是公司老板為能招到專業人才喜笑顏開。
經濟學家克里斯提安·朔爾茨是最早研究互聯網世代的學者之一。他說:“其他世代也說過‘不’,但直到現在,這些‘不’才被公司接受了。”
要求新型工作模式的不僅僅是年輕人。像“更少工作,更多生活”這樣懶散的口號已經在社會上深入人心,屬于原職場世界的理所當然之事土崩瓦解,而且和年齡無關。
疫情期間,幾乎半個德國都轉入居家辦公模式,我們發現,很多公司在員工居家彈性工作期間,也運行良好。公寓和辦公室,家庭和工作,按照個人喜好,更緊密地聯系在了一起,老一套“朝九晚五”工作模式的根基松動了。

氣候保護者艾米麗· 福爾克“我一直都很清楚,沒有什么工作是我愿意每周干40小時的。”
新型工作生活平衡已經成為職場現實,也表現在2023年4月,德國最大的工會五金工會宣布,將在鋼鐵行業爭取每周四天工作制,每周工作32小時而不是35小時,并且收入保持不變。這么做也是為了讓這個行業對年輕人更具吸引力。社民黨聯合主席薩斯基婭·艾斯肯甚至要求所有人都每周工作四天。
2023年2月,德國聯邦勞動部長安德莉亞·那勒斯在接受報紙采訪時講到勞動力市場上的新型權力關系。記者問她:“一些年輕人在面試時要求能帶狗進辦公室,而且絕對不加班,你對此有什么看法?”那勒斯冗長的回答以這句話結尾:“辦公室不是跑馬場。”
這引發了激烈的爭論。實際上,那勒斯是想努力理解年輕一代的。她出生于1970年,這代人伴隨著失業的恐懼長大,即使是物理學博士,畢業后也可能要去開出租車。而如今應該感到恐懼的是企業,因為有那么多職位招不到人。
對勞動部長那勒斯來說,一些年輕人公開表示,比起工作,他們更關注自己的私生活,而且有數據表明,德國人的平均工作時長多年來一直在下降,這是一個重大的問題,而她已尋找答案良久。
就在發表那句頗受爭議的“跑馬場”言論之前不久,那勒斯在一次電臺節目中透露,她的床頭書是《世界要滅亡了,我還必須工作?》,作者是數字領域的專家薩拉·韋伯,生于1987年。在書中,韋伯反對“無休止地指責青少年懶惰”,并說出了自己的故事:在一次因工作而身心耗竭后,她開始質疑工作狂文化,得出了應縮短工作時長的結論。
2022年5月,艾米麗·福爾克開始為“健康地球–健康人類”基金會的可持續發展部門工作。從一開始,她就只想一周工作四天。福爾克表示,在面試中,她很艱難地爭取到了這個機會,因為26歲的她沒有需要照顧的孩子或需要護理的家人,不做志愿工作,也不打零工。她和上司商量好了具體的工作時長——每周32小時。
福爾克表示,她想一周工作四天,只是因為她不愿意花太多時間在工作上。每周五,她可以睡個懶覺,做做飯,和閨蜜打個電話,或是沿著萊茵河騎行。福爾克說:“我一直都很清楚,沒有什么工作是我愿意每周干40小時的。”這也是她為碳減排所作的努力。確實有研究表明,工作時長和碳排放量呈正相關。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更少工作的人,收入往往更低,也就更少消費,而這意味著更少的碳排放量。
盧卡·赫克霍夫的生活在12平方米的面積里展開。他在比勒菲爾德的一間合租公寓房里學習、工作。24歲的他是經濟心理學專業的大學生,同時在萊茵根斯公司工作。這家數字代理公司以一天五小時全薪工作制聞名,其創立者——42歲的拉塞·萊茵根斯于2017年秋引入了這一制度。目前,萊茵根斯幾乎完全專注于紐約咨詢業務,其客戶包括貝塔斯曼集團和歐特家博士食品公司。
赫克霍夫于2022年1月成為萊茵根斯的實習生。“當一位教授說到比勒菲爾德一家實行五小時工作制的公司時,我想:我們市還有這么富有革新精神的企業呢!”他發送了一封求職信。實習結束后,他作為大學生助理顧問留了下來,因為這份工作他做得很開心,而且他能彈性工作,靈活地安排工作時間和地點。“我絕對不會去不讓我居家辦公的公司。”赫克霍夫說。

對他來說,這也是工作生活平衡的一部分:在他希望的任何地方工作。2022年秋天,他得以陪同女友去愛爾蘭學習一個學期,上線上講座課,同時繼續為萊茵根斯工作。現在,他又回到了比勒菲爾德,只在他覺得有必要的時候進辦公室,比如新項目啟動時。其他日子他更愿意居家辦公,以免浪費在住所、辦公室和高校間來回奔波的時間。他說:“我希望將來也有這種自由。以后我會成家生子,在陪娃哄睡折騰一整晚后,我希望不用早起踏上通勤路。”
萊茵根斯公司的工作時間是逐漸展現出更大靈活性的。最開始是疫情期間所有人都被要求在辦公室從8點工作到下午1點,到現在很多人已經選擇完全居家辦公。赫克霍夫強調,企業領導們必須認識到,工作效率和工作時長并不能劃等號,重要的不是把職工盡可能久地綁在工位前或是圈在辦公室里,而是讓他們以最高效的方式完成任務,而如何達到這一狀態,員工們自己知道得最清楚。

大學生盧卡·赫克霍夫“我絕對不會去不讓我居家辦公的公司。”
然而,萊茵根斯也意識到了彈性工作制度帶來的挑戰。“我觀察到,包括我在內,部分員工有過度壓榨自己的傾向。”他說。如今,他就像臺考勤機,負責監督他的12名員工,確保他們每周工作25小時,而不是40小時。
此外,完全居家辦公的員工可能沒法和團隊保持緊密聯系。為解決這個問題,赫克霍夫和一位女同事約定每周去辦公室一次。赫克霍夫強調溝通的重要性。他說:“我會提前告訴所有人我的工作地點和時間。”
莫娜·加齊14歲開始學習企業經濟學,16歲時創立了第一家公司。現在,21歲的她已經擁有了第二家公司——奧普提瑪公司,一家幫助企業職員通過軟件交流知識的公司。據調查,在14到26歲的年輕人中,約有1/3被視為工作狂,他們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或學業中,為之付出艱辛的努力。加齊就是其中的一員,盡管如此,她還是會反思工作量多大比較好。
她說,以前,她的智能手機會在下班后響起,度假時也會收到工作郵件,她很難放松自己。她有時覺得很累,無精打采的,晚上也睡不著覺。而現在,她更加注重自身感受和健康,每天都要睡八到九個小時。加齊這樣描述自己的日常生活:“我早上六七點自然醒,先在日記里寫下讓我感恩的事,然后去健身房鍛煉,吃早飯。九到十點,我開始工作,一直到晚上七點。這之后,我常常和朋友們碰面。我們約好,說完各自近況后不再聊任何工作相關的話題。”

企業家莫娜·加齊“九到十點,我開始工作。”
很多企業創始人都夢想著擁有充足的財富和獨特的地位。然而,加齊表示,對她來說,工作生活平衡比財富更重要。她最近在攀巖,還想報個舞蹈課,但都只是業余愛好。
還有一點對她那一代人來說非常典型:加齊在各個地方上班。不久前,她在佛羅倫薩和其他開公司的朋友們碰了面。不久后,她會在華沙待幾天。她公司的總部設在柏林,她在那里租了套公寓,但目前她常常去錫根和父母住。她說,這種自由給了她生活質量,而她也把這種自由給了她的員工。在奧普提瑪公司,每個人都可以自己決定是否去公司以及多久去一次。
如果與經濟學家和招聘專員聊聊互聯網世代,就會發現,沒有人認為年輕人徹底不再愿意努力工作。德國勞動力市場和職業研究所的經濟學家恩佐·韋伯認為,沒有證據能夠證明,如今的年輕人總體來說比前幾代工作得更少。任仕達的《工作趨勢報告》顯示,對于約3/4的18到24歲人群來說,工作一如既往是生活最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
盡管如此,仍有一個明顯的趨勢:年輕人希望依照自己的條件工作,匹配他們的生活和價值。很多人不再愿意像他們的父母那樣加班到崩潰。他們希望有時間留給家人和朋友,自行決定他們何時何地工作多少。不是所有地方都像互聯網行業和辦公室職位這樣容易實現這一點,醫生、護工和教師就不能按自己希望的時間和地點工作。而且,在不實行五金工會要求的全薪四天工作制的地方,工作時間的減少常常伴隨著減薪。
據調查,18到29歲的年輕人中,有超過一半表示他們傾向于比父母花更少時間工作。39%的人認為工作首先是為了保障生存,25%的人將工作描述為“只是實現目標的手段”。工作是為了實現自身價值,激發身份認同?年輕人不太看重這個。
最近,德國伊弗經濟研究所主席克萊門斯·弗埃斯特面試了一位高技能人才。這位應聘的女士說,她最看重工作生活平衡,而且,生活是擺在第一位的,然后才是工作。那么,她應該是互聯網一代的典型代表吧?“并不是。”弗埃斯特回答,“這位求職者剛剛過了50歲生日。”
弗埃斯特表示,如今的員工極其看重休閑時間和工作彈性,和年齡無關。以前,如果在面試時過多地提及工作生活平衡,可能立馬就被判出局了。而如今,更像是企業被人才面試,而不是反過來。
但是,工作時間變少意味著所有人的經濟財富變少。“一個人決定只承擔少量工作,并為此舍棄部分收入,這樣做無可厚非。”弗埃斯特說,“但其后果最終轉嫁給了其他人。”國家靠稅費籌資,如果沒有這些收入,就沒有托兒所、中小學、醫療保險。如今的養老金體系實際上是年輕人在為老年人買單。“如果一代人的工作時間明顯減少,就不可能取得平衡。最糟糕的情況下,養老金體系甚至可能崩潰。”弗埃斯特說。
這也是大部分經濟學家的觀點,縮短工時的做法在經濟界并不受歡迎。那么,如果所有人的工作都變得更加高效呢?技術進步和數字化能夠提供完美的解決方案嗎?大約100年前,英國經濟學家約翰·凱恩斯就夢想著,技術水平的快速發展將使他的孫輩每周只需工作15個小時。每周四天工作制的熱情擁護者們也相信,這種模式雖然減少了工時,工資和稅收卻還能維持原樣,而且員工更有工作動力和工作效率,更少缺勤。
凱恩斯的預測并未成真,工作效率的提升不如他所預期的那樣快。弗埃斯特指出,工業界確實通過技術進步變得更加高效了,但醫院、托兒所和養老院仍然需要人力。護工不能更快速地做完護理工作以便更早回家,現在他們分配給每位病人和老人的時間本來就已經太少。在這些人力嚴重短缺的領域,少量的專業人員理論上需要工作得更多,才能滿足需求。這樣一來,將來可能就沒有人愿意從事這些工作了。而任仕達的研究顯示,如今覺得工作要適應自己生活節奏的,不只有年輕人。幾乎所有受訪者都表示,平衡工作和生活至關重要。絕大多數人都希望能彈性工作,自由選擇工作時間和地點。
德國勞動力市場和職業研究所的專家們甚至因此看到了提高德國人工作總量的方法。他們在一次分析中指出,為解決人員短缺問題,必須提升目前相對較小的在職人群比例,比如女性或者60歲以上的老人。通過更短和更加富有彈性的工作時長,我們可以讓老年雇員更長久地留在職場上。對于女性員工,除了時間上的彈性,還需要給予空間上的彈性,以便她們同時照顧孩子。
在社會學家朱塔·阿爾門丁格爾的理想世界中,男女職工的工作時長變得相近,每周四天,一共32小時。也就是說,男性平均比如今工作得少一些,女性則多一些,讓工作總量基本保持穩定。
編輯:周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