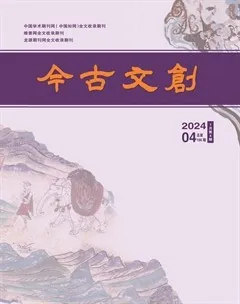《四庫全書總目》著錄提要解讀
【摘要】《四庫全書總目》是中國最大的官修圖書目錄,《分類補注李太白集》作為現存最早的李白集注本收錄于《四庫全書總目》集部;四庫館臣從傳世情況、名目及編次、考證正誤及撰注者生平四個方面對其進行評點。通過考辯,發現由《分類補注李太白集》提要的個案反映了《四庫全書總目》存在考辯有欠精核、評點精練中肯和受正統觀念影響的突出特點。
【關鍵詞】《四庫全書總目》;《分類補注李太白集》;蕭士赟;楊齊賢
【中圖分類號】I207?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4)04-0035-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04.011
《分類補注李太白集》凡三十卷,是元、明兩代相當通行的李白集注解,在明朝經多次翻刻。一般認為,《分類補注李太白集》的刪節本可以分為兩大系統,即郭云鵬校刻本系統和玉幾山人校刻本系統。其中,郭云鵬校刻本系統包括郭云鵬本、霏玉齋校刊本和四庫全書本。郭云鵬認為元版《分類補注李太白集》繁雜,將楊、蕭注刪減大半,《四庫全書》是采用郭本并進行了一定的版式的調整[1]。
《四庫全書總目》[2](以下簡稱《四庫總目》)著錄《分類補注李太白集》于集部卷二,館臣先注明該注本的書名、注本撰者、名目編次,并對其考證功夫進行簡要點評和例證,最后簡要說明注本的撰者姓名、朝代,兼及其著錄情況。《四庫總目》提要中的這段文字既為《分類補注李太白集》作了精要的點評,以供后世參閱,同時也反映出了《四庫總目》中較為突出且具有代表性的學術和思想問題。現將該提要作若干分解,并一一考釋如下:
一、注本撰者及傳世情況考釋
宋楊齊賢集注,而元蕭士赟所刪補也。杜甫集自北宋以來注者不下數十家,李白集注宋、元人所撰輯者,今惟此本行世而已。
館臣在此說明《分類補注李太白集》注本撰者和傳世情況:四庫館臣認為《分類補注李太白集》由宋楊齊賢集注并由元蕭士赟刪補,是宋元人撰注的李太白集中唯一傳世的本子,這和目前學界的觀點基本一致,且表述較為嚴謹。清黃虞稷撰《千頃堂書目》著錄有金王繪《注李太白詩》,注云“繪字質夫,濟南人,天會二年進士”。雖楊齊賢登進士年為宋寧總慶元五年,生活年代顯然晚于王繪[3],王繪所注《注李太白詩》應早于《分類補注李太白集》,但遺憾未能傳世。因此,四庫館臣“今惟此本行世而已”的說法應無誤。
此外,四庫館臣提到“杜甫集自北宋以來注者不下數十家”,四庫館臣認為相較于杜甫集,李白集注數量少、流傳也較少。從對兩家的著錄來看,《四庫總目》著錄李白的相關作品有《李太白集》《分類補注李太白集》和《李太白詩集注》3本,存目1本;著錄杜甫作品則有5本,存目16本。可見,兩家的著錄存目情況是有一定差距的。《李太白詩集注》提要中也提到相關問題:“自宋以來,注杜詩者林立,而注李詩者寥寥僅二三本。”此言不乏客觀性,但是關于李白的注本也有不少的精良本子,除上文所提已失傳的王繪的《注李太白詩》外,還有朱諫的《李詩選注》,胡震亨的《李詩通》等,但《四庫總目》僅收錄三本作品,可見其收錄之少。
四庫館臣看似公允的說法,與《四庫提要》編纂當時乾隆對于“李杜優劣論”的態度有一定聯系:乾隆在《御選唐宋詩醇》中認為“李杜勃興,其才力雄杰,陵轢古今,瑜亮并生,實亦未易軒輊”,但又稱“發于情止于忠孝,詩家者流斷以是為稱首。嗚呼,此真子美之所以獨有千古者矣”[4],可見,乾隆雖認為李杜勢均力敵,但更欲以杜甫忠孝之忱引領朝代之風氣。在這篇提要中,四庫館臣對李杜看似不分優劣的態度中隱約也傳達出左杜右李的傾向,并反映出《四庫提要》作為乾隆朝官方編撰書目批評思想的正統性。
二、名目及編次之考釋
康熙中,吳縣繆曰芑翻刻宋本《李翰林集》,前二十三卷為歌詩,后六卷為雜著。此本前二十五卷為古賦樂府歌詩,后五卷為雜文。且分標門類,與繆本目次不同。其為齊賢改編,或士赟改編,原書無序跋,已不可考。惟所輯注文,則以“齊賢曰”“士赟曰”互為標題以別之,故猶可辨識。
此處館臣結合繆曰芑翻刻的宋本對《分類補注李太白集》的名目及編次進行品評。
繆曰芑,字武子,江南吳縣人。雍正癸卯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李太白集》提要中館臣提到:“宋敏求得王溥唐魏顥本,又裒集《唐類詩》諸編洎石刻所傳,編為一集……國朝康熙中,吳縣繆曰芑始重刊之。”繆曰芑以昆山徐氏所藏蜀本為基礎,于清康熙五十六年校正刊行,世稱繆本。館臣認為楊蕭本“且分標門類,與繆本目次不同”。如今我們對繆本與楊蕭本的名目編次稍作對比便可發現,館臣上述評價較為貼切,楊蕭本的編排相對合理且清晰:
其一,繆本和楊蕭本均將詩歌分為古風、樂府、歌吟等凡二十一類,而繆本前二十三卷為歌詩,后六卷為雜著;楊蕭本前二十五卷為古賦樂府歌詩,后五卷為雜文。
其二,繆本把古風列在了最后一卷,而楊蕭本列在了第一卷,并且沒有給每一首表明次第,而蕭本表明清楚了“其一”“其二”。
其三,編排分卷的方式不同,楊蕭本卷七、卷八均為歌吟,卷九至卷十二均為贈類,卷十三、卷十四都是寄類,卷十六至卷十八都是送類,凡二十五卷。而繆本的編排分卷較為混亂,有時一類的詩分在上卷一半,留在下卷一半,比如第六卷的下半部分是“歌吟上”,而“歌吟下”就放到了第七卷去了[5]。繆本分類和分卷不一致,而楊蕭本相比較而言就相對合理了。
此外,雖然此書究竟是楊齊賢改編的還是蕭士赟所改編的,由于原書沒有序跋已經不可考了,但是在此書的注文中分別用“齊賢曰”“師赟曰”互為標題來加以區別,因此注文出自誰手尚可辨識。在這方面,《四庫提要》對《分類補注李太白集》中批注出處有清晰標識也提出了認可。
三、考證之考釋
注中多征引故實,兼及意義。卷帙浩博,不能無失……此類俱未為精核。然其大致詳贍,足資檢閱。中如《廣武戰場懷古》一首,士赟謂非太白之詩,厘置卷末,亦具有所見,其于白集固不為無功焉。
以上所引中,四庫館臣對楊、蕭注進行了整體評價,即認為其注雖有一定貽誤,但多旁征博引,內容翔實且值得閱讀,仍較具有文獻價值,評價主要可以分為三個層次進行解讀:
第一,注釋方法。館臣認為“注中多征引故實,兼及意義”,即注本多采用“征引式”的注釋方法來補充注解,幫助讀者理解原文,并結合自身對李白詩本意的發明。明胡震亨對此本的注釋方法批評云:“蕭之解李,無一字為本詩發明,卻于詩外龐引傳記,累牘不休。”胡震亨對其注釋時大量征引故實提出批評,認為大多無關詩意,而四庫館臣對此認為“大致詳贍,足資檢閱”。清代考據學快速發展,四庫館臣多重考據,蕭注“多征引故實”的文獻學價值得到認可尚在情理之中。
第二,考據正誤。館臣認為楊蕭本卷帙浩博,因此在征引故實時,有時缺少了對于詩歌及史料出處的精細考證,導致內容有一定貽誤。館臣主要舉出了兩個例子:
一是關于《寄遠》七首一詩。在元版《分類補注李太白詩》中楊齊賢和蕭士赟的注分別為:
齊賢曰:舂陵,漢江,見前。《法華經》云:佛言舍利弗汝于來世當得作佛,號曰花光。王仲宣詩:風流云散,一別如雨。
士赟曰:《楚辭》:秋草榮而將實。謝瞻詩:開軒滅華燭。古詩:被服羅衣裳。曹植詩:羅衣何飄搖。一本“暉”下添云“昔時攜手去,今時流淚歸。遙知不得意,玉箸點羅衣。”
以目前通行的文淵閣版《四庫全書》影印本為例:文淵閣版《四庫全書》收錄的《分類補注李太白集》[6]中《寄遠》一詩注為:
一本“暉”下云“昔時攜手去,今時流淚歸。遙知不得意,玉箸點羅衣。”齊賢曰:舂陵、漢江見前。
明人唐覲在延州筆記中指出“滅燭解羅衣”一句是出自《史記滑稽傳》“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四庫總目》收錄的注本并沒有“謝瞻詩……曹植詩……”一段,故有學者認為四庫館臣在論述楊蕭本注釋正誤時可能只是借鑒了明人唐覲的看法進行評判,并非單純發自一本被刪節的注本[1]。
二是關于《臨江王節士歌》一詩。《漢書·藝文志》中云:“《臨江王》及《愁思節士》歌詩四篇。”即《臨江王》與《愁思節士》二者并列,南朝陸厥作《臨江王節士歌》,是對上題的誤合。庾信賦詩云“臨江王有愁思之歌”也是沿襲了這個誤合,李白此詩亦是誤合。而楊蕭二人并沒有在注中指出相應錯誤,都是沒有對內容進行仔細核查的緣故。
第三,總體評價。四庫館臣認為《補注》總體對李白詩進行了較為細致的校讀,值得查閱,對李白的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貢獻,這是從文獻學角度做出的較高評價。館臣對此舉了《登廣武古戰場懷古》一例,但是館臣之語仍存疑。元版《分類補注李太白詩》下作注:
齊賢曰:……太白謂籍沉湎于酒,狂言妄呼,如嗤嗤之氓,不足據也。
士赟曰:余曰:“此非太白之詩也,先儒所謂偽贗之作也。”……曰:“……太白有識者也,肯作此等語乎!吾故曰此非太白之詩也。”
蕭士赟從李白語意、見識、用意風格等方面指出此詩非李太白之作,可作為判斷之參考,可見其注在旁征博引為頗有自己的見解;而文淵閣版《四庫總目》中并無蕭士赟注的內容,而館臣卻稱“中如《廣武戰場懷古》一首,士赟以為非太白之詩,厘置卷末,亦具有所見”。同樣,此處館臣是參考了不同版本的刪節本并依據其他本子進行評價,還是借鑒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尚存疑,后人評閱時尚需仔細甄別。但其對蕭士赟這一發現為文獻學做出的“其于白集不為無功矣”的大體判斷還是有理的。
總體來說,《四庫總目》對《分類補注李太白集》在考證方面的點評是客觀的:《四庫總目》對于《補注》的批評主要在于其考證方面的不夠精細,然而考慮到《補注》卷帙浩繁的客觀事實,《四庫總目》稱其“大致詳贍,足資檢閱”的評價是比較準確且不為苛刻的,且對其“于白集固不為無功”的價值判斷也不失中肯。
四、作者之考釋
士赟字粹可,寧都人,宋辰州通判立等之子。篤學工詩,與吳澄相友善。所著有《詩評》二十余篇及《冰崖集》,俱已久佚,獨此本為世所共傳云。齊賢字子見,舂陵人。
這段中四庫館臣記錄了撰注者的生平。
館臣記載認為,蕭士赟字粹可,所著有的《詩評》二十多首以及《冰崖集》,都已經佚失很久了,只有《分類補注李太白集》一本流傳于世。據胡振龍所考證,《四庫提要》關于蕭士赟著述的說法并不完全可信,主要存在兩個錯誤[7]:一是將詩評二十篇誤為書名,“評詩”是指其言說內容為詩評,而不是著作的名稱為《詩評》,蕭士赟評詩的內容約有二十多條,編集名為《粹齋庸言》。二是將蕭士赟之父蕭立的詩集《冰崖集》誤認為是蕭士赟所作,從《故縣尹蕭君墓志銘》“君之父諱立之,詩宗江西派,絕句有唐人風致,其集曰《冰崖》”可知《冰崖集》為蕭士赟父親所作。
楊齊賢字子見,舂陵人。楊齊賢其人,史書無傳,僅能在部分文集中窺其生平梗概。在《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中稍詳細記載楊齊賢生平:“楊齊賢,宋寧遠人,字子見。寧宗慶元五年進士。官至通直郎。穎悟博學。有《分類補注李太白集》。”明高儒《百川書志》:“楊齊賢《集注李白詩》二十五卷。”[8]舂陵,是寧遠東北處一地,故楊齊賢又稱楊舂陵。楊齊賢其人生平在眾多書目中僅能尋得少許材料,《四庫全書總目》中無較為詳細的記載亦在情理之中。
由此可以看出,雖然《四庫全書總目》集中國古典目錄學之大成,對撰注者的生平情況收錄記載較為完善,但依然時有訛誤。受編纂時的物質條件、信息手段等因素影響,《四庫提要》在文獻、史跡等存在一些問題,需要后人結合多方史料再進行考證、辨析。
五、總結
由《分類補注李太白集》的個案反映出了《四庫總目》一些突出且有代表性的特點,歸納如下:
(一)考辯有欠精核
編撰《四庫總目》的館臣在對于史料的考述方面存在較多漏洞,部分考證是在其史料視野較為有限的情況作出的,如對《冰崖集》作者的張冠李戴顯然是由于其史料搜集有限,未得見相關記載而導致的。此外,四庫館臣在論述著者得失時較多借鑒他人成果,并非單純出于自己的思考且可能未經仔細考辯,雖可以作為今人研究考證資料和正誤的參考,但是使用時需加以仔細甄別。
(二)評點精練中肯
《四庫全書》的編纂是一項國家主導的采集、整理并評價中國文學史中重要遺產的活動,館臣作為知識學人對著作有較為精練且準確的評價,盡可能從名目及編次、批注及考辯功夫、集注者等多角度進行客觀精煉的評點。總體來說,館臣在著錄時自覺將詩文評和史評分開,評點時語言簡明扼要,注重與不同版本的比較,重視對編者考據功夫的褒揚,并將著錄編撰的客觀條件納入考量范圍,體現出了評點的自覺學術規范和清代學術的考據學轉向。
(三)受正統觀念影響
劉婷和張麗玲認為,《四庫全書》的編纂是皇權對地方政權或知識群體忠誠度的一次考察,是皇家權力與知識整理者的一次思想碰撞和學術合作[9]。《四庫總目》作為清代官學的產物,受官學性質的制約,四庫館臣在收錄著錄和語言評價等方面不能做到完全的公允。以《分類補注李太白集》為中心,聯合《李太白文集》《李太白詩集注》及杜集的著錄情況來看,可以看出在提要編纂時,評點的體系和思想是與清王朝政治和思想統治需要緊密相連的,始終為最高統治者的意旨服務;四庫館臣在收錄李杜注本并進行評點時呈現左杜右李的傾向即可作為佐證,即館臣所言:“圣裁獨斷,義愜理精,非館臣所能仰贊一詞者矣。”
參考文獻:
[1]張佩.楊齊賢、蕭士赟《分類補注李太白詩》版本系統研究[M].北京: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
[2]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M].北京:中華書局,1965.
[3]胡振龍.史書閱讀與李白詩歌的史傳思維特征[J].綿陽師范學院學報,2022,41(04):10-16+31.
[4]乾隆.御選唐宋詩醇[M].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5]詹瑛,楊慶華.《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及其不同板
本[J].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7,(04):1-10+18.
[6]永瑢,紀昀等.文淵閣四庫全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7]胡振龍. 《四庫提要》 “分類補注李太白集”條辨正[J].中國典籍與文化,2022,(03):112.
[8]高儒等.百川書志 古今書刻[M].上海: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
[9]劉婷,張麗玲.《四庫全書》編纂思想探析[J].四庫學,2022,(01):49-63+166.
[10]申風.李集書錄下載[J].李白學刊,1989,(03).
作者簡介:
孫潘懿,女,漢族,江蘇昆山人,蘇州大學,本科,主要從事明清文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