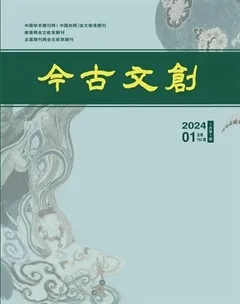不能忽視的形象
張楚鈺
【摘要】《百合花》是一篇形象塑造鮮明的小說,探究主要人物形象及所蘊含的人性之美是把握其主題的關鍵,一直以來都是文本研究的重點。抒情主人公“我”雖然不是小說的主要人物,但在結構上承擔了敘事視角和情節線索的任務,在內容上又具有烘托主要形象、點化主題內涵的作用,具有一定的研究價值。
【關鍵詞】《百合花》;人物形象;文本解讀
【中圖分類號】I207?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4)01-0013-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01.004
《百合花》是一篇以戰爭為題材的小說,敘寫了通訊員、新媳婦和“我”三人在包扎所附近發生的動人故事,塑造了充滿人性光輝的形象,贊美了戰爭時期真摯的人際關系,表達了作者在特殊年代對真情的呼喚,具有深刻的教育意義和審美價值。整理相關研究資料可以發現:現有研究多集中于探究新媳婦和通訊員的人物形象,分析小說敘事手法,解讀文本意象以及主題內涵幾個方面。雖然內容豐富,形式多樣,但對次要人物“我”的關注卻相對不足。部分研究者能看到“我”的敘事作用,但對“我”在小說內容表達上的意義關注不夠。實際上,準確把握“我”的形象意蘊及表達作用能夠幫助讀者抵達文本深層,更為深刻地感受到小說的情趣魅力。
一、從文本中解讀“我”的人物形象
茹志鵑談《百合花》創作時曾表示:“我寫《百合花》的時候,正是反右派斗爭處于緊鑼密鼓之際,社會上如此,我家庭也如此”,“我不無悲涼地思念起戰時的生活和那時的同志關系。”[1]作者親歷過戰爭,面對當時的社會氛圍,無不懷念戰時同志間真誠的感情。她希望以寫作展現人性美好,呼喚被扭曲的親密人際關系,那么如何以戰爭題材敘寫人性主題就成了創作的首要問題。對此,作者選擇以女性特有的溫柔筆觸去書寫戰爭里的溫情點化主題。在此基礎上,作者刻畫了一個文工團的女兵形象,從女性視角出發去講述這一清新俊逸的故事。“我”是小說的敘述者,又是參與者,文本內自然包含了“我”的主觀情感。讀者以“我”的視角閱讀小說,首先就要理解“我”的形象特征和思想情感,這樣才能真正進入故事深層。
“我”是一個性格倔強要強的文工團女兵。從身份上看,“我”自然比不上長期四處傳遞消息的通訊員體力足。在去包扎所的路上,“我”因腳傷路滑走得慢,既因趕不上通訊員而著急,又不愿叫他等,怕他用性別偏見來嘲笑自己,兀自對他生起氣來。這樣的心理活動能看出“我”雖是女性,但面對男性的體力優勢,依然不愿示弱的要強性格。除此之外,“我”看到通訊員背向我遠遠地坐下,“好像沒我這個人似的”,“我曉得這一定又因為我是個女同志的緣故”,便“帶著一種反抗情緒走過去,面對他坐下。”面對男女性別隔閡,“我”不僅沒有不好意思,而且還敢于表達自己的反抗,突顯出“我”作為一個女兵的自尊心和倔強。
“我”是一個活潑大方而心思細膩的女性。雖然不滿通訊員的態度,但在進一步觀察他,特別是知道他是自己的同鄉后,“我”對這個年輕人產生了濃烈興趣,交流中表現得落落大方,體現了“我”性格的開朗。同時,“我”能夠注意到通訊員槍筒里用來做裝飾的樹枝和菊花、他肩頭被鉤破的布片以及他“繃著臉、垂著眼皮、憨憨地笑了一下”等一系列的微表情,都表現出“我”對通訊員的記掛與關懷,也體現出“我”心思的細膩柔和,為文章增加了幾分情味,于無聲之處襯托人性主題。
“我”是一個成熟穩重且思想覺悟高的革命者。面對團長的安排,“我”表示“包扎所就包扎所吧!反正不叫我進保險箱就行”,能夠看出“我”對因女性身份而被派去戰后的安排有些不樂意,但只要能為革命盡一份力足矣的革命奉獻精神。這時“我”主動將革命者的身份放到首位,而女性身份則默默隱藏其后。同通訊員進村借被時,“我”能快速借到棉絮,了解到通訊員借被失敗的情況后,又馬上親自去與新媳婦溝通,害怕“得罪了老百姓影響不好”,說明“我”對軍民關系的看重,善于與群眾溝通,在處理事情上更為穩重理性。從這些細節中展現了“我”思想的成熟和對革命的熱情,是政治思想覺悟較高的革命者。
二、從敘述結構上看“我”的作用
《百合花》是高中語文必修上冊的第一篇小說,其單元導語明確寫到“把握小說敘事和抒情的特點,體會詩歌和小說的獨特魅力”。本篇小說在敘事上不同于十七年文學主流的戰爭宏大敘事,即一種“在時間和空間上受到嚴格限制的小敘事”[2]。這種“小敘事”來自作者對小說情感主題的準確把握。她無意去展現波瀾壯闊的戰爭史詩,只想探尋生活本身,挖掘人性中深層次的光輝,帶給讀者真切的審美體驗,因此對生活本真的細致刻畫才是其創作追求。事實上,將“我”作為敘事視角,以“我”的所見所聞和情感變化作為敘事線索,從空間上把故事舞臺限制在包扎所這一小地點,從時間上將一天中三個非連續的情節片段串聯在一起,正是作者達到寫作目的的巧思。
(一)“我”是敘事視角
小說幾乎是從“我”的視角來敘寫的,屬于第一人稱內聚焦敘事。第一人稱“我”的使用,將敘述者與讀者的心理距離縮小,增加讀者對人物敘述內容的信任,給讀者真實感和代入感,增加了人性主題的表達力度。熱奈特在《敘事話語》中提出了三種聚焦模式,他認為“內聚焦的特點為敘述者僅說出某個人物知道的情況,可用‘敘述者=人物’的公式來表示”[3]。這種敘事視角的選擇限制了讀者信息獲取的范圍,所了解的只源于“我”的見聞,從而造成了小說一定程度上的敘事留白,增加了讀者的想象空間。例如通訊員初次向新媳婦借被時,由于“我”的參與缺失,導致這次互動一筆帶過。通訊員為何第一次沒有借到被子?他和新媳婦之間發生了怎樣的談話?這些讀者都不得而知,只能根據“我”與通訊員的互動推測兩人由于性別差異導致的尷尬,想象還原兩人初次見面的對話,填補小說的隱藏內容。值得一提的是在戰爭題材的小說中,英雄犧牲情節通常被作為故事高潮,但本文別出心裁地通過限制視角將這一情節省略,由擔架員的轉述簡單告知讀者情況,轉而精心刻畫通訊員犧牲后眾人的反應,自然而然地突出人物的情感碰撞,增加了主題表達的力度。
對《百合花》而言,內聚焦敘事除了能增加小說敘事留白,由于“我”特殊的人物身份,還起到了限制故事發展空間的作用。由于女性身份,“我”被派到包扎所工作,導致故事一開始就被鎖定在戰場后方,實現了戰爭題材小說對正面戰場回避,舒緩了戰爭緊張的氛圍。茹志鵑曾說:“我特別注意從生活中發現富有深刻思想的有閃光的東西。”[4]《百合花》以“我”的視角限制故事舞臺,將被戰爭宏大題材遮蔽的生活小場景擴展開來,開掘人與人之間樸質深沉的情感正體現了她獨特的創作風格。
(二)“我”是敘事線索
《百合花》主要敘述了三個故事情節,可以用三個短句進行概括。首先,“我”與通訊員在前往包扎所路上結識;之后通訊員與“我”進村借被,與新媳婦發生誤會被解決;最后,他為救戰友犧牲,“我”看見新媳婦將百合花被獻給通訊員。可見整個故事是依據“我”的行動軌跡不斷向前發展。“我”既是小說的視角人物,也是線索人物,將相對零散的情節片段串聯到一起,形成較為完整的故事脈絡,因此“我”的見聞是小說的明線。
與此同時,小說還存在一條暗線,巧妙地隱藏在文本內推動劇情發展,那就是“我”對通訊員的情感變化。故事開篇寫道通訊員總是“把我撩下幾丈遠”,“我”怕自己跟丟到不了包扎所而對他生氣。最初由于“我”不了解通訊員,情感傾向是埋怨責備的。但后來“我”發現通訊員表面疏遠自己,但實際上有著笨拙的體貼,特別是后來同鄉身份的發現讓心理距離得以縮短,“我”開始對他親近起來。借被時,通訊員雖有冒失幼稚的一面,但又心思單純地想要補救。“我”看到了他作為年輕人任性又善良的一面,“已從心底愛上了這個傻乎乎的小同鄉”。至此,“我”對通訊員的感情經歷了生氣、好奇到最后喜愛的三個階段,隨著“我”對他的了解越多,感情愈加濃烈,也就為后來情感高潮做了鋪墊。
在內視角下,“我”的情感變化,也就是讀者的心理變化。敘述者在敘述時有主觀情感注入,那么“讀者也會順著敘述者的情感傾向產生認同,進而把握人物形象及心理情感。”[5]“我”的情感流動是故事發展的暗線。讀者在“我”的引領下逐漸認識通訊員,最終取得窺見小說的情感主題內核。
三、從表達內容上看“我”的作用
《百合花》的三個主題,即軍民情深、人性美好和青春生命都集中體現在通訊員和新媳婦的交往中。小說的高潮結局也都圍繞兩人展開,他們是小說的主要人物,也是理解小說主旨的重點。但“我”作為小說的次要人物,在內容表現上也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閱讀時同樣值得關注。
(一)烘托主要人物
“‘次要人物’的存在,將主要人物形象襯托得更加鮮明。”[6]“我”對通訊員形象的襯托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反襯出他性格中的青澀忸怩,二襯托出他對革命的熱情。在“我”與通訊員互不認識的情況下,通訊員因性別隔閡一直與“我”保持距離。當“我”靠近并同他對話時,他“立刻張惶起來”,“臉漲得像個關公”一連串神態描寫為讀者呈現出一個清純羞澀的小戰士形象。此處“我”的侃侃而談與通訊員的坐立不安形成鮮明對比,更襯托出他未經世事的青澀。作者借“我”之力將通訊員的普通一面塑造地越生動,當他犧牲時展露出的英雄品質就越令人動容。其中那震人心魄的感染力才能喚醒最純質的人性美好。
其次,當“我”邀請通訊員同去時,他躊躇地答應了。“躊躇”的神態能品讀出通訊員的心理矛盾:他因性別關系不想與“我”單獨行動,但又從大局考慮選擇答應。即使借被受到委屈不愿再見新媳婦,但被提醒群眾影響后,他又馬上“松松爽爽地帶我走了”。這些行為細節都能反映通訊員不拘泥于個人情感的革命大局觀。作者不僅用細節塑造了“我”的革命形象,還突出了通訊員識大體顧大局的革命精神。從不同層面對他進行性格塑造,讓人物形象更加豐滿立體,充滿人性光輝。
對新媳婦的襯托,首先體現在她靦腆的女性形象上。“我”與新媳婦同為女性,但與通訊員的相處情況卻截然不同。“我”對他是毫不拘謹地開玩笑,新媳婦是不好意思地扭著頭笑他,兩相對比足以表現新媳婦的羞澀靦腆。對于幫傷員擦身的事務,我是“做這種工作,當然沒什么,那些婦女又羞又怕,就是放不開手來,都搶著去燒鍋,特別是那新媳婦”。這里“我”與男性的接觸自然,更反襯出新媳婦的保守思想,與她后來超越性別隔閡為通訊員擦身的行為形成反差,為人性主題的表達埋下伏筆。
其次,同為女性的“我”更能觀察到新媳婦的內心世界,從細節中表現她純粹的人性美。通訊員犧牲后,“新媳婦依然拿著針,細細地、密密地縫著那個洞”。此時“我”看到新媳婦的動作是“細細地、密密地、一針一針地”,這些形容詞足見她對待此事的極度認真。新媳婦表面在縫補破洞,實際是在表達內心的愧疚與敬意。她沒想到這位害羞的“同志弟”能有這樣的勇氣,后悔對他的調笑,后悔沒有為他補衣服,更對鮮活生命的倉促消失感到痛心。這些情緒對內心震顫的新媳婦來說難以言表,只能通過行動來表達。新媳婦與通訊員雖只有一面之緣,但卻能真誠待他,尊重這個勇敢的生命,這是新媳婦至純至美的真情流露,充滿了人性的光輝。面對小同鄉的離去,“我”同樣悲痛不舍,與新媳婦產生了情感共鳴。這樣心思細膩的“我”比周圍人更能察覺到她沉默行為背后的洶涌澎湃,從而捕捉到“細細、密密、一針一針”等飽含情緒的細微動作,從而點化新媳婦如百合花般的純美形象。
(二)點化情感主題
小說圍繞著“百合花被”敘寫了一則戰爭中的溫情故事,表面上體現軍民情主題,深層則歌頌人性之美,奏響了一曲青春與生命的贊歌。小說故事中“我”雖然是次要人物,但也能起到點化主題作用。
對于軍民情主題,“我”充當了軍民間交流的橋梁。由于“我”拜托通訊員進村借被,他才與新媳婦有所交際產生后續故事。在兩人產生誤會時,“我”開導通訊員,并同新媳婦解釋借被原因,才化解了兩人誤會。正是因為“我”的調解,兩位軍民代表才能進一步產生情愫,軍民情主題才能自然呈現。
對于人性美的歌頌,除了新媳婦那超越物質的人性光芒外,“我”對通訊員的復雜情感也能增加人性主題的厚度。“我”和通訊員僅在中秋節這天有所交際,盡管時間短暫,但卻產生了深厚情誼。文中寫到“我已從心底愛上了這個傻乎乎的小同鄉”,稱呼中的“小”字暗示著“我”將他作為小輩看待。“‘我’帶著類似手足之情,帶著一種女同志特有的母性來看待他、牽掛他。”[7]因此“我”所說的愛,不是男女之愛,而是一種類似于長輩關愛晚輩的親情。通訊員犧牲后,小說對“我”描寫不多,但從細節看依然能體會“我”的痛心。“我強忍著眼淚”,“想看見他坐起來,看見他羞澀的笑”,這眼淚深藏著對戰友犧牲的悲痛,對同鄉勇氣的敬佩和對生命早逝的嘆息。作者曾說“戰爭使人不能有長談的機會,但是戰爭卻能使人深交……就在這個一剎那里,便能夠肝膽相照,生死與共。”[1]僅一面之緣的新媳婦與通訊員是如此,“我”和通訊員的情感也是如此。雖從表達效果上看,兩人間的感情并不是小說刻畫的重點,但依然能點化人性美的主題。
“我”雖然不是核心人物,但卻能成為理解小說主題內涵的突破口。讀者從“我”的視角去閱讀小說,把“我”的見聞作為理解線索,解讀三人的形象特征,品味人物間真摯的人情美,還能從敘述層面去解讀小說,搭建起理解小說主題的雙層階梯。可見,探究“我”的文本作用能夠找到小說情感密碼,從而領會作品文字下涌動的綿綿情思。
參考文獻:
[1]茹志鵑.《百合花》的寫作經過[J].語文教學與研究,1996,(05):3-4.
[2]徐志豪.論《百合花》中的“小敘事”[J].今古文創,2022,128(32):19-21.
[3]申丹.對敘事視角分類的再認識[J].國外文學,1994,
(02):65-74.
[4]茹志鵑.生活經歷和創作風格[J].語文學習,1979,
(01):15-17.
[5]盧昶波.《百合花》第一人稱內聚焦敘事賞析[J].名作欣賞,2021,739(35):128-130.
[6]郜元寶.無材可去補蒼天——怎樣看小說的次要人物[J].小說評論,2015,(05):31-36.
[7]茹志鵑.我寫《百合花》的經過[A]//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茹志鵑研究專集[C].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