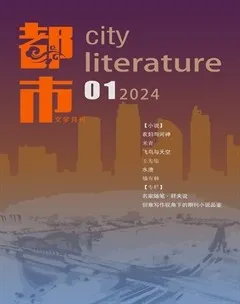生活和藝術的距離
李葦子,2007年開始文學創作,作品散見于《當代》《花城》《大家》《青年文學》《鴨綠江》《西湖》《山西文學》《黃河》《湖南文學》等純文學刊物。有作品被《北京文學·中篇小說月報》《海外文摘》《視野》《教師博覽》等雜志轉載。著有小說集《歸址》。晉中信息學院創意寫作教師。
生活就像一片片零散的葉子,藝術將這些葉子串聯起來,攢成一棵搖曳多姿的樹,樹上有枝,有葉,有花,有鳥巢。對于小說來說,這個從葉片到樹的過程,便是虛構。王安憶曾在《虛構與非虛構的》演講中如是說:藝術還是應該到藝術里找,生活不會給你提供藝術,生活提供的只能是一個掃興的結果,一個不完整的故事。
關于生活和藝術的距離,我們不妨借用《最后的晚餐》進一步闡明。拋開作品的宗教指涉性不談,最基本的信息是:一群人在吃晚飯。畫面中,一字排開的人皆坐在桌的同一側,即,觀眾的正對面,除了c位的男性以正面示人,其余皆是側面或半側面。這根本不符合現實生活的真實面貌。在現實中,無論是長條桌還是方桌、圓桌,人們都是繞圈而坐。但是,假如完全照搬生活,按照一點透視的原理,c位的男性將成為離觀看者最遠的一個,相應地,他在畫面中的占比最小,那就徹底違背了創作者的初衷,也影響了構圖的和諧,藝術的主體性喪失殆盡,淪為生活的奴仆。
這便是“藝術來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最生動的例子。
探討這個問題的目的不是這個問題本身,而是想厘清長久以來困擾我的問題——什么樣的小說才是好小說?作家該如何處理生活和小說的關系?離生活太遠,小說會變成奇觀,靠過度擴張的情節會削弱作品的嚴肅性,而緊緊貼住生活(這似乎是當下倡導的一種創作態度),小說就變成生活的鏡像還原,變得瑣碎無聊,藝術性蕩然無存。大概,正是因為后者的泛濫,才有了這樣一種抱怨:看小說不如看非虛構。
相比書寫當下經驗的故事,我們更愿意看過去的事情,相比國內作家的作品,我們更愿意親近國外作家的作品,這是不是恰恰說明了一點,陌生經驗的重要性?在構成一個好故事的諸多必要條件中,獵奇到底有沒有一席之地?也許,“獵奇”的表述太言重,我們不妨還是用陌生化吧。問題的關鍵在于陌生化的程度,我想起王祥夫老師的一個短篇小說,包工頭想睡一年輕民工的女朋友,最后帶著女人爬上了高聳入云的建筑工地的塔吊,在那間狹小的操作間里顛鸞倒鳳。包工頭、女朋友、工地和塔吊,這些素材本身沒有任何陌生性,然而,組合在一起后卻出現了陌生效果。盡管我們都知道這是虛構的故事,但我們依然深信不疑,知道虛構和深信不疑,會不會就是藝術和生活之間的距離?
生活中,吃飯是為了填飽肚子,但是,假如在小說中用到了吃飯這一素材,吃飯就不再和飽腹有關,而是為了引出別的東西,或遇見一個推進情節進展的人,或發生一件重要的事。卡夫卡為什么讓格里高爾變成甲蟲而不是患病或工傷?大抵正是因為后者離生活太近,前者離生活較遠,它像一枚大一號的針,更能刺激人們麻木的神經,人變成甲蟲聽上去過于奇觀,但是接下去,作者用現實主義手法營造出一幕幕真實無比的生活場景,將二者之間的間隙做了彌合,讓這一虛構具有了穿透現實的力量,而不是滿足對生活的簡單還原。
金暉的《在閣樓上唱歌》(《青年文學》2019年第2期)篇幅不長,大約只有六千多字,這個小說比較符合我心中好小說的標準。首先來說說作者的空間營造。故事發生地是一個江南小鎮,對于我這個北方人來說,杏花煙雨江南幾乎就是文學的代名詞。“南方梅雨季節帶來的水汽還沒有完全褪盡,薄霧像輕煙一樣在南方低矮的屋檐間若隱若現,偶爾一陣風吹來,輕盈得像鳥過枝頭,一下就沒影了。”這個描述讓我想起蘇童的“香椿樹街”,潮濕和神秘,還帶著一點兒腐爛的味道。《在閣樓上唱歌》里的街道有個極富詩意的名字“蓮池巷”,可是,在這詩意的表象之下是一個凌亂、骯臟、治安很差的地方,“經常有警車呼呼地開進小巷來,抓了人后又呼呼地開走”。還有一群如嗜血動物般專門以刺探別人隱私取樂的可怕的當地人。這可真是對“出淤泥而不染”的蓮的莫大諷刺。第三個空間是閣樓。我們總是在江南作家的筆下看到這一重要意象,狹窄的空間,晦暗不明的光線,樟腦的味道,木地板,舊家具,老物件,一個時髦的女人站在閣樓上聽唱片。這大約是骯臟的“蓮池巷”上唯一的凈土。魯迅先生說,悲劇就是把美好的東西撕碎了給人看。蓮池巷的人們似乎深諳其道,他們果然聯手將這個女人的生活踩到了泥土中。“盡管知道秋喜和蓮池巷的女人相處得很好,但后來看到她們像惡狗一樣狠狠地向她進攻時,我并不感到意外。我說過,我們蓮池巷的人是有欺負外鄉人的習慣的,這也是他們日常的生活內容之一。”可怕的恰恰是那個“我并不感到意外”,這是比偶發的暴力事件更深層的暴力,是一種如皮癬般揮之不去的惡疾。
我先總結一下這個部分,我想說的還是藝術和生活的距離,江南小鎮、蓮池巷、閣樓三個空間讓我陷入遙遠的遐想,它們是陌生且極富詩意的,而填充材料的樸素又將我拽回到日常生活的真實,甚至是殘酷。
蓮池巷的生活本來是單調無聊且重復的,突然有一天,一個普通的三口之家“突兀地出現在這塊執拗而閉塞的”小鎮上,這可真是朝饑餓的狼群中投擲出了羔羊。現在,一組對立關系出現了:本地人和外地人,土著和新人類,傳統與現代,守舊與新鮮,不變與變。這是一個很大的主題,一個永恒的、世代作家都在書寫的歷久彌新的主題,金暉能用一個篇幅極短的小說表現這一主題,是我喜歡這個小說的第二個原因。
女主角秋喜是個漂亮、時髦又充滿神秘色彩的人,神秘之處主要集中在她有那么多漂亮衣服,卻從來不出門工作。她的美和漂亮衣服讓鎮上的女人們瘋狂。“雖然他們對外鄉人心里總是隔隔的,但女人們天性總是愛美的,于是她們就去找秋喜取經。”這是一群實用主義至上的現實的人。但是,實用主義還有另外一個特點,那便是用完即棄。當人們再也不能從祥林嫂那里消費到快樂時,祥林嫂便會被貼上不潔的標簽打入遺忘的冷宮。秋喜則是另一極的祥林嫂。對一個女人最大的傷害莫過于罵她是個蕩婦,而妓女則是蕩婦里最淫蕩的那類。于是,當地人用自己的陰暗給秋喜的“不尋常”找到了最心安理得的答案——她是個暗娼。這句話最終由一個小孩說出來,原本最純潔無瑕的孩子,說出一句如此惡毒的話,我們當然知道孩童背后的操縱者是誰,總之,這是一把邪惡的鑰匙,打開了潘多拉的魔盒,將仇恨、嫉妒、罪惡統統釋放出來,人性之惡像蝙蝠一樣布滿蓮池巷的上空,讓一個無辜的人找不到容身之所。劉慶邦在北師大的一次講座中說,好的小說總是人性大于社會性,人性足夠深刻,小說也就具有了社會性。這是我喜歡這篇小說的第三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