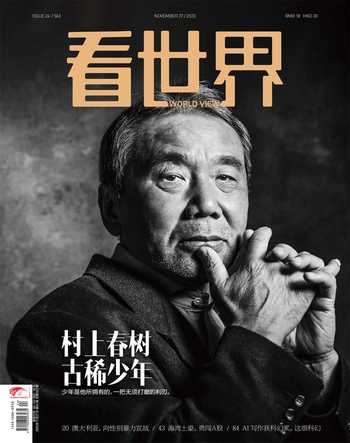AI寫作獲科幻獎,這很科幻
徐乃帥

在劉慈欣的科幻中篇《詩云》中,超級文明的個體“李白”,為了超越人類詩詞藝術的巔峰,打算“把所有的詩都寫出來”。于是,“李白”消耗了整個太陽系的物質,創造出“一片直徑一百億公里的,包含著全部可能的詩詞的星云”,即“詩云”,以此宣告—技術超越一切文學。
如此圖景,猶如技術浪漫主義者對文學本身的顛覆、反諷,又隱含了仿若克蘇魯神話式的寓言:某種絕對強大的媒介,以蔑視的姿態碾碎了人類思想文化的精粹。所謂“詩云”,儼然是一團指向“文學”的混沌深淵,以一種令人不寒而栗的方式,“混淆”了技術與文學的邊界。
今年10月,一篇“100%由AI創作”的名為《機憶之地》的小說,獲得了江蘇青年科普科幻作品大賽的二等獎,被稱為“文學史上首次”—不得不說,這本身就是一句相當科幻的敘述。
AI或將引領文學“革命”?
據了解,這篇小說是清華大學新聞學教授沈陽通過對話形式,逐步提示AI創作而成的。他指定了卡夫卡風格,經過66次對話,輸出約43061個字符,從中復制出5915個字符,完成了《機憶之地》的參賽版本。縱觀這篇小說,它有著相當新穎的構思和一個引人入勝的開篇。
“這是一個有趣的嘗試。”據主辦方介紹,在作品征集階段,他們了解到沈陽正在嘗試用AI創作小說,就向其發出了邀請。這篇由AI生成的作品,混在普通參賽作品中,交到了6位不知情的評委手上,只有一位評委看出了其中的“AI味兒”。最終,《機憶之地》以高票獲得了大賽二等獎。
AI創作的作品獲得文學獎項,足以成為AI寫作技術發展過程中,頗具標志性的一幕,證明AI寫作技術已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同時,它也引發了近期文學界關于“人的文學和AI的文學”的探討。

小說《機憶之地》的AI插畫
本是關于概率論的命題,成為了AI寫作的絕妙預言。
實際上,相比對傳統文學界的沖擊,自從去年ChatGPT橫空出世,國內的各種相關產品如雨后春筍般接連涌出,早就有不少網文作者嘗試將其應用到寫作當中—對于他們而言,AI寫作并不陌生。
而在當今時代,在被傳統文學圈子刻意忽視的區域,網絡才是“文學”最前沿、競爭最激烈的舞臺。
今年7月,“閱文創作大會”于成都召開,閱文集團展示了國內網絡文學行業首個AIGC(生成式人工智能)寫作輔助大模型,以及基于這一大模型的應用產品,它可以幫助作者在世界觀設定、角色設定、情景描寫和打斗描寫等方面豐富細節,生成大段補充內容,從而輔助創作。
顯而易見,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強勢入場,以及日后的優化迭代,在寫作效率攸關生死的網絡文學領域,極有可能會引發一場新的“革命”,無法跟上趨勢的作者將被逐步淘汰,唯有緊跟潮流,才能享受新一輪技術紅利。
值得思考的是,人們借助AI進一步解放想象力和創作力的同時,這是否也意味著作者主體性的又一次淪喪?正如過去二十多年來,當草根式網絡文學向精英式的傳統文學發起了沖擊,那些網文作者們發現自己為了生存不得不更多地去迎合讀者,于是自嘲式地冠以“寫手”之名。
這一次,當作者將更多的主體權利讓渡給AI的時候,他們還能繼續心安理得地接受并認同自己屬于文學創作者嗎?
“AIGC不會取代作家,它是創作的金手指,而主角永遠是作家。”針對不少人的擔憂,閱文集團首席執行官兼總裁侯曉楠在會上給出了回答。
但,AI寫作技術,真的將僅止于此?
敲出十三行詩的“猴子”
“就好像出現了一個魔法精靈,可以滿足人類的所有愿望,通常這樣的故事不會有好結果。”近日,在倫敦舉行的全球首屆AI安全峰會上,特斯拉的首席執行官馬斯克如是表達了對AI技術的擔憂。
1913年,法國數學家埃米爾·博雷爾提出,“如果給予一只猴子足夠的時間,它可以在鍵盤上敲出莎士比亞全集”。本是關于概率論的命題,成為了AI寫作的絕妙預言。
一百多年后,人類通過教會猴子各種“算法”,不斷糾正其失誤,讓它成功敲出了一首十三行詩。
敲出了十三行詩的猴子,能否被稱為“詩人”?
回到《機憶之地》的“創作”過程,可以看出,教授沈陽依然是作品完成的絕對主導者。一方面,AI并不具備主觀的創作意識,創作過程完全由人類推動進行;另一方面,AI創作的文本質量良莠不齊,自身也做不到去完善修改,只能通過接受來自人類的指令,對角色設定、故事走向、文字風格、敘事細節等進行調整,才能確保創作出具有一定水準的作品。
可以說,目前的AI距離獨立進行文學寫作,還相當遙遠。但倘若立足人工智能技術才剛剛起步的當下,放眼去展望未來,上述幾點都并非堅不可摧的壁壘,理論上都是有解決方法的—同時相比人類,AI其實有著一個無可超越的優勢,那便是幾乎零成本的寫作。

美劇《愛,死亡和機器人》劇照
目前的AI距離獨立進行文學寫作,還相當遙遠。
對于資本世界而言,“零成本”是一個危險的潘多拉魔盒。
這將是一個有些可怕的展望:AI的數據庫可以囊括人類古往今來所有的文學作品,它可以將作品中的“元素”進行拆分重組,盡可能地去窮盡所有可行的選項,在極短的時間里生成海量的“作品”。
只要人類還有閱讀文學作品的需求,互聯網大數據就可以幫助AI急速成長,就像已經在音樂、繪畫領域已經發生過的那樣。終有一天,AI創作的文學將足以“以假亂真”。
如進入AI寫作的時代,傳統的作者將變得不被需要。至于文學,迎來大繁榮時代的同時,也敲響了屬于它的“末日鐘”。為滿足人類娛樂的愿望,所有新穎的設定、題材、手法都將猶如瘋長的野草,無節制地肆意擴張,在極短的時間里被AI耗盡其生命力。
所有唯美的、悲壯的、震撼的……那些飽含情感的詞句都將被AI濫用,直到其意義被磨損殆盡;所有主題的故事都不再是獨一無二的璀璨珍珠,而是AI流水線生產出的無數雷同沙礫中的一顆。
極短的時間內,文學所具有的美學內涵被徹底消解,在一場饕餮盛宴般的狂歡過后,人類徹底失去了對文學的欣賞能力。
如無約束,AI將終結文學—這絕非危言聳聽。
人類始終是自己的裁判
在上個世紀90年代,加州大學圣克魯茲分校的一次音樂會上,樂隊演出了幾首巴赫風格的贊美詩,現場觀眾反應熱烈,興奮地講述著這些音樂如何觸碰他們內心最深處。
隨后,主辦方宣布,這些樂譜都是由一個叫作EMI(Experiments in Musical Intelligence)的程序編寫出來的。許多觀眾聞言,被氣得一言不發,甚至有人勃然大怒。
此事傳開,在古典音樂圈引起了軒然大波。不少音樂家認為,只有人類創作出的音樂才是靈魂之作,程序寫出來的樂譜死氣沉沉,很容易分辨出來,由此引發了一場“人機音樂對決”。

2023年4月22日,廣東東莞,閱文IP宇宙裝置藝術展在東莞圖書館舉行
但對決結果證明,人類其實根本無法分辨出哪些音樂是EMI譜寫、哪些音樂是人類譜寫出來的。
盡管如此,依然有人不依不饒,認為EMI的音樂技術雖然出眾,但還是缺少了什么,“一切太過準確,沒有深度,沒有靈魂”—在他們事先知道哪首歌曲是由AI譜寫的前提下。
無獨有偶,此次關于《機憶之地》獲獎的各種討論中,最普遍的觀點便是“AI無法理解人類的情感,也就很難創作出能引起人類共鳴的作品”。但這個幾乎是達成共識的論調,多少帶著些窘迫的意味,仿佛是已經預見到了AI很快就要在各個方面超越人類,故而找到了一個最為安全的“指控”。
而實際上,就AI寫作的發展本身而言,它并不需要真的去理解人類的情感,只需要模擬出有情感的表達就足夠了—語言才是情感的載體。
又或許,這里面其實隱含了一個更關鍵的哲學命題,“AI創作的文學是否真的有意義?”也即,“AI創作的文學是否有被欣賞的價值?”
正如當觀眾得知,那些悅耳的巴赫風格的贊美詩是由EMI編寫的那一刻,音符所編織的意義之網便瞬間破滅,直抵心靈的共鳴之廊頃刻倒塌,究其本質,文學藝術終究是人類獨創的產物,反映的是人類的情感體驗,其服務于人類,創作主體也只能是人類,這是人類內心深處欣賞文藝作品的底線。在文學欣賞過程中,作者、文本、讀者,三者缺一不可。
為了應對AI音樂的發展勢頭,今年6月份,美國流行音樂最權威的獎項格萊美的主辦方宣布更新了一系列評選規則,明確指出,“只有人類創作者才有資格被提名或贏得格萊美獎”—和圍棋領域不同,在文學藝術領域,盡管人類依然可能會一敗涂地,但人類始終是自己的裁判官。
所以,對于讀者而言,無論AI寫作發展到何種高度,也終究不過是惟妙惟肖的模仿,是那只永遠不會被承認的“打字機前的猴子”。出于種群自我認同的防御機制,人類將始終守護著內心的凈土,作為情感載體的文學永不消亡。
AI所代表的技術理性,無法取代人類對于美好浪漫的向往和想象。
至于說,倘若有一天,AI演變成了真正意義上的智能生命,也擁有了和人類相近的情感……很顯然,這已然屬于更高維度的命題了。屆時,人類想必已經對“文學”和“技術”的邊界,有了全新的認知。
責任編輯吳陽煜 wyy@nfcma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