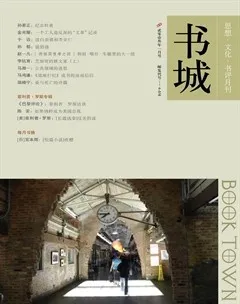“中國風”與外銷扇的圖像翻譯
陳慶
十七世紀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檔案材料中有一項記錄頗為耐人尋味,那便是私人貿易(private trade,或稱private cargo)清單。它們散見于商船早期進出口貿易各類數據的不起眼角落里,記下隨船人員以個人名義進行貨品交易的名稱、數量、價格等。以一六七四年至一六七五年為例,這一年在毛織品、金屬出口一項中,東印度公司的出口總額為十五萬五千鎊,其中私人貿易高達四萬五千鎊,約占總數的百分之三十;銀塊和鑄幣的出口總額為四十一萬鎊,其中有九萬鎊為私人貿易,約占百分之二十二。考慮到船員個人所能攜帶的貨物限制,上述數字已稱得上驚人。雖然私人貿易的記錄處在邊角之處,但這些數字卻令人浮想聯翩,它不僅聯系到船員的冒險傳奇,也關乎對“神州中國”神秘旖旎的無盡想象。在長達兩個多世紀的時間里,“為什么是中國”與“為什么到中國去”是歐洲有關“神州中國”龐大敘事的一體兩面,正如休·昂納(Hugh Honour)在《中國風:遺失在西方800年的中國元素》(劉愛英、秦紅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以下簡稱《中國風》)一書中所寫的那樣,“神州就是那一望無垠的大陸,它處在已知世界的東方疆域之外”,在這片“充滿神秘色彩、魅力無窮的土地,詩人才是唯一的歷史學家,而瓷器畫匠才是最可靠的地形學專家”。伊蓮娜·亞歷山大(Hélène Alexander)更明確地寫道:“自馬可·波羅的游記問世以來,中國對歐洲的誘惑一直存在,這種誘惑伴隨著遠航船只帶回的精美昂貴的中國器皿變得直觀且熱切,它吸引著眾多歐洲人甘愿冒著危險橫渡重洋。”(《中國制造:升雯閣及扇子博物館所藏中國外銷扇目錄》,作者譯)
在這一前提下,東印度公司允許船員以“私人貿易”的名義從事貨品買賣,或許是公司為了鼓勵更多冒險家加入遠航去東方而出臺的刺激政策。然而一艘貨船的體積有限,刨除公司規定貨物所占的空間,分到每個船員的私人儲貨份額非常狹小,且嚴格按照個人等級序列進行分配。以一個英國海軍候補少尉為例,分到他頭上不過一平方英尺(約0.093平方米)。如何在狹小的空間里盡可能塞進去更多的貨物,船員們為此想出各種辦法:比如將整束馬六甲白藤手杖扎緊豎放,采購小型不占地方的瓷器、漆器,可以折疊起來的絲織品,等等。所有這些貨品中,外銷扇格外受到青睞,因為扇子本身輕巧便攜、扇匣薄扁細長,很適合裝填狹長細窄的空間。同時,外銷扇制作工藝精美絕倫,尤其是象牙扇和漆器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歐洲工匠無法仿制,因此“幾乎沒有競爭對手”,價格也居高不下,成為深受歐洲上流社會喜歡的奢侈品。
成千上萬的外銷扇便這樣通過私人貿易的方式進入了歐洲。有學者認為是中國外銷扇的到來才掀起歐洲上流社會使用扇子的熱潮,但這種說法并不符合歷史。事實上,與其說是中國外銷扇引領了扇子熱潮,不如說是歐洲貴族階層早有使用扇子的習慣,因此船員們才根據已有的市場意向選擇將中國外銷扇輸入歐洲。大概從十六世紀中葉起,扇子已經成為歐洲各國的名媛淑女出入社交場合的必備之物,隨著這種風潮漸次影響民間,這種輕巧精致的物品同樣也成為市民階層女性的選擇。其中最直觀的視覺證據來自女子肖像畫—十五至十六世紀的歐洲女子畫像一直保留著中世紀的圖像程式,畫家在著筆前已明白畫中女子需處處展現女性基督徒虔誠、貞潔的品行,于是她們手里拿著什么道具便顯得至關重要—那件東西必須具備一目了然的符號意涵,令觀者在第一時間便明白該物品對畫中女子道德品質的象征作用。因此當我們觀看那個時期的女子畫像時,常常可見到畫中女子被刻畫成面容嚴肅、神情莊重的模樣,她們無論老少,手中常持著念珠、小本經文、百合花等物。然而情況到了十六世紀中葉開始發生變化,隨著城市經濟的發展與中產階級的興起,女子畫像不再總是被描繪成神情呆板、不茍言笑的,她們開始神情生動、嫵媚活潑,手上所持之物也開始出現一些世俗化物品,如刺繡精美的手絹、皮質手套以及我們要談及的扇子。從這一時期開始,扇子成為女子畫像中常見的道具,上自皇室下至市民階層皆不能免俗。其中比較著名的畫像如英國都鐸王朝宮廷畫師小馬庫斯·海拉特(Marcus Gheeraerts, the Younger)于一五九二年為伊麗莎白一世繪制的《迪奇利肖像》(Ditchley Portrait),畫中女王身著裙撐鼓脹的披風長裙,儀態莊嚴地站在巨大的地球儀上,腳下便是英國地圖(有學者將女王足尖落點處勘定為牛津郡),右手持著一把形制與中國折扇相類似的卜瑞斯扇(brisé)。倘若我們將《迪奇利肖像》與一七四八年的法國宮廷畫家查爾斯·安德烈·范·盧(Charles André van Loo)為皇后瑪麗·萊什琴斯卡(Marie Leszczynska)所繪的肖像比較可發現,兩者無論從繪畫風格、繪畫技藝、人物服飾上皆截然不同。畫中的瑪麗皇后身著繡滿金色花草紋樣的法式長袍(robe à la fran?aise),這種長袍在瓦蘭提斯長袍(robe volantes)的基礎上加入大量的絲帶和蕾絲裝飾裙面,脖子與頭部所戴配飾簡約明快,這是因為瑪麗皇后所處的時代正值藝術史上的洛可可時期,華麗厚重的巴洛克風格余音未了,而洛可可風格之輕盈精細漸次凸顯,此時的歐洲宮廷服飾早已擯棄十六世紀笨重的裙撐、巨大的環狀皺領和僵硬夸張的衣袖。有趣的是,瑪麗皇后盡管全身上下的裝束皆與英女王不同,但她的手上也執有一柄卜瑞斯扇。
服飾在歐洲宮廷從來不僅意指時尚表現,更是權力和尊貴的象征,當伊麗莎白一世與一百多年后的法國皇后都在各自彰顯王權的肖像畫中選擇手持扇子時,意味著扇子早已成為歐洲宮廷貴婦對外展現王室威儀或自我形象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說明了在十六世紀末至十八世紀的歐洲宮廷服飾搭配規則中,扇子是不同時期宮廷服飾語法規則中的一個通用元素。在這種情況下,扇子的私人賞玩性早已被公眾展示性替代,并由此發明出全新的所指系統,在不同的政治人物身上生產出不同的外延。
到了十八世紀,扇子的公眾展示性與性別表達發生勾連,形成一套表達上流社會女性隱秘欲望的特殊暗語—“扇子語言”。女人們通過持扇的不同手勢在公開場合表達有關兩性關系的競勝與退讓,曖昧與斡旋等微妙關系。以維多利亞時期的名媛淑女們所發明的“扇子秘語”(secret language)為例,在這套語言的作用下,女士們得以與男伴在大庭廣眾之下不動聲色地“暗通曲款”,如右手執扇遮面意為“跟我來”,左手執扇遮面意為“渴望了解你”,扇置于左耳意為“我想擺脫你”,以扇輕劃額頭意為“你變了”,等等。其中一個有趣的秘語是,當一個女士故意在男士面前丟下扇子,千萬不要以為她在表達不滿,相反,這一動作的密語意為“我們可以成為朋友”,若該男士事先無法對這套語言熟稔于心,不僅會錯失與該女士進一步接觸的機會,還會因此被排除出特定的圈子。如此一來,扇子秘語通過語言學上的“交際性”暫時彌合了“女性/男性”“公眾/私人”“遮蔽/展現”之間的矛盾。當我們將這樣的道具置換成中國外銷扇時,這種“交際性”必然被注入來自東方異域的另一種意涵。也就是說,中國外銷扇進入歐洲,以來自中國的圖像符號增補和延展了歐洲扇子原有的所指體系。那么,外銷扇的圖像生產遵從怎樣的語法結構呢?
我們知道,十七、十八世紀,“中國風”(chinoiserie)曾在歐洲風靡一時。所謂“中國風”,一般指在歐洲風行的帶有中國元素和中國特色的藝術風格。休·昂納在《中國風》一書中提及,十七世紀中期時中國神州的形象深深刻印在歐洲人的想象中,加上來自東方的工藝品如紡織品、陶瓷、漆器等大量充滿著巴黎、倫敦和阿姆斯特丹的市場,整個歐洲國家的工匠們都忙著仿制東方進口的柜子、陶瓷容器和繡品上看到的古雅景致。然而,這些“中國式”圖案真的源自中國嗎?一六六九年,由于印度生產的織物不符合英國市場對“中國樣式”的狂熱追捧,倫敦東印度公司的董事們決定直接寄去圖案樣板—上面繪滿了都鐸王室的薔薇、紅磚房及報信的動物,這顯然是英國人想象中的“中國情趣”,是地道純粹的英國圖案。換言之,這些英國商人非常清楚他們理想中的“中國式”織物圖案是什么樣的。
可以說,“中國風”與中國圖案的“真實”無關,只與中國圖案的“據實”(factual)有關,就如戴安娜·葉(Diana Yeh)所言,無論這些“中國風”產品來自西方還是中國,它都標志著純粹的歐洲的“中國觀念”,是歐洲有關“神州中國”的集體想象(《英國現代主義與中國風》,作者譯)。藝術史家奧利弗·伊姆佩(Oliver Impey)對此有更深入的見解,他指出“中國風”之所以復雜,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大量“中國風”的圖像符號并非源自中國,而是歐洲人“對中國的奇特詮釋”;另一方面,那些代表“東方”“中國”風格的符號意涵并非固定不變,而是會隨著時代的變遷而變遷(《中國風:中國風格在西方藝術與裝飾中的影響》,作者譯)。比如大象的圖像符號在十四世紀時曾被認為是典型的東方動物,但到十八世紀時由于大航海興起與殖民擴張,這種動物已不再神秘,其所指結構中的東方意涵也被剝離。除這兩點外,倘若我們對“中國風”一詞進行詞源學上的探究,也能發現語義上的變異與重組:一八二三年,當傅立葉(Charles Fourier)率先使用“chinoiserie”一詞時,他是直接在名詞“chiois”(中國人)上加后綴“-erie”構成新詞,用來表示“中國人式”的保守、安于現狀、故步自封等意。然而時隔十二年后,法國詩人泰奧菲爾·戈蒂埃(Theophile Gautier)寫了一首詩,題目就是“Chinoiserie”,這個詞在詩中意指完全不同,充滿關于中國的神奇幻想,在語義上幾乎與傅立葉的用法截然相反。在這種情況下,與其將“中國風”視為一個固定的概念,不如將之視為一個被反復實踐、外延廣泛的場域。在這個場域中,與此相關的圖像生產不只是“雇主—產品”的單向作用,也包括工匠將雇主的“中國風”想象進行技術化再現的反向作用。特別是當這個過程所涉雙方—雇主(藝術贊助)與工匠(藝術創作)—分處在歐洲/中國不同的文化體系中時,其中的圖像生產與圖像構成則更為復雜—外銷扇的情況便是如此。
上文已經提到,早期外銷扇進入歐洲的一個主要渠道是私人貿易,但隨著這種制作精美的扇子大受歡迎,英法兩國的制扇匠人爭相模仿中國外銷扇樣式,尤其是卜瑞斯扇。巨大的利潤令許多商人聞風而動,與之相應的,廣州也開始出現專門制作歐美訂單的外銷扇作坊。其中絕大多數的訂單來自英國和法國。根據卡爾·克諾斯曼(Carl Crossman)的說法,美國直到一七八四年才由“中國皇后”號第一次將中國外銷扇運至北美,一開始只是少量的紙面彩繪扇及綢扇。一七八六年,這艘船再度前往廣州,返航時帶回了不少價格較貴的精致外銷扇,如其中一項為二十四柄貝母扇及兩柄羽毛扇,總價值二十三美元。(《中國外銷品中的裝飾藝術:繪畫、家具與異國奇錄》)由此推測,當時貝母彩繪扇每柄價格不到一美元。一個世紀后,中國外銷扇已經大量被運往美國,以至于十九世紀初期,東海岸地區的淑女們幾乎人手一把外銷扇。外銷扇一直暢銷到十九世紀后期,光緒六年(1880)的出口貨物清單上,清晰記錄了該年出口外銷扇多達六百多萬把,總價近四萬兩白銀。
長期高效地維持如此大規模的外銷扇定制出口,其背后必然有分工明確的生產鏈條,維持這樣的生產鏈條高速運轉,則扇面、扇骨、扇頭等部位的圖像符號必須具備可復制性,扇子整體的圖像程式也不會趨向復雜化。然而即便如此,定制者與制作者之間對同一圖像符號的理解經常出現不對等,甚至是風馬牛不相及的狀況—倘若我們借用翻譯的視角,將圖像符號的跨文化轉換理解為圖像翻譯,或許能將這種圖像中的文化互涉狀況說得更清晰。就如文字翻譯一樣,“中國風”作為歐洲人想象中國的圖像再現,本身已然是對中國圖像的一種“翻譯”;當西方訂購者將這種翻譯后的圖像作為外銷扇的“樣本”回流中國時,廣州制扇匠人因文化隔閡,又不可避免要對“樣本”進行重新闡釋,這便造成某種圖像上的“再翻譯”。這樣一來,即便是同一個圖像符號在這一過程中也可能產生意義層面上的斷裂、顛倒與重塑,更遑論對中西圖像中固有程式的變動與推倒重來,于是外銷扇的圖像生產中便常常出現在今天看來怪誕、陌生、“不倫不類”或“不中不西”等狀況。如一七六○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曾往廣州的扇子作坊中送去一些“樣本”,要求當地匠人按照樣本復制人物并加上“中國風”元素,但經過廣州匠人的一番重新演繹,希臘神話中的珀爾修斯和安德洛墨達兩人被畫成了“四不像”。
伊蓮娜·亞歷山大在其文章中曾提到造成這種狀況的歷史原因:“在當時,與外國人接觸被明令禁止,因此外銷扇中對‘洋鬼子’的再現正如瓷器和其他器皿那樣,依據‘洋鬼子’們自己提供的圖像進行復制,這就難怪這些圖像看起來多少總有些‘古怪’了。”(《中國制造:升雯閣及扇子博物館所藏中國外銷扇目錄》)上文所說的廣州匠人將珀爾修斯與安德洛墨達畫成“四不像”,一方面固然是因為他們對歐洲的歷史、文化及圖像意涵一無所知,另一方面卻也與他們對圖像進行的“改造式翻譯”有關,這是異域文化圖像再現的某種“變通式”處理,在早期外銷扇的圖像生產中屢見不鮮。現存英國扇子博物館(The Fan Museum)的十七世紀初期象牙彩繪外銷扇中,有一類卜瑞斯扇的扇面圖案與同時期外銷瓷中的“中國伊萬里”風格相似,很可能是受其影響。這類圖像以大紅、靛藍、金、黃等顏色為主,濃烈鮮艷,扇面常繪身著中式服裝的西洋男女游樂形態,他們按照中式瓷畫的布局錯落有致地分布在畫面兩側,背景多點綴中式畫法的松柏、花草和湖石,呈現出一種中國傳統游園圖的祥和恬淡之風。結合當時的訂購方式可知,這類扇面圖案很可能是廣州的制扇匠人按照訂購方提供的有限“樣本”,通過揣摩洋人喜好,將各種圖像符號元素打亂再重新布局的“東方西景”。
然而,這種“西洋人游樂圖”的變體中符號意涵也可能被改造得面目全非,以其中一柄被命名為“幸運之輪”的象牙彩繪扇為例,該扇的主要圖像符號便充滿中西文化的雙重指涉。這柄制作于一六八○年前后的象牙扇在大紅底色上有彩蝶戲花圖案若干,中間設橢圓下凹形大開光,大開光下又有橢圓小開光。大開光中畫面沿中軸線分為兩邊,左二右一共三個西洋人,均穿中式袍服,身上繞著巾帛飄帶,然而露出來的腿上卻著西式緊身襪。左邊兩個西洋人背靠藍色與粉色相間的屏風一立一坐,立者舉起一臂似在講話,坐著凝神仰望,右邊的西洋人手也舉起,似乎與之交談,形成畫面上的呼應,人物之上有兩個推著金色藍框“幸運之輪”的裸體天使,身后皆有藍色翅膀和如中式仙童畫一般的紅色飄帶。乍眼看去,這些人物身邊都綴有花草,似乎又是一幅“西洋人游樂圖”。然而仔細看卻能發現,人物與天使身下皆以白線勾勒祥云朵朵,更有白線勾勒的影影綽綽的欄桿;而天使推著的“幸運之輪”內用金色線條勾勒的符號是十字架形狀,因此這并不是一幅凡間景象,而是表現基督教中的天國花園場景。在對西方人的信仰體系一無所知的情況下,匠人只能挪用中式神仙圖的通用符號來塑造天國場景,于是圣徒們身穿麻姑獻壽式的仙袍,天使身上飄著仙童標配的紅色飄帶,所有人物均腳踩祥云。匠人在最頂部加上三處粉色帷幔,帷幔之下還有清晰可見的流蘇,這很可能是挪用了中國傳統佛教講經母題中人物頭頂常見的帷幔元素,目的是強調場景的宗教性。然而這種西式帷幔又將畫面的神圣感拉回世俗層面,甚至帶有戲謔意味,仿佛再一次悄然重申這一切不過是戲仿洋人,做數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