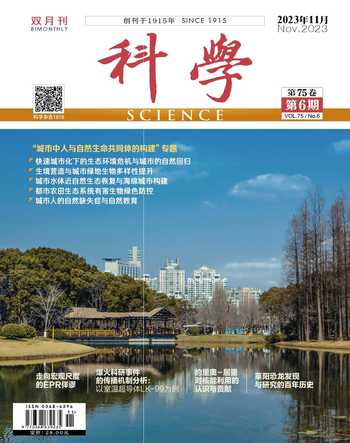約里奧-居里對核能利用的認識與貢獻
李云逸
法國科學家約里奧-居里(J. F. Joliot-Curie)約見楊承宗時的寄語,對中國核能研究史稍有了解的人來說并不陌生。當時,這位法國核能之父表示:“你回去轉告毛澤東,你們要保衛世界和平,要反對原子彈,就要有自己的原子彈。原子彈也不是那么可怕的,原子彈的原理也不是美國人發明的。你們有自己的科學家,錢(三強)呀、你呀、錢的夫人(何澤慧)呀、汪(汪德昭)呀。”[1]
這段在中國成為信史的記述被認為是約里奧-居里對中國人民正義事業的有力支持,并在后來中國決心發展自己的核武器時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不過,法國學者在約里奧-居里看待核能利用問題上的研究卻呈現了與上述話語的矛盾之處。在法國與境中,約里奧-居里被描述成核武器的堅定反對者與核能和平利用的熱情倡導者。那么,他對核能開發的態度究竟如何?是什么樣的與境塑造了他的觀點?
人類對核能利用的基礎是對鏈式反應的發現。1939年1月16日,德國科學家哈恩(O. Hahn)和斯特拉斯曼(F. Strassmann)發表了第一份鈾在中子作用下發生裂變的證據(文章完成日期是1938年12月22日),立即引起了約里奧-居里的興趣。從1月26日到1月28日,約里奧-居里設計并進行了實驗,從而成功證明了不僅是鈾,連釷也會發生這種現象。他將其稱為“爆炸性碎裂”(la rupture explosive),并推測除鉛之外,其他元素也能產生不同類型的碎裂。[2]在1939年2月11日,邁特納(L. Meitner)與弗里施(O. R. Frisch)于《自然》(Nature)雜志上的發文則將這一現象稱為“裂變”,該詞成為沿用至今的專業名詞。
鈾核里的中子比例大于核裂變產生的原子核里的中子比例,這讓約里奧-居里想到了新問題:裂變產生的中子能有多少?這些中子能否產生其他裂變?同時期,美國和蘇聯的科學家也在進行探索。三個團隊采取的方法大同小異,但法國人走在了前面。

約里奧-居里與哈爾班(H. von Halban)、科瓦爾斯基(Lew Kowarski)組成了研究小組。1939年1月末起,約里奧-居里組決定先將裂變釋放的中子與放射源釋放的中子區分開。他們設計了兩個實驗方案,一是定量法,即將源浸入一個足夠大的吸收系統中,以確保內部產生的中子沒有明顯的機會逃逸。二是定性法,即使用一種對初級中子不敏感,對次級中子敏感的探測器。這兩項實驗于2月同時進行。定量實驗提供了第一個裂變產生中子的證據,3月18日,約里奧-居里組在《自然》雜志上公布了該結果。3月27日,他們在給法國科學院的報告中指出,“每次爆炸都有幾個中子發射,這是產生鏈式反應的必要條件”,并進一步揭示了次級中子與初級中子在能量上的不同。[3]緊接著下一步便是確定裂變射出中子的數量。4月7日,約里奧-居里組向《自然》雜志發布了結果(文章于4月22日刊登),測定了裂變中子數為3.5±0.7,并認為“裂變鏈將自我延續”。至此,法國在發現核鏈式反應上取得了優先權。
約里奧-居里組對鏈式反應的研究發現是人類邁向利用核能的重要一步。此外在法國,還有另一個關鍵人物佩蘭(F. Perrin)。他確定了鏈式反應的延續必須使鈾達到臨界質量,這使得計算材料量和研究觸發鏈式反應的裝置成為可能。佩蘭與約里奧-居里組在1939年4月取得了聯系,后者在當月公布的數據成為佩蘭測算臨界質量的基礎。在吸納了佩蘭后,約里奧-居里決定在實施進一步實驗之前為研究申請專利保護。四人以國家科研基金會(Caisse nationale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CNRS)的名義于5月1日、2日和4日,提交了三項專利申請:《能源生產裝置》《能源生產裝置的穩定工藝》和《炸藥的改進》。第一項專利內容提到了可能的燃料與減速劑,以及遠程啟動、停止和調節技術及防輻射技術等。第二項專利涉及減緩或吸收中子以穩定鏈式反應的不同方法。在爆炸物方面,四人建議:“將爆炸物的核心分成兩半,以便爆炸從中心部分開始,引起一定程度的真空填充,將它們分開。這兩個部分在爆炸時可能會靠近也可能不會靠近。也可以在核心里創造一個中央空腔,這將起到類似的作用。”
三項專利都獲得了批準。雖然從其內容上來看,它們反映了數年后出現的核反應堆和原子彈的基本原理,不過,佩蘭在之后的回憶中表示,當時核能被理解為一種更便宜的能源,核爆炸物則被設想用于開鑿運河等大型公共工程。專利的起草像是在寫科幻小說。[4]145-146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法國當時的技術還遠未達到實現專利內容的水平。但是,這三項專利確實是最早提及核研究民用與軍用價值,并受到官方批準的正式文件,因此它們成為二戰之后法國重拾科技創新與自立自強信心的重要來源。1945年8月,約里奧-居里接受《世界報》(Le Monde)的采訪。當被問及美國向日本投擲原子彈一事時,他說:“雖然人們必須欽佩美國為此所作的巨大努力,但法國發現了最初的原理。”

約里奧-居里希望能將核能利用的專利推向實用化。在國家科研基金會的協調下,約里奧-居里組與上加丹加聯合礦業公司(Union minière du HautKatanga, UMHK)的董事長會面。該公司控制著比屬剛果的鈾礦。雙方達成了一項協議,聯合礦業公司將提供5~50噸氧化鈾用以進行約里奧-居里組的實驗,并為相關裝置的建造提供技術支持。這是世界上第一個有關核能利用的合作項目。5噸氧化鈾在1939年5月下旬到位,約里奧-居里組還獲得了5萬法郎的特別撥款。對氧化鈾的化學處理被他們安排在鐳研究所位于巴黎南部亞捷(Arcueil)的附屬機構中進行。在伊夫里(Ivry)的原子合成實驗室(Laboratoire de Synthèse atomique),他們建造了一個巨大實驗裝置。其直徑3米,高2.5米,盛有充當反射器的水。一個填滿粉狀氧化鈾或水的銅球被浸入其中。約里奧-居里組使用水或300千克的氧化鈾填充球體,一個光電子源被放置在球體的中心。他們發現,一次碎裂至少產生8個中子,而所有這些中子并不可能都來自單一的鈾核。約里奧-居里組認為,“二次、三次等等的碎裂已經發生,我們處于一個聚合型鏈式反應中”。[5]此次實驗也表明,這種鏈式反應很快會中止,因為氫會捕捉中子,所以必須采用低吸收性的調節元素。
1939年10月底,團隊提出用氘替代氫,這就需要大量的重水作為慢化劑。當時只有挪威的產能可以滿足要求。法國軍方遂派遣別動隊于1940年2月至3月秘密從挪威運回167升重水,以保證實驗。時任軍備部部長多特里(R. Dautry)在1951年的一封長信中回憶道,1939年11月,有人向他轉述約里奧-居里愿意為軍備部開發核爆炸物。但這能否成為約里奧-居里同意為法國軍方研發原子彈的證據呢?這份記錄距離事發時間已經過去了12年,而且還是轉述,因此不足以說明約里奧-居里會為軍方制造原子彈。即便能說明,正如佩蘭的回憶,以當時約里奧-居里組的認知,這種爆炸物應當不會是1945年投向日本的原子彈的水平。另外,法國人當時的技術能力還存在問題。
約里奧-居里在1940年2月和4月都曾表示,就時下對鏈式反應的了解,核爆炸物制造很難實現。如果實驗能夠獲得成功,那么最重要且較容易取得突破的應用將是通過天然鈾和重水的組合來生產大量的能源,以節省煤炭與石油。5月初,新的實驗計劃被制定。裝滿粉末狀氧化鈾的銅球將被浸入重水里。此外,需要增加鏑探測器,同時還需要一個新的放大器。但是,二戰的進程沒有給他們更多的時間。6月,法國政府在德國軍隊的攻勢下最終選擇投降,實驗由此徹底停止。約里奧-居里決定留在法國參加地下抵抗組織。哈爾班與科瓦爾斯基則前往倫敦,并于7月公布了此前在發散型鏈式反應上的工作。
1942年12月,世界上第一個核反應堆在美國發散,為法國人研究的有效性提供了證明。
二戰期間,被德國占領的法國在核能利用上的工作幾乎處于停滯狀態。1944年8月巴黎解放后,約里奧-居里受到英美科學家關于德國核研究情況的質詢。他由此敏銳地意識到了美國的動向。他很快聯系流亡海外的法國核科學家了解情況,并通過基礎數據推想出“曼哈頓”計劃的階段性進展。同時,他也獲悉美國正在制造核爆炸物。
約里奧-居里決定盡快恢復法國的核研究工作。1944年11月,他與戴高樂將軍見面,談到了未來法國的核能探索。這次會面除了留下了戴高樂那句“我很少相信人,但,約里奧-居里,我對您完全信任”的名言外,根據佩雷菲特(A. Peyrefitte)——一位長期跟隨戴高樂的法國政治家的回憶,約里奧-居里答應戴高樂為法國制造核爆炸物。這一記述與多特里的證詞存在相同的問題。它同樣是來自他人(戴高樂)的轉述,且轉述時間(1966年)與事發時間相差太遠。
從12月開始,約里奧-居里一方面積極聯系海外的法國核科學家,并在本土勘探鈾礦。他堅信美英會將法國納入“曼哈頓”計劃。另一方面,他希望挪威政府恢復法國戰敗前的重水供應。由于保密政策,約里奧-居里的合作規劃落空了,而他為取得重水與勘探鈾礦而做的努力則成為法國重啟核研究的重要一步。
當時間來到1945年的夏季,據多位法國科學家回憶,廣島與長崎的蘑菇云讓休假中的約里奧-居里陷入深深的痛苦。他認為如果完全為了破壞性的目的,任何科學家都無法成功對核能利用進行研究。在8月10日寫給法國共產黨機關報《人道報》(L’Humanité)的文章中,除強調法國在該領域的優先權外,他表示核能將在和平中為人類提供寶貴的服務。[6]他這種主張核能和平利用的觀點,被認為是早年受到朗之萬(P. Langevin)等人關于科學家應當將世界變得美好的社會責任的影響。約里奧-居里認為科學家有能力也有義務為和平與人類福祉發揮特殊的作用。這也從側面印證了那些孤證中,他希望建造的“核爆炸物”與“原子彈”是兩個概念。
一戰后,戰爭與科技帶來的可怕破壞使得和平主義成為一股影響力極大的思潮。在被稱為“30年代危機”的時期里,動蕩不安的局勢使得知識分子群體追求和平與科學用以維護和平的行動變為一種必然。與此同時,法國的知識分子群體也愈發變得具有批判性。他們跳出自身原有的職業定位,深刻反思社會問題,批判資本主義,并擁有極強的社會責任感。朗之萬是其中的代表,其最有影響力的社會活動就是號召反法西斯力量,進行國際反戰活動。他成為國際反法西斯群眾大會的執行主席,并與其他科學家建立了知識分子反法西斯警惕委員會。約里奧-居里在二戰之后也走上與朗之萬相似的道路。
1945年10月18日,在戴高樂的授意下,法國原子能委員會(Commissariat à l’énergie Atomique,CEA)正式成立。這是一個具有科學、技術和工業性質的機構,被賦予民事人格、部級權力以及行政和財務自主權,由法國政府領導和控制。原子能委員會的創新之處在于它是世界上第一個進行核研究的公共機構,體現了法國在體制上對這項學科的重視。在核科學領域,法國雖不像美國匯聚大量世界知名的科學家,但仍擁有許多一流的研究人員,原子能委員會便將他們集中起來,希望采取一切措施,使國家能夠從其發展中得益。而在美國,相應的組織在1947年才成立。法國原子能委員會由一個行政委員會負責管理,設有高級專員和總干事兩個職位。約里奧-居里為第一任高級專員,多特里為第一任總干事。其實驗室設置在巴黎以南五千米的沙蒂永堡(Fort de Chatillon)。約里奧-居里為原子能委員會制定了任務性質:進行有關核科學和技術的研究,以便在科學、工業和國防的各個領域使用核能。原子能委員會的軍事任務包括研究輻射檢測與保護,向政府和武裝部隊提供有益的建議,但僅僅是進行研究,讓國防的各個領域使用核能,而非制造原子彈。
從原子能委員會成立到1950年被迫卸任總干事一職,約里奧-居里在科研上的基本工作是組織團隊進行核能利用的實驗性研究。1948年12月15日,法國也是歐洲大陸首個核反應堆——ZOE(Z代表零能量,反應堆是實驗性的;O代表氧化鈾;E代表重水)——在沙蒂永堡成功發散。它由原子能委員會動用了庫存的天然鈾和重水建造而成。其反應爐高約1.8米,包含浸泡在鋁包層中垂直安置的氧化鈾棒與5~6噸重水。反應堆的控制由兩組鎘棒實現。調整板位于反應爐外側,更外側的則是厚90厘米的石墨反射器,它們的位置可以通過中央面板控制的伺服機調整。ZOE由一個厚1.5米的混凝土防護罩保護。由于是零功率,因此反應堆省去了復雜的冷卻機構,僅通過反應爐周圍實施的空氣循環以及重水的對流完成冷卻。從核能產量上看,ZOE的意義并不大,其實際就是一個實驗型反應堆。它產生的輻射可用于實驗,譬如作為中子源,產生的中子可以用來研究晶體材料的結構。然而,ZOE在政治與公眾輿論上的影響卻是非凡的,是法國核研究復興的一大標志。
約里奧-居里還拓展了原子能委員會的研究場所,更大的設施在巴黎南郊的薩克雷(Saclay)進行建設。世界第一座氣冷堆于1949年在薩克雷動工,然而他已經無法在總干事任上見證它于1952年的成功發散。
從1940年代末開始到1950年代初,在東西方關系日益緊張并最終爆發冷戰的情況下,和平問題變得至關重要。而在核能被軍事利用之后,“禁核”也成為一個時代的主題。1948年2月,在法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部分前法國抵抗運動的成員組織了西方陣營中第一個和平主義活動團體。很快在8月,波蘭召開了第一次由兩大陣營知識分子參加的和平主義會議。盡管聲稱中立,但大會的宣言明顯指責了西方大國對戰后和平氛圍的破壞,因此被認為是得到了蘇聯的支持。正是在后者的推動下,1949年4月,第二次國際性和平主義會議召開,約里奧-居里積極參與。冷戰的鐵幕阻礙了東方陣營國家的知識分子前往巴黎參會,由是布拉格被設立為分會場。來自72個國家的2千多名代表在會議期間通過了《世界保衛和平大會宣言》,并選出了由約里奧-居里領導的世界保衛和平大會常設委員會。也正是在這次會議上,約里奧-居里收到了由錢三強委托轉交的為中國購買核研究材料的經費。此次會議產生了轟動性的影響。在西方陣營看來,和平主義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已經建立起聯系。

在美國決定研制氫彈的背景下,1950年3月,約里奧-居里起草了《斯德哥爾摩宣言》,并成為簽署宣言的第一人,他希望以此掀起一場運動。宣言指出,應當禁止核武器。對任何國家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府將犯下危害人類的罪行,并被作為戰爭罪犯對待。該宣言通過世界保衛和平大會常設委員會發布后,確實在各國民眾間掀起了“禁核”浪潮,但約里奧-居里卻失去了自己在原子能委員會中的職務。
無論從約里奧-居里所取得的研究成果,還是他所發表的言論,不難看出,他是核能和平利用的堅定支持者,并且反對原子彈這樣的核武器研發。其對法國核能研究的創新與自立自強能力的建設也基于此思想。這種思想的形成與他早年的研究經歷和法國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密切相關。在當時的認知中,科學既是“好的結果”,也是道德化的來源。它能夠在“反戰”與和平問題上展現出榜樣性的力量。
即使在約里奧-居里參與的那場讓他丟失原子能委員會管理職務的和平主義運動中,他也沒有展現出激進性,而是出于科學的反思而非冷戰的意識形態。在1945—1949年,他的理想依然是建立一個公正而統一的世界,一個科學為人類造福并被科學治理的世界。為實現這一理想的呼吁是根據科學家的良心行事,不惜冒著犧牲職業生涯的風險。盡管在原子能委員會成立時,他所設計的機構功能中涉及軍事領域,但僅僅是輔助作用,可以認為是協助法國軍方認知核武器及其放射性帶來的風險,而不是制造核武器。
那么,如何理解約里奧-居里對楊承宗所說的話?從時間節點上來看,1949年4月,錢三強托人將經費轉交約里奧-居里時,后者依然是法國原子能委員會的負責人。此外,蘇聯那時還沒有進行自己的第一次核武器試驗。這可能是約里奧-居里并未托人向錢三強表達相關意見的原因,他似乎仍然對和平使用核能的前景抱有幻想。而當楊承宗與約里奧-居里在1951年見面時,后者已經從原子能委員會卸任,并以法國共產黨黨員與和平主義支持者的身份全身心投入國際和平主義運動中。此時,蘇聯已擁有核武器,并與美國朝著“核均勢”的道路邁進,威力更為強大的氫彈也在研制中。約里奧-居里將核能服務于人類福祉的理想在這樣背景下業已破滅。而中蘇同盟的建立與朝鮮戰爭的持續也成為了當時重要的國際事件。約里奧-居里在1950年代曾經表示,核武器不會給第一個使用它的人帶來勝利,而蘇聯永遠不會是第一個使用核武器的國家。在評論蘇聯的核武器研發工作時,他指出,他對蘇聯取得的進展印象深刻,蘇聯的科學家是服務于人民的科學家,是進步的科學家。[4]537-539如此,在那個西方陣營咄咄逼人、不斷威脅世界和平的時期,東方陣營掌握核武器在他心中似乎具有了合法性。可能出于上述因素的考量,才有了約里奧-居里支持中國研發核武器的言論。

[本文為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十四五重大項目“中外科技創新史比較研究——科技自立自強之路”(E2291J01)“工程創造”專題的階段性成果。孫烈研究員對本文提出寶貴意見,特致謝意。]
[1]劉培. 楊承宗: 為原子彈加鈾的科學家. 學習時報, 2021-07-07(A6).
[2]JOLIOT M F. Preuve expérimentale, de la rupture explosive des noyaux d’uranium et de thorium sous l’action des neutrons. présentée par PERRIN M J. Paris: Compte rendus hebdomadaires des séances de l’Académie des Sciences, la Séance du 30 janvier,1939: 341-343.
[3]DODé M, HALBAN H VON, JOLIOT F, et al. Sur l’énergie des neutrons libérés lors de la partition nucléaire de l’uranium. présentée par LANGEVIN M P. Paris: Compte rendus hebdomadaires des séances de l’Académie des Sciences, la Séance du 27 Mars, 1939: 995-997.
[4]PINAULT M. Frédéric Joliot-Curie. Paris: Odile Jacob, 2000.
[5]HALBAN H VON, JOLIOT F. Mise en évidence d’une réaction nucléaire en cha?ne au sein d’une masse uranifère. J Phys Radium, 1939(10): 428-429.
[6]PINAULT M. Naissance d’un dessein: Frédéric Joliot et le nucléaire fran?ais (ao?t 1944-septembre 1945). Revue d’histoire des sciences, 1997, 50(1-2): 3-48.
關鍵詞:約里奧-居里 核能利用 法國原子能委員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