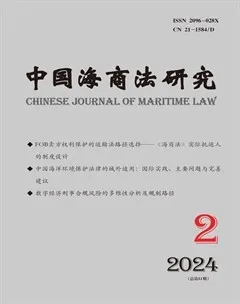論國家主管機關的人命救助方主體資格
摘要:《海商法》第185條對國家主管機關因履行職責而救助人命時是否具有人命救助方主體資格規定不明。根據文義解釋,“在救助作業中救助人命的救助方”應包括國家主管機關,且這一解釋符合第185條的立法目的,故應作為解釋該條的最優方法;學理研究則援引區分理論,以國家主管機關救助人命系履行法定職責且缺乏自愿性為由,否定其人命救助方主體資格。承認第185條項下國家主管機關的人命救助方主體資格,既有司法實踐的有力背書,又可為人命救助優先原則的有效落實提供保障。否定國家主管機關的人命救助方主體資格有違第185條的文義解釋,而且有損人命救助優先原則的基本精神,并因缺乏合理性基礎而不具可采性。以《海商法》修改為契機對
第185條予以完善,通過明確規定國家主管機關人命救助方主體資格的方式來定分止爭,有助于提高《海商法》的確定性、權威性和實效性。
關鍵詞:《海商法》;國家主管機關;人命救助方主體資格;人命救助優先原則
中圖分類號:D922.29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2096-028X(2024)02-0015-11
一、問題的提出
《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商法》(簡稱《海商法》)自1993年7月1日施行以來,對維護中外當事方的合法權益、促進中國國際貿易和航運經濟的發展,發揮了里程碑的作用。參見司玉琢:《艱辛的歷程,輝煌的成就——紀念〈海商法〉實施三十周年》,載《中國海商法研究》2023年第2期,第7-13頁。為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借鑒國際立法和實踐經驗,彌補在長期司法實踐檢驗中顯露出來的制度缺陷,參見傅廷中:《國際視野內的中國海難救助立法》,載《國際法研究》2022年第3期,第19-24頁。《海商法》修改工作于2017年7月正式啟動,現已進入關鍵階段——在2023年9月7日發布的《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中,《海商法》被列為第一類立法項目,即條件比較成熟、任期內擬提請審議的法律草案。參見《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載全國人大網2023年9月8日,http://www.npc.gov.cn/npc/c2/c30834/202309/t20230908_431613.html。
《海商法》第185條涉及海上人命救助,規定“在救助作業中救助人命的救助方,對獲救人員不得請求酬金,但是有權從救助船舶或者其他財產、防止或者減少環境污染損害的救助方獲得的救助款項中獲得合理的份額”。《海商法》第185條是根據《1989年國際救助公約》(簡稱《公約》)第16條制定的。《公約》第16條“人命救助”規定:“1.獲救人無須支付報酬,但本條規定不影響國內法就此作出的規定。2.在發生需要救助的事故時,參與救助作業的人命救助人有權從支付給救助船舶,其他財產或防止或減輕環境損害的救助人的報酬中獲得合理份額。”回顧《海商法》的修改歷程不難發現,第185條似乎并未引起修法者的足夠重視。這表現在:一方面,自《海商法》修改工作啟動以來,海上人命救助的議題在相關文獻和研討中鮮有涉及;另一方面,交通運輸部2020年1月7日提請國務院審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商法(修改送審稿)》第216條對《海商法》第185條僅作了“保留原條文”的處理。
“保留原條文”很容易使人產生這樣的理解,即《海商法》第185條的規定因不存在任何問題而無需修改,或者即便存在問題也尚未達到到需要以修法的方式予以應對的程度。然而,實際上,至少就人命救助方的主體資格而言,該條存在著規定不明的缺陷。具體而言,實踐中常有海上搜救中心等國家主管機關因履行職責而救助人命的情形,那么在此情形下,該國家主管機關是否有權依據《海商法》第185條從其他救助方獲得的救助款項中獲得合理份額呢?換言之,履行人命救助職責的國家主管機關是否屬于《海商法》第185條規定的“在救助作業中救助人命的救助方”呢?
對于這一問題,《公約》和《海商法》第192條均無法給出明確答案。理由在于,這些規定的調整對象是國家主管機關實施的以船舶或其他財產為對象的救助作業,因此對于以人命為對象的救助活動不具有可適用性。《公約》的前言指出,該公約旨在通過協議制訂關于救助作業的統一的國際規則,而根據《公約》第1條(a)項,救助作業系指可航水域或其他任何水域中援救處于危險中的船舶或任何其他財產的行為或活動。據此,即便《公約》第5條規定了國家主管機關在救助作業中的權利和補償問題,并允許締約國通過國內法對上述權利和補償的范圍予以確定,《公約》第5條“公共當局控制的救助作業”規定:“1.本公約不影響國內法或國際公約有關由公共當局從事或控制的救助作業的任何規定。2.然而,從事此種救助作業的救助人,有權享有本公約所規定的有關救助作業的權利和補償。3.負責進行救助作業的公共當局所能享有的本公約規定的權利和補償的范圍,應根據該當局所在國的法律確定。”也不能適用于國家主管機關因履行職責而救助人命的情形。同理,因為《海商法》第192條《海商法》第192條規定:“國家有關主管機關從事或者控制的救助作業,救助方有權享受本章規定的關于救助作業的權利和補償。”是對《公約》第5條的國內法化,其適用范圍也僅限于國家主管機關從事或者控制的救助作業,所以自然無法回答第185條項下國家主管機關人命救助方主體資格不明的問題。
在《海商法》第185條關于國家主管機關人命救助方主體資格規定不明的情況下,若以不同的視角和依據對該條進行解釋,將會得出截然不同的結論。這一解釋爭議揭示了《海商法》第185條所存在的立法漏洞,預示了引發實踐中糾紛的潛在危險,并因此侵蝕《海商法》的確定性、權威性和實效性。這樣的消極后果恐怕是立法者始料未及的。在《海商法》修改過程中,有一種值得肯定的觀點主張,“應實實在在以問題為導向,切合實際地完成本次海商法修改。”許俊強:《對〈海商法〉修改的幾點看法》,載E航網2020年10月22日,http://www.ehangwang.cn/article/detail/post-15918.html。堅持問題導向的《海商法》修改,要求對于第185條存在的人命救助方主體資格不明的問題既不可輕描淡寫地一筆帶過,更不應采取選擇性無視的非理性立場,而應以修法為契機,在理論界和實務界充分討論的基礎上,通過科學的、切合實際的修法措施予以積極應對。
二、解釋論視角下國家主管機關人命救助方主體資格的矛盾性
一般而言,在船長和船員等私主體救助人命的情形下,施救者可根據《海商法》第185條從其他救助方獲得的救助款項中獲得合理份額,對此并不存在疑問。這是因為,在傳統海難救助制度不承認人命救助享有獨立的報酬請求權的情況下,否定人命救助獨立的報酬請求權的倫理基礎在于,無法用金錢對人的生命價值進行衡量。但近年來,針對否定人命救助報酬請求權的傳統觀點,理論界出現了越來越多的批評的聲音,承認人命救助報酬請求權的國家實踐也逐漸增多。參見袁曾:《空難水上救助的道德困境與海上人命救助制度的完善》,載《法學雜志》2017年第6期,第136-137頁。以救助款項中的合理份額來彌補私主體因救助人命而產生的經濟損失,被認為符合樸素的公平正義觀。但是,當國家主管機關因履行職責而救助人命時,由于救助人命產生的費用系由財政負擔,國家主管機關并不會因此而遭受經濟損失,于是就產生了其是否具有《海商法》第185條的人命救助方主體資格,以及能否從其他救助方獲得的救助款項中獲得合理份額的問題。對此,關于第185條的文義解釋和學理研究給出了完全相反的結論,這不僅表明解釋論視角下國家主管機關人命救助方主體資格的不確定性,同時也揭示了《海商法》第185條存在的缺陷。
(一)基于文義解釋的國家主管機關人命救助方主體資格的當然性
就其性質而言,《海商法》第185條屬于授權性規定,授權“在救助作業中救助人命的救助方”從其他救助方獲得的救助款項中獲得合理的份額。因此,為了實現第185條的立法目的,首先甄別出作為權利主體的人命救助方就顯得尤為重要。那么,究竟具備哪些條件才能成為適格的人命救助方呢?對此,應首先通過文義解釋的方法,從第185條的規范用語中探求人命救助方的構成要件。理由在于,充分尊重法律文本、按照法律條文的通常含義進行解釋,往往可以避免對法律的誤解和引起不良后果。參見吳煦:《論海商法解釋中的文義解釋》,載《大連海事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4期,第8-11頁。
《海商法》第185條以簡明的語言規定了該條的權利主體,即“在救助作業中救助人命的救助方”。據此,該條項下的人命救助方應且僅應由兩個要件構成:一是救助了人命,二是救助人命發生于救助作業中。
以下分別對這兩個要件的具體含義進行闡述。
1.關于救助人命
《海商法》和其他相關法律都沒有對救助人命的含義進行明確界定。例如,《海商法》分別在第49條第2款、第51條第1款第7項、第162條第2款第2項以及第185條使用了“救助人命”一詞,在第174條又使用了“救助海上人命”的表述,但是對于何為“救助人命”或者“救助海上人命”,《海商法》未作規定。又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海上交通安全法》(簡稱《海上交通安全法》)第66條規定:“海上遇險人員依法享有獲得生命救助的權利。生命救助優先于環境和財產救助。”同樣,對于“生命救助”的具體含義為何,《海上交通安全法》也沒有作出界定。
學理上一般認為,救助人命就是指對遇險人員的救助。參見袁曾:《海難人命救助的法律義務與現實困境之間矛盾的破解》,載《政治與法律》2020年第1期,第152頁。另有研究定義了海上人命救助,認為海上人命救助是指“對海上遭遇危險的人員進行救助的行為”。參見馮建中:《海上人命救助法律制度研究》,大連海事大學2019年博士學位論文,第117頁。這種理解與基于一般生活經驗對該詞所作的文義解釋是高度一致的。救助人命由表示行為的“救助”和表示對象的“人命”構成,因此這兩個詞的基本含義的組合即構成了救助人命一詞的全部內涵。這意味著,諸如救助的主體是誰,救助的動機為何,救助的效果怎樣等,因為都與“救助”和“人命”的基本含義無關,所以不應作為解釋救助人命一詞時的考量因素。基于此,將救助人命解釋為與主體、動機和結果無關的、純粹以人命為對象的客觀的救助行為是妥當的,因為這并不會超出人們的一般生活經驗和預測可能性。
2.關于救助人命發生于救助作業中
在《海商法》第九章中,救助作業是指有特定救助對象的救助活動,而非一般意義上的救助活動。《海商法》第171條將救助作業的對象限定于遇險的船舶和其他財產。《海商法》第171條規定:“本章規定適用于在海上或者與海相通的可航水域,對遇險的船舶和其他財產進行的救助。”《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商法(修改送審稿)》采取了完全相同的立場,根據其第202條第1款,救助作業是指“對在海上或者與海相通的可航水域遇險的船舶或者其他財產進行援救的任何行為或者活動”。雖然《海商法》第182條第2款以“救助人進行前款規定的救助作業”的規定方式,將救助作業的對象擴大到包括“構成環境污染損害危險的船舶或者船上貨物”,《海商法》第182條第1款規定:“對構成環境污染損害危險的船舶或者船上貨物進行的救助,救助方依照本法第一百八十條規定獲得的救助報酬,少于依照本條規定可以得到的特別補償的,救助方有權依照本條規定,從船舶所有人處獲得相當于救助費用的特別補償。”第182條第2款規定:“救助人進行前款規定的救助作業,取得防止或者減少環境污染損害效果的,船舶所有人依照前款規定應當向救助方支付的特別補償可以另行增加,增加的數額可以達到救助費用的百分之三十。受理爭議的法院或者仲裁機構認為適當,并且考慮到本法第一百八十條第一款的規定,可以判決或者裁決進一步增加特別補償數額;但是,在任何情況下,增加部分不得超過救助費用的百分之一百。”但就其本質而言,仍然沒有突破救助作業應以船舶和其他財產為對象的基本范疇。所以,第185條“在救助作業中救助人命的救助方”中的救助作業應僅指以船舶和其他財產為對象的救助活動,而不包括人命救助。參見司玉琢:《海商法專論》(第4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299頁。另外,就救助作業的實施主體而言,因為第185條對此沒有作出任何明確限制,所以該條中的救助作業似乎還應當理解為由任何主體實施的救助作業。基于這樣的理解,可暫時將第185條項下的救助分為兩種情形:一是救助作業的主體與救助人命的主體各不相同,即其他救助方實施了救助作業,而救助人命的救助方僅在該救助作業中實施了人命救助;二是救助作業的主體與救助人命的主體同一,即同一主體同時實施了救助作業和人命救助。但是,在后一種情形下,將不可避免地引起第185條形式上的邏輯混亂和實際上的操作不能。具體而言,在同一主體既實施了救助作業又救助了人命的情形下,一方面該主體有權因救助作業而獲得救助款項,另一方面其又可因救助人命而從上述救助款項中獲得合理份額,這樣一來就會產生該主體以其自身為對象提出分配合理份額的請求,并因此將已經獲得的救助款項再對其自身進行二次分配的不合理現象。這不可能是立法者在制定第185條時所預期的。相反,若將救助作業的主體和救助人命的主體解釋為不同主體,則上述邏輯混亂和操作不能的問題將得到有效避免。由此不難發現,將第185條規定的救助作業理解為由任何主體實施的救助作業是不恰當的。正是基于這一判斷,對于第185條項下的發生于救助作業中的救助人命,就應當理解為發生在由其他主體(即救助作業方)實施的救助作業中的救助人命,因此也就排除了同一主體同時實施救助作業和人命救助的情形。原本,根據文義解釋,《海商法》第185條項下的救助作業應解釋為由任何主體實施的救助作業,但是由于這一解釋將導致明顯不合理的解釋結論,因此需要通過運用其他解釋方法和解釋技巧進行調適。《公約》第16條第2款的規定支持了筆者的觀點,其規定:“在發生需要救助的事故時,參與救助作業的人命救助人有權從支付給救助船舶,其他財產或防止或減輕環境損害的救助人的報酬中獲得合理份額。”由此可見,“參與救助的人命救助人”與“救助船舶,其他財產或防止或減輕環境損害的救助人”應為不同的主體。
綜上所述,《海商法》第185條的人命救助方應理解為,在由其他救助方(即救助作業方)實施的救助作業中對遇險人員進行救助的任何主體,而不論其身份、救助動機為何,也不管其救助效果怎樣。有研究指出:“根據本條享有的人命救助酬金請求權,不以救助人命是否成功為前提。如果救助方未能使遇險的人員成功獲救,但作出了尋找或者打撈死者尸體等行為,亦應視為人命救助,也可根據本條規定享有酬金請求權。”參見司玉琢、張永堅、蔣躍川編著:《中國海商法注釋》,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292頁。顯然,該研究旨在論證人命救助酬金請求權對“無效果無報酬”原則的突破,而并不是要為人命救助方的主體資格增加新的構成要素。據此,對于國家主管機關履行職責的救助人命,只要發生在由其他救助方(即救助作業方)實施的救助作業中,就應當承認該國家主管機關具有《海商法》第185條項下的人命救助方主體資格。
(二)學理研究對國家主管機關人命救助方主體資格的否定
《海商法》第192條是與國家主管機關的救助活動直接相關的規定。雖然這條規定調整的是國家主管機關的救助作業而非救助人命,但是圍繞該條的解釋,特別是關于國家主管機關在救助作業中是否享有救助報酬請求權的問題,學界逐漸形成了以區分理論為基礎的研究范式,并進而通過將這一研究范式運用于海上人命救助領域,得出了否定國家主管機關人命救助方主體資格的研究結論。
1.第192條不適用于國家主管機關的海上人命救助
《海商法》第192條不適用于海上人命救助,因此不能據此直接得出國家主管機關對于其從事或者控制的海上人命救助依法享有相關權利的結論。從其規范用語可知,第192條是關于救助作業的規定,而如前所述,在《海商法》第九章中,救助作業僅指以船舶和其他財產為對象的救助活動,其中并不包括海上人命救助。盡管近年來有研究持續呼吁將救助作業的對象擴大到包括人命救助,但就現階段而言,此類呼吁還沒有得到理論界和實務界的積極回應,因此也不可能產生擴大現行法下救助作業對象的效果。參見張新平:《海商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383頁;袁曾:《空難水上救助的道德困境與海上人命救助制度的完善》,載《法學雜志》2017年第6期,第138-139頁。據此不難得出結論,即因為海上人命救助不在《海商法》所規定的救助作業的范圍之內,所以國家主管機關從事或者控制的海上人命救助不受《海商法》第192條的調整。換言之,由于《海商法》第192條的規定與海上人命救助并無直接關系,故不能直接援引作為支持國家主管機關救助人命時的權利主張的規范依據。
2.以區分理論為基礎的國家主管機關救助報酬請求權的二分
關于國家主管機關在其從事或者控制的救助作業中的救助報酬請求權問題,當前的理論研究傾向于以區分理論為基礎來進行評價。在區分理論下,國家主管機關從事或者控制的救助作業被區分為職責內的救助作業和職責外的救助作業,對于職責內的救助作業,國家主管機關無權請求救助報酬或者補償,而對于職責外的救助作業則有權主張。
例如,有研究在解讀《海商法》第192條的含義時指出,該條規定的救助作業實際上是指《海商法》第九章所規定的以自愿為前提的救助作業,而不包括主管機關授權履職的強制救助,因此國家主管機關根據該條從事救助作業時,仍然符合海難救助的構成要件,故有權依法取得救助報酬和特別補償。相反,當國家主管機關因履行職責而實施救助時,因成立海難救助所必須的自愿性條件沒有得到滿足,所以此種救助不屬于海難救助,故國家主管機關無權依法取得救助報酬和特別補償。參見司玉琢:《海商法專論》(第4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311-312頁。類似的觀點認為,公務人員對“遇險的船舶、人員及財產實施救助是他們的職責,因而缺乏自愿的因素,不能請求救助報酬”。參見張麗英:《海商法學》(第4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22年版,第274頁。
可見,以區分理論為基礎的研究范式遵循“三步走”的分析進路:首先,對國家主管機關的救助行為進行定性,區分其為職責內救助還是職責外救助;其次,以傳統海難救助中的自愿性構成要件作為評價工具,對于國家主管機關因履行職責而實施的救助,因不滿足自愿性構成要件而將其排除在海難救助的范圍之外;最后,基于國家主管機關職責內的救助不屬于海難救助,得出其無權因此類救助而請求救助報酬和特別補償的結論。由此,在基于區分理論的“三步走”分析進路指引下,對于國家主管機關從事或者控制的救助作業的救助報酬請求權問題,研究者們得出了具有高度同質性的研究結論。例如,有研究認為,國家有關主管機關負有救助義務時不享有救助款項請求權,理由是傳統的海難救助報酬的請求權成立條件之一是救助的自愿性,即救助方沒有救助義務時才能請求救助報酬。參見胡正良等:《〈海商法〉修改基本理論與主要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449頁。類似的研究結論認為,“相對而言,以職責內外進行劃分的原則建立在海難救助報酬自愿性要件基礎之上,與現有海商法理論相符,更值得贊同”。參見劉長霞:《公共當局海難救助報酬請求權研究——以確立原則為視角》,載《河北法學》2015年第4期,第82頁。
3.區分理論適用場景的擴大化
雖然區分理論衍生于對國家主管機關從事或者控制的救助作業的研究,但這并不妨礙研究者將其適用場景擴大化,以其作為方法論來評價國家主管機關救助海上人命時的相關權利問題。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涉及到救助局的海上救助。
有研究在對救助局的救助進行類型化的基礎上,分別對其相關權利進行評價。參見胡正良等:《〈海商法〉修改基本理論與主要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448頁。一是僅實施了人命救助。此種情形下,一方面,救助局由于具有救助海上人命的義務,因此不享有《海商法》第九章規定的酬金請求權;另一方面,基于同樣義務,若在同一救助中有其他救助方對船舶或者其他財產實施了救助,則在確定其他救助方可以獲得的救助報酬或特別補償中不應考慮救助局救助人命的因素。二是僅實施了財產救助。此時由于救助局不具有救助船舶或者其他財產的義務,其實施的救助行為屬職責外救助,因此無論此種救助是否涉及人命救助,其均具有《海商法》第九章規定的救助報酬或者特別補償的請求權。三是同時實施了財產救助和人命救助。此種情形下,救助局的救助行為包括針對財產救助的職責外救助和針對人命救助的職責內救助,前者可依法取得救助報酬或者特別補償,但因為救助人命是其法定義務,因此在確定可以獲得的救助報酬或者特別補償數額時不應考慮救助海上人命的因素。雖然客觀上并不能排除同一主體同時實施救助作業和救助人命的情形,但是基于以下兩點理由,筆者認為《海商法》第185條的規定并不適用于這種情形。其一,如文中所述,將第185條適用于同一主體同時實施救助作業和救助人命的情形,將引發邏輯混亂和操作不能的問題。其二,考慮到第185條的立法目的,立法者所設想的該條的適用場景應是人命救助方純粹救助人命的情形,因為只有在此種情形下,按照傳統海難救助制度,人命救助方才無權獲得任何補償,也因此才需要特別的制度設計來鼓勵其救助海上人命;相反,在救助方既實施救助作業又救助人命的情形下,救助方即兼具了人命救助方和救助作業方的雙重身份,因此其完全可以基于傳統海難救助制度以救助作業方的身份主張救助報酬或者特別補償,而沒有必要通過另外設立合理份額請求權的方式來對其救助人命的行為予以補償。
由此,不難窺見當前相關理論研究的一個鮮明立場,即國家主管機關因履行職責而救助人命的,不僅無權請求酬金,而且無權從其他救助方獲得的救助款項中獲得合理的份額。在《海商法》第185條規定之下,有權從其他救助方獲得的救助款項中獲得合理份額的主體是“在救助作業中救助人命”的人命救助方,所以上述立場實際上相當于否認了國家主管機關在《海商法》第185條項下的人命救助方主體資格。
三、國家主管機關人命救助方主體資格應然性的證成
關于國家主管機關因履行職責而救助人命時是否具有《海商法》第185條項下的人命救助方主體資格,該條的文義解釋和相關學理研究呈現出針鋒相對之勢。導致這一結果的根源在于第185條規定的不明確性。由于長期以來學界對第185條所涉海上人命救助的關注度不夠,加之司法實踐中的海難救助糾紛多為救助合同履行糾紛而極少涉及人命救助,因此一定程度上遲滯了這一對立的顯在化進程。《海商法》的修改為從根源上消除第185條的解釋對立提供了機會。以《海商法》修改為契機對第185條加以完善,以明確承認國家主管機關人命救助方主體資格的方式來定分止爭,不僅有利于維護《海商法》的穩定性和權威性,而且還能為將來可能發生的海上人命救助糾紛提供明確的裁判指引,從而切實提升《海商法》的實效性。當然,為了實現這一目的,還需要基于有說服力的理由,對承認國家主管機關人命救助方主體資格的正當性進行論證,以此作為啟動和推進相關修法程序的必要法理支撐。
(一)司法實踐對國家主管機關人命救助方主體資格的背書
根據對證成國家主管機關人命救助方主體資格應然性所發揮的功能不同,可以把當前的司法實踐分為兩類。第一類是發揮直接功能的司法實踐。這類實踐雖然數量極為有限,這類案件數量極少的主要原因已在文中闡述,需要強調的是,不能據此便得出司法實踐對國家主管機關的人命救助方主體資格持消極態度的結論。實際上恰恰相反,在當前的司法實踐中,還未見明確否定國家主管機關人命救助方主體資格的案例。但是因為司法機關在判決中旗幟鮮明地表達了其認可的立場,因此自然成為支持國家主管機關人命救助方主體資格的最有力論據。第二類是發揮間接功能的司法實踐。這類實踐多與國家主管機關在其從事的救助作業中的救助報酬請求權有關,因而并不直接涉及人命救助。這類實踐的共性在于,司法機關在判決中毫無例外地承認國家主管機關職責內救助作業的救助報酬請求權,這樣就明確排除了被研究者援引作為理論基礎的區分理論的司法適用空間。在這樣的背景下,若繼續以區分理論的擴大化適用來否認國家主管機關的人命救助方主體資格,則將無法回避如何與主流司法實踐進行調和的問題。
1.明確承認國家主管機關人命救助方主體資格的司法實踐
筆者以中國裁判文書網和中國海事審判網為檢索平臺,分別以“海難救助”“人命救助”“《海商法》第185條”為關鍵詞進行檢索,對檢索結果進行閱讀、篩選后,僅獲得一篇明確承認國家主管機關人命救助方主體資格的裁判文書,即上海海事法院(2014)滬海法商初字第908號民事判決書,所涉案情如下。
被告杰德有限責任公司所有的“杰德”輪于2011年11月30日18時35分在上海長江口水域擱淺。上海海上搜救中心接到被告的遇險信息后,向原告交通運輸部東海救助局先后發出第53號和第54號搜救任務書,要求原告對難船和船上人員進行救助。原告接受了兩份任務書指派的任務,派出“東海救116”輪前往事發海域施救。11月30日20時17分,“東海救116”輪抵達事故現場施救,12月1日凌晨1時04分,12名遇險船員全部登上“東海救116”輪,救助人命任務完成。12月1日凌晨2時29分,原告得知被告委托案外人上海打撈局負責后續救助事宜后,指令“東海救116”輪離開事故現場。原告訴稱,其受上海海上搜救中心指派對“杰德”輪進行了財產救助,在財產救助期間對船上12名船員進行了人命救助,并在防止環境污染損害方面作出了貢獻,因此請求判令被告支付救助費用及利息損失。被告辯稱,原告系由國家財政補助收入的事業單位法人,此次救助是人命救助,且系原告的法定職責,因此原告無報酬請求權。
上海海事法院認為,本案爭議的焦點在于:涉案救助作業的性質和原告的救助報酬請求是否成立。筆者認為,法院“涉案救助作業的性質”的表述一定程度上存在邏輯混亂的問題。如文中所述,救助作業在《海商法》中是指以船舶和其他財產為對象的救助活動,其本質上就是一種財產救助,因此似乎沒有必要也不可能再去探討救助作業在性質上究竟屬于財產救助還是人命救助的問題。筆者推測法院的本意是要認定涉案救助活動(而非救助作業)的性質為何。關于前者,法院指出,原告所有的“東海救116”輪施放救助艇,使12名遇險船員安全登船,脫離危險,因此認定涉案救助活動是一起成功的海上人命救助案例。關于后者,法院認為在案證據不能證明原告對“杰德”輪存在救助行為,原告也未能證明其采取的措施與“杰德”輪成功獲救之間存在因果關系,取得了救助效果,故其無權獲得救助報酬。但法院同時指出,雖然原告依法不能就海上人命救助向被告請求酬金,但根據《海商法》第185條的規定,原告有權從救助船舶或其他財產、防止或者減少環境污染損害的救助方獲得的救助款項中獲得合理的份額,因此“原告仍有權通過其他合法途徑獲得合理的補償”。
對于法院的上述判決,有必要從以下兩點作進一步評價。
第一,在法院看來,《海商法》中的救助報酬請求權僅適用于財產救助的情形,遵循“無效果無報酬”的基本原則,且單純的人命救助不能作為救助報酬請求權的基礎。該案中,雖然法院認定東海救助局對“杰德”輪的救助是一起成功的海上人命救助案例,但是并沒有因此而承認東海救助局享有救助報酬請求權,這表明法院堅持的是傳統海難救助制度中“純粹的人命救助不產生救助報酬請求權”的基本立場。而且,在東海救助局以實施了針對“杰德”輪的財產救助為由主張救助報酬時,法院以不存在被證據所證明的救助行為和因果關系為由不予認可,同樣彰顯了法院對傳統海難救助制度中“無效果無報酬”這一基本原則的堅持。
第二,法院在判決中明確承認了國家主管機關因履行職責而救助人命時的《海商法》第185條項下的人命救助方主體資格。訴訟中,被告提出了原告系由國家財政補助收入的事業單位法人,此次救助是人命救助,且系原告的法定職責,因此原告無報酬請求權。雖然法院的判決因最終否定了原告的報酬請求權而客觀上回應了被告的關切,但很顯然這并不意味著法院采納了被告的抗辯理由。如前所述,法院的判決是基于對傳統海難救助制度中基本原則的堅守,法院并沒有因為原告的救助人命系履行法定職責而直接否定其救助報酬請求權。換言之,本案中原告的國家主管機關身份,以及其履行法定職責的行為性質都并沒有為法院作出上述判決貢獻任何原因力。相反,法院在援引《海商法》第185條的基礎上指出,“原告仍有權通過其他合法途徑獲得合理的補償”,這表明法院對第185條的解釋立場是,即便國家主管機關因履行職責而救助人命時無權請求救助報酬,也不能向被救助人員請求酬金,但其仍有權作為第185條項下的人命救助方,從其他救助作業方獲得的救助款項中獲得合理的份額。
盡管上海海事法院對《海商法》第185條作出了明確的釋法說理,并且為東海救助局因救助人命而獲得補償指明了合法的路徑,但東海救助局并沒有向本案的救助作業方請求分配其救助款項的合理份額,而是選擇了提起上訴,在二審中繼續主張己方實施了針對“杰德”輪的財產救助并因此有權獲得救助報酬。本案后經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主持調解,雙方達成協議,被告杰德有限責任公司自愿向東海救助局支付2萬美元作為對其人道主義精神的支持。那么,為什么東海救助局沒有以《海商法》第185條的人命救助方的身份請求從救助作業方獲得的救助款項中分配合理份額呢?根本原因或許在于,本案中請求分配合理份額的客觀條件沒有成就。如前所述,在《海商法》第185條項下,只有救助人命與救助作業主體不同且相伴發生,申言之只有在由其他救助方實施的救助作業中救助了人命,人命救助方才有權從前者的救助款項中獲得合理份額。根據法院認定的事實,一方面,“杰德”輪擱淺后,被告杰德有限責任公司
于當晚與上海打撈局簽訂了“無效果無報酬”的勞氏標準格式救助合同,上海打撈局則根據合同派出拖輪前往現場,并于12月1日4時50分抵達;另一方面,東海救助局對被告12名遇險船員的救助于12月1日凌晨1時04分結束,至12月1日凌晨2時29分,原告在得知被告委托上海打撈局負責后續救助事宜后便指令“東海救116”輪離開了事故現場。可見,東海救助局的救助人命發生于上海打撈局的救助作業之前,其性質實為一起純粹的人命救助,因此并不受《海商法》第185條調整,故東海救助局無權根據該條請求分配合理份額。據此筆者認為,法院作出的“原告作為在救助作業中救助人命的救助方……仍有權通過其他合法途徑獲得合理的補償”的判決值得商榷。但這并不影響法院在判決中表明對《海商法》第185條的基本立場,即國家主管機關因履行職責救助人命的,有權根據《海商法》第185條獲得合理的份額。
2.否定以區分理論來評價國家主管機關救助活動的司法實踐
否定國家主管機關人命救助方主體資格的學理研究的結論,是以區分理論為論證的邏輯起點,通過將評價對象由國家主管機關的救助作業替換為國家主管機關的人命救助活動而構建起來的。這一結論的缺陷在于,把區分理論默認為一種先驗的、具有天然可適用性的評價工具,并在此基礎上展開進一步的邏輯論證。但實際上,《海商法》第192條并沒有對國家主管機關的救助作業作職責內外的區分,這就從制定法層面對適用區分理論的正當性提出了有力質疑。不僅如此,關于國家主管機關救助報酬請求權的司法實踐也沒有給區分理論預留下任何可能的適用空間。
例如,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汕頭海事局訴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廣東粵東石油分公司救助合同糾紛案”中,參見廣州海事法院(2005)廣海法初字第182號民事判決書。廣州海事法院認定原告汕頭海事局對被告所屬“明輝8”輪船載貨油的救助行為是基于履行防止船舶污染海域職責的行為,且該救助作業屬于國家主管機關從事或者控制的救助作業,因此原告作為控制救助作業的救助方,有權根據《海商法》第九章的規定獲得救助報酬。在“嵊泗縣人民政府防汛防旱防臺指揮部辦公室訴帝遠股份有限公司海難救助糾紛案”中,參見寧波海事法院(2017)浙72民初290號民事判決書。履行行政職責的原告為了公共安全,對涉案船舶采取了派船員上船值守、拖輪拖帶、沖灘沉底等安全措施,并承擔了相應費用。寧波海事法院經審理認為,原告的行為構成國家有關主管機關直接從事的海難救助,依法有權享受救助作業的權利和補償,有權請求被救助人支付合理的救助費用。
長期的司法實踐表明,司法機關在評價國家主管機關的救助報酬請求權問題時,已經形成了明確排除區分理論適用的基本立場,即“只要是主管機關的海難救助行為,不管其是否屬于主管機關的法定職責,都具有海難救助報酬請求權”。參見劉長霞:《公共當局海難救助報酬請求權研究——以確立原則為視角》,載《河北法學》2015年第4期,第88頁。如此一來,司法實踐就通過一種類似于“釜底抽薪”的方式,切斷了否認國家主管機關人命救助方主體資格的學理研究的理論供給。換個角度而言,這類司法實踐實際上間接地為證成國家主管機關的人命救助方主體資格提供了實證支撐。
(二)承認國家主管機關人命救助方主體資格有助于人命救助優先原則的落實
《海上交通安全法》第66條規定“生命救助優先于環境和財產救助”,從而在制定法中確立了海難救助中的人命救助優先原則。人命救助優先原則明確了海難救助中不同價值之間的位階關系,通過賦予生命價值相對于環境價值和財產價值的優先順位,不僅在理念層面彰顯了對生命的尊重,回應了時代關切,而且在實踐層面為海難救助活動提供了宏觀操作指引。但是不可否認,現實中人命救助優先原則的具體落實仍面臨諸多困境,因此亟需建立完善的促進機制。參見李天生、王春霞:《〈海上交通安全法〉海上人命救助促進機制的缺陷與完善》,載《世界海運》2022年第10期,第27-28頁。
1.人命救助優先原則的困境
救助方的救助意愿是整個救助鏈條中最基礎的一環,若救助意愿闕如,則積極的救助措施和有效的救助效果便失去了期待可能性。這決定了人命救助優先原則的有效落實,有賴于最大限度地排除人命救助方的后顧之憂,充分激發其救助人命的積極性。但是,基于以下兩點原因,現行海難救助制度下人命救助方的救助積極性受到嚴重制約,并導致現實中“見死不救”或者選擇性救助的情況屢屢發生,參見袁曾:《空難水上救助的道德困境與海上人命救助制度的完善》,載《法學雜志》2017年第6期,第135頁。人命救助優先原則的落實面臨嚴峻挑戰。
一是傳統觀念的影響。受傳統海難救助制度的影響,海上人命救助系義務性、無償性救助的觀念仍然根深蒂固。傳統觀點認為唯有對物的救助才產生救助報酬請求權。參見司玉琢主編:《海商法》(第5版),法律出版社2023年版,第265頁。另有研究認為,“如果某救助方單純地在海上救助了人命,并不存在針對財產或環境的救助,因而也就不存在救助報酬和特別補償”,所以該人命救助方自然不享有《海商法》第185條規定的酬金請求權。參見司玉琢、張永堅、蔣躍川編著:《中國海商法注釋》,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292頁。雖然《海商法》第185條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緩和作用,但還不足以抵消基于傳統觀念而產生的顧慮。理由在于,在《海商法》第185條之下,人命救助方能否從救助款項中獲得合理份額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如前所述,只有當人命救助與第三方實施的財產救助相伴發生且該財產救助取得效果時,人命救助方才有權獲得合理份額。可見,人命救助行為與合理份額請求權之間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關系,不能排除人命救助方雖實施了人命救助但是無法獲得任何補償的可能情形,這成為影響其救助積極性的重要因素。
二是救助人命所固有的風險。實踐中,相對于財產救助而言,人命救助的救助方往往需要承擔更大的風險。例如,在人命救助方已經使遇險人員成功登上施救船之后,其仍負有一定的照顧義務,如果遇險人員于在船期間遭受損失,除非人命救助方舉證證明其已盡到妥善照顧義務且對該損失的發生無故意或重大過失,否則將承擔相應的責任;參見李新天主編:《民商法律熱點與案例研究(第一輯)》,武漢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47-252頁。此外,在被救人員具有外國國籍的情況下,人命救助方還將不得不面對在何地、以何種程序使被救人員離船等復雜的程序性問題。由于成功施救后的照顧義務延長了人命救助方的責任期間,而相關的程序性負擔又增加了救助人命的風險,人命救助方對救助人命往往“望而卻步”。
2.承認國家主管機關人命救助方主體資格對落實人命救助優先原則的促進
在現行制度難以充分激發人命救助方救助人命積極性的背景下,盡量擴大《海商法》第185條人命救助方的范圍,客觀上使更多的主體能夠有機會享受該條的制度紅利,寄希望于通過主體的增量來產生救助人命機會增加的效果,這對于保障落實人命救助優先原則而言,不失為一種值得嘗試的權宜之計。當然,承認救助人命的獨立的報酬請求權才是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最有效方法,但是這涉及對傳統海難救助制度和觀念的根本性變革,因此短期內實現的可期待性不大。為此,應當善意地遵守《海商法》第185條的文義解釋,承認國家主管機關在該條項下的人命救助方主體資格。
首先,承認國家主管機關的人命救助方主體資格體現了對生命的尊重,與人命救助優先原則的基本精神相符。承認國家主管機關的人命救助方主體資格,意味著一定條件下國家主管機關可因救助人命而從其他救助方的救助款項中獲得合理份額,這樣就可以為本單位救助設備的維護、保養和更新,以及救助人員的引進、培養和訓練等提供財力支持,從而不斷提升救助人命的能力,保障救助人命的效果。相反,否認國家主管機關的人命救助方主體資格,將使其在現行制度下無法因救助人命而獲得任何額外補償。參見傅廷中:《國際視野內的中國海難救助立法》,載《國際法研究》2022年第3期,第23頁。具體而言,雖然中國目前已經建立了較為完善的海上搜救獎勵機制,但其獎勵對象僅為社會救助力量,而不包括國家主管機關。例如,根據2007年的《海(水)上搜救獎勵專項資金管理暫行辦法》第4條、第5條,國家設立的海上搜救獎勵專項資金只用以獎勵參與中國海上搜救中心組織指揮的重特大海上搜救行動的社會搜救力量。在這樣的制度背景下,如果不承認國家主管機關的人命救助方主體資格,就意味著其只能以有限的財政預算為基礎來統籌運營救助人命事務,顯然,這極有可能阻礙其救助人命能力的持續提升。在中國的海難救助實踐中,長期存在公共當局所花費的救助成本收不回來的“入不敷出”的局面。參見張湘蘭:《海商法》,武漢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405頁。
其次,承認國家主管機關的人命救助方主體資格有利于進一步鼓勵海上人命救助,契合人命救助優先原則的價值目標。“設立海難救助法律制度的目的在于鼓勵海難救助”,司玉琢、吳煦:《雇傭救助的法律屬性及法律適用》,載《中國海商法研究》2016年第3期,第9頁。作為海難救助制度組成部分的海上人命救助自然也應該以鼓勵性和激勵性特征為其制度的精神內核,在制度內容的設計上配之以相應機制,最大限度地鼓勵和激發相關主體救助人命的積極性。與傳統觀念和實踐相比,將國家主管機關納入《海商法》第185條項下人命救助方的范圍,可以豐富國家主管機關救助人命積極性的生成渠道,促使其更加積極主動地從事海上人命救助,從而通過海上救助人命主體的增量來為有效落實人命救助優先原則提供保障。具體而言,承認國家主管機關的人命救助方主體資格,意味著在《海商法》第185條之下,國家主管機關的救助人命動機將受到“法定職責+經濟激勵”的雙重激勵,相較于以往基于“法定職責必須為”的單軌制而言,疊加經濟激勵的雙軌制無疑對于提升國家主管機關的救助人命積極性更加具有可行性。
(三)否定國家主管機關的人命救助方主體資格缺乏合理性基礎
1.否定國家主管機關的人命救助方主體資格有違《海商法》第185條的文義解釋
法律用語是以立法者為橋梁和紐帶的民意的文字表達,因此按照法律用語的通常含義對其進行解釋,是尊重民意、體現民主的題中應有之義。當然,為了增加變動不居的社會環境下法律的可適用性,避免機械的文義解釋造成法適用效果的僵化和扭曲,法解釋論和實踐也允許在一定情況下適當擴張或者限縮法律用語含義的射程范圍。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這其實僅是一種基于法律用語基本含義的適度變通,而非無視法律用語基本含義的解釋上的任意發揮。實際上,在法律解釋過程中,文義解釋的優先地位必須予以保證,只有在出現文義缺失、過于寬泛或過于狹隘的情況時,才可以通過目的性擴張或者目的性限縮等解釋方法的介入,成就正義的解釋結果。參見鄭菲:《文義解釋與目的解釋之關系探析》,載《法律方法》2019年第2期,第10頁。
在《海商法》第185條的文義解釋下,“救助人命的救助方”一詞具有將國家主管機關納入其中的足夠的包容性;更為重要的是,將“救助人命的救助方”解釋為包括國家主管機關,不僅不會導致引起其他解釋方法介入的文義過于寬泛的問題,而且還與第185條的立法本意高度契合。具言之,《海商法》第192條明確規定了國家主管機關從事或者控制的救助作業的救助報酬請求權,這充分表明在制定《海商法》第九章的相關規范時,立法者是將國家主管機關作為救助活動的主體來對待的。在這樣的立法觀念之下,如果立法者具有否定國家主管機關人命救助方主體資格的意圖,則其理應在第185條中作出明確的排除性規定;反之,則只能結合對第185條和第192條的體系解釋,推定立法者并無上述否定意圖。因此,應善意地將《海商法》第185條中的“救助人命的救助方”解釋為包括國家主管機關,這體現了對立法意圖及其背后的民意的充分尊重;而否定國家主管機關在該條項下的人命救助方主體資格,則不僅偏離了立法本意,而且客觀上產生了“解釋立法”的消極后果,因此是不可取的。
2.否定國家主管機關的人命救助方主體資格有損人命救助優先原則的基本精神
人命救助優先原則具有生命至上的精神內核。在現行海難救助制度中引入人命救助優先原則,要求在制度內容層面輔之以相應規范,以體現充分尊重生命的基本精神。否定國家主管機關在《海商法》第185條項下的人命救助方主體資格,在客觀層面產生的結果是,現行制度下國家主管機關救助財產和環境可以獲得救助報酬和補償,《海商法》第179條規定:“救助方對遇險的船舶和其他財產的救助,取得效果的,有權獲得救助報酬;救助未取得效果的,除本法第一百八十二條或者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者合同另有約定外,無權獲得救助款項。”而救助人命卻無法獲得任何補償。這一結果的合理性顯然是存疑的,因為其不僅無法使人從觀念上形成生命價值具有相對于環境價值和財產價值的高位階性的認知,甚至會因為規范性落差而讓人懷疑人命救助優先原則的現實意義。
既然人命救助優先原則確立了人命價值的優位性,那么就應當在規范層面作出相應的回應,以規范為載體來體現對生命價值的優先保護。在設立獨立的人命救助報酬請求權為時尚早的情況下,將《海商法》第185條的人命救助方解釋為包括國家主管機關,既體現了《海商法》海上人命救助制度吸收人命救助優先原則理念的成果,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人命救助優先原則下現行海上人命救助制度的規范漏洞,實現了制度理念與制度規范的有機協調。
3.救助的非自愿性不應成為否定國家主管機關人命救助方主體資格的依據
其一,以非自愿性作為依據,無法回答為何船長在非自愿的情形下救助人命不影響其人命救助方主體資格的問題。根據《海商法》第174條,船長在不嚴重危及本船和船上人員安全的情況下,有義務盡力救助海上人命。船長的這一救助人命的義務自羅德海法時代以來即被認為是一種強制性義務。參見馮建中:《海上人命救助法律制度研究》,大連海事大學2019年博士學位論文,第108頁。另有觀點提出,船長負有救助海上遇險人員的義務已被成文法和習慣法所確認。參見袁曾:《海難人命救助的法律義務與現實困境之間矛盾的破解》,載《政治與法律》2020年第1期,第151-152頁。據此,雖然現行法下船長對于救助海上人命并不承擔絕對的義務,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其對是否救助海上人命的裁量權不受任何限制。如果救助海上人命不致于嚴重危及本船和船上人員的安全,則船長就應當履行法定的救助義務,就此而言,現行法下船長救助海上人命也并不總是以自愿性為基礎。問題是,無論是理論研究還是司法實踐,似乎從來都沒有把船長在《海商法》第185條項下的人命救助方主體資格視為問題。換言之,無論船長救助海上人命的動機是基于人道主義還是基于法定義務,也不管其主觀意愿是自愿還是非自愿,其人命救助方主體資格都從來沒有被質疑過。既然如此,以救助人命行為系非自愿行為為理由來否定國家主管機關的人命救助方主體資格,便難免有適用雙重標準之嫌,缺乏說服力。
其二,以非自愿性作為依據,無法回答為何國家主管機關非自愿性的救助作業可以獲得救助報酬的問題。根據《海商法》第192條,國家主管機關對于其從事或者控制的救助作業享有救助報酬請求權,司法實踐則表明,該救助作業是否為國家主管機關履行法定職責所實施,對于其救助報酬請求權并無影響。顯然,當國家主管機關因履行法定職責而實施救助作業時,其救助行為并非基于以自由裁量為特征的自愿性,而是遵守來自法律的強制性命令的結果,因此具有明顯的非自愿性色彩。由此可以提出的合理質疑是,同樣是國家主管機關實施的非自愿的救助行為,為什么以財產和環境為對象的救助作業都可以取得救助報酬或者補償,而以相對而言具有更高的價值位階的人命為對象的海上人命救助卻反而不能獲得合理份額呢?在對此缺乏合理解釋的情況下,只能得出以救助行為的非自愿性來否定國家主管機關人命救助方主體資格有失妥當的結論。
四、結語
在現行《海商法》第185條的規定之下,國家主管機關是否具有人命救助方主體資格存在不確定性。根據第185條的文義解釋,“在救助作業中救助人命的救助方”的用語并沒有將國家主管機關排除在外的法律效果,因此承認國家主管機關在該條項下的人命救助方主體資格具有正當性。而學理研究則基于區分理論,主張國家主管機關的救助人命系履行法定職責,救助行為的非自愿性阻卻了其人命救助方主體資格的取得。解釋論下《海商法》第185條規范含義的沖突,有損該法的確定性、權威性和實效性,因此有必要以修法為契機對第185條予以完善,以明確承認國家主管機關在該條項下的人命救助方主體資格。作此修改的法理依據在于,承認國家主管機關的人命救助方主體資格既有司法實踐的有力背書,又可為有效落實人命救助優先原則提供保障;而否定國家主管機關的人命救助方主體資格不僅違反第185條的文義解釋、違背其立法本意,而且有損人命救助優先原則的基本精神,并因缺乏合理性基礎而不具可采性。綜上,建議將《海商法》第185條進行如下修改:
“在由其他救助方實施的救助作業中救助人命的救助方,不得向被救助人請求報酬,但是有權從其他救助方因救助作業而獲得的救助款項中獲得合理的份額。
前款規定的救助人命的救助方,包括有關國家主管機關。有關國家主管機關因履行職責而救助人命的,不影響其依據前款規定獲得合理的份額。”
Status of the Competent State Authority as the Salvor of Human Life
—A Perspective from the Perfection of Article 185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Code
ZHAO Xianghua
(School of Humanity and Law,Jiangsu Ocean University,Lianyungang 222005,China)
Abstract:There is a controversy over whether to recognize the status of the competent state authority as the salvor of human life under Article 185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Code. According to the textual interpretation of Article 185, there are two constitutive requirements for the qualification of the salvor of human life. One is that the relevant entity has performed an act of saving human life at sea,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 act is based on fulfilling legal responsibilities, and the other is that the act of saving human life occurred in the salvage operation in the sense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Code. Thus, under the textual interpretation of Article 185, the status of the entity as the salvor of human life has nothing to do with its identity, and therefore the competent state authority should be the qualified salvor of human life. On the contrary, current academic research holds a negative attitude towards the status of the competent state authority as the salvor of human life. The reason is that the salvage of human life at sea under Article 185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Code should be voluntary salvage activitie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salvage of human life at sea by the competent state authorities is an act of fulfilling legal responsibilities. Because of the lack of voluntary elements in salvage activities, it should not be recognized as a qualified salvor of human life under Article 185. The interpretation of Article 185 is contradictory and undermines the certainty and authority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Code. Therefore, the revision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Code should be taken as an opportunity to clearly recognize the status of the competent state authority as the salvor of human life. The reasons for this proposed amendment are as follows. Firstly, the current judicial practice strongly endorses the status of the competent state authority as the salvor of human life. On the one hand, in the relevant jurisprudence, the court has clearly recognized that while the competent state authority is not entitled to a remuneration when saving human life in the performance of its duties, it is entitled, as a salvor of human life under Article 185, to receive a fair share of the payment awarded to the salvors for salving the ship or other property or for preventing or minimizing the pollution damage to the environment. On the other hand, in several cases, the court refused to recognize that the lack of voluntariness of salvage has the effect of denying the status of salvage operators. Secondly, the recognition of the status of the competent state authority as the salvor of human life helps to break through the current difficulties faced by salvage of human life at sea, promotes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priority in saving human life, and reflects the greatest respect for the value of human life. Finally, there is no reasonable basis for denying the status of the competent state authority as the salvor of human life. This is not only because the negative position is contrary to the textual interpretation of Article 185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Code, but also because it undermines the basic spirit of the principle of priority in saving human life. Moreover, denying the status of the competent state authority as the salvor of human life based on the lack of voluntariness in salvage of human life will inevitably lead to confusion and conflict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Code. By specifying the status of the competent state authority as the salvor of human life in Article 185, increasing legal certainty, author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Code can reasonably be expected.
Key words:Chinese Maritime Code; the competent state authority; status as the salvor of human life; the principle of priority in saving human life
基金項目:2019年度江蘇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項目“‘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司法協調機制建構研究”(2019SJZDA016)
作者簡介:趙向華,男,江蘇海洋大學文法學院副教授,江蘇省“一帶一路”法律服務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