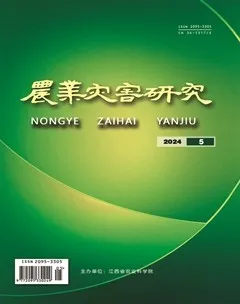數字普惠金融對首批國家生態文明試驗區綠色發展影響的研究





摘 要:數字普惠金融是當前我國經濟邁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重要驅動力,能否助力綠色發展水平的提高是首批國家生態文明試驗區未來發展的關鍵。在測度綠色發展水平指數的基礎上,利用2011—2022年閩贛黔三省的面板數據,通過雙向固定效應模型、中介效應模型和門檻效應模型考察了數字金融對首批國家生態文明試驗區綠色發展水平的影響。結果表明:數字普惠金融可以顯著提高該地區的綠色發展水平;數字普惠金融可通過提升科技創新效率間接提高該地區的綠色發展水平。
關鍵詞:數字普惠金融;綠色發展;中介效應
中圖分類號:F832 文獻標志碼:B 文章編號:2095–3305(2024)05–0-04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水平快速提升,而這種粗放型的經濟發展模式也引發了一系列破壞生態甚至威脅人類生存的事件。黨的十九大報告首次提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在2021“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中,也未設定地區生產總值的預期增長規劃,這意味著穩定、均衡、綠色、可持續的經濟高質量發展已成為當今時代經濟發展的主流。綠色發展作為高質量發展的核心形態,是生態文明建設和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的必然選擇[1]。作為一種與數字經濟相匹配的金融業態,數字金融是當前我國經濟邁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重要驅動力。“十四五”期間,國家重點實施數字普惠金融,加強數字普惠金融服務是實現共同富裕的時代需求。首批國家生態文明試驗區是“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思想的最佳體現,是將“綠色發展”的頂層設計和“地方實際”有機結合的先鋒。為此,研究閩、贛、黔三省能否實現生態良好與經濟增長齊頭并進的雙贏局面具有理論和現實意義。
1 理論假設
數字普惠金融可以通過拓寬融資渠道和優化資源配置,從而提高綠色發展水平。一方面,數字普惠金融利用互聯網、大數據等新興數字技術,能夠減少融資成本、豐富融資渠道、提高融資效率。金融中介機構通過各種融資渠道,為有競爭力的公司提供資金援助和技術研究。同時,數字技術可以實現金融服務交易的便捷化,降低金融服務的供給成本和大眾的使用成本。金融產品的普惠性使更多的企業和居民了解到數字金融產品的優勢,有助于緩解金融需求不足的問題,實現雙方共贏。另一方面,數字普惠金融能夠重新配置不同企業間的資源。傳統金融機構出于降低成本和提高收益的考慮,往往會篩選出可抵御固定資產多和盈利能力高的大型企業提供大額的信貸產品,這會導致金融資源始終流向高污染、高能耗的重工業企業,而時常無法滿足新興的服務業等第三產業的金融需求[2]。數字普惠金融可以通過其特有的信息技術精準搜集不同產業的金融需求,分別提供合理適配的金融產品和服務,將有限的資源投入產出增速較快的地區或個體,從而促進全社會資源的有效利用并提高區域綠色發展水平[3-4]。
數字普惠金融還可以通過綠色技術創新和產業結構升級間接提高綠色發展水平。一方面,數字普惠金融通過支持技術創新提高綠色發展水平。企業的技術創新是一個具有成本沉沒性、成果不確定的活動,技術和成果之間存在一定的滯后時間差。因此,數字普惠金融以其普惠、便利、低價的優勢為技術創新提供了充分的融資支持。企業的綠色技術創新可以打破原始資源稀缺和傳統技術低效的限制,在保證產量的前提下降低能耗,從而大幅提高綠色發展水平。另一方面,數字普惠金融的快速發展不僅可以通過加快技術創新替代甚至淘汰一些落后產業,還能利用新技術為傳統產業賦能增效,從而形成新的行業和模式,提高要素的配置效率,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圖1)。數字普惠金融在其運營之初即已完成資本的初始積累,并根據其需求計算出最優投入,從而使各行業間的信貸資金分布達到最優。同時,由于多元化的消費需求是助推產業結構變革的主要動力來源,因此,市面上各類豐富的數字化金融產品也會通過刺激大眾購買欲推動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最終達到提高綠色發展水平的目標[5]。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1:數字普惠金融能夠提高首批國家生態文明試驗區的綠色發展水平;
假設2:數字普惠金融通過提高創新效率和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的中介效應提高了首批國家生態文明試驗區的綠色發展水平。
2 模型構建與變量說明
2.1 模型構建
構建數字普惠金融對我國綠色發展水平影響的基準模型:
GREit=a0+a1DIFit+a2Xit+λi+ηt+εit(1)
式(1)中,GREit為i省在t年的綠色發展水平,DIFit為i省在t年的數字普惠金融水平,Xit為控制變量,λi個體固定效應,ηt為時間效應固定,εit為隨機擾動項,a0為截距項,a1、a2為回歸系數。
依據理論機制分析,再構建中介效應模型,探討數字普惠金融對綠色發展水平的間接效應。
Mit=b0+b1DIFit+b2Xit+λi+ηt+εit(2)
GREit=c0+c1DIFit+c2Mit+c3Xit+λi+ηt+εit(3)
式(2)中,Mit為中介變量,b0為截距項,b1、b2為回歸系數。式(3)中,c0為截距項,c1、c2為回歸系數。
2.2 變量選取
被解釋變量:依據《綠色發展指標體系》及閩贛黔三省生態文明建設目標評價考核中的綠色發展具體指標,并借鑒舒成等[6-7]的指標體系,構建了綠色發展水平指標體系(表1),運用熵值法進行綜合評價,并將其作為模型的被解釋變量。
核心解釋變量:選用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和螞蟻金服聯合編制并發布的數字普惠金融指數(DIF)衡量數字普惠金融水平,具有權威性和代表性[8]。
中介變量:選取科技創新效率(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例)和產業結構升級(第三產業產值與第二產業產值之比)作為中介效應的變量。
控制變量:選取城鎮化水平(城鎮人口與總人口之比)、人力資本水平(普通高等學校在校人數占總人口的比例)、對外開放程度(進出口貿易總額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例)和經濟發展水平(人均生產總值的對數值)作為控制變量,以盡可能減少因遺漏變量導致的估計偏差[9-10]。
2.3 數據來源與描述性統計
鑒于數據的可得性,選取2011—2022年閩贛黔三省的面板數據作為樣本。除代表數字普惠金融水平的數字普惠金融指數外,其余數據均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中國社會統計年鑒》和上述三省統計年鑒、環境狀況公報、中國水土保持公報等。對于部分缺失的數據,采用線性插值法進行補齊。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見表2。
3 實證檢驗與分析
3.1 基準回歸分析
根據Hausman檢驗,Plt;0.01,因此選用固定效應模型。由表3可知,數字普惠金融對綠色發展水平的估計系數均為正,且在1 %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了檢驗。加入控制變量后,影響系數增大,模型的擬合優度也顯著增加,這說明本模型選擇的控制變量是合理且有效的,驗證了前文的假設1。在控制變量方面,城鎮化水平、人力資本水平、對外開放程度的回歸系數均顯著為正,這說明城鎮化、人力資本、實行對外開放均是驅動綠色發展的堅實力量。經濟發展水平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這說明單純依靠GDP的增長對綠色發展有抑制作用,這與我國經濟發展由高速發展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政治論斷相吻合。
3.2 中介效應機制檢驗與分析
依據中介效應檢驗模型,分別檢驗創新效率和產業結構升級作為中介變量對數字普惠金融提升綠色發展水平的間接影響。
由表4可知,科技創新效率和產業結構升級都顯著地提高了綠色發展水平,但只有前者對數字普惠金融存在中介效應,且為完全中介效應。數字普惠金融能夠借助大數據、互聯網等新興的數字產業技術,減少科研投入和研發成本,激發企業的創新興趣和提高研發積極性,減少創新主體的參與成本,打破研發創新的高準入門檻,從而大力提高科技創新的效率,進而提高綠色發展水平。為了穩健性起見,采用Bootstrap法進行檢驗,結果顯示:科技創新效率拒絕了原假設,說明科技創新效率可以通過中介效應間接促進綠色發展水平;產業結構升級的間接效應不顯著,即產業結構升級不能通過中介效應促進綠色發展水平。因此,假設2并未得到驗證,只有科技創新效率證實了假設2。
4 研究結論及政策建議
本研究結果表明:(1)數字普惠金融可以顯著提高該地區的綠色發展水平;(2)人力資本水平、城鎮化水平、對外開放程度都能顯著提高綠色發展水平,經濟發展水平對綠色發展水平有抑制作用;(3)數字普惠金融可通過科技創新效率間接提高該地區的綠色發展水平。
綜合以上分析,為促進數字普惠金融對綠色發展水平的積極影響,推動國家生態文明試驗區經濟發展邁向更高的質量水平,提出以下建議:
第一,利用數字普惠金融提高綠色發展水平。相關部門應推動傳統金融與大數據等數字技術深度融合,加快數字普惠金融的數字化建設,著力改善金融服務方和受惠方的信息不對稱現象,利用新興的數字技術幫助金融組織實現對各類企業和農戶的精準識別,并根據不同需求予以專門的服務,提高資本的融通效率。
第二,加快數字化和現代化信息建設。在經濟發展相對落后的偏遠地區,移動網絡尚未實現全覆蓋,在這一情況下,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十分緩慢,人們難以通過互聯網等數字媒介實現所需的金融服務。相關部門應提高數字媒介的覆蓋率和普及率,改善偏遠落后地區因交通因素的限制而無法獲得金融服務的情況。
第三,重視科技創新的作用,利用數字普惠金融促進科技創新。當前,一些小微企業都具有高科學技術的創新型人才,但部分由于缺乏充足的資金支持,很難在創新研發活動中取得成果。科技創新可以在數字普惠金融和綠色發展之間形成間接傳導機制,因此,金融機構應對這些因資本薄弱或信用尚低而被傳統金融體系排斥在外的中小企業予以資金援助和支持,激發他們的創新動力,從而提高全社會的創新效率,推動綠色發展水平的提高。
參考文獻
[1] 葉文顯.中國省會城市的綠色發展效率分析[J].資源開發與市場,2021,37(11):1281-1287.
[2] 張翱祥,鄧榮榮.數字普惠金融對農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及空間溢出效應[J].武漢金融,2022(1):65-74.
[3] 姜振水.農村數字普惠金融發展與實現路徑[J].農村金融研究,2017(4):49-53.
[4] 黃建歡,呂海龍,王良健.金融發展影響區域綠色發展的機理:基于生態效率和空間計量的研究[J].地理研究,2014,33(3):532-545.
[5] 劉湘云,吳文洋.科技金融與高新技術產業協同演化機制及實證檢驗:源于廣東實踐[J].廣東財經大學學報,2018,33(3):20-32.
[6] 舒成,朱沛陽,許波.江西省綠色發展水平測度與空間分異分析[J].經濟地理,2021,41(6):180-186.
[7] 張仁杰,董會忠.長江經濟帶城市綠色發展水平測度與空間關聯結構分析[J].統計與決策,2022,38(8):118-123.
[8] 郭峰,王靖一,王芳,等.測度中國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指數編制與空間特征[J].經濟學(季刊),2020,19(4):1401-1418.
[9] 徐盈之,徐菱.技術進步、能源貧困與我國包容性綠色發展[J].大連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41(6):24-35.
[10] 李光龍,孫宏偉,周云蕾,等.財政分權下科技創新與城市綠色發展效率[J].統計與信息論壇,2020,35(9):83-93.
作者簡介:柴林(1998—),女,山東濰坊人,研究方向為可持續發展與公共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