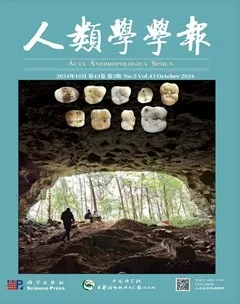新疆加依墓地人體脊椎溶解的古病理學




摘要:本文對出土于新疆吐魯番加依墓地青銅至鐵器時代的2 例罕見脊椎病理性損傷個體,進行了古病理學分析與診斷。經鑒定,個體M172 是一名10-12 歲的未成年人,個體M167 是一名35 歲左右的女性,兩例個體的脊椎均出現較為嚴重的骨性溶解病變:終板損壞,內部松質骨溶蝕、吸收,椎體中部空化形成中空現象。其中個體M172 除第7 胸椎和第3 腰椎發生溶解病變之外,手指、恥骨、肩胛骨等多部位均發現局灶性溶骨損傷,肋骨和脛骨局部反應性新骨顯著;個體M167 的第3、4 腰椎由于溶解嚴重發生椎體塌陷特征。通過CT 和X 光影像學分析骨骼損傷形態、骨骼損傷區域特征,并結合臨床醫學資料進行鑒別診斷,認為兩例個體患有化膿性骨髓炎、布魯氏菌病、放射線菌病、骨癌轉移以及一些其他真菌感染的可能性較小,推測這兩例個體疑似罹患脊柱結核病。
關鍵詞:脊椎;骨溶解;古病理;結核病
1 引言
古病理學通過古代人類病理標本所提供的信息,探索人類歷史上某些疾病的傳播、分布、特征及影響,以了解古代人類醫療條件、生活水平以及構建古代人類健康史。依據骨骼的各種病理特征,對個體的疾病做出科學的診斷和鑒定,是開展古病理學研究的首要重點。考古系列中病理的診斷依賴于對疾病引起的骨性病變的識別。例如,骨骼的溶解樣病變在古病理學中是一種常見的病理特征,其表現為骨質不同程度的溶解、流失,嚴重者使骨骼在外觀上出現巨大形態改變[1]。古病理學中,多種疾病在骨骼的不同部位均可造成溶解樣的病理損傷,例如性病梅毒、麻風病、結核病、骨轉移癌、真菌感染等[2]。在缺乏細胞病理學證據時,單純依靠骨骼上病理的形態學特征或影像學資料對個體進行疾病種類的診斷是極具挑戰性的,但經過大量古病理學和臨床醫學研究和總結,通過考慮個體的生理信息、生活環境、不同疾病給骨骼造成損傷時的特征等因素,可以極大地提高診斷的科學性。例如,不同疾病在不同的骨骼部位形成病發癥的頻率有所差異。以脊椎為例,脊椎是人體骨骼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維持人的正常生理形態與運動姿態、保護神經中樞和各大臟器、造血等方面,均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古病理學中,受到先天性、退行性、炎癥性或外傷性等因素影響,許多疾病會著重損壞椎骨,例如,布魯氏菌感染、結核、椎體主動脈瘤、脊柱炎等[3,4]。本研究通過形態學和影像學方法,對兩例出土于新疆加依墓地青銅至鐵器時代脊椎溶解病變的個體進行古病理學診斷與分析,以期豐富和擴展國內古病理學工作在病理診斷、疾病種類以及疾病分布上的探索。
加依墓地位于新疆吐魯番市亞爾鄉加依村南3 km 的臺地上,2013 年開始發掘,至2014 年共發掘墓葬244 座,葬式有仰身屈肢葬、側身屈肢葬兩種,隨葬器物以陶器和木器為主,金屬器、石器、骨角器數量較少,不見鐵器,放射性碳測年分析顯示遺址的年代約為公元前8 至公元前5 世紀,屬于蘇貝希文化第二至第三期[5,6]。M167 位于墓葬區的中東部,為單人仰身屈肢葬,M172 位于墓葬區的東南部,為單人側身屈肢葬,在隨葬品與葬式上與大多數墓葬基本類似。本文參照朱泓、邵象清、Buikstra 和Ubelaker 以及Brooks和Suchey 等提出的標準,通過顱骨、盆骨上的性二態特征以及年齡特征等推斷,M172為未成年人,年齡10-12 歲;M167 為女性,35 歲左右[7-10]。
2 病例觀察與描述
2.1 骨骼表面觀察
人骨M172 骨骼整體保存較為完整,可見顱骨、鎖骨、肩胛骨、椎骨、部分肋骨、胸骨、盆骨、骶骨、肱骨、尺骨、橈骨、腕骨、掌骨、指骨、股骨、髕骨、脛骨、腓骨、跟骨、左側足舟骨、距骨和趾骨(圖1: 左)。病變累及該個體的椎骨、肋骨、肩胛骨、盆骨、掌骨、指骨和脛骨,具體表現如下。
第7 胸椎發現溶解性病變,病變面積累及2/3 的椎體表面(圖2: 左),具體表現為:胸椎上面觀,椎體右半邊骨質發生溶蝕,被溶蝕的椎體部分密質骨已不見,露出松質骨,但松質骨已經硬化、吸收,病變區域形成了一個形狀不規則的巨大凹陷,凹陷邊緣圓鈍,最寬處約10.45 mm、最長處約20.94 mm、最深約9.61 mm,相鄰胸椎排列尚能支撐正常解剖位置、未發生明顯的塌陷或移位。
第3 腰椎發生溶解性病變,病變面積累及1/3 椎體(圖2: 右),具體表現為:腰椎下面觀右半椎體骨質溶蝕,部分密質骨已經完全溶解,露出松質骨;松質骨被溶蝕并出現硬化、吸收的特點,病變區域形成了一個類似臺階樣的凹陷或開放性的空坑;凹陷最長處約14.68 mm、最寬約11.73 mm、深約11.88 mm,溶蝕凹陷深度超過1/2 的椎體厚度;相鄰腰椎排列正常,未發現明顯的塌陷。左側恥骨內側,靠近與髖骨相連的骺端區域發生溶解性病變(圖3: a);部分密質骨和松質骨均溶解形成瘺道;瘺道邊緣光滑,形狀類似橢圓,最長約9.03 mm、寬約4.26 mm、深約6.88 mm。
右側肩胛骨中部靠近內側緣處發現兩個較小的溶蝕孔洞(圖3: b),孔洞上下各一,近圓形,上部孔洞直徑約1.88 mm,下部孔洞直徑約3.14 mm,孔洞邊緣光滑圓鈍,周邊骨質粗糙,可見少量反應性新骨。
左手第1 掌骨表面發現廣泛的新骨沉積,沉積的新骨使掌骨圍度臃腫(圖3: i);第1 近節指骨近端關節處發現方形溶蝕空坑,長6.91 mm、寬9.44 mm、深5.44 mm,侵蝕2/3 的關節面,邊緣較為規則、整齊(圖3: d)。
左手第4 掌骨背面出現反應性新骨,呈編織的花紋狀,從近端蔓延至骨干1/2 處(圖3: g)。
右手第3 近節指骨近端背面關節處(圖3: h),第5 近節(圖3: e)、中節指骨(圖3: f)的近端左側面關節處均發生凹陷式的溶蝕損傷。
第7-10 肋骨臟側面發現編織狀反應性新骨沉積,右脛骨內側面骨膜炎顯著,遠端干骺處出現大量反應性新骨沉積,呈層狀、鑲嵌樣(圖3: c)。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M172 所有椎骨椎體側面的孔洞為未成年個體正常發育過程未愈合的血管通道,屬正常現象。
人骨M167 骨骼整體保存完整,可見顱骨、鎖骨、胸骨、肩胛骨、肋骨、椎骨(頸椎缺失C4 和C5)、骶骨、盆骨、肱骨、尺骨、橈骨、部分腕骨、部分掌骨和指骨、股骨、右側髕骨、脛骨、左側腓骨、跗骨以及部分趾骨(圖1: 右)。
病變僅發生在腰椎,累及第3、4 腰椎(圖4: a)。第3 腰椎病變最嚴重,整個椎體已不完整,超過2/3 的部分已經被溶解殆盡;椎體下終板已基本不見,椎體大面積塌陷,僅剩椎體上終板和右側殘存的骨質。椎體中部厚度僅剩6.36 mm,最薄處已經貫穿。松質骨硬化、吸收明顯,變得趨于光滑,殘存的椎體側面表現出廣泛的新骨重塑并形成骨贅,整體外觀似被蛀蟲蠶食之后留下的殘殼,與相鄰的椎骨已經無法保持正常生理形態,發生顯著的塌陷和移位(圖4: b)。
第4 腰椎椎體上終板左側偏中部骨質溶解,形成了一個長19.85 mm、寬15.94 mm、深約19.55 mm 的空坑,邊緣較規則,椎體上終板右前方邊緣也發生溶蝕破壞,椎體環側面和椎弓發生顯著的新骨重塑,重塑的新骨呈流蠟狀充滿褶皺,并形成眾多骨贅(圖4: c)。
2.2 放射影像和顯微鏡表現
CT 和X 線影像是探查骨骼皮質或松質損傷范圍、損傷溶骨性或硬化邊緣以及髓腔形態變化較為準確可靠的方法,為病理學研究提供客觀的診斷依據[11]。超景深顯微鏡可以高倍放大骨骼損傷區域,通過細節判斷骨骼損傷的類型和特征。采用GE Hi-LightSpeedMedical-Systems 掃描機對M172 與M167 所有部位的骨骼進行CT 掃描,掃描參數如下:管電壓80 kV,毫安秒377 mAS,球管電流 670 mA,螺距0.37,圖像厚度2 mm,圖像間隔1 mm。采用GE 懸吊式DR Optima XR646 HD 數字化X 光機對所有椎骨進行平片拍攝。使用基恩士 VHX-2000 系列超景深三維顯微系統觀察椎骨損傷區域。
CT 影像特征顯示,M172 第7 胸椎、第3 腰椎,以及M167 第3、4 腰椎椎體均以骨質破壞為主,尤其是M167 第3 腰椎椎體幾乎破壞殆盡。椎體內部骨松質出現疏松現象,伴隨不規則侵蝕和點狀空腔,以M167 第4 腰椎(圖5: b)和M172 第7 胸椎(圖5: a)最為顯著,椎體內部呈斑點狀或蟲蛀狀的骨質疏松。X 平片中顯示,M172 第7 胸椎、第3 腰椎(圖5: c),以及M167 第3、4 腰椎(圖5: d)椎體均以骨質破壞和骨質吸收為主,不見死骨形成,骨質增生硬化不明顯。例如,M167 第4 腰椎中央出現類圓形的溶骨性骨質破壞區,但這些病損區域不見硬化邊緣。超景深顯微鏡20 倍視野下,椎骨損傷區域的密質骨邊緣光滑圓鈍,無新斷面,松質骨硬化明顯無新斷裂痕跡(圖5: e-j)。
3 鑒別診斷
根據干骨損傷特征對個體進行疾病診斷之前,首先要考慮埋藏學因素,正確區分死后變化和生前病理變化,骨骼受地層沉積、流水侵蝕、植物的破壞、動物啃咬以及人為破壞等埋藏因素的影響會發生死后變化。通過超景深顯微鏡對兩例個體椎骨損傷區域的觀察表明,損傷區域的骨質斷面圓滑,松質骨硬化、吸收顯著(圖5: e-j),判斷為生前活躍的骨反應所造成。
古代人類病理骨骼缺乏分子生物學信息,依靠形態學或影像學診斷疾病時為了盡可能降低診斷的誤導性,必須要做出更為寬泛的病理診斷。綜上所述,M172 主要的病理狀態是胸椎椎體和腰椎椎體的溶骨性病變,同時伴隨包括指關節、髖骨、肩胛骨的局灶性溶解;M167 主要的病理狀態為腰椎椎體的骨性溶解,即兩例個體最顯著的病變是脊椎發生溶骨性變化。因此,可以首先排除包括遲行性關節炎、壓縮性骨折以及舒爾曼病(Scheuermanndisease) 等不會引起溶骨性改變的脊柱疾病[12,13,14]。在古病理學中,造成椎骨溶解的疾病有很多,通過對這些疾病易感群體、流行地區、病理特征的梳理,并根據兩例個體的生理階段以及病變的形態學和影像學特征,最終確定了六類可能性較大的疾病重點診斷分析:化膿性骨髓炎(非特異性)、結核病、布魯氏菌病、放線菌病、骨轉移癌以及其他真菌感染。
3.1 化膿性骨髓炎(非特異性)
非特異性骨髓炎(osteomyelitis) 是由于化膿性細菌、病毒、真菌或多細胞寄生蟲入侵骨骼感染骨髓所引起,金黃色葡萄球菌、鏈球菌、大腸桿菌、厭氧菌和腸球菌都是引發化膿性骨髓炎的常見微生物,慢性化膿性骨髓炎中經常可以發現竇道或引流竇,竇道內可見松質死骨[3]。非特異化膿性骨髓炎發病年齡多在3~15 歲,微生物在骨骼末端聚集并進入骨髓繁殖,產生大量膿液,導致骨骼變形或形成竇道。同時,膿液通過竇道從骨骼內排出到軟組織中,骨膜下新骨反應旺盛,有時會在受感染的骨軸周圍形成一層新骨鞘,密質骨供血中斷,導致壞死區域出現與密質分離的死骨片,在髓腔內形成隔離[2,16]。膝部、脛骨、股骨是最常見的發病部位,會發生嚴重的骨溶解,薄弱區域甚至發生病理性骨折,正如Carney 和Wilson 所述:骨髓炎的特殊病理反應是骨的溶解、新骨的形成,以及死骨的存在[17]。椎骨骨髓炎的感染大多是由黃色葡萄球菌引起,通常發生在血源擴散之后[28],感染會通過椎間盤或前縱韌帶后擴散到臨近的椎骨,導致椎體塌陷和脊柱后凸,椎體半脫位、新骨形成和強直,放射性影像表現為位于松質骨不規則的溶骨性破壞,邊界清晰伴有薄層高密度的硬化邊緣,同時伴有死骨和反應性新骨[16],椎體可發生病理性壓縮骨折,可見兩半椎體呈尖端相對的楔形硬化骨塊,骨質破壞多限半個椎體,并很快出現骨質增生硬化[29]。值得注意的是非特異性骨髓炎對脊柱椎弓的影響與椎體一樣頻繁[2]。
3.2 結核病
結核病(Tuberculosis) 是由結核分枝桿菌復合體中的細菌感染所致,是一種可能呈現急性或慢性特征的疾病[18,30]。目前人類感染結核的主要菌株是結核分枝桿菌和牛型結核分支桿菌[4]。其主要流行于人口密集和人畜密切接觸的地區。骨結核是由于肺部感染的血液傳播至骨骼而引發,在血液中循環的結核桿菌大多位于具有造血功能的松質骨區域,由于椎骨、肋骨和胸骨在個體任何年齡段都具有造血骨髓,因此脊柱是主要的受累區域,同時身體的任何骨骼都有可能會被感染。脊柱的變化被稱為“波特病(pott)”[31],Aufderheide和Rodriguez Martin 指出:40% 的骨結核患者都累及脊柱,80% 的脊柱病例都涉及椎體,而椎弓極少受累[18]。在脊柱中,下胸椎和腰椎最易受波及,頸椎和骶椎很少受累,除此之外,髖關節和膝關節是除脊柱之外常見的發病部位[4,31]。結核病對骨骼的影響是骨形成和骨破壞,但骨破壞過程要比骨修復過程更顯著,局灶性、吸收性和溶解性病變是椎體主要的病理狀態。一個或幾個椎體塌陷,殘留椎弓和棘突,會導致脊柱后凸,肋骨內側可觀察到新骨增生[30],兒童好發手足管狀骨的各種類型病變(結核性骨髓炎、溶解性病變、骨膜下骨形成)被稱為結核性指趾炎或脊椎靜脈炎[2,32]。放射性影像學常表現以骨骼破壞為主,骨質增生或硬化不顯著,骨膜增生輕,一般沒有死骨形成,椎體可形成椎旁囊腫[19]。
3.3 布魯氏菌病
布魯氏菌病(Brucellosis) 又稱為“波狀熱”(Undulant fever),是一種人畜共患傳染性疾病,常見于家畜馴養地區。人類患病主要由布魯氏菌中的三個菌種所致:由山羊傳播的馬耳他布魯菌、通過牛傳播的流產布魯菌(大部分)和通過豬傳播的豬布魯菌[33]。布魯氏菌病的骨組織病變是由致病病菌在骨髓內通過血液流動傳播的,最常見的并發癥是骨關節病變,引發脊柱炎和椎體骨髓炎,膝關節、髖關節、骶髂關節和掌部的指關節常受波及。對脊柱的影響主要是胸椎下段和腰椎、脊柱韌帶、椎間盤和椎體,但是兒童不會發生脊柱病變[2,11]。在骨骼病變中,廣泛的新骨形成是布魯氏菌病的典型表現,影響脊柱時患者脊柱很少會發生塌陷現象,常見的病變特征是椎體邊緣大量硬化,出現“鸚鵡喙”狀的骨贅,同時伴有一個或多個局灶性溶骨病變[4,11]。與結核病不同的是,它不會完全破壞受影響的椎體,放射性影像學中可見多個椎體呈小囊狀破壞,椎體破壞為多發的小病灶,局限于椎體邊緣,隨著后期破壞向椎體中心發展,椎體邊緣不透光(硬化),單個骨小梁大小和數量增加[11,34]。
3.4 放射線菌病
放線菌病(Actinomycosis) 是一種由放線菌屬的絲狀革蘭氏陽性厭氧菌引起的慢性化膿性肉芽腫疾病,人畜共患,具有傳染性[35]。人類感染的菌株主要為衣氏放線菌(A.israelii)和麥氏放線菌(Actinomyces meyeri),感染可發生于全身任何部位;發病年齡一般在20-50歲,且男性患病率遠高于女性[21,36];骨骼感染病變罕見,通常由鄰近軟組織的傳播引起(75%的病例);也可能由局部創傷(19%) 或血源性傳播(3%) 引起[35];面部骨骼尤其下頜骨是最常見的受累區域,也可能會影響脊椎[37];脊柱中最常受影響的是頸椎,其次是胸椎和腰椎。病變一般為表現為椎體前部發生溶骨性損傷,但也可能擴散到椎體后部,病變邊緣重塑和硬化,偶爾伴有極端的成骨細胞反應,因此骨贅橋接相鄰的椎骨[38]。放線菌導致椎骨的塌陷頻率明顯低于結核病,與結核病不同的是,放線菌病經常導致關節突、椎板、橫突和棘突的侵蝕[3,18]。
3.5 骨轉移癌
骨轉移癌(Metastatic Carcinoma) 是由于原發在某些器官的惡性腫瘤通過血液循環、淋巴系統或腦脊液轉移到骨骼,形成繼發性惡性腫瘤,通過再轉移或直接浸潤到骨骼造成骨破壞[24]。骨轉移癌重點累及那些具有骨髓儲存庫造血功能的骨骼,因此脊柱、股骨骨骺、肋骨、胸骨、髖部、肱骨近端和顱骨最常受到骨轉移癌的影響,肢端骨骼則很少受到影響[39]。轉移癌骨損傷在40 歲以上的女性人群中更為常見[40],一般情況下骨癌轉移造成的骨骼病理性損傷分為溶骨性(與破骨細胞的破壞作用有關)、成骨性(與骨重建過程有關)或兩者混合[24]。轉移癌骨損傷通常影響不止一塊骨骼,病灶大小和形狀也往往不一致,且數量較少,偶爾可以發展成大的獨立的溶骨區域[2]。放射性影像學上,新骨沉積表現為不透明或“斑狀”密度[25]。
3.6 其他真菌感染
古病理學中一些致病性真菌或真菌性生物會引起骨骼的溶解性病變[3],一般由于外源性創傷、關節感染引起,也可由臨近的真菌性病灶,直接擴散到關節,或者系統性真菌感染血源性擴散造成[41]。例如:囊蟲病(Blastomycosis)、球蟲病(Coccidioidomycosis)、芽生菌病(Blastomycosis) 和組織胞漿菌病(Histoplasmosis) 都會對脊柱造成一定影響,但是疾病的分布地區具有特定性,主要局限于美洲地區[3,22]。
通過與以上疾病的鑒別診斷特征進行比較,根據病變累及部位、病理損傷形態、好發年齡、疾病分布地區以及影像學表現,本研究中的M172 與M167 可初步診斷為“脊柱感染性疾病(Infectious diseases of spine, IDS)”,結核病的可能性較高,布魯氏菌病等不能完全排除。未來需要進一步通過古DNA 研究對病原體進行檢測后進行最終確診。
4 討論
4.1 人群與疾病傳播
結核病通常被認為是人屬疾病中最古老的疾病之一[33],結核分枝桿菌復合體(MTBC)細菌基因組的研究表明,結核桿菌大約起源于7 萬年前[42]。中國古代很早便對結核病癥有所記載,歷代中醫古籍對結核病的稱謂包括:“尸疰”“傳尸”“鬼疰”“癆瘵”“骨蒸”“勞咳”“急癆““伏連”“肺癆”等[43]。成書于戰國時期的《黃帝內經·靈樞·邪氣臟腑病形》中已有對結核病的記載:“肺脈……微急為肺寒熱,怠惰咳唾血,引腰背胸,若鼻息肉不通 [44] 。作為一種人畜共患傳染病,結核病的傳播與人類過去文化的復雜性和社會變化有關,包括:動物的馴化和農業的發展、定居生活、城市化發展、人口過度擁擠等[45]。在探討青銅至鐵器時代新疆吐魯番地區結核病的出現和傳播時,應考慮以下幾個因素:第一,畜牧業的影響。動物結核病是數千年前結核病歷史發展的核心,它可以在野生動物和家畜中流行并傳染給人類。中國目前已發表的結核病生物考古研究表明,有關結核病的最早證據可追溯到新石器時代晚期( 公元前3900- 公元前3200 年)[46],但所有證據都晚于中國早期農業出現和動物馴化的時間[1],人類早期畜牧業的出現使得人類與動物接觸更加親密,牛被認為是對人類最具傳染性的家畜之一,包括肉和乳制品的食用,甚至對糞便和尿液的再利用[31]。加依墓地許多墓葬中都見有隨葬動物的肢體,例如羊頭 、羊腿 、羊肩胛骨等,大量生活用具及狩獵工具已經表明,畜牧和狩獵在當時的生產生活方式中依舊占據重要地位[5],這會導致加依人群與家畜或野生動物更加頻繁地接觸,增加人畜共患病發生的概率。第二,人口增長。農業的出現是促進古代社會人口劇增的一大革命,Mangtani認為,居住在擁擠地區的人數每增加1%,結核病發率就會增加12%[47]。Elender 等人還指出,這一因素對于女性來說顯得更加重要,因為傳統上女性在室內待的時間更長,即使沒有接觸感染的動物,但仍然會被攜帶分枝桿菌的人所傳染[48]。公元前8 世紀- 公元前5 世紀的吐魯番地區,盡管畜牧和狩獵仍然是重要的生業方式,但綠洲農業已經出現,男女社會分工明顯(女性更多從事紡織等手工業生產)[6,49],農業的發展為結核病的傳播提供了必要的人口密度,這一因素增加了加依人群傳染結核病的危險性。第三,人口流動。吐魯番地區自古以來為中亞和東亞交流的交通要道,考古資料和人骨穩定同位素分析均表明,加依墓地存在一定的外來的文化因素和少量遷徙的人口[6,50],張雯欣等人對加依人群的暴力創傷分析顯示該地區的人群地緣沖突顯著[51],至西漢開辟絲綢之路后,東西方交流更加頻繁,人口跨地域流動可能為人畜共患病的傳播提供了一定契機。例如,吐魯番盆地北部古車師前國范圍內的交河故城人群(公元前202- 公元200 年)中,古DNA 測序反映了較高的結核患病率,加依墓地東部的勝金店人群(公元前217- 公元前147 年)中,一例50-65歲男性骨骼顯示出了類似結核的病理特征[52]。加依人群未來的古DNA 研究工作的開展,可能會進一步揭示整體人群疾病的患染情況。
4.2 骨結核損傷與推測
骨質破壞是結核病對骨骼造成的最顯著特征,主要表現為局灶性骨溶解和骨吸收[2]。結核在滲出期(前期階段)滲透到骨髓腔,使松質骨失活,從而形成中部的松質骨壞死。增殖性肉芽腫(后期階段)階段,會導致松質骨的局部破壞和空化,但很少會引起病灶周圍的反應性骨形成,受累的骨質通常表現為病灶周圍或全身的骨質疏松,關節表現出糜爛性病變,常發生侵蝕或者溶解性凹坑[53]。脊柱結核是肺外結核最常見的形式,它是最常見的骨關節結核,約占骨關節結核的50%[54],早期階段出現椎體終板致密邊緣骨質吸收和礦物質脫離,椎間盤間隙逐漸變得狹窄或閉塞,后期階段導致前部椎體溶解性進行性破壞、前部楔形、椎體塌陷和后凸畸形[2]。此外,肋骨和長骨上的骨膜反應尤其在古病理學文獻中已有報道[2]。從外觀來看,本文中涉及的兩例個體的脊柱都存在較為嚴重病理損傷,脊椎的損傷位置均位于胸椎椎體和腰椎椎體,損傷類型主要為骨質溶解,損傷形態上都表現為椎體終板及邊緣侵蝕,椎體松質骨局部破壞,椎體空化。成年個體M167 腰椎椎體溶解程度過高顯然與布魯氏菌造成的損傷不符,椎弓未出現溶骨病變,因此罹患化膿性脊柱炎、放線菌病、轉移癌的可能性較小,因而推斷,M167 最大可能罹患結核病。而布魯氏菌病、轉移癌以及放線菌病影響未成年個體的概率較小,影像學中M172 椎骨未見邊緣硬化,無成骨反應,僅有溶骨損傷,這與布魯氏菌病的特征有很大差別,而椎弓無任何病變這也與化膿性脊柱炎、放線菌病、轉移癌不相符。因此,M172 病變與結核病契合度較高,未成年個體M172 的椎骨損傷程度低于成年個體M167,這可能與疾病累及年限有關。
5 結語
從骨骼外觀形態上對結核病進行診斷尚存在諸多不足之處,雖然我們做出最近似于結核病的診斷,但我們仍然保留做出其他疾病診斷的意見,對此類古代結核病的精確診斷還有待于古病理材料的不斷積累和古病理學方法、技術的進一步發展。本文謹通過古病理學的研究方法,對病理骨骼標本做出疾病種類的可能性診斷,并結合加依人群生產生活方式等因素淺析地域與傳染病的關系,以期為了解過去的疾病歷史和流行病學,構建古代尤其文字記載之前人類健康史提供一定學術參考。
參考文獻
[1] Vargová L, Horá?ková L, ?abatová K, et al. Unusual find of osteolytic lesion on skeleton from the Middle Bronze Age: Possible case of peritoneal absces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steoarchaeology, 2022, 32: 923-931
[2] Ortner DJ. Identification of Pathological Conditions in Human Skeletal Remains[M].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2003
[3] Robert WM, David RH. 骨骼疾病圖譜人類骨骼病理與正常變異指南[M].譯者:張全超,秦彥國.北京:科學出版社,2020
[4] 夏洛特·羅伯茨,基思·曼徹斯特.疾病考古學[M].譯者:張樺.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10
[5] 王龍,肖國強,劉志佳,等.吐魯番加依墓地發掘簡報[J].吐魯番學研究,2014, 1: 1-19
[6] 肖國強.新疆吐魯番加依墓地的發現與研究[D].西安:西北大學碩士論文,2018
[7] 朱泓.體質人類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92-106
[8] 邵象清.人體測量手冊[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5, 34-56
[9] Buikstra JE, Ubelaker DH. Standards for Data Collection from Human Skeletal Remains[M]. Fayetteville: Arkansas Archeological Survey, 1994, 15-38
[10] Brooks S, Suchey JM. Skeletal age determination based on the Os pubis: A comparison of the Acsádi-Nemeskéri and SucheyBrooks methods[J]. Human Evolution, 1990, 5: 227-238
[11] Jones C. Brucellosis in an adult female from fate bell rock shelter, Lower Pecos, Texas (4000–1300 BP)[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aleopathology, 2009, 24: 252-264
[12] 卞琴,施杞,王擁軍.椎體骨贅形成機制的研究進展[J].中國中醫骨傷科雜志,2010, 18(5): 63-64
[13] 李法軍.河北陽原姜家梁新時期時代人骨研究[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
[14] 徐文堅,袁慧書.中華影像醫學骨肌系統卷(第3 版)[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19
[15] 倪立青.類風濕關節炎[M].北京:中國醫藥科學技術出版社,2020
[16] Tony W. Palaeopathology[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85-89
[17] Carney CN, Wilson FC. Infection of Bones and Joints[C]. In: Wilson FO(Ed). The Musculoskeletal System[M]. Philadelphia:Lippincott, 1975
[18] Stone AC, Ozga AT. Ancient DNA in the study of ancient disease[J]. In: Buikstra JE (Ed). Ortner’S Identification of Pathological Conditions in Human Skeletal Remains[M].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2009, 183-210
[19] 侯代倫,柳澄.結核病影像學[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19, 20
[20] 丁惠強,原文琦.布魯桿菌性脊柱炎與脊柱結核的鑒別診斷與治療[J].中華骨科雜志,2021(20):1484-1492
[21] Tayles N, Buckley HR. Leprosy and Tuberculosis in Iron Age Southeast Asia?[J].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2004, 125: 239-256
[22] Li MC, Charlotte A. Roberts, Chen L, et al. A male adult skeleton from the Han Dynasty in Shaanxi, China (202BC–220AD) with bone changes that possibly represent spinal tuberculosi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aleopathology, 2019, 27: 9-16
[23] 陳雪雯,衛鳳蓮,溫海.隱球菌病的診治[J].皮膚科學通報,2017, 34(5): 604-612
[24] Bauduer F, Bessou M, Guyomarch P, et al. Multiple calvarial lytic lesions: A differential diagnosis from Early Medieval France (5th to 7th c. AD)[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steoarchaeology, 2014, 24: 665-674
[25] Smith MO. A probable case of metastatic carcinoma from the late prehistoric Eastern Tennessee River Vale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steoarchaeology, 2002, 12: 235-247
[26] 王虎,馬淑梅,曹得萍,等.青海包蟲病研究進展[J].青海醫學院學報,1999, 3: 46-50
[27] Hadgaonkar S, Rathi P, Purandare B, et al. Salmonella Typhi dorsolumbar spondylodiscitis mimicking tuberculosis: An interesting case report[J]. Surgical Neurology International, 2020, 11
[28] Stefanovski N, van Voris LP. Pyogenic vertebral osteomyelitis: Report of a series of 23 patients[J]. Contemporary Orthopedics,1995, 31: 159-164
[29] 呂國義,彭俊紅.X 線讀片指南[M].北京:北京大學醫學出版社,2016, 248
[30] Aufderheide AC, Rodríguez-Martín C. 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Human Paleopathology[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31] Roberts CA, Buikstra JE. The Bioarchaeology of Tuberculosis: a Global View on a Reemerging Disease[M]. Gainesville: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3
[32] Pietralata GM, Diotallevi P, Papi MG, et al. “Spina ventosa”: Osservazione di un caso[J]. GIOT, 2003, 29: 186-189
[33] 肯尼思·F,基普爾.劍橋世界人類疾病史[M].譯者:張大慶.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7, 550-551
[34] 谷野,張明香,劉洪艷.布魯菌病[M].沈陽:遼寧科學技術出版社,2019, 84-85
[35] Wong VK, Turmezei TD, Weston VC. Actinomycosis[J].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2011, 34: 785-90
[36] 陳愛鳳.肺放線菌病26 例綜合臨床分析[D].杭州:浙江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 1
[37] 王宇明,李夢東.實用傳染病學[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16, 1069
[38] Pritchard DJ. Granulomatous infections of bones and joints[J]. Orthop Clin North Am, 1975, 6: 1029-1047
[39] Marks MK, Hamilton MD, Metastatic Carcinoma: Palaeopathology and Differential Diagnosi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steoarchaeology, 2007, 17: 217-234
[40] Melikian M. A case of metastatic carcinoma from 18th century Lond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steoarchaeology, 2006, 16:138-144
[41] 廖萬清,吳紹熙.現代真菌病學[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7, 349
[42] Comas I, Coscolla M, Luo T, et al. Out-of-Africa migration and Neolithic coexpansion of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with modern humans[J]. Nat Genet. 2013, 45(10):1176-1182
[43] 陳賢邦.中國醫學史[M].北京:團結出版社,2011, 146
[44] 劉永升.全本黃帝內經[M].北京:華文出版社,2010, 207-208
[45] Ortner DJ. Paleopathology: Implications for the history and evolution of tuberculosis[C]. In: Palfi G, Dutour O, Deak J, et al.Tuberculosis Past and Present[M]. Golden Book Publisher Ltd, 1999, 255-261
[46] Okazaki K, Takamuku H, Yonemoto S, et al. A paleopathological approach to early human adaptation for wet-rice agriculture: The first case of Neolithic spinal tuberculosis at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of Chin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aleopathology, 2019, 24: 236-244
[47] Mangtani P, Jolley DJ, Watson JM, et al. Socioeconomic deprivation and rates for tuberculosis in London during 1982–1991[J]. Brit. Med. J, 1995, 310: 963-966
[48] Elender F, Bentham G, Langford I. Tuberculosis mortality in England and Wales during 1982–1992: Its association with poverty,ethnicity and AIDS[J].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1998, 46(6): 673-681
[49] 李亞,李肖,曹洪勇,等.新疆吐魯番考古遺址中出土的糧食作物及其農業發展[J].科學通報,2013, 58: 40-45
[50] 吳曉桐,張興香,李雍,等.新疆吐魯番加依墓地人類遷徙與飲食結構分析[J].西域研究,2021, 3: 83-91
[51] Zhang WX, Zhang Q, McSweeney K, et al. Violence in the first millennium BCE Eurasian steppe: Cranial trauma in three TurpanBasin populations from Xinjiang, China[J]. Am J Phys Anthropol, 2020, 1-14
[52] 王輝,貝麗姿,葉惠媛,等.中國古代絲綢之路沿線地區的疾病歷史與人群健康[J].南方文物,2023, 1: 281-287
[53] Suzuki T, Inoue T. Earliest evidence of spinal tuberculosis from the aneolithic Yayoi Period in Japa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steoarchaeology, 2007, 17: 392-402
[54] Garg RK, Somvanshi DS. Spinal tuberculosis: A review [J]. J Spinal Cord Med, 2011, 34 (5): 440-4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