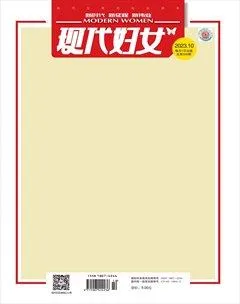江華的家風(fēng)軼事

江華,原名虞上聰,出生于湖南省江華縣,1926年加入中國(guó)共產(chǎn)黨,參加過(guò)井岡山斗爭(zhēng)、紅軍長(zhǎng)征、抗日戰(zhàn)爭(zhēng)和解放戰(zhàn)爭(zhēng),新中國(guó)成立后曾任浙江省委書(shū)記、最高人民法院院長(zhǎng)。他一生嚴(yán)以律己,身居高位而不存半分私心,手握權(quán)柄而不越雷池半步,注重言傳身教,嚴(yán)格要求家人、親戚,是涵養(yǎng)良好家風(fēng)的典范。
“我回來(lái),不能搞特殊化,不能搞脫離群眾的事情”
1985年11月初的一天,江華收到一封來(lái)自家鄉(xiāng)的快件。這是一封邀請(qǐng)函,江華瑤族自治縣人民政府邀請(qǐng)他回家鄉(xiāng)參加自治縣成立30周年慶典,江華非常高興,自己離開(kāi)家鄉(xiāng)參加革命整整60年了,戰(zhàn)爭(zhēng)年代,一直無(wú)法與家鄉(xiāng)聯(lián)系,新中國(guó)成立后,曾于1965年、1982年回過(guò)家鄉(xiāng)兩次,但回也匆匆,去也匆匆。這次他打算回一趟老家鷓鴣塘村,在生他養(yǎng)他的地方住上兩晚。
11月18日,江華吩咐秘書(shū)想辦法在北京買(mǎi)4盞馬燈。秘書(shū)迷惑不解:“現(xiàn)在到處都是電燈,大街小巷燈火通明,您要買(mǎi)馬燈干什么呢?”江華答道:“叫你去你就去吧。”秘書(shū)和司機(jī)轉(zhuǎn)了半個(gè)北京城也沒(méi)有看見(jiàn)馬燈的影子,只好回來(lái)如實(shí)告訴江華。江華想了想說(shuō):“你明天繼續(xù)幫我找,要到邊遠(yuǎn)的小商店或者老胡同,大商場(chǎng)里是買(mǎi)不到馬燈的。”果然,工作人員終于在北京郊區(qū)的一家小商店買(mǎi)到了。當(dāng)秘書(shū)告訴江華時(shí),他高興地說(shuō):“好!好!請(qǐng)把馬燈包裝好,放到我的辦公室。”
11月21日,江華囑咐秘書(shū):“23日我要回湖南,那4盞馬燈千萬(wàn)不能忘記,要幫我?guī)稀!?/p>
11月23日,江華及夫人朱潯回到江華縣城沱江,入住縣政府招待所。
當(dāng)天晚上,江華與侄女婿、縣民委副主任李先運(yùn)見(jiàn)面。江華和夫人回來(lái)參加縣慶活動(dòng),大家都非常高興,縣里在吃住方面做了精心安排。然而,江華參加完縣慶活動(dòng)卻對(duì)朱潯說(shuō)要回老家去住。
江華的老家在大石橋鄉(xiāng)鷓鴣塘村,距縣城40多公里,生活不太方便。縣里的同志就請(qǐng)朱潯做工作。朱潯說(shuō):“我了解他,他認(rèn)準(zhǔn)的事,九頭牛也拖不回的。”
李先運(yùn)告訴江華:“江華是個(gè)貧困縣,很多地方還沒(méi)有通電。縣領(lǐng)導(dǎo)聽(tīng)說(shuō)你回來(lái)要在家里住幾個(gè)晚上,特意在家里安裝了一臺(tái)柴油發(fā)電機(jī)和6盞電燈。”江華聽(tīng)后十分生氣,立即找來(lái)縣領(lǐng)導(dǎo),斬釘截鐵地要求把發(fā)電機(jī)和電燈都拆了。他說(shuō):“鷓鴣塘村100多戶人家,500多名群眾,為什么單獨(dú)為我家安裝電燈呢?我回來(lái),不能搞特殊化,不能搞脫離群眾的事情。我從北京帶回了4盞馬燈,晚上點(diǎn)上馬燈就可以了,已經(jīng)安裝的都要拆除,不然,我就不回來(lái)了!”無(wú)奈,工作人員只好立即派人把柴油發(fā)電機(jī)和電燈拆了。
11月27日,江華與朱潯前往大石橋鄉(xiāng)鷓鴣塘村。臨走時(shí),朱潯要縣里的同志給她一些舊報(bào)紙和面糊。他們以為是江華要看,那個(gè)年月鄉(xiāng)下難得見(jiàn)到報(bào)紙,就拿了幾張近日的《湖南日?qǐng)?bào)》。朱潯說(shuō):“少了。”又拿來(lái)了十幾張。朱潯說(shuō):“還不夠。”于是,縣里的同志用麻繩捆了一扎。
回到鷓鴣塘村,見(jiàn)到了闊別多年的父老鄉(xiāng)親,回到了他曾經(jīng)熟悉的老屋。江華跟侄兒侄女們嬉笑聊天、下棋,高興得像個(gè)頑童。
傍晚,鷓鴣塘村的男女老少聽(tīng)說(shuō)江華要住在家里,都去他的老屋見(jiàn)他。堂屋里4盞馬燈齊明,映照出鄉(xiāng)親們一張張歡樂(lè)的笑臉。江華坐在一盞馬燈旁,親切地和鄉(xiāng)親們聊起了家常,從鄉(xiāng)情、鄉(xiāng)景講到自己對(duì)故土的思念,講到自己的革命經(jīng)歷。他深情地說(shuō):“1938年8月,毛主席幫我改名江華,這個(gè)名字我一直沿用下來(lái),其中寄托著我對(duì)家鄉(xiāng)深深的懷念,也表示我不管死在哪里都是江華人。我13歲就外出求學(xué),后來(lái)搞了幾十年革命,打了很多的仗,吃了很多的苦,爬雪山過(guò)草地,紅軍二萬(wàn)五千里長(zhǎng)征都經(jīng)歷過(guò)。現(xiàn)在吃穿不愁了,村里要想發(fā)展起來(lái),就要想辦法把村里的水電路搞好。”他的侄子虞大灃說(shuō):“我們正在籌集資金,準(zhǔn)備明年通電。路和水的問(wèn)題村里也有了規(guī)劃。”“那好啊,村里搞什么事情,都只靠上面扶持,那是不對(duì)的,要自力更生。”那晚,他與鄉(xiāng)親們聊得很晚,直到凌晨12點(diǎn)多鐘,鄉(xiāng)親們?nèi)匀慌d致勃勃,久久不愿回去休息。
晚上,江華執(zhí)意要睡自己童年時(shí)代睡過(guò)的房。
這哪算得上是“房”呢?磚墻泥坯大都脫落,蜘蛛在四周織網(wǎng)。頭一天還是做柴房用的,聽(tīng)說(shuō)江華回來(lái)要住這里,家里人才臨時(shí)收拾一下,擺放了一張床。江華剛剛走進(jìn)房里,就覺(jué)得脖子有什么爬了上來(lái),伸手一摸,竟是一只蟑螂。江華幽默地一笑:“好久不回家,這些小玩意也來(lái)拜訪老朋友了。”朱潯也笑了:“等會(huì)恐怕要拜訪得你一夜睡不著呢。”江華說(shuō):“睡不著也要睡兩晚,這是我童年的窩嘛。”“童年是童年,晚年是晚年啊!”朱潯這樣說(shuō)著,就解開(kāi)從縣里帶過(guò)來(lái)的那一扎報(bào)紙,刷著面糊一張一張地往墻上貼。江華見(jiàn)狀,立即幫忙。
糊了報(bào)紙的墻壁帶來(lái)了清新氣息,這一夜江華睡得很香。
馬燈的燈光雖弱,卻比電燈更能照亮人心。
11月28日,江華組織鄉(xiāng)親們包粽子,要求大家要像青色的粽葉和白色的大米那樣,清清白白做人,扎扎實(shí)實(shí)做事。如今,每逢端午節(jié),鷓鴣塘村都會(huì)組織大家包“清白粽”,讓鄉(xiāng)親們牢記江華的諄諄告誡,接受廉政教育,過(guò)一個(gè)風(fēng)清氣正的“廉節(jié)”。
江華的堂侄媳李鳳英說(shuō):“他就管?chē)?guó)家的事,屋里的事一點(diǎn)都沒(méi)管。”
江華用自身的一言一行感染著家鄉(xiāng)的群眾,讓大家明白,幸福生活都是通過(guò)自己的雙手奮斗出來(lái)的。
江華嚴(yán)格要求在家鄉(xiāng)務(wù)農(nóng)的親屬,不要有任何優(yōu)越感,要老老實(shí)實(shí)當(dāng)好農(nóng)民,聽(tīng)政府的話,帶頭交公糧,不允許他們向當(dāng)?shù)卣崛魏尾缓侠淼囊蟆?/p>
“我們現(xiàn)在已經(jīng)不工作了,國(guó)家還給工資。有吃有住就行了,千萬(wàn)不要與人家比”
無(wú)論是在戰(zhàn)爭(zhēng)年代,還是在建設(shè)時(shí)期,無(wú)論是統(tǒng)率千軍萬(wàn)馬,還是閑居獨(dú)處,江華始終牢記自己是一個(gè)共產(chǎn)黨員,始終按照黨員的標(biāo)準(zhǔn)嚴(yán)格要求自己。
他出身貧寒,歷經(jīng)磨難,深知農(nóng)民生計(jì)艱難,一縷一粟來(lái)之不易。他在飲食上從不挑剔,他和朱潯一頓飯往往是一葷兩素或兩葷一素三小碟菜,以稀飯為主,只是和秘書(shū)一起吃飯時(shí),菜才可以多一點(diǎn),但他要求務(wù)必吃完。吃不了的菜他要求服務(wù)員留起來(lái),下頓再熱給他吃。一次在空軍招待所參加中央全會(huì),他中午沒(méi)吃的半條魚(yú)要服務(wù)員晚上熱了送來(lái),但服務(wù)員倒掉了,晚飯時(shí)急著找秘書(shū)想辦法。秘書(shū)只好讓服務(wù)員說(shuō)是自己吃了,他才不再追究。

1982年在零陵地區(qū)招待所時(shí),負(fù)責(zé)接待的同志特地為江華和夫人點(diǎn)了一條大魚(yú)品嘗。江華卻語(yǔ)重心長(zhǎng)地對(duì)秘書(shū)和零陵地委書(shū)記鄧有志說(shuō):“你們看看,這條魚(yú)我倆怎么吃得了呀,太浪費(fèi)了。”原封不動(dòng)地要服務(wù)員拿走了。
江華衣著樸素,兩件滌卡外衣穿了很多年。20世紀(jì)50年代做的一件灰色夾大衣,袖子短了一大截,穿起來(lái)實(shí)在難看,江華卻不同意做新的。無(wú)奈,朱潯只好將大衣袖子的里邊放下來(lái),可以稍長(zhǎng)一點(diǎn)兒。他穿的毛衣、毛褲、背心都是朱潯一針一線編織的,直到朱潯年老做不動(dòng)了才同意添些新衣服。“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在工廠勞動(dòng),自己動(dòng)手補(bǔ)襪子和棉毛衫。有一次接見(jiàn)外賓,竟穿了平時(shí)穿的那雙底部有洞的皮鞋去,朱潯要他扔掉,穿一雙好一點(diǎn)的,江華不肯。
江華只有一套毛料中山服,他平時(shí)舍不得穿,只是在出席會(huì)議或會(huì)見(jiàn)重要客人時(shí)穿一下,袖口磨破了,又翻過(guò)來(lái)重接。直到上世紀(jì)90年代初,才添置了一件黑色夾克衫。他特別喜歡穿布鞋,每次回江華,都要帶兩雙親戚手工制作的布鞋返回北京。
在住的問(wèn)題上,江華也不講究。他到地、縣一級(jí)調(diào)研,一般住招待所,不住豪華賓館。1982年,江華到郴州調(diào)研,郴州地委從安全方面著想,沒(méi)有安排住市中心的地區(qū)招待所,而是在市委機(jī)關(guān)騰出幾間房子,從招待所租幾套被子接待。盡管住的條件不怎么樣,江華表示很滿意。
江華艱苦樸素,厲行節(jié)約。他用的電視機(jī)是1975年與朱潯結(jié)婚時(shí)買(mǎi)的,一直用到去世。冰箱是單開(kāi)門(mén)的,還經(jīng)常出問(wèn)題。1989年1月,江華準(zhǔn)備去杭州過(guò)春節(jié),他找秘書(shū)張維借錢(qián),說(shuō)冰箱壞了,再也無(wú)法修,必須買(mǎi)一臺(tái)新的。秘書(shū)借給他1000元錢(qián),買(mǎi)了一臺(tái)冰箱。
江華接打電話也注意節(jié)約時(shí)間,不管是打進(jìn)來(lái)的或打出去的,只要話說(shuō)多了且涉及聊天內(nèi)容的,他馬上會(huì)說(shuō):“電話是這樣用的嗎?怪不得電話老是占線,電話局應(yīng)付不了了,快放下。”江華從領(lǐng)導(dǎo)崗位退下來(lái)后,經(jīng)常對(duì)朱潯說(shuō):“我們現(xiàn)在已經(jīng)不工作了,國(guó)家還給工資。有吃有住就行了,千萬(wàn)不要與人家比。”
為了節(jié)約紙張,江華在做筆記時(shí),把字寫(xiě)得小小的,密密麻麻的。紅鉛筆用到只剩下一點(diǎn)點(diǎn)也舍不得丟掉。他在北京醫(yī)院住院期間,醫(yī)生送他兩支鉛筆,他也舍不得用。
江華平時(shí)對(duì)自己甚儉,對(duì)有困難的人卻盡力幫助。他自己的錢(qián)不夠用時(shí)就向秘書(shū)借,用來(lái)接濟(jì)生活特別困難的人。他常常為家鄉(xiāng)落后的經(jīng)濟(jì)而焦慮。1991年,他把回憶錄《追憶與思考》的全部稿費(fèi)5300元,加上自己積攢下來(lái)的1500元錢(qián),派秘書(shū)送到鷓鴣塘村,交給村支部書(shū)記和村長(zhǎng)手中,讓他們用來(lái)辦一點(diǎn)集體事業(yè),鼓勵(lì)村干部帶領(lǐng)鄉(xiāng)親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1999年12月,江華逝世,其存款只有3萬(wàn)元。以他的身份和地位已經(jīng)是少得不能再少了。
(摘自《世紀(jì)風(fēng)采》,本刊有刪節(jié))(責(zé)任編輯 史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