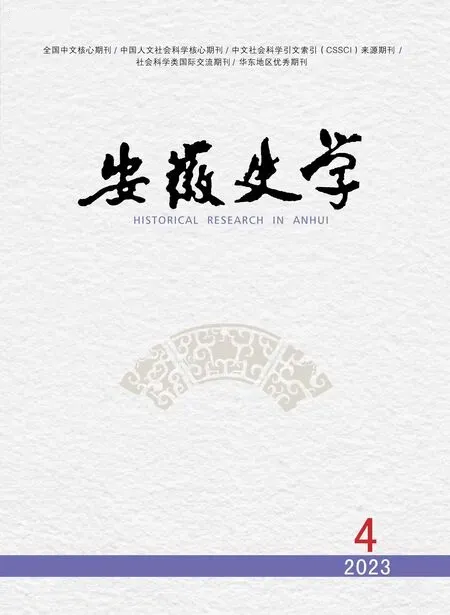1840年代的京師學術圈與曾國藩治學的三次轉向
黃 湛
(清華大學 國學研究院,北京 100084)
明清兩朝,北京作為首善之地,人文薈萃,其學術面貌也是思想發展的風向標。清中期乾隆朝,四庫館臣倡導經史考據之學,肇始于江南吳地的漢學一躍成為學術的主流聲音。嘉道以降,漢學獨尊的局面被打破,學術風氣為之一變。王國維道光之學“新”的說法(1)王國維:《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方麟選編:《王國維文存》,江蘇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07頁。,為后來學術史書寫所依循。道光時期,京師各學術群體之間是一種多元共存的狀態,漢學家(從事小學、考據學者)、文士、理學家盡管在治學方法上仍有壁壘,但彼此間并非劍拔弩張的狀態,整個京師洋溢著一種兼容并蓄、和而不同的學術風氣。士大夫在京師學風的熏染之下,或者活躍于某一群體之內,做專門的學問;或者游歷于數個群體之間,對不同學說加以會通。本文所關注的曾國藩(1811—1872)即屬于后一類中的典型代表。曾氏于道光十八年(1838)中進士后,直到咸豐二年(1852)離京歸鄉組織團練,在京師十數年的仕宦生涯中,游走于數個學術圈子,不拘一家之言,學術前后發生過三次轉向。余英時曾對曾國藩京師時期的學術思想加以考察,指出曾氏先后從事詩文之學、理學再到考據之學,最終形成了其通識博雅的“士大夫之學”。(2)參見余英時:《曾國藩與“士大夫之學”》,《現代儒學的回顧與展望》,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版,第295—319頁。本文將在余英時之論的基礎上,結合曾國藩居京期間的書信、文章、日記等材料,考察曾氏與京師各群體的互動及其思想轉變背后的交游及學習歷程。曾國藩博大包容而又獨具特色的學術風格,與當時京師的學術風氣密不可分。通過曾國藩幾經轉變的學術經歷,也可窺見道光后期京師學術圈的復雜情況。
一、初入京師:文士圈與理學圈
曾國藩于道光十五年(1835)參加京師會試時,便立意在科舉俗學之外讀書治學。他曾說自己“少時天分不甚低,厥后日與庸鄙者處,全無所聞,竅被茅塞久矣。”到京后“始有志學詩古文并作字之法,亦洎無良友。”(3)曾國藩:《致澄弟溫弟沅弟季弟》,《曾國藩全集》第20冊,岳麓書社2012年版,第49,31,42、49,38頁。兩處均寫明自己苦于缺少師友扶持,治學尚未尋到頭緒。道光十八年中進士,供職翰林院后,他的志趣仍在詩古文辭。嘉道時期,桐城學術在京師頗為流行,曾國藩在文學觀、學術觀上受到桐城派祖師姚鼐的影響,亦曾向名震京師的桐城學人梅曾亮請教。(4)謝海林:《曾國藩與桐城派古文家梅曾亮之關系發微》,《廣西師范大學學報》2017年第4期。他后來回憶早年情景說:“仆早不自立,自庚子以來,稍事學問,涉獵于前明、本朝諸大儒之書,而不克辨其得失。聞此間有工為古文詩者,就而審之,乃桐城姚郎中鼐之緒論,其言誠有可取。”(5)曾國藩:《致劉蓉》,《曾國藩全集》第22冊,第6—7頁。之所以如此重視詩古文辭,與曾國藩身為翰林院官員的自我期許有關——惟有勤于治學,才“可以無愧詞臣,尚能以文章報國。”(6)曾國藩:《曾國藩日記》,道光二十年六月七日,《曾國藩全集》第16冊,第41頁。曾氏所說的道光二十年后“稍事學問”,當指此年開始追隨唐鑒、倭仁等人學習理學事,這也是曾氏治學方向發生的第一次轉變。隨著交游日廣,學術視野日益開闊,曾氏不再囿于文學一隅。他將所要從事的學問分為進德和修業兩大類: “吾輩讀書,只有兩事:一者進德之事,講求乎誠正修齊之道,以圖無忝所生;一者修業之事,操習乎記誦詞章之術,以圖自衛其身。”(7)曾國藩:《致澄弟溫弟沅弟季弟》,《曾國藩全集》第20冊,岳麓書社2012年版,第49,31,42、49,38頁。此處的“修業”即指詩古文辭,這與他后來重視的經史小學、禮學形成對照。所謂“進德”,是指日常生活的德行踐履;從治學方面講,則指理學傳統的專門修行工夫——這也是詩古文辭以外,曾國藩此時治學的另一大重心。
曾國藩以理學和詩古文辭為治學重心,與其身處的京師學術氛圍密切相關。他在家信和日記中描述說:“京師為人文淵藪,不求則無之,愈求則愈出。”他還說自己在京師交游甚廣,朋友間治學興趣各異,“有所謂經學者、經濟者,有所謂躬行實踐者。始知范、韓可學而至也,馬遷、韓愈亦可學而至也,程、朱亦可學而至也。”(8)曾國藩:《致澄弟溫弟沅弟季弟》,《曾國藩全集》第20冊,岳麓書社2012年版,第49,31,42、49,38頁。曾國藩將友人大致劃分為詩文、經學、經世、理學四個學術門類。后來又根據《論語·先進》篇孔門四科(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提出儒學可分為義理、詞章、經濟、考據之學。(9)曾國藩:《曾國藩日記》,咸豐元年七月八日,《曾國藩全集》第16冊,第236頁。居京初期,曾國藩關注的主要是義理和詞章兩科。他的交游圈子與此對應,也可以分為理學群體和文士群體兩大類。其中,理學群體是以德行修養為治學根本者,主要有唐鑒、倭仁、吳廷棟、竇垿、馮卓懷等人。文士群體包括擅長詩古文辭的文士以及致力經史小學的“漢學家”——盡管文士與漢學家在乾嘉時期分屬針鋒相對的兩個陣營(所謂“漢宋之爭”),但就曾國藩身處的道光后期京師學術來看,文士群體多主張兼重考據、義理、辭章,彼此間的門戶分歧漸趨融合(即 “漢宋兼采”“漢宋調和”),這與唐鑒、倭仁等以尊德性為治學路徑的理學群體形成鮮明的對照。
道光朝京師的學術風氣由文士主導,其兼擅數家的治學門徑對曾國藩的影響不言而喻。曾國藩的不少師友都學有專精而涉獵廣泛。如何紹基 “長于五事:一曰《儀禮》精,二曰《漢書》熟,三曰《說文》精,四曰各體詩好,五曰字好。”(10)曾國藩:《致澄弟溫弟沅弟季弟》,《曾國藩全集》第20冊,岳麓書社2012年版,第49,31,42、49,38頁。經學、金石學、書法、詩歌皆有造詣。他在為刊刻黃宗羲《宋元學案》撰寫的序文中,亦持漢宋兼采之論,強調德行、六藝不可偏廢。(11)何紹基:《宋元學案序》《重刊〈宋元學案〉書后》,何書置注解:《何紹基詩文集·東洲草堂文鈔》,岳麓書社2008年版,第678—679、713—714頁。再如吳嘉賓理學上尊尚王陽明,文章之學則私淑桐城姚鼐,工于古文,同時在經學方面精于三禮。(12)曾國藩:《歐陽生文集序》,《曾國藩全集》第14冊,第204頁。邵懿辰尊奉桐城文學,長于治經,又熱衷讀理學家書。(13)參見王汎森:《清季的社會政治與經典詮釋——邵懿辰與〈禮經通論〉》,《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7—45頁。其他如湯鵬以詩文名,所著《浮邱子》“通論治道學術”。徐鼒擅長駢文,后專研經義,以許慎、鄭玄為宗。張穆肆力于經史考據,尤以西北史地之學聞名,而留心世務。曾國藩早期兼事文學和理學,便是受到當時京師學風的熏陶。
道光后期曾國藩所身處的京師之中,心性工夫尚未成為學術風尚,理學家數量上遠不如文士和經學家。理學家反對標榜和集會,強調暗然自修的身心工夫,此種學術態度也不利于群體的壯大。反觀文士群體,詩古文辭和經史小學本就是風雅時尚,較之理學要求的苦修式的修養磨煉更容易為人接受。但是,大約在唐鑒入京后不久,曾國藩的學術興趣卻悄然從詩古文辭轉向了心性工夫。
曾國藩與文士群體的交誼,緣于詩古文辭方面的共同志趣。盡管往來密切,但曾國藩卻對文士的雅集酬宴有所警惕:“近來聞好友甚多,予不欲先去拜別人,恐徒標榜虛聲。蓋求友以匡己之不逮,此大益也;標榜以盜虛名,是大損也。天下有益之事,即有足損者寓乎其中,不可不辨。”(14)曾國藩:《致澄弟溫弟沅弟季弟》,《曾國藩全集》第20冊,第42頁。曾國藩在一次紀念歐陽修生日的雅集聚會上,寫了一首贊賞文壇領袖梅曾亮的詩。然而詩的開篇卻道:“宴飲非吾欣,十招九不起。豈不耽群歡,未諳諾與唯。今日飲邵侯,婆娑辦一喜。多因坐上賓,可人非俗子。”(15)曾國藩:《丁未六月廿一為歐陽公生日集邵二寓齋分韻得是字》,《曾國藩全集》第14冊,第59頁。雅集酬宴是當時士大夫之間流行的社交方式,曾國藩內心強烈的道德意識卻將此等娛樂性的交游活動認定為道德墮落的表現。那些原本以追憶先賢、崇尚風雅的集會,實際上不過是追逐名利虛榮的世俗應酬。互相標榜對于個人的學問和德行沒有絲毫進益,與曾國藩的交游初衷完全相悖,這最終促使他轉而融入理學群體,積極效仿師友進行嚴密的工夫修行,開啟了一年有余的“專門理學”時期。
二、專門理學:省身日記與主靜工夫
從曾國藩在京各時期的居所,也不難看出他早年從文學到理學的微妙轉向。曾國藩在道光二十年(1840)二月入京后,一直到道光二十四年三月搬入內城期間,先后居住在“宣南”一帶的南橫街千佛庵、果子巷萬順店、達子營關帝廟、棉花六條胡同、繩匠胡同。“宣南”是指北京宣武門外以南的地區,自清中期以降,是士宦和舉子交游活動的聚集地。(16)關于宣南文化及文人交游的研究,參見岳升陽、黃宗漢、魏泉:《宣南——清代京師士人聚居區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12年版。曾國藩京師文士圈的朋友大都居住此地,比鄰而居為彼此切磋詩文、雅集酬唱提供了便利。對自我道德的強烈期許,促使曾國藩與住在內城的理學群體積極展開交往。他最終搬至內城,主要就是出于潛心踐履身心工夫的初衷。道光二十二年(1842)九月,曾國藩在家書中寫道:
吳竹如近日往來極密,來則作竟日之談,所言皆身心國家大道理。渠言有竇蘭泉者,見道極精當平實。竇亦深知予者,彼此現尚未拜往。竹如必要予搬進城住,蓋城內鏡海先生可以師事,倭艮峰先生、竇蘭泉可以友事。師友夾持,雖懦夫亦有立志。予思朱子言為學譬如熬肉,先須用猛火煮,然后用漫火溫。予生平工夫全未用猛火煮過,雖略有見識,乃是從悟境得來。偶用功,亦不過優游玩索已耳。如未沸之湯,遽用漫火溫之,將愈煮愈不熟矣。以是急思搬進城內,屏除一切,從事于克己之學。鏡海、艮峰兩先生亦勸我急搬。而城外朋友,予亦有思常見者數人,如邵蕙西、吳子序、何子貞、陳岱云是也。(17)王澧華注評:《曾國藩家書詳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49—50頁。
當時唐鑒、吳廷棟等人均居住在內城,曾國藩卻住在屬于外城“宣南”地區的繩匠胡同,往來間殊為不便,特別是夜晚城門關閉后便無法活動,空間地理上的阻隔影響了曾國藩的道德工夫進展。在寫出家書半個月后的日記中,便可以看到曾國藩在內城找房的記錄。雖然搬家心切,曾氏卻遲遲未能找到理想的房源,一直拖到道光二十四年三月,才搬到內城的前門碾兒胡同西頭路北。
搬家的前一個月,曾氏在日記中再次表達了專心致力修身工夫的急迫心情:“昨日,因作字思用功所以無恒者,皆助長之念害之也。本日,因聞竹如言,知此事萬非疲軟人所能勝,須是剛猛,用血戰工夫,斷不可弱,二者不易之理也。時時謹記《朱子語類》‘雞伏卵’及‘猛火煮’二條,刻刻莫忘。”(18)曾國藩:《曾國藩日記》,道光二十三年二月十三日,《曾國藩全集》第16冊,第155頁。“雞伏卵”用以比喻工夫持久不斷,“猛火煮”比喻工夫嚴密刻厲。修行工夫需要頑強的毅力和決心,師友間的相互督促可以有效地防范懈怠。在初事理學時期,曾國藩越發感受到居住在文人群居的宣南地區,根本無法達到理想的修行效果。正是這份焦慮,讓他最終決定搬入內城。
曾國藩下定決心致力理學主要是受到唐鑒的指引,他曾給賀長齡寫信說:“國藩本以無本之學,尋聲逐響,自從鏡海先生游,稍乃粗識指歸。”(19)曾國藩:《復賀長齡》,《曾國藩全集》第22冊,第5頁。唐鑒于道光二十年入京任太常寺卿,在他周圍很快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學人,其中吳廷棟和倭仁的治學方法給曾國藩留下深刻的印象:“吾友吳竹如格物工夫頗深,一事一物,皆求其理。倭艮峰先生則誠意工夫極嚴,每日有日課冊,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皆筆之于書。”(20)曾國藩:《致澄弟溫弟沅弟季弟》,《曾國藩全集》第20冊,第35頁。吳廷棟(號竹如)精于義理思辨,倭仁(號艮峰)則以工夫嚴密著稱。曾國藩在理學的學習上重視德行踐履,更近倭仁一路。他模仿倭仁記錄省身日記,時刻提撕此心,不使放失。工夫每有疏懶時,曾國藩都會做一番深切的懺悔和自勉,如: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日反思內心不能靜定無擾,懺悔此心“昏濁如此,何日能徹底變換”;十月廿五日反省名利心重,“日來自治愈疏矣,絕無瑟僴之意”,陋習全無改正;十二月廿三日見馮卓懷,自悔“日來工夫甚疏”,相約元旦過后“蕩滌更新”;廿六日“以今年空度,一事無成,一過未改,不勝憤恨”;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又說:“自正月以來,日日頹放,遂已一月,志之不立,一至于此。每觀此冊,不知何謂,可以為人乎!聊存為告朔之餼羊爾。”(21)曾國藩:《曾國藩日記》,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日、二十五日、十二月二十三日、二十六日;道光二十三年一月三十日,《曾國藩全集》第16冊,第113、122、142、143、152頁。省身日記在曾國藩看來,沒有發揮預期的理想功能。盡管不斷地反省、自勉,但懈怠的情況并未得到有效改善,曾國藩的省身日記只維持了161天便宣告結束。
曾國藩進行修身工夫的一個主要目的,是對自己的性格缺失和惡習予以糾正。針對浮躁易怒的性格問題,曾國藩在理學前輩的指導下,嘗試通過主靜工夫加以改善。曾國藩曾告訴唐鑒和倭仁,自己“素有忿很不顧氣習,偏于剛惡”,認為病癥在于“好動不好靜”。唐、倭二人即對癥下藥,以主靜之法相傳授。唐鑒言:
最是“靜”字功夫要緊。大程夫子是三代后圣人,亦是“靜”字功夫足。王文成亦是“靜”字有功夫,所以他能不動心。若不靜,省身也不密,見理也不明,都是浮的。總是要靜。(22)曾國藩:《曾國藩日記》,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曾國藩全集》第16冊,第123頁。
唐鑒列舉程明道和王陽明的“主靜”作為依據,明道在《定性書》中講“動亦定,靜亦定”,即是要保持內心“定靜”的狀態。陽明居滁州時,“見諸生多務知解,口耳異同,無益于得,姑教之靜坐。一時窺見光景,頗收近效。”日久漸有喜靜厭動之弊,因此改以“致良知”為宗旨統合“靜處體悟”和“事上磨練”。(23)王守仁著,王曉昕、趙平略點校:《王文成公全書·傳習錄下》,中華書局2015年版,第130頁。陽明早前所倡靜坐之法造成“喜靜厭動”的流弊,曾國藩恰與之相反,病根在于“喜動厭靜”,故唐鑒誡之以主靜。
身心工夫不僅是道德修養的關鍵,也是治病養生的法門。馮卓懷結合孟子養氣論云:“心與氣總拆不開,心微浮則氣浮矣,氣散則心亦散矣。”養氣歸根結底在于養心,靜坐法則是養心的捷徑:“舍靜坐更無下手處,能靜坐而天下之能事畢矣。”(24)曾國藩:《曾國藩日記》,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曾國藩全集》第16冊,第128頁。來到京城之后,曾國藩不僅患上癬疾,且精力日衰,眼花體弱,風寒易侵。他曾求診于頗通醫道的吳廷棟,吳氏亦教其靜坐法,認為曾氏的病根源于浮躁的心病,欲根除此病,還是要從心性修養上下工夫。
三、別有宗尚:研習漢學與師法顧、王
大致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前后,曾國藩開始重視訓詁考據,進入“漢學”領域。盡管曾氏后來將自己的學術定調為“一宗宋儒,不廢漢學”,但他所說的“宗宋儒”更應理解為一種思想宗尚,而非治學重心一貫以宋學或理學為主。(25)曾國藩提出“一宗宋儒,不廢漢學”的出發點,在于反對夏炘極力批判漢學的態度。曾國藩:《復夏教授》,《曾國藩全集》第26冊,第335頁。關于曾國藩后來何以不再專注嚴密的修身工夫,一種解釋認為,此種方法未能達到曾氏起初進德修身的預期——在自我反省的同時,內心陷入極端激烈的斗爭之中;加之記錄省身日記要耗費大量的時間與心力,與現實社會的嚴重脫節,最終促成曾國藩放棄省察克治的理學工夫路徑。(26)參見彭勃:《道咸同三朝理學家日記互批研究》,《華南師范大學學報》2019年第1期。這一說法是合理推測其內在原因,然而更為直接導致曾國藩學術發生轉向的,恐怕還是其外在身份的變化——道光二十三年底,曾國藩升任文淵閣校理,這使得他大量閱讀經史古籍,從事考據校讎,進而研習文字小學,這也正是曾氏學術的第二個拐點。在擔任文淵閣校理期間,曾國藩“每歲二月侍從宣宗皇帝入閣,得觀《四庫全書》。”(27)曾國藩:《圣哲畫像記》,《曾國藩全集》第14冊,第150頁。在二十年后所作的一首關于唐本《說文》的詩中,曾氏回憶說:“我昔趨朝陪庶尹,頗究六書醫頑蠢。”(28)曾國藩:《題唐本〈說文·木部〉應莫郘亭孝廉》,《曾國藩全集》第14冊,第84頁。文淵閣從事校讎的經歷,讓曾國藩對清儒博雅之學、考據之法有了切身的體會。他對清儒的認識不再停留于漢宋門戶之爭下對于漢學的刻板印象。
曾國藩以漢學為治學重心,尤其尊崇顧炎武和王念孫的學問。有人提議讓方苞從祀孔廟時,曾國藩認為方苞古文雖好,在學問上卻無法與顧、王比肩。他在咸豐十一年寫給曾國荃的信中說:“姬傳先生最推崇方氏,亦不稱其經說。其古文號為一代正宗,國藩少年好之,近十余年,亦別有宗尚矣。國藩于本朝大儒,學問則宗顧亭林、王懷祖兩先生。”(29)曾國藩:《致沅弟》,《曾國藩全集》第20冊,第671頁。方苞、姚鼐(字姬傳)都是桐城派文學宗師,曾國藩居京之初喜好詩文,尊崇方、姚,這正對應“少年好之”之語。后來學術重心發生轉變,“近十余年”已改為宗尚顧、王訓詁考據之學。曾氏也曾自述,在清儒“善讀古書者”中,“最好高郵王氏父子”,并計劃效仿顧炎武、王念孫做學術札記,考辨經史文集。(30)曾國藩:《諭紀澤》,《曾國藩全集》第20冊,第426頁。
促使曾國藩研習漢學的契機,除了文淵閣校理的職務因素外,還有京師友人的影響。曾國藩文士圈的朋友中不乏精于考據學、小學者,苗夔和劉傳瑩是較為重要的兩個。苗夔曾得到王念孫、王引之父子的賞拔,以《說文》學聞名其時。曾國藩推許苗夔的小學造詣,認為足以接踵江永、戴震、段玉裁、孔繁森等乾嘉樸學大師。(31)曾國藩:《題苗先麓〈寒燈訂韻圖〉》,《曾國藩全集》第14冊,第66—67頁。但他對苗夔的《說文聲讀表》也有批評:“吾友河間苗仙路夔為《說文聲讀表》,于凡文字皆決以一定之音讀,其不可齊者亦強之使齊,于是以臆為斷,頗傷專輒。于古無征,動成瑕疵。偶記一則,將以詒之。”(32)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詁訓雜記》,《曾國藩全集》第15冊,第122頁。對于苗夔音韻著作的不滿顯示出,曾國藩對音韻學的掌握已不輸給素治此道的專家。道光二十五年,曾氏在寫給友人劉傳瑩的信中,坦言自己“數年看《說文》,總無心得”,其中當然有謙虛的成分。值得注意的是,曾國藩將這一問題歸結于“不能記憶篆體,則不能因形以得聲,因形聲以究義”,說明此時他已完全接受了清儒因聲求義之法。曾氏“將顧、江、戴、段說聲之書,悉心參校”,在《說文》學方面終于“略有端緒”,取得了良好的效果。(33)曾國藩:《致劉傳瑩》,《曾國藩全集》第22冊,第14頁。
道光二十五年八月,曾國藩熱毒發作,身體狀況欠佳。因家中客多,鮮少清靜,不利養病,遂移寓離家較近的呂祖閣廟內,道光二十六年十月又寄居城南報國寺。自生病以來,曾國藩“拋棄書冊,心如廢井”,直到同年六月,“始復重理故業,見從事《說文》之學。”(34)曾國藩:《致陳源兗郭嵩燾》,《曾國藩全集》第22冊,第24頁。曾氏在病情稍微恢復后,繼續鉆研訓詁考據之學。在報國寺養病期間,劉傳瑩也居住其中。劉氏自幼篤嗜胡渭、閻若璩的考據之書,精于方輿、六書、九數之學。自道光二十六年夏秋之交,曾國藩便因病僦居于報國寺,向劉氏請教《說文》之學:“漢陽劉公傳瑩,精考據之學,好為深沉之思,與公尤莫逆,每從于寺舍,兀坐相對竟日。”(35)黎庶昌:《曾國藩年譜》,岳麓書社1986年版,第10頁。
劉傳瑩向曾國藩討教理學,曾國藩則從劉氏學習漢學,兩人之間相互切磋,取長補短。在此期間曾國藩有詩贈予劉氏,詩中有:“惜哉數子琢肝腎,鑿破醇古趨囂嚚。書史不是養生物,雕镵例少牢強身。”(36)曾國藩:《丙午初冬寓居報國寺賦詩五首》(其二),《曾國藩全集》第14冊,第52頁。數語調侃文字小學耗費精神、不利養生,從側面反映出曾國藩致力于訓詁考據的事實。
報國寺中特辟顧炎武祠堂,曾國藩贈予劉氏的另一首詩中寫的就是顧炎武。其中有“俗儒閣閣蛙亂鳴,亭林老子初金聲”;“獨有文書巨眼在,北斗麗天萬古明。聲音上溯三皇始,地志欲掩四子名”等語(37)曾國藩:《丙午初冬寓居報國寺賦詩五首》(其四),《曾國藩全集》第14冊,第52—53頁。,對顧炎武(亭林)的音韻和輿地之學尤為激賞。顧祠由何紹基、張穆于道光二十三年創建,此后每年召集在京士人定期舉行公祭集會。何、張是曾國藩在京師文士圈中的朋友,與曾氏相熟的邵懿辰、朱琦、湯鵬、劉傳瑩等人也都是顧祠會祭的成員。(38)徐鼒記錄道光二十五年后參與顧祠會祭者名單中有曾國藩。據考證,曾國藩并未參與過顧祠會祭。徐氏蓋為誤錄。參見段志強:《顧祠——顧炎武與晚清士人政治人格的重塑》,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09、143頁。道光朝以降,士人追捧顧炎武或折服于其遺老孤臣的人格魅力,或是將顧氏視為程朱博雅之學的嫡傳,或是把他追溯為反理學的漢學先驅。無論偏尚漢學還是宋學,都以顧炎武的學術和人格為榜樣。曾國藩對于顧炎武學術人格的尊崇,同樣也是時代學術氛圍影響下的結果。
相比之下,唐鑒、倭仁等理學家對顧炎武雖然也有所認可,卻又頗有微詞。倭仁即批評顧氏之學“用多體少”。(39)陸心源:《上倭艮峰相國書》,《儀顧堂集》,《續修四庫全書》,第1560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411頁。唐鑒的學術史名作《國朝學案小識》將清初理學家陸隴其、張履祥、陸世儀、張伯行四人列為“傳道”的正統學人,顧炎武則被列入次一等的“翼道”類。學案中對顧氏學術的書寫,也只是強調其駁斥王陽明《朱子晚年定論》的理學態度,以及博雅之學方面繼承朱子學。(40)唐鑒撰、李健美點校:《國朝學案小識》,岳麓書社2010年版,第313—318頁。曾國藩在給《學案小識》作跋時對此作了微妙的調整,他說:“我朝崇儒一道,正學翕興。平湖陸子,桐鄉張子,辟诐辭而反經,確乎其不可拔。陸桴亭、顧亭林之徒,博大精微,體用兼賅。其他巨公碩學,項領相望。二百年來,大小醇疵,區以別矣。”(41)曾國藩:《書〈學案小識〉后》,《曾國藩全集》第14冊,第229頁。
在曾國藩的序文中,顧炎武代替張伯行,躍升為第一梯隊“傳道”學案中的學者,這一改動明顯是有意為之。曾氏曾形容劉傳瑩的學術“遠師朱子,近法顧氏,以義理為歸而考之實事”(42)曾國藩:《致洪汝奎》,《曾國藩全集》第22冊,第36頁。,實際上這也是曾國藩自家學術的寫照。在他看來,顧炎武要比拘泥于門戶偏見的衛道士更有資格成為朱子學的嫡傳。
四、禮學歸宿:紹續清儒及經世意圖
將顧炎武納入朱子學術序列,在乾嘉時就已經成為一種共識,如章學誠有“顧氏宗朱”的說法(43)章學誠:《浙東學術》,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523頁。,江藩則指出:“亭林乃文清之裔,辨陸王之非,以朱子為宗。”(44)江藩撰、鐘哲整理:《國朝漢學師承記》,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33頁。嘉慶年間署名為阮元的兩卷本《國史儒林傳》,對曾國藩認識顧氏(及清儒學術)的影響尤為關鍵。曾氏每以《國史儒林傳》為依據評論清儒,其《圣哲畫像記》列入顧氏,根據即是“我朝學者以顧亭林為宗,國史《儒林傳》褎然冠首。”(45)曾國藩:《圣哲畫像記》,《曾國藩全集》第14冊,第152頁。
實際上,《國史儒林傳》以顧炎武居首并非阮元的主張,而是嘉慶年間宣南詩社的核心成員顧莼在進呈本中所作的改定。阮元在《儒林傳稿》中僅將顧炎武列于第七位,他對顧炎武學術的肯定,也主要體現在經史考據方面。至于《日知錄》中的經世之學,阮元批評其“有矯枉過中之處。”(46)阮元:《顧亭林先生〈肇域志〉跋》,鄧經元點校:《揅經室集·續三集》,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673—674頁。經世之學重在致用,阮元卻指責其說不切實際。顧炎武在道光后期學術地位的升高,與顧祠成員的推動存在直接關系。(47)王汎森:《清代儒者的全神堂——〈國史儒林傳〉的編纂與道光年間顧祠祭的成立》,《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第565—602頁。關于阮元《儒林傳稿》與二卷本《國史儒林傳》之間關系的研究,參見戚學民:《阮元〈儒林傳稿〉研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版,第245—278頁。顧祠成員強調顧炎武的學術兼包經世及經史小學,如何紹基《別顧先生祠》一詩評價顧炎武學問說:“兵刑禮樂尊,九數六書衍。漢宋包群流,周孔接一線。”(48)何紹基:《別顧先生祠》,何書置注解:《何紹基詩文集·東洲草堂詩鈔》,第168頁。曾國藩對顧炎武的評價,與以何紹基為代表的顧祠成員一致。在致力訓詁考據時期,曾氏在敘述中更為推重顧炎武的經史小學,后來卻轉而強調顧氏的經世之學,特別是其禮學上的經世意義。如他說:“顧亭林氏著書,以扶植禮教為己任。”(49)曾國藩:《孫芝房侍講芻論序》,《曾國藩全集》第14冊,第206頁。又說:“吾讀其書,言及禮俗教化,則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誰之志,何其壯也!”(50)曾國藩:《圣哲畫像記》,《曾國藩全集》第14冊,第152頁。這一論述重心的變化,與曾國藩在道光二十七年自身學術轉向禮學相關聯。
道光二十七年下半年,曾國藩升任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因職務所需,開始重視禮學。這是曾氏學術的又一次轉向,禮學也是其后來一貫致力的學術面向。在曾國藩的學術體系中,禮學被定位為經濟/經世之學,也就是孔門四科中“政事”的范疇。曾氏自早期從事心性工夫到后來轉向禮學,無不以致用為旨歸。追隨唐鑒學習理學期間,唐鑒告訴他學問可分為義理、考核、文章三途,三者之中以義理為宗,經濟之學亦在義理之學的范疇內。當時曾國藩問及經濟之學的具體內容,唐鑒則答以“不外看史”,從史書中探究古人所立法戒及歷代典章制度。(51)曾國藩:《曾國藩日記》,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曾國藩全集》第16冊,第92頁。曾國藩完全接受了唐鑒的觀點,他在道光二十三年的家書中就談及:“義理之學最大。義理明則躬行有要而經濟有本。詞章之學,亦所以發揮義理者也。”(52)曾國藩:《致澄弟溫弟沅弟季弟》,《曾國藩全集》第20冊,第49頁。詞章是發揮義理思想的載體,義理之學是道德踐履、經世致用的根基。這與當時曾氏熱衷于理學相吻合。從曾國藩和唐鑒的對話中,可以發現曾國藩此時已具備明顯的經世意識,但禮學卻是在他研習漢學之后,始成為其經世思想的重心。
道光二十三年的曾國藩受姚、唐等人的影響,對漢學仍抱有門戶偏見,于考據之學“無取焉”。到道光二十七年轉向禮學后,曾國藩的經世思想也發生了改變。他說:“蓋古之學者,無所謂經世之術也,學禮焉而已。”(53)曾國藩:《孫芝房侍講芻論序》,《曾國藩全集》第14冊,第206頁。禮學并非要做文獻上的考古,必須通過博稽考核進而本末貫通。它一方面是“考先王制作之源”,以求圣人制作之意;另一方面更是“辨后世因革之要”,從歷代制度因革中考察治世之法。從禮儀制度與道德修養、經世致用的關系上講:“自內焉者言之,舍禮無所謂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禮無所謂政事。”(54)曾國藩:《筆記十二則·禮》,《曾國藩全集》第14冊,第410頁。禮學是道德性命之學的基礎,是經世學的主體,這與曾國藩早年所講的“義理明則躬行有要而經濟有本”迥然異趣。李鴻章說曾國藩“學問宗旨,以禮為歸”(55)李鴻章:《曾文正公神道碑》,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6頁。,可謂的論。
曾國藩對禮學的研究涵蓋三禮經典、禮制考證、禮俗改良等方面,前人對此已有不少討論。其中,通禮學最能代表曾氏居京時期的經世思想和禮學特色。道咸之際的數年中,曾國藩籌備編纂一部通禮之書,將禮法分為十四大項,包括官制、財用、鹽政、漕務、錢法、冠禮、昏禮、喪禮、祭禮、兵制、兵法、刑律、地輿、河渠——禮制的內容幾乎囊括了所有經世之務。曾氏又以清代禮制為核心,“歷溯前代之沿革本末”并加以折衷。(56)曾國藩:《曾國藩日記》,咸豐元年八月二十二日,《曾國藩全集》第16冊,第246頁。從曾國藩在京師擔任禮部官員時的治學情況看,他的通禮學思想深受乾隆朝漢學家江永《禮書綱目》及秦蕙田《五禮通考》兩部通禮類著作的影響。特別是秦蕙田《五禮通考》,曾氏有“私獨宗之”之語。(57)曾國藩:《圣哲畫像記》,《曾國藩全集》第14冊,第152頁。鑒于《五禮通考》缺少“食貨”部分,欲續為補編。(58)曾國藩:《孫芝房侍講芻論序》,《曾國藩全集》第14冊,第206頁。
根據周啟榮對清代禮學的考察,清代前期禮學主要延續宋、元、明的脈絡,特別重視朱熹的禮學思想。(59)參見周啟榮:《清代儒家禮教主義的興起》,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23—280頁。江永《禮書綱目》、秦蕙田《五禮通考》都曾受到朱熹《儀禮經傳通解》的啟發。其中,江永鑒于《儀禮經傳通解》體例未愜,重做編排,“欲卒朱子之志,成禮樂之完書”。(60)江永:《禮書綱目序》,《叢書集成續編》經部第11冊,上海書店1994年影印廣雅書局本,第153頁。秦蕙田于三代之外進一步稽考歷代禮制,《五禮通考》的撰寫初衷亦在繼承朱子之志。(61)參見曹建墩:《論朱子禮學對〈五禮通考〉的影響》,《江海學刊》2014年第5期。到了乾嘉漢學興盛之際,禮學重心則轉向三禮注疏和古禮考證。曾國藩紹續江永、秦蕙田的通禮學思路,一反乾嘉考證古禮的傳統,也是對漢學的糾偏。盡管江、秦禮書常被歸為漢學典范,但曾國藩卻強調二氏之書“可以通漢、宋二家之結,而息頓漸諸說之爭。”(62)曾國藩:《復夏炘》,《曾國藩全集》第23冊,第730頁。將博稽考核為主要方法的清儒通禮學上溯至朱子,由此會通漢宋,這正體現了曾氏一貫反對門戶之爭、博采眾長的治學態度。
嘉道之際,士人的經世意識開始覺醒,京師洋溢著濃厚的經世學風。曾國藩編纂禮書,用意正在改革制度、施行教化、匡正人心風俗——通禮學背后蘊含的經世意圖與京師經世學風相契合。就禮學思想而言,晚清禮學具有調和漢宋、經世關懷、因時制禮等特點,通過闡明制度,以期進行社會和禮俗的改良。曾國藩的禮學也具備這些特點,但在方法形式上又有其獨特之處。因為當時禮家多是圍繞三禮注疏和禮制考證展開討論,鮮少如曾國藩一般強調通禮學研究。(63)參見羅檢秋:《學術調融與晚清禮學的思想活力》,《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5期。僅就曾氏居京期間的友人為例,邵懿辰《禮經通論》一書,是據大戴《禮記》篇次順序重組《儀禮》各篇,議論則以發揮禮意為主。吳嘉賓《喪服會通說》專就禮經和歷代喪服制度加以考證。郭嵩燾《禮記質疑》兼采漢宋諸儒之說,考辨文字注疏。曾國藩以江、秦為法的通禮學思想不僅在道光后期的京師學術圈獨樹一幟,即使放眼于整個晚清禮學,亦足成一家之言。
總 結
自會試及第后,曾國藩一直在翰林院供職。道光二十五年升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后又陸續擔任翰林院侍講學士、日講起居注官、文淵閣直閣事等清要之職,因此有大量時間專注于讀書治學。(64)曾國藩在家書中即言:“詹事府本是東宮輔導太子之官,因本朝另設有上書房教阿哥,故詹事府諸官毫無所事,不過如翰林院為儲才養望之地而已。男居此職,仍日以讀書為業。”曾國藩:《稟父母》,《曾國藩全集》第20冊,第104頁。道光二十七年七月,曾國藩升任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閣學雖兼部堂銜,實與部務毫不相干”,仍較為清閑。直到道光二十九年正月升任禮部右侍郎,三十年又分別兼署工部、兵部侍郎銜,部堂專職“事務較繁”,加之應酬私事,導致“日內甚忙冗,幾于刻無暇晷”,盡管如此繁忙,卻仍有余力讀書。(65)曾國藩:《稟父母》,《曾國藩全集》第20冊,第160頁。咸豐元年(1851)六月復兼署刑部侍郎,“日日忙冗異常,迥不與禮部、工部、兵部相同。若長在此部,則不復能看書矣。”(66)曾國藩:《致澄弟溫弟沅弟季弟》,《曾國藩全集》第20冊,第192頁。
在此前長達十年的居京生活中,曾國藩的治學重心經歷了三次轉變:初入翰林院時,曾氏以詩古文辭為志趣,后加入唐鑒理學群體,從事身心工夫;進入文淵閣校館后,始尊尚清儒漢學,致力于訓詁考據,這是曾氏治學重心的第二次轉向;第三次轉向以進入禮部任職為節點,禮學成為曾氏后期的學術旨歸。結合曾國藩闡發《論語》孔門四科的說法,我們可以將其學術發展總結為:從詞章到義理、再到考據、最終歸于經世學的轉移。曾國藩自始至終未曾改變的是抱持一種通達包容的儒學觀念,每次轉入新的治學領域時,并未摒棄以往的學說思想。其治學重心的轉向,其實是一個學術遞進成長的過程。曾國藩游走于京師理學圈子和文士圈子的獨特經歷,讓他真正意義上超越漢宋門戶壁壘——不止是一種兼容的態度或者調和的論調——更是能夠深入研習詩古文辭、道德性命、訓詁考據、禮學經世等不同領域,切實體會各家精神,最終造就了曾國藩宏大深厚的學術面貌。其中既凝聚了曾氏個人矢志求學的努力,更離不開京師學友和整體學風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