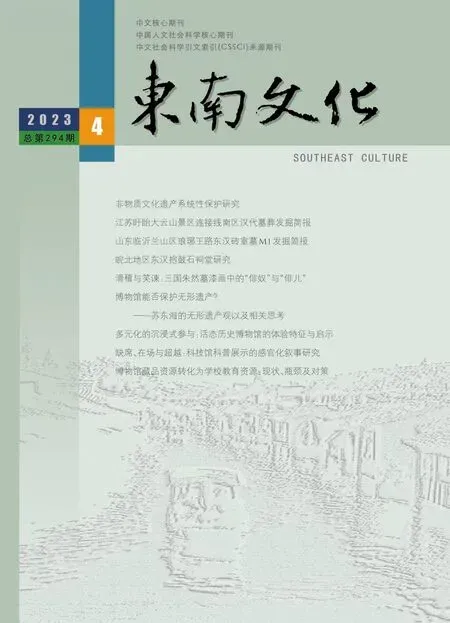博物館能否保護(hù)無形遺產(chǎn)?
——蘇東海的無形遺產(chǎn)觀以及相關(guān)思考
陳佳璐 尹 凱
(山東大學(xué)文化遺產(chǎn)研究院 山東青島 266237)
內(nèi)容提要:直至今日,遺產(chǎn)學(xué)界與博物館學(xué)界關(guān)于無形遺產(chǎn)的本質(zhì)與保護(hù)問題的討論從未停歇。21 世紀(jì)初,蘇東海先生曾以無形遺產(chǎn)為主題發(fā)表過若干文章,其核心觀點(diǎn)是無形遺產(chǎn)的特殊性使得博物館在保護(hù)無形遺產(chǎn)上是無能為力的。與“能否保護(hù)”的學(xué)術(shù)討論相伴而生的是“如何保護(hù)”的實(shí)踐探索,尤其是無形遺產(chǎn)在2007 年被寫入博物館定義之后,一系列保護(hù)嘗試影響甚至重塑了博物館的潛力。雖然博物館與無形遺產(chǎn)之間的關(guān)系是動態(tài)的、情境化的,但是博物館能否保護(hù)無形遺產(chǎn)依然是一個值得重申的學(xué)術(shù)議題。無形遺產(chǎn)的特殊性和傳統(tǒng)的保護(hù)模式不得不讓博物館世界重新思考博物館在保護(hù)無形遺產(chǎn)上所扮演的角色。
一、無形遺產(chǎn)進(jìn)入博物館世界
為了彌補(bǔ)世界遺產(chǎn)制度在原住民社區(qū)、傳統(tǒng)文化和活態(tài)文化等議題上的疏漏,2003 年,《保護(hù)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公約》(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以下簡稱“《非遺公約》”)在聯(lián)合國教育、科學(xué)及文化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UNESCO)第32 屆大會上通過。自此,無形遺產(chǎn)[1]被正式納入U(xiǎn)NESCO 主導(dǎo)的國際遺產(chǎn)保護(hù)體系。
在《非遺公約》通過前后,無形遺產(chǎn)作為一個有趣的話題進(jìn)入博物館世界,并引起持續(xù)關(guān)注。1998 年,國際博物館協(xié)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ICOM)在墨爾本大會通過的決議上指出,要關(guān)注旅游業(yè)發(fā)展對無形遺產(chǎn)資源的影響[2]。2001 年,ICOM 在巴塞羅那大會上第一次“把收藏和保護(hù)無形遺產(chǎn)列入博物館定義的外延之中”[3],隨后,ICOM 將“博物館與無形遺產(chǎn)”(Museums and Intangible Heritage)確定為2004 年“國際博物館日”以及ICOM 第20 屆大會的主題。2000 年與2004 年,國際博協(xié)博物館學(xué)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Museology)先后兩次將“博物館學(xué)與無形遺產(chǎn)之間的關(guān)系”作為年會主題進(jìn)行討論。2002 年10 月,“國際博物館協(xié)會亞太地區(qū)第七次大會暨博物館無形文化遺產(chǎn)國際學(xué)術(shù)討論會”在上海召開,大會圍繞“博物館、無形遺產(chǎn)和全球化”的主題討論了博物館與無形遺產(chǎn)的理論和實(shí)踐問題。2007 年,ICOM 在奧地利維也納(Vienna)召開的第21 屆大會上修訂了博物館定義,博物館的工作對象由“人類及其環(huán)境的物證”調(diào)整為“有形和無形遺產(chǎn)”[4]。至此,無形遺產(chǎn)被正式納入博物館的官方定義,相應(yīng)地,博物館與無形遺產(chǎn)的關(guān)系也成為博物館研究領(lǐng)域的核心議題。
關(guān)于“博物館能否保護(hù)無形遺產(chǎn)”這一問題,學(xué)界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diǎn):一種觀點(diǎn)著眼于概念與理論的推論,從無形遺產(chǎn)的特殊性以及無形遺產(chǎn)與博物館之間的“非常規(guī)”關(guān)系入手,認(rèn)為博物館保護(hù)無形遺產(chǎn)存在著將無形遺產(chǎn)固化的風(fēng)險(xiǎn),因此,博物館在保護(hù)無形遺產(chǎn)上是相對無力的[5];另一種觀點(diǎn)則著眼于博物館介入無形遺產(chǎn)的實(shí)踐,對其進(jìn)行觀察與歸納,認(rèn)為博物館可以憑借其收藏、研究和教育職能,利用實(shí)物、影像和演示等手段,通過對無形遺產(chǎn)過程性現(xiàn)象的可感知化與再語境化以及信息的闡釋與傳播等策略來保護(hù)無形遺產(chǎn)[6]。隨著無形遺產(chǎn)正式進(jìn)入博物館定義,博物館保護(hù)無形遺產(chǎn)的正當(dāng)性與合理性似乎越發(fā)不言自明,后者的聲音日漸在遺產(chǎn)學(xué)界和博物館學(xué)界占據(jù)上風(fēng)。這些有益的探索雖然在某種程度上彌合了博物館與無形遺產(chǎn)之間存在的鴻溝,但是對深層次的問題語焉不詳。換句話說,這些研究繞過了博物館“能否”保護(hù)無形遺產(chǎn)這一根本性問題,而直接聚焦于“如何”保護(hù)無形遺產(chǎn)。
21 世紀(jì)初,著名博物館學(xué)家蘇東海先生(以下省略敬稱)注意到了無形遺產(chǎn)的發(fā)展態(tài)勢及其引發(fā)的相關(guān)爭論。在保護(hù)無形遺產(chǎn)已是共識的今天,重拾蘇東海的無形遺產(chǎn)觀有助于博物館界在思考與實(shí)踐無形遺產(chǎn)保護(hù)問題的同時(shí),進(jìn)一步追問無形遺產(chǎn)的本質(zhì)、博物館角色與功能的轉(zhuǎn)向、博物館保護(hù)無形遺產(chǎn)的悖論等更加核心的命題。
二、蘇東海的無形遺產(chǎn)觀
蘇東海的無形遺產(chǎn)觀可以看作是對無形遺產(chǎn)進(jìn)入博物館過程中所產(chǎn)生的一系列困惑的回應(yīng)和思考。對此,他主要關(guān)注兩大問題:一為無形遺產(chǎn)相比于有形遺產(chǎn)的特殊性,二為無形遺產(chǎn)與博物館的關(guān)系。
(一)無形遺產(chǎn)的特殊性
蘇東海認(rèn)為,無形遺產(chǎn)的定義以及我們對它的理解存在著混亂,這主要是因?yàn)闊o形遺產(chǎn)的定義并不明晰。蘇東海在評價(jià)無形遺產(chǎn)的相關(guān)定義時(shí)指出,《非遺公約》提出的是一個冗長的、列舉式的工作定義,并不準(zhǔn)確、精煉;與此同時(shí),我國國務(wù)院2005 年頒布的《關(guān)于加強(qiáng)文化遺產(chǎn)保護(hù)的通知》(國發(fā)〔2005〕42 號)僅列舉了我國《文物保護(hù)法》和《非遺公約》對于有形遺產(chǎn)與無形遺產(chǎn)的定義描述[7]。上述有關(guān)無形遺產(chǎn)的定義及其描述對于正確認(rèn)識無形遺產(chǎn)的特殊性、辨識無形遺產(chǎn)與有形遺產(chǎn)的關(guān)系來說效果有限,更不用說無形遺產(chǎn)的保護(hù)與利用了。
據(jù)此,蘇東海給無形遺產(chǎn)下了一個“反定義”,即“人類遺產(chǎn)中不是有形遺產(chǎn)的都是無形遺產(chǎn)”[8]。在他的無形遺產(chǎn)觀中,無形遺產(chǎn)與有形遺產(chǎn)的差異表現(xiàn)為精神與物質(zhì)、過程存在與終結(jié)存在、活著的與逝去的。基于此,筆者將無形遺產(chǎn)最根本的兩點(diǎn)特殊性概括為無形性與活態(tài)性。
首先,無形遺產(chǎn)具有無形性。無形遺產(chǎn)與有形遺產(chǎn)存在著精神與物質(zhì)的差異:物是有形遺產(chǎn)的載體,物質(zhì)性是其最顯著的特征;相反,無形遺產(chǎn)屬于精神領(lǐng)域,是無形的,只能靠特殊的介質(zhì)來呈現(xiàn),其中,人與物便是感知無形遺產(chǎn)的介質(zhì)。在無形遺產(chǎn)“無形性”的基礎(chǔ)上,蘇東海進(jìn)一步探討了與之相關(guān)的兩個子命題。其一,無形遺產(chǎn)不等同于有形遺產(chǎn)的無形內(nèi)涵。有形遺產(chǎn)的形式與內(nèi)容是一個統(tǒng)一體[9],不能將有形遺產(chǎn)的內(nèi)涵視作無形遺產(chǎn)。2003 年,意大利博物館國家委員會主席喬凡尼·皮那(Giovanni Pinna)認(rèn)為,“無形遺產(chǎn)包括構(gòu)成有形遺產(chǎn)的實(shí)物所具有的象征和隱喻意義”[10]。蘇東海對此評論道,皮那的表述混淆了無形遺產(chǎn)與有形遺產(chǎn)的無形內(nèi)涵這兩個不同的概念[11]。其二,無形遺產(chǎn)不等同于無形遺產(chǎn)的有形介質(zhì)。蘇東海反對將無形遺產(chǎn)與無形遺產(chǎn)存在的介質(zhì)混為一談。無形遺產(chǎn)的有形介質(zhì)并非無形遺產(chǎn)本身,究其本質(zhì)而言,它并不能單純地代表無形遺產(chǎn),而只是無形遺產(chǎn)存在過程的一種表現(xiàn)形式。無形遺產(chǎn)就是無形遺產(chǎn),無論是有形遺產(chǎn)的無形內(nèi)涵還是無形遺產(chǎn)的有形介質(zhì),都不可與無形遺產(chǎn)混淆。
其次,無形遺產(chǎn)具有活態(tài)性。無形遺產(chǎn)的活態(tài)性由無形遺產(chǎn)及其介質(zhì)的存在狀態(tài)所決定。與有形遺產(chǎn)相比,無形遺產(chǎn)是活著的,其介質(zhì)是過程存在。關(guān)于有形遺產(chǎn)與無形遺產(chǎn)的載體與介質(zhì)的差異,蘇東海認(rèn)為,有形遺產(chǎn)的文化內(nèi)涵已被凝固在物質(zhì)載體內(nèi),物質(zhì)載體是有形遺產(chǎn)文化內(nèi)涵的終端;而無形遺產(chǎn)的文化內(nèi)涵由介質(zhì)所負(fù)荷,通過人或人與物的運(yùn)動而被展示出來——“結(jié)果與過程就是載體與介質(zhì)的差異之所在”[12],即終結(jié)存在與過程存在的差異。同時(shí),這二者的區(qū)別也影響了有形遺產(chǎn)與無形遺產(chǎn)的保護(hù)模式:對前者是按一個歷史物的特征來保護(hù),對后者是按一個現(xiàn)實(shí)物的特征來保護(hù)[13]。無形遺產(chǎn)與有形遺產(chǎn)之間介質(zhì)與載體的差異根源在于這兩種遺產(chǎn)的存在狀態(tài):無形遺產(chǎn)作為一種過程,能夠在各類介質(zhì)的相互作用之間獲取并保持自身的生命力,且不斷再生,在使用與傳承中延續(xù)它的存在;而相比于仍然“活著”的無形遺產(chǎn),有形遺產(chǎn)已經(jīng)失去了生命力。所以,可再生性與不可再生性是無形遺產(chǎn)與有形遺產(chǎn)的又一區(qū)別。
綜上,無形遺產(chǎn)的無形性和活態(tài)性在一定程度上定義了無形遺產(chǎn)的特殊性,即無形遺產(chǎn)就是無形遺產(chǎn),而不是其他。透過上述對無形遺產(chǎn)特殊性的論述,我們能夠體會到蘇東海作為馬克思主義者的立場:蘇東海對無形遺產(chǎn)的認(rèn)識與理解建立在物質(zhì)與精神、有形與無形的辯證關(guān)系與比較研究的基礎(chǔ)之上。這種二分法突出體現(xiàn)在蘇東海對于無形文化遺產(chǎn)學(xué)與有形文化遺產(chǎn)學(xué)二分的推崇上,他認(rèn)為分別建立這兩類文化遺產(chǎn)學(xué)“可能會比把兩者綁在一起建立廣義文化遺產(chǎn)學(xué)更容易些”[14]。蘇東海對無形遺產(chǎn)特殊性的認(rèn)識以及對統(tǒng)一無形遺產(chǎn)與有形遺產(chǎn)的不同看法,最終影響了其對于“博物館能否保護(hù)無形遺產(chǎn)”這一課題的思考。
(二)博物館與無形遺產(chǎn)的關(guān)系
隨著社會對無形遺產(chǎn)的日益重視,博物館在保護(hù)無形遺產(chǎn)中的獨(dú)特角色也被傾注了越來越多的目光。然而,無形遺產(chǎn)與博物館的相遇并非是相互契合、全然美好的,其各自的特殊性決定了兩者之間必然充滿著摩擦、爭議與沖突。遺產(chǎn)學(xué)界和博物館學(xué)界關(guān)于“博物館能否保護(hù)無形遺產(chǎn)”的問題,不應(yīng)該因?yàn)榧侄乇埽鼞?yīng)該做的是將其視為核心命題而予以充分的關(guān)注與討論。
事實(shí)上,蘇東海對于博物館與無形遺產(chǎn)關(guān)系的看法并非是一以貫之的,而是在認(rèn)識的過程中發(fā)生了轉(zhuǎn)變。2002 年《上海憲章》(Shanghai Charter)發(fā)布后,蘇東海在評述文章中寫道,博物館“應(yīng)根據(jù)自己的科學(xué)保存設(shè)備、專業(yè)水平和永久性保存機(jī)構(gòu)的優(yōu)勢條件,理所當(dāng)然地成為保護(hù)和永久保存非物質(zhì)遺產(chǎn)的最重要的機(jī)構(gòu)”[15]。在2004 年“北京國際博物館館長論壇”,蘇東海作了題為《無形遺產(chǎn)保護(hù):博物館的特殊價(jià)值及其局限》的講話,他提到了博物館保護(hù)無形遺產(chǎn)的特殊價(jià)值,同時(shí)也指出博物館的保護(hù)是要將無形與有形遺產(chǎn)統(tǒng)一起來。而在兩年后的《建立廣義文化遺產(chǎn)理論的困境》一文中,蘇東海表達(dá)了無形遺產(chǎn)可能難以統(tǒng)一于廣義遺產(chǎn)概念之中的觀點(diǎn)[16]。2012 年,蘇東海在接受采訪時(shí)表示:“在傳統(tǒng)博物館中接納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多少有一點(diǎn)空想成分,難以有效實(shí)現(xiàn)。”[17]
從“理所當(dāng)然保護(hù)”到“難以有效保護(hù)”,蘇東海為何會在博物館與無形遺產(chǎn)的關(guān)系上經(jīng)歷如此大的觀念轉(zhuǎn)變?要想回答這個問題,我們不得不回到蘇東海關(guān)于無形遺產(chǎn)進(jìn)入博物館的方式與過程的論述中一探究竟。
蘇東海指出,博物館對無形遺產(chǎn)的保護(hù)必須經(jīng)過以下兩個階段。首先是無形遺產(chǎn)的物化階段。“必須把無形遺產(chǎn)有形化,博物館才能接納它,才能達(dá)到無形遺產(chǎn)與有形遺產(chǎn)的保護(hù)一體化。”[18]這意味著無形遺產(chǎn)必須經(jīng)過物化,才能被博物館這種可視、可觸的文化形式[19]所保護(hù),才能與博物館的物質(zhì)本質(zhì)統(tǒng)一起來[20]。這同時(shí)也體現(xiàn)了蘇東海對于博物館物的強(qiáng)調(diào):始終堅(jiān)持“博物館物是博物館存在的物質(zhì)基礎(chǔ)”[21]這一思想,認(rèn)為博物館物是一切博物館實(shí)踐的出發(fā)點(diǎn)與落腳點(diǎn)[22]。其次是無形遺產(chǎn)的博物館化階段。“必須把無形遺產(chǎn)的原生存在轉(zhuǎn)換成博物館存在,才能對它的保護(hù)達(dá)到博物館水平。”[23]若是要實(shí)現(xiàn)博物館對無形遺產(chǎn)的保護(hù),似乎不可避免地要將無形遺產(chǎn)與其原初語境割裂開來。不過,蘇東海也提出了替代性方案,即生態(tài)博物館、社區(qū)博物館可以在文化原生地以博物館的方式對無形遺產(chǎn)實(shí)現(xiàn)保護(hù)[24],這與蘇東海對生態(tài)博物館專業(yè)化的觀念相一致[25]。
在蘇東海看來,博物館保護(hù)無形遺產(chǎn)必然要經(jīng)歷物化與博物館化兩個階段,這是博物館保護(hù)無形遺產(chǎn)得以可能的前提,同時(shí)也暗示了博物館無力保護(hù)無形遺產(chǎn)的事實(shí)。對此,蘇東海指出,這種無力與博物館和無形遺產(chǎn)各自的特性不無關(guān)系。具體而言,“作為無形遺產(chǎn),它是鮮活地存在于它的生存環(huán)境中,但是博物館的存在是一種歷史的存在,是處于過去式存在而不是進(jìn)行式存在。”[26]無形遺產(chǎn)博物館化的前提是脫離其自身的社會和文化語境以及創(chuàng)造該遺產(chǎn)的特定知識系統(tǒng)與價(jià)值,而無形遺產(chǎn)在進(jìn)入博物館后,博物館從歷史的角度將無形遺產(chǎn)建構(gòu)為一種過去的有形表征。有形表征意味著無形遺產(chǎn)的物化,這又給無形遺產(chǎn)帶來了固化與化石化的風(fēng)險(xiǎn)。
三、從“能否”的悖論到“如何”的實(shí)踐
在“博物館能否保護(hù)無形遺產(chǎn)”這個問題上持否定態(tài)度的不只有蘇東海一人。《非遺公約》通過后的幾年間,國際博物館界的許多學(xué)者就博物館保護(hù)無形遺產(chǎn)的悖論進(jìn)行了分析與闡發(fā)。2007年,無形遺產(chǎn)作為工作對象被正式納入博物館的官方定義之中。受此影響,“博物館能否保護(hù)無形遺產(chǎn)”的合法性論證逐漸消退,“博物館如何保護(hù)無形遺產(chǎn)”的實(shí)踐正式拉開帷幕。
(一)博物館保護(hù)無形遺產(chǎn)的悖論
如前所述,蘇東海雖然對“博物館能否保護(hù)無形遺產(chǎn)”這一問題的認(rèn)識存在變化,但是其最終立場是明確的,即博物館在無形遺產(chǎn)保護(hù)上是相對無力的。其中,無形遺產(chǎn)的特殊性——無形性和活態(tài)性與博物館保護(hù)無形遺產(chǎn)的前提條件——物化和博物館化之間的矛盾關(guān)系構(gòu)成了博物館保護(hù)無形遺產(chǎn)的悖論。
早在2004 年,加拿大博物館學(xué)家雷恩·梅蘭達(dá)(Lynn Maranda)便以口頭傳統(tǒng)(oral traditions)為例闡釋了保護(hù)無形遺產(chǎn)的悖論。梅蘭達(dá)指出,將口頭傳統(tǒng)記錄下來不僅意味著傳統(tǒng)文化消失與死亡的狀態(tài),而且還將改變與破壞其文化價(jià)值[27]。據(jù)此,梅蘭達(dá)總結(jié)了保護(hù)無形遺產(chǎn)的矛盾之處,即無形遺產(chǎn)就其本質(zhì)而言無法被儲存,它是流動的、有生命的,而一旦它以有形的形式被記錄和封裝,其情境關(guān)聯(lián)和文化意義的生命力就被終止了。
梅蘭達(dá)的考慮是基于無形遺產(chǎn)的博物館化而提出的,而比利時(shí)博物館學(xué)家安德烈·戈布(André Gob)則從無形遺產(chǎn)的物化角度出發(fā),表示無形遺產(chǎn)本身不能被保護(hù),人們只能以物的或物化的形式設(shè)法保留一些無形遺產(chǎn)的痕跡。更為重要的是,博物館在保留這些痕跡時(shí),理應(yīng)且必須確保對無形遺產(chǎn)的記錄不會成為固化和凍結(jié)無形遺產(chǎn)的規(guī)范性形式。令人遺憾的是,這一目標(biāo)在實(shí)踐中難以得到百分之百地實(shí)現(xiàn)。從上述觀點(diǎn)來看,博物館無法成為保存無形遺產(chǎn)的主要能動者[28]。
相比于戈布,美國人類學(xué)家理查德·庫林(Richard Kurin)的態(tài)度似乎更為悲觀。他在《博物館與無形遺產(chǎn):死去抑或存活的文化》(Museums and Intangible Heritage: Culture Dead or Alive)一文中尖銳地指出:“博物館通常是保護(hù)無形文化遺產(chǎn)的糟糕機(jī)構(gòu)——唯一的問題是,可能沒有更好的機(jī)構(gòu)來做這件事。”[29]庫林認(rèn)為,無形遺產(chǎn)的有形介質(zhì)以及相關(guān)的記錄只是一些文化碎片,而“針對這種文化碎片的行動本身并不會恢復(fù)或保護(hù)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文化”[30]。無形遺產(chǎn)是一種嵌入持續(xù)的社會關(guān)系中的活態(tài)文化,而博物館對無形遺產(chǎn)的保護(hù)往往是將無形遺產(chǎn)抽離于原初存在的語境,并將其轉(zhuǎn)化為有形的形式。究其本質(zhì),這種保護(hù)行為是對變化的一種固化[31],是將蘇東海所言的“過程存在”凍結(jié)為“終結(jié)存在”。顯然,這與無形遺產(chǎn)的活態(tài)特性相矛盾。
博物館保護(hù)無形遺產(chǎn)的悖論不僅源于無形遺產(chǎn)和博物館機(jī)構(gòu)的特殊性,而且也與將兩者連接起來的“保護(hù)模式”有脫不開的干系。
從博物館官方定義的用詞conserve 可以發(fā)現(xiàn),博物館是基于“保存模式”(preservation mode)來保護(hù)無形遺產(chǎn),這背離了《非遺公約》所倡導(dǎo)的“保護(hù)模式”(safeguarding mode)。前者指的是以有形形式記錄、保存過去的實(shí)物與知識的工作,這些工作由政府與專家主導(dǎo),帶有權(quán)威化與專業(yè)化的色彩。后者指的是“確保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生命力的各種措施”[32];強(qiáng)調(diào)“社區(qū)、群體,有時(shí)是個人的最大限度的參與”[33];重點(diǎn)“在于世代傳承或傳播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所涉及的過程而非產(chǎn)物”[34]。
由此可見,保護(hù)模式指涉了保護(hù)無形遺產(chǎn)的兩個基礎(chǔ)性要素,即不斷生產(chǎn)和再生產(chǎn)無形遺產(chǎn)的“行動者”以及作為過程的“生產(chǎn)實(shí)踐”。如果博物館堅(jiān)持基于保存模式,以有形形式記錄、展示、傳播無形遺產(chǎn)而不包含延續(xù)無形遺產(chǎn)實(shí)踐的行動,那么,博物館“在最具決定性的一點(diǎn)上將不符合UNESCO 對保護(hù)無形文化遺產(chǎn)的理解”[35]。如果博物館界對兩種保護(hù)模式及其背后的旨趣所知甚少,那么博物館保護(hù)無形遺產(chǎn)的悖論就難以揭曉。
(二)博物館保護(hù)無形遺產(chǎn)的實(shí)踐
如前所述,蘇東海面對無形遺產(chǎn)進(jìn)入博物館所引發(fā)的困難和爭論得出了博物館無力保護(hù)無形遺產(chǎn)的結(jié)論。不過蘇東海并未草率地將其視為該問題的最終答案,而是積極呼吁“當(dāng)理論貧困時(shí),還是讓我們先做起來”[36]。當(dāng)面臨理論困頓之時(shí),蘇東海具有換個視角的辯證眼光。在承認(rèn)博物館無法保護(hù)與傳播無形遺產(chǎn)的同時(shí),蘇東海巧妙地指出“博物館的優(yōu)越性遠(yuǎn)遠(yuǎn)大于它的局限性,其局限性也許在實(shí)踐中能夠找到方法來改善它”[37]。由此可見,蘇東海的無形遺產(chǎn)觀暗含著一種從“能否”的理論討論到“如何”的實(shí)踐探索的轉(zhuǎn)向,主張從實(shí)踐中尋求破局之法。
很快,蘇東海的預(yù)言就兌現(xiàn)了。當(dāng)無形遺產(chǎn)在2007 年被正式寫入博物館官方定義之后,博物館界放棄了對博物館能否保護(hù)無形遺產(chǎn)的理論追問,轉(zhuǎn)而投身到無形遺產(chǎn)的保護(hù)實(shí)踐中。在過去十幾年間,博物館在保護(hù)無形遺產(chǎn)的具體實(shí)踐中積累了豐富經(jīng)驗(yàn),有時(shí)甚至被總結(jié)為某種理念或模式。雖然這些實(shí)踐探索會因無形遺產(chǎn)項(xiàng)目、博物館類型和社會文化語境的不同而呈現(xiàn)差異性和多樣性,但是某些共通性的觀照還是有跡可循的。
為了彌補(bǔ)實(shí)物展示的不足,博物館嘗試在特定的文化空間中進(jìn)行無形遺產(chǎn)的活態(tài)表演。對于表演藝術(shù)類無形遺產(chǎn)而言,文化內(nèi)涵與其說是體現(xiàn)在有形的物質(zhì)形態(tài)中,毋寧說是經(jīng)由無形的表演實(shí)踐表達(dá)出來。其中,最常見的做法是建立特定的博物館或在博物館中開辟專屬場所進(jìn)行無形遺產(chǎn)的表演,這將與靜態(tài)展示共同構(gòu)成“動靜結(jié)合”的理念。國內(nèi)的南京博物院成立專門的非遺館,小劇場和老茶館常年表演傳統(tǒng)音樂、曲藝、戲劇等表演藝術(shù)類無形遺產(chǎn)。位于意大利巴勒莫的國際木偶博物館(International Puppet Museum)通過演出新的戲劇節(jié)目而保持木偶戲的創(chuàng)作活力。從長遠(yuǎn)來看,這種記錄、傳承與表達(dá)無形遺產(chǎn)的活態(tài)方式在某種程度上轉(zhuǎn)變成為博物館的“藏品”,為未來的保護(hù)提供了契機(jī)[38]。
為了與現(xiàn)實(shí)生活保持聯(lián)系,博物館嘗試邀請或聘請無形遺產(chǎn)的傳承人進(jìn)入博物館進(jìn)行講解、展示與表演。隨著對無形遺產(chǎn)概念理解的加深,創(chuàng)造與實(shí)踐文化表達(dá)、生產(chǎn)和使用文化物件的“人的要素”之于無形遺產(chǎn)的重要性得到凸顯。南京博物院的“大師工坊”常年有傳統(tǒng)技藝類無形遺產(chǎn)國家級傳承人駐場展示,上海土布博物館群以手工坊的方式引入無形遺產(chǎn)傳承人工作室,西安非遺博物館強(qiáng)調(diào)傳承人在互動、傳習(xí)與教育中的主體地位……相較于國內(nèi)對傳承個體的重視,國外在無形遺產(chǎn)的保護(hù)與闡釋過程中更加強(qiáng)調(diào)“實(shí)踐社區(qū)”(practising communities)的重要 作用[39]。對此,越南民族學(xué)博物館(Vietnam Museum of Ethnology)館長阮文輝(Nguyen Van Huy)指出:“博物館通過與社區(qū)的密切合作,既能夠保護(hù)瀕臨消失的文化表達(dá),也能夠復(fù)興那些對人們生活非常重要的文化實(shí)踐。”[40]
從上述實(shí)踐來看,博物館顯然已經(jīng)觸及了無形遺產(chǎn)的特殊性,并試圖通過對實(shí)踐過程和行動主體的強(qiáng)調(diào)來達(dá)到保護(hù)無形遺產(chǎn)的目的。博物館中的活態(tài)表演不僅在很大程度上規(guī)避了將無形遺產(chǎn)物化的風(fēng)險(xiǎn),而且有助于捕捉文化表達(dá)中微妙而短暫的細(xì)節(jié)之處。博物館與傳承人和實(shí)踐社區(qū)的伙伴關(guān)系一方面將博物館化的影響降至最低,另一方面也做到了以持有者的內(nèi)部眼光來保護(hù)與闡釋無形遺產(chǎn)。除了這些保護(hù)無形遺產(chǎn)的傳統(tǒng)實(shí)踐外,生態(tài)博物館的整體保護(hù)、原地保護(hù)、自我保護(hù)和動態(tài)保護(hù)的特征[41]與無形遺產(chǎn)保護(hù)中對活態(tài)、可持續(xù)性發(fā)展的要求完全契合;社區(qū)博物館則通過多元行動方共同參與和多樣化的社區(qū)實(shí)踐,兼顧了無形遺產(chǎn)的動態(tài)過程和活態(tài)存續(xù)[42]。這些新型博物館的實(shí)踐探索,因其對行動者與實(shí)踐過程的天然關(guān)注而成為無形遺產(chǎn)保護(hù)的新趨勢。
四、結(jié)語
蘇東海的無形遺產(chǎn)觀中隱含著一種從“能否保護(hù)”的理論討論到“如何保護(hù)”的實(shí)踐探索的轉(zhuǎn)向,這與現(xiàn)實(shí)世界中博物館與無形遺產(chǎn)的關(guān)系演變軌跡是一脈相承的。2007 年,博物館經(jīng)由將無形遺產(chǎn)寫入官方定義的方式解除了其被質(zhì)疑能否保護(hù)無形遺產(chǎn)的合法性危機(jī)。自此之后,博物館保護(hù)無形遺產(chǎn)的實(shí)踐在世界范圍內(nèi)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如前所述,這些嘗試與探索在一定程度上兼顧了無形遺產(chǎn)的特殊性,且在保護(hù)的操作環(huán)節(jié)竭力避免出現(xiàn)物化與博物館化的現(xiàn)象。此外,博物館保護(hù)無形遺產(chǎn)促成了兩者之間互惠關(guān)系的建立,即保護(hù)無形遺產(chǎn)的舉措在對傳統(tǒng)主流做法的挑戰(zhàn)、機(jī)構(gòu)基本功能的改變、現(xiàn)實(shí)生活的參與、與實(shí)踐社區(qū)伙伴關(guān)系的建立等方面反哺博物館。
在當(dāng)代社會,保護(hù)無形遺產(chǎn)的目的或是激發(fā)博物館介入社會的潛力,或是以文化的方式服務(wù)社會公眾,或是促成傳統(tǒng)的創(chuàng)新性轉(zhuǎn)化與再利用。在此過程中,無形遺產(chǎn)淪為一種工具,與之相應(yīng)的,以權(quán)威機(jī)構(gòu)而自居的博物館忽視了對無形遺產(chǎn)持有者的真正關(guān)切。在這種情況下,回到“博物館能否保護(hù)無形遺產(chǎn)”這一根本性問題,能夠?qū)υ摾Ь匙鞒鲈\斷并開出富有啟發(fā)的良方。
根據(jù)《實(shí)施〈保護(hù)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公約〉的業(yè)務(wù)指南》(Operational Directiv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的內(nèi)容,保護(hù)無形遺產(chǎn)的重點(diǎn)與核心是對社區(qū)、群體、個人的賦權(quán)以及對與無形遺產(chǎn)相關(guān)的持續(xù)性實(shí)踐的保護(hù)[43]。基于此,博物館等機(jī)構(gòu)在無形遺產(chǎn)保護(hù)中扮演的角色,與其說是掌控全局的“通才”,倒不如說是具有協(xié)調(diào)能力的“文化經(jīng)紀(jì)人”(cultural broker)[44]。如此這般,博物館才能跳出自身的思維定勢與機(jī)構(gòu)框架,成為遺產(chǎn)共同體中的一份子,與社區(qū)、觀眾、學(xué)校、專家等行動者產(chǎn)生積極且平等的聯(lián)系與互動,經(jīng)由轉(zhuǎn)譯、中介的功能發(fā)揮而真正達(dá)成保護(hù)無形遺產(chǎn)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