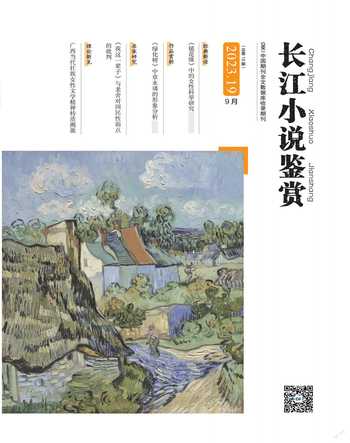《我這一輩子》與老舍對國民性弱點的批判
[摘? 要] 《我這一輩子》以一個平民的悲劇結尾,這樣的結尾與同類型主題藝術成就最高的《駱駝祥子》相比存在較大差異,即老巡警并沒有如祥子一般走向墮落。原因在于老巡警與祥子的人生觀存在差異,老巡警比祥子有著更清醒的社會認知。二者人生觀的差異既是人物性格和精神的主觀因素所致,也有環境和遭遇的客觀差異的影響。《我這一輩子》是老舍國民性批判主題成熟后的創作,老舍將歷史事件放置于小說中,以底層小人物第一人稱視角展示社會道德淪喪的橫截面,表現出國家與國民性的雙向關聯,具化了時代劇變中環境對國民性的消極影響。同時,老舍將部分底層人民的國民性弱點隱藏在日常行為的深處,揭露了數千年來某些人在天命觀和利己思維影響下“退而生存”的策略及所帶來的階級局限,這種策略給他們的生活帶來了適當的好處,卻無法從根本上改變他們的人生悲劇,這種局限是他們自身難以突破的。
[關鍵詞] 老舍? 國民性批判? 《我這一輩子》? 結尾
[中圖分類號] I106? ? ? ? [文獻標識碼] A? ? ? ? [文章編號] 2097-2881(2023)19-0064-05
老舍被譽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杰出的市民社會的表現者與批判者”[1],尤其擅長通過作品表達對城市底層人民的人道關懷,他的筆下曾多次出現底層人民不斷努力卻不斷失敗,基本生活欲求在最大限度的努力下依舊無法實現的主題,代表作有《駱駝祥子》《月牙兒》《我這一輩子》《茶館》等。其中,《駱駝祥子》是同類主題中藝術成就最高、關注度最廣的作品,《我這一輩子》卻常常被評論家忽視。《我這一輩子》是老舍于1937年發表的中篇小說,與《駱駝祥子》創作于同一時期。這兩部小說都以一個平民的生活經歷為主要描寫對象,以 “幾起幾落”為主要模式建構故事脈絡:《駱駝祥子》中的祥子以買一輛自己的車為主要目標,為此吃苦耐勞,卻一步步被無奈的現實吞噬,陷入絕望,最終走向墮落;《我這一輩子》中老巡警一輩子努力上進,改變自己,卻止不住地往下滑,最終連棺材本也買不起,只能等著餓死。這兩部小說在主題、故事發展脈絡上有很大的相似性,但是結尾卻存在較大差異:祥子最終出賣了革命者阮明,標志著他真正走向墮落,而老巡警最終卻依舊在為生活苦苦掙扎著。本文試圖以《駱駝祥子》為參照,以《我這一輩子》中老巡警的結局為主要研究對象,探討老巡警沒有墮落的原因。祥子與老巡警的悲劇結局既是社會環境所致,又有自身的局限,從中可以看到老舍對國民性問題的進一步思考。
一、老巡警的悲劇
悲劇是人與環境、時代、命運等強大力量產生矛盾沖突,歷經苦難,卻在對抗苦難中一敗涂地,肉體與精神在生命重要關頭處于悲慘境地,表現了價值的毀滅和美好的幻滅。老舍書寫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表現生活中自然出現又無可避免的“人物與環境或時代或其他人的性格的不能合拍”[2]。《我這一輩子》與“指示出一切人類努力的虛幻”[3]這一悲劇命題相關,描寫了一個小人物的具有社會普遍性的人生悲劇。
老巡警的悲劇是一出社會悲劇。小說設置了一連串的外部現實困境,迫使小人物不斷妥協,降低自己的生活理想,消解拼搏的希望與意義。“我”是一個聰明靈活的人,能讀書寫字,吃苦耐勞,卻仿佛陷入命運的怪圈不斷往下滑,物質生活條件不斷下降,最終連基本的生存需要也無法滿足:年頭變動使手藝活的工作機會減少,妻子跟人私奔,轉行巡警卻只能勉強糊口,沒有升職空間,縮衣節食攢錢供子女讀書卻無法讓子女擺脫巡警行業,被服務了20年的巡警隊開除,兒子客死他鄉,年老體衰時還要四處謀生承擔家庭的重負。被種種現實困境折磨,“我”模糊地認識到社會不公的準則:一是當官升職需要身份背景,單靠能力無用;二是貧富差距的鴻溝無法逾越,底層的貧困具有繼承性;三是城市中的人們被金錢所異化,利己的思想滲透了整個社會秩序的建構。不公的社會環境使得老巡警的個人欲求和人生理想終生無法實現。
老巡警的悲劇還是一出精神悲劇。小說通過“我”對現實困境的所見所思消解了“我”曾一直信奉的價值理念,進一步使“我”置身于內部的精神困境中。小說中曾兩度出現“空兒”這一意象,對應著“我”的精神世界的兩次重大變動。第一次“空兒”發生在學徒時期,“我”的妻子和師哥私奔以后。周圍的眼光打破了“我”的自信,使“我”重新審視自己,原本穩固的價值觀開始破裂。第二次“空兒”發生在巡警時期,“我”目睹了兵變中的群體失控。人們在高度利己的社會中已經失去基本的道德觀念,放棄作為社會一員的本分。兵變的敘事功能是推動了“我”的價值觀的崩塌,“我”既不愿被“不夠本”的人民同化,失去自己的本性,又無法重新構建價值體系,蛻變為超越自我和他人的“超人”,始終保持著小市民無法與時代、國家、社會抗爭的傳統“順民”觀念,選擇以敷衍和順應來逃避。叔本華認為,悲劇的出現與人自身的內在本性有關,“它自動產生于人的行為和性格,或者說幾乎是人的行為和性格之本質”[4],在老舍的作品中體現為國民身上潛在的國民性弱點對他們的行為和觀念的影響。從老巡警的選擇中,可以看出他依舊以樂天安命、安分守己、順從忍讓這些傳統社會的生存觀念來應對性質已經變化的社會,傳統天命說和順民理念阻礙了他向外反抗意識的生成,他所有的改良都只是“向內用力”,無法突破底層人民的局限。在與社會現存秩序的矛盾對立中,老巡警感到無望,他“被逼得進行思考,但卻發現他的思考沒有什么結果”[5],“人無法與年頭抵抗”這一觀念經過數次現實困境后在老巡警的意識中愈發根深蒂固。他在人生末尾發出“希望等我笑到末一聲,這世界就換個樣兒吧”[6]的感慨,說明其在社會變遷下放棄了人的主體性,導致他在看透社會后所有的行動都只在茍且自保,最終只能被卷入黑暗的社會中掙扎,清醒而無奈地等待死亡。
二、老巡警的人生哲學
在老舍的作品中,墮落是人格的毀滅,具體表現為人喪失基本的道德約束和反抗意識,對欲望無節制地放縱。祥子與老巡警在結局上的差異更多是他們個人精神層面的因素導致的,主要體現為人生觀上的差異。
1.以“敷衍”為核心的適應型人生態度
人生態度是人生觀的主要內容和直接反映,主要回答了“人應該怎樣活著”這一問題,具體表現在人對生活方式的選擇上。老巡警擁有與祥子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祥子處事老實、認真,最大限度地發揮自己的精力和才干。作為一個進城謀生的鄉下人,他憑借自身良好的品質,入城三年就實現了自己的目標。目標的實現使他堅信自己能夠憑借個人的勤奮努力獲得物質和精神上的滿足。但是,西直門兵變、孫偵探的威脅、虎妞的陷阱,一樁樁變故消磨著他的熱情和品質。祥子的墮落是這些變故一步一步導致的,但卷入這些變故的原因在于祥子沒能理解并適應當時的城市生活環境,依舊保留著鄉下作風。社會認知是人們對社會性世界進行意義構建的過程,社會性世界是復雜多變的,因此人們需要了解遇到的每一種情境,才能恰當地應對身處的社會性世界[7]。“在新的環境里還能保持著舊的習慣”[8]本是祥子堅持自身信念的優點,但反過來看,這也是他沒能形成新的社會認知、缺乏適應能力的真實寫照。祥子和老巡警都具有安分守己、茍且順從的性格特點,但老巡警比祥子更圓滑、靈活,對外界環境的感知也更敏銳。在《我這一輩子》中,“我”是一個懂得靈活變通的社會化個體,環境適應性極強,通過社會認知不斷改變自己。學徒生涯和兵變事件的經歷刷新了“我”對社會的印象,影響了“我”的社會認知,“我”逐漸領悟到城市最底層的生存規則:社會充斥著利己主義,社會制度、職業制度和人際關系都是圍繞著錢與權建構的。通過這一社會認知,“我”進一步產生了社會判斷。作為最底層最沒有話語權的小巡警,“我”無力違抗不合理的命令和要求,也無法改變荒誕的社會。因此,“我”形成了以敷衍為核心的生活方式,應付著本職工作,圓滑地融于社會底層群體中,避免因認真老實而招惹是非。
這種生活方式蘊含著趨利避害以求自保的深層心理動機。“我”在擔任巡警時,個體所擁有的體力、武力與所需要應對的危險不成正比。“我”害怕給自己帶來生存和生命的危險,又不能讓上級看見“我”的不作為,所以只能敷衍。“敷衍”意味著對任何事都不較真,但這并不代表“我”不努力、怕吃苦,從以下幾點可以看出。第一,學徒生涯是“我”性格和態度形成的基礎,使“我”形成了以“忍”為核心的生存價值體系,“我”為了學手藝受盡了肉體和精神上的折磨;第二,“我”剛滿20歲就成為親友中重要的全能人物,說明“我”不畏辛勞,擁有出色的個人能力;第三,曾經雇傭“我”當警衛的馮大人多次給“我”工作機會,例如任命“我”擔任他的衛隊長,向警察局說好話幫助“我”找到好差事,甚至在“我”被撤了警察職位后,還給“我”介紹工作。如果“我”差事辦不好,是不會受到馮大人的另眼相看的;第四,更重要的是,“我”目睹了社會的動亂,卻沒有像那些中下層的民眾一般四處搶劫。這些都從側面反映出“我”是一個吃苦耐勞、自立自強的人,個人的道德底線和價值選擇是毫不含糊的。“敷衍”并不是“我”的性格本質,而是“我”洞察世事后所采取的一種生存方式。
2.“笑”背后的精神超脫
情緒能表達人的心態,而心態影響著人的思維和行動。與祥子相比,老巡警擁有著更樂觀豁達的心態。《我這一輩子》以第一人稱回顧性自述的方式展開,敘述者表達的是自己在故事中的視覺和想法的回憶,而不是故事中的視覺和想法本身[9]。小說中存在著兩個“我”,一個是事件當事人“我”,另一個是回憶過往經歷的敘述者“我”。敘述者的語調是內省與詼諧并存,沒有自怨自艾,“笑”貫穿著“我”的一輩子。無論是真笑還是假笑,都表明“我”是主動地調整著對自己有益的情緒。
同樣面對生活的苦難,為什么老巡警的心態會比祥子更豁達?主要有兩方面原因。第一,“我”擁有著多樣的消遣渠道發泄因壓抑克制而積壓的心理能量,盡力保持著自己樂觀活潑的本性:從忙碌的工作中尋找樂趣,在閑暇時看報紙和閑書充實自己的精神,受到打擊后采取抽煙、喝酒、改變精神信仰的方式排解自己心中的痛苦。同時,“我”在同行中擁有很多朋友,在拿不準主意時,“我”也數次詢問他們的意見,調整自己的心情。相較之下,祥子老實而不善言辭,沒有交心的朋友,也沒有愛好和娛樂活動,毫無發泄渠道,只是在心中默默忍受著所有的痛苦,日積月累而無處發泄的壓力最終讓他的精神世界不堪重負;第二,“我”的現實困境尚在忍受范圍內,對社會和自我的認識比祥子更清醒。“我”在打拼的過程中通過對社會的觀察與思考逐漸看透了巡警行業的“騙局本質”和社會的貧富準則。因此,“我”以笑的形式維持內心的平衡,以清醒的精神信念看淡自己所遭受的苦難,實現精神上的超脫,避免了精神的墮落。而祥子卻很少關注社會動向和職業發展趨勢,在與虎妞的婚姻中,祥子失去了對自我的主導權,車夫職業引以為傲的身體和鄉下人勤奮自立的精神都受到無可挽回的重創。“我”始終為自己的聰明、靈活、活潑感到自豪,在“我”眼中,自己的美好品質是可以終身受用的,“我要打算活下去,就別丟了我的活潑勁兒”[6]。妻子私奔和轉職巡警后的數次升降,并沒有改變“我”的自我認知。因此,“我”沒有在打拼中喪失自己的品質和道德底線,例如在兵變中,哪怕人們通過搶劫發了財,“我”也沒想過要和他們為伍。而祥子過于執著于洋車,當他為買車而偷駱駝賤賣時,他的道德準則已經服從于欲望而降低,甚至他決定與虎妞結婚都受到買洋車這一目的的支配,洋車已經成為他的物質生活和靈魂的載體。洋車和虎妞先后支配著他的行為和選擇,他在這一過程中放棄了自身美好的品質。
3.生存的精神支柱與需求的實現
人生的意義在于對目標的追求和自我價值的實現。目標是人前進的動力和精神支撐,反映出一個人生存發展的根本需要。在《駱駝祥子》中,祥子的目標高度集中,即擁有一輛屬于自己的車。擁有自己的車與租車有以下兩點不同:一是擁有這一財產的所有權,免去租車的盤剝,不受雇傭者的限制,滿足人的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二是象征著高等車夫的身份,滿足人的尊重需要和自我價值需要。車成為祥子的生存權利載體。失去車并失去擁有車的希望對祥子而言就是失去生命的全部意義。而在《我這一輩子》中,“我”的目標是動態調整的,會隨著外在因素的影響而發生變化。學徒時期,“我”的目標是賺錢結婚;轉行巡警后,賺錢供子女讀書是“我”的目標;年老后,“我”失去了奮斗多年的職業,買棺材本和養活孫子成為“我”努力的動力。雖然小說中多次描述“我”渴望當官升職,但決定“我”的職業選擇、支撐“我”繼續努力的始終是家人,尤其是“我”的子孫后代,從以下幾點可以看出:第一,“我”在初入社會時曾經想要進入官場,但因受到家人影響而選擇了學手藝;第二,“我”因妻子和人私奔而決定轉行時,雖然明知當兵比當巡警更有升職發展的空間,但為了照顧兩個孩子,“我”依舊選擇了自己曾經看不起的巡警職業;第三,在從事巡警行業時,“我”為了能給子女攢錢讀書而省吃儉用,愿意為了多得兩塊錢而冒著危險馴馬,還曾考慮過放棄前途當仆人。甚至,“我”敷衍的生活方式也有保全自己照顧孩子的考量;第四,在“我”連續經歷職場上的不順和老年喪子的苦難時,“我”沒有放棄,而是繼續尋找更底層更沒發展空間的工作,因為“我”還需要養活尚在襁褓的小孫子,年幼的小孫子成為支撐著“我”繼續在底層掙扎的精神支柱。對中國人而言,“不孝有三,無后為大”,子孫后代有著特殊的生命繼承意義。即使是將婚姻視作地獄的祥子,在得知虎妞懷孕時,也曾對孩子有過希冀。因為子孫后代象征著血脈、生命的延續,能帶給人精神和自我價值上的寄托。祥子孤身一人,沒有與任何人建立生命的聯系。而“我”這一輩子雖歷經坎坷磨難,失去工作、失去兒子、失去積蓄,目標一降再降,但始終沒有失去生存的意義,孫子的存在支撐著“我”的精神世界,避免了“我”精神上的沉淪。
三、老舍的國民性批判
老舍擅長書寫平民社會,不僅因為他出身于下層旗人家庭,熟悉底層人民的生活處境,而且因為他擁有一雙知識分子的眼睛,五四運動和留洋經歷使他擁有了懷疑精神、理性精神和中國人的尊嚴。老舍曾說:“我采用悲劇形式是為加強說服力,得到更大的教育效果。”[2]他試圖通過人物的悲劇結局警醒并教育國民。在老舍的創作中,國民性是一個重要的主題,國民性弱點是構成人物悲劇的原因之一。老舍的國民性思想以國家、民族至上的觀念為核心,他將國民性分成優劣兩類。首先,他以西方現代文化中優質的部分作為參照,矯正傳統文化中的劣質,批判傳統文化中呈現出惰性、遺留在國家民族意識深處、阻礙國家現代化發展進程的性格和文化-行為模式,這種批判并不像魯迅那般尖銳,而是以溫和的諷刺呈現在作品中。然后,他又試圖回到傳統文化中,篩選出傳統國民性中的優質部分(如務實、舍生取義),使之與西方現代文明的優質部分相融合,以此改造國民性,例如他在作品中作為批判的對立面所塑造的理想國民形象趙景純、李子榮、錢默吟,具有傳統文化和現代文明的雙重特質。
老舍的國民性批判最早可以追溯至他在20世紀20年代留學英國期間的創作,如《老張的哲學》《趙子曰》《二馬》,但這一階段的批判流于表面,為笑而笑,人物扁平化,缺乏對行為背后的社會本質和民族精神進行深入思考。30年代,老舍擴大了國民性批判的社會歷史視野,將目光投射到城市平民身上,選取不同的生活側面表現部分城市底層人民的日常行為及其背后的國民劣根性。這一類型的代表作有《駱駝祥子》《月牙兒》《我這一輩子》等,這些作品覆蓋了城市最下層的人走投無路下的幾種職業,從不同的側面反映出部分底層人民身上的國民性弱點和其與黑暗社會結合所帶來的靈魂悲劇。《我這一輩子》的國民性批判與之前的作品相比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我這一輩子》將歷史事件融入人物視野中,將其與人物的精神變化交織,更直觀地揭示了辛亥革命前后的社會道德問題——自上而下又具有自利性,強調國家制度的轉變無法改變人們被自利心異化的道德觀和文化-行為準則。國家與國民之間的影響是雙向的:“國民失了人格,國便慢慢失了國格”[10],國失了國格之后,又會對身處其中的國民帶來惡劣影響;二,老舍通過人物幾起幾落的悲劇具化了國民性弱點與時代環境之間的聯系。《我這一輩子》繼承了前期創作中對敷衍、茍且順從、樂天知命的國民性弱點的批判,但采取了第一人稱回顧性自述的敘事方法,著重敘寫老巡警的敷衍、忍讓、順從是受社會環境刺激,在生活的經濟壓力下被動形成的,為這些國民性弱點的存在披上合理的外衣,盡力表現“窮人的狡猾也是正義”,同情色彩勝于批判;三,《我這一輩子》隱匿了部分底層人民的階級局限性。與祥子相比,老巡警并沒有明顯的道德缺陷,他的國民性弱點隱藏在他面對歷史事件和社會不公時的思考和處理方式上。在古人看來,自然即天,統治者是天的象征,他們習慣于將生活的不圓滿視作違反天命的結果。而天命觀又使人們缺乏“執著心”,盡人事聽天命,將除此之外的困難歸為非人力所能及。在貧窮的老巡警眼中,國家體制的改變和傳統的改朝換代沒有差異,他將社會與新的當權者視作不可違抗的天命,自然也就繼承了傳統社會普通百姓在缺乏錢與權又面臨天命不可違時的生存經驗,即逃避、妥協以保全自己的利己策略,這正體現了數千年來中國人,尤其是被朝廷官場壓制的普通百姓面對困境時的局限,即“只考慮退而生存,不考慮進而自衛”[11]。這種策略一定程度上使老巡警避免了自身的精神墮落,給他的生活帶來了一定的好處,但又無法使之從根本上改變自己的悲劇,這也是這一國民性弱點在當時的底層人民身上難以改變的原因。
參考文獻
[1] 趙園.老舍——北京市民社會的表現者與批判者[J].文學評論,1982(2).
[2] 老舍.老舍全集:第十七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
[3] 老舍.老舍文集:第十六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
[4] 叔本華.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M].石沖白,譯.楊一之,校.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
[5] 朱光潛.悲劇心理學[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
[6] 老舍.老舍全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
[7] 鐘毅平.社會心理學[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20.
[8] 老舍.老舍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
[9] 申丹.敘述學與小說文體學研究(第四版)[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
[10] 老舍.老舍全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
[11] 內山完造,等.三只眼睛看中國:日本人的評說[M].肖孟,林力,譯.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1997.
(特約編輯 張? 帆)
作者簡介:林愛鈺,廣州大學人文學院,研究方向為中國現當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