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非遺刺繡中共有紋樣符號探究
——以纏枝紋、鳥形紋與動物角紋為例
□ 廖 越 王 敏

新疆柯爾克孜族民間刺繡中的纏枝紋和花朵紋
隨著刺繡藝術的繁榮,裝飾花紋也隨之發展。新疆非遺刺繡中共有的紋樣記錄著各民族間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記憶和情感寄托,在這些刺繡紋樣豐富的工藝呈現和藝術表達中,沉淀著各民族的精神與文化內涵。如今,這些共有紋樣已逐漸從民間技藝語言轉變為表達各民族共同生產生活方式和審美經驗的中華文化符號。本文以文化符號為研究視角,選取纏枝紋、鳥形紋及動物角紋三組新疆非遺刺繡紋樣為研究對象,結合個案梳理并分析新疆非遺刺繡中共有紋樣的符號生成、意義闡釋和傳播路徑優化方式,進而探索新疆非遺刺繡對凸顯中華文化符號和形象的意義和價值,以及其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傳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等方面發揮的作用。
《辭海》對紋樣的定義是“器物上裝飾花紋的總稱。”①在人類歷史早期,原始先民的審美意識覺醒,裝飾文化活動由此展開。由此,紋樣也逐漸發展為具有表達功能的一種文化符號。習近平總書記2022 年在新疆考察時強調:“要以增強認同為目標,深入開展文化潤疆。文化認同是最深層次的認同。要端正歷史文化認知,突出中華文化特征和中華民族視覺形象。”②新疆非遺刺繡紋樣作為新疆各族人民共有的代表性文化符號,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精神標識,對非遺刺繡紋樣中中華文化符號的提煉和傳播,既有助于新疆各族人民增強文化認同,從文化自覺走向文化自信,也有助于傳承和弘揚刺繡類非遺。

新疆哈薩克族民間刺繡中的鳥形紋
一、新疆非遺刺繡共有紋樣的符號生成
符號,指某種意義代表的標識,為感知意義而存在。顧名思義,文化符號則圍繞文化意義模式而展開。刺繡類非遺作為具有標識性的中華文化符號,其符號意義層面的共有性和具體展現形式的多樣性,體現了中華民族“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多元一體思想格局。紋樣是構成刺繡的重要元素,也是其符號意義生成的關鍵。新疆非遺刺繡紋樣因其獨特的地理區位優勢和多元文化的影響在中國刺繡類非遺中別具一格,以其豐富多元的表現形式展現出各民族豐富多彩的審美趣味和文化記憶。其中,纏枝紋、動物角紋、鳥形紋是新疆各民族共有的刺繡紋樣,歷代以來在陶瓷、壁畫、服飾、建筑等圖案設計中被新疆各族人民廣泛利用,追溯這些紋樣的圖案來源、造型特征可知,它們體現了新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發展歷程。對這些共有紋樣的符號化,就是讓這些紋樣從各民族刺繡圖案語言,逐漸轉變成體現各民族共同記憶的有形、有感、有效的中華文化符號。
首先,對纏枝紋的意義溯源可知,它是新疆各族人民共有生活記憶的體現。作為中華傳統紋樣,纏枝紋既有中華民族傳統紋樣的共性,又有新疆各民族的民族特色。關于纏枝紋的起源與發展,有的學者認為纏枝紋由中國傳統云紋或動物紋演變而來,最早可追溯至戰國時期,時人多將此圖案用于漆器上③;有的則認為,受國際文化交流影響,西方裝飾元素的應用影響了中國傳統紋樣的組合,纏枝忍冬紋即是此影響下產生的紋樣之一。作為絲綢之路要塞的新疆,其纏枝紋除了汲取中華傳統紋樣中源遠流長的歷史元素,更吸收了由絲綢之路涌入的多種文化元素。比如,中亞傳入的海石榴及葡萄等地域性植物與傳統纏枝紋結合而成的纏枝石榴紋、纏枝葡萄紋等。
具體而言,新疆非遺刺繡中的纏枝紋有兩方面的表現;一是從造型特征上看,新疆非遺刺繡中的纏枝紋延續了中華傳統纏枝紋的慣有規律,以二方連續的組合形式作為刺繡圖案的花邊,圍繞牡丹、石榴、葡萄、忍冬花等纏枝主體形成渦旋形、“S”形、波浪形圖案,力求在動靜背向、翻轉仰合之間還原蔓草生長時婉轉多姿的樣態。二是從符號化過程來看,新疆非遺刺繡中纏枝紋的符號化過程,實際上是在原本特征突出、趨勢明顯的中國傳統刺繡紋樣符號化的基礎上,增添了新疆各民族標識性符號元素形成的,突出了新疆各民族文化的豐富性和因客觀地理原因所形成的獨特性。如新疆的“纏枝牡丹彩畫毯”及一些服飾上的纏枝忍冬紋、纏枝石榴紋、纏枝葡萄紋,是新疆特色植物與中華傳統卷草紋的融匯,是新疆羊毛原料和傳統技藝與中華文化吉祥符號的結合。多元融合后的纏枝紋承載著新疆各族人民對蓬勃生命力量的共同向往,體現出民族文化交融后的共同創造,各族人民共同享有中華民族纏枝紋符號,其已成為中華各民族共同認可的文化符號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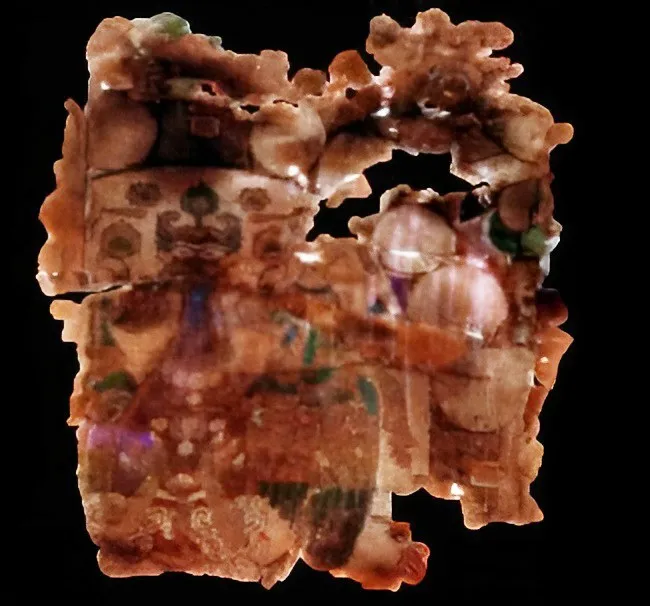
聯珠鷹紋錦⑥
其次,新疆非遺刺繡中的鳥形紋是多民族文化意義共享的成果。其所形成的符號譜系,蘊含著經由各民族在歷史長河中共創、共享的文化認知、自然崇拜及生態意識。早期,鳥形紋歷經了圖案抽象化以及題材多樣化的重要演變,日漸成為一種攜帶了特定文化認知意識的紋樣符號。商周伊始,時人常將具體實物化為抽象圖案,鳥的象形文字開始出現,裝飾圖案中也出現了鳥形紋。此時的人往往只用簡練的線條繪制鳥翼和鳥嘴,鳥翼多呈扇形,鳥嘴形狀則根據不同鳥類的生活習性表現為彎曲圓潤,或細長瘦削,如此即為鳥形紋。④后商周時期有“天命玄鳥,降而生商”⑤之說,玄鳥成為商周氏族的圖騰,用來指代商代氏族的血緣關系、身份地位。鳥形紋作為一種符號,增添了身份、權力、血緣等文化上的附屬含義,出現了典雅華美、高貴神圣的鳳鳥紋。隨著中華民族的發展,鳥形紋又衍生出了鳳紋、三足鳥紋、比翼鳥紋、鷹紋等多種樣式。
唐代,我國各民族交往互動頻繁,開放的貿易活動不僅使得鳥形紋載體更加多樣,鳥形紋的服飾、雕塑、陶瓷廣泛傳播,還使鳥形紋積聚了多民族的經驗意識,成為指涉特定文化認知的中華文化符號。例如新疆吐魯番哈拉和卓墓地出土的唐代聯珠鷹紋錦中,聯珠紋間就有展翅翱翔的雄鷹;又如同在新疆吐魯番出土的絲織物上的孔雀紋樣,其造型優雅、色彩艷美;再如在旅順博物館的藏品中,有一方自新疆出土的對鳥紋印,其上有一對玉鳥相視而立、花絮環繞;可見,被多民族藝術吸收并使用的鳥形紋符號,受到我國各民族的廣泛認同和接受,反映出華夏紋樣藝術風格的一脈相傳。在新疆,因鷹在曠野和高原中的勇猛力量和生存技能,其一度被以游牧為生產生活方式的哈薩克族、柯爾克孜族等民族視為神鳥,寓意勇敢、神圣、長壽等。經過歷史的不斷發展,飛禽在各民族不斷的想象創造中成為一種形象標識,構成了鳥形紋符號體系。新疆非遺刺繡中的鳥形紋,融匯著力量崇拜與尚武精神,展現出各民族的社會思想和文化習俗,發揮出符號指示性和象征性的文化功能,在長期的歷史流變中,共同表達出生態和諧思想所產生的自然崇拜的認知觀念,成為各民族緊密相連的精神密碼。
最后,作為民族文化標識的動物角紋,受西部特殊的地理環境與生產生活方式及其影響下的西部各民族審美價值取向影響,多以高原花草、牛羊作為紋樣的元素。游牧民族常將動物犄角視為美與力量的象征,將其繪制于服飾與器物之上。2003 年,新疆吐魯番洋海墓地出土了木器、彩陶數件,其中就有繪制動物角紋的木桶。⑦吸收傳統動物紋圖案的動物角紋,既有對稱卷曲、夸張回環、質樸古拙等傳統特征,又不乏色彩濃郁鮮艷、造型大膽獨特的民間色彩。
事實上,新疆非遺刺繡中的動物角紋不僅是游牧生活的記憶標識,還是一種精神文明的象征。新疆柯爾克孜族民間至今仍流傳著“青牛神話”:“相傳,人類生活的大地共分為七層,由一頭巨大的青牛的一只角頂著。當它這只角疲勞時,便換另一只角來頂。在換角時大地震動,就出現如今人們所說的地震。為了避免地震,防止災難降臨,民間普遍存在為勞累的青牛祈禱,祝愿它身強體壯,永不疲勞的習俗。”⑧牛角被我國新疆柯爾克孜族民眾賦予了特殊意義,他們借助牛角紋貯存早期對自然力量的想象與集體記憶,以此表達出其熱愛自然和守護家園的理念。
另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意識,在許多民間故事、神話和傳說中都有體現,這種意識可以幫助我們找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文化根源。在新疆各民族有關創生類的神話敘述中,牛、鹿等動物時常扮演著守護人類繁衍生息的神獸角色,新疆柯爾克孜族的“鹿媽媽”神話便是其中的代表。該神話講述了在柯爾克孜族人危難之際,“鹿媽媽”養育了柯爾克孜族人僅剩的兩位祖先。這些神話故事和新疆非遺刺繡中的動物角紋所代表的意義不無關聯,既體現出新疆各民族共有的崇尚自然、師法自然的理想追求,又融匯了中華民族在不同的時間、空間中統一的自我意識與身份追尋。可以說,凝聚中華民族一體觀念的動物角紋,既包含新疆各民族的文化特質,又呈現出中華文化相同的理念。
二、共有紋樣對中華文化符號的意義
中華文化符號和形象是在歷史演進中逐漸形成的各民族共有共享的文化符號。新疆非遺刺繡在各民族刺繡技藝交流學習中實現互鑒互賞,通過刺繡實踐自然而然形成的文化符號共識,有助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增強文化認同。
(一)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新疆非遺刺繡紋樣及意蘊在其傳承主體的不斷交流和學習中,逐漸生成新疆非遺刺繡共有紋樣符號。隨著社會發展,傳承主體在更廣范圍、更深層次的交往交流中,在各民族的刺繡實踐中加深了對共有紋樣符號的認知,這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傳統工藝中的體現。

新疆哈薩克族民間刺繡中的動物角紋

唐代瑞獸葡萄紋鏡⑨
一方面,在傳承本民族刺繡技藝的基礎之上,傳承人主動融匯中華各民族的紋樣特點,對中華傳統紋樣進行創造性地組合排列,推動具有新疆地域色彩的紋樣符號意義體系的形成。如新疆非遺刺繡中的纏枝葡萄紋。從西域傳入中原的葡萄,在裝飾活動主體的創作實踐中,與中華文化中的吉祥瑞獸組合出現在彩陶、石窟壁畫、唐代銅鏡等各類器物上;又如唐代的銅鏡,鏡背的花紋以瑞獸葡萄紋為主,外用纏枝紋鑲邊;再如現今新疆各民族服飾刺繡中常見的葡萄藤蔓紋樣、中華傳統紋樣中的祥云如意紋等等,都能看到文化元素的采借和自我創新。各民族藝術題材和藝術技法在此共融共通,推動各民族文化交融。
另一方面,新疆非遺刺繡紋樣還實現了審美表達和文化意蘊的共通。以新疆服飾中纏枝葡萄紋的造型觀之,葡萄圓潤飽滿、果實累累,象征著蓬勃生命力,與纏枝紋的生生不息之意交相輝映。可見,纏枝葡萄紋既包含中國傳統紋樣以“圓”為美的審美原則和文化意蘊,又寄托了中華民族對繁衍生息、綿延不絕、生活圓滿等理想的追求。纏枝紋在新疆各族民眾的創造運用中,不斷積累各民族豐富的審美意識與精神寓意,激發各民族情感上的共鳴,使其成為表征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觀念和現代文明價值觀的祥瑞符號。
總而言之,在新疆非遺刺繡中多見的纏枝紋與石榴紋、葡萄紋的組合運用中,不難發現新疆各民族所共有的對吉祥圓滿、團結互助、子孫綿延、生生不息的中華傳統文化吉祥理念的認同。新疆非遺刺繡通過紋樣創新組合所體現出的審美特點,有助于凝聚各民族的情感。這種相近紋樣間的排序組合,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體現,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情感基礎。
(二)增強中華文化自信
在各民族團結統一、精神相依的歷史和現實中,中華文化符號綜合了農耕文明的內斂含蓄、包容與共以及游牧文化的積極開放等,呈現文化復合體的特征,體現出各民族交往交流的歷史選擇和文化自覺。具備此種特征的新疆非遺刺繡紋樣,在傳承主體的實踐中,不斷拓展文化意義的共享空間,通過對共有紋樣符號所記述的故事及其主題意義的實踐傳播,增強中華文化自信。
從歷史角度看,新疆非遺刺繡的紋樣多取材于新疆民間故事、傳說與神話,力求以紋樣為媒介傳播故事中記述的集體記憶,喚起人們的情感共鳴。如新疆柯爾克孜族的民間歌謠《美麗的牧場》中記述:“過去這里是枯焦的荒原,牛羊稀少杳無人煙。荒涼干枯的山頭上,只有烏鴉野雞在游玩。如今故鄉已經變了樣,荒灘變成了肥美的牧場。看吧我們美麗的家鄉,人畜兩旺到處一片新氣象”⑩。可見,新疆柯爾克孜族人民在抵御自然災害的過程形成了對牛羊的崇拜,人們發揮想象力將口耳相傳的民間故事變成了歷史經驗,在精神上激起柯爾克孜族民眾對于自然災害的集體記憶。追溯新疆多民族的歷史傳說,均有視牛羊為神獸的記述。這些神話傳說記述著各民族的源流和共同記憶,也反映出新疆非遺刺繡紋樣符號的生成緣由。隨著時代的發展,這些紋樣符號日漸整合于中華民族適應、利用、改造自然,實現自我延續的共同記憶中。新疆非遺刺繡紋樣在描繪新疆各族人民的自然觀和生活觀的同時,以美為媒展示中華民族的文化美,推動著中華民族視覺形象的立體呈現,豐富了作為各民族共有記憶和經驗中共有主題的意義敘述維度。
三、新疆非遺刺繡中共有紋樣傳播路徑的優化方式
數字時代,隨著電視、廣播、互聯網等媒介的興起,文化符號也將在視聽媒介聯動中迎來新的發展機遇。從符號的角度來看,優化新疆非遺刺繡共有紋樣的符號傳播路徑,不僅可以推動新疆非遺刺繡的傳承和創造性轉化,還能擴大新疆非遺刺繡文化意蘊共有共享的范圍,進而推進以新疆非遺刺繡紋樣符號為媒介參與文化認同的文化實踐活動。關于新疆非遺刺繡共有紋樣的符號傳播路徑的優化,筆者總結了以下三種方式:
一是著眼于傳播物質載體的研發,推動了新疆非遺刺繡共有紋樣符號的現代性轉化。研究新疆非遺刺繡傳播載體與中華文化符號的聯通關系,從理論上拓寬新疆非遺刺繡符號傳播思路和策略,在實踐上拓展其作為中華文化符號傳播載體的應用領域,促進新疆非遺刺繡共有紋樣符號在商品社會中的傳播。
當下,新疆非遺刺繡紋樣的符號表達,需從現代人的審美需求和生活方式著手,探索承載新疆非遺刺繡紋樣文化內容的新媒介,著眼于新疆非遺刺繡衍生品的研發,在當代符號消費的大潮中,塑造突出中華文化符號的文化消費產品。新疆非遺刺繡中的共有紋樣寓意豐富,將在此基礎上創新設計的圖案應用于除刺繡、文字、影像之外的媒介,其裝飾作用與文化內涵可使文化創意產品同時實現審美價值和文化價值,進而在物質傳播間以文化建立起各民族之間的情感聯結,真正使紋飾成為有形、有感、有效的中華文化符號,同時促使其轉化為適應當下的全新設計符號,從而實現中華傳統紋飾更廣范圍的傳播。

哈薩克族刺繡作品展示
二是致力于符號展現形式的豐富,擴大新疆非遺刺繡共有紋樣符號文化共有共享的范圍。例如,展開身體可感、可享的文化互動、融合,激發大眾文化傳承意識,在文化共享中推動新疆非遺刺繡的保護與發展。隨著全球化進程的不斷推動,文化符號的傳播因科學技術縮短了交叉融合的時間,文化符號的形成增添了受眾作為客體的參與過程。具體體現為文化內涵的傳播拓寬了物質媒介和主體參與的范圍。群眾可以調動五官感知,深入感受文化符號的深層次內涵。對于新疆非遺刺繡的共有紋樣而言,建構非遺體驗園,以AR 影像展演動物角紋和鳥形紋生成文化符號的歷史故事,售賣當下流行文化與傳統刺繡紋樣結合創新設計的文創周邊等方式,既可以使古老的非遺“活”起來,也可以使傳播者與受眾全身心參與到新疆非遺刺繡傳承中,如此便能更好地宣傳多民族文化融匯的內涵。更重要的是,借此可以擴大文化符號傳播的受眾群體,他們在體驗和互動中能夠主動了解新疆非遺刺繡,聯結多民族文化心理,延續新疆非遺刺繡中共有紋樣的文化符號意義。
三是找尋紋樣符號與時代同頻共振的內涵與價值,提煉出新疆非遺刺繡紋樣體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文化符號。以新疆非遺刺繡中的纏枝石榴紋為例,石榴因“千子一房”的植物特點,其紋樣最早被用來寓意多子多孫、繁衍子嗣等。以石榴籽形象喻指各族人民團結一心、相互依存,體現出各民族同呼吸、共命運的共同體意識。如此,石榴紋與纏枝紋在各民族傳統思想觀念中,又生發出與時代號召相符合的聲音,傳遞出新時代的民族團結精神。
現今,通過當代視覺傳播手段,多種文化符號的運用創新了中華民族視覺形象的新內容。優化新疆非遺刺繡共有紋樣符號的傳播路徑,有助于凝聚各民族認同的精神符號,有利于提高中華文化的凝聚力、傳播力和影響力,進而促進非遺刺繡這項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
結語
系統思考新疆非遺刺繡如何對傳統共有紋樣符號進行傳承開發,推進中華文化符號意義的延續和深化,是借助新疆各民族非遺刺繡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任務。深入解讀新疆非遺刺繡中共有紋樣的文化符號內蘊,優化其符號傳播的路徑,有助于加深人們對各民族共有共享紋樣寓意的審美認同和情感共鳴。提取新疆非遺刺繡中共有紋樣的符號元素并將其運用于現代設計中,既是探索新疆非遺刺繡共有紋樣符號創新應用的有效路徑,又能發揮出其增進文化認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作用。
注釋:
①辭海編輯委員會《辭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79年版,第2648 頁。
②《習近平在新疆考察調研》,《人民日報》2022 年7月16 日。
③萬劍:《中國古代纏枝紋裝飾藝術史》,武漢大學出版社2019 年版,第7 頁。
④ 雷圭元:《雷圭元圖案藝術論》,上海文化出版社2016 年版,第229 頁。
⑤文學鑒賞辭典編纂中心:《詩經三百篇·下》,上海辭書出版社2020 年版,第489 頁。
⑥何星亮:《中華圖像文化史·圖騰卷》,中國攝影出版社2021 年版,第116 頁。
⑦帕麗旦木·沙丁:《新疆吐魯番洋海墓地出土的木桶》,《大眾考古》2015 年第11 期,第65 頁。
⑧何星亮:《中華文化通志·第3 典·民族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第182 頁。
⑨炭河里遺址管理處、寧鄉縣文物管理局、湖南大學:《寧鄉青銅器》,岳麓書社2014 年版,第94 頁。
⑩《中國民間歌曲集成》全國編輯委員會:《中國民間歌曲集成·新疆卷》,中國ISBN 中心1999 年版,第1238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