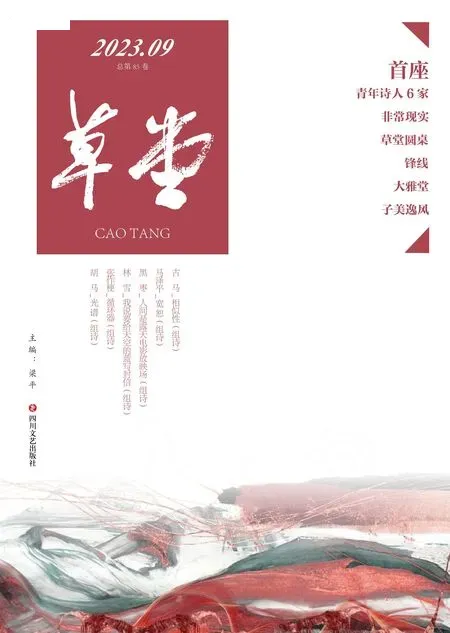如何用身體認清了秩序(組詩)
◎曹 僧
[海邊圖書館]
灣山有褶,向上,頂樓歸于海與西曬
健鴿停落窗臺,閑隔雙玻璃墜陷倦憩
憶海中的黑小丘,在沙灘上一遍遍沖浪
但不相見,或是冥冥預見于臺風之吞卷
出港的輪船,低空中歪斜的滑翔傘
種種偶得都排他于海的自知,一片空靜
每一分都在死。火的大蝸牛的爬行
悄慢,沒有端倪就靠近,就讓廳室充滿
那代代卷握,越灰燼與黑冰而來的黃金
那無數人做過,而半醒中失指啜泣的夢
翻閱臺上,大詞典像待摸的大象舒攤
這未曾說出的,是何時刻已屬于我?
[搓 繩]
當坐到松木椅子上的時候,我嘆氣,手中的櫟葉
塞進爐灶,哎,鍋底倒掛的草木灰被火焰撩動;
就像孩子的不自覺,木柵窗外的毛竹在微風中
發著無心的噪音。年輕的父親說為什么呢,為什么?
從鄉間廚房的一幕日常劇里,我們開始搓繩,
窗中略帶青苔的木條是支點,坐在灶前的換他了,
腳邊是一捆蓬松如虬菊的塑料扁絲。他粗糙的手指
捻起一根根不那么確定的小心思,它們本屬于
幾只用舊的蛇皮袋,從經緯中出走,亂了分寸;
那樣捻著,就像博斯畫里的魔術師。喜鵲在室外起哄,
苦櫧樹上有啄木鳥打鼓,總是還沒來得及看清,
這根緊繃的細股就已經變長。我在繩子的另一頭,
手上攥著鐮刀,用內彎的刀頭挑住,越退越遠,
從廚房退到院中的廊棚下:季節輪換時它也曾顫動,
和繩上頑皮的力一樣;哎,那些不知輕重的力,
有時是霰雪初降,在瓦片上噼噼啪啪,有時是暴雨
匯成水柱灌進已棄用的大缸,為孑孓建起幼年的樂園。
院子里曾經洗頭、篦虱子,晾曬為數不多的書籍;
而我站著近乎無所事事,想著,在星空下擦洗的人
是如何用身體認清了秩序,像千百年前的人那樣?
繼續向后退,就從敞開的院子來到正中的大廳,
我看不到父親了,但摸電的小秘密和無論怎樣也不能
用昏睡度盡的炎熱午后在等著;它兩側的房間
是生活用力想象的兩端,像貓和老鼠的忘情追逐,
有多投入就有多盲目。我停下,猶如發現了回南天,
從大門往回望去,繩子顫顫巍巍更像一條蛇了;
我們的老房子,我記清了那刺痛的第一縷光。
[望 江]
去奶奶家時,堵在河上
窄窄的大橋,彎成一把拉滿的弓
將我們的目光射向上游
袁河也有點窄窄的,不禁讓人
想起舟船,和緩慢的旅行
正是濕漉漉的暮春——討厭了有點
水草野長,擦拭著齊岸的船板
有人順勢入船,鞋幫上還粘著爛泥
我們的一位鄉人,不曉得名字
略有盤算,但是善良而普通
這一幕豈不親切?
又是另一天了。婚禮后的黃昏
贛江邊。水閘封控著江水
下游,有人偷偷摸摸地撒網、垂釣
夕陽為寬闊的江面涂上成熟的果色
對岸的高壓電線塔,像一根果柄
仿佛等著這岸的人將它提起
哪里還有竹篙,哪里還有馬?
世界的一切都在變,偏偏
是這清澈的水如此平靜。或許
人生代代,也都有這樣的好光映照?
映照著兩岸,映照著云天
和開始源源流入我們身軀的將來
[秘密花園]
夢里,花樹的精魂輕輕叫醒我
一陣縹緲的風,鉆過夏日的紗門
在我的失敗之外,有一座秘密花園
那里,一位淡淡的朋友枝葉扶疏
生長在天臺上,翩躚翻飛的葉片
是他談天時蝶躍的目光,的確
我們談得足夠多,又談得足夠好
瓦罐里的花也歪過頭來,為之歡悅
青苔長滿了樓梯,濕潤而又鮮活
像一些詞已經戰勝了另一些的殖民
四壁仍舊阻隔著外面,但傾頹著
土蜂從磚縫里鉆出,在空中畫圈
在導游:在我的落寞之外,有一個
陌生的我,看見草瘋長、蛙呆坐
當惡魔啟動巨大的轉盤,當鉸鏈
將壓力向下傳導而大地逐漸開裂
我有一座秘密花園,那里有藤
有花樹的精魂,有記憶切割磁感線
[后 來]
后來,我們像云一樣散盡
破爛的鞋連著腿,堆滿了郊區
被風,塵霧,和鹽,一點點侵蝕
駕著馬車的覓食幽靈,滿載
碎了一地的往事,匆匆駛過星河
輪蹄碾壓粒粒星石,發出微光與清響
也有舊時歌,隱約于四合
夜,是我們解體后化作的金屬泥
在嶙峋的荒山上,危立的高架下
夜啊親切的夜,無終亦無始地暗涌
偷渡的明月從神秘的節點升起
像一塊磁鐵,將我們的一部分悄然回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