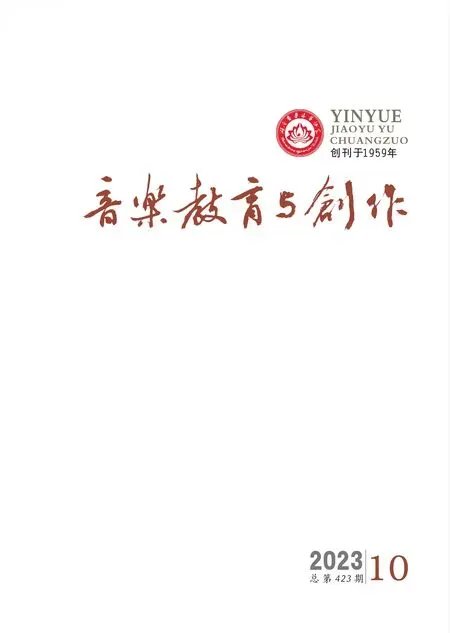黎錦暉及“明月歌舞社” 文化個案研究路徑初探
□ 彭 曉
文明是歷史積淀下的產物,人物則是構成歷史的主體。無數的史學者深信歷史是必然與偶然的結合,人物無疑成了這種結合的集中體現。對中國近現代音樂史和人物的音樂學研究,一直不絕于書。大多的研究角度采用的都是傳統的歷史研究方法,即以時間為軸線、以音樂人物和群體為主體,這些研究成果對中國近代音樂進行了歷史性的梳理。而中國近代都市音樂作為近代音樂史中的一種文化現象,必然被編纂其中。隨著研究的深入,有學者認為,近代都市音樂應該從近代音樂的大框架中摘取出來,形成專題音樂史。作為中國近代都市音樂創始人之一的黎錦暉,就是在這一歷史文化現象中不得不談的個案。
關于黎錦暉的研究,目前來看主要集中在幾個方向,其中最為集中的是采用傳統史學人物評介的手法,對其進行史學性的描述。在這類研究中大都以翔實的史料為支撐,采用傳統的歷史人物評論手法試圖還原歷史人物的藝術創作原型。此外,以時代背景為切入點,對都市音樂進行再次解讀,力求給予人物更為客觀的人文評價。然而,隨著音樂史料的不斷挖掘與翔實,如何更深入地解讀和審視已有的歷史資料已成為歷史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在解析歷史事件和人物個案的過程中,研究者開始注重歷史與文化縱橫坐標下共同構建的存在關系,從而將單邊的音樂歷史史實系統化。通過梳理,筆者認為黎錦暉及其明月歌舞社的研究契機,應是通過對空間性、歷史性和社會性進行梳理,最終構成黎式音樂的多維譜系框架。同時,也可以借鑒“質性研究”中的區域性與研究對象之間的情境關系理論,考察空間性(區域性)在構成黎式音樂譜系關系中的紐帶意義。空間觀念在研究中不再是一個單純的地理觀念,而是構成社會及文化關系的重要依據。以湖湘地域為緯度,以20世紀二三十年代為經度,以特定歷史人物和群體為研究基點,希望通過采用一種尋根式的研究方法,來探索在特定文化區域中,特定文化現象、特定人物與其賴以生存的地理環境、人文環境、經濟環境的多維關系,從而獲得更廣泛意義上的音樂文化價值。
一、 “空間性” 搭建
以音樂創作者的籍貫為基本空間性,探究在地域文化的影響下所形成的特有音樂創作思維。中國都市音樂雖然是以上海為主要發源地,但由于黎錦暉及明月歌舞社中湘籍樂人自身所帶有的文化地域特征,必然會在其音樂創作中有所體現。這種體現交織于海派文化中,形成了一種文化共生現象。
黎錦暉作為一名湘籍音樂家,其文化底色是以湖湘文化為基底的民族文化。作為生活在20世紀初的藝術家,他的藝術理念與認識首先來源于家庭的影響。黎氏家族對整個中國近代文化藝術的發展有著重要貢獻,其父兄中有8人曾對中國近代文化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歷史意義。在這種環境下成長的黎錦暉,其自身文化意識必然具有兩重性:其一為舊有的傳統文化思維;其二為“新文化”運動理念。在黎錦暉的藝術實踐中,我們不難看到這“兩重性”的相互作用。如在他的創作實踐中曾多次提到“平民化”。而“平民化”的藝術直觀體現則以作品中大量的民間音樂風格的引入為特點。顯然這種特點是與其幼年時代在湖湘一帶的生活分不開的,在這個時期他無意識地受到了大量民間音樂的熏陶。正是這種“無意識”構成了其文化思維中的慣性精神價值。當他將這種慣性精神價值與新音樂精神相結合時,則會產生出20世紀初特有的文化理念,即以民族化語匯來闡述新文化精神的音樂話語體系的理念。同時,黎錦暉的藝術實踐是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以上海為主要陣地的。“海派”文化的熏陶,從客觀上拓寬了其音樂實踐的視角。自此之后建立的歌舞人才培養學校——“中華歌舞專修學校”“明月歌舞社”,無疑皆會以其特有的藝術創作、實踐視角為底色。
因此,在對黎錦暉及其“明月歌舞社”進行個案研究時,“空間性”的體現就不可能僅限于單一的“湖湘”或者對“海派”文化的發掘。“文化共生”的影響應該成為研究的核心。通過梳理不難發現,黎式音樂實踐以及明月歌舞社湘籍樂人的藝術創作,是以湖湘文化理念為源頭的。但由于中國近代都市音樂的發源在上海,因此在“他鄉”的藝術創作者,或多或少地會受到大都市文化氛圍的影響。在20世紀20年代后都市音樂將國外歌舞音調和節奏拿來為中國都市音樂市場所用的大潮流下,讓都市音樂的通俗性、共融性為本土所接納,在黎錦暉和湘籍樂人的創作中運用了湘音湘韻及海派民族音樂語匯。
“空間性”在這里不再是單純的以音樂實踐者籍貫為基準的地域意義,它有了更為延展的內涵。通過作品、表演實踐,甚至是團體的集體意識,構成了文化內涵上的空間概念,為理解歷史時代、人物文化特質,搭建起了立體的經緯度。
二、 “歷史性” 梳理
對黎錦暉及“明月歌舞社”進行文化個案研究,從其歷史縱軸上,一定離不開對20世紀二三十年代社會歷史人物環境的理解和認識。20世紀20年代隨著我國中小學教育的迅速發展,有關“白話文”“新詩”“推廣國語”等改革的逐步深入,我國文化藝術界出現了配合這一改革的多種藝術實踐活動。黎錦暉在其兄長黎錦熙的影響之下,也熱情地投入到“白話文”的推廣中。在藝術實踐中,逐漸形成了其特有的都市文化創作風格。無論是兒童歌舞劇還是城市愛情歌曲的創作,皆反映出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都市生活的特質。通過梳理,筆者了解到從“九一八事變”和“一·二八事變”爆發之后,黎氏音樂的創作及藝術教育培訓實踐發生了較大的改變。這種改變是與歷史洪流息息相關的。黎氏音樂從創作初期就一直致力于對音樂藝術本體的改造和理解,對整個社會政治因素和歷史環境的判斷略顯不足。因此,從文化的角度上來說,他的創作確實對“平民文學”和“白話文”起到了重要的推廣作用,但在面對抗日思潮的興起時卻出現了先天的不足。
在對其進行歷史個案分析時,研究路徑的歷史性體現就必然要從兩個方面進行探究。一方面,從音樂文化本體和創新實踐,甚至是在對“新文化”運動理念的響應上來看,黎錦暉及其帶領的黎氏音樂社團的音樂實踐,無疑是符合時代的脈搏跳動的。他在20世紀20年代創辦的兒童雜志《小朋友》中,滿懷熱情地提倡新文化,普及國語拼音,喚醒國民教育,主張通過文藝作品來教育孩子形成“勇敢、勤奮、聰明、快樂、公平”的品格。而在1926年之后致力于開展歌舞藝術的實踐活動——創辦“中華歌舞專修學校”,則是從五四精神的內核出發,將平民化理念與音樂藝術實踐相結合進行具體探索。另一方面,20世紀20年代中期軍閥混戰,以上海為主的中國的主要城市陷入了軍、警、憲兵把持的特殊政治階段。作為城市音樂的主要推廣者和實踐者,黎錦暉必然會游走于社會政治浪潮中。這一時期的黎氏音樂團體,過于單純地估計了當時的政治形勢,將城市愛情歌曲轉為創作的重心。可以看出黎氏及其創作團隊的藝術實踐不論興衰、成敗,都離不開社會歷史性的影響。
三、 質性研究下的“社會性” 思考
“質性研究”中的區域性與研究對象之間的情境關系理論,表明文化事件的本質核心是人的主體性。以黎錦暉為首的明月歌舞社是中國都市音樂創作的先驅,而在這一團體中湘籍樂人成為其藝術創作的重要群體。黎錦暉與這些湘籍樂人建立了文化意義上的譜系關系,其所追求的文化理想在社團中的其他樂人身上得以延續,而這種延續最終來源于在時間性與空間性中達成的共識。通過這種“社會性”思考,可以梳理出黎錦暉及明月歌舞社湘籍樂人構成的譜系紐帶。譜系學是法國哲學家、歷史學家米歇爾·福柯和法國哲學家、符號學家、文藝理論家以及美學家、解構主義思潮創始人雅克·德里達對整個現代西方哲學進行批判時而形成的一門新的學問。關于“譜系”一詞,福柯是這樣理解的:“‘譜系’這個詞代表冷僻知識和局部記憶的結合,這種結合使我們能夠在今天建立有關斗爭的歷史知識,并策略性地運用這一知識。”本研究中正是試圖通過局部記憶的概念,針對中國近代都市音樂創作形態的知識系統展開分析。筆者認為黎錦暉和明月歌舞社,作為20世紀二三十年代都市音樂的實踐“標本”,其現象本身就具有典型性,它反映的是在特定歷史時期創作個體對整個歷史社會環境的片段化記憶和投射,也可以說是在特殊歷史時期里中國知識分子思想的多維度的表現。在黎氏音樂的表達中,愛國主義的表達是顯性的,而對生活快餐式的情感表達也是顯性的,這兩種藝術意識的輸出通過“明月歌舞社”中的其他樂人亦得到了反饋,形成了從創作理念到表演實踐的表達網格。譜系理論中提到的“片段”和“局部記憶”,為筆者了解其譜系網絡提供了研究依據。
四、 結語
在對黎錦暉及“明月歌舞社”湘籍樂人的研究中,既關注其作為“大時代”意義下音樂人的歷史意義,又認識到地域化音樂傳承者的文化意義。史學研究應跳出傳統單純地依靠羅列史料進行研究的藩籬,運用多學科相互滲透的研究方法,樹立多維的歷史觀念。黎錦暉及“明月歌舞社”湘籍樂人在空間性、歷史性和社會性的角度上建立了一種譜系關系,因此在研究此類史學個案中,師承或思想傳承應成為這種譜系關系的紐帶。將黎錦暉和都市音樂放在一個相對客觀的角度來進行思考,既認識到其社會意義的存在,又認識到其文化意義的影響。對黎錦暉及其創作的都市音樂進行研究,既要看到在特定歷史文化時期、特定意識形態下所產生的影響,又要用大歷史的眼光來檢視其客觀的歷史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