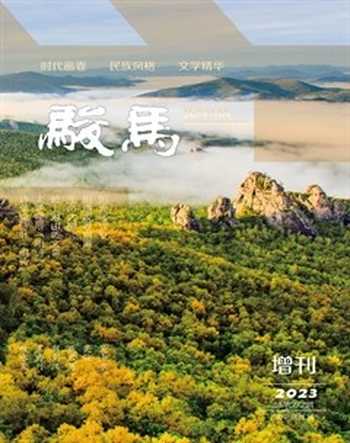相遇或者別離
吳俊
“我登機了,兩個多小時后到。”秦大亮發來訊息。
陽光透過窗子射進來,對面街道舊樓門頭上“1958”的印記,被微細雪花和枯枝遮半,“林城中心醫院”,一行字跡隱沒于時間之海,攪拌著灰塵、樹根、夢游與沉石,浮現。
這是2022年的元宵節的清晨。
“滿市今日確診4例新冠肺炎病例,軌跡如下……請14日內,來林城與其軌跡重合人員,于所在社區報備,并出示7日核酸陰性證明。”
口罩、帽子、手套、鞋套、防護服、靴套、二層手套、面屏。
污染間,推門;隔離間,推門。我裹成蠶寶寶,喘著粗氣進入清潔區。
1
此時的發熱門診,是曾經的急診所在地,樓前是一排結著松塔的墨綠色的松樹,還是二十多年前的樣子,來蘇水味蜷縮在發霉的墻角,仿佛那個黃昏的夕陽,照亮了一條街,和這靜謐又動蕩的小城。
就診人群已經從診室排到大門外,相隔一米,相隔著恐慌。空氣里帶刺的病毒粒子仿佛無處不在,每個人都高氣壓般捂緊口罩。
誰又不是呢?
這時候,一個大個子、藍眼睛、毛茸茸胳膊的俄羅斯人說道:“我下飛機是綠碼,為什么還要等兩小時后的核酸結果?”
我透過面罩上的霧氣看了他一眼,戴著橡膠手套笨拙地握著筆,做著病歷登記。住址:廣州現代汽車有限公司;目的:來我地進行冬季汽車性能測試;接著是護照數字和機票軌跡,錄入了這些信息后,我又一次查詢核酸結果,明知是徒勞,要兩個小時后才能出結果,只能是抱歉,“規定是這樣的,請您耐心等待下。”
大白隱沒了肉身,符號般執行所有的規定,空氣中的病毒刺客般閃現于世間,一切冷冰冰,帶著獻身、搏斗,另一種溫暖和赦免的味道。
“我們不能等兩個小時,有被他人傳染的風險。”娜依兀然出現,在人群中擠湊過來。
“這是規定。”煩躁的情緒再次襲來。
“國際友人講究規則與自由。”她揚起手臂,依然火焰般的熱情。娜依——突然的情景,有些不知所措,又措手不及。她的突然出現,像是這個節日,本應該是喧鬧的,卻成了沉默的焦灼……娜依、娜依,最熟悉的陌生人。
之后,事情在進展,電話的波段一截截傳出、傳入,透過我帶著橡膠味的手指,到達醫院感控部,毛發濃密的國際友人接通了院領導、市疫情指揮部,口罩下娜依的嘴貌似撇到了一邊,憤然地問道,“可以放行了吧?”我說,“我做不了主。”
這種相隔,比疫情更殘酷吧。煙花燃起的天空,不止有北方小城的寒冷,還有在元宵佳節人們的強顏歡笑。
和你,娜依,貌似無、可能有的病毒間,我看到你,你不會認出我吧,我在紙面寫出娜依,她的名字,她按下鼻根的口罩硬絲,拍了拍前胸,用纖細的手指又指了指我。
這一刻,我覺得自己真的成為一只臃腫的蠶,或是被一根針扎破的大白氣球,那么不堪,甚至呢,臉都發燙,面罩的霧氣更重了一層。
2
高中時候,和娜依、大亮,像纏繞的虬枝,根在一起,又各自指向天空不同的方向。
大亮靠在水泥乒乓球臺,不耐煩地把拍子對擊兩下,“接著,該你們了。”我和娜依就發球、接球,正拍、反拍,前推、后拉,直到汗浸得滿身濕。
黃昏的光線籠了過來,樹枝被風吹得嘩啦嘩啦響。
大亮學習出色,球又打得好,一副高高在上的樣子,有時讓我很煩感,裝什么裝,不就是球打得好點嗎?我內心的波動,枝條似的攪亂暗淡的天空,娜依也捕捉到了,她索性把球拍一扔,“不玩了。”
娜依的父親曾經是機修廠的工程師,總是一副嚴肅的神情,厚鏡片下的眼神仿佛凝固著。那時候的林城機修廠是個巨無霸,有學校、衛生院、舞廳。等我大些了,再去時大概是1995年左右,已經被荒草埋沒了大半,我走在里面還是會迷路,迷失在蜿蜒的火車軌道、磅礴的庫房鐵門和隱約的一條條年代久遠的宣傳語錄之中。
這時天色更暗了,娜依的父親靠在他的出租車旁,大口抽著劣質香煙,遠遠的像團潦倒又沉默的陰影,再沒了曾經作為工程師的榮光。
娜依轉身奔向接她的父親,留下夜和風中的我。
機修廠、荒草、工程師、出租車司機,娜依的高傲和對一切的不屑,我分明感到她生活動蕩中的某些東西,這種聯想暴露出我在低處對高處一廂情愿的消解,不懷好意的嘲諷,甚至想通過他父親身份的變化,把我同他們之間的差異解構掉,然后故作輕松地說,“沒什么的,誰又不是呢。”
明明你爸爸開出租車,回家喝一口水,或是把水杯灌滿的空當,被你媽媽堵住他跟別人睡在一個被窩。
我坐在臺階上久久不愿離開,滿腦袋都是娜依撇著嘴角的樣子。
那年秋天,雨水充沛,我家地里的大白菜長得特別壯,在幫父母賣菜時,我蹬著三輪車偷摸地給娜依家送去一車菜,我卻是那么羞愧,不是因為送菜,是什么呢?我也說不清楚。那時娜依的喜慶勁兒,她爸爸媽媽的喜慶勁兒,她家屋中電視傳來《情深深雨濛濛》的音樂聲,讓我變得慌亂,他們表現出來的是充滿陽光的,一點都不支離破碎,或是本身那些都是謠言。這樣,讓我認為的羞愧從他們身上,一下子鋪滿了我的身體,我的臉越來越紅,只顧著把菜一抱抱運到她家屋里,然后就一溜煙跑掉了。
我只能裝出愛學習的樣子,因為成績好,總有人夸獎,更多的是為比襯出娜依的糟糕。她媽總會對娜依說,“你要多向你同學看齊,才會有出息,去去,一起做做題。”
娜依又撇了撇嘴。
她家院子前面是一扇雙開的大門,后面是柴火垛夾著的逼仄的小道,有一扇小門,通向小城最繁華的地方。這時候,她父親從小道處走過來,厚厚的眼鏡片后面滿是嚴肅,進屋咕咚咚喝了幾口水,囫圇地往嘴里扒拉了半碗飯,又開他的出租車去了。
娜依的媽媽,就站在旁邊,有那么一點點神氣,有一絲不屑。多年以后,我還覺得娜依也是那樣一種神情。
我那么賣力給她講了幾乎整本書,有些筋疲力盡,娜依媽媽問她,“都會了嗎?”她微微點了下頭,蚊子般哼了聲,娜依媽媽咬著牙擠出一句,“心都被狗吃了。”
我覺得她媽媽在說我似的。
娜依媽媽一次次給我夾菜,我局促地把袖口拽緊,腳趾蜷得都快痙攣了,“多吃點啊!”我覺得她說話帶著怒氣,是對我還是對誰,我慌亂得也分不清。
“就當他們都是大白菜”,她還生著氣,“娜依,你給我聽清了,在外面大大方方的。”
我覺得她媽好像還是在說我,分明看到娜依嘴角撇了撇,一陣陣胸悶壓得我不敢呼吸。
說完娜依媽媽把白色T恤衫塞到牛仔褲腰里,捋了捋頭發,轉身說,“我出去吃飯了。”
她裹腿的牛仔褲、襯衫攏出的豐滿輪廓,讓我把頭低得更低了。
3
這一切都已遙遠,我一廂情愿地忘記,可能永遠不會再想起。
夕陽透過窗子打在桌上,密不透風的防護服還包裹著我,樓前的墨綠色松樹、樓后的茂盛榆樹都在靜默著。
旁邊的水泥乒乓球臺還是二十多年前的樣子,只是有了圍欄,前后的樓更高大更氣派了。
大亮作為省疫情督導組成員,來前給我發了訊息。
疫情形勢撲朔迷離,王華副院長一遍遍強調疫情防控的重要性。我想的是,要把我該做的做好。
發熱門診,不僅篩查風險地區外來人員的核酸情況,還負責對發熱患者的初步救治。如果發熱患者進入醫院核酸檢測結果異常,就會給整個醫院帶來傳染風險,所以發熱患者需要在這里做完核酸,持陰性結果進一步轉到專科診治。樓道的墻上掛滿了新冠肺炎處置流程,應急事件處置流程,疫情防控工作要求……
夜里十一點多,呼嘯而來的120急救車,戛然停在發熱門診前,擔架抬入一名昏迷患者。
“請出示下行程碼、健康碼,測過體溫了嗎?”伴著“刺啦刺啦”防護服的摩擦聲,我問。
“發熱,39度,”急診工作人員把患者安置在處置室,“提供核酸陰性證明,我們急診科才能收治。”
開通液路,急查CT、心電圖、抽血……
排除了低血糖昏迷、心源性、肝昏迷、肺性腦病……根據CT,初步判斷為急性腦梗。心電監護,甘露醇降低顱內壓、奧扎格雷鈉針抗凝,為下一步是否適合溶栓做準備。發熱門診是傳染病房設置,相關科室來急會診,也是需要穿防護服進入,至少半個小時,這就需要在發熱門診的醫護人員,具有一定的診治、急救的能力。做好了初步診治,再等神經內科會診,然后是兩個小時后核酸結果的反饋,才能拉送到急診或者住院部進一步治療。
大白護士大口喘著氣,癱坐在椅子上。
她在防護口罩和面屏下,深呼吸了口氣,像是一種解脫。臉上會是平靜,或者淺淺的一個微笑吧?
這一切是一種承擔,更是一種責任。
4
說起承擔,我總覺得很重很重,比如說土地里生長出的土豆、白菜、油菜還有麥子,總要為它們做很多,然后經過時間流逝,才看到它們長大、成形,成熟的樣子那么純粹,惹人愛。
可我們呢,我說過我總是羞愧于己,所以七扭八歪,畏首畏尾,疙疙瘩瘩。
娜依對于我的這些想法不置一詞,總是撇一撇嘴。
我們對于世事的看法是多么不同,可誰又不是呢?有人沉溺于大地的漆黑,一切從中生長,有人面向北方的天空,它是如此的遼闊。
那天,我們打了七局五勝,一輪過去,又是一輪,小小的乒乓球都被磨得锃亮,在夕陽下發著光,隨著一片龐大的云涌來,天色慢慢暗下。
大亮說要回去了。之后的這些年他總是這樣,按照世俗規則嚴苛要求自己,按部就班,上了名牌大學,進入體制內,一步步升職,熱愛生活,熱衷于運動,尤其是滑雪。
可娜依不愿意回去,坐在旁邊的石階上,雙臂抱膝,晚風把她的頭發揚了滿面。
我哪,我愿意一直在這里,天再晚也無所謂。回家就是干活,父母從天明到天黑,一直在干農活,種植、收割、賣掉,再種植、收割、賣掉。就像大棚里的西紅柿和黃瓜,每天我去摘下成熟的,第二天又會有一串串果實成熟,無止無終。那時想人的一生就是這無數循環的日子,永遠沒有個盡頭。
“我真不想回家,我帶你去個好玩的地方。”明知是娜依不愿回家,我之所以這樣說,是想順了她的心意。
“你還有好玩的地方,”娜依撇了下嘴,“走。”
也許那里一點也不好玩,只是一個大樹皮堆,在機修廠北門院里。
許多年前的一天夜里,父親架著馬車,我躺在鋪滿草的車廂里,被坑坑洼洼的土路顛得上上下下,忽左忽右。剛割下的青草味熏得我昏昏欲睡,天上的星星特別密,交替眨動著,幽藍的天空為底色,映襯得它們那么亮,像剛被水洗過似的。
到了門口,父親獨自走到一間鐵皮房邊,跟一個歲數挺大的人說了幾句。我還看到,父親從露著棉絮的皮襖里掏出兩條煙,他布滿泥土的手打著顫,后來彎腰點頭,拉車的紅馬咴咴噴了下鼻,脖頸的鈴鐺響了幾聲,父親向這邊看了一眼,我連忙拽緊韁繩,我仿佛看到父親眼睛里濃重的渾濁。
門口有一盞度數很低的燈泡,忽明忽暗,發出微細的咝拉聲,我覺得那晚真冷,不住地打著哆嗦,娜依抱著雙臂,也該是很冷。
父親坐在車轅上,搖動著手里的鞭子,馬車晃晃悠悠地又往里蠕動了很久,前面出現了一座濃墨般的小山,漸漸靠近,它在慢慢變大,快要把對面的天空擋住了,我低聲問,“爸,那是山嗎?”父親沉著臉不說話。
很小的時候,也是坐在馬車上,一條大路盡頭是一面墻,我迷惑地問,“爸,我們快被墻擋住了。”父親和善地笑著,“到那就過去了。”原來墻邊有一條轉彎的路,離得很遠時,看上去就是死胡同。
我們所感知和擁有的一切,都像這座山或者一道墻,有時真是幻覺,沉到底的虛無,可還是要正襟危坐、一絲不茍,板著同一個面孔往前走,那是他們給出的正確,即使盡頭是衰敗,還得全力以赴,至少看起來在全力以赴。
我和娜依并肩走在曾經的那個夜晚,她念叨著爸媽又吵架了,她媽媽總浸泡在舞廳里;她爸爸總陰沉著臉不言一語;她爸把一盆過水面條扣在地上,掀翻了桌子;她媽一把抓住他下面。娜依向我靠近了些,“真沒勁。”她撇了撇嘴,不知她在說家事的沒勁,還是說這世界真沒勁。
有沒有勁,我不知道,本來我就低到塵埃,要羞愧地面對一切。
同娜依并肩走時,世界變得很小,好像全世界就剩下沙沙的腳步聲,漆黑中掠過螢火蟲的光。
跟父親一起的夜晚,我覺得那么孤獨,父親、棗紅馬、吱吱嘎嘎響的馬車都顯得那么孤獨。天還那么冷,世界仿佛大到無邊無際,那濃墨般的山仿佛龐大到一瞬間就能把我們埋沒。
那大樹皮堆真的震驚到了我,高到看不到頭,里面冒著熱氣,四周霧氣騰騰,不走近的話,我真的不敢相信那是樹皮堆。父親把青草卸下車來,帶著我往車廂里裝樹皮,那棕紅的樹皮,肉茸茸的,它的毛刺一次次扎向我的手掌。父親往手心吐了口吐沫,用力地揮動著大板鍬。我搖搖晃晃地用尖鍬撮起樹皮,十多鍬下去就沒了力氣,坐在地上大口喘氣。霧氣彌漫得看不清周遭,滿天水洗過的星星沒了蹤影,當用青草覆蓋了滿車的樹皮,那些青草沒了本來的味道,蔫巴巴的,泛著腥味、銹鐵般腐敗的氣息。那個年代,物質是匱乏的,父親趕著馬車帶著我,偷偷來到栲膠車間,通過熟人關系,裝一車栲完膠的樹皮帶回家做取暖用的燃料。
那次經歷,愈發讓我覺得自己很渺小,龐大的樹皮堆,仿佛頃刻要坍塌,一瞬間就能埋沒掉我和變得蒼老的父親。
跟娜依進了機修廠北門,周邊拆除的平房像是埋伏在夜里的殘骸,天上的月亮遙遠、蒼白,洇出淡淡的暈。
“害怕嗎?”我低聲問道。
娜依向我靠得更近了,咯咯地笑起來,“你咋早不跟我講這些吶,那時候我爸能給你家送幾汽車樹皮。”
最終,我們也沒能看到我所給她描述的巨大的樹皮堆。濃霧般彌漫的世界盡頭,只有幾塊東倒西歪的碎石和沒到腰際的荒草叢,路途也沒有我說得那么遠,連握住的手都沒來得及溫熱。
5
醫院的疫情督導工作,讓本就緊張的疫情氛圍,更增添了一分烏云壓頂的緊迫感。
這可能是我的個人感受,上級來是督導,是查漏補缺,讓防控工作更完善,我自小的那種羞愧感,總像是要被別人揭底似的,被指認出一身的不堪。
發熱門診已經進入閉環狀態,有班上崗,沒班時在值班區休息,盡量不與外界接觸。一遍遍地考核穿脫防護服,對答規章制度,新版防治指南學習再學習,考試再考試……
大亮發來他前些年的滑雪照片,說你們鳳凰山的滑雪場全國出名,有機會要痛快玩玩。
是呀,我們有多少年沒有相見了,他的“你們”說的是我吧,我的“我們”只能是遙遠的擦肩而過,早已湮滅的記憶。有過的幾次偶爾聯系,也在聊了幾句后,變得沉默。人越來越被時間和年齡的洪流裹挾向前,直到變淡,成為陌生。疫情的年月,這種隔絕感更深。
保持社交距離,無故不要人員流動,時空相交,隔離……好似一塊塊矩陣,迫使我們凝固在有限的地方。
而娜依,她帶著國際友人與我的不期而遇,使我試圖打撈起沉睡的往事,綿薄的心總不經意疼痛幾下,可能是夜晚的緣故。也可能是窗前掛著金燦燦的月亮的緣故。在夜深處,月亮那么圓、那么低,近到一伸手就能抓住,潔凈得一塵不染,仿佛能打撈起一切,真的濕淋淋,世界再次變小,回到了從前。
分明這些又那么不確切,只能是自我杜撰出的記憶,或是洶涌而來的與她有關的痕跡,劃過一遍又一遍,才如此濃烈,把內心的漣漪打碎,泛起虛幻的浪花。
手機屏幕亮了一下,請求添加好友,接著娜依發來訊息:“真的是你,雖然你穿著防護服,我還是認出了你。”
“你真是特異功能附體,面罩的霧氣讓我看什么都不清楚。”考慮再三,我如此回道,這樣會更順暢地聊下去。
“你眼睛還是總向下看,跟以前一樣。”我看不到她說話時的神情。
“有嗎?我是防護服捂得出汗,只能那樣。”她這么說,我還是挺受用,一下近了似的。
“我也是看到你撇著的嘴角,才認出的你。”我回應道,像是回應浮起的那些記憶,又像是在做某種確認。
“別瞎扯了,我戴著口罩吶,忽悠誰呀。”
“大亮也回來了,有空聚下。”我說出來,又覺得不妥,這話似乎全無誠意。
“咱們仨有二十多年沒見了吧?”
隔了有二十多分鐘,娜依又發來訊息,“這疫情啥時候能過去?”
“會很快吧,連你們都來了……”沒等我把這條信息打完,對講機咝拉的聲音再度響起。
“有個發熱患者,進來吧。”大白護士又在召喚了,我抓緊放下手機,進入穿脫區,準備接診。
6
人生或長或短,都要經受命運之錘的敲擊,庸常日常里,或大或小的事情,不經意改變了生活的面目,人與人、物與物之間的連接,如此脆弱不堪。
1999年的冬天異常寒冷,雪下了一場又一場,日子格外地漫長,一切帶著陳舊的氣息,將要到來的千禧年,卻讓人莫名地興奮。
期盼中千禧年鐘聲響起的時候,燃放禮花的盛大景象并沒有那么熱烈,娜依撇下嘴角的樣子,我覺得那才是最酷的。“一千年怎么了!”說完,我們一起在雪地里急速奔跑,只能是娜依,才能讓世紀末日的黯淡,重新被擦亮。
已經有很久沒見過娜依了。一個大雪天,見到她攙扶著她一瘸一拐的父親,走在街對面,我向她大喊“娜依,娜依——”她也不回應,我拼命揮舞著手臂,可雪太大了,一會兒的工夫,我的臉和衣服就蓋滿了雪花,一輛車駛過,濺起的雪也要把我埋沒,看著他們父女,越走越遠,直到變成白色天地間的一個黑點。
后來我拎著一瓶山楂罐頭、一瓶黃桃罐頭去找娜依,以為是她父親雪天滑倒摔傷了腿腳。她堵在門口,“我爸出去了,可能要很久很久才回來,”她撇了下嘴,“黃桃還是挺甜的,山楂嘛,你自己拿回去吧,酸死了。”我羞愧的毛病一下又犯了,臉一下子通紅。她又說道,“我轉學了,我爸爸出國了,我媽說我會比你更有出息的。”然后笑了下,我覺得她笑得真勉強,只能回應著“是是”。娜依推上門。“千禧年就要到了。”我對著空曠的街道和緊閉的門大喊道。
千禧年就這么平淡地來了,跟平時沒有什么不同,聽說娜依的父親因為一次車禍,撞傷了右腳,不能再開他的出租車了。他的確出國了,去了俄羅斯,早年作為機修廠工程師的他俄語說得很好,不過去那里是打工,我仿佛看到他厚厚鏡片后的眼睛里也布滿了濃重的渾濁。我思忖著,算是好事吧,至少娜依會過得更好些,她爸媽不會再無休止地吵架了。
之后的幾年,娜依沒了消息,緊張的高中生活,被沒日沒夜的題海淹沒著。
偶爾跟大亮打上幾局乒乓球,也覺得沒什么意思,大亮的成績越來越好,已經沖進全校前幾名,整個人仿佛帶著光輝。我總低頭的樣子,注定面對題目都舉棋不定,只能全力以赴。我恐懼于沒有明天,害怕人生的漆黑,有時候想到娜依,她嘴角一撇,“那又有什么的”那樣的話,我才能不那么局促,短暫地擺脫于面對虛無的戰戰兢兢。
7
再一次的相見真不愿意提起,上大學后的某個寒假,我和娜依在林城的街頭不期而遇。
她漂亮了許多,帶著幾分憂郁,她說她去了北京,在那里做銷售,她要我陪她逛逛街。在我去外地上學的幾年,林城突然開始翻天覆地的變化,高樓一排排拔地而起,街道越來越寬闊,人們變得越來越時髦。這種變化,可能不僅僅是娜依的變化,而是時代變了,我卻停留在原處,在落伍于時代的地方顧自生息,對外在的一切毫無察覺。看著娜依試穿一件件很時尚的衣裝,我不覺看看自己袖口臟得發亮的棉衣,我真的感到羞愧,不只自己,我怕別人看到,我站在她旁邊,娜依也會覺得羞愧吧。
“我到門口等你吧。”我說。
“外面多冷,你看我穿這件衣服怎么樣?”她顯然沒有發覺我的想法。
“挺好,挺好。”我拽了拽我的袖口。
娜依撇了撇嘴,“我們是到這里消費的,你真是的。”
我突然一下想起娜依母親曾說過的話,“就當他們都是大白菜……”即使這樣,我也不能釋懷,多年未見,娜依還是以前那副神情,可我卻覺得那么陌生,物是人非可能就是這一種情形,可這到底是什么感覺吶,我也說不清楚。
后來我們一起吃了熱騰騰的火鍋,還有娜依一瘸一拐的父親,我們一起打了一輛車前往飯店。林城的出租車也變得興旺,都漆了綠色,顯得整齊有序,點綴在城市間,娜依父親是不是也落伍于這個時代了呢?在我糾結這些的時候,頭已經開始發暈,酒還沒喝幾口,我極力讓自己鎮定,卻醉得更快,或者不是酒的緣故。早在我們從時裝店走出時,我就頭暈起來,我覺得街道在變形、旋轉,東南西北都錯了位。
娜依說她父親剛從俄羅斯回來幾天,她媽被查出了宮頸癌,她說,“能不能再帶我去看看你說過的大樹皮堆……”娜依的臉龐變得模糊,她不會再撇嘴了吧,如果那樣就真的太過于悲傷了。
火鍋騰起的霧氣彌漫著窗玻璃,外面漆黑一片,我分明再次看到那座大樹皮堆,它就立于我們面前,我拉起娜依的手,沖出門外。
我用我的羞愧,與那龐然大物相對并且搏斗。那么多年過去,還會有更長久的日子,我要堅定地看著大地上生長著的無數好的壞的,甚至是更多的不堪。
外面聚集了好多人,一片喜氣洋洋,人們唱著、跳著,仰望著夜空。
嘩,一顆,兩顆。嘩嘩,三顆,四顆……接著整個天空下起了流星雨。
娜依也仰著臉,頭發、圍脖和身上落滿了細雪,我說,“千禧鐘聲很快就敲響了。”
她用力拍打我的肩膀,對著我耳朵大喊,“你傻了吧,這都什么年頭了。”
8
是呀,這都什么年頭了,疫情之年。
大亮發來訊息,“哥們兒,緊急任務,就要走了,都沒來得及見上一面。”
我突然覺得心一下落了底,相見不如懷念,我們不如共同應對起伏的疫情,共同祈禱病毒快些消散,輕輕松松地去陽光明媚的鳳凰山,一起滑雪,那樣的相見會更帶勁兒。
和娜依,也一樣沒有見上一面。
突然泛濫的疫情,她一直在林城冬季汽車測試場隔離,我被派往烏蘭市馳援。
相遇和別離,都這么簡單。隨著一波波疫情,每個人都偏向一隅,在各自的矩陣里艱難移動,渴望著陽光。我們曾有過的庸常生活,彼此漸漸淡忘,不再聯系。
好在,我堅信,疫情終會過去。我、大亮、娜依,我們會再見面的,一定……
責任編輯?烏尼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