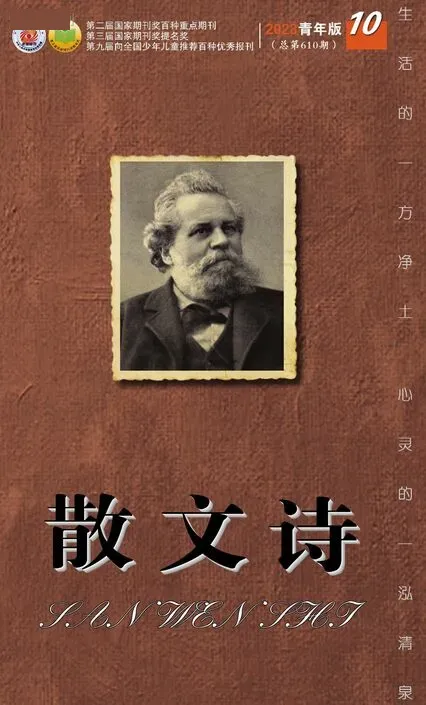從堂吉訶德到約瑟夫?K
2023-12-10 14:55:51
散文詩 2023年20期
昆德拉在《小說的藝術》 中起首就將西方現代小說視作“受到詆毀的塞萬提斯遺產”; 某種程度上, 現代性敘事正是一部關于堂吉訶德的規訓錄:“堂吉訶德從家中出來, 發現世界已變得認不出來了”, 但他或許還不曉得,唯一的真理將會分裂成無數相沖的意見, 永恒的時間將會被擊碎成分分秒秒。
如果生命被視作一種超越和征服的現象, 那么, 這一現象本身便內在地包含了一種界限——沒有界限的超越是不可能的, 超越本身必須由界限給出定位和導向。 沖突便在于此: 構成超越性的界限本身便是對超越性的否決,生命與形式相生相克。 這種沖突隱現于康德對啟蒙的思考中, 也閃爍于齊美爾對貨幣的思考和韋伯對學術的思考中, 它當然也出現在一切現代性敘事的核心之中。 在主體視閾中, 啟蒙同時是論證的對象和前提, 價值的形式化確立了貨幣這一上帝, 學術的超越性必須預設學術本身的永恒性; 至于主體本身——恰如在科學行為所示——必須被確認為曖昧不明之物。
視界的確立便是視界收縮的第一推動力, 而世界一經顯現便因視界的確立和收縮而走向了物化, 逐漸失去反思的空間; 堂吉訶德終于變成了約瑟夫?K。 問題是明顯的: 如果存在必須在時間中被規定, 那么, 存在如何才能豁免于隨時間而來的物化呢? 如果堂吉訶德注定要策馬遠游, 他要如何才能避免遭遇那只名為約瑟夫?K 的甲蟲?
猜你喜歡
紅豆(2022年9期)2022-11-04 03:14:42
紅豆(2022年9期)2022-11-04 03:14:40
紅豆(2022年3期)2022-06-28 07:03:42
南大法學(2021年3期)2021-08-13 09:22:32
阿來研究(2021年1期)2021-07-31 07:39:04
意林·全彩Color(2019年9期)2019-10-17 02:25:50
中國自行車(2018年9期)2018-10-13 06:17:10
金色年華(2016年13期)2016-02-28 01:43:27
山西大同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6期)2015-01-22 07:22:22
西南學林(2014年0期)2014-11-12 13:0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