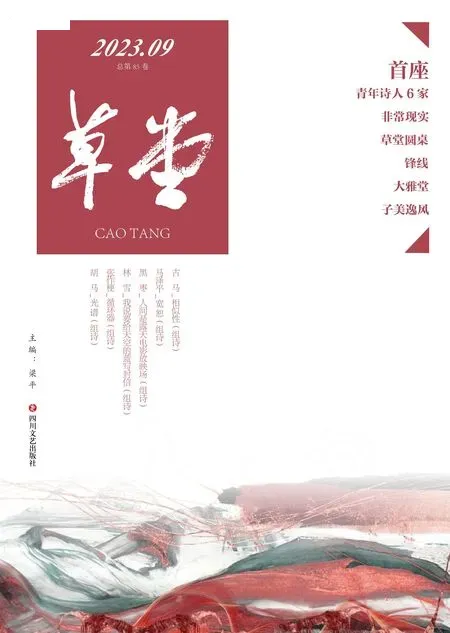詩與思的返鄉
——超越個體情感的精神追問
◎吳玉杰 鄭思佳(遼寧大學文學院)

吳玉杰

鄭思佳
德國詩人荷爾德林曾在《面包和葡萄酒》中追問:“在貧困時代里詩人何為?”而“時代之所以貧困,乃是由于它缺乏痛苦、死亡和愛情之本質的無蔽”。如今我們正處于技術時代,在人類物欲的快速繁衍中工具理性成為存在被處理和耗盡的唯一標尺,存在的一切淪為被操縱的對象和被規約的客體,失去了其原有之義。對詩人來說,技術時代最殘酷的事情是工具理性的失控驅動使語言技術化,喪失其揭示“存在”的載體和豐富的詩意,然而扭轉語言理性化趨勢的根本路徑,就是讓語言自身重新“道說”和“命名”。海德格爾認為“思者道說存在,詩人命名神圣”,“詩”有助于語言擺脫工具理性的桎梏,“思”讓語言通向“存在”的真理,“詩”與“思”的對話使人們透過語言找尋“存在之澄明”,而這種向存在汲取資源的“追尋”毋寧說是一種真正的“精神返鄉”。“存在被遮蔽”的工具理性時代,消費主義的誘惑消解著人們對終極價值的探求。詩人林雪在生活中經歷過煉獄般的折磨與洗禮后,意識到了物欲與情欲的泛濫只會讓自己遍體鱗傷,于是她與生活達成了某種和解,讓“詩”與“思”在創作中對話,去恢復時間、愛情與人生之本質的無蔽。
對時間生命的追問
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中表示“‘存在’就是時間,不是別的東西:‘時間’被稱為存在之真理的第一個名字,而這個真理乃是存在的呈現,因此也是存在本身……”在技術理性引發的貧困時代,歌唱“完滿的自然”是人類“存在的天命”,而從時間維度探尋和牽引“存在之球體”使其免于“遮蔽”,便是詩人首要的天職與使命。就像我們在林雪《給孩子們》的詩中看到的那樣:“赫圖阿拉,你的時間寫在天空之上/而我的詩句在月夜里穿過你/像一匹快馬穿過了村莊。”渴望探賾始源、“探入本己”的林雪在創作中試圖對“時間”進行詩意追問,遍布詩歌的對時光流逝和生命短暫的遺憾,以及對人生無限而生命有限的哀嘆便是她對存在本質的哲理沉思。
時光的流逝、青春的不返以及愛情的枯萎貫穿于林雪的詩歌創作,而往昔與今日的對比則是林雪詩歌“時間”主題的原型。昔日的“我”在故鄉的土院子里無憂無慮地嬉戲玩鬧,今日的“我”擠上返鄉的火車流淚張望“回不去的原鄉”(《火車》);昔日的“我”披著父親的套衫離家遠行,今日的“我”揮別青春在家中撫摸隱匿在襯衣里跌跌撞撞走過的路(《父親的套衫》);昔日的“我”與愛人“并肩躺在公園深處一個破舊的長椅上”,細數腳下的螞蟻和心中的深情,今日的“我”只能獨自一人行走在白樺林回憶那些空許的承諾(《在甜美的白樺街你愛我的日子》)。以血緣親情、炙熱愛情為肌理的幸福追憶與置身他鄉身體和靈魂漂泊境遇的今昔對比,觸發了詩人心中的憂愁,也喚醒了林雪對時間生命的追問與反思。“因為那流逝的時間/正把那水泥分解成粉末”(《小鎮》),時間摧毀事物的吞噬感和殘酷性給那些缺乏時間意識的人猛然一擊。而后,詩人又將時間的流逝與生命的消亡相連接,“深知老之將至/他衰弱,蒼白,如流水下的石塊/被磨礪。”個體消亡的必然性,讓處在物欲社會中失去意識主動性而盲目生存的人認識時間的本質,重拾生命意識,思考在被時間剝削的人生中應當如何自處。
“若非基于時間性,諸種情緒在生存狀態上所意味的東西及其‘意味’的方式,都不可能存在。”存在本身是時間性的,反過來說,林雪所強調的這些帶有時間性的情緒“標識”正是給她留下深刻記憶的帶有確證性的自我“存在”。“情緒被當作流變的體驗,這些體驗為‘靈魂狀態’的整體‘染上色彩’” 。如果說“過去”和“現在”時的時間建構使人們在自然事物的幻化中感知時間,那么“將來”時的時間想象便是生命個體深知時光無限而生命有限后的一種生存焦慮。現代社會中,工具理性的強制執行使人的價值以時間為標尺,生活的進程以時間為刻度,最后置身現代文明中的人在疲于奔命的節奏中為時間創造了權威,并在有限生命與無限時間的對話中感受壓迫,而這種時間焦慮在林雪的詩歌中以“將來”時的時間想象予以展露。如《在洛陽道街角我擁抱了你》:“還有多少年/我怕身邊會空出位置,我抱不到你/我怕自己在你身邊空著/已無擁抱你的手臂。”詩中詩人以“將來”時抽象化的形態建構時間,想象著自己垂垂老矣之后仍有許多未成心愿,于是為不留遺憾,她“停下腳步,擁抱住你”。林雪詩歌“將來”時的時間想象是一種自我意識的覺醒,是她對現代生存困境的準確認知和執著探尋。
對“過去”和“現在”的時間體驗以及“將來”的時間想象構成了林雪詩歌的時間主題,前者恢復時間之無蔽,后者觀照作為“存在”的“存在者”的現代性焦慮,而無論哪一種都是林雪通過時間維度對存在以及存在境遇的沉思。
對不完滿的愛的追問
“愛情是人類精神的一種最深沉的沖動”,而獨特的生理特征、內傾性的心理結構以及易動性的情感體驗往往使女性易于與這種沖動產生奇妙互動,因而“情愛”始終是歷代女性詩人熱衷吟詠和最擅長處理的主題。縱觀詩人林雪的詩歌,對愛的抒寫一直是她創作的“高地”。無論是初嘗愛情的懵懂、熱烈真摯的表白,還是輾轉反側的思念、甜蜜溫馨的回憶,抑或是愛情枯萎后的苦苦掙扎,都被林雪敏感捕捉又在詩歌中細膩展現。然而,當她經歷過煉獄般的情感磨煉后,女性意識的覺醒和深化使她不再囿于對愛情的纏綿悱惻,由愛情體驗引發的對愛情本質以及女性命運和生存境遇的智性思考在她的詩中漸趨顯現。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被壓抑的思想和人性,對愛的渴望與呼喚從解禁的生命中迸發。在這樣的時代語境下,舒婷、翟永明等女性詩人的主體意識在意識形態的退潮后逐步覺醒,《致橡樹》(舒婷)、《女人》組詩(翟永明)等詩歌以自覺的女性意識透視情感,以老練多樣的詩歌意象建構文本,冷靜清醒地表達對男性霸權的反抗以及對女性價值的體認,由此開啟了以彰顯女性主體意識為主題的女性愛情詩的新時代。從東洲小鎮走出來的帶著熱情與憧憬的林雪,經受過詩意時代的滋養于20 世紀80 年代將心中的愛播撒進城市的沃土。《愛的個性》中,林雪大膽地展露其對愛的呼喚:“我愛你,我就是中午熾烈的光焰/融化你,然后補充你懦弱的情感/我如果愛你,我就是艱苦的登山者/用殘損的手掌踏一路血紅的花環。”詩中一改傳統女性在愛情中的被動姿態,其對情愛虔誠般的求索以及無所顧忌的表達都是林雪主體性覺醒的深刻表現。然而,愛情之火的熄滅使林雪也經歷了一次身心的強烈震動,在漸趨自覺的女性意識的驅動下,林雪對愛情和生命有了更為深刻的思考,其詩歌也由對愛情的詩意幻想轉入對愛的理性思索和對女性命運的智性書寫。“一個女人,經過哭泣、愛情與尋找/仍然憐憫一切溫柔的事物/憐憫。是她不變的血型/她生命特質之一。”(《我能為你帶來什么》),詩中林雪細數了女人從嬰孩到老婦的生命歷程,揭示了愛是貫穿女性始終的生命屬性,她以女性視角透視女性的情感內核,以個體經驗書寫女性群體的共同記憶,詩思委婉、蘊藉深厚,表現出其對“為愛而生”的女性命運的沉思。然而在經歷過煉獄般愛情洗禮的林雪看來,“沒有一種愛是可以完成的”(《沒有一種愛是可以完成的》),“不完滿”才是世間愛情的本質和真諦。因此,她認為為愛而愛必定會使生命在愛情的重壓下枯萎,女性在咀嚼過愛情苦果后必須發出《忘掉他》的自強聲音,展現出林雪在迷惘后對新生活的向往和對女性愛情生命深層次的反思與追問。
如果說林雪愛情詩中對愛情的熱情呼喚體現了她女性意識的覺醒,那么從愛情旋渦中逃離的她在詩作中對愛情本質和女性存在的觀照,則體現了她對個體情感的自省與超越。
對苦難人生的追問
對人生的追問是詩人對人的存在的一種感知方式,而人在生存欲望與自然限制、私人話語與權力話語、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二律背反中經受的苦難與孤獨,則是詩人對人生追問的母題。經歷過生活洗禮的林雪的詩作無不體現著她對人生的感悟,靈魂與肉體的苦難、置身于虛無的孤獨成為她追問的原點,而作為詩人揭示“存在”本質的天職使命,讓她將這種個體的生命體驗上升為關于人的生存哲學的高度。
林雪的人生遍布苦難與孤獨,愛情的體驗使林雪的情感經歷了一次洗禮,隨后1992年疾病的侵蝕使苦難由靈魂深入肉體,讓她在雙重折磨的死亡邊緣掙扎盤旋。然而當她尚未完全從生活的陰影中逃離出來時,消費主義帶來的精神空虛又讓她從苦難的深淵邁向孤獨的洞穴。但是苦難與孤獨并沒有讓她失去生活的信念,在詩意的滋養下林雪的生命慢慢復蘇,而重生后的她似乎與生活達成了某種和解。她在以平和心態回憶過去的過程中發現人生就是充滿苦難的存在,而如何面對并解構苦難才是人生的關鍵。《下一首:苦難。下一首:自由》中,“生育,婚姻,勞苦,斗爭/那些孤獨和死,將會在下一首詩中讀到/在下一首里又能看到什么?/失望。下一首。苦難。下一首/遺忘。下一首。自由。自由”,林雪在詩中與充滿神性的赫圖阿拉的對話中發現,由生存欲望和瑣碎生活帶來的孤獨、痛苦和死亡無一例外會在生命中一一展現,而只要人們不放棄生活的信念,“失望”與“苦難”過后,必定會迎來理想生活的“自由”。因此,林雪呼喚“我們總要一次次愛上這世界”(《總要愛上這世界》),這種宣言式的呼喚是林雪在人生的悲劇本質被揭示后對苦難過往的釋然,也是尋求詩意人生的她重新擁抱生活的主動姿態。
在海德格爾看來,工具理性的功利擴張使存在的本質被遮蔽,人賴以生存的精神根基被抽離,人們正置身于世界黑夜之深淵。同處技術理性時代的林雪,面對人類精神文明的失落以及被“異化”和“物化”的生存狀態,將“思”注入“詩”的血脈,以個體生命經驗為載體在對時間、愛情、人生等存在的追問中聆聽存在的道說。而對澄明存在的揭示是為了能夠讓作為存在的人類更為理性、熱情地對待生活,并在詩意的建構中堅守住本真、詩性的精神家園。
(節選自《精神原鄉的詩意追尋——論林雪的詩歌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