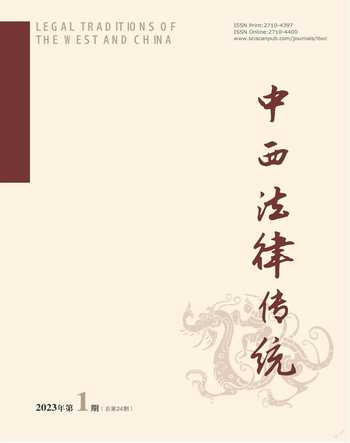史料新讀:清前期規范豪族“違禁取利”的司法實踐
摘 要|據《清代檔案史料叢編》收錄的材料,康熙三十年(1690),張恂如呈控昆山勢豪徐乾學,狀詞顯示其違禁取利。同在清前期,《紅樓夢》中的豪門賈府被查抄出了重利盤剝的借券。兩案均是豪族犯《大清律例》“違禁取利”條,司法實踐程度都較低,但細究略有不同。比較同時期的其他同類案件,更能印證司法對待豪族違律放債有著特殊傾向,至此可引發對于相關律條的法律反思。而深入探究這些條文的實踐邏輯,可知在“愛養民生”等恤民觀念下,官府超越細故對民間借貸亂象進行治理,體現出司法實踐的必要性;但同時,當清代前期君主面對諸豪族時,基于這一時期的政治需要而奉行“政貴寬平”的理念,又賦予了司法實踐以靈活性,為其特殊性處理留下了空間。
關鍵詞|違禁取利;豪族;司法實踐;大清律例
作者簡介|于艷欣,中南財經政法大學2021級法律史碩士生,研究方向:中國法制史。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清代前期,高利貸和典當取息活動極其活躍,不乏豪族之流參與其中,“京師坊市,勢豪多以私錢牟重息”[1]“京都利債,其風日長”[2]“富室大家,悍卒土豪,或開當網利,或放債盤占,吸髓吮脂,為富不仁”[3]。所謂豪族,既是家族顯赫于當政的成員,在政治活動中占有一席之地,又是門第富庶于經濟實力,累代優渥。徐乾學一門[1]、《紅樓夢》之賈府[2]皆是豪門大族。徐氏三兄弟才學出眾,簡在帝心。康熙年間,昆山民間時有“九天供賦歸東海”之謠[3],又有“京城三尺童子皆知‘萬方玉帛朝東海”的說法[4],以至于江南各縣,“具系徐府房屋田地”[5]。至于《紅樓夢》中的賈府,亦是“詩禮簪纓之族”“安富尊榮”,正所謂“賈不假,白玉為堂金作馬”。
清律有“違禁取利”律來處理錢債糾紛,徐乾學案和賈府案均涉及到“違禁取利”行為,相關材料能夠呈現出清前期司法在豪族重利放債問題上的實踐狀況。《大清律例》諸債務條款對民間借貸行為進行了規范,但其對于顯宦巨族放貸的規制效果如何,尚未出現專門的研究。因此,本文意在以這兩個案件作為研究中心,兼以分析其他類型案件,進行對比考察,從而從介入標準、實踐后果等方面梳理其中的司法實踐傾向,最終嘗試挖掘規則運行的深層邏輯,為該時期司法處理豪族違律放貸的特殊性給出解答。
一、史料新讀:兩個豪族、同種犯罪
(一)問題的提出及內涵
縱觀當前的研究成果,涉及到清代豪族違禁取利相關問題的研究并不多,且大多是對官僚放貸現象及其原因進行闡述,未作深入探究[6]。豪族不等同官僚,亦非富商大賈的代名詞。豪門大族往往世代簪纓、成員眾多,不僅具有政治上的威勢煊赫,同樣享有經濟層面的豐饒自得,因此占據了放債取利的各種優勢。清代前期豪族“違禁取利”及其司法實踐狀況的研究價值,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其一,清前期的政治、經濟形態有其特殊性,置于該具體歷史時期進行研究有利于深入理解影響清朝法律運作的各種因素。清入關以來,為使漢族士大夫誠心歸附,一方面以暴力鎮壓反清斗爭,摧毀明朝遺民的華夷觀念,一方面待到政局稍顯平穩,開始重視“文治”,轉而拉攏漢族知識分子入朝為官。同時,受戰爭、動亂及人口增長等影響,清前期民間放貸漁利之風尤熾,“違禁取利”條的運行刻不容緩。在這樣的背景下,國家司法運作很可能遭受影響。
其二,清代“違禁取利”條有著明顯的承襲性和社會必要性,以此為切入點探究法律實踐效果有利于完善對清代法律及司法實踐狀況的認識。《大清律例》參照前朝司法體制而作,經多次編修,于乾隆五年(1740)修成,這些內容是在與社會生活的對話中不斷生成的。研究“違禁取利”條的運作樣貌,不僅能夠展現清前期對于重利盤剝等社會常見違法行為的規制狀況,同時也能夠由此為基點對《大清律例》的適用性引發新的思考。
其三,豪族因自身特點而在該時期具有突出性,對這一群體的違律行為展開研究有利于通過個案分析,重點構建清前期的司法實踐模式及其基本邏輯。豪族既富且貴,毋論具有從事高利貸行業的資本,其政治影響力也不容小覷。在他們身上,影響司法運行的各種因素將會得到倍數放大。當豪族犯“違禁取利”罪,司法將如何具體實踐,是否會呈現出特殊的傾向,司法運作的背后又蘊含著何種邏輯,對這些問題的解答既能展現清前期豪族違律放貸的司法實踐狀況,豐富相關領域的研究內容,同時也將側面反映帝制時期的法律運行面貌。
(二)清代史料的再利用
《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五輯(下稱《史料叢編》)從宮中雜件選錄了康熙年間清人控告徐乾學一門的呈狀22件,其中與徐乾學違禁取利相關的有4件[1]。康熙三十年的一則“張恂如呈控徐乾學炙詐婪贓逼死父命狀”[2]記載案情最詳,是研究該時期豪族“違禁取利”的最佳樣本。《史料叢編》出版后,《歷史檔案》對該輯內容進行了簡介,指出了這些呈狀對于清代社會政治經濟研究的價值[3]。其后開始有學者對材料進行簡單利用,亦有研究者將材料結合時代背景來探尋徐氏的家族興衰[4]。學者王家范在2005年轉介了徐乾學案的主要部分,并于次年進行了史料補綴,主要就《大清律例》相關條文梳理了部分法律問題[5]。隨后,不斷有學者從社會影響、法律運作等角度對相關史料加以深入分析[6]。
《史料叢編》所載徐乾學相關案件的內容豐富,其中“張恂如呈控徐乾學案”尤為生動地展現了清代前期豪族涉嫌“違禁取利”的具體行為,這些史料均可以為研究清代社會提供大量歷史依據。總體而言,相關研究多著眼于社會、政治、經濟層面的探索,缺少對清代法律實踐效果、緣由等狀況的深入剖析。可以看到,對于清代法律制度具體運作、司法實踐狀況等方面的研究,這些內容仍具有較大的史料價值,尚待進一步挖掘。
同在清代前期,江寧織造曹寅之孫曹雪芹歷經世態炎涼,閱世頗深,于小說《紅樓夢》中生動地刻畫了賈府沒落之因,經他人續作,賈府案傳世至今。《紅樓夢》第一百零五回中,賈府因另案遭受查抄之際,被抄出了一箱重利盤剝的借券,文中司官直指這箱借券“都是違例取利的”。這亦是目前清代史料中所能見到的較為完整、直觀的豪族違律放貸案件,正好與徐乾學案構成“兩個豪族、同種犯罪”,頗具有研究價值。曹雪芹在《紅樓夢》第一回借空空道人之口,說本書“無朝代年紀可考”,從而隱去故事的年代背景。但鑒于曹雪芹歷經康雍乾三朝,曹家在雍正五年(1727)獲罪被抄沒、史料與小說內容相互印證,且《紅樓夢》成書于乾隆年間,故將相關文本置于清前期法律背景中予以解讀,最為合理。
近年來,利用《紅樓夢》文本研究法學論題的成果日漸豐碩,這些研究從清代婚姻家庭法律制度到刑法歸責理論,從法律決策機制到清代法律體系等等[1],不一而足,充分彰顯了小說的史料意義和法學研究價值。目前,對于《紅樓夢》高利貸的相關研究大多著眼于故事情節和清代社會的分析,尚沒有專門從司法實踐角度進行的論述[2]。因此,和《史料叢編》所載“張恂如呈控徐乾學案”相同,《紅樓夢》賈府“違禁取利”相關內容仍具有法學議題的討論空間。有趣的是,徐乾學同《紅樓夢》頗有淵源,他與曹家父子兩人交好,曾對雪芹祖父曹寅作《贈曹子清》,詩中有“涓埃豈云報,感恩淚盈把”一句,又在《棟亭感舊》跋詩中留下了“交分紀群殊不淺,欲題奇木思悠悠”的感嘆,紀念與雪芹曾祖曹璽之間的交情[3]。
二、徐乾學案中的“違禁取利”
(一)徐乾學案之內容
康熙二十九年(1690)五月,兩江總督傅拉塔劾徐乾學及子侄借勢招搖、競利害民,并開列了其違法詐銀、私建生祠等十四項罪行[4]。在此前后,即康熙二十九年至三十一年(1692)兩年間,徐乾學一門遭到數次法律指控。本文基于《史料叢編》所載康熙三十年的“張恂如呈控徐乾學案”呈狀及所附手札、稟帖的文本內容來探究勢豪徐乾學可能存在的違律行為。同時,由于這些材料系清宮雜件,年代久遠且相對孤立,不便驗證原告所訴事實,故不做內容真實性的考察。
“張恂如呈控徐乾學案”發生在康熙十四年(1675),時值徐乾學經歷降級歸鄉、捐復原級之際[5]。通覽呈詞可知:這一年,原告張恂如之父張希哲從太倉州學正升為山西平陽府稷山縣知縣,文憑到時因病而具文告病,意欲辭官,不久痊愈后又申文報痊,恰好昆山、太倉接壤,昆山大族徐乾學自稱可以助其順利做官,并提出為其營謀需要花費。七月初一日,徐乾學的族親逼迫張希哲立下高額借券,使其湊獻,又逼其變賣原籍田產房業。其后,徐乾學多次以手札催促張希哲償還本利,并訴說其弟徐元文在京奔走之勞。殊不知,期間張希哲已經收到京中之報,徐乾學炙詐之意昭然若揭。徐乾學屢屢遣人橫征,導致張希哲揭典變產,抱恨終天。康熙二十九年七月,徐的同鄉誆去張恂如手中的徐乾學親筆十札,張恂如憤而起訴,于康熙三十年十月訴至兩江總督傅拉塔。
(二)徐乾學案的法律分析
“張恂如呈控徐乾學案”的呈狀內容詳實,更有引用律法之語,與一般的游詞廢句相異,其中則有一段集中展現了徐乾學涉嫌觸犯“違禁取利”條的行為:
……構伊親吳升勒父逼寫借券三紙一千五百兩,從七月初一日為始,每月加五起利,又加平頭六十兩,亦按例起利勒索,連差虎仆任政、高大、張相等持札橫征,踞父任所,百般逼炙,如數湊獻。楊彩等付證。不意豪欲未滿,復又致札伊族原任山西鹽院徐諱誥武,威壓勢炙,順生逆死,逼父將原籍田房產業變賣,前后共獻紋銀叁千壹百貳拾捌兩。
這段告詞暗含了三處與《大清刑律》“違禁取利”條相違背的行為,一是在借貸主體上,突破了“不許放債于赴任之官”的國家規定,侵犯了國家利益;二是在借貸利率上,超過了“月息三分”的利率紅線,侵害了債務人的利益;三是在索債手段上,違反了律典對“豪勢以私債強奪”的明確限制,亦是極大地損害了債務人的權益。
具體而言,《大清律例》卷十四《戶律·錢債》中的“違禁取利”條規定:“凡私放錢債及典當財物,每月取利,并不得過三分”,即年利率最高為36%。上述詞狀直指徐乾學“每月加五起利”,達到了年利率60%,遠超律條限制,按律可能受到“笞四十,以余利計贓”的處罰。
同時,“違禁取利”條明令禁止放債于聽選官吏,其規定“聽選官吏,監生人等借債,與債主及保人同赴任所取償,至五十兩以上者,借者革職,債主及保人各枷號一個月發落,債追入官”。順治五年(1648)有令:“……并不許放債與赴任之官……如違,放者、借者俱治重罪”。張希哲是即將赴任之官,徐乾學向其放債,屬于該條文規定的主體情形之中。同時,在后文補詞里,張恂如訴說徐乾學在遣人勒寫借票后又多次橫征:
遣仆高大、張相二人,隨父赴任,續又遣仆任政踵至。三人出入衙署,恣行逼索,撮急借典,湊足司兌紋銀一千兩交去。未及,二使復至,又湊銀七百兩交去,……又致札于現任山西鹽院徐諱誥武號孟樞先生,系健庵通譜之弟,追父本銀二十兩,利銀一千五百兩。
照此說法,徐乾學一方顯然已滿足同赴任所取償五十兩以上的犯罪構成條件,若按律法,雙方都應當被懲以重罪,債主徐乾學應受枷號一個月發落、債追入官的處罰,至于究竟如何“發落”,并無明文。
此外,《大清律例》“違禁取利”條也對索債方式進行了限制,其中有“若豪勢之人不告官司,以私債強奪去人孳畜產業者,杖八十”之規定。本案中,徐乾學先是派遣他的虎仆任政、高大、張相等持札橫征,在張希哲的任所兩次暴力索債,而后徐乾學的族親徐誥武逼其變賣原籍田房產業,張恂如于后文中書呈:
徐鹽院立差承差曹姓者,傳父赴運城衙門。迫以上司之威命,又揭借挪移,于徐鹽院當堂交割二千零六十兩于任、高二使之手……父宰稷三年,水蘗自茹,兩袖清風,只得撮之急項,借之典鋪商家,后于原籍變賣住房田產,清償此項。以致孑身無告,徒步南歸。
徐乾學與其族親、虎仆作為“豪勢之人”,所奪價款早已超過借貸之本利,按律應當“計多余之物,坐贓論”,并“依數追還”。徐乾學等雖未直接奪去張希哲的孳畜產業,但以逼勒之勢獲得了變賣產業的價款,其惡劣程度與直接強奪相當,與出于本心、兩相和同的“準折”相區別。
除上述三處可能存在的違律行為外,呈狀所附手札及稟帖中的三處還反映了其弟徐元文欠下“旗債”的情況,一則為徐乾學的親筆手札:
向日為年翁一片熱腸,反負重累,至遘此閔兇,而猶受子母家氣。此皆旗下之債,年翁必為惻然不安者也。
另兩則為家仆高大的稟帖:
百計躊躇,托三老爺多方轉貸旗債,方得斡旋其事。
前蒙所托,家老爺一片熱腸,切囑三老爺轉貸于旗下……目下聞訃太夫人仙逝,家主奔喪在爾。債主聞知,畫(晝)夜坐索,在宅嘵嘵,必要遣人同到貴治取索。大恐旗下之使有礙鈞面,故大自認正月全楚。家老爺又多那借支持,苦不可言。
“閔兇”“畫(晝)夜坐索,在宅嘵嘵”顯示出了徐氏兄弟被追旗債的急迫情勢。同時,欠下這份“旗下之債”,于他們而言是不光彩的,家仆高大只能在無奈之下答應正月償還全部本利,并因此為由緊逼張希哲還債。《大清律例》未對旗債進行限制,只規定不得向八旗兵丁放轉子、印子長短錢,但清前期“旗下之債”在民間已靡然成風。康熙二十三年(1684),杭州旗債泛濫,民不聊生,新任浙江巡撫趙士麟到任,嘆道:“……吾蒞容小邑,民借旗債,其本不多,吾代賠……捐數百金畢矣。今杭城旗債多至三十余萬,我何以償?”[1]
三、賈府案中的“違例取利”
(一)賈府案之內容
在《紅樓夢》第一百零四至第一百零七回,賈家遭到官府查抄,王熙鳳重利放貸之事曝光。實際上小說草蛇灰線,其違禁取利的事情在寧府家宴后就開始顯露。第十一回,鳳姐從寧府回家后,問平兒家中之事,平兒遞茶并答道:
“沒有什么事,就是那三百兩銀子的利銀,旺兒嫂子送進來,我收了。”(《紅樓夢》,第十一回)
到了第十六回,賈璉帶黛玉回賈府后,又有旺兒嫂子為鳳姐送利銀的情節:
平兒道:“……奶奶瞧,旺兒嫂子越發連個算計兒也沒了。”說著,又走至鳳姐身邊,悄悄說道:“那項利銀,早不送來,晚不送來,這會子二爺在家,他偏送這個來了。幸虧我在堂屋里碰見了……”(《紅樓夢》,第十六回)
首次描寫旺兒媳婦送利銀是在十一月初二日,而這次描寫是在次年十二月,中間約間隔一年。而到了第三十九回螃蟹宴后,因襲人向平兒詢問月錢發放的事,平兒趁醉向襲人透露了其主王熙鳳暗自放賬的事情:
“這個月的月錢,我們奶奶早已支了,放給人使呢。等別處利錢收了來,湊齊了才放呢。因為是你,我才告訴你,可不許告訴一個人去!”
“何曾不是呢!他這幾年,只拿著這一項銀子翻出有幾百來了。他的公費月例又使不著,十兩八兩,零碎攢了,又放出去,單他這體己利錢,一年不到上千的銀子呢!”(《紅樓夢》,第三十九回)
旺兒媳婦在第十一回送來的是三百兩利銀,此處平兒說“一年不到上千的銀子”,可見旺兒媳婦于年底送來的利銀并非全部取利之項,從外收賬是分多次進行。平兒被鳳姐喚回去后,小廝向其告假,平兒讓他帶話給旺兒:
“就說奶奶的話,問他那剩的利錢,明日要還不交來,奶奶不要了,索性送他使罷。”(《紅樓夢》,第三十九回)
此時平兒向旺兒索要“剩的利錢”正值中秋之際,距前文兩次提到的年末之時較遠,似乎收利時間沒有定例,更加印證了鳳姐向外發放多筆借貸的事實。至第七十二回,王熙鳳向旺兒媳婦玩笑道:
“說給你男人:外頭所有的賬目,一概趕今年年底都收進來,少一個錢也不依。我的名聲不好,再放一年,都要生吃了我呢!”(《紅樓夢》,第七十二回)
這一命令隨即被旺兒媳婦委婉推辭:“若收了時,我也是一場癡心白使了”,鳳姐復道:“如今倒落了一個放賬的名兒。既這樣,我就收了回來。”這些對話意味著兩種互不排斥的可能性,其一,鳳姐放債并非短期營利,往往是留本取利,長久經營,一般不會將本利一并收回;其二,鳳姐放外債的總數目多,導致各筆貸款的放賬、收賬沒有統一時間,從而隨時有利銀可供取用。
綜上,從以上文本可以推測,王熙鳳放債多為長年借貸;借貸對象眾多,輻射各地,大多為小額借貸;收息一般為一年一收,各項利銀的收取時間不定,一部分為年底收取。鳳姐及其心腹經營多年,直到第一百零五回,錦衣府堂官趙某帶領司官查抄出一箱借券,其“違例取利”之行終于敗露:
一會子,又有一起人來攔住西平王,回說:“東跨所抄出兩箱子房地契,又一箱借票,都是違例取利的。”老趙便說:“好個重利盤剝!很該全抄!……”(《紅樓夢》,第一百零五回)
(二)賈府案的法律分析
探究文學中的法律需要與該作品的時代背景相結合,除作者曹雪芹身歷康雍乾三朝以外,用清代法律分析賈府“違例取利”、并從中考察清前期司法實踐狀況的合理性,另有三項主要例證。例證一是文本中的“違例取利”與《大清律例》之“違禁取利”條高度相似。曹雪芹為達到真事隱、假語存的目的,往往避實就虛,將法律相關的描寫進行模糊化處理,例如小說中出現了石呆子案、張華案等數個公案,但僅后四十回的薛蟠人命案展現了較為完整的司法程序。“違禁取利”之名自明代時出現,清律沿用這一叫法,《紅樓夢》雖棄“違禁取利”不用,但“違例取利”的說法明顯是由其演化而來。例證二是曹家經營當鋪,也從事取息活動。康熙五十四年(1715)七月十六日,曹頫奏報家產:“所有遺存產業,惟京中住房二所……通州典地六百畝,張家灣當鋪一所,本銀七千兩……”這僅是曹頫自覺上報的部分,至于曹家究竟有多少放貸產業,是否有違禁取利的行為,均不可知。例證三是雍正六年(1728)曹家被繼任江寧織造隋赫德抄家時,亦被查抄出了放貸取利之證。隋赫德向雍正奏道:“余則桌椅、床杌、舊衣零星等件及當票百余張外,并無別項……又家人供出外有所欠曹頫銀,連本利共計三萬二千余兩。奴才即將欠戶詢問明白,皆承應償還,”《永憲錄續編》也記載曹家被查出了千金質票。從主動上奏“本銀七千兩”到被查出“本利三萬二千余兩”,中間過去了十三年,若所奏內容皆屬實,其漁利程度可想而知。
就賈府案而言,我們無法從《紅樓夢》文本中得知王熙鳳放債的具體利率,無法看到其借貸對象、索債方式等是否合法,更不知仆人旺二等人是否會在鳳姐催促收賬之時,對借方橫加逼勒,以徐乾學案呈狀中痛斥的“豪奴”形象出現。但通過司官的“都是違例取利”“好個重利盤剝”之語,以及后文中西平和北靜二王的確證,可以知曉鳳姐極可能是違背了《大清律例》“每月取利,并不得過三分”的這條規范。僅觸犯這一項,鳳姐等人即應當按照其后規定的法定刑,承擔不低于“笞四十,以余利計贓”的法律后果。
四、徐乾學案與賈府案的司法實踐狀況
(一)徐乾學案:“從寬免其審明”及史料的印證
康熙三十年十月,張恂如向傅拉塔呈控徐乾學的違法行為,于呈狀結尾切切祈求:“泣血上呈總督江南江西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操江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傅大老爺案下施行”“躬叩憲天大老爺以申遺憾”,以求官府的審理。其在告詞中也屢屢表達了對法律的敬仰,希望得到法律庇護,如“計贓斬有余辜,難逃國法”,以及“健庵職居司寇,而行端若此,試問律例自當如何?”等語。
按呈狀所載時間推算,犯罪行為發生時徐乾學正遇降職后復職,為六品以下官員。此后他屢次擢升,在康熙二十六年(1687)遷左都御史,擢刑部尚書,升為從一品,后遭革職,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回籍編書。對于官員犯罪,《大清律例》“職官有犯”條規定應當上奏:“凡京官及在外五品以上官有犯,奏聞請旨,不許擅問。六品以下聽分巡御史、按察司并分司取問明白,議擬聞奏區處。”本案因被告的身份而在審理程序上有其特殊之處,但要追蹤案件后續處理的情況,卻實為不易。除《史料叢編》錄有該案材料外,其他史料未見分毫,無法直接知曉司法實踐的程度、具體方式等狀況。對此,只能利用相關史料從側面加以研究。
回到張恂如控告之前,康熙二十九年五月,兩江總督傅拉塔即上疏“原刑部尚書徐乾學、大學士徐元文并伊等子侄穢跡”,臚列十四項罪行,包括徐乾學二侄重利克剝貧民之事,并總結道“又復唆使爭訟,重利累民”。但面對包含了“違禁取利”的各項指控,康熙僅處理了徐家老三徐元文,而對徐乾學網開一面,下旨“所參各欵,從寬免其審明,徐元文著休致回籍。”《清史稿》亦記載“上置弗問,而予元文休致”。“從寬免其審明”雖在“張恂如呈控徐乾學案”之前出現,但案發前后,康熙帝始終對徐乾學秉承寬仁之心,該案似乎未對其造成太大影響。
從康熙二十八年回籍修書,至康熙三十三年(1694)七月卒命,徐乾學在昆山著成《憺園集》《讀禮通考》諸書,并撰寫《一統志》。皇帝時刻掛念,在徐乾學逝前還讓其去京修書。徐乾學遺疏獻書,得復故官[1]。“張恂如呈控徐乾學案”恰好出現在這期間,試想,若案件按律進行審理,徐乾學如何有安然著書之心境,康熙怎能對其寬厚如常。至此,該案的司法實踐狀況可見一斑,甚至可以推測,這些案卷材料雖被送進宮中,但被康熙棄之不理,以至于從未進入司法審理程序,最終淪落為宮中雜件。
(二)賈府案:“一概照例入官”的可能性宣告
在賈府案中,司法介入“違禁取利”事項的起因是御史參奏賈赦“交通外官,依勢凌弱”,皇帝命查抄賈赦家產,于是眾司官秉承“分頭按房,查抄登賬”,在東跨所抄出一箱“違例取利”的借票。
北靜王到后,認為應當厘清同房各爨之兄弟的家產,從而不至于禍及賈政:
“政老,方才老趙在這里的時候,番役呈稟有禁用之物并重利欠票,我們也難掩過。……獨是借券,想個什么法兒才好?今政老且帶司員實在將赦老家產呈出,也就完事;切不可再有隱匿,自干罪戾。”(《紅樓夢》,第一百零五回)
文中記載:“房地契紙,家人文書,亦俱封裹”,可見這箱借券最終被收走。至于“違例取利”之事如何處理,文中則先有“并案辦理”一說:
只聞二王問道:“所抄家資,內有借券,實系盤剝,究是誰行的?政老據實才好。”……賈璉連忙走上,跪下稟說:“這一箱文書既在奴才屋里抄出來的,敢說不知道么?只求王爺開恩。奴才叔叔并不知道的。”兩王道:“你父已經獲罪,只可并案辦理。你今認了,也是正理。如此,叫人將賈璉看守,余俱散收宅內。” (《紅樓夢》,第一百零五回)
此處賈璉見形勢不好,已經自認犯有“違例取利”罪。書至下一回,北靜王府中長史告知賈政“主上甚是憫恤,并念及貴妃溘逝未久,不忍加罪……所封家產,惟將賈赦的入官,余俱給還”,皇帝盡顯寬宥之色,獨獨囑咐查清借券。于是,對于如何處理“違例取利”,便又有“王爺查核”一說:
“惟抄出借券,令我們王爺查核。如有違禁重利的,一概照例入官;其在定例生息的,同房地文書,盡行給還。”(《紅樓夢》,第一百零六回)
前文中趙堂官、二王均稱這筆借券為重利欠票,甚至直接指其為“違例取利”,而到此處,皇帝卻讓北靜王查核是否為違禁重利,并宣告了“一概照例入官”的處理可能性。而無論是“并案辦理”,還是“王爺查核”,后文再無對后續處理結果的交代,但可以知曉四個事實,其一,借券入官后再沒有歸還;其二,賈赦、賈珍獲罪是因為石呆子古扇案和尤三姐自刎案,并未受到重利借券的影響;其三,“違例取利”的主謀王熙鳳、以及在二王面前承認“違例取利”的賈璉,均未受法律處罰;其四,賈府案后不久,賈政承襲榮國公世職。可見,對該“違例取利”案件的司法實踐程度之低、后果之輕極有可能歸結于皇帝的寬仁。
五、司法實踐傾向以及刑律條文的法律反思
(一)類型案件所見司法實踐傾向
徐乾學案和賈府案不約而同地展現出了司法對于豪族“違禁取利”行為的讓行態勢,司法實踐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阻礙。不同的是,前者是原告呼吁司法介入而未能如愿,后者則是官方力量在法律活動中直接發現違法行為,司法不得不短暫性地參與。總的來說,后者比前者司法實踐的程度略深,較多地反映出了律條的運作情況。
徐氏一族在明代就已起家,清初時昆山三徐先后歸附,成為清廷新貴,光焰甚熾;賈府一門亦發跡于清初,賈家祖上為披甲包衣,因戰功而顯赫,其后世代簪纓。小說第七回尤氏評價仆人焦大:“因他從小兒跟著太爺出過三四回兵,從死人堆里把太爺背出來了,才得了命……不過仗著這些功勞情分。”就作者曹雪芹的家族而言,明末曹家降為滿洲包衣,清初時因軍功而顯貴,世代為滿洲正白旗,與《紅樓夢》賈府的境況明白對應。因此可以說徐乾學與曹璽、曹寅相交跨越了身份,也是漢官與旗人之交,而徐案與賈府案司法實踐程度的細微差別亦顯示了清廷對于滿漢官員犯罪的不同處理。
與賈府案比較而言,徐乾學顯然受到了更多的優待。他置于“違禁取利”的控告而自如脫身,早有先例。康熙二十八年,副都御史許三禮復劾徐乾學曰:
“徐乾學發本銀十萬兩,交鹽商項景元于揚州貿易,每月三分起利。本年七月間著伊孫媳史姓家人李(湘)[相]押同景元于八月二十四日到京算賬,共結算本利[一]十六萬兩。又布商(程)[陳]天石新領乾學本銀十萬兩,在大蔣家胡同開張當鋪,契約銀號錢桌發本放債,違禁取利,怨聲載道。”
面對許三禮去而復返,康熙不追究徐乾學的罪過,反而質疑許三禮參劾有私心:“前參乾學疏內,何以不一并指出”。許有禮兩次彈劾徐乾學,未傷其分毫。
跳脫出這兩個案件,清前期“違禁取利”諸條自然也有運行之處,例如乾隆年間,武舉戴麟瑞之父戴于和向土目安起鰲放債五百兩,約定年息為米七十五石,22年來戴麟瑞屢次準折安起鰲的田土產業,安忍無可忍,赴州呈控:
經署州于良鈞差提審訊:核計安氏僅欠戴麟瑞本銀四百一十兩,前后收過息米一千四百十石,照依該地時價,約計值銀三千三四百兩,利過于本數倍。斷令安氏止還本銀,田歸安氏管業,舊欠息米免其追償。
但戴麟瑞因不服審斷、咆哮公堂,最終照“棍徒擾害”例被擬判改發極邊足四千里,折責安置,而對于其放債取利事項,則被判為:
安氏所欠戴麟瑞本銀四百一十兩追繳給領,其四十年、四十一年拖欠息米六十四石五斗,利過于本,免其追繳,田產仍歸安氏管業。
以上案件中,武舉戴麟瑞取利過本、強行索債,明顯觸犯了“違禁取利”條款,但官府用律過慎,且因他罪更惡,錢債條文未能完全施展。從止還本銀、原主管業、舊利免償的處理結果上可以看到,該判決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債務人的利益,發揮了律條處理錢債糾紛的作用。再如康熙五十六年(1717)二月,大學士馬齊、學士蔡升元等以折本請旨之事:
覆請刑部匯題案內,以九錢作一兩放債,驍騎校諾木圖議革職,枷號兩月,鞭一百一事……上曰:此內諾木圖、傅云其情可惡,枷號鞭責完日,發往三姓處當差行走。
八旗驍騎校諾木圖顯然是觸犯了“違禁取利”條款中的“違禁向八旗官兵放轉子、印子長短錢”條,其內容為“佐領、驍騎校、領催等,有在本佐領、或弟兄佐領下,指扣兵丁錢糧、放印子銀者,系佐領、驍騎校照流三千里之例,枷號六十日。系領催照近邊充軍例,枷號七十五日。倶鞭一百。”諾木圖因“以九錢作一兩放債”而遭革職,被判枷號兩月,鞭一百,并流放至三姓處,基本符合了律文的相關規定。司法在此案中得到了充分的運作,幾乎沒有遇到任何阻礙因素,康熙知曉后也未展現寬仁之態,直指“其情可惡”。
通覽以上案例可知,對于“違禁取利”犯罪,清前期司法并非始終正常運作,具體而言,當政者對待豪族較之普通官吏、舉人更加寬松,而在豪族之中,對待漢人較之八旗更加寬松。這種司法實踐的寬松狀態具體體現為司法介入的標準更高、實踐程度更低、參與方式更加柔和以及法律后果更輕。
(二)“違禁取利”條的法律反思
戶婚、田土、錢債等事項均屬“細故”之事,當民間發生細故糾紛,若要引起官府的重視,往往會夸大詞狀,進行情感性的煽動。有學者認為,在這些道德宣泄的背后正是法律意識的體現,是人們對自我權利的捍衛。在這一認識下,清代的“違禁取利”條超越細故,對民間細事進行管理,便具有從國家層面保護借貸雙方權利的意味。官方認為放債典當有其必要性和必然性,可以“通緩急之用,取利之中,有相濟之義”,同時也認識到“然必有乘人之急,而罔利無度者,亦必有遲欠違約,負賴不還者,故立此禁限也”。這些是“違禁取利”條存在于國家律法中的基本邏輯,其出發點是處理借貸亂象,保護借貸雙方的利益。
債務條文既是以保護當事人權益、平復民間糾紛而立足,若增以單純的懲治性內容,則會使得對國家利益的強烈保護需求改變原本的立法精神,從而擾亂基本邏輯。正如《大清律例》對“監臨官吏放債于所部民人”“放債于聽選官吏、監生人”等進行了限制,若一方違禁取利,國家并不會保護另一方的利益。一方面,條文中不再有余利還債務人、追本利給債權人的內容,可能僅是規定了“但犯即杖八十”“債追入官”等懲罰性條款;另一方面,債務雙方甚至可能會一起受到處罰。換言之,不能單純地將“違禁取利”條視為官方對于細故之事的治理手段,其中已傾注了國家對肅清吏治、維護統治的訴求,其內涵已遠遠超越了細故。上述徐乾學案、賈府案等均能體現這一點。
最后的法律反思是關于“違禁取利”條的適用性。條文第一句即規定“凡私放錢債及典當財物,每月取利,并不得過三分。年月雖多,不過一本一利”,但凡民間借貸,均謂之私債,條文沒有從本金數額等方面進行限制,霎時將無數借貸細故之事納入司法考察范疇之中。在高利貸盛行的清代前期,民間違法行為勢必不可勝數。而其后規定“違者,笞四十。以余利計贓重者,坐贓論。罪止杖一百”,設定的違法門檻低而法律后果相對較重,很可能影響司法實踐的運行。清承明律,大多“違禁取利”條文的法定刑都規定為笞刑和杖刑,監臨官吏犯律亦杖八十。但這樣的規定在清代前期明顯缺乏適用性,或許在大多情況下只能流于形式。清入關后待到局勢穩定,便開始奉行休養生息之策,屢次免稅,并籠絡明朝學者為官,以示仁政。若官員的“違禁取利”罪行曉于中央,反而有可能因皇帝軫恤而免于處罰,徐乾學案和賈府案即是例證。
六、清前期“違禁取利”條的實踐邏輯透視
(一)“愛養民生”與超越細故——司法實踐的必要性
司法實踐必要性背后是借貸行為存在的必然性。從古至今,借貸、典當都是維持社會運作的重要經濟手段,歷代律典均不禁止放貸,只是不允許征收重利,即“放債勿貪重利”。乾隆十年(1745),御史胡蛟齡在《推廣辟荒疏》中談到官府借錢于陜省貧民的做法有成效,希望可以沿用到其他地方:
竊查陜省之榆林、延安二府各屬近邊無業貧民,均賴出口種地,以資生計,而苦于牛具籽糧,無力措辦,不得不向富民借貸。富民放債起利,貪得無厭,窮民被其盤剝,終年力作,所獲無幾。乾隆四年(1739),經前任督臣奏明,每年酌動官銀,借給窮民,令于秋收照時價還糧。乾隆八九年(1743、1744),又經前任撫臣先后奏請,動項分發借領,照例于秋成還糧交官,共發銀六萬余兩,共收糧約十余萬石,造報戶部在案。此陜省借糧收糧已試之成效也。
貧民因富民放債起利、終年盤剝而愈窮,國家施以援手之辦法卻仍舊是“借貸”。官府將官銀借給窮民,讓他們在秋收時照時價還糧,而不進行重利盤剝。如此一來,百姓有本錢得以耕作,官府有新糧得以收儲,淋漓盡致地展現了借貸雙方的相濟之義,也足以表明借貸的價值所在。
但民間借貸行為眾多,難免有不義之舉,重利放貸導致民生凋敝,不得不制定并運行相關規則。正如張恂如在呈狀中寫道:“以微利之虛名,蹈莫大之實禍,寧不情極心慘耶!”清代前期,官方也嘗試過其他治理民生凋敝的方法,如康熙三十五年(1696)稽察錢局刑科給事中劉蔭樞在《請嚴利債之禁疏》中所奏,“竊見我皇上勸課臣工,必以清廉愛民為第一事……非世祿素封之家,常俸不足供其用。則取債于人,六七當十,六月轉票,遲至三四年間,千金之本,算至二三十倍,既乏神輸鬼運之能,又無點石為金之術,何從而清償哉……伏祈敕下該部酌議變通,嚴立科條,一切負債,俱照實在銀數三分計息,敢有折數轉票,橫肆勒索者,作何懲治,法在必行。則索者知所止,而償者易為力,潛移而默轉之,庶從前積弊,
可以漸杜矣。”[1]前文已述康熙年間官員趙士麟自填旗債之舉,此外,清政府亦嘗試自首免償的方式:
雍正十三年(1735)都統李禧請旗民一體嚴禁,借債人自首免罪,并免償放債人治罪,仍追利入官。民間爭首告冀免。至是,照疏言:“八旗佐領等官盤剝該管兵丁,放印子錢者,仍遵例擬追外,如止重利放債,悉依違禁取利本律治罪[2]。
但“追利入官”“民間爭首告冀免”侵害了當事人權益,該嘗試以失敗告終:
乾隆七年(1742)疏駁都統李僖所奏,重利放債,借債人自首免償例,已經律例館刪除,不準引用[3]。
清代前期君主愛養民生,正如康熙二十八年十月,康熙諭直撫于成龍:“直隸地方,朕屢豁免錢糧,百姓竟無起色。今年荒旱比往年更甚,朕在深宮,俯念民生困苦,衣食艱難,宵旰焦勞,時欲流涕。”在愛養民生的觀念下,為了治理因重利盤剝而帶來的民生凋敝,君主自然重視“違禁取利”相關問題。順治元年(1644)冬頒詔大赦天下,其內容有“勢家土豪,重利放債,致民傾家蕩產,深可痛恨,今后有司勿許追比。”[4]順治五年十一月有令,強調“勢豪舉放私債,重利剝民”要按律嚴懲[5]。至康熙四十八年(1709)八月,巡撫趙申喬上疏永州鎮官員唐之夔及李如松違禁取利之事,得旨:“該部嚴察議奏。”[5]到了乾隆九年四月,面對安徽巡撫范璨奏以民間違禁取利事項,乾隆旨意為:“其應查禁者,不謂汝能辦此,勉力以實為之”[6]。
這一時期,官方在“愛養民生”的觀念下,為改善民生困頓而超越細故,治理借貸問題,最終求諸于“違禁取利”法律規范,很好地印證了司法介入民間借貸的必要性。前文的諾木圖、戴麟瑞等均按律懲治,受到了較為嚴格的處理,均是清代前期“違禁取利”條司法實踐的例證。
(二)“政貴寬平”與政治需要——司法實踐的靈活性
在“愛養民生”的觀念下,“違禁取利”條的運行有其必要性,而基于清代前期實際政治需要而奉行的“寬平”理念,使得司法實踐又具有一定的靈活性。
這一時期,君主采取治下寬平的總政策,正如康熙二十六年四月,康熙在授田雯江蘇巡撫時所諭之內容:“向聞江蘇富饒,朕親歷其地,見百姓頗多貧困,爾當以愛養民生為務。至地方豪強為害于民者,不可不懲,然政貴寬平,不必一一搜訪滋
事。”[7]再如康熙五十三年(1714)十二月,皇帝向浙江巡撫徐元夢道:“爾遵朕此旨,切切在念,惟以寬恕為本”,又謂云南巡撫施世綸曰:“爾等務宜每事寬恕,以體恤下屬為念。”明珠貪擅、徐乾學與高士奇比昵,康熙皆優容待之,并告訴近臣:“諸臣為秀才,皆徒步布素,一朝得位,便高軒駟馬,八騶擁護,皆何所來,可細究乎?”[8]甲子鄉試時,徐乾學之子犯事,將送法司嚴訓,康熙對閣臣說:“從寬如何?”[9]其寬平治下之心盡顯。
清朝皇帝自順治而下大權在握,成為司法運行的最后環節[10],因此,“寬平”的政策也最終體現到司法上。“違禁取利”規則的運行因政治需要而不得不具備一定的靈活性,這表現為具體案件中的特殊司法實踐傾向,正如徐乾學案和賈府案所呈現的。君主因“愛養民生”而超越細故,對民間借貸俯身治理,反之,君主也會因為更重要的政治利益而將其重新歸入“細故”,“政貴寬平”背后暗含了皇帝基于政治需要而對司法實踐的潛在影響。透視其中的實踐邏輯,不僅能夠深入認識規則運行的靈活性,也能為豪族違禁取利案件中司法實踐傾向的特殊性提供解答。
就賈府案而言,賈府受到查抄卻能免受“違禁取利”條的懲處,既是由于祖先有護國之功,皇帝感念其功德,后人賈政勤慎居官,皇帝對其憫恤體諒,又有賈元春溘逝未久,皇帝念在貴妃不忍加罪。正如小說第一百零七回,有人在榮國府街上閑話:“聽見說,里頭有位娘娘是他家的姑娘,雖是死了,到底有根基的。況且我常見他們來往的都是王公侯伯,那里沒有照應?就是現在的府尹,前任的兵部,是他們的一家兒。難道有這些人還護庇不來么?”再觀作者曹雪芹的家族,確實俱有賈府之情狀。據清人記載,“寅字子清,號荔軒,奉天旗人,有詩才,頗擅風雅。母為圣祖保母。二女皆為王妃。”[1]康熙曾六次下江南,江寧織造曹家就接駕了四次,《紅樓夢》亦寫江南甄家四次接駕,足見其承寵的盛況。
而就徐乾學案而言,皇帝對徐乾學始終秉持“從寬免其審明”之態,這樣的態度與統治利益密不可分。總體而言,康熙無視對于徐乾學“違禁取利”等罪行的系列控訴,對其寬平以待,可能主要基于以下考慮:
其一,清代前期為鞏固基業,奉行拉攏明朝漢族知識分子的政策。徐乾學之舅為明末大儒顧炎武,與眾多明朝遺民相聯系,清政府以科舉延攬徐乾學之輩,自然優容以待。當徐乾學將一些官員的聲勢奸利之狀告知康熙,康熙疑問為何沒有其他人反映這些事,答曰不敢,康熙反問:“滿洲不敢,漢官何懼?……有予做主,何懼?”[2]足見此時朝廷對于漢官的重視和保護。其二,徐氏一門三貴,家族勢力龐大,社會根基深厚。徐乾學與其弟徐秉義、徐元文先后中舉,此后均擔任朝中要員,時人皆知昆山徐氏家族之顯赫。其三,徐乾學門客眾多,具有廣泛的政治影響。正所謂“以文章被眷顧,領纂修數局,所邀與商略皆天下名士”[3],《清稗類鈔》亦載:“徐乾學好延攬海內知名士”[4]。徐乾學主持考試時,起用韓菼等人,其后皆為當朝重臣,以至于“凡有文字,非經徐健菴改定,便不稱旨,滿、漢俱歸其門。”[5]其四,徐乾學具有突出的個人才能,簡在帝心。在他任左都御史時,告訴諸御史“惟當知有國,不知有身,愿諸公斷苞苴之路,絕欺蔽之私,整肅臺綱,宣誓天下”,切實為皇帝考慮,囑咐官員進言應當凝練:“人臣進言,當識輕重,若毛舉細過,以求稱塞,非所望也”[6]。當徐乾學受許三禮彈劾即家編輯后,皇帝贊譽他“卿學博才優”,囑咐其詳核《一統志》,殫心參訂,考據確實。其五,徐乾學承擔了修史的重要政治活動。古代官方修史活動與政治利益息息相關,往往直接被納入權力話語體系[7]。而徐乾學先后總領《大清一統志》《大清會典》及《明史》的纂修,康熙對其給予厚望,在他上疏乞歸時,叮囑他書籍隨身編輯,并賜御書“光焰萬丈”匾額[8]。直至乾學命卒前,康熙仍喚他回京修書。其六,基于平衡兩黨之爭的需要。徐乾學先攀附于明珠一黨,后聲勢日焰,遂自結一派,與其相抗。“明珠竟罷相,眾皆謂乾學主之”。兩黨之爭亦是滿、漢官員之爭,前文所述兩江總督傅拉塔即為明珠黨人,在傅拉塔歿后,有人將徐乾學欣喜之狀上奏于皇帝,康熙深知其事,但未置一詞[1]。
若豪族喪失政治價值,君主便可能不再施以“寬平”之策,此時規則復而起效,這亦是其靈活性的體現。以徐乾學為例,在其為官數年間,康熙并非始終內心欣然待之。傅拉塔參徐乾學兄弟之后,“王儼齊進密折,言徐氏害他。上又發與九卿看,曰:‘我看江南亂鬧,不過徐、王兩家。不如兩家都教他住關東地方去,庶幾清白。”[2]康熙二十八年,許有三復參徐,皇上謂:“漢人傾險,可惡已極。”[3]這些態度埋下了徐氏一族日后式微的種子。到雍正初,有人告發徐乾學幼子徐駿詩有“明月有情遠顧我,清風無意不留人”之句[4],最終徐家“以翰林累文字獄,處斬,家道遂微,移家安徽”[5]。
七、余論
借貸形式出現之初,是人們用來緩解手頭之急,以達相濟之義。歷朝歷代的借貸利率、借貸方式等并無定制,“高利貸”一詞的具體內涵不盡相同,但一般來說,各種借貸形態中具有謀利性質的部分即屬于高利貸資本,而中國古代長期存在著高利借貸的問題。在唐宋時期,高利貸行業已發展得較為完備和發達,相關規制體系也漸趨成型。發展至明清,隨著生產方式的變革和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社會財富不斷向高利貸資本轉化[6],自官府到民間、從城市到鄉村,社會對于借、貸行為的需求日益膨脹,甚至不乏皇室、官員投身其中。在清代前期,已呈現出借貸形式復雜多樣,參與主體眾多的局面,參與者之間不僅有貧富、身份之別,也可能具有民族之分。同時,其中還有同鄉會館、合會等信用團體以及票號、錢莊等金融機構的廣泛參與[7]。總體而言,這一時期的社會經濟生活對于借貸行業十分依賴,而相關法律規制與司法實踐狀況也呈現出相應的時代特征。
比較清代前期與唐宋規范內容的不同,其在立法上總體沿襲了前代反高利貸的核心思想,同時更加細致化、嚴格化和去暴力化。一是就違契不償行為的處罰而言,清代前期的管理更嚴。唐宋時期區分了非出息借貸和有息借貸(即“出舉”),據唐《雜令》,出舉任依私契官不為理,而對于官為理的非出息之債,負債違契不償的最低刑罰是笞二十;但《大清律例》則規定,違背三分利率標準和一本一利利息總量的,“違者,笞四十……”,嚴格于前者。二是就放貸主體的限制性規定而言,清前期的規范更為細致。唐宋時期主要是對監臨官員借貸進行了限制;而在清代前期,不僅對監臨官吏從事借貸行為進行限制,同時也對豪勢之人、聽選官吏、監生、旗人等多種身份的人參與借貸進行了限制。三是就違法放貸的救濟手段而言,清代前期法律所允許的救濟手段摒棄了一些前代的非人性化內容,比如不再有役身折酬、以人質債等內容,而是明文規定不許豪勢之人私自強奪孳畜產業,并不許準折人妻妾、子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