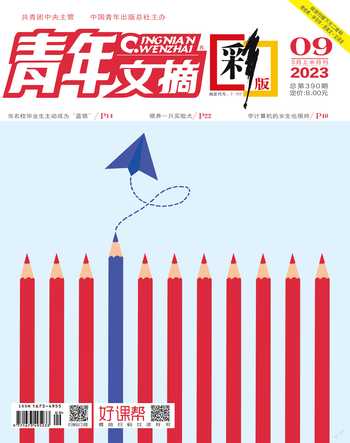擰動青春的發(fā)條鳥
歐陽晨煜

高中時(shí),我讀了村上春樹的一本小說——《奇鳥行狀錄》,小說描寫了一種名叫“擰發(fā)條鳥”的鳥類,據(jù)說是因?yàn)槠淠馨l(fā)出不規(guī)則的“吱吱”叫聲而得名。在整本小說里,“擰發(fā)條鳥”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它“擰”動了每一個(gè)故事里關(guān)鍵的環(huán)節(jié),“擰”動著每一個(gè)即將發(fā)生變化的人。主人公岡田亨因?yàn)榕既宦牭搅诉@種鳥鳴聲,本來無趣枯燥的生活有了新的轉(zhuǎn)機(jī),隨著新的朋友和事件的不斷闖入,陳舊的日子被打破,一切都開始發(fā)生變化。
看完這個(gè)小說后,我不禁想:我的身上究竟有沒有如同故事里的這根發(fā)條?如果有,我該如何擰動它?當(dāng)時(shí)的我17歲,過著平靜又忙碌的生活,拿著普普通通的成績單,游走在普普通通的高中課堂,從未引人注意,也沒有出彩之處。唯獨(dú)有一種潛藏的倔強(qiáng),仿佛在暗暗地啟示著我什么。
我向當(dāng)時(shí)最好的朋友屆訴說了這種情緒,但她對這個(gè)故事不以為然,笑了笑說:“我們每個(gè)人身上確實(shí)都有根發(fā)條啊,爸媽每天幫你擰緊,提醒你好好學(xué)習(xí);老師每天幫你擰緊,提醒你不要放松。我倒是希望哪天卸掉這根發(fā)條,才好做自己啊。”
我沒說話,但我知道,她所說的這種外部的發(fā)條和我所說的自身的發(fā)條不是同一個(gè)。我希望擰發(fā)條鳥可以鉆進(jìn)我的身體里,擰動我的發(fā)條,讓我普通的生活有所起色。
之后,我一直獨(dú)自保守著這個(gè)“擰發(fā)條鳥”的秘密,從未對別人提起,但是心里一直暗暗期待著能聽到自己發(fā)條擰動的聲音。在故事里,一旦發(fā)條被擰動,情節(jié)就會發(fā)生變化,人物的命運(yùn)也會隨之改變,那么我將不再是人群里的普通女孩,我那些連自己都不知道的閃光部分也會隨之被拖出。
為了迎接這樣的變化,我開始更加努力地生活和學(xué)習(xí),更加仔細(xì)地觀察自己,以便引出自己的獨(dú)特之處。我改變了平時(shí)隨意的態(tài)度,認(rèn)認(rèn)真真地上之前讓我頭痛的數(shù)學(xué)課,記那些冗長的歷史筆記,拼命汲取知識的養(yǎng)分。
屆發(fā)現(xiàn)了我的變化,驚訝地問:“你怎么忽然變得這么認(rèn)真了,莫非是那只奇怪的鳥找到你了?”
我沒有回答,抬頭看了看校園里最高的那棵梧桐樹,上面棲息著許多鳥:藍(lán)羽毛的華貴的鳥,嘰嘰喳喳的黑尾喜鵲,花斑點(diǎn)的鴿子……它們都不是“擰發(fā)條鳥”,在我的想象中,那是一只沉靜又堅(jiān)定的鳥,可以幫助每一個(gè)普通的孩子擰動他們最為珍貴和獨(dú)特的部分。
擰發(fā)條鳥此時(shí)一定安靜地站在樹梢上,在藍(lán)藍(lán)的天幕下,凝視著每一個(gè)在青春期里或自卑或不甘于平凡的孩子,然后鉆進(jìn)他們的身體里,仔細(xì)查看那些隱匿在世俗標(biāo)準(zhǔn)下的不為人知的特質(zhì),輕輕地?cái)Q動發(fā)條,最后悄悄地飛走。
我期待著降臨在我身上的流光溢彩的變化,為了迎接那只遙遠(yuǎn)的擰發(fā)條鳥,我覺得應(yīng)該做些準(zhǔn)備,好讓它盡快發(fā)現(xiàn)我。
于是,除了繼續(xù)認(rèn)認(rèn)真真地做每一件小事,我開始進(jìn)行大量的閱讀,甚至動筆寫起東西來。以前,我只是按照語文老師的要求,僵硬地寫著那些黑色的字塊。在我的印象中,我寫的作文就好像鋪滿小石子的路,人總有繞道而行的沖動。但是現(xiàn)在,我打算拋開那些惱人的石子,在格子里重新填滿屬于我的文字。
就這樣,我在圖書館的角落里,寫出了第一篇頗為自我的文章,它幼稚大膽,卻幾乎可以獨(dú)立而行。于是,瞞著所有人,我把它投給了一家雜志。
在等待回應(yīng)的日子里,我開始“改造”試卷上的作文,盡情地把自己的語言和想法帶進(jìn)那些禁錮的格子里,肆意地把腦海里的小旗幟插在那些田字格上。很快,我被老師請進(jìn)了辦公室。
我緊張地攥著拳頭,低著頭站在語文老師面前。她指了指我交上去的作文,說:“這是你的作文吧?”
“是我寫的。”我磕磕巴巴地回答。
“你的風(fēng)格好像變化不小,能寫出這么鋒利的文字了。”
“鋒利?”在此以前,我只聽過抒情、生動的文字,從未聽過用“鋒利”來形容文字的,我越發(fā)緊張起來。
“‘所謂書,必須是砍向我們內(nèi)心冰封大海的斧頭。’這是著名作家弗朗茨·卡夫卡在1940年寫給友人的信中的一句話。他是我很喜歡的一位作家,我很認(rèn)同他的觀點(diǎn),好的文字應(yīng)該觸動和挖掘內(nèi)心。你的文字目前應(yīng)該像是往微波蕩漾的小湖里投了一顆石子,老師很期待你以后能寫出解凍冰封大海的文字。”
她拍了拍我的肩膀,指尖仿佛傳遞著一種柔化的魔法,我卻還沉浸在剛才的話里。
隨后我呆呆地走出了辦公室,遇到了在門口嬉皮笑臉的屆,她說:“你最近真的怪怪的,居然被請去辦公室了,這可是頭一次啊,體驗(yàn)不錯(cuò)吧!”
我沒好氣地瞪了她一眼,但是她說得沒錯(cuò),原來的我就是放在盆栽館里最不起眼的橡皮樹,一切都那么普通,甚至普通到老師都會忘了澆水。而今天,這盆柔弱的橡皮樹被單獨(dú)拎出來修枝剪葉,并被贊美了一番,確實(shí)是罕見的事。
“鋒利的鼓勵(lì)”確實(shí)給了我向前的勇氣,我覺得自己身體里的某個(gè)地方開始漸漸脫落,而這種脫落,是為了露出閃閃發(fā)光的內(nèi)部,我越來越接近它了。恍惚間,我好像聽到了擰發(fā)條鳥的叫聲,細(xì)碎的吱吱的聲音好像在不遠(yuǎn)處,但猛然抬起頭,透過稀疏的葉影,它的身姿還是無處可尋。
這一天,我和往常一樣在課間“啃”著面包般厚的卡夫卡全集,正當(dāng)我奮力咀嚼時(shí),屆跳躍著沖進(jìn)了教室,把一個(gè)牛皮紙信封鄭重其事地砸在我的桌上。
“快看看這是什么?”她興奮得小辮都在飛舞。
“什么啊?”我仔細(xì)看了看牛皮紙上印著的幾個(gè)杜鵑一樣的紅字,“啊,是雜志社寄來的!”
屆先我一步拆開了信封,里面赫然放著兩本嶄新的雜志,她像整理傘骨一樣把書頁翻得極快,然后翻到中間的一篇文章,用力搖動我的雙肩:“快看,這是你的文章。”
“我的文章?”我低下頭捧著雜志,好像捧著一只綿白的貓咪一樣小心,沒錯(cuò),我的名字出現(xiàn)在了作者那欄。我驚訝得說不出話,鉛字好像云霧一樣模糊了屆的眼睛,她滴下兩滴淚,說:“你真的沒騙人,那只鳥真的來找你了,它擰動你的發(fā)條了!”
一瞬間,我感到自己的體內(nèi)真的有什么在吱吱作響,頻率雖然很慢,但真的在轉(zhuǎn)動。一些陳舊的事物慢慢地從我身上脫落,是擰發(fā)條鳥在我的青春里擰動了全新的開關(guān),推動了一根名為寫作的發(fā)條。
從那天開始,我再也沒有讓這根發(fā)條停止過,我?guī)е鼇淼疆惖兀诖髮W(xué)期間一次一次地?cái)Q動著它。這根來自青春的發(fā)條,趕走了曾經(jīng)那個(gè)普通女孩的迷茫和無措,為她擰開了一條新的路。我不斷地在雜志上發(fā)表自己的文章,并拿到了很多文學(xué)賽事的獎項(xiàng),然后還被簽約寫書。這一切,都是青春的發(fā)條在不斷轉(zhuǎn)圈的結(jié)果。
大學(xué)的暑假,我和屆見了一面,她問我:“現(xiàn)在長大了,你還真的相信擰發(fā)條鳥的存在嗎?”
我想:擰發(fā)條鳥或許早已飛走,當(dāng)初迎來它的是我對自己的那些改變和努力,而現(xiàn)在繼續(xù)擰動發(fā)條的也是我自己。
“或許它還在,在世界的某個(gè)角落,棲息在一棵樹上,擰動著無數(shù)少男少女的青春。”我淡淡地回答道。
從容//摘自《少男少女》(校園版)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