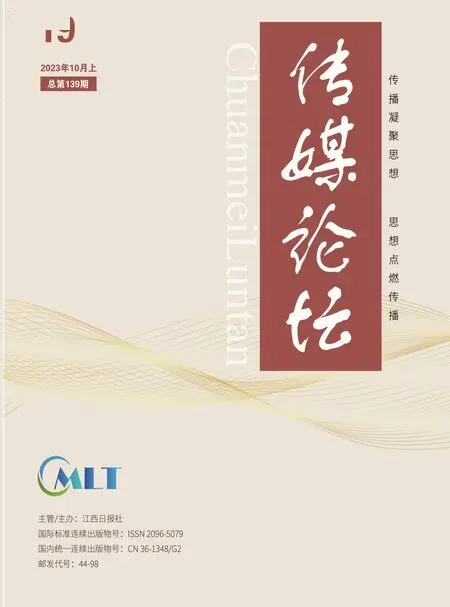基于文化結構理論的紅色文化IP創新傳播研究
——以“亮劍”為例
馬金鵬 石姝莉
隨著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發生變化,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已經成為當代經濟社會發展普遍重視的課題。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要“傳承紅色基因,賡續紅色血脈”。然而,目前“紅色血脈”的傳承模式較為單一,僅靠舊有的傳承方式在數字媒體技術日益蓬勃發展的當下顯得難以為繼,且存在浮于表面、流于形式等隱憂。因此,紅色文化亟須創新傳播路徑和形式,以期更好地對中華優秀文化基因和中國人民頑強拼搏的精神進行創新性傳播。
一、研究起點
文化的傳播絕非凌空蹈虛,它需要載體來展示出其獨特的魅力。而對紅色文化的研究,目前一直存在兩個難點:一是如何將紅色文化之概念的邊界進行界定,以能夠與相似的概念如“革命文化”“政治文化”等區分開來;二是基于紅色文化與其他類型文化之間的差異,如何采取一種行之有效的觀察和操作化標準,以更好地對其進行審視與分析。基于此,本研究在梳理過往文獻的基礎上嘗試對紅色文化做出描述性定義,并以文化結構理論作為切入點為當下的紅色文化創新性傳播提供可行的分析角度。
(一)紅色文化
紅色文化在當代是一個離不開現實生活與政治生活的概念,但究竟紅色文化是什么,一直以來并沒有太過明確地定義和解釋。馬克思在《資本論》英文版本的序言中指出:“一門科學提出的每一種新見解都包含這門科學的術語的革命。”[1]紅色文化的概念在2000年以后才在學術界被提出。但事實上,此概念也如革命一般,其意義的漂流早已散見于各個領域。
從政治學的角度來看,在俄國十月革命后,蘇維埃政權產生與發展,直到1922年成立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將紅色的元素運用到了革命與社會建設的方方面面,使其成為能夠代表蘇聯共產黨的顏色。而在蘇聯政治文化影響下,紅色也順理成章地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革命的主色調。從影像敘事學的角度來看,紅色則代表著愛情、警告與革命。不論是從不同的文化傳統上,還是從每一代人的情感認知上,人們都會對顏色賦予特定的內涵以及隱喻的象征。紅色文化的產生與發展,離不開一定的語境。因此,對紅色文化的界定要回歸中國本土,才能更好地分析出其文化內涵的源與流。
劉潤為(2013)認為,誕生在中國語境中的紅色文化,其來源主要有文化和社會兩個層面,而其中最主要的來源,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的偉大實踐。”但從這個概念出發,就極易落入僅僅觀照歷史的窠臼之中。“一談到中國紅色文化,便僅僅與上海、嘉興、南昌、井岡山、延安、西柏坡相聯系”[2],這些內容雖然也是紅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但絕非全部內容。
現代社會是高速發展著的社會,產生于血與火中的紅色文化似乎被流動著的經濟和快節奏的生活所遮蔽,只存在于路邊的宣傳欄中,不得不說這是一種極大的遺憾。因此,本研究將紅色文化定義為基于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在反帝反封建、追求獨立過程中真實歷史所形成的、既追溯過往的歷史且涵蓋當下社會的發展、還要對未來有所觀照的文化。它不局限于某種單一的物質形態,因而能夠具有強大的生機和活力,能夠鼓舞人心。創新紅色文化傳播的形式和內容,有利于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的建構和強化,形成全社會范圍內向上向善的道德氛圍,對社會成員的精神風貌和整體素質都有所裨益。
(二)文化結構理論
1871年,愛德華·泰勒在其著作《原始文化》中,首次對文化給出了整體性的概念,他認為,“所謂文化乃是包括知識、信仰、道德、法律、習慣以及其他人類作為社會成員而獲得的種種能力習性在內的一種復合整體”[3]。泰勒的定義從宏觀的視角進行切入,雖然看似泛泛,實則將文化看作是一個“復合的整體”。美國人類學家克魯克洪在《文化與個人》中認為:“文化是歷史所創造的生存式樣的系統,既包含顯形式樣又包含隱形式樣,它具有整個群體共享的傾向,或在一定時期中為群體的特定部分所共享。”[4]作為被歐美理論界廣泛認同的定義,其內涵相對較為完整。而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則予以反駁,強調“文化的發展與社會的發展息息相關,文化若是無所不包,就什么也說明不了”[5]。亨廷頓的闡述不無道理,研究文化不能將其懸置,而是需要尋找到合適的立足點。因此,對文化的結構進行梳理,才能更好地去分析其內涵與外延。
美國分類學家萊斯利·懷特在《文化的科學》中認為,文化系統能夠分為三個層次,最上層是哲學的層次,中間層則是社會學的層次,最底層是技術的層次[6]。這種分類的方式在既不破壞文化有機的整體性的同時,又對文化的結構進行了比較詳細的說明。
而最早對文化結構進行了闡釋的中國學者龐樸認為,“文化結構包含三個層面:外層是物的部分,即馬克思所說的‘第二自然’,或對象化了的勞動;中層是心物結合的部分,包括關于自然和社會的理論、社會組織制度等;核心層是心的部分,即文化心理狀態,包括價值觀念、思維方式、審美趣味、道德情操、宗教情緒、民族性格等。”[7]根據龐樸的定義來看,文化的結構存在物質形態、理論制度和心理感受三個層面。學者劉桂榮認為其中“文化的物質層面是最活躍的因素,它變動不居,交流方便;而理論、制度層面,是最權威的因素,它規定著文化的整體性質;心理層次,則最保守,它是文化成為類型的靈魂。”[8]
許蘇民在《文化哲學》一書中對西方文化哲學研究的源與流進行了梳理,以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為基礎,提出了文化結構理論。他將文化劃分為文化心理與社會意識形態兩個部分,并分析指出了文化心理結構分為表層、中層與深層三個層次,這三個層次互相滲透在物質、制度與精神文化之中。[9]
無論是國外學者還是國內學者,都對文化的結構極為重視。文化結構是一種文化的架構方式,它并非直接觀察到的,而是對有機整體性的文化內在關系的抽象梳理。當我們說到“中國文化”的時候并不是指孤立存在著的文化元素,例如燈籠、唐裝、瓷器等等,而是指由這些文化元素所構成的特有的行為模式以及其象征性的符號系統。同理,當我們談到“紅色文化”時,也并非僅指所謂的革命文化,而應當是從文化結構理論出發,具體地分析組成該文化的各部分,進而研究其在全社會范圍內發揮了怎樣的整體影響。
綜上,由于任何的文化都無法脫離載體而獨立存在,本研究從文化結構理論的視角出發,從物質、制度和心理三個層面切入,對近年來紅色文化傳播的現狀進行梳理,并以“亮劍”這個經典紅色文化IP為例來展開,進而提出紅色文化創新傳播方式。
二、紅色文化傳播現狀
近年來,國家高度重視文化事業的發展及文化形式的呈現。在這種大環境下,各級政府都意識到了紅色文化在國家建設及省市文化建設、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從主體、內容和渠道三個層面來分析目前我國紅色文化的傳播現狀。
(一)傳播主體
目前,紅色文化的傳播主體以自上而下的大方向為主,總體形成國家引領、政府主導、公眾參與的三級模式。其中,國家的引領是重中之重。國家對紅色文化的宣傳與引導,反映了從官方的角度對紅色文化的重視程度。中國從抵御外敵、獨立自強的過程中逐漸成長,形成了重視奮斗歷程、汲取歷史經驗和教訓的民族特性,也形成了在國家層面重視紅色文化的基因。各級地方政府則結合地方實際進行紅色文化傳播,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以求創新,最大限度地吸引公眾來關注紅色文化并受到紅色文化本身的精神風貌與活力的熏陶,在全社會范圍內形成向善的文化氛圍。比如紅色文化資源較為豐富的湖南省,打造了以“橘子洲”為特色的紅色打卡地,吸引游客打卡的同時也能夠帶來經濟效益;山西省則強調“太行精神”的現代化闡釋,以省內多地的文化資源為依托,共同塑造了山西這一地域的獨有紅色文化。
總體而言,目前紅色文化的傳播主體比較集中。在以往,這樣的模式效果是比較出色的,尤其是在經濟欠發達地區,這樣的方式能夠基本滿足人民群眾對于參與主流文化、了解紅色精神的需求。然而,在技術變革迭代極為迅速的當下,傳播主體的過于單一在滿足人民群眾了解并參與到紅色文化傳播的意愿方面的表現并不樂觀。
(二)傳播內容
從傳播內容來看,目前,我國對待紅色文化的傳播思路主要是以表現過去的、既定的歷史為主。在中國人民的長期奮斗歷史進程當中,在各個領域涌現了許許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無論是陷入困頓時期的堅韌不撓,還是終于撥云見日的篳路藍縷,都能夠無數次地在全社會范圍內達到振奮人心的效果。然而,歷史是線性的,目前對于歷史類紅色文化的傳播,多以單點的形式出現,少有全面反映歷史的傳播。
誠然,全面對歷史進行反映是十分困難的。這里所追求的“全面”,強調的是在典型的紅色人物或事跡的傳播過程中不能過于片面,應將特定的歷史人物放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去審視。只有將受眾帶到所傳播的語境當中,才能讓人深深地感知到該人物所作出的決策有多么不易、其反映的精神是多么偉大。當下,各個階段紅色文化時期界定并不清楚,使得受眾對于紅色文化的整體觀感較為模糊。這也是目前亟待解決的問題。
(三)傳播渠道
得益于近年來在國家層面上提出的媒體融合發展戰略,紅色文化的傳播渠道方面目前較為多元。除了以報紙、廣播和電視為主的傳統媒體,傳播渠道也在不斷地開拓新媒體領域。目前,在“兩微一抖”都存在著專司紅色文化傳播的新媒體矩陣。更為難能可貴的是,在紅色文化對新媒體領域開疆拓土的同時,也沒有忘卻對相對不發達地區進行文化幫扶。紅色文化不僅僅是作為抽象精神而存在,還可以進行開發。如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紅色旅游線路的開發都能夠為人民群眾帶來實實在在的經濟利益。以四川省為例,該省的紅色文化資源囊括了紅軍長征紀念碑、磨西會議遺址等紅色地標,以及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巧渡金沙江等紅色事跡。四川省對這些遺址和事跡進行的紅色文化資源開發,在脫貧攻堅的過程中發揮了重大作用。
但是,渠道的更新似乎放緩了內容創新的速度,新渠道傳播依然是舊內容,存在著內容與渠道適配度不足的問題。譬如在短視頻平臺中,由于其媒介形式的特性,需要時長較短的視頻內容,而目前有些傳播紅色文化的賬號在這一方面的做法仍舊比較粗糙,僅僅將已有的長視頻截取為短視頻便進行傳播,難免會出現“水土不服”的情況,自然就收效甚微。
三、“亮劍”IP的創新傳播
“亮劍”一般是指作家楊湛(筆名都梁)于1999年創作的44萬余字的長篇小說。小說塑造了李云龍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直至新中國成立時期的英勇形象。該小說于2005年改編為電視連續劇,并于同年獲得中央電視臺電視劇類收視冠軍。時至今日,電視劇《亮劍》仍是各大地方衛視重播的經典劇集。“亮劍”IP無疑是近年來極為優秀的原創紅色文化IP,其創新的傳播方式值得參考。傳播創新不僅僅是舊傳播要素的重新排列組合,更是在審視傳播活動的全局后,分層次、分領域地對文化傳播行為提出新做法、新主張的過程。文化結構理論恰能夠為分析創新傳播活動提供可操作的視角和可復制的路徑,為后來者進行創新傳播實踐提供了可能。
(一)視角轉換:物質主體的革新
根據學者龐樸的定義,文化產品的最外層形態是物質文化形態。以這一形態反觀“亮劍”這一IP,其物質形態的集群性十分優秀。除原作者的長篇小說以外,為迎合近年來耳朵經濟的發展,“亮劍”還陸續在各個平臺推出了有聲書讀物、廣播劇等音頻文本。此外,隨著游戲越來越成為年輕人所青睞的文化娛樂形式,“亮劍”IP還被授權制作為一款游戲出版發行。而作品續集的推出也成為“亮劍”這一IP拓展渠道與生命力的重要方式。這也為今后紅色文化IP的物質文化層面創新傳播提供了借鑒性極強的范例,即視角的轉換,不僅僅局限于傳統的物質形式,還要注重物質產品形態的革新。文化產品的物質性創新的主要方式就是創新文化產品的形式。同時,文化產品在物質層面的創新,也要與傳統有所勾連。“亮劍”廣播劇采用電視劇原班人馬,讓觀眾可以很快地沉浸到劇情中去,感受優秀紅色文化的浸潤。但是,“亮劍”IP在物質文化層面創新的過程中也存在一些問題。
例如續集拍攝的問題。2020年,以《亮劍》續集為噱頭的《亮劍之雷霆戰將》在湖南衛視播出,但是觀眾產生了許多質疑:八路軍戰士住豪華別墅,主角幾乎清一色都用發膠、發蠟,與真實歷史相去甚遠。最終該劇在一片質疑聲中下架,而且引發了《人民日報》在內的數家媒體的批評。此外,根據“亮劍”改編的同名手機游戲,同樣引發玩家的質疑,“不充錢就打不過鬼子”的游戲模式完全背離了“逢敵必亮劍”的精神。這也同樣警示后來希望改編為游戲的紅色文化IP應注意精神主旨上的銜接性。改編為游戲并非不可,比如2019年出版發行的諜戰主題角色扮演類冒險游戲《隱形守護者》就受到了玩家廣泛好評,究其原因還是在于文化產品物質層面的表現能否與其代表的精神內核相一致。
(二)元素切入:文化內容的豐富
就制度層面而言,“亮劍”的做法無疑十分出色。作為文藝作品中的內核,“亮劍”精神這一IP無疑完成了自己的突圍、破圈與再制度化。
在電視連續劇《亮劍》播出后的研討會上,時任沈陽軍區政治部宣傳部副部長的焦凡洪稱,“從軍區首長、離退休老干部到基層廣大官兵,大家看《亮劍》、談《亮劍》,弘揚‘亮劍精神’”[10]。如果說在軍隊中引起的反響屬于正常現象,那么許多商業企業也將“亮劍”精神作為企業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便足以看出其在文化建設及創新方面所付出的努力。文化作品一旦打造了堅挺的精神內核,創造了新的優秀文化,便能夠讓自身擁有極為強大的生命力,在各個領域中都能有所作為。
但是需要警惕的是,文化方面的創新需要自身文化IP較為豐富、底蘊較為厚重,否則的話就會畫虎不成反類犬。實際上,《亮劍》中主人公所反映出的,除中國人民艱苦斗爭精神以外,還有著武俠作品中俠客的味道。如果武俠精神能夠在紅色文化作品中得到創新傳播和元素的更迭融入,那么“亮劍”精神也能夠在新的適當的領域實現新的突破。這無疑為其他文化作品的內容制作提供了可供參考的路徑,也能夠在信息過度充斥與駁雜的當下,提供質量上有保障、精神上有創新的優秀作品。
(三)橫向鏈接:精神渠道的補足
根據龐樸的定義,文化的精神層面,屬于“心”的層面,而在這一層面,紅色文化的創新傳播實際上大有可為。
《亮劍》中的許多名場面、名臺詞被廣為傳唱,甚至已經到了“meme式傳播”的程度。“meme”一詞最早由英國生物學家Richard Dawkin在1976年出版的《自私的基因》一書中提出,他將meme定義為“一個可以用來描述模仿行為的文化傳播單位”[11],meme的傳播過程就是語言、觀念、信仰、行為方式的傳遞過程。而后,英國學者蘇珊·布萊克莫爾對meme作了進一步拓展,她認為meme是“儲存在大腦或其他對象之中的、可以通過模仿而被傳遞的任何事物”[12],在社會文化意義上具有高度的重復性。
這種高度的重復性在文化的創新與存續上有著重要的意義。長期以來,meme都是作為傳播亞文化的重要載體,而鮮有主流文化乃至紅色文化的身影。但是《亮劍》中一個小士兵的形象,從獲得戰利品的開心到戰利品被搶的傷心,前后的強烈對比使得這一組圖片被廣泛地運用于各類meme式的傳播中。這也是紅色文化進行橫向連接的重要方式,突破原有的意義,來賦予新的內涵,但這絕不是最終的目的。紅色文化與主流文化的鏈接是其天然的文化屬性,而在與其他的文化相橫向勾連時,要注意不能讓原有的意義消解,而是讓使用它的人對原有的語境感興趣,完成從“推”向“拉”的傳播變革。
精神層面的創新要多多依靠現有的受眾來完成,也即重視自身觀眾的自創、二創,這同樣是維持文化產品生命力的重要手段,也是破圈傳播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自發性的傳播過程,能夠在受眾心中完成重要的心理占位,形成強烈和長久的記憶,在此后的社會實踐中,能夠多次地被反復記憶與傳播。
四、結語
紅色文化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長期以來所形成的優秀文化,能夠與時代風貌相結合,爆發出強大的生命力和驅動力。紅色文化是沉淀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一種特定文化類型,具有獨特的重要價值。然而,新媒體時代,紅色文化面臨著缺乏吸引力、受眾認同感弱、傳播力度小、互動性弱等一系列難題。[13]紅色文化的創新傳播,要在繼承文化與精神內核的基礎上進行物質更新與迭代。此外,要注重擴大紅色文化的制度性涵蓋范圍,拓展紅色文化應用與解釋的新視角、新領域,讓紅色文化逐步走入人民群眾的生活中去。最后,應當鼓勵共創共享,共同發揚優秀紅色文化的精神基因,將其內化于心外化于行,真正將紅色血脈賡續到實處、發揚到心中。可以充分動員社會上一切的力量,并努力建立全方位、多途徑的紅色文化傳播模式,呼吁大家為實現紅色文化傳播研究和紅色文化的發展而努力[14]。